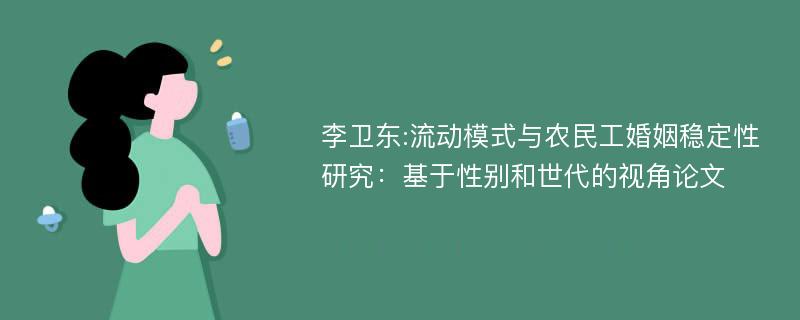
摘 要:基于广州2016年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本文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系统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分析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男性农民工,且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最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且这种影响存在性别和世代差异,其中流动模式形塑着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和离婚阻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具体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的共同影响,其中的脆弱性差异机制可以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效应和世代效应。
关键词:婚姻稳定性 农民工 人口流动 性别 世代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大量农村人口到城市务工。根据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达到2.47亿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民工。在人口迁移的过程中,中国也出现了婚姻稳定性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等现象(叶文振、林擎国,1998)。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中国的粗离婚率为0.30‰,2002年这一数据为0.90‰;之后,中国离婚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2015年,中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共有384.1万对,粗离婚率达到2.79‰,①数据来源:民政部公布的《2015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年均增长15.75%。已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是导致婚姻稳定性下降和离婚率上升的重要因素之一(杜凤莲,2010;高梦滔,2011)。一方面,人口流动降低了农民工的婚姻搜寻成本,增加了离婚风险(莫玮俏、史晋川,2015);另一方面,人口流动可能会降低农民工的婚姻收益,也增加了离婚风险 (马忠东、石智雷,2017;李卫东,2018)。
尽管已有研究发现,人口流动会导致农民工群体离婚率的上升,流动经历会增加农民工的离婚风险,但也存在不足。第一,已有研究主要采取“黑箱”的方式来解释流动经历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未从经验的角度分析其影响机制,导致不同研究对同一流动方式影响机制的解释逻辑不一致。第二,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析流动过程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流动过程中夫妻双方谁更可能产生离婚倾向并提出离婚,以及流动过程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人口流动给女性带来了更多的相对收益(李卫东等,2013),性别失衡提高了女性的婚姻议价能力(Li,etal.,2015),这有利于女性实现婚姻独立并终结不幸福的婚姻。同时,根据脆弱性假设,性别角色社会化使两性在应对外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方面存在差异(Kessler and McLeod,1984),对压力事件的体验也不同(Ickes and Layden,1978),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对人口流动影响的感受与体验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有必要从性别的视角探讨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第三,已有文献大多关注流动与不流动是否会导致婚姻稳定性差异,或者探讨流动经历对婚姻破裂的影响,将流动人口或农民工视为同质人群,忽略了婚姻稳定性在生命历程中的时间效应以及流动人口代际转换的问题。首先,再婚机会受个体年龄影响,年龄越小,再婚机会越多,反之,再婚机会就越少。其次,新生代农民工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无论是成长环境与经历(刘传江、徐建玲,2006),还是价值观、生活方式以及对工作、生活和发展的期望与需求,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都存在明显的差异。不同的成长经历会形塑不同的婚恋观和家庭观,因此,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世代差异。此外,既定世代人群的性别意识受其成长时期性别文化的影响,改革开放后性别文化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流动经历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也可能受到世代的影响。
4)Config flash:用于保存FPGA芯片的配置信息,SPI Flash用于保存密钥分量等信息;
第三,人力资本理论。西奥多·舒尔茨说:“我敢明确地说,人力资本对于增加工人的实际收入而言,至关重要不可或缺。”人力资本理论有四个部分:一是在所有资源里,人力资源位居第一;二是在发展经济的阶段中,物质资本没有人力资本的有效性大;三是人力资本以提高人的素养为核心,主要体现在对教育投资上;四是教育投资以市场供需关系作为基础。较物质投资而言,人力资本投资会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而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效率的最佳方式是教育投资。
针对以上不足,本研究引入性别和世代视角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存在怎样的态势、特点和差异?第二,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是否低于男性农民工?第三,流动模式是如何影响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的,以及这些影响机制是否存在性别差异?第四,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是否存在世代差异?本研究将采用主观层面的婚姻稳定性来测量离婚风险。法律上认可的离婚往往表现为婚姻不稳定的结果,而非婚姻不稳定本身(Booth and Edwards,1985)。婚姻不稳定是一种间接的想法或行动,可能导致离婚,但又不同于离婚,因为这种不稳定可能随年龄等因素的变化而发生变化(Booth,etal.,1986;叶文振、徐安琪,1999)。因此,研究个体层面的婚姻稳定性对把握离婚率的变动态势也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分析来自中国广州市的农民工婚姻与家庭调查数据,从世代、性别的视角理解和解释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以及内在的性别和世代效应。我们的研究发现将有助于加深对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全面了解与认识,也有助于理解人口流动背景下性别关系的变化及其对农民工生活机遇的影响。同时,由于农民工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石,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研究对促进个人、家庭、社区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视角
(一)婚姻稳定性的理论视角
为了回应社会转型和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带来的离婚率持续上升的问题,西方学术界沿着“婚姻交换理论”和“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展开研究,并形成了多种竞争性解释理论,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婚姻凝聚理论”。
利文格(Levinger,1965,1976)系统建构了“婚姻凝聚理论”框架,他认为,一桩婚姻的稳定与否受三个因素的共同影响,即婚姻收益、离婚阻力和配偶替代机会。婚姻收益表现为夫妻间积极关系的结果,如爱、支持、安全感等,而婚姻成本即婚姻中负面关系的结果,如语言和身体侵犯、配偶的不良行为习惯等(Previti and Amato,2003)。婚姻稳定首先表现为夫妻双方在心理上的相互吸引和依赖,这种心理上的吸引和依赖取决于夫妻间在婚姻中感知到的收益和成本之差(Thibaut and Kelley,1959)。帕森斯和贝克尔从婚姻收益的角度较早讨论了西方工业化后出现的婚姻收益下降与离婚率上升的问题,称之为“婚姻的角色分工假设”(Parsons,1955,1959;Becker,1981)。该理论讨论了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与传统家庭分工模式解组如何影响夫妻间的婚姻收益,并导致婚姻解体的问题。另一些研究提出了弹性假设,认为在后工业化时期,仅仅依靠丈夫赚钱养家可能会降低家庭的收益,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参与则会提高家庭总福利,进而提高婚姻收益、促进家庭融合(Oppenheimer,1997;Cooke and Gash,2010)。一些经验研究把婚姻收益操作化为个体报告的婚姻幸福或满意度,婚姻满意度对离婚想法和随后的婚姻解体具有负面影响 (Glenn,1991;Bradbury,etal.,2000;Previti and Amato,2003)。
尽管低婚姻收益会导致离婚想法的产生,但有研究发现,一些婚姻虽然已经不幸福,但依然比较稳定(Heaton and Albrecht,1991),这是因为婚姻中的当事人要解除婚姻关系还需要克服一系列困难(Previti and Amato,2003)。离婚阻力在个体心理层面表现为一种承诺或责任感(Lewin,1951),在结构层面表现为婚姻规范(Heaton and Albrecht,1991)、初级群体网络压力(Ackerman,1963)、对配偶的经济依赖(South and Spitze,1986)、子女的存在(Heaton and Albrecht,1991)等。利文格(Levinger,1976)认为,只有在婚姻出现问题或婚姻收益下降后,离婚阻力才会发挥作用来维持婚姻的稳定。从这个角度说,婚姻收益或婚姻满意度是影响离婚阻力发挥作用的内在约束条件,婚姻收益会调节离婚阻力因素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这也意味着,在婚姻收益低的情况下,离婚阻力因素的变化可能对婚姻稳定性产生重要影响。正如“经济独立假设理论”所说,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并不一定会导致婚姻满意度下降,破坏婚姻的稳定(Sayer,etal.,2000;South,2001),却可以让女性获得经济独立,结束不幸福的婚姻(Cherlin,1992)。同时,女性就业还可能逐渐改变其性别角色意识,进而弱化传统的性别角色意识对其婚姻的影响(Amato and Booth,1995)。这表明,外在环境的变化可能会影响离婚阻力因素的变化,并影响婚姻稳定。
配偶替代机会是影响婚姻稳定的另一个因素。利文格(Levinger,1965,1976)认为,每个已婚者都处于大量配偶替代的环境中(如朋友圈、同事圈等),这些潜在的替代机会可能与婚内关系存在竞争。如果当前婚姻的收益低,婚外存在较多替代机会且具有更高收益时,婚姻稳定性就会降低;如果当前婚姻收益低,但婚外没有其他替代机会时,个体也可能会维持当前婚姻(Previti and Amato,2003;Levinger,1965,1976)。与此同时,配偶替代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没有替代对象而回归单身状态(Previti and Amato,2003)。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个体所处的环境会影响配偶替代机会,但是否采取配偶替代的行为既受成本与收益机制的影响,也受离婚阻力因素的影响。当婚姻收益下降且离婚阻力较弱时,婚姻就可能走向解体。
假设1c:跨省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要比女性农民工明显,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
(二)有关移民婚姻稳定性的研究
1.流动经历与婚姻稳定性
假设2a: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其婚姻满意度而实现的。
在施工的进行中,首先需要考虑的就是制定一个详细的可行性施工方案,无论是大工程还是小工程,施工方案的制定都要做到详细与精准,一套科学合理的施工方案可以令后续准备工作的开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需要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一点,一份合理的更加科学的施工方案是施工开展的前提和基础,更是施工质量的保障。一套好的施工方案,不仅能够从根本上杜绝一些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工程的进度与质量,为施工的整个过程带来社会与经济效益。因而一个合理科学的施工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在施工方案制定的同时,也要在实践中按拟定的方案一步一步执行。
夫妻分居是移民常遭遇到的风险,分居可能会降低移民的婚姻收益,增加离婚风险。国外研究显示,受移民目的地国家法律的约束,许多移民无法实现家庭化迁移,从而呈现夫妻一方迁移而另一方留守的迁移结构,造成事实上的两地分居,给婚姻带来风险(Frank and Wildsmith,2005)。博伊尔(Boyle,2008)进一步指出,夫妻在地理上的分居还会导致婚姻紧张。因为单独迁移带来的两地分居会使留守配偶产生被遗弃感和焦虑感(Fridkis,1981;Friedman,1982),导致婚姻紧张,进而降低婚姻稳定性。
迁移还会弱化社会约束,降低离婚阻力,增加离婚风险。迁移对婚姻阻力的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迁移经历会弱化传统的社会规范对移民离婚行为的约束(Hirsch,2003;Zontini,2010)。研究发现,个体的离婚行为和倾向受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当个体长期生活在普遍接受离婚的社会环境之中时,也会变得容易接受离婚(Booth,etal.,1991;Frank and Wildsmith,2005)。移民往往会迁入现代化程度高、观念意识开放的地方,流入地的文化观念会影响移民的观念和意识,移民在继续社会化的机制下逐渐习得当地的观念和规范,其中也包含婚姻家庭观念。这个过程不仅逐渐弱化了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也会导致移民更容易接纳和包容离婚行为。对在美国的墨西哥裔移民的经验研究发现,在美国的流动经历和居留时间会显著增加移民的离婚风险(Hirsch,2003;Hill,2004;Frank and Wildsmith,2005),证实了这一规律。因此,迁移带来的夫妻文化规范观念的变化会影响夫妻之间婚姻矛盾的发生以及婚姻解体的风险(Grasmuck and Pessar,1991;Foner,1999;Milewshi and Kulu,2014)。另一方面,迁移还可能弱化社会网络对婚姻的监督力量,从而降低离婚阻力。有研究发现,在夫妻双方拥有共同的朋友圈时,离婚会存在更大的阻力(Boyle,etal.,2008),这主要是因为共同的朋友圈发挥了婚姻监督和调解的作用。迁移意味着远离原生家庭网络,进入新的环境,容易形成一些匿名化、非人格投入的社会互动,这些社会互动会弱化社会越轨带来的负罪感,也包括婚姻越轨带来的负罪感(Booth,etal.,1991),进而导致移民群体离婚率的上升(Caarls and Mazzucato,2015)。
此外,迁移还会增加移民的配偶替代机会和跨文化通婚机会。研究发现,迁移到新的地点会给移民提供不同的机会,也包括遇见潜在的新伴侣(Hirsch,1999;South,etal.,2001),从而可能增加离婚风险。
2.流动经历与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
一些对国际移民婚姻的研究发现,迁移对移民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还存在性别差异。一些经验研究发现,在迁移到美国的墨西哥裔移民中,女性的离婚倾向更为明显(Hondagneu-Sotelo,1994;Repak,1995;Hirsch,2003;Hill,2004)。已有相关研究主要从两种逻辑来解释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分别是“暴露差异假设”与“脆弱性差异假设”。“暴露差异假设”认为,由于性别角色分工,男性和女性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导致男性和女性面临不同的压力环境,进而影响两性对婚姻收益、离婚成本和婚姻机会的感知。根据“经济独立假设”,女性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使其获得经济独立,从而获得可以离开不幸福婚姻的机会(Cherlin,1992)。此外,另一些研究认为,人口迁移带给女性性别角色的转换比男性大(Boyle,etal.,2008;Zontini,2010),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移民会感到被边缘化或他们的男子气概受到妻子的威胁,与配偶产生冲突 (Manuh,1999;George,2000;Charsley,2005;Gallo,2006),婚姻收益降低。这表明,外部社会环境对社会成员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的形塑会影响其婚姻稳定性。在人口迁移的背景下,女性获得新的社会角色会改变配偶间的婚姻收益与离婚成本,使其有更多的机会离开不幸福的婚姻。
绿色生态示范区应在控制性详细规划阶段编制绿色建筑规划专章,落实潜力地图及总体规划提出的总量目标,提出各个地块的绿色建筑星级要求。建议研究制定地块生态开发控制图则,加强在土地出让环节对绿色建筑相关规划指标的控制。
脆弱性差异机制则认为,基于性别社会化的差异,男性和女性对压力事件的感知和应对存在差异(Kessler and McLeod,1984),进而也会影响婚姻关系。例如,女性是在与他人的连接经历中产生道德感,并在人际关系中获得自我认同 (Gilligan,1982),因而女性更容易受到来自人际关系方面事件的影响,婚姻关系对其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更大(McRae and Brody,1989)。迁移带来的分居问题首先会影响女性与其配偶的情感交流,因而也会给女性带来更多的心理冲击(Salgado de Snyder and Nelly,1993),并可能增加女性离婚的机会(Landale and Ogena,1995)。由此可知,在不幸福的婚姻中,女性比其丈夫更倾向于主动结束婚姻(Black,etal.,1991)。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女性劳动力市场参与的增加,以及男性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庭照顾,两性的性别角色差异在逐渐缩小。这也意味着,性别差异的影响机制可能会更多地受到性别社会化差异的影响。
尽管已有研究关注到了迁移与婚姻不稳定的性别差异问题,但系统探讨移民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还较少。目前仅有个别研究关注了中国人口流动与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问题(Li,2018),对该问题还缺乏深入探讨。
其次,深入分析医疗收费项目和价格成本内涵,将规范的诊疗路径引入作业成本法中,使成本与医疗业务流程紧密相关,与价值链中作业相互嵌套,保证项目成本分配的动因有充分的依据,使医疗服务价格反映服务的价值。
3.流动经历与中国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研究
中国的人口流动也带来了婚姻稳定性下降的问题,并在近年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一些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流动人口的家庭,有流动人口的家庭存在更高的离婚风险(杜凤莲,2010);人口外出务工比例高的村庄的离婚率要高于人口外出务工比例低的村庄(高梦滔,2011);相对于未流动的夫妻,单独外出或共同外出的夫妻的离婚风险都高(莫玮俏、史晋川,2015)。这些研究表明,人口流动可能会导致离婚风险上升,但它们主要关注的是流出地居民的离婚风险,并没有关注在流入地的流动经历如何影响流动人口的婚姻。另外一些研究转向关注在流入地的流动模式对流动人口或农民工婚姻的影响,发现流动距离和流动方式对离婚风险有显著影响(李卫东,2017;马忠东、石智雷,2017)。
虽然这些研究发现流动及流动模式会增加离婚风险,但并未从经验上探讨其中的影响机制,而是将影响过程作为“黑箱”处理,这也导致一些研究在解释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时存在不一致性。例如,莫玮俏、史晋川(2015)认为单独迁移主要是降低了婚姻搜寻成本进而导致离婚发生,而马忠东、石智雷(2017)则认为单独流动可能会降低流动人口的婚姻质量,进而导致婚姻破裂。此外,已有研究也较少关注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
受传统与现代性别意识的双重影响,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一方面,根据“暴露差异假设”,伴随着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农村女性流入城市,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不仅逐渐缩小了与男性的社会距离(Li,etal.,2015),也改变了农民工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所面临的压力环境也可能发生变化,并形成有利于女性的环境。另一方面,根据“脆弱性差异假设”,受性别社会化的影响,两性不仅应对外在环境的方式和能力存在差异(Kessler and McLeod,1984;李卫东等,2013),对压力事件的体验也不同(Ickes and Layden,1978),这使得农民工对流动经历的感知与应对也可能存在性别差异。从这个角度讲,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性别差异。
与此同时,伴随着人口流动的推进,农民工逐渐实现了代际转型,新生代农民工逐渐取代第一代农民工成为主体。根据“生命历程理论”,个体的生命轨迹受历史年龄、社会年龄和个人年龄的共同影响,并受其成长环境的长期影响(Elder,etal.,2003)。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有别于第一代农民工并呈现许多新特点。具体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多是出于追求更好的生活和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而外出务工,而非基于生存需求(王春光,2001)。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趋同于城市青年人(田丰,2009),喜欢追逐潮流和时尚消费,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较高的需求(王文松,2010)。这也使新生代农民工更关注婚姻中的情感和感受(曹锐,2010),对婚姻和性持更开放的态度(吴新慧,2011)。以上特征也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社会化情境存在差异,这可能导致这两个世代组对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一些经历有不同的认识和感知,因此,流动模式对出生于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农民工婚姻的影响可能存在世代效应。
以上三个尚未有专门探讨的问题正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本研究认为,由于流动模式是影响农民工家庭关系的重要结构性因素,而这些因素对婚姻的影响又是通过农民工夫妻双方对流动模式影响的认知来实现的,因而性别社会化带来的认知上的差异也可能使农民工夫妻对流动模式影响的评估与认识存在差异。同时,不同世代组农民工成长的时代环境存在巨大差异,使其对迁移的期待与认识以及迁移带来的影响的评估与认识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从代际和性别视角系统地探讨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将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人口流动对农民工性别关系及其生活机遇的影响。
三、人口流动情境与研究假设
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是导致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推行了一套差异化发展的经济政策,其中,沿海和大城市优先发展是该政策的核心(Ma and Wei,1997)。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大城市或沿海地区获得了持续性的快速发展,农村地区或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则较为滞后,城乡间、地区间(沿海与内陆)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一社会经济环境下,流动人口的迁移呈现单向度空间流动的特征,即城乡和地区二元社会结构形塑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由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由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流动。城乡和地区二元社会结构不仅形塑着人口流动的方向,还形塑着人口流动的距离。受家庭理性需求的约束,农民工的劳动迁移在空间上呈现长距离和短距离流动并存的特征,跨省流动是农民工长距离流动在空间上的重要体现,根据2014年和2016年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报告,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其中,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比例超过75%;同时,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人口为主,比例超过87%。由此可以看出,跨省流动是农民工基于个人或家庭理性决策下的一种行动选择。另外,户籍制度也是影响农民工劳动迁移的重要因素。户籍制度不仅形塑着农民工的流动空间,还形塑着农民工的流动方式。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附属制度决定了当地社会保障、社会福利甚至就业机会的分配与再分配(张展新,2007;张春泥,2011),并将没有当地户籍的外来人口排除在各种福利和机会之外(王嘉顺,2010),使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在流入地面临教育、医疗、就业等诸多挑战,进而导致农民工家庭为了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做出不同的流动策略。例如,部分家庭采取夫妻共同流动的方式,另一些家庭则采取一方流动,另一方留守的方式。
流动距离和流动方式作为各种制度约束下农民工基于个人理性及其家庭理性做出的一种流动模式的决策结果,反过来又会影响农民工与其原生家庭的联系与日常关系,进而可能对其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根据“婚姻凝聚理论”,婚姻稳定与否受婚姻收益、离婚阻力和配偶替代机会的影响。流动模式可能影响农民工与其原生家庭及配偶在空间及情感上的联系形式,进而影响其婚姻收益、离婚阻力和配偶替代机会。
从流动距离来看,农民工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机会,往往倾向于到大城市或沿海发达省份务工,长距离流动成为农民工流动模式的一个重要特征,并可能构成影响其婚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长距离流动意味着农民工远离其原生家庭网络,这也预示着来自原生家庭网络对农民工的监督和约束力量的减弱甚至彻底消失。原生家庭网络是个体重要的离婚阻力因素(Ackerman,1963),具有抑制离婚倾向的作用,但该作用只有在婚姻出现问题或存在离婚想法时才可能出现。这就意味着,农民工长距离流动带来的原生家庭网络对婚姻监督和约束下降的问题并不一定会导致婚姻解体,但当婚姻出现问题或婚姻不幸福时,远离原生家庭网络带来的婚姻监督功能下降才可能真正产生离婚阻力弱化的效应。这也意味着,婚姻质量或婚姻满意度可能会调节长距离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从性别角度来看,受性别社会化的影响,在正常的婚姻中,女性更期待稳定的婚姻,男性则更期待自由的婚姻(Guttentag and Secord,1983)。由此可推论,相较于女性,男性在外部约束力量弱化的情况下更可能发展婚外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男性对远距离流动带来的监督力量弱化会更为敏感,远距离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要比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明显。
研究还发现,当移民迁入新的地方后,匿名化和非人格的人际交往会降低其对婚姻背叛的负面体验(Booth,etal.,1991)。这一影响可能受到至少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流动距离。流动距离越远,个人受熟人圈子的约束就越小,匿名化和非人格的人际交往越普遍,越有利于农民工减轻婚姻背叛的负面体验,导致离婚阻力下降。二是婚姻背叛的体验受到个体认知的影响。这些认知直接来源于个体社会化了的婚姻规范。当个体认同严格的传统婚姻规范时,其背叛婚姻的负面体验会更强烈;而当个体认同更为开放的婚姻规范时,其背叛婚姻的负面体验则会越弱。从世代的角度看,出生于改革开放前的农民工成长于相对传统的婚姻规范环境中,而出生于改革开放后的农民工则成长于更为开放的婚姻规范环境中,婚姻背叛带来的负面体验因而也可能存在世代的差异,从而使两代人感受到的离婚阻力存在差异。总之,长距离迁移带来的背叛婚姻的心理成本可能存在世代差异,该差异也可能使其感受到的离婚阻力存在世代差异。
⑥取出数组Array最大数所对应的下标值,即为特征向量M在多重随机森林加权大数投票算法中的最终分类标签;
此外,虽然传统社会中性别角色分工明确,性别规范对女性的约束大于男性,但现代社会中性别角色分工在许多方面已经开始变得界限模糊,性别差异在逐渐缩小,性别规范对两性约束力量的差异也在缩小。这可能导致性别间的差异存在世代差异。据此,本文提出第一组假设:
3.4 增加文化经费投入。文化主管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家和省上的项目、资金支持,做好各项乡镇文化建设的项目申请建设、人员使用等方面的统一规划。财政部门要加大乡镇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工程的投入,保证各项目标任务的落实。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投资文化事业,培育乡镇文化人才。
假设1a: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会受到婚姻满意度的调节。
假设1b: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冲击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
大量的经验研究证明,“婚姻凝聚理论”是理解和预测婚姻稳定性的重要理论框架(Previti and Amato,2003),婚姻满意度是婚姻收益的重要体现,并能够有效降低离婚的想法和婚姻解体的风险(Glenn,1991),子女、婚姻承诺、对配偶的经济依赖等离婚阻力因素则会抑制离婚行为(Heaton and Albrecht,1991;Previti and Amato,2003)。也有研究显示,配偶替代机会会提高离婚风险(South and Lloyd,1995)。另有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该理论框架,发现配偶互动和感知到的配偶回应也会影响婚姻满意度(Gadassi,etal.,2016),配偶间的互动交流在婚姻家庭压力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Hill,etal.,2017)。
流动方式是农民工及其家庭基于经济理性的另一个重要流动策略。在户籍制度等相关因素的约束下,部分农民工在流入地无力承担父母的养老和子女的就学等压力,无法实现家庭迁移,不得不采取单独流动的方式来平衡家庭的整体需求。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规范下,未实现家庭化迁移的家庭更多采取的是男性外出流动,女性留守的流动策略。然而,随着人口流动的深入和时代的发展,虽然许多农村居民依然持有传统的性别分工观念,但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女性,开始持有更为平等的性别观念,挣脱传统性别分工的束缚,并通过流动策略付诸实践。来自田野的观察发现,在单独流动的家庭中,丈夫流动和妻子留守并不是家庭的唯一流动策略,许多家庭也采取了妻子流动、丈夫留守或妻子和丈夫分别外出的流动策略(杜平,2016)。虽然部分家庭是基于婚姻矛盾而采取“分居式”流动策略,但更多的家庭是基于家庭经济理性或追求主体性而采取单独流动的策略(杜平,2016,2019)。从这个角度来说,单独迁移可能成为影响农民工婚姻质量,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婚姻质量的重要因素。
单独流动可能会影响农民工的婚姻收益。单独流动会出现夫妻事实上的分居,不利于满足夫妻正常的情感交流,还可能导致沟通不畅等问题,从而增加夫妻矛盾发生的风险(Frank and Wildsmith,2005;Boyle,etal.,2008),降低婚姻满意度,使婚姻稳定性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其婚姻满意度而发生的,婚姻满意度可能是单独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中介变量,单独流动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单独流动也意味着弱化了来自配偶的约束,在农民工婚姻收益或婚姻满意度下降时,单独流动带来的配偶监督力量弱化可能转化为离婚阻力的弱化,从而导致婚姻稳定性的下降。也就是说,婚姻满意度可能也会调节单独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但该影响机制有别于前文提到的因果机制。
从性别的角度看,单独流动可能会对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产生不同的影响。根据“脆弱性差异假设”,由于性别社会化的差异,两性对一些外部环境的感知和应对也可能存在差异(李卫东等,2013)。例如,相对于男性,女性更容易受到来自家庭矛盾和婚姻质量的影响(Kessler and McLeod,1984),因而女性可能对单独流动带来的夫妻情感沟通不畅以及可能的家庭矛盾更为敏感,单独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对女性婚姻质量的冲击也可能更明显。同时,男主外的传统性别角色也使男性更容易认同“单独流动”的角色,男性对单独流动及其带来的影响可能不如女性敏感,进而,单独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婚姻质量的影响也更不明显。
本文数据来自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学系在广州开展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专项调查。由于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调查采取宽松的配额抽样的方法:第一步是具体调查地点的抽取。首先,根据《广州市统计年鉴2015》计算广州市各区农民工数量;然后,根据计划的1 500个样本按照等比例配额的方法,在广州市农民工最为集中的五个区(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黄埔区和番禺区,这五个区的农民工占整个广州市农民工人数的80.8%)确定各区的样本量;最后,每个街道调查100个样本,根据各区计划样本数据确定街道抽样数量,并按照简单随机抽样方法分别抽取街道,总共获得15个街道。第二步,抽取调查样本。根据2014年广州人口流动监测数据中农民工主要职业分布比例、性别比和婚姻状态的特点,采取配额抽样的方法在每个街道抽取100个样本进行调查。调查最终获得1 632个样本,其中,已婚样本1 079个,男性513个,女性566个,第一代农民工626个,新生代农民工453个。删除了缺失值,最终进入模型的样本分别为第一代农民工555个,新生代农民工423个。受访者本人和配偶的收入分别存在6.7%和2.7%的缺失值,研究采用回归插补法对本人和配偶收入的缺失值进行了填补。
从世代的角度看,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出生于不同的时代。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教育程度更高,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趋同于城市青年人(田丰,2009),喜欢追求潮流和时尚消费,对物质和精神生活有较高需求(王文松,2010)。这也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关注婚姻中的情感和感受(曹锐,2010)。而第一代农民工成长于更为传统的社会环境,务工的首要目标是养家糊口,这意味着第一代农民工在务工的过程中会更多地考虑经济因素,其次才是情感需求。因此,单独流动带来的夫妻情感沟通不畅的问题可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与此同时,由于女性对单独流动带来的情感困扰会更为敏感,在世代效应的作用下,单独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冲击的性别差异可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明显。据此,本文提出第二组假设:
电子天平(感量0.01 g)引入的不确定度包括示值误差和重复性引入的不确定度。根据电子天平的检定证书,0~50 g量程时示值最大允许误差为±0.05 g,取均匀分布的标准不确定度为重复性最大允许误差为±0.15 g,取均匀分布的标准不确定度为
西方学术界对移民婚姻进行了大量研究,发现移民比流出地的非移民有更高的离婚率,迁移会给移民的婚姻带来一系列潜在风险(Frank and Wildsmith,2005;Phillips and Sweeney,2006)。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婚姻凝聚理论”的框架分析移民的婚姻稳定性问题。
假设2b: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受到婚姻满意度的调节。
假设2b: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冲击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
假设2c:单独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要比男性农民工明显,而且这种性别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更为明显。
四、数据、变量与方法
(一)数据
以上推理主要是基于单独流动可能会降低婚姻收益的因果机制而展开的。同时,单独流动带来的与配偶分居也可能导致配偶监督力量的弱化,但监督力量能否转化成离婚阻力的弱化取决于个体的婚姻收益是否下降或婚姻是否出现问题。当个体婚姻质量下降,配偶分离带来的监督力量的弱化就可能转化为离婚阻力的弱化,从而增加婚姻不稳定的风险。此外,受女性倾向于维系婚姻而男性倾向于发展婚外关系差异的影响(Guttentag and Secord,1983),单独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弱化可能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的影响更为明显,因此,婚姻质量对单独流动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比对女性农民工明显。
(二)变量
1.因变量
婚姻稳定性 婚姻稳定性指的是婚姻中的当事人对于婚姻持续的态度或离婚倾向,表现为个体呈现离婚倾向,有离婚的想法,并可能采取行动来结束婚姻(Booth and Edwards,1985)。以艾伦和爱德华(Booth and Edwards,1985)的婚姻稳定性量表为基础,本文构建了一个从对婚姻问题认知到采取相应行动的婚姻稳定性量表。该量表既反映了个体婚姻从高度稳定到高度不稳定的水平,也能较好地与婚姻满意度区分,具体包括5个题项,分别是:A.最近一年“我想过我们的婚姻会出现问题”;B.“我与家人、朋友或网友讨论过我婚姻中的问题”;C.“我不喜欢和配偶生活在一块”;D.“我有过和配偶离婚的念头”;E.“我与家人或朋友讨论过离婚或分居”,答案包括“一直”“经常”“偶尔”“从不”,其中,“一直”和“经常”表明个体婚姻不稳定性比较严重。将取值的顺序进行转换,并将每个取值减去1,分别赋值为“从不”=0,“偶尔”=1,“经常”=2,“一直”=3,再将各题得分加总。总得分区间为0—15,0表示婚姻稳定,1—15区间表示婚姻由低度不稳定到高度不稳定。
配偶收入对数将配偶的月收入(工资、经营性收入及农产品折算现金后的收入)转换为收入的对数,为连续变量。
该量表存在离婚倾向趋强的态势,包括个人意识到婚姻出现问题,产生了离婚想法和行为上的进一步行动。其中题A、B表示意识到婚姻存在问题,代表轻度不稳定;题C、D表示不仅婚姻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出现了感情上的疏远、讨厌,产生了离婚念头,表示婚姻呈现中度不稳定;题E表示在离婚想法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行动,即开始与配偶、家人、朋友正式讨论离婚或分居的事情,这表示由离婚念头开始转向离婚行动,表明婚姻进入高度不稳定状态。基于以上特点,可以通过量表总得分来判断其婚姻不稳定性的水平层次,如:0分,表明婚姻非常稳定;1—4分表示婚姻处于低度不稳定状态,因为4分代表个体经常出现A、B两类问题;5—6分则表明个体最少出现了C、D中的一个问题,说明已经在心理上疏远配偶,甚至产生离婚念头,达到中度不稳定性;7分以上则表明个体经常出现心理疏远或离婚的念头,离婚倾向比较明显,趋于高度不稳定。根据以上特征,本文将婚姻稳定性由连续型变量合并成四分类的有序变量,即“稳定”“低度不稳定”“中度不稳定”和“高度不稳定”。
研究显示:精神科护士一年内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为57.0%~99.0%[2,12-13]。本次调查显示:我院精神科护士1年内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为75.3%。精神科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高的原因为:①精神病病人大多存在思维、行为异常,受幻觉、妄想影响,随时可能出现冲动伤人行为,而护士与病人接触机会最多,遭受暴力危害最直接[14];②在护士职业道德影响下,护士对病人暴力行为常采取忍让态度,处于较为被动地位,不能有效控制暴力;③精神科保护性约束或隔离措施的使用与暴力发生密切相关[15],护士在执行保护性约束和隔离措施时,经常遭受病人暴力。
2.自变量
流动方式本文根据配偶当前居住地,将配偶在本地居住界定为“共同流动”,赋值为0;将配偶在户籍地或其他地方界定为“单独流动”,赋值为1。
流动距离本文通过是否跨省流动来测量流动距离,为二分类虚拟变量(“跨省流动”=1,“省内流动”=0)。
3.控制变量
本人收入对数将本人月收入(工资、经营性收入)转换为收入的对数,为连续变量。
1.2.2 保脾手术 生物胶合止血、物理凝固止血和单纯缝合修补3例,脾修补加脾动脉结扎术3例。脾部分切除2例。
本人教育程度指本人所获得的正规教育的最高水平,具体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赋值分别为1—7。这里将其作为连续变量。
通婚距离通婚距离跨度划分为4类:“同县”“跨县”“跨市”“跨省”。转变为虚拟变量时,以“同县”为参照组。
性别角色意识该量表反映个体对男女性别角色的认知。具体包括8个题项,分别为“男人最主要的工作是赚钱,女人最主要的工作是照顾家庭和孩子”“如果妻子也有正式工作,丈夫和妻子应该平等地承担家务劳动”“当夫妻双方必须有一个在家照顾孩子和家庭,这个人应该是妻子”“女性在照顾家庭和小孩的时候是最幸福的”“丈夫应该比妻子挣钱多”“女人应该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有自己的事业”“与男孩相比,女孩更应该从小就学习做家务”。答案赋值分别为“非常同意”=1,“同意”=2,“既不同意也不反对”=3,“不同意”=4,“非常不同意”=5。将反向题调整后各题得分加总,得分越高则性别意识越非传统。
配偶教育程度指配偶所获得的正规教育的最高水平,具体包括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或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赋值分别为1—7。这里将其作为连续变量。
性别比结构本文将受访者工作和生活区域内异性数量的多少作为配偶替代机会的重要测量指标。具体操作化为三分类变量,即“同性居多”“异性居多”“相差不大”。
婚姻满意度该量表反映了个体对婚姻和配偶的满意程度。具体包括8个题项,分别为“我对我的婚姻感到满意”“我对我的配偶作为丈夫或妻子的角色感到满意”“我对我们夫妻之间的关系感到满意”“配偶赚钱养家的能力令我感到满意”“配偶对家庭的照顾令我感到满意”“来自配偶的陪伴令我感到满意”“配偶对婚姻的忠诚令我满意”“配偶与我的性生活令我满意”。答案赋值分别为“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3,“满意”=4,“非常满意”=5,将各题得分加总,得分越高则代表满意度越高。需要说明的是,在调节效应分析中,婚姻满意度各个题项的取值进行了反向调整,将题项得分加总后,得分越高则婚姻满意度越低。
子女数量指与当前配偶生育子女数量。本文将生育子女数转换为分类变量,即“0个”“1个”“2个及以上”,其中“0个”为参照项。
初婚年龄指初次结婚时的年龄,为连续变量。
婚姻持续时间指初次结婚时间至调查时点的跨度,为连续变量。
初次迁移年龄指受访者第一次外出务工时的年龄。
世代本文将农民工划分为两大年龄群体,即“80后”和“50—70后”,或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
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举国震惊。
主要变量描述统计见表1。
表1: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及主要变量描述统计
注:表中第一个“婚姻稳定性”为连续型变量。
?
(三)方法
为了更为详细地探讨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及其世代差异,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描述统计分析,主要从性别和世代两个维度比较婚姻稳定性及其他主要变量的性别差异及世代差异;其次采用Ologit回归模型分析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世代差异;第三,从性别的视角,分别分析流动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比较这两个世代组群的性别差异是否还存在世代差异;第四,为了进一步识别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本文还进一步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分别就流动模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分析。本文婚姻稳定性量表在题项结构上与社会距离量表类似,在赋值上与李克特量表类似,因此,量表加总得分高低可以反映受访者婚姻稳定性的高低,数据取值两极为0—15,且数据分布呈现泊松分布的特征。针对这一特点,本文将婚姻稳定性的取值进行合并,建立了四分类的有序变量,并在分析中主要采用Ologit回归模型。②根据变量结构,将婚姻稳定性转化为“稳定”“轻度不稳定”“中度不稳定”和“高度不稳定”四类,并作为因变量进入Ologit回归模型,其结果与采用原始连续有序变量的分析结果有细微差异,但结果趋势一致。同时,为了验证Ologit回归模型中交互项是否稳健,研究还引入了OGLM模型进行印证。
五、分析结果
(一)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和代际差异状况
表2报告的是分性别和代际的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水平。结果显示,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存在显著的代际差异。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农民工婚姻稳定性还存在性别差异,但该差异受到代际的调节,其中,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显著低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第一代男性农民工,但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以上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婚姻不稳定性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女性农民工婚姻不稳定性要比男性农民工明显,且这种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突出。
表2: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水平(均值)
注:+p<0.1,*p<0.05,**p<0.01,***p<0.001;星号表示F值检验结果。
?
(二)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代际差异
采用Ologit模型分别估计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全样本及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比较流动模式对这两个组群影响的代际模式差异。表3总结了模型结果,报告了流动过程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
模型1至模型9分析性别、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结果。就全样本模型1至模型3的分析结果来看,性别、世代、流动方式和婚姻满意度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相对于男性,女性身份会降低婚姻稳定性;相对于第一代,新生代身份会显著降低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单独流动会显著降低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婚姻满意度降低了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面向大众提供全方位的社会化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变革与发展的趋势.当前,高校图书馆应重视图书管理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推进图书馆网络化、数字化建设,不断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模式,建立服务社会与资源共享的长效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社会化、服务内容社会化和服务方式社会化,最大限度地发挥高校服务社会的功能,真正体现其社会价值.
模型4至模型9的结果表明,性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女性身份会显著降低其婚姻稳定性,但性别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不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性别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其中,性别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
流动距离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其中,流动距离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模型4和模型6的结果显示,相对于省内流动,跨省流动仅会显著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但在模型7和模型9中,跨省流动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支持了假设1b。值得注意的是,模型6和模型9在模型5和模型8的基础上加入“婚姻满意度”变量后,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系数有明显提高,这表明婚姻满意度可能会调节跨省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
流动方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其中单独流动仅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模型4至模型6的结果表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但模型7至模型9表明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这表明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冲击可能比对第一代农民工明显,假设2c获得支持。值得注意的是,模型6和模型9中加入婚姻满意度变量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系数有明显的下降,这表明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部分是通过影响其婚姻满意度实现的。
每天在忙碌中度过的李孝弟,不知不觉从省城“下乡”已半年。眼下,李孝弟和他的服务团伙伴们,对宜章科技支撑农业产业发展已经形成共识。
(三)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及其世代差异
本文采用Ologit模型和OGLM模型分别估计了流动模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并进一步比较这两个世代间的性别差异,分别采取分组回归和交互项回归两种方式,以判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及其影响大小的性别差异。为了初步判断流动模式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机制,首先采用嵌套模型对四个群组进行分析,以观察模型加入婚姻满意度变量后,流动模式影响的变化(表4总结了分组回归的模型结果)。其次,在模型中引入流动模式与性别、流动模式与世代的交互项,观察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是否也存在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表5总结了交互项回归的模型结果)。此外,为了进一步检验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稳定,本文还引入OGLM模型来印证交互项回归的模型结果。③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OGLM模型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
流动距离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且这种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明显。表4中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表明,在0.1的置信水平上,跨省流动会显著降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但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模型6和模型8的结果表明,流动距离对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不显著,但影响方向存在性别差异,其中跨省流动会降低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但会提高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表5中模型2的结果表明,置信水平放宽到0.106,世代与迁移距离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就具有显著影响,其中跨省迁移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显著大于第一代农民工。以上结果表明,流动距离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更为明显,并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明显。假设1c得到了部分支持。
表5:流动模式与性别、流动模式与世代的交互项回归结果
注:+p<0.1,*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
流动方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且这种差异在第一代农民工中更为明显。表4中模型1至模型4的结果表明,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直接的显著影响,但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直接的显著影响,单独流动显著降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与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类似,在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单独流动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存在相反的影响方向,对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正向影响;同时,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比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显著。以上结果表明,在两个世代群组中,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单独流动仅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有显著影响,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
为了进一步探讨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本文还对性别与流动距离、性别与流动方式做了交互并纳入回归模型。结果如表5所示,在全样本中,在0.05的置信水平上,性别与单独流动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单独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显著大于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见模型2)。性别与流动距离的交互项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不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流动距离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模型4和模型6是分别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性别与单独流动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表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其中,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大于第一代男性农民工。性别与跨省流动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都不具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不存在性别差异。OGLM模型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与表5的结果类似,说明表5中交互项的影响是稳健的,同时OGLM模型中方差方程(lnsigam)结果显示世代的影响显著,这表明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存在世代差异。
以上结果表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单独流动仅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不具有显著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并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大小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其中,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显著大于第一代男性农民工。这表明,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大小的性别差异存在世代差异。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中,跨省流动仅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有显著影响,对第一代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相反的影响方向,但影响大小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大小存在世代差异。
(四)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机制分析
根据表4的结果,婚姻满意度可能会调节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也可能在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中发挥中介效应。为了进一步分析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机制,识别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是基于婚姻收益下降的因果机制还是基于婚姻收益产生的调节机制,本文对自变量、因变量和中介调节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理,并在此基础上对流动方式、婚姻满意度与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进行了中介效应分析,同时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分别分析了婚姻满意度对流动距离和流动方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
1.中介效应分析
表6报告的是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模型1和模型4是自变量“单独流动”对因变量“婚姻稳定性”的回归分析,模型2和模型5是自变量“单独流动”对中介变量“婚姻满意度”的回归分析,模型3和模型6是自变量“单独流动”和中介变量“婚姻满意度”对因变量婚姻稳定性的回归分析。模型1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在0.0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显著降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的稳定性。模型2则表明,在0.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会显著降低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模型3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和婚姻满意度后,单独流动的影响系数及显著度都有明显下降,且在0.05的置信水平上依然显著,可见婚姻满意度会显著提高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表7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在0.01的置信水平上,中介效应显著,其中中介效应占总影响效应的32%。这也表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影响其婚姻满意度实现的,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表6:流动模式、婚姻满意度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中介效应分析
注:+p<0.1,*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
表7:Sobel-Goodman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
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中介效应不显著。模型4表明,在控制其他变量后,在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会显著降低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模型5表明,在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满意度的影响不显著;模型6显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和婚姻满意度后,在0.1和0.0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和婚姻满意度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独立的显著影响;表7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也显示,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中介效应不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同时存在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但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仅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假设2a得到部分支持。
2.调节效应分析
表8是分别就流动模式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对四个群体进行调节效应分析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3的结果表明,在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具有独立的直接影响,但单独流动与婚姻满意度交互项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说明,婚姻满意度不是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单独流动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变量。结合中介效应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单独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更多表现为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效应。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表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单独流动与婚姻满意度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都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相对于表4的模型2和模型6,表7的模型2和模型4的解释力分别提高了3%和2%。这表明,婚姻满意度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的单独流动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其中,婚姻满意度越低,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越大。
表8中模型1和模型3的结果还表明,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跨省流动与婚姻满意度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相对于表4的模型4和模型8,表8的模型1和模型3的解释力分别提高了2%和1%。这表明,婚姻满意度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跨省流动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其中,婚姻满意度越低,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影响就越大。模型2和模型4的结果表明,跨省流动与婚姻满意度的交互项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婚姻满意度不是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流动距离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变量。值得注意的是,跨省流动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对第一代男性农民工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这表明,跨省流动对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可能存在世代差异。为了检验调节效应的稳健性,本文还引入OGLM模型,④限于篇幅,本文没有报告OGLM模型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要。模型结果显示,交互项对因变量的影响与模型8的结果类似,这表明调节效应是稳健的。
表8:流动距离、流动模式、婚姻满意度与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调节分析
注:+p<0.1,*p<0.05,**p<0.01,***p<0.001;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
以上结果表明,婚姻满意度会调节跨省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假设1a得到部分支持;而婚姻满意度对单独流动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男性农民工群组中,对女性农民工群组没有调节效应,假设2b也得到支持。结合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还可以发现,婚姻满意度是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中介变量,但并不具有调节效应;婚姻满意度是单独流动对两组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调节变量,但不具有中介效应。这说明,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婚姻满意度对跨省流动与婚姻稳定关系的调节效应仅存在于女性农民工群体中,对男性农民工组群没有调节效应,但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具有显著直接影响,这表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
六、结论与讨论
尽管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问题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但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差异以及世代差异还没有得到重视,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也尚不明确。本文运用来自广州的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专项调查数据,从性别和世代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状况,并探讨了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研究发现,农民工存在较高比例的婚姻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还存性别和世代差异。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要显著低于第一代农民工,且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要显著低于男性农民工。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要低于第一代男性农民工,但不存在显著差异。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存在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
就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性别和世代差异而言,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低于第一代农民工。这可以从两个方向来解释这一现象:一是年龄效应。婚姻替代机会受到个人年龄的影响,年龄越大,婚姻替代机会就越少。第一代农民工年龄普遍在40岁以上,再婚的机会要远低于新生代农民工,这使得其婚姻要比新生代农民工稳定。二是世代效应,即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仅成长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也持有不同的婚姻家庭观念。第一代农民工持有更为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分工,新生代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则持有趋向平等的性别角色观念。在人口流动与女性就业的背景下,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遭遇社会角色与家庭性别角色分工意识的冲突,从而降低其婚姻满意度和婚姻收益,并降低其婚姻稳定性。此外,无论是经济还是思想意识,新生代农民工独立性都更强,也更关注自身的情感需求与情感感受,从而对婚姻冲突、低婚姻满意度和低婚姻收益的忍耐性也更低,这也容易降低其婚姻稳定性。就性别差异而言,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要低于男性农民工,这一特征在新生代女性农民工中最为突出,其原因可能源于性别角色意识与性别角色分工的变化:一方面,女性农民工进入城市务工实现了经济独立,降低了对丈夫的依赖;另一方面,城市生活、工作的洗礼也改变了女性的性别角色意识,越来越多的女性农民工逐渐接受平等化的性别意识,从而使得女性更容易感受到传统性别分工的不平等,并在日常生活中容易基于性别角色分工与其丈夫发生冲突,导致婚姻满意度和婚姻收益下降。以上两个因素使得女性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更容易出现下降。
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从世代差异来看,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直接影响,但对第一代农民工没有显著直接影响,其原因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世代的效应来看,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受年龄效应影响,再婚机会大为减少,这会抑制其离婚倾向;另一方面,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的婚姻观念更趋向于保守,也会抑制其离婚倾向。因而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弱化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会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从性别社会化效应来看,社会对女性的规范要求更为严格,而往往对男性持有更为宽松的态度。这一社会特征通过社会化容易形成男性和女性对于既定社会行为和态度的认知,包括他们对婚姻的认知,从而使得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减弱对于男性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并在匿名化的空间中也可能更容易对背叛婚姻的内疚感产生脱敏,导致发展婚外关系的心理成本低于女性。
就调节效应而言,婚姻满意度仅会调节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男性农民工群组的婚姻稳定性并不存在这一调节效应。这一结果与“婚姻凝聚理论”基本一致,即跨省流动削弱了来自原生社会网络的监督作用,从而弱化了离婚阻力因素,但这一因素变化对于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受到婚姻收益的调节,并存在性别差异,其中,婚姻满意度低的女性农民工在跨省流动的过程中婚姻不稳定性上升的风险更大。从这个角度说,跨省流动并不是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下降的根本原因,但跨省流动为婚姻收益下降的女性农民工提供了婚姻解体的机会。这一结果也表明,婚姻收益的调节效应是明显的,从而部分支持了研究假设中关于长距离流动主要是弱化农民工离婚阻力以及其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主要是基于婚姻收益的调节机制而发生的理论推断。值得注意的是,调节效应的性别差异也表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理可能存在性别差异。受性别社会化的影响,在正常的婚姻中,女性更期待稳定的婚姻,而男性更期待自由的婚姻 (Guttentag and Secord,1983)。因此,对于女性农民工而言,跨省迁移带来的社会网络监督力量的弱化并不一定会带来离婚阻力下降的效应,只有当其婚姻质量下降后这一效应才会显现;但对于男性农民工而言,远距离迁移意味着会带来更多的再婚机会,因而跨省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具有直接的影响。同时,受年龄效应的影响,第一代农民工的再婚机会要少于新生代农民工,因此,跨省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也可能存在世代差异,而在调节分析中仅发现跨省流动对新生代男性农民工具有主效应也间接支持以上观点。
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还存在世代差异。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要更为明显,跨省流动仅会显著降低新生代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但跨省流动对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均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跨省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更为明显,假设1c后半部分没有获得支持。这一差异可以从世代效应角度来解释:一方面,第一代农民工成长于更为传统的社会环境,内化了的传统婚姻规范会约束其婚姻行为,而新生代农民工成长于更为开放的婚恋环境,对婚外关系和离婚也更为包容,因而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减弱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更为明显;另一方面,社会规范对农民工婚姻的影响还存在性别效应,即社会规范对女性的婚姻规范约束要大于男性,从而使得跨省流动带来的离婚阻力弱化效应对男性的影响要比女性明显。因此,在世代效应和性别效应的交互作用下,跨省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要比第一代农民工明显。
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和性别差异。从世代的角度来看,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世代差异,其中,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影响,但对第一代农民工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影响。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要比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明显,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的影响方向相反。以上结果表明,在世代效应下,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加注重自身的情感需求,因而对于分居带来的情感问题也更为敏感。与此同时,世代的时间效应反映为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可能具有更多的婚姻替代机会,使得单独流动对他们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更为敏感。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单独流动仅对新生代和第一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没有显著直接影响。这表明,单独流动可能仅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因果影响,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没有直接的因果影响。中介效应分析进一步支持了单独流动对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因果机制。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在0.05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女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具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效应,其中,间接影响效应主要是通过降低其婚姻满意度而发生的;在0.1的置信水平上,单独流动对第一代女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只存在直接影响。单独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影响。
调节效应分析显示,婚姻满意度会调节单独流动对新生代和第一代男性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其中,婚姻满意度越低,单独流动就越可能降低男性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但这种调节效应并不存在于女性农民工群体。这表明,单独流动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婚姻收益下降的情况下,监督力量弱化可能会转换为离婚阻力弱化,并给了男性农民工脱离不幸福婚姻的机会,从而降低其婚姻稳定性。以上结果进一步表明,单独流动可能同时具有降低婚姻收益和弱化离婚阻力的作用,但是,这种影响机制对男性农民工和女性农民工来说存在差异,其中,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表现为因果机制,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更多是一种调节性机制。单独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机制的性别差异可能源于性别社会化机制。性别社会化使得女性更容易受到与人际和情感相关因素的困扰(Kessler and McLeod,1984),而单独流动会影响夫妻正常的情感沟通,增加夫妻矛盾发生的概率,因而也会带给女性更大的情感困扰,降低其婚姻收益,也使得女性更容易出现婚姻不稳定性问题。性别社会化使男性形成更为外向的社会认知及行为取向,其本身对情感的感受和体验就可能比女性弱。同时,男性承担了更多的养家糊口责任(Li,etal.,2015)。外出务工赚钱养家是男性农民工的首要目的,这使得单独流动对其情感和婚姻带来的冲击会被养家糊口的责任充抵和削弱,因而单独流动带来的沟通问题对男性农民工婚姻收益的干扰也就比较弱。因此,单独流动对婚姻稳定性影响的因果机制仅体现在对女性农民工的影响上,对男性农民工的影响不明显。
基于以上发现与讨论,本文认为,人口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非线性过程,会受到多种因素和机制的影响,其中,不利的流动模式既可能直接或间接地降低婚姻稳定性,也可能是在婚姻收益或婚姻质量的调节下成为婚姻解体的触发性因素或为婚姻解体提供机会。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还嵌入在农民工的出生世代,并呈现不同世代群体间的差异和分化。同时,流动过程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还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主要源于脆弱性差异机制,即农民工早年性别社会化导致其对迁移带来的压力事件的感知、评估与反应存在性别差异,比如,女性对于人际关系的相关问题会更为敏感,这使得单独流动会带给女性农民工更多的婚姻困扰。此外,社会变迁的定律意味着不同世代群组所经历的社会化情境和所处的社会结构都存在差异,因此,出生年代也会导致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存在世代群组的差异。无论是其社会化情境,还是所处的社会结构,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流动模式对其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性别差异也会呈现世代差异。以上发现还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由于人口流动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并非线性和同质,而是存在性别和世代的差异,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在制定农民工婚姻稳定性促进的政策时充分考虑到性别差异和世代差异;同时,由于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存在不同的机制,这也意味着农民工婚姻福利促进的需求存在差异,从而也形成了差异化的政策需求。
本文还存在一些局限。首先是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问题。虽然本文中婚姻稳定性是一个包含离婚行为倾向的非完全主观变量,但也包含了对婚姻的感受与态度,因而在使用婚姻满意度来解释婚姻稳定性时依然存在用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的问题。本文借鉴了基于变量测量的策略(胡安宁,2019),首先假定婚姻满意度和婚姻稳定性存在共同的心理倾向,然后利用个人感知的婚姻中的配偶亲社会行为来测量一般的心理倾向。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抽离和产生基本心理倾向得分,然后建立两个模型,一个模型是用婚姻满意度及控制变量来预测婚姻稳定性,另一个模型是在前一个模型基础上加入基于因子分析产生的一般心理倾向变量。结果显示,在控制一般心理倾向后,婚姻满意度的系数有明显下降,但其影响依然显著。⑤这说明,婚姻满意度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一部分来自一般心理倾向,但婚姻满意度对婚姻稳定性依然存在显著的净影响,这表明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第二,尽管有田野观察发现,在家庭经济理性的激励下,已婚女性单独流动也是一种重要的迁移形式,但受横截面数据的约束,无法从数据上排除部分单独迁移是源于婚姻的不稳定,从而也就无法将婚姻质量带来的调节性效应完全从因果机制分析中剥离出来。同时,虽然本文尝试通过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分析来识别流动模式、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机制,并试图分别探讨婚姻质量下降发生在流动前或非流动带来的婚姻质量下降对流动模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影响,以及流动模式对婚姻质量的影响及其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但受横截面数据的限制,无法将迁移前婚姻质量对迁移模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与迁移中婚姻质量对迁移模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调节效应剥离开。此外,由于数据无法开展趋势研究,从而无法从世代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影响的效应中剥离出生物年龄和社会年龄的影响效应。本文以1980年为分割点,将研究对象分为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而第一代农民工也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受样本量限制,本研究无法展现这些差异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进一步加以分析和解释。
参考文献(References)
曹锐.2010.新生代农民工婚恋模式初探[J].南方人口(5):53-59.
杜凤莲.2010.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5):105-111.
杜平.2016.男工.女工:当代中国农民工的性别、家庭与迁移[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杜平.2019.家庭纽带与权力博弈:南中国乡城迁移中夫妻性别秩序的重塑[R].中国社会学年会会议论文.
高梦滔.2011.农村离婚率与外出就业:基于中国2003—2009年村庄面板数据的研究[J].世界经济(10):55-69.
胡安宁.2019.主观变量解释主观变量:方法论辨析[J].社会39(3):183-209.
李卫东.2017.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代际、迁移和性别的视角[J].中国青年研究(7):74-81.
李卫东.2018.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与发展(6):39-49.
李卫东、李树茁、费尔德曼.2013.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J].社会33(3):65-88.
刘传江、徐建玲.2006.“民工潮”与“民工荒”——农民工劳动供给行为视角的经济学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5):73-80.
马忠东、石智雷.2017.流动过程影响婚姻稳定性研究[J].人口研究 (1):70-83.
莫玮俏、史晋川.2015.农村人口流动对离婚率的影响[J].中国人口科学 (5):104-112.
田丰.2009.改革开放的孩子们:中国“70后”和“80后”青年的公平感和民主意识研究[J].青年研究 (6):1-10.
王春光.2001.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 (3):63-76.
王嘉顺.2010.区域差异背景下的城市居民对外来人口迁入的态度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J].社会30(6):156-174.
王文松.2010.新生代农民工的特征、心理特点及应对措施[J].农村经济与科技 (5):55-56.
吴新慧.2011.传统与现代之间:新生代农民工的恋爱与婚姻[J].中国青年研究 (1):15-19
叶文振、林擎国.1998.当代中国离婚态势和原因分析[J].人口与经济 (3):22-28.
叶文振、徐安琪.1999.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人口科学 (7):7-12.
张春泥.2011.农民工为何频繁变换工作——户籍制度下农民工的工作流动研究[J].社会31(6):153-177.
张展新.2007.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城市外来人口研究新视角[J].人口研究(6):16-24.
Ackerman,C.Affiliations.1963.“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Differential Divorce Rate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9(1):13-20.
Amato,Paul R.and Alan Booth.1995.“Changes in Gender Role Attitudes and Perceived Marital Quality.”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0(1):58-66.
Becker,Gary S.1981.A Treatise on the Famil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lack,Leora E.,Matthew M.Eastwood,Douglas H.Sprenkle,and Elaine Smith.1991.“An Exploratory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 of Leavers versus Left as It Relates to Levinger’ Social Exchange Theory of Attractions,Barriers,and Alternative Attractions.”Journal of Divorce and Remarriage 15(1-2):127-139.
Booth,Alan,David R.Johnson,and Lynn K.White.1986.“Divorce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over the Life Course.”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7(4):421-442.
Booth,Alan and John N.Edwards.1985.“Age at Marriage and Marital Instabilit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47 (1):67-75.
Booth,Alan,John N.Edwards,and David R.Johnson.1991.“Social Integration and Divorce.”Social Forces 70(1):207-224.
Boyle Paul J.,Hill Kulu,Thomas Cooke,Vernon Gayle,and Clara H.Mulder.2008.“Moving and Union Dissolution.”Demography 45(1):209-222.
Bradbury,Thomas N.,Frank D.Fincham,and Steven R.H.Beach.2000.“Research on the Nature and Determinants of Marital Satisfaction:A Decade in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2(4):964-980.
Caarls,Kim and Valentina Mazzucato.2015.“Doe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ead to Divorce?Ghanaian Couples in Ghana and Abroad.”Population70(1):127-150.
Charsley,Katharine.2005. “Unhappy Husbands: Masculinity and Migration in Transnational Pakistani Marriages.”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1(1):85-105.
Cherlin,Andrew J.1992.Marriage,Divorce,Remarriag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oke,Lynn Prince and Vanessa Gash.2010.“Wives’Part-time Employment and Marital Stability in Great Britain,West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Sociology 44(6):1091-1108.
Elder Glen H.,Monica Kirkpatrik Johnson,and Robert Crosnoe.2003.“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In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edtied by Jeylan T.Mortimer and Michael J.Shanahan.Boston,MA:Springer.
Foner,Nancy.1999.“Immigrant Women and Work in New York City,Then and Now.”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18(3):95-113.
Frank,Reanne and Elizabeth Wildsmith.2005.“The Grass Widows of Mexico:Migration and Union Dissolution in a Binational Context.”Social Forces 83(3):919-947.
Fridkis,Ari Lloyd.1981.“Desertion in the American Jewish Immigrant Family:The Work of the National Desertion Bureau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Industrial Removal Office.”American Jewish History 71(2):285-299.
Friedman,Reena Sigman.1982.“Send Me My Husband Who Is In New York City:Husband Desertion in the American Jewish Immigrant Community 1900-1926.”Jewish Social Studies 44(1):1-18.
Gadassi,Reuma,Lior Eadan Bar-Nahum,Sarah Newhouse,Ragnar Anderson,Julia R.Heiman,Eshkol Rafaeli,and Erick Janssen.2016.“Perceived Partner Responsiveness Medi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exual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A Daily Diary Study in Newlywed Couples.”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45(1):109-120.
Gallo,Ester.2006.“Italy is not a Good Place for Men:Narratives of Places,Marriage and Masculinity among Malayali Migrants.”Global Networks 6(4):357-372.
George,Sheba.2000 .“‘Dirty Nurses’and ‘Man Who Play’:Gender and Class in Transnational Migration.”In Global Ethnography:Forces,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edited by M.Burawo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illigan,Carol.1982.In a Different Voice: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Glenn,Norval D.1991.“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Marital Quality in the 1980s:A Critical Review.”In Contemporary Families:Looking forward,Looking back,edited by Alan Booth.Minneapolis,MN:National Council on Family Relations.
Grasmuck,Sherri and Patricia R.Pessar.1991.Between Two Islands:Dominic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Guttentag,Marcia and Paul F.Secord.1983.Too Many Women?The Sex Ratio Question.Beverly Hills:Sage Publications.
Heaton,Tim B.and Stan L.Albrecht.1991.“Stable Unhappy Marriages.”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3(3):747-758.
Hill,E.Jeffrey,David B.Allsop,Ashley B.LeBaron,and Roy A.Bean.2017.“How Do Money,Sex,and Stress Influence Marital Instability?”Journal of Financial Therapy 8(1):21-41.
Hill,Laura E.2004.“Connections Between U.S.Female Migration and Family Formation and Dissolution.”Migraciones Internacionales 2(3):60-82.
Hirsch,Jennifer S.1999.“En el Norte la Mujer Manda:Gender,Generation,and Geography in a Mexican Transnational Community.”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2(9):1332-1349.
Hirsch,Jennifer S.2003.A Courtship after Marriage:Sexuality and Love in Mexican Transnational Families.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ondagneu-Sotelo,Pierrette.1994.Gendered Transitions:Mexican Experiences of Immigration.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ckes,William and Mary A.Layden.1978.“Attributional Styles.”In New Directions in Attribution Research(Vol.2),edited by J.H.Harvey,W.J.Ickes,and R.F.Kidd.Hillsdale,NJ:Erlbaum:119-192.
Kessler,Ronald C.and Jane D.McLeod.1984.“Sex Differences in Vulnerability to Life Event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49(5):620-631.
Landale,Nancy S.and Nimfa B.Ogena.1995.“Migration and Union Dissolution among Puerto Rican Women.”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29(3):671-692.
Levinger,George.1965.“Marital Cohesiveness and Dissolution:An Integrative Review.”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27):19-28.
Levinger,George.1976.“A Socio-Pyschological Perspective on Marital Dissolution.”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32):21-47.
Lewin,Kurt.1951.Field Theory in Social Science.New York:Harper.
Li,Weidong.2018.“Migration and Marital Instability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Based on Gender Perspective.”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4(2):218-235.
Li,Weidong,Shuzhuo Li,and Marcus W.Feldman.2015.“Gender Differences in Anomie among China’s Rural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ntext of Gender Imbalance and Population Migration.”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1(4):605-624.
Ma,Laurence J.C.and Yehua Dennis Wei.1997.“Determinants of State Investment in China,1953-1990.”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Geography 88(3):211-225.
Manuh,T.1999.“‘This Place is not Ghana’:Gender and Rights Discourse among Ghanaian Men and Women in Toronto.”Ghana Studies (2):77-95.
McRae,James A.,Jr.and Charles J.Brody.1989.“The Differential Importance of Marital Experiences for the Well-Being of Women and Men:A Research Note.”Social Science Research18(3):237-248.
Milewski,Nadja and Hill Kulu.2014.“Mixed Marriages in Germany:A High Risk of Divorcefor Immigrant-Native Couples.”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30(1):89-113.
Oppenheimer,Valerie Kincade.1997.“Women’s Employment and the Gain to Marriage:The Specialization and Trading Model.”Annual Reviews Sociology (23):431-453.
Parsons,Talcott.1955.“The American Family:Its Relation to Personality and to Social Structure.”In Family,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edited by Talcott Parsons and Robert F.The Bales.Free Press.
Parsons,Talcott.1959.“The Social Structure of the Family.”In The Family:Its Function and Destiny,edited by Ruth N.Anshen.Harper:241-273.
Phillips,Julie A.and Megan M.Sweeney.2006.“Can Differential Exposure to Risk Factors Explain Recent Racial and Ethnic Variation in Marital Disruption.”Social Science Research35(2):409-434.
Previti,Denise and Paul R.Amato.2003.“Why Stay Married?Rewards,Barriers,and Marital Stability.”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3):561-573.
Repak,Terry A.1995.Waiting on Washington:Central American Workers in the Nation’s Capital.Philadelphia,PA:Temple University Press.
Salgado de Snyder,V.Nelly.1993.“Family Life across the Border:Mexican Wives Left Behind.”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42(2):391-401.
Sayer,Liana C.and Suzanne M.Bianchi.2000.“Women’s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the Probability of Divorce:A Review and Reexamination.”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1(7):906-943.
South,Scott J.2001.“Time-Dependent Effects of Wives’Employment on Marital Diss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6(2):226-245.
South,Scott J.and Glenna Spitze.1986.“Determinants of Divorce over the Life Course.”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51(4):583-590.
South,Scott J.,Katherine Trent,and Yang Shen.2001.“Changing Partners:Toward a Macrostructural-Opportunity Theory of Marital Dissolution.”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63(3):743-754.
South,Scott J.and Kim M.Lloyd.1995.“Spousal Alternatives and Marital Dissolu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60(1):21-35.
Thibaut,John W.and H.H.Kelley.1959.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roups.New York:Wiley.
Zontini,Elisabetta.2010.Transnational Families,Migration and Gender,Moroccan,and Filipino Women in Bologna and Barcelona.New York:Berghahn Books.
Migration Pattern and Marriage Instability among Migrant Workers:From a Gender and Cohort Perspective
LI Weidong
Abstract:The data for this study come from “Social Integration,Marriage and Family Survey in Guangzhou”in 2016.The study investigates the influence of migration pattern on marriage stability among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nder and cohort.The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cohort and gender differences in marriage stability among migrant workers with younger generation exhibiting higher instability than older generation,females than their male counterparts,and female young generation scoring the highest in marriage break up. Migration pattern has significant effects on marital instability but the impact differs in gender and cohort.Marriages of the firstgeneration migrants appear to be little affected by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Nevertheless,migration without spouse seems to have some impact on the marriage stability of first-generation female migrants butits most significant influence is on young female migrants.Both mediation and moderation analysis show that between migration with or without spouse,marital satisfaction acts as a mediation variable among female young generation but as a moderation variable among all male migrants.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rovincial migration and marriage stability,marital satisfaction has moderating effect among all female migrant workers but not male migrants.This study shows that migration pattern exerts significant but different influences on marriage stability among migrants of different gender and cohort.
Keywords:marriage stability,migrant worker,population migration,gender,cohort
*作者:李卫东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Author:LI Weidong,Department of Sociology,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Government,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E-mail:lwd@snnu.edu.cn
**本研究受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RK037)资助。[This research is supported by National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No.19BRK037).]
感谢吴愈晓、赵延东、洪岩璧、程诚等诸位师友和《社会》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意见。文责自负。
责任编辑:张 军
标签:农民工论文; 婚姻论文; 稳定性论文; 新生代论文; 性别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2019年第6期论文; 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9BRK037)资助论文; 陕西师范大学哲学与政府管理学院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