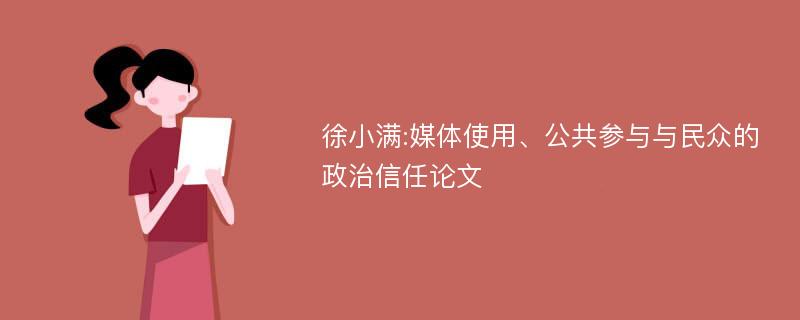
摘要:政治信任源于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互动, 它涉及公民、政府与特定价值之间的特定关系,是构建执政合法性和政策有效性的政治心理基础。本研究基于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主观”数据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间的“客观”数据,从多层次上探讨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媒体使用、公共参与与民众政治信任的关系。研究发现,在个体层次上,社会信任、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和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在国家层次上,固定宽带使用率、互联网用户数量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影响,公共参与则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
关键词:互联网;传统媒体;公共参与;政治信任
政治信任又称政府信任,它一方面可以反映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认可度,体现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意愿,这将影响政府政策施行的有效性。而信任危机的出现,往往源于政府无法有效回应公众的信任和期待,这将导致政府和公众信任关系的断裂,甚至会引发“治理危机”。本研究通过使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主观”数据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间的“客观”数据,从个体和国家两个层面上探讨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因素,尤其关注媒体使用、公共参与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试图揭示各国民众政治信任程度的差异和共性,以及其背后的共同影响因素。
一、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设
政治信任通常被定义为公民对政府或政治系统将运作产出与他们的期待相一致的结果的信念或信心[1],既可以表现为民众对政府等国家机构或者某一政党的态度和期待,也可以表现为民众对某一领导人的看法和判断。不论是在政治学领域还是在社会学领域,政治信任的议题一直备受关注。由于政治信任的生成机制涵盖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广阔的进程,存在多种可能的影响因素,因此,究竟“哪些因素会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该因素的影响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等问题就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焦点。
(一)政治信任机制中的媒体因素
个体的政治信任会受到政治信息的影响,只有了解个体的政治信任是如何受到政治信息影响的,才能理解信任的形成或变化。在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公众被信息重重包围,高度依赖媒体,媒体是现代公众获取政治信息的重要途径。这就使得“民众关于政府官员能力与诚意的信念不来自直接经验,而由新闻记者来告知”[2]。公众需要依赖媒体提供的消息、意见,适时地修正自己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所以媒体内容以及公众对于媒体的使用会影响其政治信任[3]。
传媒与政治信任之关系的探讨源于西方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媒体抑郁症”(media malaise)理论,即新闻媒体主要传播的是负面消息,从而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负面的影响。在新闻的产生过程中,为获得发行量或收视率,记者往往对能引起轰动的政治人物或事件(特别是政治丑闻、贪污腐败)“高度再现”,而对常规政治“低度再现”。作为持续接触和使用媒体的结果,公众往往对现实政治环境产生“认知错位”,对现实政治形成更多的负面评价,导致政治信任下降[4]。由于(媒体)对各种腐败案例的广泛报道,公众会形成一种政府与官员都是不诚实的、从而根本不值得信任的观念[5]。史天健等对中国社会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新闻媒体对于公众的政治信任有负面影响,使得公众并不信任政府[6]。还有学者认为,电视媒体具有负面的和反政府的特性,强化了政治冷漠,对电视的依赖性越大,便对政府越疏远[7]。
徐穆实打破了中文冗长分散的句子结构拆分成短小部分,结合直译方法将具有浓重宗教仪式感的风葬习俗展现给西方读者。最后,徐穆实采用“The Last Quarter of the Moon”的意译形式的标题获得了良好的“译后”翻译效果。一些研究者评论道,正是徐穆实和出版机构共同的努力才使得英译本《右岸》在欧美主流世界俘获口碑[6]。
虽然诸多研究者支持媒体的使用会导致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下降的这一说法,但是在后续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认为传媒在民众的政治信任中扮演了正面的、积极的作用。王正祥的研究表明阅读报刊对于大学生政治信任有着积极影响[8]。祝建华的研究显示,媒体在政治动员和教育民众方面具有强大效果,对维持公众的高政治信任具有积极意义[9]。国外也有研究者指出媒体有助于提升民众的政治兴趣和政治知识[10]。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出现,不仅为民众提供了表达思想的空间,更为民众增添了获取多元信息的渠道。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相比,更具有自主性和开放性等特点,正日益成为重要的政治信息传播、表达、互动和参与渠道。有学者认为,网络可以促进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合理化,可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11]。但是Kaid在研究选民对候选人的信任时发现,对另类政治资讯的使用会进一步降低选民对候选人的信任[12]。在我国,以网络揭黑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舆论监督形成的公共舆论“倒逼”政府,使党和政府的形象受损[13]。网络对负面新闻的报道负面影响社会公众的政治信任感[14]。
大数据时代,风险与便利是并存的。对于企业来说,大数据的应用为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风险。因为在这个信息共享的时代,信息泄漏问题也是不容小觑的,如果企业内部被不法分子盗取遭到泄漏,那么对企业来说这些危害就是致命的,重则会影响企业的发展。
关于媒体与政治信任关系的研究到目前为止仍没有获得统一的结论,甚至因研究对象、地区、时间等的不同,出现了相异的研究结果,尚需进一步的研究来予以检验。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假设:
耕地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重要资源,其所面临的土壤安全问题急需解决。对此,贵州开磷化肥有限责任公司农化中心主任田树刚表示,全球面临着与土壤相关的水资源紧张、环境污染、气侯变化、能源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退化等多种问题,而土壤本身也面临着退化、污染等问题。高强度不合理的农用化学品的投入是造成土壤及环境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不合理的肥料添加也为土壤带来了严重的危害,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肥料产业各方的共同努力。
层二方程:β0j=γ00+γ01W1j+γ02W2j+ …… +γ0mWmj+u0j
假设1: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政治信任度越低。
假设2:一个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越多,该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低。
(二)公共参与和政治信任
公共参与行为可以分为制度化参与和非制度化参与两种类型。制度化的公共参与包括常规的政治活动和社会组织参与,例如选举、参与社会团体等,非制度化的公共参与形式则主要是社会运动。
现有的有关于政治信任的研究多是将民众的团体活动和社团参与纳入社会资本的范畴来进行考量。在帕特南关于意大利社团生活和治理的著名研究中,社会资本被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 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 即它们通过促进协调行动, 能提高社会的效率”[15]。社团组织的繁衍一直被学界和政府视为产生社会资本的一种方式,当前国内学界也极力推崇社团组织的创建和繁衍, 并认为其所创造的社会资本将能有助于改进治理水平和政府问责,从而增强民众的政治信任。根据胡荣等学者的研究,城市居民的社团参与会增强他们的政治信任[16]。但是有学者在检验韩国社会资本和政治信任之间的关系时发现, 参与社团活动、社会信任都与政治信任和选举活动并不相关[17]。尽管存在争论,研究者对公共参与与政治信任的正向关系持有肯定的态度,进而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一个地区民众的公共参与对该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具有正向的影响。
二、数据来源、变量处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2010年至2013年进行的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The World Values Survey,WVS)和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世界价值观调查是由密歇根大学英格尔哈特教授主持的长期调查项目。目前该项目在世界范围内已进行了六波调查。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涉及了全球52个国家和地区,共收集了7万多个样本。根据研究的需要,本研究从总体样本中随机抽取了14个国家[注]随机抽取的14个国家包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中国、韩国、印度,美洲的美国、墨西哥、秘鲁,欧洲的德国、俄罗斯、瑞士,非洲的加纳、尼日尼亚、厄瓜多尔。,每个国家各200个,共计2800个样本,其中有效样本为2772个。借助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我们能够在个体与国家层次上分析公众的政治信任度及其相关影响因素。
(二)变量处理
1.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民众的政治信任。来自于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受访者对法院、军队、公安部门、中央政府、政党、国会、行政机关等国家正式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的均值。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4个等级:“完全不信任”、“比较不信任”、“比较信任”和“完全信任”,并由低到高分别赋值1至4分。
参考郑陆的动物训练模型[6] ,运动组动物均进行一次性力竭离心运动(持续下坡跑),依次进行第I级负荷(0°,8.2m/min)15min(相当于53%VO2max)、第II级负荷(-5°,15m/min)15min(相当于64%VO2max)、第III级负荷(-10°,19.3m/min)(相当于76%VO2max)直至力竭。力竭标准为长时间运动后,大鼠趴伏于跑台上,在驱赶下也不能进行移动。
2.自变量
个体层次。主要使用以下变量:(1)传统媒体的使用频率。来源于问卷中要求受访者回答报纸、杂志、电视新闻和电台新闻的使用频率。答案根据李克特量表设计成5个等级:“从不”、“少于每月一次”、“每月”、“每周”和“每天”,分别赋值1至5分。计算每位受访者四个题项的均值。(2)社会信任。来源于问卷中“您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值得信任的,还是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这一题项。本研究中将回答“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归为“信任”,将回答“越小心越好”归为不信任(0=不信任,1=信任)。(3)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要求受访者对家庭财政状况打分,范围从1分到10分,1分代表完全不满意,10分代表完全满意。(4)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1=完全不感兴趣,2=不是很感兴趣,3=有一点感兴趣,4=非常感兴趣。
本研究采用HLM7.0学生版统计软件进行两层的HLM分析,采用FEML( Full maximum likelihood)法估计模型中的回归系数参数和方差。具体结果如下:
不会参与
不会参与)]/n
最后,在种子处理之后要进行播种和分苗。7月下旬将催好芽的砧木种子均匀播入苗床,把装好营养土的营养袋入畦[1]。当砧木苗铜钱大小时移到营养袋,接穗8月中旬播种,2叶1心时分苗,之后进行嫁接。在嫁接时,一般选择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之间,当砧木长有5片真叶,接穗长有3片真叶时为嫁接适期。在前一天下午给茄苗消毒,采用劈接法嫁接。
均值结果模型可以对层二的国家变量进行单因素检验和初步筛选。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除移动电话租用数量[β=-0.006,S.E.=0.003,t(df)=-1.739(9),p=0.108]与民众的政治信任度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外,其余所有国家变量都与因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不同的是固定宽带使用率[β=-0.049,S.E.=0.014,t(df)= -3.371(9),p<0.01]、互联网用户数量[β=-0.022,S.E.=0.007,t(df)= -3.218(9),p<0.01]对因变量的影响是负向的,而公共参与 [β=8.541,S.E.=2.213,t(df)=3.847(9),p<0.01]对因变量的影响是正向的。
表1变量情况的描述性统计
层一变量样本数%层二变量均值标准差社会信任不信任183465.90固定宽带使用率16.4613.81信任95134.1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完全不感兴趣53119.00互联网用户数量(每百人)52.5727.52不是很感兴趣89432.00有一点感兴趣98435.20移动蜂窝式无线通讯系统的电话租用(每百人)98.0123.25非常感兴趣38713.80均值标准差公共参与结构指数0.00750.18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6.282.40传统媒体使用频率3.640.85
(三)研究方法
传统线性模型(OLS) 的基本假设是线性、正态、方差齐性以及独立性。然而,现实生活中很多问题大多体现出多层次、嵌套式的数据结构,多层次模型( 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则能很好地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非独立数据。除此之外,多层次模型还能有效连接宏观区域数据和个体数据,并明确区分个人效应和组效应。就本研究而言,不同国家的数据可以假设相互独立, 但是同一国家的数据由于受相同国家层面变量的影响, 很难保证相互独立,因此需要采用多层次模型,以了解各水平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HLM在分析时,将传统回归分析中的误差分解为两部分, 其一是个体间差异带来的误差, 另一个是因隶属不同的国家而带来的误差。本研究以两层HLM作为分析模型,层一方程为个体层次, 层二方程为国家层次。具体设定为:
层一方程:Yij=β0j+β1jX1ij+β2jX2ij + …… + βnjXnij+rij
施复亮:《“五四”在杭州》,方建文,张鸣《百年春秋 二十世纪大事名人自述》,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第500页。
(4)聚类结果表明,一些欠发达地区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增幅较大,反而有些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创新效率增幅不高,是由于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总体创新能力较强的原因主要基于较大的研发投入,但是相比其他地区创新效率增幅并不明显;反而一些落后地区,尽管投入不高,但是单位创新产出效率相对要高,当然这与一个地区的创新基数也有很大关系。表明不管创新基础如何,都需要重视创新资源的优化利用,进一步提高创新产出效率。
β1j=γ10
β2j=γ20
……
βnj=γn0
农村公路的养护一直以来不被重视,其主要原因主要有2个:①农村公路的养护建设资金有限;②管理养护体制混乱. 在城市副中心的大力建设下,对于农村公路的权属首先要明确其管理单位,实行责任到头,避免管理混乱造成道路养护不及时;同时,对于有需求的农村公路应该及时进行相应的提级改造,争取养护资金,加强养护管理.
在层一方程中,Yij为受访者报告的政治信任度。模型左端显示的个体层次的主要变量Xnij为传统媒体使用频率、社会信任、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和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nj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rij为方程残差。在层二方程中,Wmj为国家层面变量,如固定宽带使用率、公共参与结构等。γ0m为二层次变量的回归系数,u0j为二层次方程残差。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1.政治信任的个体差异
在对样本进行描述性统计时发现,受访者对法院、军队、公安部门、中央政府、政党、国会、行政机关等国家正式机构的信任程度评价的均值大于等于3的比例为26.5%,即仅有26.5%的受访者拥有较高的政治信任,绝大多数受访者的政治信任度较低。
以笔者所在省市为例,植保无人机购买主体相对分散,且多集中于合作社、农机大户和农场等,并非专业性植保组织。而在生产企业培训期间,该类农户虽取得相应的合格证书,但因经验少、作业效率低等问题,使之难以掌握相关灾害防控能力,更谈不上无人机在农业植保中的充分应用。
3.均值结果模型
样本的政治信任平均水平为2.49,居于比较信任与比较不信任之间。图1显示,各个国家民众的政治信任平均水平差异非常明显(原点取值为样本总体的平均水平)。政治信任得分均值最高的国家是中国,为3.22;最低的国家是秘鲁,均值为1.71。其他12个国家的政治信任均值均在2-3之间。
图1 14个国家政治信任均值分布图
(二)多层次分析结果
国家层次。本研究对国家层次预测变量的操作化包括:(1)互联网使用效应。我们选取了两个指标来衡量互联网使用效应,一是固定宽带使用率,二是互联网用户数量(每百人)。数据采用的是世界银行发布的2010-2012年国家统计数据的均值。(2)移动通讯设备使用效应。选取的指标是移动蜂窝式无线通讯系统的电话租用(每百人),同样也是使用2010-2012年国家数据的均值。(3)公共参与。这一概念的测量指标来源于对2010-2012年间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各国情况的汇总。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四种集体行动分别为“受访者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抵制活动、参加示威集会和参加罢工”。问卷询问了他们的参与情况,包括“参加过”、“想(可能)参加”、“不会参加”三种类型。本研究按照陈福平在《社交网络:技术vs.社会——基于社交网络使用的跨国数据》中所使用的方法,通过计算三类人群的比例衡量其实际动员、潜在动员和反对结构;利用I和In所示公式,对四种集体行动的参与水平进行了分项和综合衡量[18]。具体操作化方式如下[注]假定两个国家回答“参与过”、“想参与”和“不会参与”的比例分别是10%、20%、70%和20%、40%、40%。如果仅以参与过/想参与的结果来反映社会运动水平,这两个国家的水平是相等的。然而这就忽视了回答不会参与的70%和40%的差异。基于此,设计了这一指标的测算公式(陈福平,2013)。:
1.零模型
“厚葬”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行为,无异于埋金于下而书表其上,“丰财厚葬以启奸心”,难怪乎棺椁被毁、形骸曝露,被人剥臂捋环、扪肠求珠,以财招掘、自取其辱。“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皇甫谧的振聋发聩之声,不知被多少人记住?
零模型是HLM模型分析的第一步,模型中没有加入任何自变量。它的作用在于考察因变量是否存在显著的层间差异,是否有必要进行分层分析。从零模型统计分析中发现,模型的组间方差为0.124,组内方差为0.325,由此计算出ICC(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的值为0.2762,该结果表明约有27.6%的误差变异来自于第二层变量,即来自于国家层次,因此需要使用多层次模型。
2.随机系数模型
在零模型的层一方程中纳入个体层次的自变量, 结果(如表2所示)发现:社会信任[β=0.141,S.E.=0.030,t(df)=4.629(2754),p<0.01]、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β=0.022,S.E.=0.007,t(df)=2.969(2754),p<0.01]、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0.090,S.E.=0.021,t(df)=4.277(2754),p<0.01]与传统媒体使用频率[β=0.056,S.E.=0.014,t(df)=4.068(2754),p<0.01]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度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这些变量均需放入条件模型中进行进一步检验。
2.政治信任的国家间差异
钨钼矿石建造的钼矿床矿体形态为大的巨型块体,就像草帽状扣在花岗斑岩岩株的顶部,这些矿床的资源量往往非常巨大,钨钼总量常常大于几十万吨,其矿床品位在0.03%~0.15%之间,矿床中偶尔也会有较大的石英脉状矿体产出,但脉状矿体独立工业意义不大,个别矿脉有时可达1 万~2万t,品位达0.5%~1.0%。
4.背景模型
背景模型的目的在于考察有统计控制的情况下,层一和层二变量对因变量政治信任度的综合影响的显著程度。表2 各列分别显示了零模型、随机系数模型、均值结果模型以及背景模型的统计结果。通过随机系数模型和条件模型的对比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出加入国家变量后,方程截距、个体变量的斜率及显著程度的变化情况。
表2显示,背景模型的AIC、BIC和CAIC均小于其他三个模型,说明背景模型的拟合度要好于零模型、随机系数模型和均值结果模型。
在背景模型中,社会信任[β=0.143,S.E.=0.030,t(df)=4.735(2754),p<0.01]对民众政治信任程度的影响是显著的。社会信任的系数为正数,说明对社会上大多数人表示信任的民众要比表示不信任的民众具有更高的政治信任。社会信任即普遍信任, 是指对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程度。它往往被认为是预测政治信任的一项重要指标,因此本研究也将其纳入了考量范围。在文化主义的解释范式中,政治信任被认为和社会信任一样,产生于人际信任。根据这个视角,社会上的人相互合作、相互信任的信念是具有政治后果的,即增进了人们的民主取向。当一个社会缺乏必要的社会信任时,会造成政治信任的流失,甚至会导致政权的不稳定。本研究得出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观点,即民众的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存在着正相关。
郭永旺:农药的应用为农业的增产增收起到了重要作用,它帮助人类解决了饥荒和贫困,丰富了农产品的种类,把农民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与社会信任的作用方向类似,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β=0.022,S.E.=0.007,t(df)=2.883(2754),p<0.01]对于政治信任的影响同样显著。随机系数模型和背景模型均显示出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与政治信任呈正相关关系。民众对家庭财政状况的满意度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民众对自身生活状况的满意程度,另一方面也能体现出其对政府绩效的认可。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到依法行政、贫富差距改善、稳定社会治安,小到社区配套设施建设、提供就业岗位,都能体现出政府的办事能力和管理效率。因此,可以说政府绩效就是政府能力的体现。一个有能力的政府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才能保障民众的生活,也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0.090,S.E.=0.021,t(df)=4.282(2754),p<0.01]与政治信任也具有正相关的关系,民众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越高,其政治信任也就越高。这说明提高民众的政治信任可以从培养政治兴趣入手。民众对政治感兴趣,就会关心政治问题和政府的作为,就会积极地参政议政。而这也会督促政府积极地开展工作,并做到工作的公开化和透明化,从而使民众越来越满意政府的工作,越来越信任政府;政府为民众提供了更多参政议政的途径,也更有了工作动力。这无疑是一种良性循环的“共赢”状态。
媒体使用和政治信任的关系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媒体为政治信息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并为民众评价政府提供了依据。在背景模型中,有三个变量代表了媒体使用这一因素,一个是个体层次的传统媒体使用频率,另两个是国家层次的固定宽带使用率和互联网用户数量。其中,个体层次的变量传统媒体使用频率[β=0.057,S.E.=0.014,t(df)=4.154(2754),p<0.01]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正向的,而国家层次的两个变量固定宽带使用率[β=-0.046,S.E.=0.014,t(df)=-3.291(9),p<0.01]和互联网用户数量[β=-0.023,S.E.=0.007,t(df)=-3.048(9),p<0.01]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却是负向的。究其原因,传媒可以直接或间接地改变人们的认知,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往往被认为是政府机构在政治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延伸,虽然它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但这种由商业化、市场化和产业化带来的“新闻自由”被认为是一种“消极自由”,这种自由仅能落实于非政治领域[19]。传统媒体更多的是传播主流文化、主流价值观和声音,更多的是宣传一种“正能量”。和传统媒体不同的是,互联网为民众获取多元的信息提供了渠道,已成为民众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点的重要平台。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不乏基于正义感的网民发布政治信息、评论时事政治、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但也有一些网民基于好玩或跟风心态参与网络反腐和政治传播,或者只是为了宣泄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失落。由于网络具有虚拟性、匿名性和开放性等特征,传播速度快、信息量大,用户也不用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这就导致互联网上充斥着挑战与质疑官方的声音,成为了社会情绪的宣泄窗口。特别是遇到一些突发事件,传统媒体往往没有及时公开信息,民众就希望通过网络来弄清事情的真相,结果导致谣言滋生,使得民众对政府愈发质疑与不满。互联网对民众的权威主义认同产生了负向影响,削弱了政治信任的文化基础。除此之外,宽带覆盖率高、网民比例多的国家多是西方发达国家,和正在走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他们已经进入了民主化巩固的阶段,互联网不仅仅是获取信息、表达意见的渠道,更是公民社会组织进行资源动员的手段与工具。民众的民主意识高,对政府也有着更高的要求与期待。因此,模型的结果否定了假设1,验证了假设2,即传统媒体使用频率越高的民众,政治信任度越高;一个地区的互联网用户数量越多,该地区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低。
公共参与是本研究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在背景模型中,公共参与[β=7.356,S.E.=2.232,t(df)=3.450(9),p<0.01]对政治信任呈现出正向影响。本研究中的公共参与包括在请愿书上签名、参加抵制活动、参加示威集会和参加罢工四种集体活动,并用公式对四种集体活动的参与水平进行了综合衡量。模型结果表明,一个国家民众的公共参与水平促进了政治信任,即该国整体的公共参与水平越高,民众个体对政治的信任程度也越高。本研究提出的假设3得以验证。公共参与是通过计算某国家民众“参加过”、“想(可能)参加”、“不会参加”四种集体活动的比例得出的,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公共参与水平。该值越高一方面可以说明民众的政治参与度高,另一方面也从侧面体现出该国的政治民主程度高,正因为拥有较高的民主化程度,才会允许社会集体行动合理、合法地存在。通过参与集体行动,民众向政府表达了自身诉求,也让政府了解到民众关心的是什么,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以满足其需要,民众也因此更信任政府。
表2模型结果汇总
空模型随机系数模型均值结果模型背景模型固定效应Coefficient (SE)t(df)Coefficient (SE)t(df)Coefficient (SE)t(df)Coefficient (SE)t(df)截距(β0)β002.493∗∗∗(0.095)26.353(13)1.881∗∗∗(0.092)20.395(13)3.418∗∗∗(0.397)8.615(9)2.851∗∗∗(0.370)7.697(9)固定宽带使用率,γ01-0.049∗∗∗(0.015)-3.371(9)-0.046∗∗∗(0.014)-3.291(9)互联网用户数量,γ02-0.022∗∗∗(0.007)-3.218(9)-0.023∗∗∗(0.007)-3.408(9)移动电话租用数量,γ03-0.006(0.004)-1.787(9)-0.006(0.003)-1.739(9)公共参与结构,γ048.514∗∗∗(2.213)3.847(9)7.356∗∗∗(2.232)3.450(9)社会信任(γ1)γ100.141∗∗∗(0.030)4.629(2754)0.143∗∗∗(0.030)4.735(2754)家庭财政状况满意度(β2)γ200.022∗∗∗(0.007)2.969(2754)0.022∗∗∗(0.007)2.883(2754)对政治感兴趣的程度(β3)γ300.090∗∗∗(0.021)4.277(2754)0.090∗∗∗(0.021)4.282(2754)传统媒体使用频率(β4)γ400.056∗∗∗(0.014)4.068(2754)0.057∗∗∗(0.014)4.154(2754)随机效应Variance(df)χ2Variance(df)χ2Variance(df)χ2Variance(df)χ2γoo0.124(13)1064.672∗∗∗0.109(13)994.761∗∗∗0.069(9)598.230∗∗∗0.060(9)560.399∗∗∗σ20.3250.3060.3250.206层一样本量2772277227722772层二样本量14141414AIC4819.574657.784819.464557.74AIC4837.364699.294860.974622.97CAIC4840.364706.294867.974633.97
资料注:* p<0.1, ** p<0.05,*** p<0.01
表2还显示,残差方差已经由零模型的0.325下降到了背景模型的0.206。从这两个数据计算出方差的削减比例为36.62%。这说明,在加入个体层次变量和国家层次变量之后,有36.62 %的残差方差已经被解释掉。从国家层次变量对政治信任的解释程度来看,残差方差由随机系数模型的0.306下降到了背景模型0.206。因此,固定宽带使用率、互联网用户数量、移动电话租用数量以及公共参与等几个变量解释了政治信任国家差异的32.68%。
四、结论与讨论
利用第六波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主观”数据与世界银行发布的国家间的“客观”数据,通过建立多层次模型,可以获得以下几点结论与思考。
其一,从总体上来说,绝大多数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较低,且民众的政治信任存在国家间的显著差异。民众偏低的政治信任以及背后隐藏的原因应该引起学者和政府的重视。因为只有民众信任政府,政府的各项工作才能顺利地开展和落实,国家才能稳步、健康地发展。
其二,从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来看,传统媒体的使用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正向影响,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程度对于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影响。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如何应对互联网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已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现实问题。互联网已成为民众获取信息、表达观点的重要场域,只有合理地予以引导和利用,才能够减弱其对政治信任的负面影响,乃至将负面影响转化为正面影响。为此,从政府角度来说,一方面政府需要净化互联网环境,规范互联网秩序;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加强信息公开,特别是在遇到突发事件时,要及时向民众公布信息,这样民众才不会相信网络上的所谓“小道消息”。而从民众自身来说,一方面要规范自身行为,不随意发布、传播有关国家或政府的虚假消息;另一方面,要有辨识能力,不随便相信网络上的虚假消息和负面言论。
第四阶段(1998年—2012年),快速增长阶段。以1998年全省第一次个私经济工作会议的召开为标志,云南省范围内掀起了非公经济发展热潮。2000年,出台了43条支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同时外省特别是沿海地区很多投资者到云南投资兴业。这期间催生了大批知名民营企业,如祥云飞龙、云南锗业、昊龙实业、俊发集团、南磷集团、龙润药业、一心堂、沃森生物等,2000年全省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为21%,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纳入统计范围,并对各级各部门工作进行目标考核。同时,随着住房改革的推进,房地产业、旅游业成为省内投资者投资云南的热门领域。
其三,就公共参与和政治信任的关系而言,一个国家民众的公共参与对该国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当前,世界各国的大多数政府对社会集体行动都是持有中立或是压制的态度,认为集体行动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甚至会导致政权的颠覆。然而本研究却表明,公共参与水平越高的国家,民众的政治信任程度越高。这是因为社会集体行动是民众参与政治、表达诉求的重要渠道,也是政府了解民众所思所想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不能“谈集体行动色变”,而是要引导社会集体行动合理且合法地开展,并及时解决民众的诉求。
参考文献:
[1]舒全峰.基层民主、公共领导力与政治信任——基于CIRS百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17(4):71-81.
[2]Cappella,J.N.,Jamieson,K.H.Spiral of Cynicism:The Press and the Public Good[M].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3]牛静.传媒及政治信任关系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国际新闻界,2012(1):54-59.
[4]张明新,刘伟.互联网的政治性使用与我国公众的政治信任——一项经验性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14(1):90-103.
[5]柯红波.腐败与公众信任———基于政府官员的调查与解读[J].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学报,2009(6):72-78.
[6]Xueyi Chen, Tianjian Shi.Media Effects on Political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ost Tiananmen Period.”East Asia,2001(4):84-118.
[7]卢春龙,严挺.政治传播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以中国农民的政治信任为考察对象[J].学习与探索,2015(12):48-56.
[8]王正祥.传媒对大学生政治信任和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J].青年研究,2009(2):64-73.
[9]祝建华.文传播研究之理论化与本土化:以受众及媒介效果的整合理论为例[J].新闻学研究,2001(6):1-21.
[10]Norris,The Virtuous Circle:Political Communication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M].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
[11]漆国生,王琳.网络参与对公共政策公信力提升的影响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0(7):21-23.
[12]Kaid,L.L.Effects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in the 2000 presidential campaign:Comparing traditional media and Internet exposure[J].Th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2003(46):677-691.
[13]李异平,袁娜.试论网络舆情事件与政治信任的构建[J].东南传播,2010(6):25-27.
[14]齐正发,郝宇青.大学生政治信任状况实证研究[J].江淮论坛,2012(3):85-89.
[15]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M].王列,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
[16]胡荣,胡康,温莹莹.社会资本、政府绩效与城市居民对政府的信任[J].社会学研究,2011(1):96-117.
[17]Ji Young Kim.Bow ling Together Isn’t a Cure All: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apital and Political Trust in South Korea[J].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2005(2):41-52.
[18]陈福平.社交网络:技术vs.社会——基于社交网络使用的跨国数据[J].社会学研究,2013(6):72-94.
[19]李金铨.超越西方霸权:传媒与文化中国的现代性[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MediaUse,PublicParticipationandthePoliticalTrustofCivilians
XU Xiao-man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hu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Hefei 230051, China)
Abstract:Political trust is an interaction between people and governments. It involves a specific relationship between citizens, government and particular values, and it is the political and psychological foundation for constructing the legitimacy of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policies. By using the “subjective” data of the Sixth Wave World Values Survey and the “objective” data between the countries published by the World Bank to explore at multiple level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especiall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 use,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and people’s political trust. The study found that,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social trust, family financial satisfaction, the degree of interest in politics, and the frequency of traditional media use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at the national level, fixed broadband usage and the number of Internet user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and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political trust.
Keywords:Internet; traditional media;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ucture; political trust
DOI:10.16614/j.gznuj.skb.2019.02.005
收稿日期:2018-12-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警察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研究”(17ASH0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徐小满(1991—),女,安徽巢湖人,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实习员,博士。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农村社会学。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9)02-0039-09
责任编辑 彭国胜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政治论文; 民众论文; 模型论文; 国家论文; 互联网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与民族论文; 国家与人民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警察信任与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研究”(17ASH005)论文;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