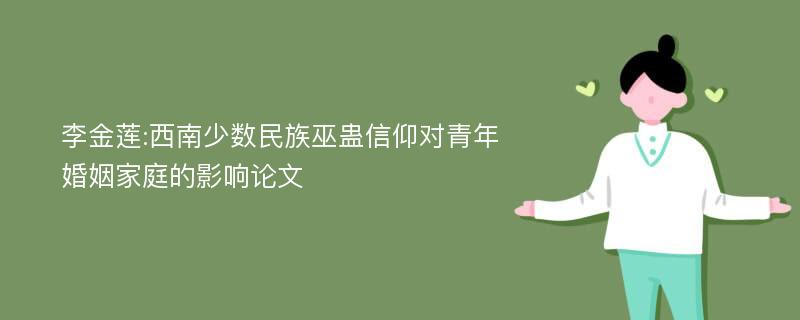
摘要: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着巫蛊信仰,该信仰对少数民族最首要最严重的影响便是婚姻家庭。由于“蛊”具有传女不传男和传染性,所以被认为会放蛊的女子和家庭成员(无论男女)都无法正常婚配,已婚配的则婚姻破裂或解除婚约。只能与同样会放蛊的人家里进行婚配,或者与贫穷、有缺陷的人通婚。为了反抗这一信仰的迫害,有的青年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由于国家法的震慑作用,“放蛊”观念被限定在隐形的状态。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巫蛊信仰对人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巫蛊信仰;婚姻家庭;负面影响
西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巫蛊信仰,该信仰在少数民族中有着各种不同的称呼。云南省盈江、陇川、瑞丽、潞西等地的傣族叫“琵琶鬼”(“枇杷鬼”“皮拍鬼”)。“琵琶”是傣语魔鬼附身的意思,魔鬼附身,就会随时咬人或牲畜。景颇族叫“扑死鬼”“阿皮鬼”(阿枇鬼)。爱尼人叫“皮抽”,一种喜吃死尸上的肉,常披着兽皮进入人家伤害病人的鬼。阿昌族叫“放歹”,“歹”是指特殊的人。认为这种人依附着魔鬼,会暗暗的伤害人畜。白族叫“养药鬼”或“撒魂鬼的女子”。楚雄高峰乡的彝族叫“使鬼”“放蛊”“放歹”“养药(王)”等,彝话称“诺其渣”,“诺其”义“药”,“渣”义“有”,直译为“有药”,意译为“养药”或“养药王”。贵州布依族把未婚先孕或者有婚外性行为的女性称作“毒c”(音译)。“毒c”是一种妖魔,会对好人放蛊。贵州省凯里市的炉山和黄平县称为“老虎鬼”。在雷山县南部的一些短裙苗族地方称“蛊”为“有药”“酿鬼的女子”。在台江县中部“蛊”的苗语发音为“家缺”。
一、少数民族的巫蛊信仰
据说每个寨子都有蛊。据西双版纳曼迈乡20世纪70年代末统计,全乡十一个寨子都有“琵琶鬼”,有66 人被人们认为是“琵琶鬼”,其中雇农10人,贫农 23 人,下中农 17 人,中农 10 人,上中农 4人,小商人1人,贫下中农占75.8%。曼乱典寨有40个农民认为是琵琶鬼[1]。1985年盈江县统战部宗教科统计:德宏州全州傣族寨子几乎每寨都有几户“皮拍鬼”,虽不公开讲,但大家心里明白。卡场乡19 个景颇寨,每寨都有“皮拍鬼”户;普关乡大寨共41 户,其中“皮拍鬼”就有11 户,占总户数26.83%;马鹿塘共6 户,其中“皮拍鬼”有3 户,占总户数50%;吾帕乡4 个景颇寨,有“皮拍鬼”13 户;丁林寨有7户“皮拍鬼”,占该寨总户数16.7%。[2]楚雄高峰乡大小树村的彝族村民用隐语称“养药的人家”为“浑水”。认为大约七八代前“浑水”淌进村,就越来越坏了。最初只有三户是“浑水”,现在有11 户,占全村户数的12.5%[3]198-199。黔东南的香鸽寨一共有47户,下等亲就有19户(其中10户被认为有鬼,2户被认为有蛊,7 户是鬼蛊兼具)[4]62。在云南的腾冲、梁河几乎每个阿昌族寨子都有一两户人家被说成会“放歹”。
虽然各地各民族巫蛊的名称有所不同,但总的特征就是,“蛊”有遗传性,会传子传孙,男女皆可为,但多数是传女不传男。所以,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描述中,“放蛊”的多是在任何方面看不出丝毫异象,姿容秀丽、劳动积极的女性。在有些地方,“蛊”还具有传染性,会通过结亲或亲近进行传染。楚雄高峰乡彝族认为万一不慎和养药人结亲沾边,那么世世代代都是浑水人。浑水人的后代永远是“浑水”,“清水”却会不慎通过血液相混变“浑水”。小树村的普×贤因家贫找不到媳妇,后找了个老姑娘,吃了定酒后才知其家是“浑水”,从此变成了“浑水”。[3]196-199黔东南苗族有“dliangb gel”或“jab”(酿鬼或老虎鬼)的人家的女儿出嫁时,它要跟着这个姑娘到夫家去,而夫家就有了“dliangb gel”或“jab”。有“dliangb gel”或“jab”人家的未婚男青年也如此,女孩只要嫁给他们,他们的子女及其亲戚也成了有“dliangb gel”或“jab”的人家,世世代代都要受到隔离和歧视。[4]41据说凯里舟溪苗族的“老虎鬼”还能随同姑娘到丈夫家去,谁要是娶有“老虎鬼”人家的姑娘了,他家就会有“老虎鬼”,就会遭人厌恨[5]。
根据饵料鱼不同的配套模式、设计单产量、上市季节等不同,翘嘴鳜“华康1号”养殖可分为饵料鱼专池饲养和饵料鱼、鳜鱼混养两种模式。它可以按照鳜鱼共性的技术标准、操作规范和生产流程进行养殖,诸如清塘、苗种消毒,或单一品种精养,或多品种立体混养或者轮捕轮放,饲料投喂,开展病害防治以及防灾减灾,同时该鱼养殖也有个性要求。
在现实生活中,巫蛊是没有办法“证实”的极为独特东西,看不到也摸不着,但它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少数民族的观念世界里。人们认为,会放蛊的人通过巫蛊任意作祟,招灾引祸,会使寨子发生瘟疫疾病等灾祸。会使别人身体致病,家庭失和,祸祟不断,因此受到村民的唾弃。在一些傣族、拉祜族地区,凡某家突然有人畜染疾、死亡或有人患病发高烧说胡话时便被说成是有“琵琶鬼”“扑死鬼”附身作祟。爱尼人认为“皮抽”依附到人身以后,本人并无知觉,但“鬼”可以通过她贻害他人。布依族谁肚子痛、头痛或者发烧,就认为是被“毒c”放蛊了,会对整个村寨产生不吉利的秽气。苗族地区地处偏僻山区,文化相当落后,卫生条件很差,人、畜病疫多,又缺医少药。一旦发病,就怀疑是某人“放鬼”,全村人即对被怀疑者进行报复,搞的村寨不得安宁。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关于蛊的观念基本上都是相似的,是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一种长期存在于人们思想中的观念,这些观念的一些残余基本上传承到现在。
巫蛊信仰对青年男女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深受其害最大的首先是婚姻家庭。巫蛊信仰使男女甚至终身难以婚配或婚姻破裂,倍受精神的折磨。一旦某女子被认定为放蛊或者经鬼师或巫师,或经神明判断为降灾于人的某种鬼时,就一定逃脱不了厄运,她们无法替自己辩解。放蛊或出自有放蛊的家庭在婚姻上会受到严重的歧视,必遭排斥。在炉山缔结婚约时,首先要探听对方家庭是否“清白”。所谓“清白”,指的是家中没有蛊,没有“老虎鬼”[6]。雷公山地区苗族聚居地方各家姑娘出嫁或儿子娶妻前都要对对方进行调查。黔东南的苗族如果遇上陌生的求婚团体,一般说来,都要经过一道不能明言的暗地手续——qaf khat(清客),看对方是否属于khat yut(小客)、hxiub khat yangf(坏亲戚)或者 ax hsab ngas(不干净)[7]。这些都是指有“鬼蛊”的人家,断然不可通婚。
二、巫蛊信仰对青年婚姻家庭的影响
(一)难以婚配
在问卷中怎样选择护士这个职业的调查,其结果显示有57.1%是通过父母选择的。因此推测可能是由于一年级的学生刚入校对于护士这个职业还比较懵懂,认识比较模糊。而通过在校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接触和学习,逐步对护理行业有更清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其整个认同度是逐渐增加的。但又发现四年级的同学认同度又回归到二年级的水平,可能是由于其邻近实习有实习焦虑或其他相关因素的影响。
在各村寨中,人们如果违反有关潜规则,与被认为有“蛊”或“酿鬼”的人家通婚,就会受到惩罚,被划入另类。30多年前,德宏自治州陇川县芒东小寨的许克容与一个姓毕的姑娘恋爱并准备结婚,但寨子里有人说这个姑娘“会放歹”。于是,遭到男家父母的反对而未能结成伴侣[8]102。虽然传说“蛊”传女不传男,但是其家人甚至与之联姻的人家或者与之有亲戚关系的人家都会受到牵连。在黄平非但被认为附有“酿鬼”的本人遭人排斥,连他的家属、亲戚,甚至朋友都受到连累,也被认为有“酿鬼”。被传为有“蛊”或“酿鬼”的人终身甚至后代或亲戚朋友都背上了沉重的包袱,精神上遭受痛苦。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只要传染了鬼蛊,即使至亲也要分道扬镳,纷纷向社会宣布自己与结婚当事人断绝关系,不但断送了很多本该成立的婚姻,也使一个完整的家庭四分五裂。假如一个女子嫁给了被认为有“蛊”或“酿鬼”的人家的儿子,她父母和兄弟会去男子家把女子拉回家,如果女子死活都不肯回家,那么,女子父母兄弟等家人会从此与她断绝关系,世世代代不相往来。假如被认为没有“蛊”或“酿鬼”的人家要讨一个被认为有“蛊”或“酿鬼”的人家的女儿,男方的父母会问女子以后还要不要和娘家人来往,只有表示不再来往,他们才同意女子和他们的儿子结婚。如果女子坚持与家人往来,他们的儿子还坚持与此女子结婚,那么,等女的娶回来,男方的父母便会马上与其子分家,还会被迫与父母、兄弟姐妹等断绝关系[13]。总之,由于与有巫蛊人家通婚或亲近的人会染上巫蛊,因此都是对她(他)们采取避而远之或断绝一切社会关系的态度。
巫蛊信仰不知道冤枉了多少青年,限制了他们应有的婚姻生活。傣族被认为是“琵琶鬼”的家庭子女禁忌与其他老百姓的子女结婚。女子如果到了二十岁以后,还找不到配偶,父母会为她焦急,当然她自己也着急,因为别人会在背后议论她,说她身上有“琵琶鬼”等等,以后就很难找到丈夫了。[9]盈江卡场公社的一个大队有12个女青年已达婚龄,因其家庭历史上被诬为“皮拍鬼”,有的已年过三十,但无人娶,有的感到在家乡无望,只好离开村寨,远走他乡[10]232。楚雄高峰乡现在11 户“浑水”的年轻人找对象十分艰难。一个谁也看不上的“清水”男人宁愿打光棍也不会娶一个如花似玉的“浑水”姑娘。普×会因为家贫,其子37 岁仍未找到媳妇。“浑水”送上门也不敢要,至今仍打光棍[3]198-199。黔东南剑河县岑松镇x 村有一人家在解放初期,家庭条件挺好,姑娘长得也出众,但不幸的是家中被传出有鬼。结果,姑娘想嫁无门,儿子想娶也没处娶,最后成了老姑娘、老后生[11]。
例如在进行《茉莉花》这首歌的教学时,笔者会重视学生主体地位在课堂中的体现。在教学开始时,先为学生讲述这首歌的一点故事,为下阶段教学的开展打好基础。接着要求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自主学习《茉莉花》,在相对自由和谐的课堂氛围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明显提升,同时因为有故事之间的铺垫,趣味性也得到了增强,有效地提高了教学质量。最终学生都能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完成音乐学习任务,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
被传为有“蛊”或“酿鬼”人家的青年难以成家,应有的婚姻生活受到了限制。人们通常的做法是,姑娘都不愿意嫁到被认为有“蛊”或“酿鬼”的人家里,男孩子也不愿意娶被认为有“蛊”或“酿鬼”的人家的女儿。黔东南苗族有“dliangb gel”或“jab”的人家的姑娘无论长得多么聪明漂亮,在婚姻上一定非常困难。有“dliangb gel”或“jab”人家的未婚男青年也如此,别的女孩也不愿嫁给他们。同样,被视为有“老虎鬼”的人家,不管女儿长得姿容如何秀丽,如何能干,但婚姻前途还是很暗淡的。景颇族人们都害怕与被指为“阿皮鬼”的人接触,不用说恋爱结婚了。父母为自己的儿子选姑娘,或者男儿自己去谈情说爱,必须注意所相的姑娘是否有“琵琶鬼”。爱尼人的“皮抽”也被人们排除在通婚范围之外[8]102。阿昌族绝对不能和有“歹”的人家通婚,也不会跟有披拍鬼的人家的子女结亲,婚配对象的选择必须要排除有巫蛊人家的子女。贵州和湖南的苗族忌与会放“蛊”“酿鬼”或有“老虎鬼”的人家结亲。雷公山地区苗族聚居地方不与被认为有“蛊”或“酿鬼”的家庭通婚,当地苗族村寨的共同点是,家庭是否“干净”,也就是是否被怀疑为有“蛊”或“酿鬼”是决定婚姻是否成立的必要条件。
(二)婚约解除或婚姻破裂
那些被认为不“干净”的、有“鬼蛊”的姑娘人家,往往远嫁他乡,即使自己品貌双全,也只能降低标准,嫁给品行不端、智力低下、五体不全、年龄差距过大或家境比自己较贫寒的男子。被认为有“鬼蛊”的男人,他们的遭遇也与蛊女相同,在情场上备受冷落,在婚姻上同样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些青年终身甚至给后代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精神上的痛苦可想而知。新中国成立前云南梁河勐科有个没结婚的阿昌族大姑娘被人说成会放歹,这个姑娘到30多岁了也嫁不出去,因为没有哪个小伙子敢沾惹她,实在无奈只能远嫁到腾冲山里的汉族人家。[12]有些青年一旦被群众认为家里不“干净”(有蛊),往往只能与其他被认为不“干净”的人家通婚,才能找到对象结婚。傣族被认为是“琵琶鬼”的家庭,其子女只能与另一“琵琶”家庭的子女结婚。曼乱典寨与曼允寨这两个“琵琶鬼”两寨只能互为婚嫁。一代又一代,都是如此。布依族“毒c”的子女只能和“毒c”通婚。由于“毒c”比较少,通常,“毒c”的子女往往找不到对象而独身一辈子,一家人就这样自生自灭。在黄平非但被认为附有“酿鬼”的本人和家属、亲戚,甚至朋友一般人都不愿和他们结婚。结果这些被另眼看待的人只好在自己的行列中互相通婚[15]。
按照式(5)的定义,图9和图10分别给出了r1为35 mm,r2为50 mm时,花岗岩中粒子速度的频率响应函数的实部和虚部随圆频率的变化曲线,并采用幅值按指数衰减的正弦振荡函数曲线进行了拟合,拟合结果一并在图中给出。拟合函数为
虽然有的青年会义无反顾地和“巫蛊”人家结亲,但结局往往很不好。或者私奔,有家不能回;或者迫于各种压力,最终离婚;甚至有的青年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2002年的冬月,黔东南香鸽寨的吴X 反对女儿嫁给巴屯寨勾X 的孙子,原因是勾X 家不干净(有鬼、有蛊)。两个年轻人为了结婚,寻找国家力量的支持,先到乡政府办了结婚证,然后私奔了。虽然如愿结婚,但从此却有家归不得了。贵州施秉县苗族有的人会被诬陷为会施行巫蛊的不干净的下等人。巴屯寨张X的女儿H与杨X的儿子N相好,但杨X家说张X家族亲戚是下等人,拒绝娶张X 的女儿为儿媳。最终,这对年轻人被双方家长赶出了家门,只好临时搭建一个草棚居住。随着社会压力越来越大,日子越过越艰难,三年后,俩人离婚,H 远嫁给了一个汉族男子[4]68-73。高峰乡一对彝族青年双双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都未能冲破巫蛊这条无形的婚姻界限。1993年,高峰乡××村彝族青年胡××与××村彝族女青年××英要求结婚。因为女方父母打听到胡家是“浑水”,坚决拒绝。最终,××英服敌敌畏身死。胡××知恋人身死,毫不犹豫,跳水而亡[3]197。
(三)婚姻圈子
即或由于不了解情况,和放蛊人家订婚之后,一旦有所发觉,也可以无条件解除婚约。若她们已成婚,则婚姻必定破裂,被丈夫逐出家门。梁河一带的阿昌族盛行拐婚的习俗,儿子把有歹人家的姑娘给拐来,父母知道后连家都不让进;自家的姑娘不听话跑去有歹的人家,爹妈被气病掉的情况也有。有些时候,有歹人家的儿子从外寨拐来的姑娘,还被姑娘家爹妈请人追回去,即使已经结婚了,事后女方家知道放歹的事情也容易闹离婚。如果女方会歹但在婚前不告诉男家,日后也会因此而闹离婚。在阿昌族村寨,据说夫妻二人有一个会放歹,就会经常吵架,关系不好。梁河关璋有一名老妇人是从墩欠那边嫁过来的,刚到寨子的时候,人们就流传说她会放歹。丈夫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一直和她吵闹,闹得她差点就要跳悬崖。老妇人的大儿子找不到媳妇,就由外婆做主,硬是把哥哥家的女儿弄来嫁给他,来了以后两个人吵了一阵子[12]。黔东南苗族如果男方家族属于“不干净”的人家,那么女方家族就会强硬地退婚,到男方家拉走他们的姑娘。如果女方家族估计强硬的退婚不成,可能会采取欺骗的手法——假意同意姑娘回门。在回门途中,女方家族突然拦截,抢走新娘,婚姻就此宣告解除[4]80。
云南景洪地区的曼允寨是第一个被贴上“琵琶鬼”标签的全民信仰基督教的村子。本寨15 户人家,来自十几个地方。这些被认为是“琵琶鬼”附身的村民不能再回村,与以前的村寨断绝关系,他们聚众居住,久而成村。曼乱典寨与曼允寨一起,被认作“琵琶鬼”寨。这两个“琵琶鬼”寨的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愿也不敢说明自己是那里人,否则马上就会招致巨大的灾难和不幸。他们的子女成年以后,也不敢到别的寨子去串姑娘或赶摆,更不能同别的寨子的人互通婚。“我们村里的小伙子到村上去找那些女孩,但是到结婚的时候真的很麻烦的,因为人家要调查,要了解。女孩如果嫁给这两个寨的男孩,家长就一直反对,要嫁过来就要断绝关系。以后过了几年,有的十多年才恢复关系的,家里人才承认她。因为我们被称为‘琵琶鬼',‘鬼'那是很恐怖的,所以家里的人就不允许姑娘嫁过来。”[14]因此,大多数青年都不会以个人的力量同自己的亲戚和整个村寨抗衡,和有蛊人家结亲就等于把自己孤立起来,所有的亲戚都不会承认这门亲事,自己还被划入另类备受歧视。虽然有些年轻人不相信有“放蛊”或“酿鬼”的问题,但大家都这样认为,只能随波逐流了。
在现实生活中,有的年轻人不信“蛊”也不怕“蛊”,执意要与会放蛊的人家结婚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在经历了青年人的反抗,各种限制已经阻止不了年轻人的勇气了,曼乱典寨和曼允寨这两个“琵琶鬼”寨的姑娘有嫁到大寨去的,也有大寨来“琵琶鬼”寨上门(招赘)的。康朗燕,曼回索人,爱上了“琵琶鬼”寨的姑娘,大家都劝他不要结婚,否则以今后不分给田相威胁,但康朗燕不顾一切,终于到“琵琶鬼”寨来上门了[10]232。过去,曼飞龙村与被认定为“琵琶鬼”寨里的村民通婚更为传统所不容。1986年,曼飞龙村一少女与“琵琶鬼”寨的男青年相爱,虽受到父母亲朋的强烈反对,但他们仍然结成百年之好[16]。雷山县有一种情况是,女方出落得比较漂亮,又两情相悦。即使明知女方为蛊家之女,男方也会不再顾忌而迎娶的,只是在婚礼的形式上做些改变,即不要明媒正娶,而是沿用本民族的“偷婚”形式[17]。
三、行政与司法干预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族工作队在少数民族地区也想尽了各种办法来改变这一风俗恶习,可是用了很多办法也没有改变过来。最终不得不身体力行,通过娶“琵琶鬼”为妻来向老百姓证明这些都是封建迷信。西双版纳勐捧儇尼寨子曼庄有个叫依丙的妇女,因为拒绝了头人儿子的逼婚,被诬为散播瘟疫的“琵琶鬼”驱出寨子。若她再进寨子,将面临被烧死的危险。为了躲避灾难,依丙带着女儿依章离乡背井,流落他乡。解放军来了,西双版纳解放了,仍没有一个寨子允许她们进寨住。1958年,漂泊了十年的依丙,虽然在大军的保护下可以进寨子居住了,但仍被寨子里的人视为不可接触的瘟神。眼看依章成年了,但她家的竹楼却没有小伙子来串门,她的婚恋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农场工作队发现这事后,动员小伙子去找依章,他们都坚决拒绝。在他们看来,串“琵琶鬼”的女儿就是跟死亡定亲。工作队说:“这是迷信啊!”小伙子说:“不相信?你们去拿(娶)看死不死人。”尽管各级党组织围绕这个问题开展了宣传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破除迷信的教育和动员活动,但农场小伙子依然没有一个乐意接受依章为妻。最终,依章看中了勐润农场一个叫吴道恒的生产队长,在“她妈已经是一个悲剧了,你要是再给我制造一个悲剧,我可饶不了你!”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压力之下,彝良的吴道恒娶了傣族“琵琶鬼”依章为妻[18]。在云南,很多支边子女成了少数民族的丈夫或媳妇,其中不乏与“琵琶鬼”联姻的。这些婚姻,一定程度改变着人们对“琵琶鬼”的认识和禁忌。
新中国建立以来,虽然不少地方政府都有禁止相关行为的规定,但并没有禁绝巫蛊信仰及相关的行为。早在土地改革时,政府便明令禁止赶“琵琶鬼”。1953年,中共保山地委发布《次要改革纲要》,其中明确规定:不准诬陷农民为“皮拍鬼”[2]29。针对历史上的“屁拍鬼”“猴子鬼”等不法活动抬头,导致农村地区出现大量严重侵害公民人身自由、生命安全和财产等违法犯罪现象,针对社会上存在以“琵琶鬼”“扑死鬼”为名侮辱、诽谤他人的不良行为和造成的社会影响,1986年3月29日,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县关于严禁撵“琵琶鬼”和残害双胎婴儿的决定》。1986年5月26日,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第七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禁止追“屁拍”(鬼)等封建迷信活动的通知》[19]。《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自治条例》第一章第十条规定:自治州的自治机关加强法制教育,依法禁止和取缔诽谤他人为“放歹”等违法行为[20]。虽然要禁绝这些民族习惯非常困难,但有了这些重要的规范性文件之后,自治县行政和司法机关在处理该类案件时有了重要的依据。在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有过与此类问题相关的婚姻案例,2006年曾有人到雷山县法院起诉离婚,其理由就是认为对方有“酿鬼”。由于“蛊”或“酿鬼”问题无法证明其存在的真伪,以事实为依据的国家司法自然不可能认可所谓“蛊”或“酿鬼”的理由[8]160。
创新驱动是指从个人创造力中获取发展动力,通过对知识产权进行充分利用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活动[1]。创新是推动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近几年,人们对高速公路的要求越来越高,工程管理作为提高高速公路建设质量的重要措施方法,也必须不断创新,从而更好地为高速公路建设提供服务。
时至今日,在这些少数民族的思想观念中,依然有“放蛊”或“酿鬼”的现象存在,“蛊”的问题依然神秘,认为有“蛊”的人用意念即可以害人,而且这种观念还会在较长的时间内存在。由于巫蛊信仰的这种神秘性和民族习惯的特殊性,很难用国家法消除其负面影响。但在国家法的震慑作用下,“放蛊”或“酿鬼”观念的危害被限定在隐形的状态,人们至少知道了“诬陷”与“诽谤”,慢慢了解了“罪”与“非罪”,至少不会轻易去伤害别人了。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放蛊”或“酿鬼”观念对人们的影响会越来越小。
参考文献:
[1]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编.西双版纳傣族小乘佛教及原始宗教的调查材料[Z].云南省历史研究所印刷,1979:66.
[2]张建章.德宏宗教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宗教志[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2:31.
[3]唐楚臣.从图腾到图案——彝族文化新论[M].芒市:德宏民族出版社,1996.
[4]刘锋.巫蛊与婚姻——黔东南苗族婚姻中的巫蛊禁忌[D].昆明:云南大学.
[5]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中国科学院贵州分院民族研究所.贵州省黔东南舟溪地区苗族的生活习俗(贵州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之八)[Z].1963:25.
[6]吴泽霖.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1:272.
[7]吴通才.黔东南施洞地区苗族的婚姻[J].贵州民族研究,1982,(2).
[8]怀英等.滇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婚姻家庭制度与法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88.
[9]中山大学历史系编:滇西民族原始社会史调查资料[Z].中山大学历史系印刷,1979:95.
[10]《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修订编辑委员会.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4[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11]田维武.人性人伦的扭曲:黔东南苗族婚姻的特殊门第观念透视[D].贵阳:贵州民族学院,2012.
[12]朱和双.云南梁河阿昌族原始宗教中的巫蛊信仰[J].宗教学研究,2007(1).
[13]周相卿.黔东南雷公山地区苗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191.
[14]中国宗教学会秘书处.中国宗教学:第4辑[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133.
[15]伍忠纲,伍凯锋.镇宁布依族[M].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14:104.
[16]何耀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建会30周年精选学术文库:云南卷[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400.
[17]荣志毅.南方巫蛊习俗述略[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3(2).
[18]薛媛媛.中国橡胶的红色记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03.
[19]当代云南佤族简史编辑委员会,赵明生.当代云南佤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5:159.
[20]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云南省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汇编
Influence of the Witchcraft Belief among Southwest Minorities on Marriages and Families of Young People
LI Jinlian,YANG Limei
(School of Marxism,Chuxiong Normal University,Chuxiong,Yunnan 675000,China)
Abstract: Witchcraft belief is widespread among ethnic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and the marriages and families are first and most ser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belief.Because witchcraft are traditionally passed to women instead of men and are contagious,the women who play witchcrafts and their family members(both men and women)are unable to get married normally,and the married or engaged ones would break up.They can only be married to family members of people who also play witchcrafts,or to poor or defective people.To fight the persecution of the belief,some young people even sacrificed their lives.Due to state law's deterrence,the notion of“witchcraft playing”is shrouded in a secret state.With progress of social economy, culture and education, witchcraft belief will increasingly lose its influence on people.
Keywords:southwest ethnic minorities;witchcraft belief;marriage and family;negative 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K89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9)02-0014-05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9-03-1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建立以来婚姻政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实施研究(17BDJ059)。
作者简介:李金莲(1975— ),女,云南昆明人,教授,历史学学士,研究方向:少数民族婚姻家庭、民族理论与政策。
标签:琵琶论文; 苗族论文; 傣族论文; 的人论文; 寨子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神话与原始宗教论文; 原始宗教论文;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建立以来婚姻政策在西南民族地区的实施研究(17BDJ059)论文; 楚雄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