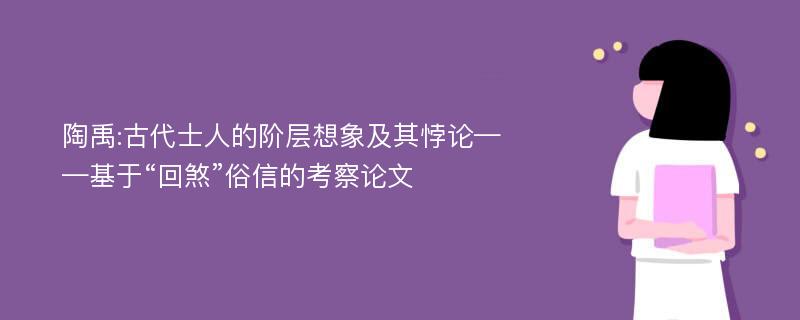
[摘 要] 回煞俗信集中体现出对逝去亲属的恐惧与排斥,冲击了中国古代士人所持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基于智性与道德的优越感,士人群体有意以“俗”界定回煞及其相关人群,试图将自身置于“俗”对岸的理想世界,从中获得区别于庸众、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士人以儒家品格矫正“俗”世界的使命性作为,主要表现为话语批评与躬行示范两种模式。而士人心态与行为的焦虑和分裂,证明其对“俗”阶层的表述与规训终归是一种话语想象的产物。回煞俗信为认识和揭示古代士人的多维思想世界提供了别具价值的角度。
[关键词] 士人 儒家 阶层意识 俗信 回煞
“回煞”是中国古代社会广泛流行的丧葬俗信,意谓亲人死后,其魂魄会于某一可以事先推知的时日返回家中,为害亲人甚至邻里。丧家例邀阴阳师预为卜算,届期则外出躲避,称作避煞。在学界,关于该俗信的专论已有张成全、王小婷二文,对回煞的成因、形式、评价等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讨论。[1-2]
教师利用语言真实的互动情境,为学生提供一个特定的场景,引学生进入学习之中。教师也可以通过故事的讲解或以问题引发学生讨论,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使他们全身心地参与到课堂互动之中。如在《彩色世界》一课教学中,教者创设情境如下:“为庆祝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小海龟画了一幅三角旗,你觉得怎样?如果在画图软件中画这个图形,你想如何美化它?”教者以情境激发学生的探学热情,引导学生思考如何用Logo实现画图软件中设置前景色、背景色的功能。
关于回煞俗信,除今日个别地区尚可见其孑遗外,对其了解只能依赖于文献记录的爬梳。这些记录者主要集中于“四民”之首的士人阶层。作为古代的社会精英,他们常以“文人”身份出场,对文字表述有着垄断性的掌控。此等错位曾导致学界对下层民众发言权的普遍焦虑,从而在民间日常精神世界的挖掘和复原方面投放了更多关注,力图在被少数人“涂抹”和“扭曲”的有“局限性”的史料中,剥离并重构某些“俗文化”的原相。前贤对于回煞的研究基本上是这一理路的实践。
这种孜孜不倦的挖掘又反过来忽略了多数史料究竟是士人产品的事实。几乎所有的讨论——不论对象有多么通俗——都在传统知识精英的想象中展开,因而透露了远不止于事实本身的珍贵信息。围绕回煞的无心陈述或有意评论中,隐现着士大夫对自我形象的体认及其对社会型构的想象。因此,考察文本中的“傲慢与偏见”,对于观测和揭示古代士人阶层复杂的内心世界,不失为一条别具价值的途径。
一、“回煞”俗信与儒家伦理的冲突
19世纪中叶,英国伦敦曾出版一部介绍中国风情的画册,书中对“祭奠去世的亲人”作了如下描述:
中国人祭奠亡灵的仪式与拉丁人埋葬肉身部分的仪式(这一仪式使得非肉身部分被允许渡过冥河)之间的差异很少。不过,在中国人的仪式中,包含了更自私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为死去的亲人获得通往福地的通行证。它们害怕死者以鬼魂的形式重现人间,来恐吓(即便不是报复)活着的人。[3](P165)
作者的观点未免偏狭,人类学研究早已表明类似的心理结构广泛存在,马林诺夫斯基揭示这一“极其复杂,甚至于互相矛盾”的心态道:
一面是对于死者的爱,一面是对于尸体的反感;一面是对于依然凭式在尸体的人格所有的慕恋,一面是对于物化了臭皮囊所有的恐惧:这两方面似乎是合而为一,互相乘除的。这种情形……在丧礼底程序上也可以看得见。最近的亲属……都是具有某种程度的反感与恐惧同真诚的爱恋混在一起,从不曾单有消极的质素表现出来或者是占了优势。[4](P30)
然则此等充满张力的情感,并非源于某一国族的异质。不仅如此,倘就中国古代文献观之,这种一体两面的平衡更常被发达的“礼”所打破,反倒表现为对死者的极端尊崇。中国古代的丧礼有着一整套复杂且抗拒变更的规程,实质上是经由一系列整肃、抽象和引申将死亡制度化。对死者的处理被表述为某种理论原则,并极度强调其作为道德义务的一面,如孔子释“孝”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5](卷2,P2462)虽然本质上所有丧仪都暗藏着生死隔绝的潜在目的,但儒家文化的规约却使得绝大多数死亡仪式与习俗都被解释或演绎为人伦准则的日常实践,此正是列维·布留尔所谓:“自远古以来,在中国社会中,为死人操心,给活人带来了多么沉重的负担。”[6](P293)对逝去亲人的侍奉承担着凝聚家族伦理、维系社会理念的重任,故而有关逝者矛盾心理的负面部分被压制和遮蔽,随即转为暗流。
“俗师”“俗巫”的仰赖者,毋庸多言是普通百姓,他们也被士人冠名以“俗”。俞文豹称:“世俗相承,至期必避之。”[18](P124)清人小说云:“人死而回煞,其有无不辨可知,而世俗咸信之。”[19](初编卷3,P93)这个面目模糊的“俗”群体,有时可替换为“愚民”一词。明清之际李渔即言:“回煞之说,不知昉于何时?大抵殷俗尚鬼,其时士大夫欲神生死之事,故设为是说,愚民信以为实,遂蔓延至今,未可知也。”[20](P120)清郝懿行笺注前引《颜氏家训》时,毫不客气地指出:“今田野愚民,尤信此俗。”[14](P99)
在油菜高产创建活动中,农业局在下属各站中抽调人员组建了技术组,全面负责技术培训、技术指导、承担各种实验、示范,从油菜播种到收割全程深入田间地头,及时发现并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不仅为油菜高产创建项目提供了技术支撑,而且为科技人员相互学习,共同提高创造了条件,实现技术人员的自身价值。
“回煞”俗信可以视作以上压抑心理的集中爆发,在一系列慎终追远的死亡仪式之间,避煞堪称“畸点”,犹如暗河伏流跃出地表。该悖礼之行有时表现得更为极端,唐王梵志诗《愚人痴涳涳》:“贮积留妻儿,死得纸钱送。好去更莫来,门前有桃棒。”项楚先生解读曰:“此诗之‘好去更莫来’,即死者妻儿嘱死者杀鬼莫来之语,颇有‘送瘟神’的意味。下云‘门前有桃棒’,则继之以恐吓,于死者何太无情耶?”[9](卷2,P119、122)清纪昀也介绍说:“或有室庐逼仄,无地避煞者,又有压制之法,使伏而不出,谓之斩殃。”[10](卷7,P125)对故去亲属的排斥竟发展至剑拔弩张,故而回煞俗信不仅对传统人伦关系构成了严峻挑战,更直接冲击了士大夫恪守的儒家价值观。
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对于高校的各个年级都有不同的意义,对于大一大二需要知识检索,拓展知识面,而到了大四阶段则需要为毕业设计服务,对于图书馆文献检索的需求更加专业化。在课程设置中针对不同需求做相应布置,在大学的前期做好通识性的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满足学生拓展专业视野与知识面的需求。对于大四阶段,按照专业的不同提供更加专业化的图书馆信息素养教学课程。在已有的通识性学习基础的条件下进一步发展学生的图书馆信息素养,为更进一步科研创新提供支持。通过分层次与具有延续性的课程的开设,帮助学生更好地接受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
马克思·韦伯曾指出士人在中国是“一切‘智识’(Intelligenz)的代表”,[11](P127)余英时亦尝谓古代的士与君子很大程度上具有合一性。[12](P271)士人普遍为丧礼中的不和谐因素忧心忡忡,但回煞性质究非令官方神经紧张的“淫祠”,很难受到政府的强制性干预。而该俗信的泛滥,到底意味着儒家社会秩序某种程度上的失控,因之必然牵发出士人的留心与回应。
面对一种与其安身立命的儒家道德完全相悖的习行,古代知识精英如何安顿自身与风俗的关系?其回应流俗的手段与效率如何?对某些原则的标榜是否意味着他们与一般民众的信仰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此意义上,作为异例的回煞无疑堪为观察士人姿态、行动及其微妙矛盾的窗口,从而为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士人的心理世界提供了绝佳的切入点。
二、“俗”的对岸:士人的自我设定
诚然,当代学者对“大、小传统”“精英—草根”等文化分层问题的讨论已颇有建树,但学术眼光的观照始终属于以今视昔的理性追认。就身处“庐山之中”的古代士人而言,其对回煞的书写与评判本身也包含着有关社会结构的根基性假设:社会群体的心智和道德可以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层次。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中的一段故事将此心态展露无遗:
[2]王小婷.中国民间传统丧葬习俗——避煞[J].民俗研究,2011(4).
沙门达多发塚取砖,得一人以进……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安平人也。父名畅,母姓魏,家在城西准财里。死时年十五,今满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即遣门下录事张秀携诣准财里,访涵父母,果得崔畅,其妻魏氏。秀携问畅曰:“卿有儿死否?”畅曰:“有息子涵,年十五而死。”秀携曰:“为人所发,今日苏活,在华林园中,主人故遣我来相问。”畅闻惊怖曰:“实无此儿,向者谬言。”秀携还,具以实陈闻,后遣携送涵回家。畅闻涵至,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13](卷3,P173-174)
作者没有就此给出评价,但崔畅与魏氏的冰冷绝情之所以获得关注和记录,显然缘于二人的行事方式违背或偏离了作者所持的某种常理。作为“隐形的在场者”,杨衒之与所述之事的隔阂至为明显,崔涵父母似乎生活在一个难以理喻的“异质世界”中,而杨氏本人正立足于某个智性和德行都更为正确的阶层,以俯瞰的方式远距离审视普罗世界中的荒谬。透过平实的叙写和冷静的笔触,作者完美地暗示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分歧与不可对话。
崔涵父母驱赶其子所用手段之“门前起火”,尚见于《颜氏家训·风操》:“偏傍之书,死有归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然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这段文字不仅是现存对回煞的较早记录,更蕴含了作者对当时知识及其载体的价值判断。所谓“偏傍之书”,清卢文弨注云“谓非正书”,暗示知识技术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而“偏傍之书”携带的知识也是来路不“正”的。颜之推接着评价道:“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14](卷2,P98-99)根据是否信从“回煞”,社会人群又可以相应地划分出儒雅—邪僻、正统—异端的等级差别,而避煞往往是道德观念不规范人群的罪恶。不惟如是,在士人群体创造的文本中,回煞观念的相关人等,总是可以归纳在“俗”——中国古代一个与心智、德行缺陷紧密相关的词语——之下。
掌控回煞知识并为此提供技术指导之人,主要是活跃在民间且具有专业技能的阴阳先生或巫觋。如翟灏《通俗编·仪节》云:“阴阳家以人死年月日之干支,推算其离魂之日数……谓死之后,如其日数而魂来复,于是计日用祝巫以招之。”[15](卷9,P197)佛道似亦参与其事,清顾张思云:“始死有所谓煞者。富家延僧道作法,曰接煞;贫者扃门尽室出,曰躲煞。”[16](卷2,P18)这些宗教服务者常自称“良师”,且云受命于“天师”,民众敬称其为“师公”。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文人笔下,以上尊号常被置换为另一种称呼,《太平广记》“彭虎子”条:“母死,俗巫诫之云:‘某日殃煞当还,重有所杀,宜出避之。’”[17](卷318,P2521)又,宋俞文豹曰:“俗师,以人死日推算。”[18](P124)“俗巫”“俗师”显然是带有歧视的称谓,暗示其合法性只在为部分群体服务时有效,于作者及其所属阶层而言则缺乏正当性。
但是只要我们将目光稍稍偏离儒家经典,便可随手拈出与逝者切断联系的决绝愿望,譬如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篇:“人妻妾若朋友死,其鬼归之者。以莎芾、牡棘枋(柄),热(爇)以寺(持)之,则不来矣。”[7](P130)又如东汉《延熹九年韩袱兴镇墓文》:“生人自有宅舍,死人自有棺椁,生死异处,无与生人相索。”[8]凡此种种,皆将去世的亲人当做一种无论如何都必须加以处置的普遍威胁。由是而论,前述英国作者的感觉又不为无理。
当士人将“俗”作为一种指称凸显出来时,试图借助这一文化符码实现何种目的?该现象牵扯到一个重要的话语和意识系统。至少从战国的哲学传统开始,“俗”已被赋予“低级”的意味而指代未开化的众生,是圣人的教化应当予以纠正者。[21](P189-212)士人谈论回煞时,“俗”作为蕴含贬义的评价性语汇也同时内化为作者对自我的理解方式,暗示了他们位居一个与俗众的价值观念、信仰趣味截然不同的世界中,其背后是士人阶层关于正统、儒雅和规训等的自我设定与认同。
士人对回煞的否定,既无关宗教意义上的“圣俗”之别,也并非文学艺术上的“雅俗”区分。这种日常信仰方面的分歧得以反映,缘于“俗”被抽象为必须抛弃的有局限性的人生品性。通过使用一系列以“俗”为核心的词语,回煞等不端行为统统被放逐到“俗”的世界中。与此同时,一个与之相对的高尚世界逐渐浮现。布迪厄认为,文化趣味的对立实际上反映着一种区隔的权力关系。[22](P6)在这里,“俗”是低级阶层的标志,往往与缺乏智识、品德低下等特征相联系。士人认为只有下层民众被这种力量所束缚,因而具有盲目的服从性,最终被“俗”的代表俗师、俗巫控制,如王符斥责俗巫“欺诬细民,荧惑百姓”,[23](卷3,P125)司马光则曰“野俗无识,妖巫妄言”。[24](卷5,P688)二者的搭配与互动发生在独立的同士人无涉的“俗”世界中。
鄱阳民韩氏妪死,请族人永宁寺僧宗达宿焉。达瞑目诵经,中夕,闻妪房中有声呜呜然,久之渐厉,若在甕盎间,蹴踏四壁,略不少止,达心亦惧,但益诵《楞严咒》,至数十过。天将晓,韩氏子亦来,犹闻物处户声不已,达告之故,偕持杖而入。见一物四尺,首戴一甕,直来触人。达击之,甕即破,乃一犬呦然而出。盖初闭门时,犬先在房中矣,甕有糠,伸首呧之,不能出,故戴而号呼耳。谚谓“疑心生暗鬼”,殆此类乎?[27](乙志卷19,P352)
在这三种“道”义中,第一种意义的英译尤为困难。因为儒道是中国特有的哲学概念,在英语世界很难找到对应的表述。
士人区别于缺乏思考能力的民众,其所修习的圣人的智慧是建立在经典文献之上的普遍真理。俞文豹引赵希棼语:“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扄灵柩于空屋之下?又岂有人父而害其子者?”[18](P124)李渔曰:“筮其期可也,絮酒击牲待之可也。若举家徙宅而避之,是塞人子念亲之心,开天性倍本之渐,此先王之教所不容也。”[20](P120)这里的评判原则不是个体利害,而是人伦教条、亲孝大义。士人以道自任,凭借其占有的知识和学理上的资源,将自己目为最高智慧的传习者,不仅扮演经典正统的解释者,也充当价值尺度的代言人。
在一系列对“回煞”不遗余力的嘲讽中,《初刻拍案惊奇》的一段评价为两个世界的清晰分层提供了绝佳样本:
[25](明)凌濛初撰,石昌渝校点.初刻拍案惊奇[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回到家之后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我脚扭伤了,她送我去医院处理。我们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我拖着受伤的脚,她拖着受伤的鞋,那双卡其色的LANVIN的鞋,鞋跟已经断掉,应该是刚才跑过来的时候坏掉的。
在作者看来,“俗巫”的身份是“乡里村夫、游嘴老妪”,其特质是“无知”,行为则属“妄称”“假说”“哄动”“糊弄”,同该行径关联的人群是“乡民”或曰“愚人”。与之相对的群体即作者一般的“正经人”“有识之人”,他们将“俗师”与“乡里人”及其所为当做“笑柄”。在这样的探讨中,世界得以清晰地分层,士人将自身与庸众区别开来,获得了一种独立高级的身份维度,而“俗”的群体则在文化结构中沦为备受歧视的丑角。
阿东晚上回家把所有照片拷进电脑,然后开始制作幻灯片。他从网上下载了音乐,这音乐便是阿里巴巴。旋律响起的时候,阿东脑海里立即浮出母亲当年一边炒菜一边唱这歌的样子。这是她最爱唱的一支歌,她是因为阿里而唱。
中国古代的士人介于“上智”的圣人与“下愚”的民众之间,但心态无疑更靠近前者。他们观察、评述的对象多半为普通人,甚至不一定受过教育。对“他者”的言说过程中,士人以自矜的姿态“隐形”在场,赋予自身一种抽离的智慧高度。在一系列居高临下的批判乃至嘲笑中,作者不断提炼和确认其理性优势,一个士人群体及其特有的心智标准浮现于“俗”的对岸。中国士人很少正面表达群体的精神定位,但“俗”无疑是其精英意识形态的倒影。文本中创造出的两极世界将士人与他们心目中的俗人区别开来,契合了古代士人阶层的自我想象和身份认同。虽然在长时段历史中,士人的群体地位及其精神面貌都在变动,时空之中的个体差异也不容忽视,但这种精神上深固的优渥意识从未失却,成为士人话语稳定的背景音之一。
三、说与做:士人对“俗”的两种回应
士人宣称的自我境界理想而高调,相应地,为庶民分配的流俗世界是卑弱和可疑的。一方面,这个自觉而清醒的理性世界需要群体内部不断加以确认和巩固;另一方面,智性和道德方面的优越感很容易催生出教化民众的使命感,况且儒家从始便为自我塑造了以影响社会为己任的精神品性,因而对俗众思想的规训是士人的职责期待之一。儒家对世界的过问和矫正主要表现为经世与修身两个维度,相应地,对回煞的干预也大致基于文人掌控的话语权力与身体力行的示范效应两种途径扩散。
对待回煞盛行的风气,上引颜之推给出的方案是“弹议所当加”。得益于文化方面的权威,就公事务发表见解一直是士人介入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除了大量针对“回煞”陋习的直白说教,[1-2]这类社会批评者的角色还可以从笔记小说作者在控制文本方面的能动性中觅出踪影。虽然无法证明现有材料是否存在改笔,但作者们有意选取体现某种认识的事例加以记录,或于叙述中偏重某种价值观的表达,其本身即反映出文人阶层试图影响舆论,以期按照“先王之教”规约同侪理念并修正下层民众行为的动机。前文曾提及,彭虎子之母死,俗巫戒其避煞,之后作者写道:
合家细弱,悉出逃隐,虎子独留不去。夜中,有人排门入,至东西屋,觅人不得。次入屋,向庐室中,虎子遑遽无计,床头先有一瓮,便入其中,以板盖头。觉母在板上,有人问:“板下无人耶?”母云:“无。”相率而去。[17](卷318,P2521)
作为殃煞还家的母亲向同行煞鬼撒谎以保护儿子,如此情节令回煞成为宣扬母子情长的一个契机,家鬼为害的说法被转化为士人极为喜爱的母慈子孝的“亲亲”题材。有时,文人也采用想象性场景提示回煞陋习对人伦大义的破坏,如一则清人手笔写道:
俗传回煞日,于亡者卧室陈设如生时,列筵款煞神。道光朝,江阴有赵大成者,伉俪最笃,妻亡,恸甚。是夕……妻至榻前,揭帐,坐床上,叹息曰:“郎君安在?咫尺家庭,不能一见耶?”因泣下。[26](P3568)
夫妻情笃一以贯之,回煞的不伦便自行显现。此外,南宋洪迈记载的一出闹剧又颇具“辟谣”性质:
何必这样的奔逃呢,前路也是在下着雨,张开我的伞来的时候,我这样漫想着。不觉已走过了天潼路口。大街上浩浩荡荡地降着雨,真是一个伟观,除了间或有几辆摩托车,连续地冲破了雨仍旧钻进了雨中地疾驰过去之外,电车和人力车全不看见。我奇怪它们都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至于人,行走着的几乎是没有,但在店铺的檐下或蔽阴下是可以一团一团地看得见,有伞的和无伞的,有雨衣的和无雨衣的,全都聚集着,用嫌厌的眼望着这奈何不得的雨。我不懂他们这些雨具是为了怎样的天气而买的。
与上面两例相似,这段记述缺少直截了当的否定之声,但曲折的叙事和滑稽的笔触已然彰显了作者对此等子虚乌有之事的负面态度,从而形成隐晦的低调抨击,结语“谚谓‘疑心生暗鬼’,殆此类乎”可谓点题。此类文本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回煞的恐怖氛围,亦试图将之纳入儒家知识结构的系统中。士人作者们假设,基本的亲缘关系和礼仪是一种永恒正确的固定模式,写作本身即意味着借由某些语汇将这种秩序强加在议题之上。笔记小说虽少有直接的教训,却作为士人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传声筒而具有不可轻忽的力量。借用潜移默化的文学资源,士人搭建了同儒家话语相适应的世界图景,提供了对回煞的另一种解释,由此进行思想和精神上的引导。
围绕回煞的言说,本质上是“先王之教”与“神道设教”的民智争夺。有别于近现代知识分子借助公共传媒释放影响力,在中国古代,文学毕竟是极少数人独占的领域,文人写作对大众读者的天然拒斥也致使其圈层倾向封闭。任何一种教化都难以在缺乏基本社会交往的环境中进行,是故无论暗自流露鄙夷,抑或严正表示愤慨,作为抽象的符号形式,文字言论更多只能输出观念给具有相近知识水准的同道,很难触及民众的精神世界,王充所谓“冀俗人观书而自觉”,[28](卷30,P1192)恐怕只是美好的愿景。以是观之,文本权力对基层生活的干预力量终究有限,士人对民众日常习俗的控制能力显然不及完全融入“俗众”的“俗师”。
在另一向度上,不少士人致力于以更高的道德水准扭转社会风气。前揭痛斥避煞的赵希棼,于其父回煞之日“独卧苫块中,终夕帖然无事”。[18](P124)清徐时栋号召“知礼之君子,宜有以正风俗矣”,且举明人张邦奇之父对“鬼怪诞妄之说一无所惑”,治丧废黜回煞之事,张氏宣称:“至今吾乡俗无避煞之扰。孝子慈孙得以致慎终之诚,自府君始也。”此言恐怕有所夸大,连引用者徐氏也说:“文定虽如此说,然此风由明至今未革也。”[29](卷4,P625)事实上,士人修身的姿态也可理解为无可奈何的退守,有如隔岸观火,谨防被拖入其中。俞文豹自述:“平时以此(指前述赵希棼事)诏其子弟,庶几临时不为俗师所惑。”[18](P124)宋人吕祖谦将上引《颜氏家训》之语采入其家训《少仪外传》。[30](P262)“俗”被认为是“带菌”的,合格的儒者势必坚筑壁垒,否则就有被“流俗”染污的危险。修身,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伦理训诫的直接影响范围只有右族子弟,德行不被腐蚀的前提是与“俗”保持安全距离,而非一意消灭之。
傅斯年曾提出,儒家文化有“礼不下庶人”的“阶级性”:“庶人心中如何想,生活如何作心理上的安顿,是不管的。于是庶人自有一种趋势,每每因邪教之流传而发作。”[31](P2124-2125)此言未免绝对,但士人所崇奉的智慧确实显示出阶层性和封闭性,其学说将人的存在过于精神化,高雅却缺乏生命力。这种设计缺陷致使儒者无力回应日常生存实际导致的叛逆,其试图逆转的言行也就湮没在更强有力的“俗”的信息之下。
四、士人的心理分裂与行为矛盾
士人面对回煞的尴尬,不止于对基层思想控制的捉襟见肘,更源于自身心态的暧昧。虽然文字记录一再暗示,他们无论从心理抑或行为上都与“俗”拉开了相当的距离,但文本中透露的微妙信息却显示,过高估计二者间的心智差异是极其危险的。
《滦阳消夏录》中,同所有娴熟的批判一样,纪昀以戏谑口吻记叙两盗伪煞互骇之事:
表叔王碧伯妻丧,术者言某日子刻回煞,全家皆避出。有盗伪为煞神,逾垣入,方开箧攫簪珥。适一盗又伪为煞神来,鬼声呜呜渐近。前盗皇遽避出,相遇于庭,彼此以为真煞神,皆悸而失魂,对仆于地。黎明,家人哭入,突见之,大骇,谛视乃知为盗。以姜汤灌苏,即以鬼装缚送官。沿路聚观,莫不绝倒。[10](卷5,P94)
这则故事很可能确有现实背景,[32]而作者言语间的揶揄之意也至为明显,纪氏评论道:“据此一事,回煞之说当妄矣。”随后他话锋一转:“然回煞行迹,余实屡目睹之。鬼神茫昧,究不知其如何也。”[10](卷5,P94)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共存于此,思想的缝隙颇堪玩味。
事实上,纪昀留下的数则与回煞相关的讨论都在反复表达这种摆荡的焦虑感。《滦阳消夏录》又曰:“世有回煞之说,庸俗术士,又有一书,能先知其日辰时刻与所去之方向,此亦妄诞至极矣。”“庸俗”“妄诞至极”等评价似乎与其他文人的抨击态度别无二致,随后却骤然宣布“余尝于隔院楼窗中遥见其去”,且声称“与所推时刻方向无一差也”,复又描述“两次手持启钥,谛视布灰之处”所见的异状:“手迹足迹,宛然与生时无二。”作者用亲身经历令自己的价值观再度沦陷,也印证了他一贯的省思:“‘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然六合之中,实亦有不能论者。”[10](卷4,P76-77)与之类似,《如是我闻》中纪昀先是批评回煞推算之术“别无奇奥”,不过“诡词取财而已”,并谓斩殃之法“尤为荒诞”,随即又用一次耳闻目击证明其“似又不尽诬”。最后,纪氏再次重申了同样的论调:“天地之大,何所不有;幽冥之理,莫得而穷。不必曲为之词,亦不必力攻其说。”[10](卷7,P125)当然,这样的想法无疑会因为违背群体的坚信而导致作者身份危机。据《槐西杂志》记载,作者坦承所见回煞后,其父与之言曰:“我童子时,读书陈氏舅家。值仆妇夜回煞,月明如昼,我独坐室外,欲视回煞作何状,迄无见也。何尔乃有见耶?然则尔不如我多矣。”纪氏亦表示“至今深愧此训”,[10](卷14,P342)似乎感到自己违背了精英阶层应有的某种道德水准,并为此苦恼不已。
傅斯年曰:“六经之内,都是十分之九以上但为装点之用,文章之资的。”[33](P2050)关于这种价值尺度的动摇,纪昀或是为数不多的自我剖白心路陂陀的文人,更多的时候,同道德律令扞格不入的思想总是被小心翼翼地掩藏。尽管如此,文本中仍然可以窥见言说与实践不相表里而产生的裂隙。
历史研究的常识提示我们,描述回煞的材料之丰富,抨击声浪之高涨,往往与该俗信的流行程度及其对士人的心理影响成正比。只消考虑讨论和志录回煞的热忱,便可察觉到知识精英常常同纪昀一样扮演“流俗不诬”的见证者。如唐《宣室志》记载的两位回煞目击者分别是儒生郑氏和同畋于野的隰州郡官,类似遭遇发生在京兆尹崔光远身上,而搜罗两起事件的张读本人也是大中年间进士,官至尚书左丞。[34](P1078)抛开立论角度的不尽相同,回煞作为士人之间的谈资,恰恰体现他们在严肃论调之外,与“俗”世界割不断的关系。
何况,士人生活与回煞的关系也并非如他们描摹的那般界限分明。士人非但热衷于陈述“俗”之事相,其日常生活恐怕也与“俗”难脱干系。沈复之妻芸娘去世后,届回煞之期,复“冀魂归一见”,且与人曰“所以不避而待之者,正信其有也”,当夜察觉到异样后,更“心舂股栗,欲呼守者进观;而转念柔魂弱魄,恐为盛阳所逼”。[35](卷3,P39)此处的思考方式完全是“民间式”或曰“俗”的。“回煞”的阴影笼罩士人阶层的并不止于个案,清代小说《歧路灯》中的一段对话可为证:
潜斋道:“近来竟这宗邪说恨人!岂有父母骨肉未寒,阖家弃而避去之理?”耘轩道:“这也无怪其然。近日士大夫家,见理不明,于父母初亡之日,听阴阳家说多少凶煞,为人子的,要在父母身上避这宗害。”[36](P100)
此外,大量的墓志铭也显示,不信“俗巫”是可以于盖棺论定时加以表彰的重要美德。宋吕祖谦《义乌楼君墓志铭》云:“终君世,巫祝不至门。”[37](卷10,P88)刘宰《潘君墓志铭》叙其不以回煞为然:“君曰:‘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谓有室神也,可使死者无依,又以妖巫怛之乎?’斥其说不用,卒亦无异。”[38](卷29,P682)这样的举动耐人寻味:浓缩逝者一生的“墓志铭”,肯花相当的篇幅称颂其排斥俗巫的品格,证明此举非但高出一般俗众,即便在士大夫圈层之中也实属难得,因而值得作为个人标签流芳百世。换言之,对个别士人不信避煞的嘉许,反倒透露出此俗在士人之间极为流行的隐情。
[21]Mark Edward Lewis. The Constructionof Space in Early China[M].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6.
俗巫魂灵之说,甚或因为迎合士人的心理期待而获其青睐。清俞樾记载:“一日,有士人托致其父之魂,良久,竟不至。巫者甚愧,往见其师而问焉。”此处特别强调了丧家的儒门身份,巫者之师的解释是:“大凡其气益清,则其升益高。故孔、孟、颜、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间绝无肸蠁,盖其气已升至极高之地,去人甚远也……其品愈下,则浊气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于寻常之人,则生本凡庸,死亦阘冗。”此言显然令俞氏极为受用:“余谓此论及精,非他巫觋所能见及……余尝疑匹夫匹妇,死犹有鬼;而士大夫一经易篑,则反寂然,殊不可解。得此巫师之论,乃释然矣。”[39](卷4,P3937-3939)该巫祝之说与一般“俗”说实则并无不同,不过是满足了士人对于社会分层的设想,达成了另一种逻辑上的自洽,因而暗度陈仓地获得赞许。可见民间信仰与社会地位、知识水平等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只是以何种方式更容易被采信而已。
清季一则评论尝云:“我中国三教并行,立意各不相若,独于回煞之谬,同然一词。羽流信之,释子从之,儒门每附和之。”[40](P482)回煞盛行,缘于儒家教化难以就某些现实的心理需求进行有效回应。士人与民众面对相同的境况,注定分享某些相似的世界观。回煞凸显了士人超然的精英意识与其植根的俗世土壤之间的分裂与焦虑。综括上文,对待回煞,士人笔下与心中的态度并不完全相称,他们的日常生活不免沾染许多世俗性,文本表达却构造出一个纯粹忠于儒家教化的“精英阶层”,给予士人日常之外的另一重身份。这种超越性的审视,有时基于一种虚幻的迷障而近似文化幻觉,但较之学界常说的底层百姓“无声的声音”,士人对回煞的记载可谓“有声之无声”,没有明确表达的想法维系着不可见的精神世界潜藏在文字之下。倘若忽略士人暗自表述的“言外之意”,文化精英就只不过是另一个“失语”的群体。在这方面,回煞提供了一些深层、独特甚至意想不到的张力与矛盾,为揭示士人阶层意识的一体之两面提供了一个支点。
注释:
[1]张成全.“回煞”考论[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4).
三峡升船机下闸首卧倒门支铰座采用A2-70-M36螺栓,预紧力矩为1 233 N·m,它在试运行过程中曾发生断裂故障,左侧上支铰座的8根螺栓断了7根,右侧上支铰座的8根螺栓断裂了3根。所有螺栓断裂部位均发生在螺栓头部(螺帽与光杆的结合部位),部分螺栓断口呈现典型的疲劳断口宏观形貌特征,部分螺栓断口呈现颈缩特征,支铰座与门体之间出现间隙,如图1所示。
③安装支撑板B和水池座:保持支撑板、水池板与底座垂直,用少许混凝土固定其间隙,同时要保证水池座上平面与支撑板两个突出钩爪面水平,连接出水管水平管道及阀门,安装排水管道。
[3][英]乔治·N·赖特文(George N. Wright)著,[英]托马斯·阿洛姆(Thomas Allom)绘,秦传安译.晚清河山[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4][英]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著,李安宅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
[5]论语注疏[C]//.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
[6][法]列维·布留尔(Lucien Lévy-Bruhl)著,丁由译.原始思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7]吴小强.秦简日书集释[M].长沙:岳麓书社,2000.
[8]王泽庆.东汉延熹九年朱书魂瓶[N].中国文物报,1993(3).
[9]项楚校注.王梵志诗校注(增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10](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11][德]马克思·韦伯(Max Weber)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综上所述,病程较长、文化水平较低、使用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为慢性荨麻疹患者治疗依从性差的影响因素,提示了对此类患者进行健康教育的重要性。
[12]余英时.儒家“君子”的理想[C]//.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3]范祥雍校注.洛阳伽蓝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4]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5](清)翟灏.通俗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16](清)顾张思著,曾昭聪、刘玉红点校.土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7]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1.
[18](宋)俞文豹著,张宗祥校订.吹剑录全编[M].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19](清)长白浩歌子撰,冯伟民校点.萤窗异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20](清)李渔.笠翁一家言文集[C]//.李渔全集·第1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据勘查,昌乐境内蓝宝石富矿区450平方公里,储量数十亿克拉,占全国蓝宝石总储量的90%以上,是继泰国、澳大利亚、斯里兰卡蓝宝石矿之后世界上发现的第四大蓝宝石矿床。昌乐蓝宝石化学成分和矿物成分与缅甸、泰国、柬埔寨、斯里兰卡等国家生产的蓝宝石并无大的不同,“其化学成分主要是三氧化二铝,就是金属铝的氧化物,因为含有微量元素钛和铁而呈现蓝色,并且具有颗粒大、颜色纯、质量好、双色性、易开采、奇异宝石多等特点。尤其是昌乐蓝宝石独有的双色性,即表面呈现蓝色,侧面则是神奇的绿色,颇受国内外珠宝界青睐,昌乐也因此被誉为“蓝宝石之都”。
[22]Pierre Bourdieu. translated by Richard Nice.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23](汉)王符著,(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宋)司马光.家范[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那无知男女,妄称神鬼,假说阴阳,一些影响没有的,也一般会哄动乡民,做张做势的,从古来就有了。至到如今,真有术的巫觋已失其传,无过是些乡里村夫、游嘴老妪,男称太保,女称师娘,假说降神召鬼,哄骗愚人。口里说汉话,便道神道来了,却是脱不得乡气。信口胡柴的,多是不囫囵的官话,杜撰出来的字眼。正经人听了,浑身麻木忍笑不住的;乡里人信是活灵活现的神道,匾匾的信服,不知天下曾有那不会讲官话的神道么……而今并那邪不成邪,术不成术,一味糊弄。愚民信伏,习以成风,真实痼疾不可解。只好做有识之人的笑柄而已。[25](卷39,P405)
整个实践活动包括四个阶段,分别是:M+C(强调创意的构思)阶段、M+D(强调创新的设计)阶段、M+I(强调创造的实施)阶段、M+O(强调分享的运行)阶段,各个阶段的活动内容见表1。整个过程体现了体验教育、快乐教育、基于项目的教育和创造中学等教育理念。
[26](清)徐珂.清稗类钞[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7](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现代工业中含重金属离子废液的不合格排放会严重污染土壤、水源,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因此,对废液里的重金属离子进行合理处理十分重要[1-2]。目前,对重金属离子的处理方法[3]有离子交换法、吸附法、化学沉淀法、铁氧体法、膜分离法、浮选法等。其中,吸附法[4-5]是利用具有高比表面积的固体材料通过吸附作用去除废水中的重金属离子,操作简单、环保、有效。吸附剂的选择是影响吸附效果的重要因素,研究表明,成本低、来源广的农作物等生物质炭用作吸附剂对铅、铜、锌等众多重金属离子有较好的吸附效果,已成为吸附方向上的研究热点。
[28]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9](清)徐时栋.烟屿楼笔记[C]//.续修四库全书(第116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0](宋)吕祖谦.少仪外传[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0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1]傅斯年.中国学校制度之批评[C]//.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2]清代笔记小说《萤窗异草》有婢女假殃窃货之事,与此极类,见长白浩歌子著,冯伟民校点《萤窗异草》初编卷3,第93页。沈复也曾提到“有因避眚被窃者”(氏著《浮生六记》卷3《坎坷记愁》,黄山书社2007年版,第39页),理或当然。
[33]傅斯年.论学校读经[C]//.傅斯年全集(第6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34](唐)张读撰,萧逸校点.宣室志[C]//.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5](清)沈复.浮生六记[M].合肥:黄山书社,2007.
[36](清)李绿园,李颖点校.歧路灯[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7](宋)吕祖谦.东莱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8](宋)刘宰.漫塘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70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9](清)俞樾.右台仙馆笔记[C]//.笔记小说大观(第16编·第7册).台北:新兴书局,1977.
[40]回煞辨[J].益闻录,1885(504).
TheImaginationandParadoxofStratumbyAncientIntellectuals——Based on Folk Custom of Huisha
TAO Yu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 610064,China)
Abstract:The folk custom of Huisha, epitomizing the fear and exclusion on the dead relatives, impacted the Confucian ethical values held by ancien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olding the superiority of wisdom and morality, scholars intentionally defined Huisha and the related people as “su”. To distinguish from vulgar and acquire independent and advanced identity, they located themselves in an ideal world opposite. The behavior of scholars with Confucian character to rectify the “su” world was mainly manifested in two modes: contemptuous language and hands-on experience. The anxiety and split of their mentality and behavior just proved that their expression was a product of imagination. The folk custom of Huisha provides a valuable perspective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revealing of the thoughts of ancient scholars.
Keywords:intellectuals; Confucianism; stratum consciousness; folk custom; Huisha
[收稿日期]2018-09-25
[作者简介]陶禹(1989-),男,内蒙古乌兰察布人,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B21;K103
[文章编号]1002- 3054(2019)06-0091-1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3262/j.bjsshkxy.bjshkx.190609
标签:士人论文; 儒家论文; 世界论文; 阶层论文; 作者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北京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论文; 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