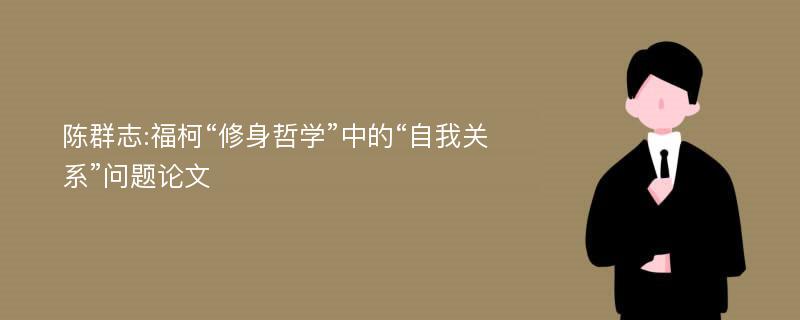
东与西
摘 要:米歇尔·福柯晚期极力探索如何对知识-权力关系约制作出反抗。他沉思了多年才有答案,这个答案就蕴藏在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身哲学”中的“自我关系”的讨论中。然而,皮埃尔·阿道却批评福柯的诠释太过于美学化了,因而忽视了上达“普遍理性”的要求。但事实上,福柯探究修身问题中的“自我关系”内涵并不是如阿道所批评的那样,而是也有上升到普遍性的解释。他之所以重视希腊化时期的“自我关系”模式,是因为它不仅强调了以“自我转化”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必须“反求诸己”的修身实践,而且展开了一种把自我安立在世界之中的诉求。
关键词:福柯;修身哲学;自我关系;自我关注;生活技艺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晚期著述、演讲和访谈中都非常重视“自我关注(souci de soi)”“自我技艺 (techniques de soi) ”“自我修养(culture de soi)”“自我治理 (gouvernement de soi) ”“自我实践(pratiques de soi)”“生存美学 (esthétique de l’existence) ”“生活技艺(tekhnê tou biou)”“生存艺术 (l’art d’existence) ”等修身概念的阐发,这些表述在一定程度上与他转向探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有关。[1]在这条与前期不同的研究道路上,他颇受古希腊-罗马思想史家皮埃尔·阿道(Pierre Hadot, 1922—2010)所揭示的“精神操练(exercices spirituels)”(1)参见P. Hadot, “Exercices Spirituels”, “Exercices Spirituels Antiques et ‘Philosophie Chrétienne’”, in ExercicesSpiritualsetPhilosophieAntique, Deuxième édition revue et augmentée, Paris: éthdes Augustiniennes, 1987, pp.13-58, 58-74。观念的启发。[2](P.161)然而,福柯死后,阿道却撰文批评:“令我担忧的是,福柯的解释太过于强调自我修养、自我关注和自我转向(一般定义其伦理模式为生存美学)。他提出的自我修养显得太美学化了。换言之,这可能是一种新型的‘时尚(Dandyism)’,一种二十世纪晚期的风格。”[3](P.211)阿道的看法源自于他认为,福柯“六经注我”式地把古代哲学重构成了一种单纯的“自我关系(rapport à soi)”,一种全然“自我关注”(2)福柯指出,在古希腊-罗马文化中,“自我关注”是一个古老议题,从色诺芬笔下的居鲁士到柏拉图描述的苏格拉底,“自我关注”都是作为“生活技艺”的中心原则。从柏拉图主义者到伊壁鸠鲁主义者,从斯多亚学派的塞涅卡到马克·奥勒留,无不表示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要采取各种方式转向自我,把人生变成一种追求永恒的修行。参见M. Foucault, Histoiredelasexualité:vol.3,Lesoucidesoi, Paris: Gallimard, 1984. pp.61-75。此书英译本信息为M. Foucault, TheCareoftheSelf,Volume3oftheHistoryofSexuality,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6, pp.43-54。中译本信息为福柯《性经验史》(增订本),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30-338页。的主张,从而无法上达“普遍理性(universal reason)”或“宇宙理性(cosmic reason)”,但“自我”必须要以“普遍理性”为原则才能获得理解。[3](PP.207-208)
现在看来,有理由相信,福柯并没有拒绝“普遍理性”的诉求,与之相反,他在“自我关注”与“自我技艺”[4](P.225)的阐述中,不仅表明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古人那里,“世界知识塑造着主体的精神体验”(3)此处参见M. Foucault, L’HerméneutiqueduSujet:CoursauCollègedeFrance(1981-1982), Paris: Gallimard, 2001,p.465;中译本福柯《主体解释学》,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4页;英译本M. Foucault, TheHermeneuticsoftheSubject, trans., Graham Burchell, New York: Palgrave Macmjllan, 2005, p.485。本文所引《主体解释学》中的段落,均参照了中译本,部分内容笔者依据法文本与英译本有所改动,特此说明。,而且强调主体藉由哲学修行(askêsis philosophias)塑造自我之时,“人就安立自身在世界之中,或者把自身当作与世界相即之物”(4)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304页、中译本第334页、英译本第319页。。福柯诠表欧洲文化中的“修身哲学”并不仅仅为了成就某种思想史研究,而是试图为当代人提供一种“精神性”的生活方式。[1]笔者认为,对欧洲哲学中的这种“修身实践”或“伦理实践”(按照中国哲学儒、释、道的讲法即修身、修行和修炼的“工夫”)的重新重视,并把“修身体验模式”的论题纳入到“另类启蒙”的视野之中,福柯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启示之一。[5](PP. 5-32)本文的目的一方面为了解明福柯论修身问题并不是如阿道所批评的那样,另一方面则试图厘清他探索“自我关系”的缘由、理路和归宿。
一、修身问题的提出及其缘由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福柯思想有重要转变,我们可以从较晚的两次访谈中找到线索。在题为“论伦理学的系谱学:研究进展综述”的一次访谈中(1983年4月),福柯表明,系谱学的核心议题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historical ontology of ourselves)”,而这种标签最终追问的是“我们自身”的伦理实践问题。[6](P.262)“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就是对“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的批判实践,三种“主体形象”能够勾画出有关真理、权力和道德之间的辩证关系,构成“我们自身”的身份。[7]而在另一次福柯逝世前不久的访谈中(1984年1月),他不仅回顾了几十年来所探究的权力与知识、主体与真理之间的关系,而且更加突出了自己学术进展的最后领域,即“自我关注”作为修身哲学中心问题,我们如何回归古代伦理的这种自由实践。[8](PP.284-285)问题是,福柯为何会有这样的转变呢?
福柯早已表明自己多年思索的问题是: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存在究竟有何价值?[9](P.447)就像尼采所说的那样:“古代希腊哲学家们对存在的价值的判断所说的东西比一种现代的判断要多得多,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像在我们这里,思维的感觉迷失在生活的自由、美和伟大的愿望和对真理的欲望之分裂中,这种真理只问:存在究竟有什么价值?”[10](P.271)福柯的追问正是沿着尼采的道路, 通过古希腊-罗马时期思想家的启示,在思考如何理解“自我认识(connaissance de soi)”和“自我关注(souci de soi)”之关系的基础上,重新提出了修身问题的重要性。
2.儿童文学善于表现儿童生活的游戏行为。在儿童文学作品《小鹰的一个星期天》中,小鹰在星期天跟着伙伴一起上山采野果、挖鸟蛋。锁柱的星期天是去捉小兔(《锁柱的星期日》)。它们都充分表现了儿童生活的游戏行为。
在基督教模式中,转向问题不同于柏拉图的“epistrophê”概念,而是以“metanoia(精神转变)”形式出现的。“metanoia”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告解(忏悔);二是指思想与精神的彻底转变。这个“metanoia”涉及一种突变,由一种存在类型转成另一存在类型,由死去转成新生,由必死的命运转成永生的极乐,由黑暗转成光明,由魔鬼的统治转成上帝的统治。在此过程中,主体内部需要断裂,否弃自我,重获新生,其生存方式和精神风貌与原来的自我之间有一种全然不同的风格。(13)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02-203页、中译本第223-225页、英译本第211-213页。在此之中,“自我认识”是通过“自我注释(exégèse de soi)”的方式来完成的,它要求分析自己内心的诸种隐私,通过告解(忏悔)来理解其来源、目标和形式,以此破除内心的妄念,抑制心性的欲望,抗拒人间的诱惑。更重要的是,基督教的“自我认识”不是回向自身的“自我关注”,而是否弃自身的“自我注释”。因此,基督教模式中的“自我否弃”也是一条理解“自我认识”与“自我关注”之关系的纽带,只是这条纽带与柏拉图的“灵魂回忆”不同,其目的在于否弃自身,回向天堂。(14)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44-245页、中译本第269-270页、英译本第254-256页。
从福柯晚期的一系列著作和他本人苦行般的“自我训练”与本能式的“自我转化”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哲学理论阐述与自我修身实践是完全一致的。在《快感的享用》中,福柯解释了改变学术进程的动机,认为必须把新的尝试当成是自我在真理游戏中的体验,这种体验是哲学活生生的呈现,它一直以来就是一种苦行实践,一种自我修行。(5)此处参见M. Foucault, HistoiredelaSexualité:vol.2,L’UsagedesPlaisirs, Paris: Gallimard, 1984, p.16;英译本M. Foucault, TheUseofPleasure,Volume2oftheHistoryofSexuality, trans.,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5, p.9;中译本福柯《性经验史》(增订本),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本文所引《快感的享用》中的段落,均参照了中译本,部分内容笔者依据法文本与英译本有所改动,特此说明。由此进路,福柯已转向了“关注自我”修身技艺的伦理阐述,亦即从知识-权力分析转向了生命-主体诠释。就像他在《何谓启蒙》中所说的那样,“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理论或教条,也并非一套客观的知识体系,而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精神品性,一种哲学生活。[11](P.73)可以说,福柯扬弃了康德的启蒙观,认为还需要进行新的启蒙,进而理解“我们自身”的身份,以便塑造美学实践的生存方式。[7]
在希腊化模式中,转向问题与柏拉图模式的“epistrophê”和基督教模式的“metanoia”都不相同,“epistrophê”和“metanoia”两者都不适合用来描述希腊化模式中的修身实践方式。希腊化模式不是把“自我关注”与“自我认识”统一起来的“回忆模式”,更不是把“自我关注”纳入“自我认识”之中,而只是强调“自我关注”,或者说是把“自我认识”纳入“自我关注”之中,保持其自主性。于此而言,转向问题作为回归自我的呈现方式是内在性的,它不是建立在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相对立的基础上,而是早已摆脱我们不能控制的事物,回到能够自我主宰的事物,心灵因而得以解放。它无需肉体与灵魂的分离,无需刻意地去摆脱身体的束缚,只是确立自身与自身的一致性和完整性。在此模式中,转向自身的根本要素不是认识,而是实践和修行。它不是要“自我注释”,也不是“自我否弃”,而是必须迈向自我,迈向自我以自身为唯一目标,人迈向自我的运动即是人回归自身的运动。希腊化模式的转向不存在基督教模式那样的断裂,而只是自身与周围事物的断裂,它是一种回避与退隐,一种解放自身的断裂,一种恩惠自身的断裂,一种填补自身的断裂。转向必须把自身置于眼前,必须关怀自己,审视自己,神化自己,检查自己。它是以“自我关注”为中心的,但这种“自我关注”的体悟绝对不能替代认识自然,因为只有凭借理解认识自然与“自我关注”之间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回向自身,人必须把一切知识都纳入“生活技艺”或“修身技艺”之中,才能“成为自我”。(15)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46-248页、中译本第270-273页、英译本第256-260页。
倘若由此出发,那么我们应该藉由什么样的“自我关系”模式才能“成为自我”呢?或者说,像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为了成为伦理主体,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改变自我,从而达到合乎伦理的修身实践”?
这三种“自我关系”模式,福柯最重视的是在时间上介于柏拉图模式与基督教模式之间的希腊化模式。他曾清楚表明:“柏拉图给予了德尔菲神谕‘认识你自己’以优先权。‘认识你自己’的特权地位是所有柏拉图主义者的特征。尔后,在希腊化和希腊-罗马时代,这种情形倒转了过来:重心不再是自我认识而是自我关注。后者被赋予了一种自主论,甚至被视为一个至高无上的哲学议题。”[4](P.231)也就是说,在希腊化时期,“自我关注”是哲学思考的主轴线,它强调以“自我转化”为目的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必须“反求诸己”的修身实践。
二、修身问题中的三种“自我关系”
式中:Fr为钻孔轨迹摩阻力,kN;q为钻杆单位长度重量,kN/m;L为孔深,m;C1为正常钻进屏蔽系数;C2为事故处理屏蔽系数;Fj为孔底钻具遇卡阻力,kN。
在福柯眼中,希腊化时期所创造的东西,没有知识-权力那样的固定形式,而只是一种伦理的或审美的规则,“每个人都必须关注他自己,希腊伦理注重于自我选择的问题,生存美学的问题”[5](P.260)。伦理的或审美的规则组成了生存的方式与生命的风格,犹如尼采所赞颂的艺术家作风,是一种“生命可能性”的创造。而“生命可能性”的创造就是主体如何改变自己与如何回归自身的问题,他们只有通过“自我关注”的修身实践才能完成。这样的“自我关注”有三层含义:(一)它是一种对待自身、他人和世界的态度;(二)它还是一种由外向内“看”的方式,即由外部、他人和世界转向“自己”的所思;(三)它总是指人自身的修身活动,由此修身,人们得以控制自己、改变自己、净化自己。(19)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12-13页、中译本第11-13页、英译本第10-11页。必须要明白的是,修身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将自身确立为自己的生存目的,坚定不移地令主体自然与真理相即。(20)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464页、中译本第504页、英译本第485页。希腊化模式中的修身哲学之根本意义就在于保证自身真理的主体化,使真理内居于主体之中。
基于这种状况,福柯非常关注古希腊-罗马时期对“精神性(spiritualité)”诉求的肯定,这些思考浓缩在他的心灵深处,与他同生共死。(8)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304-305页、中译本第333-334页、英译本第318-319页。然而,从16世纪开始,“精神性”诉求就渐渐被“认知性”诉求限制、覆盖和抹杀。如果仔细阅读笛卡尔、帕斯卡尔和斯宾诺莎等人的文献,我们即可发现从“精神性”向“认知性”的转变。更典型的是,“浮士德形象”向我们综合展现了“精神性”与“认知性”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从16世纪到18世纪这3个世纪中前两者之关系是如何提出来的。福柯强调,这300年就是“认知性”对“精神性”的分化与代替的开始期,浮士德代表着“精神性”的权势、魅力和危机。他提到了马尔洛维的浮士德、莱辛的浮士德和歌德的浮士德,而歌德的“浮士德形象”集中体现了对“精神性”消失的最后挽歌和对“认知性”问世的忧伤致意。(9)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95-297页、中译本第322-325页、英译本第307-311页。
(五)坚持“管长远、管根本”,进一步健全长效机制。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4]31。坚持发展“枫桥经验”,必须从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着手,使预防和化解矛盾、平安建设、维护稳定等工作走上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轨道。要建立健全源头预防矛盾机制,推广“村级民主程序”,推进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坚持和完善社会稳定“三色”预警机制,从源头遏制矛盾的发生。要建立健全矛盾摸排机制,定期分析社会稳定形势,定期排查矛盾隐患;深化“大调解”体系,健全完善专业调解、行业调解,实现矛盾化解全覆盖。要建立健全应急处置机制,完善预案,加强演练,有效预防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
不过,近代以来的一些哲学家也试图在基督教之外,来重新理解古希腊-罗马思想,这种转变,尼采给予了极为有力的贡献。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发现原有的伦理价值,而在于批判吸收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营养,建立新的伦理价值,以此获得彻底解放。从对修身实践的重视和对“精神性”诉求的尊崇中可以看出,福柯的哲学理论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其最终趋向不在于那些抽象的理论体系,而在于求得“我们自身”存在的实践智慧。[13](P.491)他穿梭于知识、权力和道德之间,试图揭示传统主体论思路的实质,寻得自我的真正精神之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的一切书写文字,都是自我体验所呈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哲思。
在此思路指引下,福柯提出了三种“自我关系”的模式:(一)柏拉图模式,以“自我认识”为核心;(二)基督教模式(指的是3—4世纪的早期基督教),以“自我否弃”为核心;(三)希腊化模式(斯多葛派的学说即为典型代表),以“自我关注”为核心(10)笔者按:福柯特别重视希腊化模式,因此放在最后讨论。。
在柏拉图模式中,转向思想是以“epistrophê(返回)”概念出现的。这种转向在于摆脱世俗现象,摆脱易变的事物,进而明了自己的无知,从而回向自身,自我觉醒。通过“灵魂回忆”,人能够回到自身的本质、真理和存在。柏拉图的“epistrophê”具有三重含义: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根本对立;灵魂脱离肉体而获得自由;在回忆活动中,“自我认识”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认识真理就是解放自我。(11)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01页、中译本第222-223页、英译本第209-210页。至于“自我认识”与“自我关注”的关系问题,在《阿尔喀比亚德篇》中是作为总体框架出现的。[14](P.88)我们知道,经由苏格拉底的质问,阿尔喀比亚德发现了自己的无知,但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无知,为了回应这种无知,他就必须返回自己,自我关注。在“自我关注”的这种“epistrophê”中,“自我认识”的律令显得极为重要,“自我认识”是灵魂对自身存在的把握,灵魂依靠“自我认识”的理智之镜来审视自身。柏拉图的“灵魂回忆”是连结“自我关注”与“自我认识”的纽带,灵魂在回忆“自我之所见”时发现了“自我之所是”,在回忆“自我之所是”时也发现了“自我之所见”。(12)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44页、中译本第268-270页、英译本第254-255页。
根据Lakoff(1987)、Lakoff&Turner(1989)、Radden&Kövecses(1999)等人的观点,ICM 是指我们组织百科知识所依托的结构,它是我们通过自然、社会和文化活动从其一个特定领域的各种体验中抽象出来的心理表征。Radden&Kövecses(1999:21)认为,一切事物经过概念化后都有ICM,从这个意义上说,ICM涉及现实、概念和语言这三个不同的维度;而且,只要有ICM就会出现转喻,因此,转喻可谓无处不在。
在这种追问“自我究竟意味着什么”的过程中,福柯最关注的是伦理轴心中的“自我关系”,它决定了个人如何将自己建构成自身行动的道德主体。此处涵摄着四个问题:(一)“自我”的哪些部分与道德行为联系最紧密?是“情感”与“动机”,还是“欲望”或别的什么?(二)人们以何种“主体化模式”去发现道德义务的方式?它是否是经典文本中所揭示的神圣律法或普遍法则,抑或是在任何条件下都适用的自然规律或宇宙秩序?(三)为了成为道德主体,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来改变自我,从而达到合乎伦理的修身实践?(四)当遵从道德标准之时,我们所追求的是何种存在?是否能够变得淳朴、自由或不朽,是否能够成为“我们自身”的主人?[6](PP.263-265)以上问题相互纠缠又彼此独立,共同构成了福柯修身哲学的基本主题。
德勒兹曾指出,《快感的享用》与福柯先前的著作存在着明显的“断裂”,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再仅仅从17至19世纪这样的短时期来做研究,而是进一步延伸,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再到现代的长时期考察;其二,发现了“自我关系”,认为“自我关系”是不同于“权力关系”与“知识关系”的新维度。[12](P.107)自《快感的享用》之后,福柯的确作出了第三个重要“变更”。“为了分析所谓的学术进程,在理论上有所变更是必要的,如此致使我去探究与人文科学相关的散播着的实践形式。再者,为了分析所谓的‘权力’现象,一种理论上的变更也是需要的,如此促使我去研究关于权力运作中的诸种关系、公开策略和合理技术。复次,为了分析所谓的‘主体’,我现在必须作出第三个变更,由此恰当地探求个体是根据何种自我关系的模式得以建立而被认可为主体。”(6)此处参见《性经验史》法文本第12-13页、中译本第109页、英译本第6页。
由此可见,学术兴趣的转向有其内在理路,这种理路并不受外在因素的影响,而是一种自然的交互发展,是一种由表(真理游戏、权力关系)及里(主体形态、自我关系)的自身反求。从知识考古学到权力系谱学再到道德系谱学,福柯所关注的知识主体、权力主体和伦理主体诸问题,始终有其内在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就展现在如何揭示“我们自身”的奥秘之中,亦即为了寻求如何成为真实的自我,如何获得存在的价值。
三、希腊化模式中的“自我关注”
藉由上述讨论可知,在福柯所认同的“自我关注”的领域内,柏拉图的“epistrophê”和基督教的“metanoia”都无法用来描述公元1—2世纪希腊化时期文本中的修身实践方式。实际上,福柯有关“epistrophê”和“metanoia”的讨论,受到了皮埃尔·阿道的文章启发。阿道认为,在西方文化中,存在着两种主要的“返回”模式,即“epistrophê”与“metanoia”。“epistrophê”涵摄着灵魂追根的“返回”模式,凭借如此活动而回到生命存在的至善,并直至回归存在的永恒。这种“epistrophê”的内核就是“觉醒(prise de conscience)”,“anamnêsis(回忆)”是“觉醒”的根本方式,人睁开他的眼睛,回到光明的源泉,亦即回到生命存在的源泉。关于“metanoia”,阿道则指出,它属于与“epistrophê”不同的模式。它涉及一种精神的剧烈改变,一种彻底的更新;涉及一种主体依靠自己的重生,即位于亲身体验和自身否弃之中的死亡和复活。在阿道看来,正是由于“epistrophê”和“metanoia”之间的这种分别,甚至对立,西方思想、西方精神和西方哲学才成了永恒的两极分化。(16)参见P. Hadot, “Epistrophê and Metanoia”, in ActesduXIcongrèsinternationaldephilosophie,Bruxelles, 20-26 aot 1953(Louvain-Amsterdam: Nauwelaerts, 1953), vol. XII, pp.31-36;亦可参见P. Hodot, “Conversion”, in ExercicesSpiritualsetPhilosophieAntique, pp.175-182。缘于阿道的观点,福柯觉得“epistrophê”和“metanoia”的阐述能够构成一个极好的分析框架,不过,倘若以历时性的发展来看,仅仅凭借这两种模式来作为从柏拉图到基督教这一时间段的阐释与分析框架,恐怕显得有些相形见绌,难以令人满意。因为“epistrophê”概念在希腊化时期的伊壁鸠鲁学派、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那里已然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他们都试图以不同于柏拉图的“epistrophê”观点来思考“自我转化”。再者,希腊化时期的“返回”方式也不同于基督教的“metanoia”模式,因为基督教模式在于否弃自我和颠覆主体。正是如此,福柯尤其推崇希腊化时期的那种有别于“epistrophê”和“metanoia”的修身实践方式。(17)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07-209页、中译本第228-231页、英译本第214-218页。
确切来讲,希腊化模式中的修身哲学是一种依据“自我关注”原则而来的“生活技艺”,这种哲学化的生活风格在古代文化史上是很重要的现象。“自我关注”不再像柏拉图所描述的那样是向有关城邦或他人敞开,而是转回到了自身,以自身为中心,也只有在自己的修身实践中才能教化自我、拯救自我、圆成自我。福柯认为,在希腊化时期的诸多学派中(尤其是斯多葛学派),哲学的真正方式在于探求“生活技艺”,它伴随着我们的一生,引导我们直到生命的终点。在这个时代里,“生活技艺”与“修身技艺”、“生活技艺”与“自我关注”已合二为一。至此,“生活技艺”的问题——“为了真实生活,我应当做什么?”——已被纳入如下问题:“为了让自己成为理所应当的那个样子,我该做些什么?”如此一来,哲学(有关真理的思想)就越来越明显地变成了一种“精神性”诉求(有关主体生存方式的转变),而“生活技艺”的问题再次成了另一种形式:“为了通达真理,我应当如何改变自己?”(18)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171-172页、中译本第191-192页、英译本第177-178页。
1.1 一般资料 选取淮安市第一人民医院2015年6月至2017年10月收治的132例房颤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分为地高辛组及观察组,每组各66例。地高辛组:男性34例,女性32例;平均年龄(58.27±12.05)岁;心功能Ⅰ级17例,Ⅱ级29例,Ⅲ级20例。观察组:男性37例,女性29例;平均年龄(57.91±13.02)岁;心功能Ⅰ级19例,Ⅱ级30例,Ⅲ级17例。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酒店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想办法改变人力资源的策略,提高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使“流入”的知识、能力、素质的比例日渐高于“流出”的知识、能力、素质所占比重。通过高素质人才的引进逐渐更替较低层次水平的员工,使酒店员工整体素质与水平得到提升。
在1982年2月17日的授课中,福柯明确,主体必须“转向自身”,通过“自我关注”来达到合乎伦理的修身实践,“自我关注”是人生的永恒法则,是生命存在的象征。为此,他引证了许多希腊化时期斯多葛派学者关于“转向自身”“回归自身”“关注自身”的表达文字,如:eph’heauton epistrephein(埃比克泰德语),eis heauton anakh?rein(马克·奥勒留语),ad se recurrere(塞涅卡语),ad se redire(塞涅卡语),in se recedere(塞涅卡语),se reducere in tutum(塞涅卡语)等等。(7)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37-238页、中译本第263页、英译本第248页。如其所见,必须思考这种修身实践在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因为在当今时代,“转向自身”“回归自身”“关注自身”的本来意义已完全丧失,人们在社会机制的约束下,要活出本色难之又难。
总而言之,“自我关注”与“生活技艺”是合一的。在“主体解释学”课程的最后时刻,福柯总结道:“‘生活’,我所说的生活是一种考验,藉此世界在我们的生存经历中即刻呈现,它有两层意思。体验层面的考验,即经过我们体验自我,我们认识自我,我们发现自我,我们揭露自我,这个世界才被认为已然存在。再者,考验在这个世界,这个生活的意义上也是一种修行,即基于它,凭借它,缘于它,我们塑造自我,我们改变自我,朝向一个目的或拯救前进,或迈向我们自身的圆满境界。我认为,事实上,凭借‘生活’,世界成了依靠我们认识自我的这种体验,成了依靠我们转化自我或者保存自我的这种修行,就古希腊思想而论,这是一种转化,一种极其重要的转变,在此之中,‘生活’应当是‘技艺’的对象,亦即一种理性的与合理的技艺对象。”(21)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466页、中译本第505-506页、英译本第486-487页。这是福柯回归修身哲学的最终归宿之所在。
四、结语
如果哲学是关于“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那么主体如何能够得到体证?这是困扰福柯多年的问题。实际上,在福柯的思想中,人要“如何成为自我”已经不再是“认知性”的问题,而是“精神性”的问题,亦即生命主体的修行之道与归隐之途的问题。犹如马克·奥勒留所说的那样,人们寻求退隐自身、隐居乡村。归隐乡间即是一种回归自我,一种主体退回内部的“自我修行”。[15](PP.36-37)凭借这种实践活动,人能够同化真理,并将其转化为日常生活的具体行为,形成一种永久性的生活风格。
为了体证“欲望身体”的意义,福柯还曾在一座禅宗庙宇中进行过坐禅修行,以此来领会东西方对待欲望的不同方式。在他看来,尽管禅佛教和基督教两者都重视修行,但对待“欲望身体”的态度并不相同。基督教是通过忏悔来审查身体,来了解是否有可耻行为在酝酿或发生,于是身体自然成了问题,欲望因此受到质疑。禅宗则是通过坐禅修行来把握“欲望身体”,它与基督教的忏悔活动截然不同,在禅修过程中,身体能够直接充当载体,修行实践为达某种境界而进行。[16](P.466)
关于建筑业的绿色化发展,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对我国绿色建筑的发展造成了障碍,同时也造成了能源浪费,不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
东方禅道的那种以“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的实践修行不知福柯是否能够理解,然而,那种求诸内心的言语道断、不杂不染、百物不思的境界却可圆融为一。因为,唯有此道方能心体与万物同归于寂,方能达到精神的宁静与安详。福柯的哲学就在于思考自己的历史(过去),使自己摆脱所思之物(现在),并最终以非思的方式思考(未来)。[9](P.465)
思考自己的过去,即如尼采那样,重估一切价值,揭示现行诸类思想弊病的缘由,从而理解西方文化在“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的双重进程中,知识-权力-道德机制对人本身的规训与征服。摆脱所思的事物,即通过对古希腊罗马时期修身实践与生活技艺的领会,而对自己的生命体验进行沉思,将所理解的人生修行转变成一种气质,一种风格,一种态度,以便满足哲学与非哲学生活方式的要求。以非思的方式思考,即以自己独特的天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照亮思想运动,努力更新哲学活体,自我转化,自我超越,像古代雅典的第欧根尼一样,傲世轻物,自由自在,回归内心,获得非哲学意味的离言体验。
晚年,福柯受到疾病的困扰,个人的危机迫使他转向自己的内心深处,因为死神已在蹂躏着他的肉体。他试图改变自己,希望把自己的生活塑造成一件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风格”的作品,超越诸种限制,超越一切生死。(22)此处参见《主体解释学》法文本第273页、中译本第300页、英译本第285页。倘若如此,那么“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就成了哲人生命的最好选择,也是纯然正义的“归隐”选择。
参考文献:
[1] 陈群志:《阿道与福柯的修身哲学之争》,《世界哲学》,2015年第6期。
[2] 何乏笔:《自我发现与自我创造:阿道与福柯修养论之差异》,黄瑞琪主编:《再见福柯:福柯晚期思想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3] P. Hadot, PhilosophyasaWayofLife:SpiritualExercisesfromSocratestoFoucault, ed and intro., Arnold I. Davidson, trans., Michael Chase,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1995.
[4]M.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in P. Rabinow, ed., RobertHurleyandOthers, trans.,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The Essential works of Foucault, 1954-1984; vol.1),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7.
[5]何乏笔:《修养与批判:福柯〈主体诠释学〉初探》,《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5年第3期。
[6] M. Foucault, “On The Genealogy of Ethics: An Overview of Work In Progress”, in Ethics:SubjectivityandTruth(TheEssentialworksofFoucault, 1954-1984; vol.1),P. Rabinow,ed., Robert Hurley and other, trans., New York:The New Press,1997.
[7]于奇智:《从康德问题到福柯问题的变迁——以启蒙运动和人文科学考古学为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5期。
[8] M. Foucault, “The Ethics of the Concern for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in Ethics:SubjectivityandTruth(TheEssentialworksofFoucault, 1954-1984; vol.1).
[9]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高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0]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1] M. Foucault, “Qu’est-ce que les Lumieres?” , inMagazinelittéraire, No.309, 1993.
[12]吉尔·德勒兹:《福柯 褶子》,于奇智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
[13]高宣扬:《当代法国哲学导论》上册,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
[14] M. Foucault, “Subjectivity and Truth”, in Ethics:SubjectivityandTruth(TheEssentialworksofFoucault, 1954-1984; vol.1).
[15]马可·奥勒留:《沉思录》,何怀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
[16]福柯:《福柯集》,杜小真选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
OnFoucault’sTheoryofSelf-relationsinthePhilosophyofSelf-cultivation
CHEN Qun-zhi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period of Michel Foucault, he tried to explore how to resist the restriction of knowledge-power relationship.He pondered for years before coming up with the answer, which was embodied in a discussion of “self-rela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elf-cultivation” during the ancient Greek-Roman period. However, Pierre Hadot criticized Foucault’s interpretation as too aesthetic and thus ignoring the need for “universal reason”. In fact, Foucault’s exploration on the connotation of “self-relations” in the issue of self-cultivation is not as such criticized by Hadot, as it also explains the universality. The reason why he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self-relations” model in Hellenistic period is that it not only emphasizes the practice of “self-transformation” of the way of life and spirit, but also carries out a kind of appeal to plunge oneself into the totality of the world.
Key words: Foucault; self-cultivation philosophy; self-relations; self-concern; techniques of life
中图分类号:B5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5-0073-07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5.007
收稿日期:2019-06-2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时间理论研究”(19BZX1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陈群志,中山大学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时间哲学与心性现象学、修身哲学与修身伦理等研究。
标签:自我论文; 主体论文; 希腊论文; 法文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时间理论研究”(19BZX101)的研究成果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