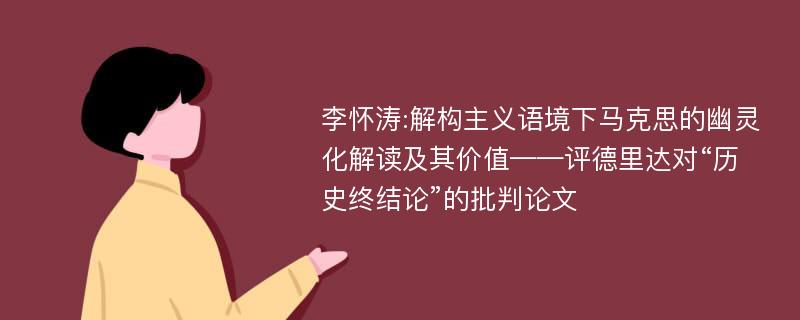
摘要:苏东剧变后,美国学者福山借用历史终结论进一步倾轧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存在空间。为了驳斥历史终结论,同时力证马克思在新的世界形势下存在的意义,德里达运用解构主义的方法,对马克思做了幽灵化的解读。他强调解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一致,进而运用解构主义延宕、异质性、不在场的在场等方法解读出幽灵化的马克思,并真诚地向世人宣称这是人类不可丢失的宝贵遗产。但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方法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所保卫的幽灵化的马克思是难以超越现代性的。
关键词:德里达;历史终结论;解构主义;幽灵化的马克思
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福山借苏东剧变指出自由民主制度不存在以往诸种制度的缺陷和根本性矛盾,因而资本主义将因此成为“历史的终点和降临人间的福音”。[1]这种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自然就宣告破产了,恐将成为永远的过去式。这种论调受到了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历史终结论广泛传播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暗合了彼时西方世界对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敌对心态。他认为马克思不需要为苏东剧变负责,因为马克思不再附着于一种实际的制度上,而是变成了幽灵。他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对马克思做出了幽灵化的解读,他认为马克思以幽灵的形式继续存在并时刻影响着我们。
一 德里达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
1993年,在美国一场以马克思为主题的研讨会上,德里达呼吁人们在资本主义的“胜利”面前保持冷静,理性反思马克思及其遗产的重要价值,他率先展开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德里达将历史终结论划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范畴,将其看作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当代延展。他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福山毫不犹豫地走向了黑格尔,并将后者“为得到承认而斗争”的国家的观念进一步演进成“基督教眼界有优先地位”的国家,而这种认识在本质上“与目前罗马教皇关于欧洲共同体的话语是一致的”。[2]由此,历史终结论所描述的那种人类发展的完善形式就与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的那种对共产主义进行联合围剿的欧洲旧势力联合具有了某种同质性,二者均带有对马克思的强烈敌意,反映出福山对国家的认识仍然未能摆脱黑格尔哲学的国家认识范式。
对黑格尔国家观念的追随导致福山在解释现实问题时陷入了思辨哲学的泥淖之中。面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诸如恐怖主义、种族灭绝等问题,福山试图将其弱化为“事件”,这种做法被德里达贬损为自欺欺人的“修辞艺术”和“耍花招”,认为这是企图通过理想与现实的游离来干扰视听,将那些有悖于自由民主制度“完满性”的情况完全搁置。德里达就此认为,福山无法克服的矛盾以及他处理这一矛盾时表现出的那种主观任意性,恰恰是“历史终结论”谬误的最有力证明。尽管福山本人非常明确这一点,但他以及那些推崇“历史终结论”的人们仍在掩耳盗铃,因为他们始终不愿承认自由民主制度实际上同完善的社会理想相差甚远。
德里达认为,历史终结论的广泛传播是独断主义愈演愈烈的表现。他指出,现在我们处于一个脱节的时代,“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谋求通过建立起前所未有的霸权形式,而使一个新的、自然是新的动乱稳定下来”。[3]在此背景下,一种独断主义的新形式霸权正在悄然形成着,其主要表现是通过反复宣判马克思的死亡并在同一时间鼓吹市场经济万能论,以期将资本主义社会包装成人类社会发展的“终章”,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与政治自由美化为全人类谋求幸福的“福音”。德里达将这种做法指认为西方世界针对马克思的一次集体密谋,而历史终结论是同这次密谋有关的言论中“最喧闹、最中立、最成功的”。
但是,德里达并没有完全否定这种时代的脱节,因为他强调只有这种脱节,这种历史发展的断裂才能为幽灵的出场开辟空间,他还批判了海德格尔对断裂的否定性理解。海德格尔认为,古希腊人是由在场之统一性中经验在场者的,在场者的经验具有聚集属性。海德格尔指出:“自早期思想以来,‘存在’就是指澄明着——遮蔽着的聚集意义上的在场者之在场,而Logos就是作为这种聚集而被思考和命名的。”[4]因此,海德格尔那里的断裂是消极的,是一种暂时性、否定性的状态。但是,德里达却凭借自身的解构分析,发掘出了断裂的另一层内涵——在场者得以在场的真正前提,并且将断裂定义为一种于在场者而言早已内嵌于解构活动中的先决条件,“必要的裂隙或者说正义的祛总体化的条件在此实际上就是在场者的条件——同时也是在场者和在场者在场的真正条件……这个条件本身就在结构活动之中,且仍然在也必须在(这就是指令)Un-fug的裂隙中”。[5]德里达认为,正是这种裂缝,这种不断打破总体性的解构所产生的裂隙,才能为他者的产生提供空间,从而真正展示出解构活动与“在先的异质性”之间的关系,德里达因此反问道:“裂缝不正是他者的可能性本身吗?”[6]因此,幽灵作为一种相较于现实存在者的异质性存在,只有断裂才能让其得以显现,在这个脱节的时代,马克思幽灵化的显现恰逢其时。
二 马克思幽灵化的解构主义解读
面对“马克思已死”的宣判,德里达坚称:“不能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没有对马克思的记忆,没有马克思的遗产,也就没有将来:无论如何得有某个马克思,得有他的才华,至少得有他的某种精神。”[6]他借助《哈姆雷特》的“回魂”场景引出了“幽灵”概念,指出马克思在新世界形势下将以幽灵的方式继续存在,而“现在该维护马克思的幽灵们了”。
作为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所秉承的解构理念既拒斥一切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又质疑任何本质的、确定性的结论,因而他必然对历史终结论及其构建的所谓“新世界秩序”所带有的先天确定性表示激烈反对,“呼吁异质性”成为德里达此时最为迫切的愿望,而马克思主义于西方话语体系中反映出的鲜明的异质性,正是德里达找寻马克思的幽灵的根本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所具备的这一特质被德里达所倡导,却被西方意识形态阵营所排斥,他们如今又策划对马克思幽灵们的再一次联合围剿行动。在德里达看来,这种针对马克思幽灵们的驱魔活动是绝对的错误。
阿里成长到现在,也遇到许多批评指责。不少批评是中肯的,但是有的指责则是恶意的。船大了,风就来了嘛,我们“借假修真”,修出自己的真材实料。就拿我的脾气来说,过去一点就爆,现在也好多了。
在《哈姆雷特》中,老哈姆雷特的肉体已经死亡,却以幽灵的形式反复显现,最终引导哈姆雷特走上复仇之路。老哈姆雷特的幽灵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存在,一种始终处于形成状态中的肉体,一个众多互为颠倒特质的结合体——非生非死,在场又不在场,可见又不可见。在德里达看来,这些特质恰如其分地表征了马克思在当今世界的境遇,它并未彻底死去,而是变为幽灵,以一种显隐不定的状态继续存在、显现。德里达将马克思的幽灵的在场视作一种非存在的实在性在场,它始终注视着我们并向我们发送指令。德里达指出,马克思的幽灵承载着他的精神,与一般的幽灵相异的是,马克思的幽灵是具有实在性的,近似于拉康口中“大写的真实”。他将幽灵的显现视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我们不能时刻感知马克思的幽灵,它被“面甲效果”所遮蔽;另一方面,我们恰逢脱节的时代,现实的错位与断裂又为幽灵显现提供了机会,但幽灵不能自为地显现,必须凭借解构才能对其加以把握。德里达指出,《共产党宣言》中所显露出来的最为醒目的东西就是幽灵,是“第一个父亲般的角色”,马克思这位“慈父”正如老哈姆雷特的亡灵向哈姆雷特所做的那般向我们发送着指令。此外,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是复数的,包括《共产党宣言》中的共产主义理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旧哲学家们的清算以及《资本论》中的商品和货币幻影等等在内都是幽灵,它们正在并且将继续以一种资本主义末世论潮流中的异质性成分而存在并发挥作用。
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幽灵是马克思最为宝贵的精神,主要表现为激进的批判精神,正是它促使马克思主义不断地进行自我革新,在当前的新形势下依旧保持着活力。但是,德里达所指涉的马克思的幽灵并非“固定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躯干上”的具有统一性与整体性的马克思主义,即通常意义上理解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的理论,而是借助解构才能捕捉到的“好的马克思主义”。德里达将其规定为一种不断自我否定进而取得发展的激进的批判精神,“要想继续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中汲取灵感,就必须忠实于总是在原则上构成马克思主义而且首要地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批判的东西……这种批判在原则上显然是自愿接受它自身的变革、价值重估和自我再阐释的”。[7]在他看来,马克思借由文本向我们展示的恰是一种解构的方法,它提醒人们应该对周围的一切知识时刻保持警惕,与此同时不断地展开理论革新与知识的重构以保持理论活力,正是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批判特质使它即便被宣判“死亡”,依然能够以幽灵的形式“还魂”。除此之外,“好的马克思主义”还包含一种解放精神,一种“弥赛亚式的声明”。德里达认为,解放不仅是一种意识的活动,更是行动、实践、组织等等的新的有效形式。也就是说,德里达推崇的解放,不仅是意识领域的解放,而且是实践领域的解放。在圣经中,“弥赛亚”是拯救者,是依照神谕降福人间的。在德里达看来,他引用了弥赛亚并不是为了强调一种宗教上的“弥赛亚主义”,而是表征一种即将到来的解放状态,他说:“如果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是我永远不打算放弃的话,那它绝不仅仅是一种批判观念或怀疑的姿态,它甚至更主要地是某种解放的或弥赛亚式的声明……”[8]
[6]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33页。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中小零售企业电子商务商业运营模式的市场价值,企业要结合相关性因素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并且针对相应的指标建立对应的管理机制,从创新和发展的角度出发提高电子商务发展转型水平,有效整合创新机制和管理流程,维护管控工作的基本效率。最重要的是,要从思想意识层面形成创新动力,优化创新化产品销售路径和宣传媒介,维护中小零售企业经济运行综合水平。
冯永孝(1993—),男,江苏徐州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为船舶运动控制。E-mail:1596532730@qq.com
预后方面,华盛顿大学Loannou(摘要885)一项研究旨在构建能够预测NAFLD及ALD患者HCC发生风险的模型。模型共纳入年龄、性别、糖尿病、身体体重指数、血小板计数、血白蛋白及AST/ALT比值。该模型有助于判断肝癌风险,制定精准的筛选方案。
德里达对“conjuration”一词进行了解构分析,认为它代表着“密谋”,是决心同某一权力作斗争的共同起誓。不过德里达指出,早在资本主义联手开展对马克思幽灵进行驱魔之前,马克思本人就在《资本论》中进行了这一活动。他回到《雅典的泰门》,解构了马克思对货币进行“幽灵化的非肉身化”的表征过程,指出马克思正是通过批判货币的幽灵化来完成货币拜物教的批判,货币的“幻影”被马克思表述为一种幽灵般的东西,而马克思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将“货币的幽灵效能与在攒钱的欲望中对人死后在另一个世界金钱的用途的沉思做了比较”来反对这个幽灵,召唤它同时反过来驱除它。此外,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针对德国旧哲学的清算,也被德里达视为“一场针对鬼魂们和亡魂们或鬼怪的不可阻挡的和没完没了的围剿”,一次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激进的彻底的颠覆。在此意义上,西方世界对马克思进行的驱魔活动,反映出人们依然为共产主义的幽灵而焦虑不安,它在过去的世界和现在的世界中依然被视作一种威胁,只能通过反复确证它的死亡来确证死者已死,它的目的是为了确认死亡,但真实的动机却是驱魔者“说服自己让自己放心”,一种“行为性陈述”。
在德里达看来,驱魔活动还发挥着另一重作用,即反向唤醒了我们对于幽灵的记忆。德里达指出,“conjuration”不仅代表着“密谋”,还在英文中翻译为“咒语”,表示召唤某种魔法或精神。因此,“conjuration”还可被解读为一种反复吟诵宣判死者已死的咒语的活动。但若我们依照后现代主义的标准去考察,任何一种过于确信的同义反复都必然隐含与逻辑的非同一,进而引发本体论的风险。正因如此,德里达才断言这种针对马克思死亡的反复确认,最终会因这个过程中驱魔者们所表现出的决绝态度而引发人们的质疑,在它想让我们入睡的地方将我们唤醒,其结果不仅是无法使世人遗忘马克思,反而会一再唤醒我们对他的记忆,并在哀悼中反复召唤他的精神。
三 对马克思幽灵化解读的评析
在《马克思的幽灵》中,德里达充分运用解构的方法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互文式的解读。他对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对马克思存在方式的阐释,以及新形势下应如何继承与发展马克思的精神的思考,这些论辩是振聋发聩的。
德里达运用解构主义捍卫马克思的精神,他始终将自己对马克思的捍卫视作一次正义的行动,他并未将视角聚焦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而是选择聚焦于马克思理论的异质性。德里达将马克思的幽灵,尤其是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异质性成分,并反复声明其重要性,“必须有断裂、中断、异质性”。[13]对此,伊格尔顿评价道:“马克思刚到边缘位置,德里达便想靠近它,这样才更符合他的后结构主义打算。”[14]在德里达看来,马克思的幽灵们并不指向任何特定目的,它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体现着某种反同质性的达成,并且人们对马克思异质性精神的继承从来不是一项需要刻意完成的任务,“甚至在我们愿意或者拒绝做他的继承人之前, 这项使命就摆在我们面前了”。[15]因此,任何针对马克思的驱魔活动都是毫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幽灵仍会作为一种共时性存在闪现于人们的思考与行动当中,我们“仍旧是在用马克思主义的语码而说话”。德里达倾向于在任何一种确定性的、本质性的结论面前保持警惕,坚决反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2.要做好水质调控,培育加州鲈鱼苗的水质不能过肥,池水透明度应保持在25~35cm,养殖期间要保持清新的水质和较高的溶氧量,每10~15天需换水1次,每次换水量约占池水的1/3,如能采用微流水或增氧措施养殖,则效果更好。
德里达将马克思的遗产视为整个人类文明的成果,他对马克思的解读,在驳斥历史终结论的同时,也为社会主义国家认清新自由主义所潜藏的西方中心主义价值内核提供了借鉴,进一步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价值。此外,在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这笔“遗产”方面,德里达公开宣称自己已经与中国达成了共识,“在今天,坚持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新危险——进行仍然有生命力的批判”。[16]在新形势下,继续坚守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批判精神,持续对资本主义抱以警惕,是社会主义国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需要思考的问题。
但是,尽管德里达对马克思幽灵们的辩护是发人深省的,我们仍旧需要对解构主义以及幽灵化的马克思抱以审慎态度,要看清这一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首先,德里达对马克思的幽灵化解读以及他所要捍卫的马克思的幽灵,从根本上区别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德里达解构主义方法崇尚异质性与碎片化,而为了论证解构主义方法对于马克思而言的重要价值,德里达选择了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作为中介,试图将其拟写为一种敢于自我分裂与重构的解构主义精神,这显然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抛弃了,这种对马克思的理解无异于“管中窥豹”,他的解构只能得到片面的结论。其次,德里达反复强调新形势下的马克思必须经由解构才能继承,这种做法显然是用后现代主义去确证马克思,这无疑是一种逻辑倒置,尽管他一再强调自己秉承着“不可能决定的决定”的决定论立场,他仍然被很多人纳入虚无主义的阵营中。
德里达试图将解构当成消解西方哲学自古以来的“Logos”中心主义以及由此形成的一系列西方哲学的固有观念的利器,为马克思的幽灵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出场开辟空间。但马克思的精神同德里达所召唤的马克思的幽灵们存有本质差异。马克思是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视角去批判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而德里达不过是从反意识形态霸权以及反逻格斯中心主义的角度去批判资本主义的观念形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对现代性的科学的批判和超越,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则仅仅是一种对现代性的反思,但这种后现代主义却未能成功跳脱现代性的认知范式,而仅仅是这一范式的当代延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幽灵化与其说是借由解构主义来捍卫马克思,不如说是借由马克思来论证解构主义。此外,德里达所擅长的文本“延宕”,常被学者诟病为文字能指与所指的“游戏”,并因此将德里达形容为“概念破坏者”。这种能指的“游戏”和概念的转换不仅令德里达的文字异常晦涩,也为其蒙上了鲜明的“学院派”色彩,未能被大众广泛接受。为了对抗西方的“新世界秩序”,德里达列举了其“十大祸端”,并以此提出“新国际”理念,但“新国际”中的人没有协作、政党、国家和共同体,没有共同归属的阶级,这种被德里达形容为“没有机构组织的联盟友谊的东西”将由于缺少现实的制度支持而止步于观念,因此从根本上区别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想。面对外界对“新国际”无阶级、无政党的质疑与批评,德里达回应他所说的“无政党、无阶级”并不是对阶级的故意忽略,而是“新国际”不需要依附于某个特定阶级才能建立。但是,这种在阶级问题上的含混,恰如马克思主义者批评的那样:“他遗弃了阶级、国家、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概念,但他所宣扬的这些概念无法构成革命政治学的基础”。[17]
进入21世纪,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辉煌,加之西方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福山也不得不转变自身立场。在《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福山虽然没有放弃历史终结论,却也承认它的实现过程充满了“难以想象的复杂性”。德里达对于福山的批判,他的解构主义方法对于马克思幽灵化的解读的理论得失,让我们更好地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更好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
注释:
分别以G40沪陕高速公路、G2京沪高速公路中的某互通为研究实例,对3路和4路相交互通增设匝道的具体设计进行系统分析:
图2显示了全球自动驾驶技术公开专利申请排名前10 的国家或组织分布。可以明显看出,全球自动驾驶技术专利公开国(组织)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差距,中国凭借14 407件公开专利申请排名第1,专利总公开数量大约是美国的2倍。总排名前5 的其他国家(组织)分别为美国、日本、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欧洲专利局。从各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请的2677件公开专利来看,各国也比较注重《专利合作协定》PCT国际专利的申请,申请总量位居专利公开排名第4。
[1]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9页。
对于乳罩,从原则上讲,孕期是不主张戴的。只是女性从青春期就开始戴,怀孕后突然不戴了会感觉很不习惯。如果戴的话,建议孕妈妈选择宽松、舒适的乳罩,棉质乳罩比人造纤维的舒服些,透气性也好。另外,还要注意乳罩的尺寸。孕妈妈最好去母婴用品店或大的商场买,自己亲自试一下,还可以请有经验的售货员帮助选择。
[2]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80页。
[3]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52页。
[4]马丁·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372页。
[5]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29页。
关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的意义,伊格尔顿曾总结道:“马克思主义……已经与现代文明交融在一起,像牛顿对于启蒙运动的重要意义一样,已成了我们历史无意识中的一大部分。”[9]德里达认同伊格尔顿对马克思主义的肯定性理解,并进一步将马克思的诸种精神形容为留给后人的一笔重要遗产,即“在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正式名字下写入历史记忆的诸种精神之一”,它代表着马克思的精神已经融入人类文化当中,无论我们是否认同它都是他的继承人。德里达认为,马克思的精神所具有的根本的和必要的异质性,那种必须通过自我拆解、分离和延宕之后才能成为自身的解构主义特质,在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而言愈发珍贵。此外,由于遗产是对债务“批判的、有选择的和过滤的再确认”,因此一笔遗产必然伴随一项债务,我们必须在继承马克思的遗产的同时自觉承担起它所绑定的债务,而马克思的遗产所绑定的债务于我们而言是“不可磨灭且无法还清的”,那是因为:一方面,无论人们对其尚未认识抑或是有意反抗,都无法磨灭马克思为人类留下的思维印刻,将这笔债务抵消;另一方面,这笔债务依然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暗地里构造所有哲学或所有有关哲学问题的思考的政治哲学中”。[10]
德里达认为,目前西方世界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驱魔,根本上缘于资本主义社会对共产主义幽灵终将显形的恐惧,他指出:“《共产党宣言》中说全世界的共产党、共产国际将是那幽灵的最终化身或实际在场,因而也是那幽灵的终结。”[11]马克思在世时,共产主义仍似幽灵般游走于欧陆大地,他借助历史唯物主义预言了幽灵显形的必然性,同时激发了欧洲神圣同盟对共产主义幽灵的疯狂围剿。德里达认为,即便在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的背景之下,共产主义已经不再是历史的必然,但它却化为永远“即将到来”的幽灵,“共产主义一直而且将仍然是幽灵的;它总是处于来临的状况”。但是,即便是这种幽灵化的共产主义,仍然足以引发资本主义世界的恐惧,如今不再是幽灵的显形,仅仅是这种存在的可能性就早已迫使西方社会展开驱魔活动。他指出,西方世界一直希望借社会主义运动走入低潮之机对世界的权利版图进行重新分割,以颠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构建的世界格局,推行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新世界秩序”。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的幽灵时常令他们感到不安,“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12]
[8]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90页。
死体可燃物含水率(Y)与降水(X1)、相对湿度(X3)、连旱天数(X4)、风速(X5)、蒸发量(X6)之间的数学模型为:
[7]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89页。
[9]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马海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8页。
[10]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92页。
[11]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100页。
[12]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38页。
[13]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36页。
王荣(1984.05-),女,上海,国家建筑信息模型(BIM)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助理研究员/经济师,南京工业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在职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建筑产业现代化,工程建设标准化、建筑信息模型BIM。
[14]特里·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第120页。
[15]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第56页。
[16]杜小真、张宁编:《德里达中国演讲录》,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17]阿比奈特:《现代性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技术与社会变革》,王维先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5页。
中图分类号:B5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19)04-0117-06
基金项目: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国外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及其方法论研究”(18YJA710025)
作者简介:李怀涛,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100037;敬沁,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北京市,100037。
责任编辑 顾伟伟
标签:马克思论文; 幽灵论文; 德里达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福山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新视野》2019年第4期论文; 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 国外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批判及其方法论研究"; (18YJA710025)论文;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