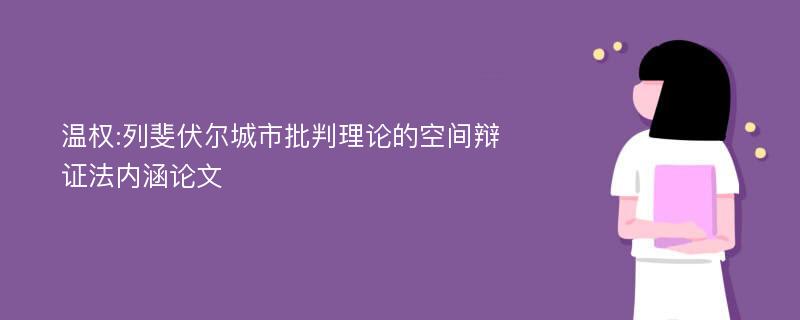
摘 要:列斐伏尔的城市思想是其日常生活批判的有机延伸。通过建构社会空间的三元辩证法,他试图从“它者”或“第三项”的元哲学语境中,诠释以“差异空间”为前提的现代城市乌托邦,对以“抽象空间”为座架的资本空间再生产机制的消解作用。其理论始基,则是在“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象征空间”“抽象空间-空间矛盾-差异空间”以及“资本-土地-劳动”三组三元辩证体系中,对资本主义缘何长期幸存这一问题的深刻剖析,和对日常生活-城市革命的激进展望。据此,列斐伏尔在空间辩证法的开放视域中,重新定位了马克思实践理论同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阶级斗争学说的内在统一;进而,以城市为切入点,勾勒出在资本剥削方式已发生转向的情境下,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当代路线图。
关键词:空间三元辩证法;空间实践;差异空间;日常生活;城市革命
20世纪60年代,列斐伏尔的研究旨趣从日常生活批判转向城市空间反思。对此,他曾明确指出,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既“包括对都市现实的批判分析,另一方面包括对日常生活的批判分析;实际上,日常生活与城市,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分析建立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ensemble)之上”。①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页。这表明,列斐伏尔学术聚焦的游移,实则揭示出他对嵌套在资本生产范式下的社会总体实践进行的检视在不断深化。而后者又引申出一条解读马克思经典社会批判理论的三元空间辩证法线索。其中,涉及以下三方面内容:
一方面,从元哲学的视角来看,建基于日常生活之上的现代城市空间,可视为涵盖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并标志其特殊空间形态或构型的“空间实践”(La pratique spatiale),同社会关系在其中被权力秩序强行编码的“空间表象”(Les reprèsentation de l’espace),以及隐匿于或意欲逃离现行权力结构并以符号形式呈现的“象征空间”(Les espace de reprèsentation)三者的辩证统一。①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7,p.33.据此,列斐伏尔指出,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幸存,毋宁说是受资本逻辑操控的“空间表象”所传递出的抽象权力对总体性的“空间实践”进行异化,并篡改“象征空间”的社会性后果。这同时意味着,资本在社会空间内的商品生产,已转化为它对空间本身的生产,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另一方面,从政治学的层面来讲,为资本逻辑建构并维系资本空间再生产机制的均质化“抽象空间”,尽管实现了对城市多元日常生活的拜物教化,但遵循资本生产与交换法则而零分碎切的社会空间,被纳入等级性的资本权力秩序时,资本的抽象整体性与空间的碎片性彼此间的蹩脚关系,势必产生扰动资本主义政权(即国家)的“空间矛盾”。而后者不啻为列斐伏尔在“它者”视域下,提出能够超越资本二元矛盾的“差异空间”,并建构克服资本异化的城市乌托邦的必要前提。值得一提的是,“抽象空间-空间矛盾-差异空间”的三元辩证关系,又引申出列斐伏尔对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重新定位。在马克思于《资本论》结尾处有关“资本-土地-劳动”三位一体关系的论述中,列斐伏尔最终找到以日常生活-空间批判为理论依据的城市革命,对资本主义制度予以瓦解的实践合法性。
一、资本残存与“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象征空间”的三元辩证法
资本主义在当代的长期幸存及其对日常生活的不断殖民,是列斐伏尔建构城市空间批判理论的直接诱因。对此,他专门指出,“在《资本论》问世后的近百年中,资本主义业已发现自己能够淡化自身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内部矛盾,并成功获取了全新的‘发展’契机。尽管我们无法估算其代价,但却深知其手段:占有并生产出一种空间”。②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76,p.21.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资本的空间生产究竟以何种方式促使资本主义制度规避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风险?以及,它在何种意义上营造出符合资本当前积累节奏的城市景观?围绕上述议题,列斐伏尔首先指认了以“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象征空间”为支点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并对其在资本生产结构中产生的社会效应进行了深刻的元哲学反思。从学理上来看,这又与他对日常生活实践得以展开的社会空间之内在属性的重新定位密切相关。
关于算法1,接下来针对其性能进行量化分析.由于算法1中是对pu做目标函数加扰的差分隐私保护处理,因此是对pu的性能进行分析.
作为重构西方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的大胆尝试,列斐伏尔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视为一种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s concretes),并强调,“其抽象性表现在它所有组成部分的可交换性,故而无物持存;其具体性则反映为,它在社会意义上真实不虚,并因此能被定位出来”。③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342.显然,由抽象和具体的辩证统一所标识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二重性,实则是以抽象劳动与价值交换为核心的资本逻辑在现实层面的投射。马克思在谈及商品价值与货币的关系时,曾旁敲侧击地说明,以抽象劳动为前提,“为了在观念上决定产品的价值,只要在头脑中进行这种形态变化就够了(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产品单纯作为量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存在)。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这种抽象就够了;而在实际交换中,这种抽象又必须对象化,象征化,通过一种符号来实现”。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88页。从中不难看出,当抽象的生产和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交换取消物的实体性之后,商品(或产品)由以产生的具体实践过程就被纳入抽象的资本逻辑当中。藉此,资本就赋予社会空间的抽象特质以物质力量,并促使其凌驾于具体性之上。与之相对应,“空间也就不再是一种中性的中介,而毋宁说是能够创造、现实化和分配剩余价值的地域性集合。它成为社会劳动的产品,生产的最一般的客体,以及剩余价值形式的结果”。①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Minnesoda: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2009,p.155.这就引申出被资本逻辑的抽象权力编码的“空间表象”,对总体性的“空间实践”的异化效应。后者既体现为资本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又反映为资本逻辑对“象征空间”的篡改。
实际上,通过对马克思“土地-资本-劳动”三位一体公式的空间辩证法解读,列斐伏尔试图从相反的方向明确城市革命的基本任务。而后者由于具体侧重点的不同,将在作用机理和实践指向上同时囊括以下两方面内容:
一方面,列斐伏尔认为,在资本生产的对象从具体的商品跃迁至整个社会空间的情境下,“与过去的符号和象征(自然的、美学的、宗教的、伦理的)相比,空间变得没有意义(insignifiant)了,而同时,与物品在符号学上那些新的方面相比,空间又是具有超级意义(super-signifiant)的了(超物体)”。②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第88页。所谓“具有超级意义”的“超物体”,无疑表明,资本化的社会空间已成为传递资本的抽象权力,并将事物及其附随的实践性要素全部纳入资本异化秩序的物质性载体。它意味着,个体或人类总体的日常生活实践将沦为资本空间规划的附属品。而“处于问题核心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过程……则在每一个社会行动中得以完成。这既包括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又涵盖诸如休闲、日常生活、居所和栖息地、对空间场所的使用,以及全球化的主体等各方面内容”。③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Maiden 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ing,2000,p.187.换言之,资本的空间生产已然将“空间表象”强化为具有物质力量的意识形态。进而,成功操控了以日常生活为座架的“空间实践”过程。而其突出例证,就是遵循资本理性得以规划并予以建构的现代城市景观,对下辖居民的社会性规训。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主要体现在,“每一个城镇的详细规划都隐含着一个日常生活计划。无论清晰与否,城镇的详细规划都涉及人的、生活的和世界的整个观念。在我们的新城里,项目或计划都是明显的。……人们像打包一样对待日常生活……这种现代性安排了他们反反复复的行为举止”。④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04页。正因为如此,以城市为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才成为资本社会关系持续再生产的异化场域。与此同时,“这些关系又深入到社会深层……在个人、肉体、行为举止的层面复制出一般的法律和政府的形式”,并体现出“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效应”。⑤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28、32页。究其实质,这无疑突显出,作为资本权力能指的“空间表象”及其连带的抽象符号编码体系,对日常生活中生动的“空间实践”展开的“知识性”规训。诚如马克思所言,“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而马克思所指认的“一般政治”,在列斐伏尔那里,毋宁说是操控“空间实践”样态,并维系资本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的资本“空间表象”所传递出的知识性权力集合。
被资本逻辑编码的“空间表象”对“空间实践”和“象征空间”的双重异化,可视为传递资本抽象权力并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的“抽象空间”向日常生活不断外化的过程。由此产生的社会后果,毋宁说是“之前处在抽象空间内的观念,被投射于社会空间当中且与带有明确指向的策略相关联。当它们获得可以展开的条件并与世俗相面对时……包括心理和社会在内的自我探索就处于被设计的生存空间当中”。①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p.197.显然,该论断以黑格尔式的口吻指认了寓于资本“抽象空间”的“观念性”权力对日常生活的统治过程。而这无疑牵涉出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批判向度。对此,他进一步指出,“这个生产出来的对象(社会存在——笔者注)跨过抽象,没有消失在抽象里,也没有离开抽象。抽象并非是某种事物具体的复制,但抽象和具体是不可分的,抽象和具体的统一决定了日常生活”。②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672—673页。言下之意,就是说为资本操控的日常生活实际上是作为整体的资本抽象权力,同资本抽象权力的具体社会性表达相混合的二元性存在。
应当说,为资本逻辑操控的“空间实践”“空间表象”与“象征空间”,三者在日常生活领域和社会空间层面的三元辩证关系,构成列斐伏尔解读资本主义制度在当今幸存之内在原因的根本出发点。据此,他不但揭示出,用于缓解资本生产结构之内部矛盾的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机制,是承载并传递资本抽象权力的“空间表象”对总体性的“空间实践”进行异化的结果;而且还指出,资本逻辑消除外部风险的直接手段,是把作为“它者”的“象征空间”整合进异化的社会关系再生产进程当中。而现代城市景观恰好是资本实现以上诉求的最佳场域和直接产物。因此,“资本主义创造了城市;城市创造了一种折射其复杂多变现实的意识;然而这种意识使注意力偏离了支撑城市生产和功能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首要力量,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大秘密”。⑤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南京: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17页。换言之,资本在歪曲社会空间之三元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所构建出的城市景观,实则是异化的“空间实践”、传递资本抽象权力的“空间表象”和被篡改的“象征空间”彼此融合而成的“抽象空间”。它通过消除与资本积累的即时性诉求相左的“它者”,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长时段的空间性再生产及其政治霸权。
二、政治冲突与“抽象空间-空间矛盾-差异空间”的三元辩证法
无独有偶,在另一方面,资本化的“空间表象”又凭借抽象的知识性符码体系,篡改了原本独立于资本生产节奏之外的“象征空间”所蕴含的超越意义。而后者通常标志着与资本逻辑保持距离的自律性艺术或文化创造的可能。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尽管它只能以美学或伦理性的无力反讽唤起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信任,但毕竟透过一种神秘力量揭示出,“日常生活是由矛盾定义的:幻觉和真相、力量和无助、人控制的部分和人不控制的部分交织在一起”。⑦参见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倪晓晖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4—20页。鉴于此,“象征空间”就能被视为与“空间实践”密切相关,且构成资本“空间表象”之“它者”的绝对性存在。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表现为以日常生活、家庭、城市,乃至全球为坐标的剩余价值实现、分配与消费的空间性再生产;还反映在对决定社会功能的艺术、文化、科学以及其他领域的再生产”。⑧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p.96.如此一来,“象征空间”就成为资本“空间表象”之符号能指的具体所指,其言说范围也因此囿于资本逻辑的一元叙事所设定的限度之内。这直接体现为,社会空间当中的均质化抽象劳动,对创造性实践活动的褫夺。其中,“无处不在的机械重复打败了别具一格,人造与设计的东西将自发和自然的东西从各个领域驱逐出去。总之,此时产品已然战胜了作品”。①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76.值得一提的是,该状况毋宁说是与工业文明媾和的货币形而上学在日常生活与社会空间两个维度的具象化。马克思曾指出,“作为财富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物质上和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175页。遵循这一论断,列斐伏尔进一步强调,为了达成这一目的,资本理性和工业技术既要完全占有“空间实践”背后的时间尺度,还要把“象征空间”内的创造性时间转化为纯粹用于商品生产的线性时间。③该观点在《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和《空间的生产》两书的对照解读中可以得到印证。列斐伏尔在《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中曾谈道:“理性和工业技术已经打破了循环时间。现代人让他自己独立于循环时间。现代人控制着循环时间。这种控制首先体现为干扰了时间循环。循环时间被与轨迹或距离一起考虑的线性时间替代。”(参见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第277页)至于线性时间的性质及其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中的作用,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从史学角度出发并以城市为坐标专门予以说明。他指出,“处于社会转型期的16世纪,空间和时间都城市化了。换言之,商品和商人,连同与之相关的举措、账簿、合同契约以及承包商的时间和空间都获得了主导地位。此时,时间以与可交换商品的生产、运输、出售以及资本配置的形式,为测量空间服务”。(Cf.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p.277-278)因此可以推知,列斐伏尔就线性时间对循环时间的替代,及其之于空间的从属地位的指认,实则隐晦地表明,资本逻辑对“空间实践”及由此可能产生的“象征空间”的瓦解。况且,马克思在《1857—1858政治经济学手稿》当中也曾提到:“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16页]显然,按照列斐伏尔的理解,所谓“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无疑是用资本化的线性时间去消灭与资本积累要求不符的“它者”空间。其中,当然包含对资本生产来说不合时宜的“象征空间”。这样一来,资本“物”的丰裕性就彻底取代了实践中“人”的尺度,成为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与此同时,“对于城市而言,为资本的丰裕性所修饰的空虚性与谵妄性,在产生双重遮蔽效应时,又引起了更为严重的盲目性。它挪用了对象与产品,以及工业化之前各时代的技术与科学性操作。于是,城市被隐匿了,它远离了思想,并因此自我遮蔽且逐渐凝定于远离真实的所谓资本逻辑的清晰性当中”。④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pp.40-41.在列斐伏尔看来,这无异于资本的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策略在当代的最大狡计。
(4)综合考虑投资收益、相邻空冷岛凝汽器的投资、复杂性、运行调节难度和阀门的可靠性、严密性要求,空冷凝汽器散热面积增加16.7%或33.3%较为合理,即扩大利用临机空冷岛的1排或2排空冷散热器组最优。
第一,消解以资本土地所有制和资本雇佣劳动为支点的城市拜物教空间。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与乡村土地资本化效应引起的城市化趋势密切相关。马克思认为,作为资本生产的必要条件,“雇佣劳动就其总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从而使原本作为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变成了纯粹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34页。于是,伴随着社会关系的转向,以及生产者自身劳动属性与空间定位的更迭,资本主义就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交换……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人口的精神生活”。③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从中不难看出,由资本逻辑催生的现代城市景观,奠定了资本之于“劳动-空间”关系的决定性作用。这不仅体现在,植根于其上的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而且意味着由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者的倒错结构所主导的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其矛盾聚焦点就在城市空间之内。据此,列斐伏尔认为,城市革命是继工业革命取代传统农业文明之后,能够进一步推动社会形态变迁,并祛除资本异化因素的历史必然。他强调:“工业革命与城市革命是世界激进变革的两个方面。它们是同一过程、同一理念,即全球革命的两个要素(辩证统一)。只不过后者的重要性恰恰在于它不再屈从于前者,而是把社会实践从资本生产中剥离出来,进而导向总体性的城市实践。”⑤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pp.144-145.至于总体性的城市实践,毋宁说是指向“差异空间”的日常生活批判,在“空间实践”领域的具象化。它预示着一种可能的社会存在样态。“在这个社会里,一旦‘劳动者们’掌握了他们如何不同于其他人,他们就会带着他们异化劳动的伤疤,带着旧的特殊性而消失。……因此,这个可能的社会将避免抽象的和强制的一致性。因为差异中的平等是具体的。”⑥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第634页。换言之,列斐伏尔所谓的城市革命,可视为对差异性城市乌托邦的激进建构。
这段文字传递出有关“空间矛盾”之政治意义的双重信息。其一,是资本“空间矛盾”的产生与作用机理的政治定位问题。这涉及列斐伏尔对“空间矛盾”的哲学与实证分析两方面内容。对于前者而言,他认为,“空间矛盾”得以产生的形而上学根源,毋宁说是“抽象空间”赖以具象化的社会实践活动自身矛盾性的显现。还原到马克思的语境中可知,由于资本逻辑对空间的均质化效应,在由此形成的货币资本体系中,“正像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9页。于是,实践本身及其对象也成为被资本权力编码的虚无性存在。但同时应当看到,“对象的这种虚无性对意识来说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有肯定的意义,因为对象的这种虚无性正是它自身的非对象性的即抽象的自我确证”。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8页。这就从相反的方面表明,“观念性”的资本抽象权力及其政治实践活动对“真实”的空间对象的操控,是在空间本身的虚无化进程中实现的。它对社会日常生活的宰制,实则反映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除了获得诸如金钱、商品、资本以及抽象空间等抽象物之外一无所有”。③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348.这就在客观上揭示了,资本逻辑的抽象政治架构同社会空间的具体存在样态之间难以弥合的深层罅隙。如此一来,对于后者来说,它在现实层面就转化为,“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追求的是理性,然而在实践中,它却被商业化、碎片化、并被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一些冲突,特别是在抽象的空间(想象的或者观念的、总体性的和战略性的)与直接的、被感知的、实际的、被分隔和被售卖的空间之间”。④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第33页。而“抽象空间”与社会空间的对立又进一步转化为,资本主义国家政权与大众日常生活之间的政治性冲突。对于列斐伏尔来说,后者既表征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压迫,还体现在“以资本生产和社会关系再生产为目标的国家官僚体系,其整体性的空间规划策略及附随的科学技术理性,同用于商业并进行交换的空间碎片之间彼此的拮抗关系”。⑤Henri Lefebvre,Writings on Cities,p.188.因此,寓于资本“抽象空间”之内的“空间矛盾”,可视为资本“空间实践”之异化状况的政治性表达。
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是培养初中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方式之一。语文核心素养的塑造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学生的学习能力在实践中得以提升,从而养成良好的核心素养。例如在讲解《变色龙》的时候,因为文章的情节非常跳跃,文章中的人物又都个性鲜明。为了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文章,教师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每个小组进行自导自演,将课本内容以话剧的形式表演出来。学生感兴趣就能够迅速展开讨论文章、编写台词、设计动作、排练,等等。学生在不断的演绎中更清楚地明白了书中的人物特点,更好地理解了文章。
虽然空间本身既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物,又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工具,但现在这却成为它固有矛盾的体现。也就是说,曾经在时间中出现并通过自身的现实化而表现出的空间辩证法,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开始在空间中发挥作用。这直接表现为,空间矛盾并没有消除从历史时间中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它留在身后,并将旧的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提升至更高的水平。伴随一些矛盾的削弱,另一些矛盾却得到充分的强化。此时,矛盾体系呈现出全新的意义并标志着“某种它者”,即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诞生。⑥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29.
其二,是资本“空间矛盾”对全新社会存在样态的政治引导问题。在列斐伏尔看来,由“空间矛盾”衍生并能够取代资本“抽象空间”的“它者”,才是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关键所在。而“它者”(l’autre)毋宁说是扬弃“抽象空间”并昭示全新的社会生产与实践方式的激进空间构想。其中,蕴含着列斐伏尔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创造性发挥。围绕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二元对立特质,列斐伏尔指出,“在两项中,我们引入了第三方。第三方是‘存在’的一部分……第三方总是那些具有可能性的,正是这种可能性创造了两项或在‘现实’中有区别的主体之间的共同尺度,通过产生误解和最终达成一致的可能性”。⑥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第522页。显然,与资本“抽象空间”的理性必然性形成鲜明对照,“它者”空间无疑预示着超越资本二元对立结构的全新可能性。它引申出“另一个世界,一个彻底开放的元空间,一切事物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新的可能发现与政治策略层出不穷;但在这里人们始终要永不停息,不断进行自我批评,以迈向新的地点和新的认识……这是一个‘他性’的空间,一个‘超越’已知的和理所当然的空间之外的战略性的和异类的空间”。⑦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42页。对此,列斐伏尔将之称作“差异空间”。而“差异空间”的实质则是打破资本逻辑的空间规训,并建构出日常生活之总体性实践得以展开的激进平台。它意味着资本空间生产与再生产过程的终结,以及个体自我批判的开启。从这一点上说,列斐伏尔对“差异空间”的设想,与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并实际地反对和改变现存事物”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5页(译文有改动——译者注)。的激进论断不谋而合。归根结底,它以空间哲学的口吻揭示出实践自身的总体性革命向度。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革命之历时态属性的过分倚重相区别,列斐伏尔所谓“差异空间”对“抽象空间”的扬弃,实则突显出空间辩证法的共时态内涵。他指出,“如同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的辩证法一样。……今天的辩证法不再囿于历史性或历史性的时间,也不再是寓于时间结构内的‘正题-反题-合题’抑或‘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与之相反,这是一种新的悖论性辩证法:它不再依附于时间性”。①Henri Lefebvre,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p.17.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由于空间辩证法的“悖论性”,才真正诠释了植根于“空间矛盾”之上的空间革命,及其衍生的“差异空间”所具有的全部激进内涵。在列斐伏尔看来,尽管“抽象空间”以闭锁的权力秩序赋予主体特定的社会地位或政治立场,但后者却因其潜在的实践多元性,而成为看似透明的资本逻辑无法完全刺穿的不透明容纳物。②Cf.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183.于是,对于主体而言,资本空间就在客观上产生悖论性的镜像效应,即个体认识自身的手段(空间尺度)和结果(空间中的形象),与本真的个体之间持续的建构与解构关系。③按照索亚的解读,列斐伏尔在此实则借用了福柯在“异志地形学”中有关“它者空间”的“镜像理论”。福柯指出,“镜子作为一个无地之地,构成个体审视自我的特殊乌托邦。它促使个体在不真实的虚空间中看到本不在那里的自己。即主体能够通过虚像在自身不在的空间中看到真实的自己”。但福柯同时强调:“由于镜子的存在真实不虚,并对主体所处的位置产生反作用,故而它又是一个异托邦。……它使主体在镜子里看自己的那一刻所占有的空间立即变得绝对真实。与此同时,该空间又变得绝对不真实,因为要被看到就必须越过在该空间处的那个虚点。”(Cf.M.Foucault,“Of Other Space”,translated from the French by Jay Miskowiec,1986)从中不难看出,以镜子为坐标所突显出的空间乌托邦与空间异托邦的辩证关系,实则构成列斐伏尔从“空间矛盾”中引申出“差异空间”的理论始基。而这不啻为列斐伏尔游牧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端。反映到城市政治层面,这直接体现为,原本构成统治阶级和国家权力之政策中心的城市,同时又是分裂资本一元霸权的空间载体。④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第101页。正是由于这种共时态的空间矛盾结构,寓于资本异化空间内的城市革命才具有可能性。
显然,列斐伏尔对资本“抽象空间”所蕴含的“空间矛盾”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差异空间”,这三者间三元辩证关系的深入发掘,无疑是其在日常生活的总体性实践维度为激进的城市空间革命奠定政治基础的关键环节。而据此衍生的“它者化”或“第三化”,则以破坏性建构的方式既终结了资本生产关系的无意识再生产链条,又开辟出全新的空间实践场域。从它的作用机理与政治指向来看,这“不是源于先前二元项的简单叠加,而是源于对它们所假定的完整性的拆解和临时重构,从而产生一种开放的选择项”。⑤索杰:《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的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第77页。由此可见,列斐伏尔对资本政治秩序与城市空间景观的瓦解,实则是要在资本逻辑所蕴含的一系列即时性“空间矛盾”中,为日常生活能够最终摆脱异化探寻长时段的空间实践条件。后者作为“差异空间”的基本属性,又以共时态的形式潜藏于“抽象空间”当中。
三、城市革命与“资本-土地-劳动”的三元辩证法
在列斐伏尔看来,由总体性的“空间实践”所引导的城市革命,是建构“差异空间”并最终扬弃资本“抽象空间”的唯一路径。反映在当下,“这种全新的斗争形式意味着,它将为处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框架中的城市权力和有关日常生活的控制权而战”。⑥S.Roweis. Urban Planning in Early and Late Capitalist Societies, Toronto:University of Toronto,Departement of Urban and Regional,1975,p.140.换言之,城市革命标志了日常生活及其空间政治形态的重新定位。而后者在政治经济学层面则进一步引申出,同时作为城市景观和个体日常交往之物质性前提的土地及劳动要素,与资本逻辑之间的三元辩证关系。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结尾处曾强调,“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这就是把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切秘密都包括在内的三位一体形式”。⑦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1页。沿着该理路,列斐伏尔立足空间哲学对其进行了创造性发挥。他指出:
资本主义的“三位一体”以同样的方式在空间中确立起来,土地-资本-劳动的三位一体不再是抽象物,而是在一个等边三角形的三重制度性空间中建构起来的空间:首先,这是一个完整的权力空间,其中强制性的规划被贯彻实行,并据此形成一个消解差异的拜物教空间;其次,它又是一个碎片化的空间,并呈现出分裂与脱节状态,因此是一种被特殊定位化且以位置特殊化或地点分化为前提而实现的空间上的相互交换;最后,这还是一个等级性的空间,在一条涵盖从最低端的位置到最高端的位置的序列中,涉及从禁忌物到至高无上者的关系。①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282.
Analysis of concrete early strength under different story construction progress
2.3 不同耕作方式对夏玉米农田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从图3可以看出,不同耕作方式下,免耕土壤黏粒含量显著高于深松耕和常规耕作(P<0.05),深松耕和常规耕作差异不显著(P>0.05)。常规耕作土壤的粉粒含量大于深松耕和免耕方式,深松耕大于免耕,且3种耕作方式间差异显著(P<0.05)。免耕方式土壤的砂粒含量显著大于深松耕和常规耕作(P<0.05),深松耕和常规耕作方式无显著差异(P>0.05)。免耕方式土壤含水量大于深松耕和常规耕作,深松耕大于常规耕作,且3种耕作方式间土壤含水量差异显著(P<0.05)。
鉴于此,列斐伏尔强调,资本逻辑的空间政治旨趣就是在不断推进日常生活抽象化的同时,消除人们对资本抽象权力的反思或质疑能力。于是,“被拜物教化了的抽象空间就引起了两种实际的抽象化结果,即个体在抽象空间之中对自身的处境茫然无知,而思想也无法与这种抽象空间保持批判性的距离”。③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93.换言之,资本的“抽象空间”意欲在社会关系无意识地再生产中,建构与资本积累节奏相吻合的异化政治秩序。其“综合效果是为一个单一宇宙的假设提供了必要基础。它是一种有关时间、有关时间过程中的横断面的看法。它不允许真正的‘它者’的声音”。④多琳·马西:《保卫空间》,王爱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56页。至于“抽象空间”在社会日常生活领域的现实化手段,列斐伏尔则指出,这恰恰取材于被资本异化的“空间表象”所内涵的具有权力编码作用的知识体系。只不过后者又再度具象化为人格化的技术或理性权威对空间景观的规划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作为一种产品,社会空间是按照一群专家、技术权威手中的操作指令制造出来的,而这些专家、技术权威本身代表了特定的利益,同时代表了一种生产方式。……所以,没有地地道道或纯正的空间,只有按照一般社会结构内某种特殊群体发展起来的一定模式(也就是生产方式)生产出来的空间”。⑤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3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第652页。在这样的情形下,总体性的实践逐渐退场,而具有物质力量的资本抽象权力及其意识形态则占据了整个社会空间。然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列斐伏尔正是在社会空间自身的辩证关系中,发现了看似牢不可破的资本抽象政治结构自身无法规避的“空间矛盾”。对此,他专门指出:
财务风险预警系统,可以进行信息收集。它通过收集与企业经营相关的产业政策、市场竞争状况、企业本身的各类财务和生产经营状况信息,进行分析比较,判断是否预警。还可以预知危机。经过对大量信息的分析,当出现可能危害企业财务状况的关键因素时,财务预警系统能预先发出警告,提醒经营者早作准备或采取对策,避免潜在的风险演变成现实的损失,起到末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此外,还能控制危机。当财务发生潜在的危机时,财务预警系统还能及时寻找导致财务状况恶化的根源,使经营者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制定有效的措施,阻止财务状况的进一步恶化。
第二,终止以资本等级秩序和资本空间再生产为座架的城市拜物教政治。应当说,无论是迎合资本价值交换之地理性要求的碎片化空间形态,还是由此产生的等级性空间秩序,都是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进程的政治性表现。从形而上学的视角来看,它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给它统治的空间加上条纹,或把平滑空间用作交流工具,使其服务于条纹空间。……更普遍地说,是要建立控制整个‘外部’,控制横亘全世界的所有流动的一个权力地带”。⑦德勒兹:《游牧思想》,陈永国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23页。而这往往起始于镌刻在土地之上并弥散于全体劳动者之间的资本空间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泛化和向城市景观的集中。按照列斐伏尔的说法,“作为一种最高的制度,它倾向于巩固自身的状况,保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区分,进而区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以及城市和乡村的区别。……并在强化决策中心的同时,将城市中心转变为权力的堡垒”。①Henri Lefebvre,The Urban Revolution,p.79.于是,资本、土地和劳动三者间彼此倒错的辩证关系,就进一步成为资本主义城市拜物教政治的前提。而后者则以权力为手段,从外部维系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空间性再生产。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②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940页。鉴于此,城市革命就被赋予了鲜明的政治意义。它只有从资本空间生产的结果,即以城市为地理节点的资本主义政治体系内部,重塑被资本抽象权力异化的“劳动-空间”关系,才能在总体上打破由等级性的资本空间序列所表征的资本社会关系再生产结构。其实质,就是与资本空间规划相左的“它者”因素,对斗争运动的持续唤起。而这在列斐伏尔看来,直接体现在“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意识到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所面对的社会现实,进而意识到社会整体,意识到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者的行动,以及意识到无产阶级的政治未来”。③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1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第132页。据此,城市革命又能被看作日常性的阶级斗争对社会未来愿景的激进定位。
值得一提的是,“资本-土地-劳动”的三元辩证关系,尽管在学理上最终指认了城市革命瓦解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但同时应当认识到,这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其原因既导源于城市革命由以产生的资本主义城市化进程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又取决于城市革命所依托的日常生活批判特有的长时段属性。对于前者而言,列斐伏尔指出,为资本逻辑推动且在“全球范围内随时发生形态变迁的空间生产,作为改变日常生活的社会基础,始终向无穷的可能性开放”。④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p.423.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城市革命的实践旨趣和预期效应,不可能囿于某一时间节点内特殊的社会情势。诚如马克思所言,“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正因为如此,以之为物质性前提的城市(或都市)社会,就只能是一种正在形成的现实。作为真实与虚构的辩证统一,它一直处于尚未完成的不断形成之中。⑥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第2版),李春译,第51页。于是,伴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城市革命的实践结构也必然处于间歇性的变动不居当中。此外,对于后者来说,既然社会生活的空间-时间构建“赋予日常生活的各种循环性实践以具体的形式,同时也赋予这些运动和实践以具体的位置”,⑦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第193页。那么,构成城市革命之理论起点的日常生活批判,就不能被视为一劳永逸的即时性行为。与之相反,它只能基于不断更替的社会症候,而显现为长时段的总体性批判集合。这无疑从相反的方向表明,“正在展开的历史不能穷竭革命带来的那些可能性”,⑧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第2卷,叶齐茂、倪晓晖译,第441—442页。也就是说,空间革命将伴随资本的空间生产始终。
毋庸置疑,列斐伏尔城市革命策略的提出,为总体性的“空间实践”及由此形成的“差异空间”对资本“抽象空间”的扬弃奠定了现实性基础。它从日常生活、空间政治以及社会交往三个层面,击穿了由“资本-土地-劳动”三者倒错的三元辩证结构所表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再生产体系,并据此引申出激进的城市乌托邦构想。后者作为与资本空间规划相对立的彼岸世界,将扬弃以资本逻辑为前提的物的生产,转而引起新的社会关系的生产。而这在列斐伏尔看来,毋宁说是马克思解放政治的当代表达。
结语
从列斐伏尔自身的思想演变轨迹来看,围绕“空间实践-空间表象-象征空间”“抽象空间-空间矛盾-差异空间”以及“资本-土地-劳动”三重隶属不同层次的三元辩证关系,而最终确立的城市革命构想,可视为其早前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的升华与具象化。对日常生活中异化的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批判,就进一步被提炼为对资本城市景观内的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的批判。据此不难看出,列斐伏尔的城市批判思想及其连带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实则分别以抽象的哲学关照、一般的政治经济学反思以及具体的阶级政治旨趣,再度诠释了资本逻辑在日常生活领域的运行机制,和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在当代的实践路径,即以日常生活的总体性革命所建构的城市乌托邦愿景、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空间性再生产的终结与长时段的扬弃。
不可否认,由列斐伏尔开启,并在此后甚嚣尘上的“新城市马克思主义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尝试终结对都市和空间的忽略……并将20世纪的社会运动置于资本主义消费与再生产的范围之内”。①艾拉·卡茨纳尔逊:《马克思主义与城市》,王爱松译,第98页。但是,把城市景观视作解读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切入点,并试图以城市革命取代马克思阶级斗争的全部内涵,无疑曲解了马克思人类解放思想的最终旨趣。况且,列斐伏尔对空间三元辩证法中所谓“它者”或“第三项”的过分强调,又必然引发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正因为如此,城市乌托邦只是遥不可及的幻想。
The Connotation of Spatial Dialectics in Lefebvre’s Urban Critical Theory
WEN Quan
Abstract:Lefebvre’s urban thought is an organic extension of his criticism for daily life.By constructing the ternary dialectics of social space,he tries to interpret the modern urban utopia premised on“differential space”from the meta-philosophical context of“other”or“third item”,and to dissolve the reproduc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 space based on“abstract space”.The theory is based on the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longterm survival of capitalism in the three sets of ternary dialectical systems of“spatial practice-spatial representation-symbolic space”,“abstract space-spatial contradiction-differential space”and“capital-land-labor”,and the radical outlook of daily life-urban revolution.Therefore,in the open perspective of space dialectics,Lefebvre repositioned the internal unity among Marx’s practice theory and the criticism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theory of class struggle.Then,with the city as the entry point,the contemporary road map of the proletariat’s liberation is outlined under the situation that the mode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has turned.
Key words:space ternary dialectics,spatial practice,differentia space,daily life,urban revolution
作者简介:温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南京21002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7FZX036)
DOI编码:10.19667/j.cnki.cn23-1070/c.2019.04.002
[责任编辑 付洪泉]
标签:空间论文; 资本论文; 抽象论文; 日常生活论文; 城市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求是学刊》2019年第4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卫·哈维马克思主义空间政治哲学思想研究”(17FZX036)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