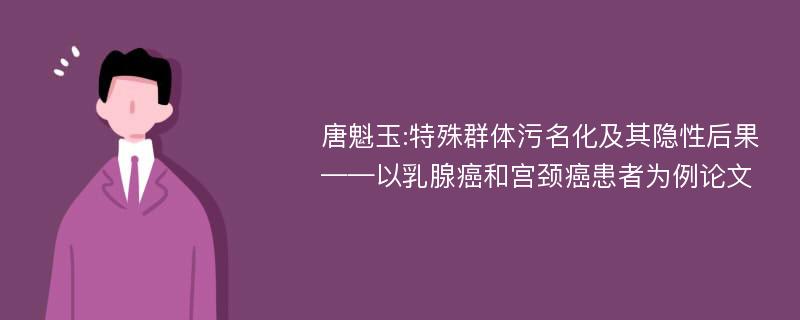
·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
摘 要: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女性在工作和家庭中扮演了多重角色,她们的身体健康尤其值得关注。女性在确诊乳腺癌和宫颈癌后,由“健康人”变成“恶性肿瘤患者”。与此同时,在“癌症等于死亡、癌症是可以传染、乳腺癌是可以遗传的、宫颈癌是私生活不检点所导致的、切除了子宫和乳房的女人不是完整的真正的女人”等污名化的影响下,这些特殊疾病的承载者在身体、行为和关系上承受,并显示出了一系列的社会后果及其隐性后果。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我们对人类疾病群体的污名化知识得到了一次全新的认知和积累。
关键词: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隐性后果
众所周知,女性乳腺癌和宫颈癌是中国女性常见的两种癌症,其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1],两种癌症的高发病率产生了大量的乳腺癌和宫颈癌患者及幸存者,并组成了庞大的乳腺癌和宫颈癌群体。然而,女性一旦被确诊为乳腺癌、宫颈癌后,就被医院和社会贴上了“乳腺癌患者”“宫颈癌患者”的标签,使之从“健康人”转化为“病人”的角色,将完整的个人变成一个打折的、残缺的人,所以乳腺癌和宫颈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认为是具有污名化的疾病[2]。社会人群对乳腺癌、宫颈癌存在着犹如“乳腺癌症是可以遗传的,癌症是绝症”等负面的刻板印象,以及对于宫颈癌和私生活不检点相关联的认知,使乳腺癌、宫颈癌群体在她们由健康人到患者的身份转变的过程中,遭受一定的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社会学家对污名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但是重点聚焦于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的研究则少之又少,对乳腺癌、宫颈癌群体的日常生活所遭遇的污名化原因进行探索,对她们遭遇污名化社会后果进行分析,有利于消解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群体紧张的社会关系。
一、文献回顾
一般认为,处于污名化日常生活状态下的人群可以依据戈夫曼方法划分为三类,一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患者,如精神分裂症;二是身体有缺陷的人,如艾滋病人、乙肝患者、癌症患者;三是一些特殊的族群或种群,如黑人、同性恋者等[3]。其中,癌症患者常感受到 “癌症等于死亡”“癌症等于对社会生活的威胁”“癌症等于癌症缠身的生命”严重污名化[4]。正是因为癌症与死亡和糟糕的生存状态关联,增加了健康人自身对疾病和死亡的易感性,所以他们对于癌症患者会采取回避行为以及撤回社会支持,61%的健康人士承认会避开癌症患者[5],此举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癌症患者的社会支持,造成癌症患者与社会隔离。所以,癌症患者更有可能经历微妙形式的污名化,就像被他人回避和由此导致的社会孤立,而不是公开的歧视行为[6]。这种对癌症患者的回避的微妙污名化,并不是对癌症患者有意的伤害[7],而是来自于与癌症患者相处会感到不适[8]。
癌症特征的强烈也会影响健康人群对癌症的认知,从而影响癌症污名化,Harcourt和Frith[9]对化疗期间脱发的乳腺癌患者的调研发现,明显的癌症状况可能引起人们过多不必要的关注,具有明显癌症副作用的人更容易受到歧视且更不容易得到普通人的帮助[10]。乳腺癌群体在治疗的过程中会出现身体的变化(治疗的副作用)、情感混乱以及社交功能障碍,并且会经历与治疗相关的社会污名[11],她们在经历所有治疗阶段以及之后,往往会出于对积极心态的预期和对被污名化的恐惧,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12]。
癌症污名化与患者所患癌症“可控”性多寡具有一定的关联,人们倾向于对那些有癌症“可控”性有负面反应,例如人们会更加愿意帮助一个在满是灰尘的工厂工作20年的肺癌患者,而不愿意帮助一个有20年烟龄的肺癌患者[13]。这是因为肺癌与吸烟关系的高度相关,而吸烟是一个人为可控制的行为,人们认为不可以原谅一个吸烟的肺癌患者,所以肺癌患者通常比其他癌症患者更能受到污名的影响,但这种情况下那些多年前戒烟或从未吸烟的癌症患者,会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指责与歧视[14]。另一项研究发现,人们会考虑引起癌症原因时,向肺癌研究捐款的可能性低于乳腺癌研究[15]。事实上癌症患者有时也会自我责备,患有“可控”性较多的癌症(如肺癌)的患者比患有“可控”性较少的癌症(如乳腺癌或前列腺癌)患者,更愿意把患癌的责任归咎于自己[16],从而产生自我污名。
宫颈癌与HPV之间关系会导致人们对宫颈癌评价更加负面,产生强烈的厌恶反应,所以当人们考虑宫颈癌的病因时,他们会对患宫颈癌的女性做出道德判断,并对宫颈癌女性进行责备归因(私生活混乱),并且随着人们对HPV与宫颈癌之间关系的认识提高,对宫颈癌患者的歧视可能也会增加[17]。Gregg[18]的研究发现,没有一个患有宫颈癌的女性抗拒甚至质疑围绕着她们疾病的污名,而对性不洁的污名化隐喻为许多患癌症的女性自身提供了一种组织疾病叙述的方法,并由此理解她们新的、患病的、不同的自我与她们一直以来所熟知的世界之间的关系。
二、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及内在原因
(一)何为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
癌症等于死亡的认知,是人们对死亡临近的感觉和对疾病严重性的认知,尽管癌症存活率不断上升,人们对癌症等于死亡的态度依然存在,人们对癌症的恐惧超过了其他威胁生命的疾病[23]。癌症患者本身也对癌症惧怕,有着癌症缠身的生命,对死亡话题非常敏感,以及计算剩余的存活天数,即使完成全部的治疗过程也会提心吊胆生活在对五年存活率的恐惧中,例如乳腺癌患者网友A-1在乳腺吧里写:“我也是三阴乳腺癌、去年八月做的全切手术,看了很多网上说的,三阴存活率只有五年,真有点吓人,到底该怎么预防复发,还有点茫然,该注意些什么,三阴真的活不了多久吗?”所以癌症等于死亡的污名,不仅是公众污名,也是癌症患者本身自我污名化。
在我们看来,一切事物的污名化过程通常自名词始,但背后隐为实体。这些典型的事物实体,主要表现在身体、行为和关系等三种特质上。其中,体现了对疾病患者的污名的名与实的两个方面。从表面显示和隐含暗示的角度出发,本文将对女性患者的乳腺癌、宫颈癌的污名化分为显性污名和隐形污名两种类型。应该说明的是,这种恶性肿瘤的污名化远不如在对艾滋病患者等特殊传染性疾病的污名化的强度为高,但事实上也存在着忌讳、区隔与疏离等隐形的污名化意味。这正是我们在此文中将重点阐释的一个创新观点。
(二)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产生的内在原因
现状研究成果一般通过VISSIM、 TRANSYT-7F、Synchro等仿真软件进行评价. 应用方面,林晓辉等[16]则利用Visnal Basics 软件工具开发了城市交叉口时空资源综合利用优化配置的决策应用软件,将协同优化技术通过软件得到应用.
癌症患者在住院或者治疗后回家,都被家人单独准备一副碗筷以及单独洗漱用具和生活用品,尽管知道癌症是不传染的,但是他们还会认为患者会带有一定病菌,避免与其接触,而且患者本身也认为自己的东西不够干净,所以患者的一切生活都特殊化,从而产生了她们是带有病菌的不干净的污名化。
一般说来,污名化有四种情形或过程[19]。首先,人们被分类并贴上不同的标签。第二,根据不受欢迎的特征和刻板印象标记差异。第三,被贴上不良品质标签的人被归入“他们”类别,这与“我们”类别从根本上是不同的。第四,属于“他们”范畴的人(即被贴上标签的人)被排斥、拒绝、贬低,从而失去地位、备受歧视。污名有四种类型[20]。首先,公众污名,是对一个拥有的污名的个体的感知者。第二,自我污名是污名者对污名的理解并内化。第三,联想污名是与污名患者有关联的人所面临的污名。第四,结构性污名,是社会意识形态加剧的或者引入公共政策的污名耻辱。
乳腺癌、宫颈癌患者确诊后,有些人的老公当时提出离婚,治疗途中出轨提出离婚,或者生存期分居的现象都极为常见;有些女性的男朋友,也在确诊之后就离开了,暂时没离开的男友也不一定能冲破家里人的层层阻隔。因为乳腺癌、宫颈癌女性大多数手术后会切除身体的生殖器官,从此被定义为不是一个正常的女人,加之激素分泌和心情变化,对男女双方的性生活和谐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会使丈夫和男友与一个不是女人的女人离婚、分居和分手。宫颈癌与私生活混乱相关的污名,也会让女性丈夫或男友认为自己妻子或者女友对自己不忠,背着自己与别的男人乱处男女关系,使夫妻关系或者恋爱关系紧张,乃至离婚和分手。
在婚前贞操、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文化背景,女性宫颈癌经常被认为是未经治疗的、累积性病的最终结果,最终导致了宫颈癌患者受到严重的污名化,她们常常被指责、贬低,甚至被怀疑有性病。被污名化的宫颈癌,实际上是人们对于男女两性自由交往的焦虑,但这种不负责任的污名化,将男性导致女性患宫颈癌的责任淡化,导致宫颈癌妇女不仅是病痛的承受者,而且容易被定义为疾病的罪魁祸首, 落下“自作孽,不可活”的污名[25]。有不少人认为癌症是个人罪孽的惩罚,是因为曾经做了恶事,才落得得癌症的报应,例如王娟娟[26]调查的一位乳腺癌患者说:“自从我得了这个病,我就在想是不是我上辈子做了太多恶事,所以不仅仅是我老公、儿子死了,现在我自己也得了这个病,这是老天给我的报应啊。”她以一种因果报应的非理性化的观点解释自己的疾病,乳腺癌在此被当做了一种邪恶的标志,是一个人因做错事情而受到的惩罚。
三、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的女性身体隐性后果
乳腺癌和宫颈癌不仅意味患者有身体的疼痛折磨,还意味着站在主流的身体文化对面,完全背离了“正常”“完美”的身体定义,具有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残缺”的女性身体,并且使乳腺癌和宫颈癌女性对自己身体产生认知错误,她们完全接受了自己不是“完整的女人”的定义,例如宫颈吧里宫颈癌患者A-3的担忧,“哎!才32岁,以后怎么办?没有子宫的女人不是完整女人”。所以,患者本身对自己缺失了身体也会有担忧,认为自己不够完整。
她们在公共娱乐空间行为也会受到身体残缺的污名影响,例如在泡温泉和游泳的时候,为了避免被别人看到身体上的不对称乳房和疤痕,她们躲在角落里,不敢来回走,甚至到最后不会再涉足曾经喜欢的游泳活动。也有些乳腺癌患者游泳洗澡找一个靠边的地方,并不是因为自己怕难看,而是怕别人看了会受到影响,担心自己异样的身体会引起别人的不舒服,她们自己默认了身体残缺带来的污名并独自承担污名化的后果。她们生活在被他人和自己所建构的身体残缺的污名中,没有实施反抗的行为,而是屈从于污名而自己远离人群活动。
从身体社会学的角度看,乳房和子宫代表了女性的性别形象,彰显了女性性别状态的重要器官,切除“乳房、子宫”不只带来了身体的残缺,并从根本上影响了女性气质的建构,失去乳房和子宫是对女性身体形象的极大破坏,更破坏了女性的性别形象。乳腺癌患者A-4在乳腺吧里纪录:“不怕姐妹们笑话,我至今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伤口。手常常有意无意碰到左胸,却只能感到一个凹洞,男友帮我擦洗伤口时问我疼不疼,那个曾经最敏感的部位,现在任凭怎么触碰,都只有一种酸涩麻木的迟钝感。你的身体在随时提醒你曾经受过的苦难,治疗的每一步,尤其内分泌治疗,也在一点点逼迫你放弃更多属于女性特有的魅力。”所以,看出乳房是作为女性性别的标志,是一个女人拥有作为女性的权力,失去乳房就会一点点地失去女性魅力,损坏了女性形象,以至于自己不愿意看,甚至都不敢让男朋友或老公看——乳腺癌患者A-5就表示,自己不敢看也不敢让男朋友看。
乳腺癌和宫颈癌患者在乳房和子宫残缺引起的羞耻感之外,还会遭遇在不同治疗阶段的羞耻感,化疗引起的掉头发、掉眉毛,放疗引起的皮肤松弛是治疗过程副作用的最强有力的外显,严重影响了她们自身的形象。而人们对乳腺癌、宫颈癌患者以及她们外在身体变化的关注,即使是好奇、同情、怜悯、痛苦和过度谨慎的态度都会使乳腺癌、宫颈癌患者感到不舒服。她们认为自己目前的发量是不能见人的,她们开始从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更加看重自己的身体,反思身体的重要性,她们认为“穿着好看”会影响情绪状态和自我价值,而“看起来不错”能够取消大众的关注,避免了社会大众从社会判断和潜在的刻板印象来感知她们[27]。
尼伯勒德等人认为,乳腺癌、宫颈癌的污名化产生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普通大众认为癌症是可以传染的;二是癌症是个人罪孽的惩罚;三是癌症即是死刑[21]。此外,某种乳腺癌与某种基因的缺陷相关所导致人们认为乳腺癌是可遗传的,宫颈癌与人体乳头瘤病毒的高度相关都是污名化,乳腺癌和宫颈癌治疗过程的切除手术使女性丧失了女性特征,化疗过程中的皮肤和头发变化特征都与传统的女性形象相违背,这些都是污名化的重要原因。乳房和子宫的切除以及掉头发等身体受损导致患者不只经历身体的残缺,且身体会被建构为不符合社会规范的性别态身体[22],承受来自社会的异样的眼光。
四、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的行为隐性后果
(一)社会行为隔离
非完整的女人与残缺的女性认知,导致了乳腺癌、宫颈癌患者我们与她们不同的认知,在社会行为上也会出现与得病之前表现出差异,明显会出现人际交往退缩,社会行为边缘化,远离人群。她们接受不了自己的头发、眉毛没了等外在身体的残缺,认为自己的形象很丢人,较低的自我评价导致自我污名不敢出门,很恐惧也很自卑。一位36岁的乳腺癌患者(A-6)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头发全都掉光了,我整天一个人闷在家里,好几个月闭门不出,特别的自卑。”她们害怕别人异样的目光,总觉得别人会在背后偷偷议论自己,所以拒绝出门。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 2000—2017年全国范围内部分城市降尘重金属的研究结果,所收集的数据涉及工业区和非工业区,为避免数据来源单一化,工业区包括矿区和冶炼区;非工业区包括商业区、文教区、居住区、交通区等,具体数据见表1、表2。
不与陌生人社交可以理解为女性乳腺癌患者不愿意承受来自他人对自己身体形象的污名,但是她们也不愿意与熟人社交。她们见到熟人就会绕道而走或者躲起来,出门看到邻居也会觉得很麻烦,心情不好。因为碰到熟人需要停下来,而寒暄的一句“哎呀,你怎么样啦”就会使癌症患者陷入不好的联想,她们会以为别人都是基于“癌症等于死亡”的前提下做出的问候,认为自己在别人眼里就要死了,导致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尽管自己活着,在其他人眼里都会是个奇迹,但基于的前提依然是“癌症等于死亡”。在“癌症等于死亡”和乳腺癌、宫颈癌患者是身体残缺的负面标签下,乳腺癌、宫颈癌患者为了减少他人的异样的眼光,怕别人不舒服或自己不舒服,开始远离公共娱乐空间活动,并减少同熟人的见面,从而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1) 黑水角阀结构。该阀门主要由阀体、阀盖、阀杆、阀芯、阀座和扩散段等组成,结构如图1所示。角阀工作时,介质从左侧入口流入,流经阀芯与阀座之间形成的节流口,再依次经过阀座和扩散段后从下侧流出,即侧进底出,通过阀杆的上下移动改变阀芯与阀座之间的相对位置从而改变黑水流量。
(二)医疗行为隔离或延迟
宫颈癌与性生活不洁高度相关的污名,不仅会影响到宫颈癌患者社会行为,也会影响到正常女性的宫颈癌筛查行为(HPV和TCT检测)。绝大多数宫颈癌是由高危HPV病毒的持续感染导致,而HPV病毒通过性传播感染,所以就导致社会大众对宫颈癌女性私生活不检点的污名。年轻女性有性生活以后应该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但因为惧怕宫颈癌的污名,会担心自己进行HPV和TCT测试而被周围人认为自己的男女关系混乱,害怕别人说三道四,所以她们尽量会避免进行宫颈癌筛查。女性也不愿意去进行宫颈癌筛查,她们害怕阳性的测试结果会让家人对自己产生偏见和歧视,害怕影响男女朋友关系、夫妻关系和代际关系。有的女性会基于宫颈癌的污名化,延迟自己的就医时间,她们常常等身体出现明显不好的症状,并且疼痛不能再拖的时候,才会去医院检查治疗。
甘蔗被切稍器断尾,分蔗搅拢将交叉倒伏的甘蔗分开,通过割台将甘蔗砍切,随着输送装置向上输送,经过切段装置时被切成23~28cm长的甘蔗段;此时蔗叶被除杂装置抽出吹走,切段后的甘蔗落到升运器上,向上提升输送,在挡蔗器的协助下装到运输车上,送入糖厂进行压榨。主要技术参数:
五、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的关系隐性后果
社会人都是处在各种关系中,而乳腺癌和宫颈癌的污名化会导致很多女性癌症患者的关系有所改变。首当其冲的是亲密关系,因为乳腺癌和宫颈癌的治疗,都会涉及在女性性器官上开刀或者切除性器官,多数情况下会影响女性和丈夫或者男友之间的生活,使得亲密关系发生紧张或者断裂。其次是社会关系,女性癌症患者的日常生活空间是家庭社区,而癌症幸存者也会重返工作领域,工作关系和人际关系也会受到污名化的影响变得生疏或者隔离。最后是代际关系,因为抚养和赡养的责任义务,亲情关系难以分割,但是女性乳腺癌、宫颈癌患者也会面临直系亲属的偏见和歧视。
DICSSAC一次冷却的喷射式凝汽器体积很小,可就地布置在距离主排汽管最近的位置,极大地减小排汽管长度,大大减小排汽压损。
(一)亲密关系后果
女性乳腺癌、宫颈癌是女性常见的两种恶性肿瘤,但它的诊断和治疗后果影响绝不仅限于患者自身,同样也影响她们的男友和丈夫。一方面,疾病导致恋爱或婚姻关系中的角色重新分配,原来女性承担的照顾角色转化为男友或者丈夫承担,他们为女性癌症患者生病期间经济和照顾支持;另一方面,乳腺癌、宫颈癌不仅仅个体身体疾患,其病变部位是女性的生殖器官,是维持两性关系的重要部位。女性癌症家属男女关系中角色转换和维护两性关系的女性器官的缺失以及产生的乳腺癌、宫颈癌的污名化会使两性之间亲密关系紧张或断裂。
许多医学文献中显示,8%~10%的乳腺癌的发病是因为女性遗传一种有缺陷的基因,如BRCA来自父母一方的基因[24],所以乳腺癌被人们认为是可以遗传乳腺癌患者的女儿,产生社会大众对乳腺癌群体及她们的女儿的污名。在婚恋选择时,人们会认为乳腺癌患者会将乳腺癌遗传她们女儿,由此产生联想污名,导致乳腺癌患者女儿在婚姻市场中不被选择,处于弱势地位。并且,部分乳腺癌患者由于知识不够全面,自己本身也认为乳腺癌是会遗传的,自己生产出自我污名。乳腺吧里面乳腺癌患者A-2发表的回帖中表示:“医生说至少五年后才能生孩子,我也怕这个病会遗传。哎,太多后悔的了!”
乳腺癌和宫颈癌都是治疗后存活率较高的癌症,所以女性患者经历治疗后会考虑重返工作岗位工作,但是这时候女性癌症幸存者往往会因为“癌症等于死亡或者疾病缠身的生命”的污名而被歧视、照顾、隔离或者冷处理。所以她们会面临两种窘迫状态,一是调岗到清闲的岗位;二是主动或者被动离职。她们在重新找工作时也因为自己身患恶性肿瘤而受到歧视,承受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根本不会给予工作的机会。
结果显示,吸烟成瘾组的男性比例高于其他两组,网络成瘾组的女性比例高于其他两组(χ2=29.066,P<0.05),3组被试在性别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年级、民族、是否为独生子女以及家庭所在地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二)社会关系后果
1.工作关系隔离或断裂
并且,癌症给人极容易误会的污名就是癌症是绝症,治不好了,那么有些男性就不愿意和妻子或者女友共同承担风险,不愿将自己陷入与一个即将走向死亡的人纠缠在一起的生活,所以选择分手或者离婚,导致亲密关系断裂。因为乳腺癌会遗传的污名化,使有的乳腺癌患者男友的家人也会担心,他们结婚以后养育的孩子会遗传乳腺癌,所以为了后代着想,阻碍两个人恋爱关系。良好的亲密关系会为乳腺癌、宫颈癌患者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但实际因为患与生殖器官相关的癌症加之社会施与的污名,使乳腺癌、宫颈癌患者的亲密关系紧张或者断裂,也减少了妇科女性肿瘤患者的社会支持,降低了其生活质量。
根据调绘成果,坡体受断层F切割,断层破碎带宽约1.5 m,断层破碎带由角砾、泥质等充填胶结,胶结程度很差,对坡体发展不利。此外,坡体存在一组顺向结构面,倾向160°~170°,倾角40°~61°,这组结构面极有利于滑坡的形成。
很多女性乳腺癌患者治疗后回归工作岗位,因为身体的疾病导致被认为不能胜任以往的工作被调到一个养老的岗位,从此由一个在人前活跃的人变成了一个边缘人,看着别人热火朝天地工作,内心极其失落。也有女性患者在确诊后就失去工作,在治愈后找工作又受到偏见和歧视。所以,现实情况是患癌的女性需要一个工作使自己处于一个工作的环境,与人有所接触远离疾病的生活状态,或者补充家庭经济收入。在鼓励病人回归社会的背景下,却受到就业歧视与偏见,以至于癌症幸存者需要在违背内心的情况下隐瞒自己的病史去找工作。
2.人际关系的生疏
3.口腔内的创面没有愈合,饮酒是会出现疼痛的,这是常人不愿意忍受的。因此,咬伤后每天喝酒不一定是符合事实的。
人际关系专家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存在各种人际关系,因为居住和工作,乳腺癌、宫颈癌患者难免会与同事和邻里接触,但因为疾病改变了社会成员对她们的认知,工作场域中与同事以及居住环境与邻居的相处模式都会受到污名的影响,进而破坏女性乳腺癌、宫颈癌患者的同事关系和邻里关系。一位乳腺癌患者就表示自己在单位上班后,同事关系变得极为尴尬:“回单位上班,人人怕你,说你得了癌症了怎么不提前退休,健康时常在一起玩耍的同事全部疏远你,气死了。”(王娟娟,2017)基于癌症等于死亡的污名化,同事们都和乳腺癌、宫颈癌的幸存者保持距离,并且会认为她的身体不适合继续工作,可能出于避免意外的角度刻意避免与她们所谓的不必要接触,从而使原本融洽的同事关系生疏。但是,在女性癌症患者看来曾经共同参与玩耍的同事们,对自己敬而远之,会产生极大的失落与尴尬,也会产生自我怀疑与气愤的情绪。
癌症是可以传染的这个污名化的原因,会导致人们从此不愿意亲近癌症患者。避免与其近距离接触的行为,在农村社区的邻里相处模式体现得更加明显。“不知道是不是我太敏感了,我觉得村里的人觉得我得了乳腺癌都在避嫌,以前常来串门的都不怎么来了,以前邻居之间还会送点吃的什么的,现在都不一样了,这又不传染,但是看她们的表情,好像我会传染给他们一样。”[26]乡村社会邻里之间相互串门和互相赠送家常食物是极其正常的交往模式,但是因为癌症传染的污名化,使邻居避免接触癌症患者,既不串门也不赠送食物。同事关系生疏和邻里关系隔离也使女性乳腺癌患者从原本人际关系中抽离出来,重新与人建构人际关系,而新关系的另一方往往就是她们的病友,只有与病友在一起相处才更加舒服,也相互理解。
(三)代际关系后果
中国人注重家庭观念,父母或子女对女性乳腺癌、宫颈癌的态度与行为直接会影响患者的代际关系。有些儿女在为患乳腺癌、宫颈癌的母亲治疗过程中,会深受“癌症即是死刑”影响,以及从其他癌症的相对低的生存率联想到乳腺癌、宫颈癌低存活率产生联想污名,认为自己的母亲也治不好了,最后的结果也是死亡,不如不给母亲治病,以免花冤枉钱。这样对乳腺癌和宫颈癌的偏见,父亲和母亲会认为孩子不孝顺而对孩子心灰意冷,而孩子也会认为父母不够理解自己,会导致父母和子女的代际关系紧张。有些父母对自己患宫颈癌女儿也会受到“癌症等于死亡”和宫颈癌是因为私生活不检点所致的污名化影响,认为女儿在外面私生活混乱,让自己在亲朋邻里之间蒙羞、丢面子。加之癌症就是死亡的定论,有些父母对女儿的言语恶劣,宫颈吧的一位性生活不到一年的20岁宫颈癌患者的父亲甚至让她去撞车,还能给家里赔点钱。
结 语
毫无疑问,乳腺癌、宫颈癌作为一个在女性身体特殊部位病变的癌症,从确诊之初就对女性的心灵造成了极大恐惧,每一个治疗过程都伴随着巨大的疼痛,切除使自己身体缺少一个部位,化疗使头发掉落、皮肤松弛,却也没放弃对生命和长寿的坚持及追求。但还要受到“癌症等于死亡、癌症是可以传染、乳腺癌是可以遗传的、宫颈癌是私生活混乱导致的、切除了子宫和乳房的女人不是完整的真正的女人”导致的污名化影响。她们接受身体残缺的认知,将别人施与自己身体上的污名接受下来并产生自我污名,并且承受来自他人对自己身体的异样关注。乳腺癌、宫颈癌患者的行为与生病前大不相同,社会行为隔离,变得不想出门、不去公共娱乐空间活动,不愿意与熟人说话;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会导致女性的医疗行为隔离与延迟。乳腺癌、宫颈癌污名化还给女性患者的关系带来一定的后果,亲密关系变得紧张或断裂,工作关系变得隔离或断裂,人际关系变得生疏以及代际关系变得紧张。我们认为,在“健康中国”语境下在电子健康社区中寻求女性肿瘤患者的网络美好生活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也具有现实可能性。
参考文献:
[1] Wanqing Chen, Kexin Sun, Rongshou Zheng, et al.,“Cancer incidence and mortality in China, 2014”,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Vol.30,No.1,2018,pp.1-12.
[2] Goffman E, Stigma: 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63.
[3] 唐魁玉、徐华:《污名化理论视野下的人类日常生活》,《黑龙江社会科学》2007第5期。
[4] Tang P L , Mayer D K , Chou F H , et al. ,“The Experience of Cancer Stigma in Taiwan: A Qualitative Study of Female Cancer Patients”,Archives of Psychiatric Nursing, Vol.30,No.2,2016,pp.204-209.
[5] Peters-Golden H ,“Breast cancer: Varied perceptions of social support in the illness experience”,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Vol.16, No.4,1982, pp.483-491.
[6] Fife B L , & Wright E R ,“The Dimensionality of Stigma: A Comparison of Its Impact on the Self of Persons with HIV/AIDS and Cancer”,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Vol.41, No.1,2000, pp.50-67.
[7] Flanagan J, Holmes S, “Social perceptions of cancer and their impacts: Implications for nursing practice arising from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Vol.32, No.3,2000, pp. 740-749.
[8] Stahly G B ,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the stigma of cancer: An overview”, Journal of Psychosocial Oncology, No.6,1998, pp.3-27.
[9] Harcourt D , Frith H ,“Women’s Experiences of an Altered Appearance during Chemotherapy: An Indication of Cancer Status”,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Vol.13, No.5,2008, pp. 597-606.
[10] Knapp-Oliver S , Moyer A ,“Visibility and the Stigmatization of Cancer: Context Matters”,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39, No.12,2009, pp.2798-2808.
[11] Suwankhong D, & Liamputtong P, “Breast cancer treatment: experiences of changes and social stigma among Thai women in southern Thailand”, Cancer Nursing, Vol.39, No.3,2016, pp.213-222.
[12] Trusson D , Pilnick A ,“Between stigma and pink positivity: women’s perceptions of social interactions during and after breast cancer treatment”,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39, No.3,2017, pp.458-473.
[13] Peters L, den Boer D J, Kok G, Schaalma H P , “Public reactions towards people with AIDS: An attributional analysis”, Patient Education and Counseling, Vol.24, No.3,1994, pp. 323-335.
[14] ChappleA , Ziebland S, McPherson A ,“Stigma, shame, and blame experienced by 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qualitative study”, BMJ, pp.1470.
[15] Knapp-Oliver S, Moyer A ,“Causal attributions predict willingness to support the allocation of funding to lung cancer treatment programs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42, No.10,2012, pp. 2368-2385.
[16] Else-Quest N M, LoConte N K, Schiller J H, Hyde J S, “Perceived stigma, self-blame, and adjustment among lung, breast and prostate cancer patients”, Psychology &Health,Vol.24, No.8,2009, pp. 949-964.
[17] Shepherd M A , Gerend M A ,“The blame game: Cervical cancer, knowledge of its link to human papillomavirus and stigma ”,Psychology & Health, Vol.29, No.1,2014, pp. 94-109.
[18] Gregg J L ,“An Unanticipated Source of Hope: Stigma and Cervical Cancer in Brazil”,Medical Anthropology Quarterly, Vol.25, No.1,2011, pp. 70-84.
[19] Link B G, Phelan J C ,“Conceptualizing stigma”,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27, No.1,2001, pp.363-385.
[20] Bos A E R, Pryor J B, Reeder, G D, Stutterheim S E, “Stigma: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Basic and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Vol.35, No.1,2013, pp.1-9.
[21] Nyblade L , Stockton M , Travasso S , et al.,“A qualitative exploration of cervical and breast cancer stigma in Karnataka, India”,BMC Women’s Health, No.1,2017, pp.58.
[22] 黄盈盈、鲍雨:《经历乳腺癌:从“疾病”到“残缺”的女性身体》,《社会》2013年第2期。
[23] Balmer C , Griffiths F , Dunn J , “ A qualitative systematic review exploring lay understandingof cancer by adults without a cancer diagnosis”,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Vol.70, No.8,2014, pp.1688-1701.
[24] Lanfranchi A, “The science, studies and sociology of the abortion breast cancer link”, Issues in law & medicine, Vol.21, No.2,2005, pp.95-108.
[25] 姚霏、鞠茹:《医疗内外的社会性别——近代中国子宫癌的认知、发病与诊疗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6期。
[26] 王娟娟:《乳腺癌患者的污名建构研究——以云南省Z医院患者为例》,昆明:云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7年。
[27] Brunet J, Sabiston C M, Burke S, “Surviving breast cancer: women's experiences with their changed bodies ”,Body Image, Vol.10, No.3,2013, pp.344-35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18BSH032)
作者简介:唐魁玉,1962年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生活方式研究会副会长;杨静,1990年生,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19)05-0091-07
[责任编辑:杨大威]
标签:污名论文; 宫颈癌论文; 乳腺癌论文; 癌症论文; 患者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黑龙江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社会质量理论视野下的网络美好生活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18BSH032)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人文社科与法学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