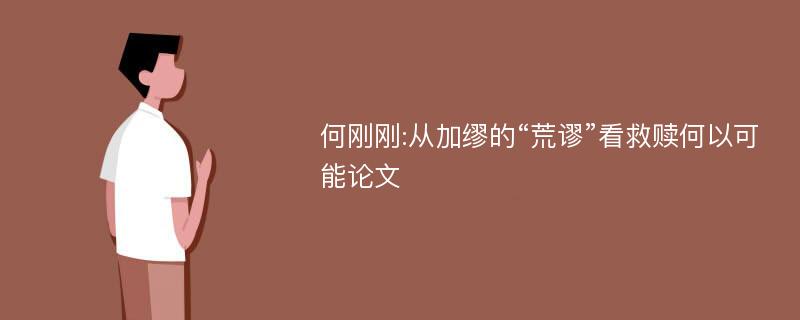
摘要:“荒谬”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很深刻的历史渊源,而加缪则将“荒谬”这一概念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以加缪哲学中的“荒谬”与“救赎”为主线,探讨处在荒谬之中的孤独个体何以能够实现自身的救赎,我们会发现加缪不仅将西方传统中非理性的荒谬感上升到了哲学概念的高度,而且他的“荒谬”不同于虚无主义,因为他虽然入于荒谬,却又能出于救赎。加缪对于人性尊严的认可以及对于光明的追求才是其哲学的核心之所在。
关键词:荒谬;反抗;加缪
一、荒谬哲学之“荒谬”及其“救赎”
(一)“荒谬”的历史流变
“荒谬”一词来自于拉丁文,意思是“不合乎曲调,无意义的”。“absurds”其前缀“ab”作用是加强语气,后缀“surds”意思是“聋”或“被蒙住”。由此推断,“荒谬”是人感觉的一种判断,主要是指一种直观感受,而且在主体看来这种直观感受是非理性甚至无意义的。从西方哲学来看“荒谬”具有深远的历史背景。基督教哲学家德尔图良就曾说过“因为荒谬,所以相信”。在德尔图良这里“荒谬”一词已经不同于日常用语,而是带有哲学意味。但是这也并未上升到概念层次,它仅仅是指一种与理性精神性相冲突之后产生的感觉。
在德尔图良之后,“荒谬”在西方哲学中一直存在,但是由于近代理性精神的兴起压制了这种非理性因素,直到克尔凯戈尔又将“荒谬”一词重提。然而在克氏那里,荒谬仍是被视作一种情感性的词语。在克氏之后舍斯托夫开始公开地反抗黑格尔主义。他认为人的生存就是一个没有根据的深渊,人要么求助理性及其形而上学,要么听从于上帝的呼告。然而恰恰是这样一种关心活着的人的真理,却被人们认为是荒谬和不可能的。舍斯托夫的荒谬基于他对必然性的驳斥。尊重必然性,崇拜理性,这是西方哲学的一贯传统,特别是笛卡尔之后理性之墙就更加牢固。然而面对这样一堵墙,舍斯托夫提出了“以头撞墙”的理论。他认为必然性才是最大的荒谬,必然性不过是为了让人们更加顺从而已。“这种对于必然性的承认与顺从,使得人们的心灵在失去自由的时候得到补偿。全部哲学教导他们同样违背人的意愿,而我们需要在荒谬之中依靠信仰去撞理性之墙。”[1]118在意识到荒谬的事实之后,几乎每个哲学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从克尔凯戈尔到舍斯托夫,随着对于荒谬认识的深化,救赎方式也在发生改变。
(二)“荒谬”视野下的“救赎”
克氏用为上帝献子的亚伯拉罕来说明当信仰与理性出现悖论,个体产生一种荒谬感的时候,人应该如何去实现救赎。克氏给出的答案是人应该去委身于信仰,依靠激情的力量来实现救赎。亚伯拉罕之所以如此坚定,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也可以拒绝献上以撒,同样可以去热爱上帝,但是由此而言,他却没有了信仰。因为一个没有信仰的人若是热爱上帝,那实际上只是在反映自己而已[2]32。其次,作为一个虔诚的信仰者来说,那种充满恐惧与颤栗之路本身就是通往信仰之路。克氏认为上帝对于个体的考验是一个过程,而且必须独自去承受。对于亚伯拉罕而言真正的考验绝非献上儿子那件事本身,而是整个事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巨大的荒谬,而最后委身于信仰实现救赎。克氏显然是将信仰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层面,这对一般受众来说根本难以达到的高度。而舍斯托夫相信上帝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上帝那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哲学的使命就在于把自己从理性精神中解放出来,去寻找荒谬与悖论。他认为哲学就是依靠信仰去将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的东西,并依靠勇气在无尽的荒谬中寻找真理”。虽然舍斯托夫与克氏的救赎观点有所不同,但是舍斯托夫认为,依靠信仰就能获得救赎的观点与克尔凯戈尔很是相似。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仅仅从信仰的角度出发,这就把那些无信仰的人就排除了。当舍斯托夫提出“以头撞墙”时,他们的意思是“信仰依靠荒谬支撑,任何人都不会对这种论断产生怀疑”。荒谬是实现信仰的前提,究竟人是为了救赎还是为了信仰,这是一个问题。德尔图良和克尔凯戈尔坚决声称,“因为荒谬才可信,正因为不可能才肯定,争取把不可能变为可能,乃是一场疯狂的斗争,都是一场疯狂的斗争,是以眼泪、呻吟和诅咒为代价的斗争”。然而这种斗争似乎只有少数信仰者才可以完成,可是对于那些不信上帝的人又何以救赎,这是他们所没有解决的。
二、加缪之“荒谬”及其“救赎”
(一)加缪之“荒谬”
在西方思想史中真正将“荒谬”上升到哲学概念高度的人应是加缪。他对于荒谬的论述最为深刻。西西弗斯的荒谬的思想来源建立在尼采提出的“永恒轮回”的基础上。尼采将传统西方时间观从直线型变成了圆周式的“永恒轮回”。他说:“你现在和过去的生活也就是你以后的生活,并且再过无数遍,其间将没有任何新东西,而只有每一种痛苦与快乐,每一思想和每一声叹息包括这个蜘蛛与树间的月影,也将一再重复。”[3]317尼采以“永恒轮回”对传统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单一维度下所最终追求的目的论进行了激烈的驳斥。永恒轮回保证了生命永恒的同时,也使得生命的神圣性消失,荒谬由此而出现。加缪正是在这一点上进行了分析。加缪对于“荒谬”的论述是从人的存在状态切入的。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判断人生值得存在与否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其余的,如世界是否是三维的,精神是否有九个或者十二个等级都在其次。”[4]624他从对自杀的探讨中推论出荒谬,探讨荒谬。他认为荒谬是人的自杀的情感来源。人的存在的意义,不过是出于一种自我慰藉。有一天当人突然被剥夺了幻觉之后,意识到自己在世上不过是一个局外人,这种放逐便是荒谬感。
加缪对于荒谬的论述更多的是侧重于每一个个体的感受,而非严格的理性证明。我们的日常生活——起床、吃饭、电车、下班——这些不过是程序化的事情。但是当人在循环之中如果追问到“意义”之时,就会对自己所在的世界以及所做的事情产生质疑。西西弗斯如果能够一直推石头,始终不去思考“为什么”的问题的话,那么天神的惩罚本身也就没有太多的威慑力。然而已经身处在程序化之中却依然看清了这种虚无性,那么荒谬感也就由此产生了。
在《局外人》中加缪将这种荒谬感表现得淋漓尽致。主人公默尔索已经意识到了荒谬,而且力图为生命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性。姑且先抛开他的“反抗”不谈,仅仅就其对于荒诞的体会来说也是深刻至极的。默尔索在母亲去世后并没有异常的痛苦,而是依旧以局外人的姿态来审视这个世界。在给母亲送葬途中,默尔索看到风景那一刻觉得“这片土地上将最绝望的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而面对着这种绝望由此而来的荒谬感,默尔索认为出路是没有的”[5]11。这些都是对于荒谬的具体感受。至于荒谬的体会如何成就荒谬的概念,在更深层次上而言,是由于人所生存的无根基性所致。
默尔索曾说:“我曾以某种方式来生活过,我也可能以另外一种方式来生活。我做过这件事,没有做过那件事,什么都毫无意义。我很明白这是为什么。”[6]126默尔索的这段话表达了他对人类生存信念的质疑。他认为人们所过的生活和所做的选择也是没有意义的,而且来世与救赎本身也没有意义。上面可以看出,在加缪这里“荒谬”不再是一种情感性的个体体验,而是作为哲学概念出现的。
对六安红军邮局进行扩建,开发许多吸引游客的特色产品,设计文创产品,进行“文化创意”。可以制作以当地红军为主题的邮票、信封、信纸、印章、印泥等一系列原始的通信工具,可自己保存亦可作礼物送人,既具有收藏价值又具有使用价值;制作系列连环画将当地红军的故事画下来,整理成册,可作为中小学红色思想教育的趣味读物,新颖不失教育作用,让孩子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感受到那个年代发生的故事,并且珍惜当下;再例如制作“游客感受展览墙”,游客将参观当地红色景点及该邮局过后的所思所想通过写信的形式写出来,并在墙上展示出来,又或者给将来的自己或者是自己的家人写一封信,景区到了约定的时间便给自己指定的地点寄过去。
综上所述,从第一个问题谈起。对于那些不认为世界是荒谬的人能否实现救赎。从古至今的任何一种宗教必须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似乎得救者必须信仰,对于那些不信教的人而言似乎只能堕入黑暗。倘若加缪的哲学也是如此,那么也就没有存在下去的意义。因为仅就加缪所批判的基督教而言,也比加缪的救赎理论要精致得多。加缪的哲学之所以能被奉为时代的良心,就在于它能够使得人类实现一种普遍性的救赎。
(二)从“局外人”到“西西弗斯”式的救赎观
加缪对“荒谬”与“救赎”的论述是同时展开的。《局外人》中的默尔索,生活方面与常人并没有什么不同,唯一有区别的是默尔索的生活得过且过,而且异常敏感。他尤其注重那些被别人忽视的细节。这两个特点,前者最能表现一种“局外人”的状态,而后者则引起“荒谬感”。在开篇中得知母亲死后,默尔索依然在意的是日期,而非母亲去世的这一事实;给母亲守灵时他所关注的依然是别人的衣着和神态;最后在送葬的路上,默尔索甚至欣赏起风景来。整个事件中,他似乎没有表露出任何悲伤,但是直至法庭对他进行“审判”时,默尔索对于荒谬的认识才展露无余。
阿尔及利亚刑事审判系统的官员们把先前出现的所有偶然事件以及默尔索被动的反应联系在一起,企图把他描绘成一个怪物。这种看似合乎理性与逻辑的审判系统本身就有许多荒谬之处,因为他们尽可能去证明一个已经接受了的前提,即默尔索是有罪的。加缪试图从对默尔索的审判来批判整个刑事审判系统的荒谬性。以刑事审判系统为代表的国家机器,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毁灭默尔索,是因为默尔索实际上在以一种极端的荒谬来反抗荒谬。“默尔索在荒谬中代表的是一种真正的威胁。他恐怖之处不是他犯罪或者作恶的倾向,而是他对于大多数人赖以生存的希望、信念和理想的漠不关心。默尔索由此变成了一个极度危险的人。”[7]54这个“危险的人”一词是针对法庭而言的,但是如果站在法庭的对立面而言的话,默尔索却是一个反抗英雄。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冷眼旁观和随遇而安与中国道家哲学中的“顺其自然”不同。后者是一种顺从的哲学,而前者则代表着反抗。
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认为,“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概念”,对于新媒体的概念,至今未有明确定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就是一种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通过信息的传递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它是一种媒介,当然,它采用的是当代最新的科技手段。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黎瑞刚认为,新媒体是继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之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它通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有线网络等渠道以及电脑、手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
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西西弗斯在加缪那里已经成为了全人类命运抗争的代言人。在这点上《鼠疫》表达得更为清楚。加缪给里厄医生设置了更为荒谬的生活场景,但是里厄与默尔索的不同在于他关注别人的幸福。他对别人的痛苦以及自己的职业道德有着清醒的认识。作为医生,他的使命就是与痛苦死亡来战斗。尽管他也知道鼠疫对于他来说不过是一场无休止的失败。这点可以说是对于西西弗斯精神的继承,但是与西西弗斯不同之处在于里厄除了嘲笑天神和勇敢前行之外,他还有一层道德意义上的崇高。因为他始终在尽自己的可能去保护他人享有更加美好和长久的未来。而且,里厄认为这些付出都是理所当然的,因此这就将西西弗斯精神从自我救赎提高到了全人类救赎的高度。
走笔至此,加缪似乎完成了从荒谬到救赎的指引。但是,加缪的救赎方式依然存在三个问题。首先是人何以认识到荒谬的事实。从加缪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反抗的前提正是建立在认识到荒谬的基础之上。但是如果对于局中人而言,依然躲在理性之墙下企图寻找到慰藉。那么对于这些人来说救赎是否是可能的?第二个问题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所推的是石头。可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荒谬的具体事物是不断变化的。如果石头变成了其他东西,那么同样的救赎方式能否依然适用?最后一个问题是反抗本身并不是目的,所有人都应该在反抗中得到幸福与尊严,因此反抗的限度何在?
在加缪看来不仅现存的东西需要反抗,而且连上帝和彼岸都是如此。在默尔索与神父的交流中,他认为自己至少能把握现在,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而没有别的指引。死亡在他眼里更加无所谓,因为所有人都要死,殊途同归而已。而代表着基督教的神父在他看来还不及女人的一根头发。这点充分表现了加缪的反神论倾向,高扬了人道主义。
1)杜兰德为18世纪巴黎当时颇具影响力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建筑学院的老师、建筑师,是新古典主义中的重要人物,理性主义理念的重要代表,他为每个可以想象的建筑类型提出了易于重现的构想,从传统的宫殿、教堂,到新兴的图书馆、监狱、市场和博物馆。
三、加缪的救赎观何以可能
这样说来,局外人的出现是因为个体感受到了人生的荒谬,以一种反观荒谬的视角来摆脱荒谬。可以说默尔索的反抗是极其深刻的,但是这种反抗本身却成了最大的荒谬。而且反抗竟然以生命作为代价,而这种形式的反抗究竟值得与否,这正是《西西弗斯神话》中加缪所要探讨的话题。加缪在文中提出:“认识到世界是荒诞时是否就意味着生活不值得过呢?”他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认识到荒谬之后依然可以有尊严地去生活。除此之外,加缪认为荒谬的结果应该是激情,西西弗斯知道自己的未来永如今日,自己只有改变自己来与命运抗争。这样他就比惩罚他的诸神更加坚强。他用执拗的热情拒绝悲哀来拥抱自己的劳动,以此来嘲笑诸神,并且声称 “不存在任何嘲笑所无法改变的命运”。而西西弗斯拒绝去顺从神明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主宰。纯粹的幸福也就在这一主宰之中,因此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考察以往永磁无刷直流电机产品,电枢冲片梯形槽均是以Ansoft计算所得理想梯形槽参数为基础,利用传统作圆求交点法所制。经分析,由传统作圆求交点法所制梯形槽与实际Ansoft计算所得理想梯形槽存在较大差异,现以一台某型号无人机用永磁无刷直流舵电机(基本参数如表1)为例,先阐述传统作圆求点制电枢冲片梯形槽法;然后对比理想梯形槽找出差异,再分析差异对电机槽满率及性能的影响,最后,提出以作平行线求交点法制理想梯形槽电枢冲片的完善措施。
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他的生存方式与人类大不相同。加缪认为人类终生都在做同样的工作,这种命运同样也是荒诞的。但是与西西弗斯相比,人类却更容易得到幸福,因为平凡的生活可能更有意义。尽管工作单调重复,但是人通常也盼望着完成手头的工作。对于工人来说,不论他认识到他自己的整体命运与其他人是否有相似之处,这不是十分重要。因为他生活着,他装一个零件,完成一件工作,其实就是在反抗。每完成一个目标,实际上都是在追求幸福。这种对于幸福的追求本身就是一种救赎,因为天神以荒谬的形式来惩罚西西弗斯就是让其陷入绝望与痛苦。但是纵使没有意识到这种荒谬感的人,他们也是在追求一种拯救。如果说已经意识到天神在惩罚他的西西弗斯乐此不疲地推石头是一种崇高,那么在根源上能用人类固有的对于幸福的追求的动力去溶解掉荒谬本身,就更使得天神的做法显得幼稚而无意义。因此在加缪这里,即便是对于那些毫无信仰,对于彼岸世界没有依恋的人也能获得救赎。
其次,需要讨论的是西西弗斯手中的石头如果变成了其他东西,那么这种反抗是否依然适用。日本作家安部公房在小说《砂女》中将西西弗斯手中的“石头”变成了柔软的“沙粒”。一片荒漠之上的孤独感和村中日复一日的挖沙的行为交织在一起,使得追求自由的人最终深陷于松软的沙粒之中无力反抗。西西弗斯所推的石头,这坚硬无比的东西具有一种天生的反抗感,当客体与主体一致时必须变得同样坚硬。而沙子不同,它代表的是一种柔软与流变。因此安部公房说:“确实,沙子不适合生存,但是固定不变对于生存是否就不可或缺呢?正因为人们执着于固定与不变,所以才会出现厌恶。假如一切如沙子般流动,那么这种感觉就会消失。”[8]5当个体处在松软的沙粒之中得到快乐的同时也丧失了反抗的勇气。现代人承担的荒谬感前所未有,而且这种荒谬是一种无定型的琐碎的东西。如果说,对于西西弗斯手中那个巨大无比的石头的反抗需要勇气,那么反抗现代性的沙子般的荒谬则需要耐心。加缪在书中多次提到了地中海的阳光和沙滩。因此不能只看到西西弗斯的悲壮,还要看到当默尔索躺在地中海岸边沙滩上的惬意。即使默尔索身处在监狱之中,还似乎想起了泥土的香味和海水的味道。反抗与享受,苦难与阳光,这些看似相反的东西实际上也就是事物的一体两面。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不忘记反抗,也不忘记生命的乐趣所在。当沙子流下的时候可以与阳光作伴,而当其威胁到生存时就尽力去反抗。从这一点上而言,只要有足够的拥抱苦难与追求阳光的勇气和耐心,个体就能最终得到救赎。
第三,反抗的限度。加缪提倡反抗荒谬,但是他始终认为反抗应该有一个限度。他认为反抗不应该局限于个体的利益,而且也要为别人的价值考虑。那种以反抗为名义去进行暴力和掠夺的行为毫无意义。因此加缪一生反对暴政和苏联的极权主义。加缪指出,每个人都渴望自由、尊严和美丽,渴望赋予自己存在的统一性。他认为,对于人性而言,存在调整、限制、适度的根本原则。如他所说:“反抗在历史上也是一个无规律的摆钟,在不确定的弧形上不停摆动,不断追寻自己最完美、最深刻的节奏。但是,这种不规则不是绝对的,他始终围绕一个中轴,有自己的调整与限度。”[9]294因此任何暴力学说本身都是与加缪救赎理论背道而驰的,反抗本身是为了追求阳光。这里体现了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也只有给予反抗以限度,才能让加缪哲学中的反抗成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最终给予身处在孤独与荒谬之中的全人类以救赎。
常规的自动化控制技术早已无法紧跟当前时代发展的脚步。常规的电气工程自动化控制必须以相应的控制模型为基础,而创建控制模型会提高电气工程的复杂程度,且取得的效果也并不是十分的理想,造成最终结果严重缺少准确性。具体来讲,也就是说创建出的控制模型还有较多的不足之处,但通过充分运用智能化技术,就能够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在运用智能化技术的过程当中,不仅无需建立相应的控制模型,同时还能在不建立控制模型的同时提高电气工程整体的控制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发挥出了电气设备应有的作用,降低了相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另外,在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中应用智能化技术还能够大大提高操作的精确性,加快了电气行业的发展步伐。
四、结语
加缪继承了传统西方哲学关于“荒谬”的探讨,并提出了他独特的救赎观。加缪身上独特的地中海气质使得他像一个游离在边界的游侠,在历史盲目的潮流中固守着理性与激情的平衡。可以说,他的思想是在生命与爱的前提下,用节制与平衡以及古希腊智慧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准则。面对荒谬,他主张的反抗也是建立在博爱和人道主义基础之上的。加缪对于人类生存的无根性以及荒谬感的论述独树一帜,但是,他又能入于荒谬而出于救赎。这种救赎不同于以往依靠彼岸或者上帝。加缪认为荒谬是不可逃避的事实,但是,他认为正是因为荒谬,所以才要反抗。这种反抗从心理上到实际行动上再到集体反抗,每一次反抗都是在靠近幸福。作为个体的人只能依靠自己来获得尊严。所以加缪哲学根本不是大众所理解的那种虚无主义。相反,加缪对于人性尊严的认可以及对光明的追求很是强烈。在他的反抗哲学中,依稀可以看到那个出身于阿尔及利亚贫民窟的孤儿。不论一生多么艰难坎坷,他都始终没有忘记对于地中海阳光的追求。正如诺贝尔奖给予加缪的评价一样,他的哲学冷静而热情地阐明了人类的良知以及向往,这些也许就是他毕生所追求的东西。
参考文献:
[1] 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M].张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祁克果.恐惧与颤栗[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 尼采.快乐的科学[M].黄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4] 加缪.西西弗斯神话[M].郭宏安,译.上海:译林出版社,1999.
[5] 加缪.流放与王国[M].杨灿,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6] 加缪.局外人[M].柳鸣九,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7] 理查德·坎伯.加缪[M].马振涛,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8] 安部公房.砂女[M].千荣胜,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9] 加缪.反抗者[M].吕永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AnalysisonthePossibilityofSalvationthroughCamus'sConceptof"Absurdity"
HEGanggang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100)
Abstract:The concept of "Absurdity" has a deep historical origin in western philosophy. And Camus raised it to a level of philosophical. From the concepts of "Absurdity" and "Salvation" in Camus's philosophy,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that how could the lone individual in the absurdity to achieve his own salvation. It will find Camus not only promoted the irrational sense of absurd in western traditions to the level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 but also made it different from nihilism. Because although he started from "Absurdity" but concluded it with "Salvation". Recognition of human dignity and pursuit of light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kernel of Camus's philosophy.
Keywords:absurdity, resistance, Camus
中图分类号:B1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612X(2019)01-0043-05
收稿日期:2018-10-09
作者简介:何刚刚(1994- ),男,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哲学史、科技思想史。
DOI:10.16276/j.cnki.cn51-1670/g.2019.01.008
(责任编辑:邹建雄)
标签:荒谬论文; 加缪论文; 哲学论文; 的人论文; 斯托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法国哲学论文; 《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