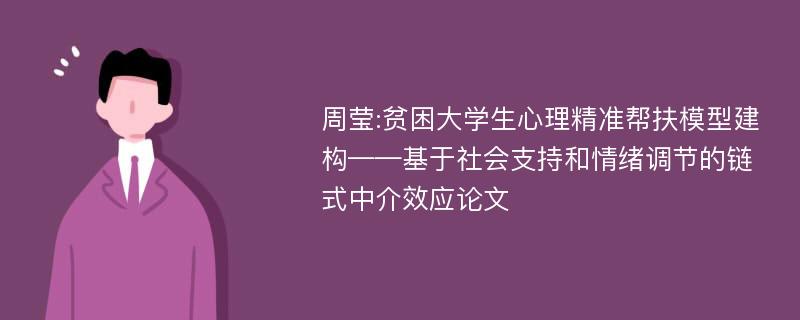
[摘要]在精准扶贫攻坚阶段,心理扶贫亦须精准。贫困大学生帮扶工作不能单纯以经济资助代替帮扶的整体范畴,也要在帮扶工作中充分考虑贫困生群体的心理特征。本研究在参考了权威问卷并结合专家和贫困生访谈后,编制了符合当下贫困生群体特征的生活应激事件量表;将外源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和激发贫困生内在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结合,建构心理精准帮扶的内外源链式中介研究模型。并且,在此基础上提出“精准预防-精准识别-精准建构-精准干预”的方案,帮助贫困生心理脱贫。
[关键词]贫困生;心理扶贫;生活应激;社会支持;情绪调节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贫困大学生帮扶是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据教育部统计资料显示,2017年全国重点高校共录取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10万人,较2016年增长9.3%[注]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2017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再增长9.3%》,2017年8月28日。,作为高校中数量较大、不容忽视的特殊群体,贫困生因物质贫困和资源匮乏饱受经济问题困扰。自1999年6月国家多部门印发《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的管理规定(试行)》(国办发〔1999〕58号)以来,通过一系列资助政策对贫困生的帮扶力度和效果逐年增强。然而,同普通大学生相比,贫困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存在自卑、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注]王静、孙婧:《高校大学生“精准扶贫”实践路径探析》,《高教学刊》2016年第16期。。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在精准扶贫战略的攻坚阶段,心理精准帮扶才能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注]傅安国、黄希庭:《开展心理精准扶贫 破解世代贫困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5日;谢治菊、李小勇:《认知科学与贫困治理》,《探索》2017年第6期。。然而,现阶段的帮扶工作多是“输血式”的资金救助,如何做到助人自助,形成“造血式”的多元化干预路径是一个重要议题。
当前,诸多关于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结论不一。有研究表明,95%的贫困生认为国家助学贷款等经济方面的资助帮助他们缓解了经济压力、激发了学习动力[注]张梅、孙冬青、辛自强等:《我国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1998—2015》,《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第5期。。然而,也有研究显示,相对于普通大学生,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大学生,尤其是被认定为贫困生的大学生,其心理健康水平明显低于非困生[注]程刚、张大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大学生抑郁情绪的影响: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心理与行为研究》2018年第2期;张吉庆、涂叶满:《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追踪观察》,《中国学校卫生》2015年第11期。。贫困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在精神病性、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敌对因子等[注]梁雅丽、姚应水、石玮等:《贫困大学新生心理健康与社会支持应对方式的关系》,《中国学校卫生》2013年第6期。,其中抑郁是一种典型表现,也是贫困生心理健康较差的重要表征之一[注]Dixon, S. K.et al, “Depression and College Stress among University Undergraduates: Do Mattering and Self-esteem Make a Difference?”, in JournalofCollegeStudentDevelopment, Vol.49(2008), pp.412-424.。据此,本研究选取抑郁这一突出心理问题作为因变量。影响贫困生抑郁心理的因素有哪些?国内外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就该问题展开了研究。
(六)三叉形器。良渚诸多墓穴出土了三叉形玉器,这种器是做什么用的,至今没有定论,比较普遍的看法是,这种三叉形玉器是良渚人的冠饰,不是一般人,而是部落首领将其戴在额头上。这种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三叉形器不多,一般一墓只有一件,且放置在墓主人的头部。各墓出土的三叉形器体制差不多,不同的主要是中间的竖梁,有长有短。三叉形器的造型类似汉字“山”。如果将它与圆雕玉鸟比对一下,当发现它们其实是很相像的,所不同的,仅在于玉鸟的双翅是平的,而三叉形器的两边类翅的两叉向后弯曲,如果将三叉形器理解成飞鸟的造型,那么这双翅的靠后就有点变形了,这种变形为的是突出鸟飞得快。
抑郁的产生与发展受到个体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其中大量研究结果指出,人们日常生活中经历的社会生活情景和重要事件的累积,会增加个体的抑郁易感性[注]Kendler K.S.et al, “The Interrelationship of Neuroticism, Sex, and Stressful Life Events in the Prediction of Episodes of Major Depression”, in AmericanJournalofPsychiatry, Vol.161(2004), pp.631-636; Kessler RC., “The Effects of Stressful Life Events on Depression”, in AnnualReviewofPsychology, Vol.48(1997), pp.191-214.。并且,同单一危机事件或转折性生活事件相比,这些日常生活应激事件(Life Stress Events)长期累积形成的叠加效应对个体的身心发展危害更大[注]Kanner, A.D.et al,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Stress Measurement: Daily Hassles and Uplifts versus Major Life Events”, in JournalofBehavioralMedicine, Vol.4(1981), pp.1-39.。目前,国内对致贫生活应激事件的研究除了以往较多关注的经济负担和资源匮乏外,近些年也显示出诸多复杂应激条件,主要涉及个体、人际、环境三个层面:个体层面主要包含自身能力、“贫困生”标签化[注]徐璐璐、吴佩佩、贺雯:《贫困大学生元刻板印象威胁对群际关系的影响:群际焦虑的中介和自尊的调节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8年第4期。、家庭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等;人际层面涉及城乡差异、阶层固化、文化疏离感,以致形成封闭又难以逾越的文化圈[注]叶宝娟:《文化疏离感对汉区高校少数民族大学生幸福感的影响: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和文化智力的调节作用》,《心理科学》2017年第1期。;环境层面主要是学校、制度方面,比如贫困生资格认定中隐私信息过分透明导致 “歧视知觉”增加,甚至部分大学生放弃申请学校的各种补助[注]谢其利、宛蓉、张睿等:《歧视知觉与农村贫困大学生孤独感:核心自我评价、朋友支持的中介作用》,《心理发展与教育》2016年第5期。。
国外研究经历了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本、从注重外部因素到聚焦个体内在机制的研究脉络。20世纪50年代,从英国学者罗森斯坦·罗丹和美国的罗斯托为代表的单纯强调物资匮乏导致的贫困,到60年代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主张教育为阻断贫困产生的作用,再到阿玛蒂亚·森于2003年提出,人的能力及全方位素养的缺失是导致贫困的主要诱因。这些观点虽然各有价值,但也存在以下几个问题:观点较为片面,缺乏立体生态环境下致贫归因的审视;现有研究缺乏有效的测量工具,数据掌握不全面;帮扶手段碎片化、短视化现象严重。因此,针对高校贫困生生活应激事件的精准量化识别,以及这些事件对高校贫困生身心发展产生的具体影响,正是下一步心理精准扶贫首先需要回答的源头性问题。生活应激事件如何影响贫困生抑郁心理?中介分析可以揭示自变量(生活应激事件)“怎样”对因变量(抑郁)起作用[注]温忠麟、叶宝娟:《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竞争还是替补》,《心理学报》2014年第5期。。所以,应探讨生活应激影响贫困生抑郁心理的中介机制。
应激的压力缓冲模型(Stress Buffering Model)[注] Lazarus, R.et al, “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New York: Sprin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84.指出,即使面对同样的事件或相同强度的压力,个体会因环境或个人认知因素的不同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而这些应激源与应激反应之间的中介因素发挥了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注]Cohen, S.et al,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tress and Disorder”, in R.W.J.Neufeld(Ed.), Advances in the Investiga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1988, pp.235-283.。能够缓解负面应激反应(如抑郁)的中介变量称为保护性变量(Protective factor),相反,引起问题行为或加重负面应激反应的是威胁性变量(Risk factor)[注]Rutter, M, “Psychosocial Resilience and Protective Mechanism”, in J.Rolf.A.Masten.etal(Eds.), Risk and Protective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Psychopathology,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81-214.。Gerdes将保护性变量分为内源性的个人因素和外源性的社会因素[注]Gerdes. H.et al, “Emotional, Social, and Academic Adjust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Retention”, in JournalofCounselingandDevelopment, Vol.72(1994), pp.281-288.。具体到以往心理精准帮扶模型的研究中,多是单一保护性变量,即要么是外源性的家庭、学校、社会系统,要么是内生性的个人认知、应对方式、情绪等因素。但序列性的中介变量,特别是结合外源性-内生性系统的序列模型建构不足。从外源性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 System, 以下简称SSS)视角看,黄希庭以世代贫困(Intergenerational Poverty)为线索,首次提出“心理精准扶贫”[注]傅安国、黄希庭:《开展心理精准扶贫 破解世代贫困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8年3月5日。。徐海燕从社会支持视角,提出开展具有区域民族特色的精准心理扶贫研究[注]徐海燕:《社会支持视角下少数民族贫困大学生精准心理扶贫研究》,《科教导刊》2016年第6期。。从内生性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以下简称CERS)视角看,CERS对由于负性生活事件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社交焦虑、抑郁等有重要的缓解作用[注]参见伍新春、周宵、刘淋淋等:《青少年的感恩对创伤后成长的影响:社会支持与主动反刍的中介作用》,《心理科学》2014年第5期;曾嘉鸿、陆爱桃、郭熠阳等:《高校贫困生的社会支持和社交焦虑的关系: 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心理研究》2017年第2期;杨慧芳、熊俊霞、董潮恩:《大学生情绪调节方式在社会支持与抑郁间的中介作用》,《中国学校卫生》2017年第8期。。从以上研究成果观察,将SSS和CERS做序列中介进行定量研究的文献较少。并且,由于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时期和大学管理体制的差异性,国外文献中现有的路径模型能否直接运用还有待商榷。
假设1:生活应激事件对高校贫困生抑郁有正向预测作用;
综上所述,以往心理精准扶贫的整个过程,缺乏贫困大学生心理动态的数据信息化管理手段,仅仅对贫困生家庭收入、消费能力等信息做建档立卡,而对每位贫困生的具体致贫原因、心理问题程度和正在接受的帮扶手段、效果却难以客观考量和追踪调研。这将直接导致贫困生易遭受“心理返贫”和“物质返贫”的双重打击。综上,本研究建立了如图1所示的假设模型,并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2:在生活应激事件对高校贫困生抑郁的影响过程中,SSS和CERS充当链式中介作用。
图1拟检验的假设模型M1
二、数据测量
(一)调查对象与测量工具
本研究选择国内2—3个经济较不发达的城市,对约8所高校不同年级的贫困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根据学校资助中心或学工部提供的贫困生数据库名单,进行内部招募以保护贫困生的隐私;主要筛选标准为家庭经济困难,人均月收入低于所在城市低保线的贫困生)。共发出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46份(回收率92.3%),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625份(有效率96.7%)。其中男生297人(占47.5%),女生328人(占52.5%)。被试年纪结构为大一228名(36.5%),大二148名(23.7%),大三140名(22.4%),大四109名(17.4%)。
1. 生活应激事件量表(Life Stress Events Scale)
本系统主要通过选择一个3层神经网络结构,在输入层中加入样本X,通过对NET进行使用,确保能够表示所有来自输入层的神经元Om的输入总合,而且其得到的输出结果为On。同时将Wmn作为系统权系数定义,通过不断采用sigm oid函数,确保能够将其作为激发函数作用的所有的神经元。
采用朴智元根据Cobb和Wills对社会支持的分类编制的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该量表共25道5级Likert题项,分为情感支持(共11项)和信息支持(共9项)两个维度,得分越多表明获得的社会支持程度越高。本量表先由教育心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翻译成中文,然后交由留韩教育学博士再翻译成韩文,并由教育学专业教授进行进一步修改和调整。经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39,KMO值为0.962>0.8,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为0.000<0.05,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CES-D是评定个体抑郁状态的问卷,主要判定过去一周时间内抑郁症状或感觉出现的频率。CES-D共20题,其中4个为反向计分,每个条目分为1—3级评分。本研究采用Radolff四因素结构,包含抑郁情绪、积极情绪、躯体症状、人际4个维度。全量表的重测信度0.877,4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441—0.854。
本研究使用SPSS18.0及AMOS23.0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管理与分析。首先,修订生活应激事件问卷。在正式问卷形成之前,通过前期相关量表收集、专家咨询和贫困生访谈,确定贫困生背后潜隐的生活应激因素,作为修订初始量表的参考资料。并咨询3—5位专家对量表的问题项进行修改和完善,对约200名贫困生进行小范围施测,征集被试对问卷的反馈和修改意见。其次,对贫困大学生生活应激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效度检验。第三,使用SPSS软件就抑郁影响因素的分布特点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变量间Pearson相关分析和中介变量逐步检验分析。最后,使用AMOS进行链式中介检验和模型拟合度检验。
在抛锚式教学中,学生通过多种方法解决问题后,在教师的组织下对自主学习的结果进行讨论和交流。随着学生大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倾听其他人的意见,从而补充并修正自身对问题的理解,让学生在过程中培养了交流与表达的能力,以及得出结论的能力。
本研究参考了国内外普通大学生和贫困大学生生活应激事件的相关量表和文献,从压力源出发编制贫困大学生可能遭遇的生活应激题项并进行无记名问卷调查。生活应激事件量表共50题,分为以下8个维度:价值观、朋友关系、经济状况、师生关系、家庭、恋爱、职业规划、学业状况,每个维度包含4—8题。问卷设计基于5点Likert量表形式进行计分,得分越多表明生活应激程度越高。经检验,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922,KMO值为0.898>0.8,Bartlett球形检验sig值为0.000<0.05,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3. 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量表(Cognitive Emotion Regulation Strategies Questionnaire)
采用由Garnefski等人编制的自我评估问卷,国内研究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应用最为广泛的有朱熊兆的中文修订版且信度良好。问卷由积极重新关注、积极重新评价、理性分析、积极重新计划、接受5种适应性策略,以及责难自己、灾难化、责难他人、沉思4种非适应性策略共9个量表组成。由于本文致力于探寻缓解贫困大学生抑郁情绪的模型,因此选取积极重新关注(4项)、积极重新评价(4项)、理性分析(4项)、积极重新计划(4项)、接受(4项)5种适应性策略,采用1(从不)—5(总是)5级Likert题项。CERS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1,5个分量表的α系数为0.48—0.91,全量表的重测信度0.906,5个分量表的重测信度为0.591—0.790。
4. 流调用抑郁量表(The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al Studies-Depression)
穆公见之,使行求马。三月而反报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马也?”对曰:“牦而黄。”使人往取之,牡而骊。穆公不悦。召伯乐而谓之曰:“败矣!子所使求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马之能知也?”伯乐喟然太息曰:“一至于此乎!是乃其所以千万臣而无数者也。若皋之所观,天机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见其所见,不见其所不见;视其所视,而遗其所不视。若皋之相者,乃有贵乎马者也。”马至,果天下之马也。
(二)研究程序与分析工具
在征得调查学校领导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同意后,研究团队以学校为单位展开调查。主试由受过教育学或心理学专业训练的人员担任,将统一标准化指导语和量表填答方式向被试做详细介绍,被试自填。同时在指导语中强调对被试的隐私保护及调查结果的完全保密,要求被试依据自身实际状况如实填答,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问卷填答时间约为25分钟。
2. 社会支持量表(Social Support Scale)
三、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和变量间的关系
对贫困生的生活应激、抑郁、情绪调节和社会支持等变量在男女性别上进行均值比较t检验,所得结果见表1。生活应激方面,总体看男生显著高于女生(t=3.60,p<.001),抑郁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和两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CERS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上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积极重新关注(t=-2.12,p<.001)和理性分析(t=-2.68,p<.001)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即女生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造成的抑郁时,比男生更善于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这两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SSS方面,女生不仅在总体水平上显著高于男生群体(t=-3.89,p<.001),并且在信息支持(t=-3.40,p<.001)和情感支持(t=-3.82,p<.001)两个维度上均高于男生群体,即相对于男生,女生更多地使用社会支持手段。
表1各变量间的性别差异
变量男女NMSDNMSDT生活应激2972.55.523282.41.483.60∗∗∗抑郁2972.38.503282.34.521.00情绪调节2972.99.653283.08.62-1.92社会支持2973.12.733283.34.68-3.89∗∗∗
*p<.05, **p<.01,***p<.001
提水泵站是在新建水源大口井中取水,将水泵置于井内,水泵底端距井底0.8 m,水泵出口接DN 75出水管,出水管用夹板卡住支撑在盖板上。
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差检验ANOVA对625名贫困生进行多组样本间差异显著性分析,所得结果见表2。生活应激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t=11.565,p<.001),大四学生的生活应激水平最高,大二和大三的学生比大一的学生应激水平高。抑郁方面总体水平上呈现年级间的显著性差异(t=8.379,p<.001),大一年级学生抑郁水平最低。SSS和CERS方面,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SSS的信息支持维度(t=3.417,p<.05)呈现年级间的显著性差异,即大一和大三的学生获得的信息支持高于大二和大四的学生。CERS的积极重新关注(t=3.860,p<.01)和积极重新评价(t=3.267,p<.05)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大一和大三的学生更多地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评价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
(二)生活应激事件、抑郁、CERS和SSS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对生活应激与抑郁、SSS、CERS进行相关分析(表略)。生活应激总体同抑郁总体呈现显著正相关(r=.58,p<.001),和CERS总体呈显著负相关(r=-.18,p<.001),和SSS总体呈现显著负相关(r=-.27,p<.001)。抑郁同SSS总体呈显著负相关且相关程度较高(r=-.43,p<.001),抑郁同CERS总体呈显著负相关(r=-.38,p<.001)。SSS和CERS总体呈现较高的显著正相关(r=.72,p<.001)。
表2各变量间的年级差异
变量学年NMSDFDuncan生活应激大一2282.35.49大二1482.50.47大三1402.51.55大四1092.68.4411.565∗∗∗4>1,2,32,3>1抑郁大一2282.24.45大二1482.47.53大三1402.36.53大四1092.47.558.379∗∗∗2,3,4>1情绪调节大一2283.08.66大二1482.95.62大三1403.08.65大四1093.04.571.498n.s.社会支持大一2283.28.73大二1483.14.70大三1403.30.75大四1093.19.611.740n.s.
***p<.001
(三)生活应激事件、SSS和CERS对抑郁预测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生活应激、SSS、CERS以及抑郁两两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这符合进一步对SSS和CERS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的统计学要求。为进一步验证生活应激、SSS和CERS对抑郁的预测作用,以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选取生活应激8个维度、SSS的2个维度和CERS的5个维度作为自变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来评估各维度对抑郁的影响,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生活应激事件变量的价值观(B=.32,p<.001)、朋友(B=.16,p<.001)、家庭(B=.17,p<.001)和恋爱(B=.12,p<.01)4个维度对抑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总体上生活应激事件对抑郁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可以解释39.8%的总体差异(F=50.428,p<.001)。CERS的积极重新关注(B=-.36,p<.001)、积极重新评价(B=-.26,p<.001)和接受(B=-.25,p<.001)3个维度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总体上CERS对抑郁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可以解释27.5%的总体差异(F=46.420,p<.001)。SSS的信息支持(B=-.74,p<.001)和情感支持(B=-.30,p<.001)对抑郁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总体上社会支持变量对抑郁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可以解释30.1%的总体差异(F=132.136,p<.001)。
表3生活应激事件、SSS和CERS对抑郁预测作用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SEBtPβ常数.0812.03.000价值观.02.327.83.000.58朋友关系.03.163.92.000.58经济状况.02.041.24.216.75师生关系.02.01.23.821.70家庭.03.174.13.000.60恋爱.03.122.97.003.62职业规划.03.01.37.712.64学业状况.03.051.22.224.67R2=.398,修正后R2=.390, F=50.428, p=.000, Durbin-Watson=1.681常数.0934.98.000积极重新关注.03-.36-7.13.000.46积极重新评价.04-.26-4.37.000.35理性分析.03.051.02.306.49积极重新计划.04-.10-1.84.069.38接受.03-.25-5.72.000.61
R2=.275,修正后R2=.269, F=46.420, p=.000, Durbin-Watson=1.453常数.0840.36.000信息支持.04-.74-14.23.000.42情感支持.03-.30-5.72.000.42R2=.301,修正后R2=.298, F=132.136, p=.000, Durbin-Watson=1.689
(四)社会支持系统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为了确定自变量(生活应激事件)和中介变量(SSS)对因变量(抑郁)的预测作用,采用Baron&Kenny的因果逐步回归分析法,以抑郁为因变量,生活应激事件和SSS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4)发现,第一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负向预测SSS(B=-.267,p<.001);第二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580,p<.001);第三阶段加入SSS(中介变量)后,生活应激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减弱(B=.501,p<.001),SSS显著负向预测抑郁(B=-.295,p<.001)。
同样,为了确定自变量(生活应激事件)和中介变量(CERS)对因变量(抑郁)的预测作用,以抑郁为因变量,生活应激和CERS为预测变量进行多元层次回归分析。结果(表5)发现,第一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负向预测CERS(B=-.180,p<.001);第二阶段生活应激事件(自变量)显著正向预测抑郁(B=.580,p<.001);第三阶段加入CERS(中介变量)后,生活应激事件对抑郁的直接效应减弱(B=.529,p<.001),SSS显著负向预测抑郁(B=-.293,p<.001)。
大梁接过碗,咕噜噜水灌下了,撩起衣襟,擦掉胡须上的水珠。他瞄着自个儿的脚下,鞋尖儿几寸外的地面上有一摊溏鸡屎。他像是盯着这坨鸡屎说:“东洋人把金宝他女儿放回了,你去上塆看看吧。”
表4社会支持系统的中介效应检验
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R2BT因变量1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2阶段(自变量→因变量)3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生活应激.072-.267-6.901∗∗∗生活应激.336.58017.689∗∗∗生活应激.336.50115.651∗∗∗社会支持.416-.295-9.220∗∗∗社会支持抑郁
***p<.001
表5认知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检验
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R2BT因变量1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2阶段(自变量→因变量)3阶段(自变量/中介变量→因变量)生活应激.032-.180-4.540∗∗∗生活应激.336.58017.689∗∗∗生活应激.336.52916.931∗∗∗情绪调节.420-.293-9.373∗∗∗情绪调节抑郁
***p<.001
(五)社会支持系统和认知情绪调节策略链式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建立结构方程模型进行SSS和CERS链式中介效应的检验。采用Amos23.0建模与分析。
图2修正后链式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M2
本研究对SSS、CERS在生活应激事件和抑郁的中介模型进行验证,如表6所示,模型拟合指数良好(X2=206.269,df=29,p<.001,CFI=.945, RMSEA=.100),但生活应激事件至CERS的路径(C.R.=1.79,p>.05)、SSS至抑郁(C.R.=0.28,p>.05)的路径不显著(表7),M1模型(图1)没有得到支持。进一步验证链式中介模型M2(图2),修正后模型拟合指数良好(X2=209.786,df=31,p<.001,CFI=.944, RMSEA=.097)。并且生活应激事件至SSS(C.R.=-7.83,p<.001)、SSS至CERS(C.R.=21.43,p<.001)、CERS至抑郁(C.R.=-5.21,p<.001)的路径显著,同时生活应激事件至抑郁的路径系数仍显著(C.R.=10.92,p<.001),说明SSS和CERS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综上,M2模型拟合指标均达到统计测量学标准,表示接受该模型。
表6M1中介作用模型拟合指数
模型dfX2IFITLIRMRCFINFIRMSEA>.90>.90<.05>.90>.90<.10检验模型29206.269.945.914.030.945.936.100
表7M1路径系数估计表
路径非标准化系数标准化系数S.E.C.R.生活应激→社会支持-0.76-0.430.10-7.48∗∗∗社会支持→情绪调节0.820.860.0418.62∗∗∗生活应激→情绪调节0.140.080.081.79情绪调节→抑郁-0.22-0.270.07-3.20∗∗∗生活应激→抑郁1.010.750.1010.02∗∗∗社会支持→抑郁0.020.030.070.28
***p<.001
根据M2结果计算(表略),首先,生活应激事件对SSS的直接效应为-.433(p<.01),对CERS和抑郁的总效应分别为-.289(p<.01)和.818(p<.001)。生活应激事件对CERS和抑郁间接效应的路径为生活应激事件→SSS→CERS,生活应激事件→SSS→CERS→抑郁。虽然生活应激事件对CERS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081,p>.05),但生活应激事件通过SSS对其产生间接效应(B=-.370,p<.01)。其次,SSS对CERS的直接效应为.856(p<.01),对抑郁的总效应为-.202(p<.01)。SSS对抑郁间接效应的路径为SSS→CERS→抑郁。虽然SS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不显著(B=.026,p>.05),但SSS通过CERS对其产生间接效应(B=-.228,p<.01)。最后,CERS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为-.266(p<.01)。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科学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对食品品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食品安全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的健康,更事关国家的荣誉和经济的发展。庞国芳指出:“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水平在不断提升,但是我国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仍然存在薄弱环节,我国仍处于食品安全风险隐患凸显和食品安全事件高发期。”因此,顺应时代需求,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方面的应用型人才显得尤为重要,这不仅是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而且针对高校其他专业的大学生也应加深对食品安全方面知识的理解,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新疆是温带大陆性气候,昼夜温差大,属典型的大陆性干燥气候。尤其是处于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南疆部分地区,气候异常干燥,年降雨量较小,缺水严重,而当地土壤沙化现象严重,土壤保水能力差,缺水与土壤保水能力差的现状无疑增加当地棉花种植成本,成为制约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一个瓶颈。
四、结论与讨论
以上研究表明,贫困大学生整体上比普通大学生生活应激水平要高,其中来自于职业规划方面的压力最大,之后依次为学业、价值观、家庭、经济和师生关系等。值得注意的是,以往研究中经济压力等物质性匮乏是导致贫困生心理问题的突出因素,但本研究数据显示,当今贫困生来自个体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等内在需求的压力逐渐加大。并且生活应激事件和抑郁的相关分析显示,价值观和抑郁的相关程度更高。这表明,一方面,1999年至今针对高校学生“奖、贷、助、补、减”等一系列“多元混合”的资助政策体系帮扶效果显著,有力地帮助贫困大学生缓解了经济压力[注]李琳:《对当前高校多元化学生资助体系现状的思考》,《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6年第5期。;但另一方面也应注意到,贫困生经济诉求在得到有效关切后,关于个人能力发展、职业拓展和社会融合等个人提升方面的需求正日益旺盛。
对贫困生的生活应激事件、抑郁在男女性别特征上的统计结果显示,生活应激事件总体看男生显著高于女生,其中经济状况、恋爱和职业规划3个方面也显著高于女生。但在抑郁心理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和两个维度上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和以往研究中男大学生心理健康随年代变迁改善比女大学生更为迅速的结果[注]辛自强、张梅、何琳:《大学生心理健康变迁的横断历史研究》,《心理学报》2012年第5期。相反。其原因分析可能为,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国家人口和计生委)自2003年开始在11个省(区)的11个县(市)启动“关爱女孩行动” 试点工作以来,女生尤其是来自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女生在上学、就业和心理健康层面受到重视有关。相关研究也显示,女贫困生群体心理上更加敏感、易受情绪问题困扰、抑郁易感性也更强,相应问题若得到足够重视和及时干预,其情绪和心理问题的改善也必定明显[注]国力心:《高校贫困女大学生人际交往心理问题研究》,长春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欧阳修后来有所反思,对晏殊也有比较公平的评价,而他《晏元献公挽辞三首》(其三)“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中“明哲保身”一词,至今被不合情理地误解为对晏殊的批评(对此笔者有专文辨析,此不赘),某些宋人笔记也津津乐道于晏殊之“富贵”。由此,长期以来对晏殊等人之评价延伸着自宋以来的偏见。
同时,男女贫困生群体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导致的抑郁心理时,女贫困生在社会支持获得方面不仅在总体水平上显著高于男生群体,并且在信息支持和情感支持两个方面均高于男生群体,即相对于男生,女生更多地使用社会支持手段,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情绪调节方面,男女生群体在总体水平上虽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在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两个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女生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造成的抑郁情绪时,比男生更善于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理性分析这两种积极情绪调节策略。
本研究进行年级间差异显著性分析结果表明,大四学生的生活应激水平最高。在价值观、经济状况、家庭和职业规划方面,大四学生均高于其他年级的贫困生,学业方面大二和大四学生生活应激水平最高。同时,抑郁方面不仅总体水平上呈现年级间的显著性差异,在抑郁情绪、人际和躯体症状三方面呈现显著性差异。这些生活应激事件的年级特点也同样反映在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方面:虽然总体水平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但具体维度看,大一和大三的学生获得的信息支持高于大二和大四的学生。情绪调节的积极重新关注和积极重新评价呈现显著性差异,其中大一和大三的学生更多地使用积极重新关注和评价这两种情绪调节策略。相关研究也显示,即将毕业的大四贫困生面临的首要挑战就是就业压力,而大四学生如果在此时期既没有得到来自外源性学校和相关帮扶机构充分的就业信息和生活指导,也没有充分获得家人的情感支持,那么容易造成更严重的情绪和心理问题,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感、迷茫、失落感将陡增[注]杨静:《社会支持在贫困大学生父母养育方式与心理健康间的中介作用》,《中国学校卫生》2016年第7期。。
研究发现,生活应激事件同抑郁变量间成正相关且相关程度较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注]参见席畅、凌宇、钟明天等:《神经质在大学生应激与抑郁关系中的调节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6年第4期;薛朝霞、卢莉、梁执群:《贫困大学生抑郁情绪调查研究》,《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2010年第7期。。KS Kendler等人在对生活应激事件与抑郁关系的研究中也发现,在抑郁症发病前约有92%的人都经历过琐碎的、无规律的生活应激事件,表明二者之间有紧密关系[注]Kendler KS.et al, “Life Event Dimensions of Loss, Humiliation, Entrapment, and Danger in the Prediction of Onsets of Major Depression and Generalized Anxiety”, in ArchGenPsychiatry, Vol.60(2003), pp.789-96.。而且本研究显示信息支持、积极重新评价和积极再关注情绪调节策略与抑郁水平呈显著负相关,这表明,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导致的抑郁心理时,缺少相应社会支持手段和积极情绪调节策略的贫困生,更容易表现出抑郁的症状。并且,社会支持和情绪调节呈现显著正相关,这表明有更高水平社会支持手段的贫困生更倾向使用积极情绪调节策略,对应激事件进行积极重评和关注来降低抑郁水平。据此,假设1成立。
由图1可以很明显看出,硬质合金与钢两侧界面区内有一定的反应产物形成。当间隙为0.05mm时反应产物贯穿了整个焊缝,随着接头间隙的增大,反应产物越来越不明显。因此,对界面区内产物及钎缝中心区的元素构成进行分析有助于确定界面区产物的类型及钎焊接头形成机理。
基于这种关系本研究进一步探讨生活应激事件与抑郁水平间关系,建立SSS和CERS链式中介模型探讨二者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结构方程模型显示,生活应激事件至SSS、SSS至CERS、CERS至抑郁的路径显著,SSS和CERS共同起到了链式中介作用。由此可知,在实证的角度证明了贫困生在面对生活应激事件导致的抑郁时,环境因素的SSS和个体内在因素的CERS结合,会更有利于缓解抑郁等不良情绪。这也验证了Emmons[注]Emmons RA.et al, “Emotional Conflict and Well-Being; Relation to Perceived Availability, Daily Utilization, and Observer Reports of Social Support”, in 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Vol.68(1995), pp.947-959.和King[注]King LA, “Ambivalence Over Emotional Expression and Reading Emotions in Situations and Faces”, in JournalofPersonalityandSocialPsychology, Vol.74(1998), pp.753-762.的前期研究成果:情绪表达冲突的个体会较少的体会到来自于他人的帮助和关怀。高情绪表达的个体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很大的不适应性,不仅影响其社交能力,限制的交际圈更促使其自闭情绪和更多地使用负向情绪调节,这样消极的认知会加重个体的抑郁水平[注]叶俊杰:《领悟社会支持、实际社会支持与大学生抑郁》,《心理科学》2006年第5期。。据此,假设2成立。
基于实证研究的链式中介模型,本研究提出“精准预防-精准识别-精准建构-精准干预”的方案,帮助贫困生“心理脱贫”:首先通过“精准预防”为高校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预防方案,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贫困生生活压力和支持手段的测评工具,同个人建档立卡信息一起,收集心理精准帮扶数据信息,动态追踪贫困生突出的心理问题,做到及早发现、及早干预。其次,“精准识别”贫困生致贫生活应激事件。从源头找寻贫困生的生活应激源,才能进一步明确“个体-人际-环境”等立体生态系统中心理问题的影响因素,认识贫困生的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制定帮扶策略。第三,“精准建构”心理帮扶的内外机制,通过外源性的社会支持系统和内生性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为链式中介的研究模型,克服单一中介视角的片面性,建立生态系统内及生态系统间缓解贫困生心理问题的联合作用机制。精准指导贫困生学业、就业、心理等一系列核心问题,让贫困生不仅“上得了学”,还能“上的好学”。最后,“精准干预”贫困生的问题心理,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实施生活应激源和焦虑、抑郁等问卷,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咨询和介入,提供朋辈、老乡联络会等人际支持以及学业指导和就业岗位信息指导等社会支持系统;同时激发学生的内在动力,分阶段训练学生的认知情绪调节策略,使贫困生参与到积极心理共建中。综上,在具体的施策过程中,既织好外源性社会支持系统的“面”,也要激发个体内生性情绪调节策略的“点”,通过建立贫困生心理健康数据库,促进高校贫困生的物质、心理双向脱贫。
收稿日期:2019-02-20
作者简介:周 莹(1988—),女,教育学博士,临沂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AWTJ51)、临沂大学2018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山东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研究” (项目编号:18LUBK20)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C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6-0168-08
(责任编辑:陆影)
标签:抑郁论文; 贫困生论文; 社会支持论文; 事件论文; 情绪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心理学论文; 发展心理学(人类心理学)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论文;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新时代教育思想研究”(项目编号:18AWTJ51) 临沂大学2018年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精准扶贫背景下山东高校贫困生心理健康影响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8LUBK20)论文; 临沂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