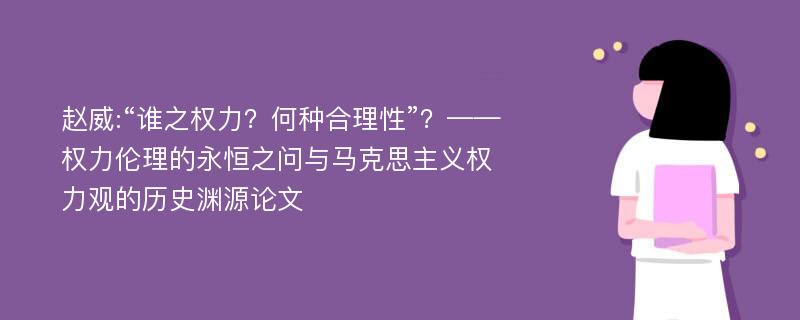
摘要:“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是古今中外政治学的永恒之问,也是权力伦理的核心问题,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自古希腊以来, 先贤已就“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之问展开追寻,他们借助信仰的形式、引入超验的视角、运用思辨的力量,建构一个以终极价值为形上依据,以政治、伦理、法律为形下落实,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指向的权力伦理框架,以表达正义的品格、宣示国家的目的、追溯权力的来源、论证人民的权利,由此揭示了它来自民之权力,走向民之权利,体现民之正义的应然逻辑。对这个永恒之问的求解进程虽然包含了从古希腊经中世纪到近现代的若干历史超越,并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传统资源。但从现实角度看,迄今为止剥削阶级的国家并没有把权力的应然逻辑转化为历史的实然状态。只有“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才真正实现了历史的超越和时代的升华。
关键词:权力伦理;超验;正义;马克思主义权力观
国家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的核心问题则是体现其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权力伦理。自人类进入政治社会以来,先贤们在努力追寻国家善政的过程中,均不约而同地围绕“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问题展开探索,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例外。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注]《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09页。在“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问题上,“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一权力伦理之问的精辟回答。[注]习近平把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为“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新华网2010年9月2日。这一回答既来自对人类文明史上具有人民性的权力伦理思想的继承,又包含着对它的超越。然而,学界目前对权力伦理的研究较少,哲学、政治学即使关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也很少把它聚焦到权力伦理的层面上。在当前强化反腐的新形势下,深化权力伦理的学理研究已成为一个紧迫的课题,因此,本文将循着这一权力伦理之问追寻权力伦理的历史生成及马克思主义对它的时代超越。
一 权力伦理之问: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
学界对“权力”的定义是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的。当代纽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权力论》作者丹尼尔·朗通过综合霍布斯和伯兰特·罗素的权力定义给出这样的权力概念:“权力是某些人对他人产生预期效果的能力。”[注]朗友兴、韩志明主编:《政治学基础文献选读》,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82页。但这个概念偏于宽泛,它可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而其中只有国家政治权力才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因素。王沪宁在《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政治权力指某一个政治主体凭藉一定的政治资源,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强制性的制约能力。”[注]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它一般有如下特征:1.它能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力;2.它是一套系统性的制度安排,而不是单一的行政权力;3.它又是一种可以限制其他集团权力的最高权力。然而,即便政治权力有无上权威,仍需要体现公共性和伦理性,因为只有公共性和伦理性才能维持共同体的稳定存在,并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所以国家的目的和权力的设置只有维护公共利益、增进人民幸福才能实现其价值目标。因此本文所谓权力伦理,就是从伦理角度审视国家权力的本质属性、核心价值、主客关系、渊源流变的一套系统理论,即把“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问题展开为若干环节,如民众为何需要国家?国家权力从哪里来?该权力的本质与核心价值是什么?权力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如何?它为何要包含公共性并体现伦理性?具有公共性的权力伦理追求什么目标?这些问题涉及的虽然只是一种理想型,但它对检视现实状况仍有标尺意义。
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始终是影响人们分析社会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与此相应的是思想家的致思取向也可分为应然和实然两个层面。应然是理性建构的产物,而实然是力量博弈的结果,故应然比实然更有指导意义,也是政治哲学与权力伦理关注的理论焦点。民众为何需要国家呢?从实然的角度看是生存利益的需要。利益好比一只“看不见的手”贯穿在人类的历史时空之中:在自然状态下,支配利益获得的是无序的丛林法则。由于丛林法则的无序只会使自然权利无从保障,它会产生多败俱伤的后果,故需要建立公共组织以行使公共权力、维护公共秩序和分配利益。所以国家作为公共组织,其产生是一个利益、秩序、合理性三者长期博弈的过程。从历史上看国家产生之前通常有一个部落联盟实行原始民主的过程,其中已隐含着无名有实的契约。进入国家状态后,支配利益获得的虽然变为强制的有序的权力法则。这种有序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但由于人性天生有自利化倾向,掌权者如果缺乏有效制约必使权力走向异化,中国上古从“公天下”走向“家天下”的转变即反映了国家产生与权力异化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权力异化和权力垄断的国家既不可能形成符合公共利益的合理秩序,也不利于政治共同体的长期稳定与健康发展,因此,从应然的角度思考国家的应然本质仍然是有必要的。苏格拉底虽然生活在现实的城邦国家中,但他仍主张“在理念中建立国家”,不是由于他无视现实,而是因为他要为现实国家寻求一个有批判鞭策意义的理想型,权力伦理即蕴含在理想型之中。即使是古代的“民本”理论也要承认人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也有“天下为主,君为客”(如黄宗羲)的主张,有如现代政治社会关于人民与授权政府的主客关系在古代的萌芽;古希腊思想家与中世纪神学家更是直接诉诸人民主权;在近代“民主”理论的语境中,无论是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还是马克思宣告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均可以逻辑地推导出人民才是国家的权力主体。从人民授权的角度说,被赋权政府只是权力的客体;但政府被赋权后又拥有依法管理公共事物的权力,这使人民与政府实现了主客体的转换,因此,对“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之问亦可归纳为:它来自民之权力,其合理性应体现为秉持正义服务人民。中国古人云:“夫立国之道,惟义与权……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者,则存乎其义……居上必明其义,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使人日用而不知,则为国之权得矣!”[注][唐]陆贽:《陆宣公文集》卷二。见吴枫主编:《中华思想宝库》,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513页。可见古人深知道义与权力是立国的两大利器,裁处是非、体现权力的国家法制,其基础在于道义,故掌权者须深明道义,通达权变,使道义与权力相融无间,这才算是深得国家权力之精髓。西方圣贤奥古斯丁说:“若没了正义,王国还成什么体统?不就成了强盗团伙了吗?”[注][美]莫德玛·阿德勒:《西方思想宝库》,周汉林等编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796页。所以道义或正义才是国家权力伦理的核心价值,只有兼具赋权的合法性与用权的合理性即法理权威于道义权威的统一才能使国家权力获得它的正当性,只有在权力中贯彻正义原则才能实现政治共同体的公共利益。如下图所示,即使政治实然状态还不符合这一应然理想,人类理性也要在理想的鼓舞下不断改造不合理现实,推动社会政治秩序向合理化方向发展。
其实,在认识国家的本质这一点上,马克思也看到国家“处处陷入它的理想使命同它的现实前提的矛盾中。”[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页。这就是应然与实然两个层面的矛盾:就“理想使命”而言,“国家应该是政治理性和法的理性的实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马克思问道:“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65页。所以国家“主权这个概念本身就不可能有双重的存在,更不可能有对立的存在。”“一个是能在君主身上存在的主权,另一个是只能在人民身上存在的主权。”[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8页。但就“现实的前提”而言,无论是奴隶制封建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与人民利益相对立的。当然,这不是说阶级国家的权力不存在任何公共性。所谓“公共”是指社会成员公平地共有某一事物某种权益。既为共有,就需要有一套共同认可且能维护共有利益的合理规则,——这正是蕴含伦理价值的客观基础。虽说政治权力是与国家状态相联系的,但公共权力早在氏族社会即已萌生,恩格斯曾指出原始农业社会已存在着维护共同利益的公共权力,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等,这种公共权力就是“国家权力的萌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它已包含朴素的伦理意识。但到氏族公社末期,随着私有财产发展与阶级分化,掌握公共权力的群体逐渐蜕变为既得利益阶层,为了使私有财产神圣化,为了使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和阶级统治永久化,国家就被发明出来了,于是,原初的公共权力就异化为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虽然把“公共权力的设立”作为国家的两大特征之一,却认为它并非真正的公共权力,而是“特殊的公共权力”,并明确指出国家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反差:“按照哲学概念,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这虽然是国家权力应有的伦理内涵,但“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11页。马克思则直接把国家称为“冒充的共同体”“虚幻的共同体”,并称“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页。在马克思看来,国家制度、统治者的权力及其所依据的旧社会,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只有它的解体才是政治解放。[注]这句话的原话是:“政治解放同时也是同人民相异化的国家制度即统治者的权力所依据的旧社会的解体。”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4页。也可以说,经典作家对国家起源及其本质的论述已指出了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揭示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作为权力主体与客体之间被颠倒的关系,并从实然意义上得出政治权力是实现阶级利益的工具等科学论断。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与“虚幻的共同体”形成鲜明对立的真正共同体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样的“自由人联合体”。由此可见,理想维度也是经典作家批判现实的价值坐标。
先看作为信仰且高居三者之上的宗教。“宗教关注的首先是正义”[注]吕大吉:《西方宗教思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873页。,西方先贤认为,正义价值如果要代表公共利益,就不能来自有既得利益的统治者,因为让他们定义正义必定捎带私利。要使正义保持超然独立的品格,就必须寄托于一个超越于一切私利之上的终极存在,只有它才是屏蔽特殊利益的“无知之幕”。于是哲学思辨就把价值问题追向最高问题:社会价值应来自终极存在,这个终极存在应是虚拟的神(GOD而非gods),正因为它虚拟、超验,才不会有自己的私利,才不会以权谋私。因此古人精明地将超验的神或预设的自然法视为政治、法律、伦理价值之终极依据。例如,在政治上,世俗王权被认定是上帝授予并用于增进人民福祉的,其形式就是接受授权时的宣誓。在那个信仰虔诚的时代,宣誓是很有约束力的。因此,被授权的国王既要承诺他与上帝之间的圣约,又要信守他与人民之间的民约,而连结上帝、君主、人民之间的价值纽带便是遵从正义这一精神性的誓约。在道德上,上帝所象征的“终极实体是一种普遍的道德秩序。”“社会的本质取决于神、或自然所建立的正义与道德的标准。”[注][美]斯特伦:《人与神——宗教生活的理解》,金泽、何其敏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26、199页。这是因为,除了从上帝或自然法那里引出具有普遍效用的道德律外,任何个人都无权宣称他自己就是道德正义的最高标准。在法律上,宗教通过上帝的永恒法或自然法提供法律的超验之维,因为“一切法律毕竟是从永恒法产生的”,“全部法律都以人们的公共福利为目标,并且仅仅由于这个缘故,它才获得法律的权力和效力。”[注][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11、123页。上述四者均指向人民,并与权力伦理有脉络性的关联:宗教是权力的来源;政治是权力的载体;法律是权力的依据;伦理是权力的灵魂。但如果按黑格尔关于“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注][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53页。的论断看,伦理又是宗教、政治、法律的内在生命:宗教以神圣的权威论证伦理;政治以合理的制度体现伦理,法律以规范的力量捍卫伦理,而权力伦理就在这一系统结构中生成。当然,这个以超验的终极价值为形上依据,以正义的政治、伦理、法律为形下落实,以人民利益为根本指向的权力伦理脉络并非在一朝一夕间形成,它是一个历史与逻辑的进程。
古希腊早期的宗教思想主要是自发的祖先崇拜和神灵崇拜。祖先和神成为人们的价值来源,正义被说成是神带给人们的城邦秩序原则。哲学勃兴后,“哲学呼吁从信奉祖先到信奉善,一种本质的善,一种合乎自然的善”,“自然和公正的思想是在抵制传统权威和非正义的同时产生的。”[注][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第25页。哲人们从思辨的高度,从对自然理性的感悟中追寻国家的伦理内涵。一般认为最早的自然法思想源自赫拉克利特,这位哲人认为一切法律都是以神圣的、足以支持一切的唯一的自然法则为基础,它们最终都只是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神圣法则而做出的努力。[注]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25页。这是自然法的最初形态,也是对价值来源作出超验的探索。有学者指出:“经由赫拉克利特……自然法作为一种自然的不变的法则,而所有人法均由其获得力量的观念,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中。”[注][德]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和哲学》。姚中秋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6页。其后,柏拉图又从伦理的角度把国家的目标定为正义,提出掌权者应该是“法律值勤者”,是人民的“公仆”,主张通过培养美德以实现他心中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指出:“世上一切学问(知识)和技术,其终极(目的)各有一善;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48页。由此勾勒出国家的政治—善德—正义—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罗马思想家西塞罗也指出,国家“是很多人依据一项关于正义的协议和一个为了共同利益的伙伴关系而联合起来的一个集合体。”[注][古罗马]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沈叔平、苏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5页。他还主张要把崇高道德用于国家治理,这也道出了国家权力必须包含伦理价值的内在诉求。所以有现代学者认为政治学方法论的最初阶段就是伦理学。[注]王沪宁主编的《政治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把政治学方法论的发展概括为伦理学、神学、法学、社会学四个阶段。第21—23页。其实对权力伦理的生成过程来说,伦理学始终在场。
二 权力伦理之道:正义价值的系统建构
其实,从古代到近代,权力伦理都不是一个单一学科的、孤立的技术性问题,因此,我们不能只从政治理论和国家学说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要从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的大背景来审视该问题。在近代宗教“祛魅”之前,“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页。按照孟德斯鸠的说法,社会的基本框架大致由宗教、伦理、法律、政治四者构成,[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页。即以宗教、伦理为主的隐性秩序和以法律、政治为主的显性秩序,权力所依托的框架就在这四者之中:它溯自上帝授予,依靠伦理滋养,借助法律规范,通过政治运作。如果说这些领域皆需以某种价值为基础、且各种价值皆需有一个所谓“价值公设”的话,那么这个价值公设只能是正义,因为正义乃是“诸价值的价值”[注][美]迈克尔·J·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万俊人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20页。,从而也是宗教、政治(包括权力)、伦理、法律的核心价值。英国教授杜兹纳曾敏锐地指出:“古典的正义理论可以被描述成一种伦理政治学说,”“但是这种理想不是上帝、天启或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的恩赐,而是思想的建构。”[注][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6页。这不是说古典的伦理政治理想没有宗教支撑,而是说思想的建构之所以借助宗教这一传统的力量,实际是为了以道义对抗强权。孟德斯鸠说:“有一件东西人们有时候可以拿来对抗君主的意志,那就是宗教。”[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第19页。上帝、天启或自然法这些理论预设虽然是思想的建构,但先贤们利用它们来表达政治诉求,其目的在于借“天启”之名来抑制“王启”及“权启”的任性。于是“代神立言”就成为那个时代“代民立言”的表达形式,在追寻政治、伦理、法律的人民性时也借助了信仰的力量。
1.3检测方法 我们根据《中医妇科学》相关的诊断标准来进行诊断,显效:患者的中医证候评分降低超过80%,月经量不超过100ml;有效:患者中医证候评分降低超过60%,月经量减少一半;无效:患者的中医证候评分减少超过60%,经量无改善。有效率=(显效+有效)例数/总例数×100%。
因此,即使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除了存在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外,还涌现许多富有人民性的先进思想,并成为后世进步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既然国家的应然目的与实然状况出现明显的落差,那就会促使一些思想精英从应然方面对实然的国家权力进行拷问,并在批判暴政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政治哲学和权力伦理的逻辑建构。虽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尚未出现“权力伦理”的概念,但如果我们脉络性地解读先贤的政治思想,仍可看到其中含有清晰的权力伦理意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对权力伦理的论述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借助信仰的形式、引入超验的视角[注]按照布朗森的定义,超验主义是“一种建立在超越或超出感觉和知性之上的学说。”参见史蒂夫·威尔肯斯、阿兰·G·帕杰特著:《基督教与西方思想》卷二,刘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运用思辨的力量、建构体现人民性的政治思想体系,以求解“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问题。
父母们以为最大限度尊重孩子的意志,就是制造了民主的家庭氛围,事实上很容易走向极端,制造出专制的氛围。孩子成为本质上的独裁者。孩子一哭,全家就得启动紧张模式,分工合作满足孩子当下需求;孩子要睡觉,全家就得保持安静;孩子怕热,全家就得跟着开空调,冷也得乖乖忍着;孩子爱看动画片,全家就得低龄化,每天守着喜羊羊和灰太狼傻笑。
国家既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那么,政治权力何以会有公共性呢?这是因为,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体,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和社会财富的唯一来源,也是建构国家理论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政治权力作为有组织的暴力,虽然可以有效地把统治者的意志强加在人民身上,但对它所统治的人民也不可权力任性,因为过度压榨只会激化社会矛盾并产生“覆舟”危险,要消除这种危险就不能再简单地依靠暴力,而要对权力进行一定的制度约束和伦理约束。汉初贾谊《新书·大政上》就从暴秦速亡中得出结论:“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进一步说,即使在“载舟”得以维持的情况下,国家仍需要履行社会管理的职能,这就要求国家权力必须以独立的公共权力的面目出现,扮演矛盾调停人或争端仲裁人的角色。因此,即使是阶级统治的国家也明白建构以公平正义为内涵的权力伦理的必要性:就算公平正义不符合当权者的特殊利益和眼前利益,但它符合政权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几乎所有政权都想既成为权力掌控者又充当道义的体现者,为此,它不仅不会赤裸裸地鼓吹压迫有理,还会尽力打造一套冠冕堂皇的官方论述来粉饰自己的统治,为国家权力涂上浓厚的道德色彩,以便使其政权获得合理依据和国民认同,马克思说:“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它们变成某种独立自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他们设想为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她们提出来作为生活原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是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92页。如中国历代王朝虽然皆为阶级统治的国家,但都高举“爱民如子”“为民作主”的大旗。因此即使在“虚幻的共同体”中,从稳定统治的角度看权力伦理仍然是有必要的。但如果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待这个问题,那就不是被动地祈盼“青天大老爷”恩赐雨露阳光,而是要通过根本性的社会革命和制度改造把权力的授予、监督、收回皆握在人民手中,使“为民作主”变为“人民作主”,只有人民的权力才能真正实现维护人民的利益、真正落实权力伦理的价值目标。
国有企业在财务管理预算监督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的现象较为明显,尤其是财务管理部门对其下属单位的监督性不够,直接造成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下降。国有企业及其下属单位属于一个不可分割的利益共同体,其下属单位的财务预算管理工作通常情况下监督的力度远远不足,其中,缺乏科学的规划、目前不明显是最为突出的问题,从而给国有企业的长足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Application of waterscape in small-scale space landscape design
那么洛克是怎样“排挤(基督教先知)哈巴谷”的呢?由于近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启动世俗化的进程,神学政治的色彩开始淡化,以自然法为根据的法学逐渐成为论证权力伦理的主要方法,霍布斯和洛克以自然法与契约论为理论工具,分别从实然和应然层面分析国家权力。霍布斯声称在自然状态下,利益争夺造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结束这种互相伤害的战争状态,人们达成契约,成立国家,把自己的自然权利交国家及其主权者,社会才进入秩序状态。他虽然承认人民是主权的授权者,“不应放弃从中获得利益的权利”,也说过统治者的法律不能违背自然法等,但他又说:“当人缔约放弃某些权利,就理应不去对那些他赋予权力的人设置障碍”[注][美]列奥·斯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上)》,李天然等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这等于说人民不应对赋予的权力实行限制。就算这种追溯比较符合历史实然状态,但它并未回答如果统治者违背契约滥用权力该怎么办的问题。与霍布斯鼓吹“利维坦”式的国家主义理论相反,洛克的解读是:人类的原初状态是平等的,历史的原初状态和个体的原初状态是相同的,这应该被视为正义的原始基础;而现实的不平等不正义是后天的社会条件造成的,因此,现实状态不能成为界定合理与正义的依据。洛克的思路是以人类的本然状态为依据,从对实然状态的批判改造转向对应然状态的追求,也就是说,社会正义在于对不平等不正义的现实的超越。此外,洛克对“权力”起源的解释也比霍布斯合理,他认为在原初状态下人们对自身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受他人侵害而行使的自卫和惩罚,就是自发的权力,但这种权力容易被滥用或不公正,因此需要把这种不够理性的自发权力发展为中立公正的公共权力,国家权力就是为改变自然状态下权力不方便不适当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注][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0页。由此论证了权力的起源、权力的发展与权力的目的。与此同时,洛克对“战争状态”的解读也比霍布斯仅把自然状态视为战争状态的观点深刻,他说:“谁企图将另一个人置于自己的绝对权力之下,谁就同那人处于战争状态。”“因为我有理由认为,凡是不经我同意将我置于其权力之下的人,在他已经得到了我以后,可以任意处置我,甚至也可以随意毁灭我。”“所以我可以合法地把他当作与我处于战争状态的人来对待。”[注][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第13页。可见即使在国家状态下,绝对权力同样会造成一种“战争状态”(“官逼民反”之前即是一种战争可能态)。因此,他肯定人民拥有对不守契约的暴政的反抗权,强调必须约束权力,声称统治者除了依照国家的法律所表示的社会化意志行动外,“他没有意志、没有权力,有的只是法律的意志、法律的权力。”[注][英]洛克:《政府论(下册)》,叶启芳、瞿菊农译,第93页。为此他提出分权政制与限权政府的理论。其后,孟德斯鸠又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并提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2页。的主张,这些著名论断至今仍被全世界普遍认可。但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对政治权力的研究也逐渐从政治哲学领域转向政治科学领域,从理论求索走向制度建设。
“书刊印刷有历史延续性,我们觉得,要把中科印刷发展起来,还是应该按照市场经济的模式,按照企业自身的特性来制定发展规划。”在中科印刷,一方面,出资人要对企业负有直接责任,其经营决策和自己的利益直接挂钩;另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在企业的经营模式转换上,起到决定的作用,确定企业实行股权社会化,即进行企业社会化的改造。有了政策的支持,2015年,中科印刷便在市场大河中寻找到了国彩,两家企业重组合并,进行资金与社会资源的双结合,产生了1+1的效应。
如果说神和自然法在希腊罗马时代构建政治理论中的作用还不如伦理学的话,那么在基督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神学和自然法则明显处在中心地位,只不过是神学其表、伦理其里罢了,因为神学家从上帝和自然法那里引出国家权力应维护社会正义以增进人民福祉的主张,其落脚点是很“世俗”的了。早在中世纪早期,奥古斯丁就反驳“正义就是有利于强者的一切”的谬论,他声称民众是“由对权利的共同承认,由利益的一致性所联系起来的群体”,“权利是从正义之泉流出来的一切,没有真正的正义,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权利。”[注][美]莫德玛·阿德勒、查尔斯·范多伦编:《西方思想宝库》,周汉林等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第802页。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王权也不例外,“上帝一开头就没有把享有无上权力的君王置于他们(指人民)之上。”他宣称如果治理社会的目的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服从统治者的私利,那就是政治上的倒行逆施,是非正义的政治。他还强调“在组织上应作出这样的规定,使国王一旦当政时没有机会成为暴君。”[注][美]《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30、46、57页。到16、17世纪宗教改革时代,加尔文主义的神学家继续高扬主权在民的历史传统。加尔文重申:“上帝是所有权力存在的合法性的源头。”[注][美]道格拉斯·F·凯利:《自由的崛起》,王怡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页。苏格兰神学家又继承加尔文的理念:“人民的直接权力在‘圣约’的观念下,要求政治机关负有责任,依照超验的律法所赋予的有限权力履行政府功能。”1573年神学家霍特曼宣称:“人民始终是国家的所有者,而政府要受到明确的制约。”17世纪的神学家卢塞福声称:“人民在上帝之下,显然保留着政体的权力来源。因为他们同意授予国王的权力是有限的,人民被允许保留的权力相对于国王则是无限的,并且约束和限制着国王。”所以有学者指出:“以上帝主权为中心的加尔文主义恰恰推动了个人和国家的自由,以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平衡。”[注][美]道格拉斯·F·凯利:《自由的崛起》,王怡等译,第69、56、5、130页。正是这些神学化的政治思想成为后来洛克世俗化的政治思想的先声,也为后来的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也说:“正像当时的革命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2页。可见马克思也承认僧侣曾经是革命思想的传播者,先知也曾是革命者反封建的引路人。马克思又说:“克伦威尔和英国人民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革命,就借用过旧约全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当真正的目的已经达到,当英国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造已经实现时,洛克就排挤了哈巴谷。”[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72页。
二 权力伦理之路:历史的超越与马克思主义的升华
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立场出发,我们应肯定西方古代传统对权力伦理建设的贡献,其中中世纪与近现代之间的“伟大历史联系”尤其值得重视。恩格斯曾批评欧洲近代“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未能看到它的成就,这样“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页。马克思也肯定这种历史联系,他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又主张可以“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第464页。我们对历史传统的态度也是如此。
约翰·密尔曾经指出:犹太民族先知们从来都是独立于统治者的对抗性力量,他们“不仅能够以上帝的直接权威对任何他们认为值得如此对待的事情进行公然抨击和表示异议,而且能够提出对民族宗教的更好的和更高的解释。”[注][英]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35页。中世纪神学家们正是遵循这个古老的精神传统。循着先贤追寻权力伦理的足迹,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主线:那就是借助神或自然法的超验之维来表达正义的品格、宣示国家的目的、追溯权力的来源、论证人民的主权……如果我们去掉其神学外衣即可窥见其中的合理内核,因为这些先贤对权力的定位既不是君主本位的,也不是国家本位的;而是利用上帝本位的神学形式来论证人民本位的应然逻辑。这也是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都披着宗教外衣,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来反抗暴政的原因。我们还要看到,在先贤的神学外衣背后,权力主体与客体之间潜藏着巧妙的虚实转换:在人神关系上,表面上是神为主,民为客;但实际上是神为虚,民为实,这与《左传·桓公六年》所说的“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者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而后致力于神”几乎不谋而合,神不过是人民利益愿望的施设罢了。中世纪神学家胡克也说:“人民的声音就‘代表’了上帝的声音。”[注][美]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王怡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这与《尚书·泰誓》说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又何其相似!其高明之处在于,所谓“圣约”“民约”的说词,皆为了“制约”(权力)!再从君民关系上看,在主权在民的逻辑中,上帝所爱护的人民才是君主权力的授权者,对此神学家布鲁图说:“全体人民位于国王之上”,“即使在委任一个国王的时候,人民以特别附加权利条款的方式,也总是保留着原初的主权。”[注][美]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王怡等译,第62页。所以理论上是民为主,君为客;只是在王权统治时代,人民并没有真正享有主权,所谓民为主是虚的,君为主才是实的,所以用超验的预设抑制君权是必要的:对上帝权威的利用已无须多言,即便是虚拟的自然法,也不过是先贤提炼的社会理性,并把它附会为对自然理性的领悟罢了,在洛克们那里,它甚至无须借助上帝权威也可成立,其逻辑是:人民的自然权利是在自然状态中与生俱来的,它早于国家权力的产生。既然它并非统治者恩赐,统治者当然无权把它从人民身上夺走。对此格劳修斯认为,即使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假设,“从自然人及其社会需求考虑,推导出这些原则也是合理的。”[注][美]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自由的崛起》,王怡等译,第33页。因为,价值理想的有效性并不在于它的真实性,而在于它的合理性。正义的理想就是如此,即使上帝的正义是虚拟的,它也能借助传统的力量起到鞭挞强权正义推进人民正义的作用。
透过这种虚实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到君主与那些“铁肩担道义”的先贤在双方的博弈中存在着各自的理论困境与实践困境。在阶级统治的历史条件下,统治者与人民总是处在利益对立的状态之中,君主尽管手握国家重器,但他既不敢对先贤们那些国家必须为民造福的政治主张作出公然的驳斥,也无法创立一套能绕开民心民意、论证自身利益的政治理论,结果“爱民”的说词总是成为官方的标准论述,而“徇君”逻辑不得不处于只做不说的隐秘状态,这使君主始终无法摆脱理论的困境。但另一方面,先贤们纵然能以上帝的名义“代民立言”,这使他们拥有统治者所没有的软实力,但在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和阶级基础尚不具备的情况下,面对国家这个强大的“利维坦”,他们也无法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落到实处,这又成了先贤们无法摆脱的实践困境。更重要的是,在唯心史观盛行的时代,由于先贤们并未看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91页。,而是企图在对“永恒正义”的追寻中找到他们心中的理想政治,当然也就无法突破他们的历史局限,但必须承认他们的理想追求仍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纵观历史长河,人类文明的发展就是一个在理想的感召下不断批判现实改造现实的历程,权力伦理的演进也是如此。虽说自从阶级产生以来政治权力就是维持阶级统治的工具,但先贤们仍借助应然的人民正义批判实然的“权力正义”,并呈现出不断超越自身的辩证否定:“轴心期”希腊精神的觉醒和哲人对国家政治的伦理诉求就是第一次超越;而基督教建立后又用天国的上帝主权论抑制了人间的君主主权论,以统一的精神秩序超越了希腊个体性的自发探索;近代之初思想家又以世俗化的权力伦理超越了中世纪神学化的政治伦理,完成了权力制衡的理论建设;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制度性建设再超越了启蒙思想家所憧憬的政治理想……由于辩证否定是一种联接新旧环节并包含肯定因素的否定,因此上述诸多环节的演进也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权力伦理的真正实现需要三条件:一是人民主权的理论建设;二是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三是权力基础的根本改造。从古典时代到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先贤们虽然完成了权力伦理的理论建设和权力制约的制度安排,但作为权力基础的私有制这个根本问题并未被触动。马克思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43页。而在马克思看来,所有制问题才是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因为政治权力是建立在所有制基础上的。他说:“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70、171页。在这两种权力都控制在少数人手中的社会结构下,纵然会有一些个人命运的沉浮,但作为资产者或无产者的“整个阶级”的命运并不会改变,国家作为“理想的总资本家”(恩格斯语)的性质也不会改变。因此,只要这个社会制度坚持私有财产神圣,那么社会大多数人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放,实现公共利益、增进全民福祉这个国家目的及其权力伦理便不可能真正实现。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桎梏;但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就要彻底否定其国家本质和权力结构。其实,权力伦理有技术性改进与系统性再造之分:在封建的中世纪,先贤们建构的否定专制王权的权力伦理属系统性再造;但自从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来,权力伦理就停滞在技术性改进的层面。然而,即使奴隶制封建制消亡了,国家的阶级性改变了吗?没有!资产阶级在解放了教会的精神束缚和封建的政治束缚之后,有继续推进经济解放和人的解放吗?没有!只是在形式民主的包装下,阶级统治并不是直接通过剥削阶级世袭政治权力来实现的,它也不会公开宣传“权为钱所用”的拜金政治,而是通过维护私有制来确保对富人有利的制度结构,以事实的不公平来消解虚幻的平等原则。时至今日,西方的两极分化还在扩大,几年前美国发生“占领华尔街”的抗议运动已暴露了99%与1%的对立。就算有社会福利和再分配,但它最多只是弥补性正义,决不是制度性正义。因此,“权力伦理之问”在私有制社会里几乎是无解的。更要注意的是,资本主义为了美化自己的正当性,还把自己的模式说成是“历史的终结”,企图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信神的奴役制。马克思早就指出:“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8页。这就揭示了社会革命的整体性和基础改造的必要性。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地却吸收了二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注]《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99页。并由此实现了历史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不但是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也有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这正是社会主义权力伦理的制度保障。中国政府已向全世界庄严宣布:“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中央为此提出以“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新型权力伦理。进入新时代后,习总书记在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基础上,还加强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制度建设,使“谁之权力?何种合理性”的权力伦理之问在中国有了最好的阐释与实践。因此,只要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继往开来,就一定能使权力伦理真正实现时代的升华。
“WhosePower?WhatKindofRationality?”——The Eternal Question of Power Ethics and the Historical Origin of Marxist View of Power
ZHAO Wei
Abstract: Whose power and what kind of rationality are the eternal ques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in all times and all countries, and also the core issue of power ethics. Since Ancient Greece, the sages have searched for the question of power ethics about “whose power and what kind of rationality” with the forms of faith, the transcendental perspectives and the power of speculation to construct a framework of power ethics in which the ultimate value was thought as the basis of metaphysics, the political ethics and law were thought as the implement of physics, and the interests of people were thought as the basic orientation, so as to express the character of justice, to declare the purpose of the country, to trace the source of power, to demonstrate the rights of the people, and to reveal the logic of the people’s justice. Although the process of solving this eternal question contains several historical transcendence from the middle ages in ancient Greece to the modern times, it has formed the traditional resource of constructing Marxist view of power. But from a realistic point of ciew, so far the countries of the exploiting class have not transformed the logic of the power into the historical reality. Only the Marxist view of power that “power is endowed by the people and used by the people” can truly realize the transcendence of history and the sublimation of the times.
Keywords: power ethics; transcendent; justice; the Marxist view of power
作者简介:赵威,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西政治思想与正义理论比较(E-mail:lotus1975@hqu.edu.cn;福建 泉州 362021)。
中图分类号:D09;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398(2019)01-0005-10
收稿日期:2018-12-06
【责任编辑龚桂明】
标签:权力论文; 伦理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论文; 国家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