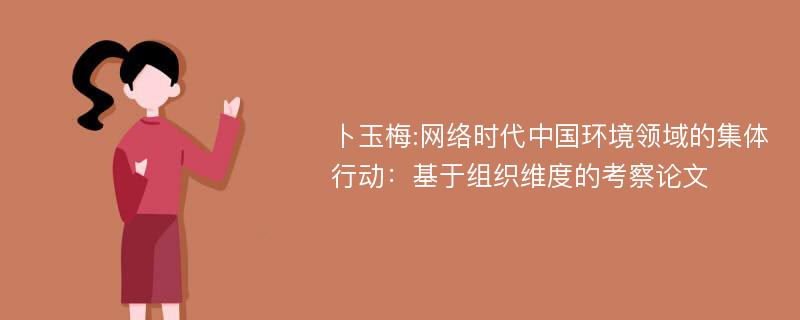
[摘 要]通过对3个抵制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集体抗争行动过程的描述发现,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是从启动社交媒体平台开始的,但随着集体行动的延续,创建组织成为行动者的期望并进而发展成为行动尝试和实践,而在创立组织受阻后又转向倚赖社交媒体。案例比较表明,组织和社交媒体在不同环境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动员过程中占据着不同的地位,由此构筑起网络时代环境集体行动的3种类型: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自组织集体行动和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不同集体行动类型的生成,是社会政治因素、网络技术因素与行动者主体因素多重制约的结果。3种集体行动类型也可以用于中国其他领域集体行动类型的概括。总体而言,在集体行动中,社交媒体虽然具有实现行动决策和资源动员的可能,但从行动者的选择逻辑和基于社交媒体的行动网络存在的限度来看,组织的意义并未被消解,传统的组织也并没有完全被社交媒体所取代。
[关键词]网络时代;环境抗争;环境集体行动;集体行动动员
一、 问题的提出
鉴于中国的社会政治情境中,集体行动/社会运动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和安全性困境[1],“组织”一度成为一个极其复杂而深邃的议题:一方面,组织可以为集体行动的动员和发展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因组织对社会秩序可能造成的威胁,组织的创立往往会授人以柄甚至受到压制。这种矛盾也导致了学术研究对集体行动是否有组织以及组织化程度的观察和讨论并在农村研究中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取向:其一,在“以法抗争”的解释框架下,认为底层民众的抗争具有了明显的组织性,是一种“有组织抗争”[2];其二,在“草根动员”的解释范式下,认为底层民众虽然在进行动员时表现出精心组织的面向,但依然呈现出一种“弱组织”状态[1]。对于城市的社会运动,一贯得到认同的是,“那些具有相应组织化行动能力的知识分子、中产阶层,在今天的中国城市,亦缺乏以正式的、组织化的政治活动来变革制度的政治/法律空间”[3]。因此,一个初步的观察是,虽然组织化行动在集体行动/社会运动中依然若隐若现,但是,去组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成为行动者的主动选择。并且,这样一种去组织化的集体行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网络虚拟串联和网络传播实现的[4]。
随着城市信息网络建设和应用的不断加强,互联网正深入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小区业主论坛、QQ群为代表的社区媒体得到了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因环境污染及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等问题引发的抗争呈现日渐增多的趋势,在这些环境抗争事件中经常可以看到,行动者通过社交媒体进行集体行动动员。结合集体行动/社会运动面临的“组织”困境来考虑,在网络时代,集体行动自然会对新兴、便捷的社交媒体加以运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行动者对社交媒体的应用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同时,在组织化行动的政治/法律空间有限的情境下,行动者对传统组织形式,尤其是组织本身的取舍逻辑如何?换言之,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技术环境中,行动者究竟是会创建传统意义上的组织,还是会选择倚赖社交媒体?在此基础上,如何勾画出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综合图景?本文力图通过翔实的案例比较研究,对上述问题予以回答。
二、 文献回顾:社会运动中的组织与社交媒体
从学术源流来看,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应置于社会运动的脉络中予以探讨。从理论视角来看,由于面临同样的问题或困境,对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动员,在社会运动的资源动员理论框架下予以审视更为恰切。因此,下文将从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的相关研究中,寻找审视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有益资源。
以上这四点都属于经营要素,如果做不到,企业还是经营不好。管理的核心就是把这些经营要素管住,使这些要素不断地积累放大,并且围绕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做业务要配置人,人是核心资源,通过管理把人的价值越大,业务就会得到更大的扩张。招聘来的人一开始可能是不达标的,他的能力如何在做业务的过程里得到提升和成长,并且变得更好,这离不开管理。再如,技术是关键资源,如何通过管理把技术积累得更强,更能满足业务的需要;还有业务过程,随着业务环境的变化,规模的增长,人员结构的调整,业务过程如何更新和积累更多的经验,如何调整适应环境的变化,是需要管理的。
网络技术和网络社会带来了社会运动组织层面的策略变化[5]。从结构上看,在社会运动中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式,从小规模的非正式地方团体到国家层次的有正规会员资格的组织,再到分权或集权的跨国组织以及世界范围的但却松散联结的网络[6],其中,组织和社交媒体是两大核心组织力量。在这种形势下,对于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的探索和拷问以及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体对传统的组织(形式)造成了怎样的冲击等问题构成了网络时代社会运动研究的重要议题。统观目前学界的研究文献,可以概括出3种主要的判断和研究取向。
1. 社交媒体作为组织的工具
这一取向的研究大多关注社会运动对社交媒体的使用及使用形式。例如,在各种社会运动中,绿色和平组织、地球之友等组织利用邮件列表、论坛、网站等网络技术所提供的方式传递信息,促进内部沟通和联络,并借此与其他团体进行沟通[7]。一些正式的政治组织也发现日益完善、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可以帮助他们降低开展动员和协调所耗费的资源成本[8]。但是,使用社交媒体技术可能会影响组织的内部结构,包括权力结构,改变组织自上而下的沟通方式[9]。也有学者认为,社会媒体的使用并没有改变组织活动的根本原则,但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即当组织愿意降低对集体身份/认同保持一致的要求,从而接受参与者之间建立更为个人化的社交网络时,可以改变组织的“游戏规则”[6]。总体而言,这一取向的研究倾向于将社交媒体视为社会运动所需的传统组织的工具,但仅仅是作为组织所使用的各种媒介中的一种,被整合到传统的组织实践中。
2. 社交媒体对组织的消解
社交媒体既能被庞大的、强有力的组织所运用,也能被有着广泛地理延伸的非正式网络所运用,后者则展现了在传统组织和资源累积缺失的情况下,人们利用网络技术实现社会运动基本功能的能力。然而,互联网能够实现快速传播、即时聚合、突破信息封锁以及提供实时现场信息,加速扩散,这与传统意义上作为社会运动中枢的组织所能发挥的功能相去甚远。也因此,这种新兴的组织形式被认为可以取代传统的组织和组织形式,形成对社会运动所需要的组织的意义的削弱甚至消解。
这种削弱与消解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领袖不再成为必要。少数积极分子可以通过互联网而组织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形成一种新的组织模式[10]。维基社区的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产生了一种“无领袖”组织模式,并因此挑战了寡头政治观点[11]。但也有学者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寡头政治的消失,而是产生一种新形式的寡头——“理念”寡头(“ideational”oligarchy),包括已有的领袖以及那些掌握着广泛传播方式和技术的人,他们会阻碍那些试图取代他们角色的团体和个体[12]。二是改变了传统的、垂直的和科层化的组织在社会运动中的位置和作用。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很难再被观察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运动几乎没有传统的正式组织的参与,缺乏成员名单、章程、主席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社会运动的非正式、碎片化甚至是无组织的特征会越来越普遍。并且,正式的组织失去了成员,组织关系正被大规模、流动性的社交网络取代[6]。对此,有学者认为,并非数字媒体行动正在取代正式组织,而是它也能够实现正式组织的协调功能。威尔士提出,许多年轻人在政治运动中转向使用非垂直的、个人化的数字媒体,是因为他们本身漠视和拒绝传统的、制度化形式的政治和组织。因此,行动方式并不是技术的产物,而实际上是参与者心态的产物[13]。
11月9日,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发布公告称,受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浙江销售分公司委托,交易中心自11月起通过官方网站对外公开发布中国海油浙江LNG接收站出站基准价格,该价格将作为中海石油气电集团浙江销售分公司LNG线上交易及合同执行基准。
3. 社交媒体与组织互为补充
社交媒体在短时期内产生的巨大效应让人们的乐观心理展露无遗,同时,也引发了一些学者的慎思甚至悲观,这可以通过3种相互联系的观点体现出来:其一,网络动员和参与形式被认为是对人们参与心理的浅层满足[14]。参与在线行动会让行动者“感觉良好”,以致没有意向再转化为现实世界中的行动。因此,对网络组织和行动所做的宣传不仅言过其实,甚至它还会成为现实行动的阻碍,滋生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15]。其二,基于互联网而建立的联系是一种弱关系,水平而非垂直的结构使其很难导向高风险的行动,而只适用于低风险的情况[16]。由于缺乏传统组织的激励机制和决策机制,一些网络团体在建立之后就陷入了“等待戈多”的境地,因为他们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其三,在线网络是与制度政治分离的,这意味着行动者难以将其影响力施加于制度[17]。例如,“占领华尔街”运动虽然拒绝正式领导和政策,却是以其声音不被正式权力倾听,并丧失接触正式权力的渠道为代价的[13]。概言之,网络组织形式难以带来重要的社会变迁或变革,甚至难以实现小范围的社会改良,而只能产生浅层奉献[15]190。因此,传统的组织(形式)被认为依然不可或缺。
赵鼎新指出,“大多数社会运动,特别是那些大规模社会运动的动员离不开传统意义上的组织、社会网络和空间环境,而互联网在这样的动员中所起的可能只是一个辅助作用”[18]。琼斯针对左翼组织的研究发现,社会媒体可以成为传统左翼组织的有益补充,但它的作用不应被夸大,更不能盲目、武断地相信或宣称它可以取代后者,而应该思考它在巩固和重建组织方面可以发挥何种作用[19]。卡普也指出,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何种组织形式在复杂的政治社会情境和技术环境中具有更好的适应性。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是了解事件是如何成功地将网络媒体所产生的创造力和能量,与只能在组织中找到的战略能力相结合,或者说传统组织形式与原子化、创造性的表达是如何联系到一起的[13]。
班尼特等学者的新近研究所做的正是这方面的努力,他们首先区分了建立在互联网上共享的个人化内容基础上的“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的逻辑与我们熟悉的高度组织化的、形成集体身份/认同的“集体性行动”(collective action)的逻辑。在区分两种行动逻辑的基础上,班尼特等提出了大规模行动网络的3种理想化类型,分别是自组织网络(self organizing networks)、组织驱动型网络(organizationally enabled networks)和组织代理型网络(organizationally brokered networks)。其中,自组织网络和组织驱动型网络属于连结性行动,在自组织网络中,很少或无组织协调行动,社会运动避免现有的正式组织的介入;在组织驱动型网络中,松散的组织存在于松散的相互连接的网络中,协调行动;组织代理型网络为传统的社会运动,强大的组织运用社交技术来组织参与和协调目标及行动[6]。
那么,置于国际学术的脉络里,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又该包括哪些类型?基于已有研究的启发,下文将以现实的案例为基础进行阐发。
三、 案例选择
本文选取B市和G市3个抵制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集体抗争行动案例进行比较分析(见表1)。案例的择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案例爆发时间的序列特征及其与网络技术环境的关联性。3个案例分别于2006年、2009年和2011年启动社会运动,并分别于2011年、2009年和2012年结束。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的环境类集体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互联网技术不断推陈出新,并开始影响运动的特点与走向[20]。第二,行动的持续性。持续性是网络动员的关键[15]。3个案例的持续时间都长达3个月以上,理论上会将互联网快速聚集人群的优势削弱[21],并对组织形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三,3个案例发生的地点L区、P区和X区均为城市商品住宅区,网络全覆盖,居民普遍受过良好教育,属于城市中等阶层,在权利意识和行动力方面具有一致性,这为发现其共同的行动和组织逻辑奠定了基础。第四,L区和X区同属B市,P区隶属G市,分别为同城比较和城市间比较提供了条件。第五,3个案例的结果最终皆如业主所愿,即政府宣布缓建、迁址或弃建。由此,对组织形式与行动结果之间关联进行讨论的意义让步于对组织方式和过程本身的探讨。
本研究的案例资料部分来自媒体信息,包括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部分来自笔者的在线参与观察与线下访谈[注]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对所涉核心案例的地名和人物等信息做了匿名处理,本文承诺,所使用的网名仅用作学术目的。。媒体报道与参与观察的相互补充和印证,为尽可能地还原和揭示组织发展的过程和意义提供了可能。
表1 3个案例概况
L2006.08—2011.01BLZHF、BWM—P2009.09—2009.12GPLJ、HLW、BGY— X2011.11—2012.06BXLXX、LX、BY
四、 集体行动的“组织”选择路径
在3个抵制垃圾处理设施选址的集体抗争行动案例中,行动者究竟是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进行集体行动动员的?面对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行动者对待创建组织是何种态度?又有哪些具体的实践?社交媒体和组织是如何动态地贯穿于整个集体抗争动员过程中的?
1. 启动社交媒体的迅疾
(5)行动者的网络技术实践
⑨由于风浪影响或水位测量误差可能造成水闸上下游水位偏差,为防引排倒流,设定上游水位比下游水位高0.01 m以内时,闸门一次性关到底(不分级关闸)。
案例P来自HLW小区、BGY小区和LJ小区进行的抵制垃圾焚烧厂行动。垃圾厂选址的信息爆出后,2009年10月12日,“kingbird”建立了专门反对垃圾焚烧的QQ群,起名“垃圾讨论关注”,很快200个名额就被加满;10月16日,“JWJ论坛”首页开辟“垃圾焚烧专版”,大量网民点击和发帖;从10月16日起,论坛正式成为反对垃圾焚烧事件中居民意见表达的平台。为了让政府倾听社区居民的呼声,他们积极运用社区论坛、QQ和微博等平台展开组织和动员,也正是在这些网络空间里,造就了“樱桃白”“阿加西”与“巴索风云”等“风云人物”。
案例X的故事主要由LXX小区、LX小区和BY小区居民构建。2011年11月3日,LXX小区业主论坛上的一条有关垃圾站选址的消息被置顶,“大家组织一下吧”的号召引来了众多跟帖,拉开了X区业主抵制垃圾站的序幕,“建五”是论坛的主要管理员。而后,专门讨论垃圾站议题的“反垃圾QQ群”很快建立,“新硅谷C4-Dream许”是核心管理员。11月11日,小区专业IT人员“FW”制作的用于投票和发布信息的youmyth网站启用,“FW”运作这一网站。
一是强化部门主体责任,精简审批事项和流程。财政部门不再直接参与主管部门发布项目申报指南(通知)、组织项目申报、评审论证、遴选立项、制定资金分配方案、制定“任务清单”或明细计划、组织项目实施、项目考评或验收、资金和项目公示等具体事务,主管部门独立负责。精简优化联合发文、会签、审批等环节。基建项目进度款从财政部门审核改为主管部门审核、省财政部门事后抽查,提高行政效能。
2. 创设组织的尝试
在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很快就有不少业主不再满足于这些社交媒体。案例L中,2006年11月6日,“kaku妈妈”提出,“迫切需要一个组织,加强宣传,群策群力”;12月21日,“bfc99”发帖号召在ZHF小区会所召开关于垃圾场问题的行动交流会,重点讨论成立行动筹备组,以分工负责的方式实施下一步行动;12月24日,“LYZHAO”连夜草拟了“第一阶段活动方案(草案)”,详细规定组织的特别要求、领导机构构成和职能分工。领导机构全称为“行政投诉和行政诉讼活动领导机构指挥中心”,或简称“行动筹备组”,由财务小组、宣传小组、法律小组、推进小组共同组成(见表2)。“第一阶段活动方案(草案)”还规定,各小组“统一接受指挥中心负责人的领导,通过集体决策共同确定活动方案”,“各小组分别由专人负责,对所负责工作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及时沟通,以确保目标的达成”。
与此同时,BWM小区成立业主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为业委会的成立作相关准备。进而,“为了发挥集体的力量和智慧,同时,也为了兼顾效率”,筹备委员会吸收ZHF小区居民,扩大规模成立维权核心小组。2007年1月8日,维权核心小组名单公布(包含网名、邮箱地址和所属小区3个方面的信息),初期共包含15位业主,其中7位为ZHF小区业主,8位是BWM小区业主。在特定的准入资格基础上,还规定了“该小组成员不是一成不变的,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增减”。1月14日,维权核心小组综合居民的意见和建议,确定了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涉及宣传工作、向政府部门递送材料以及招募写作人员和环保、法律等方面的专业人员等事宜。
表2 案例L行动筹备组职能分工
、、;、;;,,,、,,、,,
案例X中,2011年11月5日,“新硅谷C4-Dream许”即向反垃圾QQ群友发布了“临时委员会建立流程草案”,表示“为了确保最终目标行之有效,各小区管理员一致同意建立行之有效的组织”。“临时委员会建立流程草案”规定,“群主确保周边大部分社区业主加入相应社区群后,由群内业主自愿加入业主临时委员会(为使之更有效率,每小区限2人),此业主临时委员会为核心组织,各区/业主必须服从临时委员会统一协调,统一行动”。“临时委员会建立流程草案”还明确了加入临时委员会的步骤和条件等(见表3)。然而,临时委员会一直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基于以往集体收房事件所创建的LXX小区业主自助委员会得以在其中发挥些许作用。此外,LX小区和BY小区业委会在组织业主签字和填表方面取得不错的效果,促动LXX小区业委会的成立。
表3 案例X临时委员会相关条款
1. 2. 3. (/,)4. 5. ,6. ,,2/31. ,,,2. 、、、、、3. 4,4. ,,5. 18,,,
如此,创立了组织的,予以隐匿。① 不以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名称发号施令。在案例L和案例X中,我们分别都能看到业主以实体组织的名义进行动员的经历,如X区业主以业主自助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散步”的公开信,P区业主以行动小组的名义提出“发起一次合法的社会运动”的倡议以及募集资金和招募志愿者等。在意识到行动的危险性之后,这些组织从此在集体动员的文本中销声匿迹,并转化为非公开活动。② 对外宣称“无组织”。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不以组织名义与政府部门接触或谈判,二是对社会、媒体宣称“无组织”。
生活中,学习中,到处布满荆棘,常常听到很多人在感叹生活或学习中的苦闷。大自然尚且阴晴变化,何况是人呢?所以,当你被失败和挫折的阴影笼罩时,不妨点亮心烛。
由此可见,一方面,在3个案例中,行动者都未把网络平台当作真正意义上的“组织”;另一方面,创设一个能够整合力量的实体组织,曾成为各区行动者的期望和愿景。但结果正如我们所见,一个成功创建了组织,一个试图成立组织但遭遇挫折而夭折,而另一个不曾付诸实践。
3. 隐弃组织的理性
当行动进行到一定阶段时,参与者越发意识到组织的成立可能会使其“合法”的行动转变性质。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社会运动没有任何组织的存在,反而可以为其行动的合法性添加筹码,甚至因此获得更多外在力量的同情和支持。由此,隐弃组织成为行动者的不二选择,其希冀达到的,就是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即他们不需要组织,他们也不曾创立任何组织,以此构建起自我保护的重要机制。
(3)线上学习。学生使用泛雅学习平台,学习教师提前上传的消费税征税范围、税目、税率和应纳税额计算的视频、智能习题、“连连看”游戏等线上学习内容。本教学站的学生对所学知识有自己的控制权,听不懂的部分可以重复学习;若吸收能力比较强,也可以提前进行到下一环节的学习,不用再等其他学生。学生通过智能习题进行练习,如果答错了,可以立刻得到正确答案。而参与“连连看”游戏可以有助于学生对学所知识的深化理解和熟练掌握。
P区业主并非如L区和X区业主一样,表现出创建实体组织的迫切。然而在P区的集体行动发起一个月后,有业主指出了其中存在的弊病:“更多时候是各自为战,严重缺乏组织力量,很多资源、意见、力量都无法很好地整合”。“Kingbird”更是明确表达了对组织起来的期望,“很多业主想为焚烧厂的事情出力,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会议组织”。
意图创立组织的,予以彻底放弃。X区业主虽然为临时委员会的成立做了很多筹备工作,但仍然选择放弃。P区业主未进行组织构建的尝试,直到“无组织,有理性!”的口号成为一种光环,其权变所带来的效应也得到了验证。
(1)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
无论是否创设组织,行动者都表现出对领导者予以保护的审慎。一方面,虽然在遇到问题和遭到利益侵害时,普通业主很自然地流露出“还是要有人出头”“希望有人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的”的愿望,一些普通业主甚至会不自觉地暴露组织者的存在,发出“还是希望我们的组织者和他们沟通”的信号;另一方面,行动者在各种场合所强调的“没有组织者”、没有“领头羊”、只有“志愿者”以及对特定活动所作的“特别说明”,又将一种小心谨慎且着意保护的心理展露无遗,这种无意识地暴露和有意识地掩护的矛盾心理,不时流露出来。
4. 凸显社交媒体的刻意
与之并行不悖的,是互联网及社交媒体的作用被凸显甚至放大。无论是创立了组织的社会运动,还是没有任何组织的社会运动,所有行动者的代号都是具有个性特色的网名。在面对媒体回顾事件时,“感谢网络!”这样的语词不时地从P区业主的口中冒出。的确,案例P完全依托社交媒体进行动员:从反建议题的问题化、诉求的调整到运动框架的构建以及线下行动的协调、召集,都是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商讨,在征集网民意见的基础上再做出决策的,如晒车大会、车贴行动的发起,都是在业主论坛发布信息、讨论和决策。2009年11月23日上千名业主及村民的“散步”活动,也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动员实现的快速聚集。
X区业主同样依托业主论坛和业主QQ群进行协商和动员,不同的是,反垃圾QQ群和自制抗议网站的运用(尤其是后者),将社会运动的网络技术应用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创的抗议网站上的在线投票数达上百次;二次环评公示期间的8 000余份环评意见书,就是在各网络平台上的大规模宣传,辅助线下的“扫楼”动员下完成的,以致最终取得的成功被谑称为“码农的胜利”。无论是“感谢网络!”还是“码农的胜利”,都是互联网作用的彰显。
而在案例L中,业主论坛虽然自始至终承载着信息发布的作用,但很多时候,组织者只是将网络平台视为一种信息发布和动员的工具加以有意无意地利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表现出对这种组织形式作用的凸显。这种刻意,又像是某种“障眼法”,对组织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掩护。
5. 倚赖社交媒体的限度
然而,互联网并非总是能令人满意。3个案例中初期创立传统组织的意愿表达,侧面反映了行动者们对网络组织方式的质疑。成立组织受挫后,随着行动的持续,这一问题更加凸现。要达成目标并非一朝一夕的事,如何使社会运动维续下去以达成目标成为问题的关键,也成为各组织方式所面临的挑战。如此,即使完全依托网络平台进行动员的案例P,也在必要的时候采用了线下会议等传统的组织动员方式加强效果,“206会议”的多次召集便是例证。但是,就案例P而言,人们的行动热情是被一步步激发出来的,在酝酿了数月之后,于2009年11月23日启动大规模社会运动,由此得到了政府“暂缓项目选址和建设工作”的回应。社会运动也在业主热情最高涨的阶段得以告一段落,这也便无需再对参与者和组织者提出更多更高的要求。
在案例L中,运动“战线”很长,持续了数年时间,但在最初阶段,只是通过行政复议或上访等行动表达诉求,一直维持着不温不火的集体活动,在一年以后汇聚为一场愤慨情绪的大爆发并生成千人抗议行动,而后续的行动又持续了数年。而案例X中,社会运动动员启动数日后,就在“散步”行动中达到了高峰,随后的延续性行动,都是小范围的群聚和琐碎事务的处理工作,而这样的阶段又持续了数月。与案例L相似的是,案例X公开的社会运动虽然引起了政府和社会、媒体的关注,但并没有马上获得相关方面的确切回应。
由此可见,对组织和行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的是案例L和案例X。不同的是,案例L中,有传统组织的运作和策划,从整个运动历程来看,有条不紊的社会运动在组织的策划下得以继续,尽管参与者是以特定的少部分人为主。因此,问题的焦点在于,主要依托网络平台进行动员的X区业主在行动维持阶段的表现如何。实际情况是,在案例X中后期阶段,业主论坛和QQ群里的“牢骚”甚至“不满”,给依然火热的网上讨论氛围泼了一些冷水,尤其是意见领袖“白猫”多次表现出的对参与状况的失望和无奈,暴露出了依托互联网进行动员的限度,即对浅层行动的有效性而对深层行动的乏力[22]。
五、 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类型及影响因素
基于以上陈述,我们对组织和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表现已有了初步的印象。那么,组织和社交媒体分别在各案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或者说,两者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并促使集体行动得以向前发展的?进一步而言,根据不同的组合,如何区分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类型?对不同类型进行判定的依据是什么?受哪些因素的影响?以下将尝试对这些相互关联的问题予以回答。
1. 组织与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定位及环境领域集体行动的类型
各案例所运用的“组织”及社交媒体类型见表4,其中,行动筹备组具有章程和明确的分工,对资金来源有明确的规定和管理方法,并曾以组织的名称来发号施令。核心小组虽然不具有正式的章程,但有确定的准入资格,成员相对固定。业主自助委员会与核心小组类似。这些组织因其临时性特征且都是在制度外自发成立的草根组织,因此,难以获得正式制度的认可或批准,皆属于非正式组织,与能够获得制度认可的业主委员会相对应,后者也是业主维权的唯一合法组织[23]。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文的案例中,业委会的实际作用并不突出:已成立业委会的小区,业委会处于缺位的状态;未成立业委会的小区,在环境运动大潮的推动下,积极筹建,但行动结束后才初具形态[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成立业委会本身并非易事,而成立后的业委会也很容易失去独立性,以至于限制其在集体抗争中作用的发挥。可参见:徐琴.转型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对城市业主维权困境的解读[J].学海,2007(2):123-128.。并且,在3个案例中,集体行动的组织和动员,都是由积极分子组建的“领导团体”来引领。
表4 环境领域集体行动中的“组织”和社交媒体
LPX、—、ZHF、BWM,QQJWJ,QQyoumyth、QQ,QQ,LXX“bfc99”“”“”“”“”“”“kingbird”“”“”、、、“”“C4-Dream” “”“FW”
在集体行动中,一方面,要生成行动决策和计划,这涉及决策过程;另一方面,信息要得以传递和扩散,这涉及动员过程。从3个案例的组织选择路径和组织形式应用来看,动员或信息传递所倚赖的主要都是社交媒体,但在决策方面,在不同的案例对组织和社交媒体的倚重并不一致。基于此,可以初步发现3种不同的结合,并确立3种不同的组织模式(见表5)。
BOG压缩液化实验装置主要包括10 m3储罐、2 m3储罐、压缩机、压力传感器、温度传感器,流量计等。具体连接如图3所示。
这种集体行动以案例L为参照。在案例L中,行动的决策主要由行动筹备组和核心小组做出,随后,组织成员再将活动相关信息、意见和建议在业主论坛或QQ群上以“通报”的形式向小区居民传播。根据笔者统计,业主论坛上以“通报”为题发布的信息逾20条。“通报”所折射的,一方面是业已生成的决策,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参与者线下活动状况的再现,进行进一步动员,因此,从决策的角度而言,组织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而社交媒体只是组织成员间相互联络和传递信息的工具。从动员和信息传递的角度而言,社交媒体发挥着主导作用,但这显然得益于组织的幕后操作,因此,由于组织的幕后运作及其对全局的掌控作用,组织驱动着集体行动向前发展,社交媒体则更多呈现为组织的工具,成为一种补充或延伸。
(2)自组织型集体行动
这种集体行动以案例P为参照。P区业主并未成立任何传统形式的组织,并主动避免组织的介入,组织的缺失,使其完全依托社交媒体维持集体行动。在社区论坛和QQ群上,参与者经由表达、协商和辩论等方式,形成集中意见,以引导和协调行动。针对具体的行动实施,参与者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号召、动员。尽管如此,社交媒体在协调行动中的作用不应该被无限度夸大。从案例过程中可见,在特定情况下,面对面的会议或互动依然很重要(如“206会议”“1220会议”的召开)。总体而言,在这一模式中,社交媒体基本上完成了原本需要组织进行的行动联络、协调和动员等事务,在一定程度上替代甚至超越了组织的功能。由于不存在任何组织的指令,整个行动系统在积极分子的引导下,协调地、自动地形成了有序的、相对民主的动员和决策模式,可以概括为自组织型集体行动。
(1)对“有组织”的政治认知的强化
这种集体行动以案例X为参照。在案例X中,经过精心筹备的临时委员会未能成立,但业主自助委员会一直存在,并在特定的时候发挥其作用。然而与案例L不同,案例X业主自助委员会在“散步”行动后便在公开文本中销声匿迹,转为隐性存在,后续的行动主要由各社交媒体的管理员或意见领袖主导意见协商,形成决策和计划,并依托社交网络进行信息传递而产生社会动员的力量。因此,除了“散步”行动是经由组织依托互联网进行动员之外,其他行动都是倚赖社交媒体而得以开展。而隐性存在的组织(业主自助委员会),在网络信息传递和动员的基础上,对网络动员进行进一步强化,并在必要的时候展开线下二次动员,动员亲友、邻里网络[22],实现对社交媒体动员效果的加强。社交媒体无论是在决策还是信息扩散、传递过程中都居于主导地位,组织则对之予以辅助。由于社交媒体不仅推动着集体行动向前发展,也对隐性存在的组织具有鞭策和联合的作用,因故归为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
国际数学教育大会(ICME)是代表数学教育界最高水平的学术会议,也是世界各国数学教育最新进展和成果的展示、交流平台,迄今为止已召开了13届.经过中国数学教育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华东师范大学获得2020年ICME-14的举办权,这是国际数学教育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以此为契机,西南大学将承办ICME-14少数民族数学教育卫星会议,旨在让世界各国研究者相互交流本国民族数学教育问题,分享民族数学教育中的特色、经验,探讨民族数学教育发展的路径,目前会议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中.
表5 组织与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定位及类型划分
LPX
2. 不同类型集体行动生成的影响因素
至于为什么会生成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笔者认为,有5个方面的因素(见表6)。
(3)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
2005年以来,国内爆发了一系列、大规模的与环境议题相关的环境抗争或运动,并以2007年厦门PX事件为转折点,进入凸显期,引起了国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国家既要在社会力量的博弈中平衡利益格局,也要维持大局稳定;另一方面,涉及组织,政府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分类控制策略,对具有现实挑战能力的组织,实行禁止[24],使得组织合法性成为一个问题。
在这种情境之下,对于行动者而言,他们也会意识到“有组织”存在风险及必须“踩线不越线”[1]。这种对体制运作规则的基本认知和行动共识主要来源于行动者的生活经历和维权历练[25],此外,便是来自于其他环境运动的扩散及对其进行的模仿。作为环境运动的标志性事件,厦门PX事件开启了城市居民和平、理性维权的序幕,也以其借助短信、互联网等新技术力量推动运动,影响地方政府公共决策的特征而广为传播[20]。这也意味着,环境抗争的动员在组织层面具有更多的可能,实体组织并非推动运动向前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此为节点,厦门PX事件及其后的环境抗争都会宣扬一点,也即在法律框架内开展行动并尽量避免触碰体制的敏感点,其中就包含对成立组织的谨慎和对“领头羊”的保护。因此,在2009年爆发的案例P和2011年爆发的案例X中,行动者对于组织都保持着一种极为谨慎的态度,尤其是案例P中的业主对“组织”的极为清醒和理性的认知。而在2006年爆发的案例L中,行动者创立组织的顾虑并没有那么多。在组织运作上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体现了客观的政治现实与行动者主观的认知之间的连接及其对于组织模式的影响。
(2)城市机会结构的弹性程度
现有法律规范对社会救助权要件的规定主要集中于国家义务条款之中,国家义务条款对国家给予社会救助的条件予以规定,某种程度上也划定了社会救助权的构成要件。当然,无论《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式的综合性立法,还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式的单项立法,在国家义务条款之外又设置了社会救助权的其他构成要件。通过对相关条文进行解释可以得出现有法律规范主要规定的社会救助权的两项要件。
那么,发生时间相对较晚的案例X为何依然拥有组织,并试图建立更加规范性的组织呢?由于案例X与案例L发生在同一城市,结合案例P,我们可以从城市机会结构的角度进行比较。在多层级的弹性政治结构中,中央政府有条件地给予地方政府自主权来处理环境运动,同时保留对地方政府的制约力,这既可以使绝大多数环境运动局限于地方层面,也可在可控范围内选择性地为社会诉求提供表达的出口并维持国家的合法性与稳定[26]。因此,在B市这样多层级的政府结构下,尤其是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共存,社会组织发展的机遇也比较多[27]。从最基层政府到最高政府以及各种不同类别的权力机关,存在着多重空隙,这就为L区和X区业主的组织实践创造了空间。而G市政府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所需承担的主要责任,使他们对于制度外组织的容忍度相对较低。P区行动者如若建立组织,相对而言遭遇更大阻力[注]然而,一方面,正如陈映芳所言,G市地处边陲又紧邻香港的特殊的边缘性,可能为行动者的维权运动提供相应的可能条件;另一方面,鉴于政府对草根NGO的态度是不加干预,这两者却着实为G市草根NGO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其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也得以凸显。对于环境运动而言,P区的部分积极分子在取得一定成果之后,被吸纳进NGO,推进进一步的环境保护行动,也证实了G市特殊的机会结构及其对组织培育所具有的另一种可能。参见: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J].社会学研究,2006(4): 1-20;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 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73-89.。
(3)大型集体行动的发生时间与组织成立之间的关系
行动历程尤其是高峰出现的时段,不仅会影响行动者的热情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行动的持续性,也会对组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一方面,集体行动所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制造声势,引起政府、媒体、社会的关注;另一方面,由于集体行动尚属于体制外行动,在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关注后,行动遭到遏制,未取得制度认可的组织也因此可能受到打压。一般在集体上访或大规模行动发生之后,积极分子和意见领袖都面临被瓦解的可能[28]。L区业主在成立实体组织前后,所从事的多为筹备行政复议等制度内活动,他们遵循着“踩线不越线”的行动策略,用合法和半合法手段,在向政府提供行政复议材料的同时运用有节制的群体聚集手段边缘性地触响秩序的“警铃”,直到实体组织成立半年之后,才生成了近千居民聚集于原国家环保总局门前表达抗议的大型活动。而经历过此前长时段的活动,组织的运作已经比较成熟。X区则不同,在“临时委员会建立流程草案”发布几日后,数百人聚集的“散步”活动爆发,扩大的事件影响力也给组织的成立带了压力和限制。所以,有被访者表示,是“由于时间太紧,来不及成立,而且在‘散步’事件之后,出事了,大家也就都很低调了”。(访谈材料,2012年5月25日)这也就为组织的创立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4)组织要素的实现难度
在使用移动工具学习的过程中,学生建立学习记录夹。首先选取材料,然后,将材料置入移动工具中,最后,听读。貌似简单的事情,实则需要持之以恒,做到一日一读,最终实现英语听读成绩的提升。
组织要素的实现难度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组织是否跨越多个小区。区内和跨区的不同空间范围会对组织的成立带来不同的难度。L区的行动筹备组和X区的业主自助委员会都是区内组织,成立起来相对容易。L区的核心小组和X区的临时委员会均为跨区组织,但是L区在反对垃圾填埋场时已经建立起了跨区的联系网络,而X区则不具有这样的前期基础,因此,被访者说,“相互之间还不熟悉,要凑起来太难了”。二是对组织成员的期望和要求。从表3中可见,X区临时委员会加入条件之一为“每天累计4小时以上网络在线时间”,有被访者指出,“这不太现实”。(访谈材料,2012年5月25日)可以说,这种高要求直接导致了这一组织的“半途夭折”。
公共项目选址和建设的消息大多由业主论坛散播开来。案例L主要发生在ZHF小区和BWM小区。2006年8月29日,“HOME2006”在ZHF小区业主论坛创建记录垃圾场臭味扰民的帖子,跟帖数百,点击过万;9月5日,“RENNICE”发帖称,他从中国建设招标网上,查到有关L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的招标情况,引发热议。上述两个帖子的发布激发了L区居民的情绪和权利意识,社会运动的动员序幕由此开启。ZHF小区业主论坛也从此成为信息发布和动员的重要阵地,随之,“ZHF小区—我们的家”等业主QQ群陆续建立或动员起来,“bfc99”“乾翁”等网友尤其活跃。
在案例L中,行动者对QQ群和业主论坛的应用属于基础应用,也即基于现有的技术平台加以利用;在案例P中,行动者在业主论坛中开创垃圾焚烧板块,使得信息的发布点更加集中;而在案例X中,对QQ群予以创造性运用,并利用自身技术开创抗议网站。总体而言,行动者的网络技术水平和利用互联网进行组织的能力在逐步提升,这使得行动者在创立组织受阻后,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互联网所具有的组织潜力开发上,也使得晚近发生的环境运动对互联网的倚赖更大,社交媒体的作用更突出。
表6 不同集体行动类型生成的影响因素
() “”①L()—P()——X()—①,3。
①技术应用水平的高低,仅就3 个案例之间的比较而言。
六、 结论与讨论
组织是社会行动的场域和驱动力[29]。如果说怨恨、情感是社会运动的推力,那么,组织则是社会运动的拉力[30]。对于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组织维度的探讨显得极为必要,因为依托互联网互动而形成的网络社群的崛起意味着一场组织形式、社会运作流程的革命[31]。而在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合法性问题的制约,使得行动者在创建组织的道路上如履薄冰。为了最大程度地动员资源,行动者在组织化和去组织化之间徘徊的复杂心理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组织策略的权变性,也使得组织维度复杂化。基于本文的案例比较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和判断。
第一,伴随着集体行动的扩散效应,基于行动者对“组织”政治认知的逐渐强化,行动者对“组织”的选择和应用越来越理性,显性的组织化在集体行动中越来越难以见到。
第二,在机会空间存在的情况下,作为具有勇气的行动者,他们往往也会尝试成立组织,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允许,组织依然是行动者的志愿和选择。在机会空间越大的地方,行动者越有可能成立组织。
第三,在大规模或有影响力的集体行动发生后,政治控制的介入会增加组织成立和运作的难度,隐弃组织并转而走向倚赖社交媒体来维持行动,成为行动者的策略选择。
第四,网络技术提供了集体行动决策和动员的媒介,动员活动一般都是从启动社交媒体开始,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以及行动者技术应用水平的提升,运用社交媒体进行组织的手段也越来越成熟。然而,社交媒体虽然能够实现行动者快速的聚集,但集体行动的持续性问题成为一大挑战,社交媒体的限度也随之凸显。
基于以上几点,社交媒体虽然具有替代组织的技术可能,实现组织所发挥的决策和动员功能,但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行动者组织选择的内在逻辑以及基于社交媒体的行动网络存在的限度来看,组织以及传统的组织形式并不会完全被社交媒体所取代。因此,在这种复杂的情境和行动者的理性运作之下,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具有3种不同的类型:
一是基于组织相对稳定的结构特性和决策能力,社交媒体进而沦为组织的辅助工具,社交媒体虽然对于集体行动行动动员意义重大,但这依然取决于组织的幕后操作,这便构建起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
二是基于组织的非规范性和特殊环境中的非公开或小范围活动的特性,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动员中的主导作用也随之显现出来,组织在决策中的作用不再显现,组织的动员也逐步转变为社交媒体动员的强化和延伸,由此形成媒介主导型集体行动。
此次样本分析以SPSS 19.0统计学软件处理我院诊治的75例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患者涉及的所有临床数据,对动态心电图检测与常规心电图检测冠心病无症状心肌缺血患者诊断敏感度、准确度、特异度以率(%)的形式表示,采取X2检验,对P<0.05,统计学组间数据具有分析意义。
三是在组织缺失的情况下,社交媒体的作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以致集体行动的决策和动员均通过社交媒体实现,构筑起自组织网络,进而替代甚至超越组织以满足集体行动决策和动员全程的功能性需求,以此生成自组织型集体行动。
笔者认为,从组织维度来看,上述3种类型可以覆盖网络时代中国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的所有类型,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这3种类型也可以用于中国其他领域集体行动类型的概括。这是因为:一方面,集体行动所面临的宏观的社会政治环境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集体行动动员的组织媒介无非就是创建实体组织和利用社交媒体两种。当然,组织和社交媒体并非是相互排斥的,创建了组织的集体行动必然会同时使用社交媒体协助动员。正如前文提及,实际上,在中国这样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在抗议性集体行动中,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创建组织?假如创建组织的话,组织的作用能否一如既往得到发挥?进而,社交媒体在其中是发挥主导作用还是辅助动员也取决于此。鉴于这种情形,从组织维度审视环境领域的集体行动甚至更大范围内的集体行动,具有题中应有之义。
回到班尼特等的理论可以发现,本文所叙述的集体行动中,集体身份/认同和个人化行动框架的区分并不明显,当然,这与本文所选取案例诉求目标的趋同性相关,以致环境运动在问题化和框架化以及集体身份的建构方面,具有趋同性,然而这也意味着,要区分网络时代的行动网络,应该要有其他的判断依据。本文从决策和动员两个层面来看组织和社交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并构建集体行动的类型,既为与西方的研究进行对话,也是中国本土集体行动的经验使然。一方面,自组织网络与组织驱动型网络与本文的自组织集体行动和组织驱动型集体行动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这表明在网络社会发展的全球大潮之下,中国各类抗议性集体行动也成为世界社会运动中的重要一环,它们在组织和社交媒体的运用方面具有趋同性;另一方面,组织与社交媒体的战略结合,抑或因为组织的缺位而造就的自组织模式,重塑了中国抗议性集体行动的组织化水平,彰显了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组织困境的超越。尽管如此,集体行动的组织化程度仍然较低,弱组织化仍然是主要的形式。
由于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未曾在人的终极关怀维度上使用“超越”或“超越性”等词汇,因此目前学界以超越为主题或关键词进行马克思哲学有关终极关怀和意义世界的研究,即全面发掘马克思思想中实践、自由和信仰的整体性思想的研究成果寥寥无几。这里关涉着对于文本的解读方法和研究入路的认识,“对于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有益而恰当的态度应该是注重从马克思已经说出来的东西当中读出来未曾说出来的东西。”[2]完全地拘泥于文本或全然天马行空式地自由发挥,对于研究哲学家尤其是马克思这样一位伟大的哲学巨擘而言实在是不可接受的。
2.5 不同戒烟年限组及与非吸烟组间椎体骨折阳性率比较 结果表明:戒烟<5年、5~10年、>10年组椎体骨折阳性率分别为23.1%(39/169)、19.9%(28/141)、23.1%(9/39),不同戒烟年限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经两两比较,发现仅戒烟<5年组与非吸烟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3)。
[参 考 文 献]
[1]应星.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7 (2): 1-23.
[2]于建嵘.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J].社会学研究,2004(2): 49-55.
[3]陈映芳.行动力与制度限制:都市运动中的中产阶层[J].社会学研究,2006(4): 1-20.
[4]陈晓运.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 G 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12 (2):67-75.
[5]CASTELLS M.Toward a sociology of the network society[J].Contemporary Sociology,2000,29(5):693-699.
[6]BENNETT W L,SEGERBERG A.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 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2012,15(5):739-768.
[7]DONK W VAN DE,LOADER B D,NIXON P G,et al. Cyberprotest: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s[M].London: Routledge,2004.
[8]吴强.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涨落: 新媒体政治前沿[J].国外理论动态,2015(1):65-74.
[9]WRIGHT S.Informing, communicating and ICTs in contemporary anti-capitalist movements[M]∥ DONK W VAN DE,LOADER B D,NIXON P G,et al. Cyberprotest:new media, citizens and social movements[M].London: Routledge,2004.
[10]EARL J,SCHUSSMAN A.The new site of activism: on-line organizations, movement entrepreneurs, and 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decision-making[M]∥ COY P G.Consensus decision making,Northern Ireland and indigenous movements. Amsterdam:JAI Press,2002:155-187.
[11]SHAW A,HILL B M.Laboratories of oligarchy? how the iron law extends to peer productio [J].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4,64 (2): 215-238.
[12]GRAY P W.Leaderless resistance, networked organization, and ideological hegemony[J].Terrorism and Political Violence,2013,25(5): 655-671.
[13]WELLS C.Civic identity and the question of organization in contemporary civic engagement[J]. Policy & Internet,2014,6(2): 209-216.
[14]SCHULMAN S W.The case against mass E-mails: perverse incentives and low quality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U.S. federal rulemaking[J].Policy & Internet,2009,1(1).
[15]MOROZOV E.The net delusion:the dark side of internet freedom[M].New York: Public Affairs,2012.
[16]GLADEELL M.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EB/OL].[2019-01-18]. https:∥www.docin.com/p-564139708.html.
[17]COLEMAN S,BLUMLER J G.The internet and democratic citizenship: theory,tractice and policy[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18]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263.
[19]琼尼·琼斯,陈后亮.社会媒体与社会运动[J].国外理论动态,2012(8):38-47.
[20]童志锋.互联网、社会媒体与中国民间环境运动的发展(2003—2012) [J].社会学评论,2013(4): 52-62.
[21]KAVANAUGH A,REESE D D,CARROL J M, et al. Weak ties in networked communities[J]. Information Society, 2005,21(2): 119-131.
[22]卜玉梅.从在线到离线:基于互联网的集体行动的形成及其影响因素——以反建 X 餐厨垃圾站运动为例[J].社会,2015(5):168-195.
[23]管兵.维权行动和基层民主参与:以B市商品房业主为例[J].社会,2010(5):46-74.
[24]康晓光,韩恒.分类控制: 当前中国大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5(6):73-89.
[25]施芸卿.机会空间的营造——以 B 市被拆迁居民集团行政诉讼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7(2):80-110.
[26]CAI Y S.Power structure and regime resilience: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China[J].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2008, 38(3): 411-432.
[27]管兵.城市政府结构与社会组织发育[J].社会学研究,2013(4):129-153.
[28]徐琴.转型社会的权力再分配——对城市业主维权困境的解读[J].学海,2007(2):123-128.
[29]POWELL W W,BRANDTNER C.Organizations as sites and drivers of social action[M]∥ABRUTYN S.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2016:269-291.
[30]KITTS J A.Mobilizing in black boxes:social networks and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J].Mobil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2000,5(2): 241-257.
[31]张文宏.网络社群的组织特征及其社会影响[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1(4):68-73.
[中图分类号]C912.21;C91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287(2019)03-0050-14
[收稿日期]2019-01-3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及机制研究”(16CSH016);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体语境下集体抗争的话语及组织机制研究”(20720161083)
[作者简介]卜玉梅(1983-),女,湖南衡阳人,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助理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环境社会学。
[责任编辑 章 诚]
标签:组织论文; 集体论文; 社交论文; 媒体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媒体语境下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及机制研究”(16CSH016)厦门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新媒体语境下集体抗争的话语及组织机制研究”(20720161083)论文; 厦门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