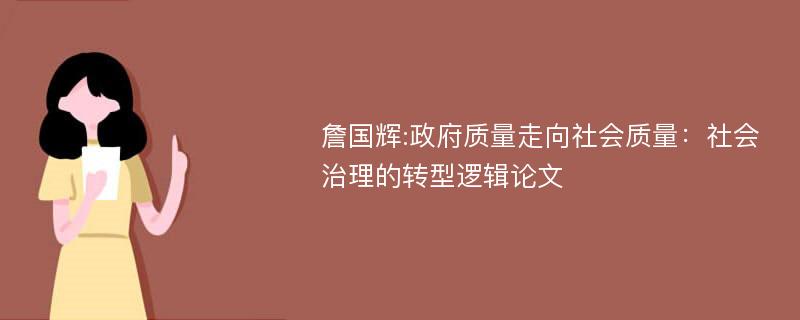
摘 要: 当下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社会治理正面临着结构性流变之风险,社会治理的转型已成为进入新时代的重要现实命题。社会治理从传统模式向新模式的转型过程所映射出的行动逻辑是从“政府质量”转向到“社会质量”。前者强调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指标的递增;而后者凸显社会福祉的提升。这一转型逻辑彰显了“社会性”的主体功能,映射了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生互构共生关系,同时这亦有效契合当下风险社会治理的时代主题。事实上,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内在本质要求建构出“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的内容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坚持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核心原则,凸显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意在型构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治理长效图景,力图实现社会整体性福祉的提升,旨在进一步提升转型期的社会治理质量,进一步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政府质量;社会质量;社会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关系失衡的问题愈加突出,诸多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日益频发,城乡社会冲突风险不断扩大,社会治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客观要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与转型,提升社会治理质量和水平。由此,社会治理应该被纳入到一个系统的完备治理体系之中,而这一关键性问题在于如何有效建构完备治理体系。正是基于治理系统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社会治理主客体以及外部治理生态显然陷入了结构性障碍。如若无法客观而又系统性把握社会治理之结构性转型,中国特色型社会治理会处于一种自相矛盾的“西西弗斯”神话之中[1]。但既有社会治理模式的显著性弊端体现在未能有效激活社会本体的应有治理活力,进一步制约了社会治理的长效性,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型构出地方政府的“本本位治理模式”。如上种种,进一步蚕食了社会治理的普惠性福利。社会治理的演变实质是以国家权威主导的社会治理变迁过程,“变迁逻辑”映射出社会结构的断裂与重构。重构的结果是社会置于国家政府治理之下,社会主体依附于国家主体,社会本体的主体性功能丧失,致使社会结构陷入“分化”之困境,社会主体被政府主体高度组织化。从那一历史演变阶段的现实图景可以映衬出,城市场域的“单位制与街居制”,乡村场域的“人民公社”。国家力量高度延伸于社会的每一处角落,整体社会被纳入到国家行政权力的支配范畴之中。政治整合与政治命令是当时社会治理的既定模式,社会尚未构成一种独立式的自治模式,国家权力对整体性社会实现了全域治理,城乡高度覆盖的无边界式治理格局。随着现代性的渗入,社会治理结构和组织形态已然发生了质变和异化,但旧有的治理权力格局和治理规则仍然在延续,治理效能并非呈现出断裂式减弱[2]。从现实治理实践来看,“自主性”缺失常流于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之中,社会主体的自治功能与效应被消解。传统社会演变到现代社会的过程昭示了社会治理结构的社会化变革,但其实质仍未超脱于国家统一的管制体系之中,换言之,这是一种“规划的社会治理”。现代权利意义下的社会治理尚未能建构而成,社会的主体性功能效应丧失。由此认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以“政府质量”为主导逻辑。正如研究者所言,“从国家出发的社会治理,不能没有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同样,从社会出发的社会治理,不能没有政府的参与和引导”[3]。进入新时代后,全面深化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社会治理场域空间充斥了内生不确定性和复杂性,治理主体间的合作困境日益突出,社会治理质量难以维持高水平。
二维路由是一种新型路由协议,它在进行路由决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目的地址,还要考虑源地址。传统路由协议中,去往相同目的地址的报文的下一跳往往是相同的(不考虑等价多路径);但是在二维路由中,目的地址相同、源地址不相同的报文,其下一跳可能不同。二维路由的这种特性带来2方面的好处:一是流量控制的粒度变细,网络管理者可以更加灵活地管理网络,如进行流量调度、策略路由等;二是用户的多样化需求可以被更好地满足,例如:享受专门的转发通道等。
因此,如何审视社会治理的转型逻辑,以及如何有效把握社会治理本质逻辑的演变趋势,这成为当下社会治理转型研究的重要现实命题。换言之,社会治理从“政府质量”为主导转型到以“社会质量”为导向的新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演变过程的背后隐含何种价值命题及运行逻辑?新时代的社会治理转型路径又应当如何?对如上命题的诠释恰恰构成了本文对社会治理转型研究的关键贡献所在。
二、政府质量:社会治理的传统逻辑
(一)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追求目标
社会治理的“好与坏”评价不一,各个历史阶段下的社会治理模式存有异同。但评价社会质量的“好”,关键在于如何界定这一社会是否为 “好社会”,这一论述逻辑形同与社会治理之善治。何为“好社会”?历史的演进,社会的变迁,古今学者都在对“社会治理”研究进行诸多学术与实务层面的想象与现实建构。以中国社会的历史传统演变为例,从春秋时期的孔子对“太平盛世”的积极“赞美”,倡导建构丰衣足食式的“小康社会”;近现代的康有为先生的“大同社会”以及孙中山的“天下为公”之社会。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单位制”型构了建国后社会治理的承载体。就其治理理念的历史演变轨迹可知,在某种程度上凸显出了政府质量导向的“好社会”之建构意愿,但其并未立足于社会本位,始终是以政府治理统合者的角色为主。比较各个历史阶段下的社会治理之“好模式”,或者社会治理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与实践无非都是积极嵌入到“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结构之中”,治理的外延主体尽管打着追求“社会整体福利”之旗号,然其未能超脱于世俗化的统合治理阶层的利益,其仍然是以统治阶层为主导所建构出的“好社会”,并未以社会性为治理行动之最终目标[4]。由此看出,传统治理模式下的治理导向仍然是以政府治理为导向,其本质仍然是以“政府质量”导向为主。换言之,传统治理模式是以“财富分配、调和个体与集体的失衡关系”为主,并未立足于社会之本位需求,以一种看似追求“社会福利”,实则以政府治理质量为行动导向,进而以此行动形塑出社会治理之图景。梳理上述观点可以发现,这些无疑都可以集聚为一个关键要点——“政府质量”,但这一“质量”并非是以社会为本位,而是以政府为核心导向,抑或以政府治理为导向。
社会治理传统模式的现实治理建构行动都在某种意义上致使公民社会的“善治”缺失,更为关键的是在社会场域空间中的行动主体的“社会性”容易遭致外部治理阶层的实质压制与摒弃。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治理的现实建构行动往往都是建立在政府以国家政治动员形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动逻辑,实现社会资源的有序配置与社会秩序的调整,从而达成政府之于社会的治理[5]。由此看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国家与政府的角色往往是高于社会本体之角色,其社会治理行动往往是会“忽视”、割裂甚至磨灭“社会性”在治理行动的生存空间,以便于形成国家和政府对社会的一种统合性治理之效。而在这种治理境况之下,治理行动容易引致“集权与专制”式的治理模式。传统模式的行动追求与价值导向并未是建构出以“社会”本位的理想型社会,而是通过“制度—生活—行动”的三维互动逻辑,进而有效调节国家(政府)与社会,抑或个体与集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尽管诸多学术理论或创想都在呼吁“社会性”的建构,但“理想的丰满”正昭示了现实社会治理行动之“骨感”,仍然是以政府导向为主的一种治理增量[6]。对于“社会性”的治理追求并未得到社会治理现实行动的有效回应,经济社会增量以及反哺政府质量已然成为传统社会治理模式的基本研究内容[7]。诚如西方学者加尔布雷斯将其所认为“好社会”更加具象化,使得其更具有概念与内涵体系充斥了操作性,“好社会”应当是一个能够充斥了民主责任、政府责任、社会责任,并使其能够有效调和,各方主体追求相互兼容利益的社会[8]。因此,在这一社会之中,社会成员在性别、种族以及本质特征并无差异性,能够以自身的劳作行动获取一种有价值的生活;但其严重摒弃“私有制模式”和“社会主义治理模式”,这些治理模式并未能在根本上化解“好社会”的结构性障碍,调和“政治—经济—社会”之间的有机结构,进而能够有效型构出美好社会之愿景。阿玛蒂亚⋅森(Sen)对社会发展和社会治理之论断延续了加尔布雷斯的自由主义思想[9]。但森与加尔布雷斯还存有差异点,森认为一个善治之社会是集中保障全体行动主体的“可行能力”。基于可行能力的视角,森对善治社会之主题,他还建构出一整套的评价指标体系,上述理论与实践已经在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获得一致性的认可。
鉴于上述理论观点的梳理,评判社会治理的“好与坏”程度并未超脱于政府治理社会的视角,仍然是立足于“政府要治理好社会”之主体论断,由此产生的治理行动关注的是政府治理社会之增量[10]。换言之,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治理增量集中表现为经济增量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之增量。因此,以政府质量为导向的传统治理模式尚未凸显出“社会性”之体现,社会本体之“积极意义”无法映射于现实世界中的治理行动,治理行动自然无法有益于社会发展。传统治理模式往往是被治理行动者所“操纵”,以期满足其特定的行动利益(政府主体),实现特定的政府行动者的偏好需求。
(二)以政府质量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治理限度
社会质量的本体要求在于社会性的集中体现,而“社会性”在当下中国语境下意味着整体性改革的创新,让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体系。同时社会性更突显了新时代下“社会人”对于“社会之权利”的积极争取。诚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所指出的,“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全面推进平安中国建设,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维护最广大人民之根本利益的治理行动关键在于提升社会民众的整体性福祉;社会治理场域空间的社会福祉亦会反作用于社会主体,最终促成社会主体自由而又全面的发展[25]。社会治理从“政府质量模式”嬗变到“以社会质量”的新模式,其内中演变逻辑昭示了社会治理的转型路径。具体而言:
社会治理的转型逻辑必然需要嵌入社会本体的现实治理诉求,积极回应社会本体的现实治理诉求,倡导以社会本体为主导。强调“社会性”是当下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的全球化共识,以“民本”需求为导向的社会治理行动将促成深化改革红利惠及于社会民众,从而推动社会治理的转型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时代精神与改革方针有机契合了社会质量理论内核,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的转型。从本质来看,传统社会治理模式是“以物为本而非以人为本”的治理行动原则,强调政府与市场经济的增量。这种政府质量导向的治理行动模式严重割裂了社会本体的行动结构,进一步引致了治理质量的弱化效应。这一行动负效应反映在现实治理图景的是:社会参与治理的渠道变得狭窄,治理职能相互错位,政府对于社会民情民意知之甚少,政府脱离社会民众之需,社会突发事件爆发之时政府往往呈现出被动应付局面[26]。政府与社会主体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弱化了社会主体的自治能力,社会治理效能被减弱,社会质量必然不高。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反思当下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强调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以期适应社会民众之需,在社会质量导向下实现社会治理的能力现代化。
其二,过度关注政府质量而忽视了社会质量。传统上社会治理模式下的突出特点在于质量导向,这一质量仅仅注重生活质量与社会稳定质量,但却忽略了社会质量。无论是传统社会、计划经济时代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治理模式仍然是立足于政府,社会治理仍然置于政府治理之后。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以经济建设为主的国家发展战略,生产与生活体系的日益丰富,社会民众的政府质量日益增加。但传统社会治理的政府质量导向,强调经济与政府治理质量的增量,但却忽视了“社会性”,其结果往往呈现出“恶果”之效,例如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土地肆意征用、强拆强办、医患冲突等等社会治理风险激增[13]。过度注重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质量,社会治理亦会内生“逆向激励效应”,其作用于现实社会治理图景之中,往往会呈现出“悖论”:一则是社会民众在社会治理行动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获得整体性的物质福利,且能持续改善民生生活质量;反之则是社会民众的怨恨情绪肆意蔓延,社会幸福感与满意度并未与之相互提升。尽管代表物质水平的政府质量获得了提升,但却未能改善社会民众的生活满意度与社会幸福感,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幸福指数是呈现出下降趋势。由此可见,当社会民众的物质获得的同时,社会民众的精神与社会价值诉求表现出一种渴望。而上述现实图景恰恰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相互匹配的。我们不可以否认的是加尔布雷斯的生活质量理论的无效,其加尔布雷斯在理论建构之时已然将“社会性”考虑在内,尝试着突破以经济建设为主的片面式治理模式,但理论建构与现实的治理行动往往存有行动“空白区”,治理“失灵”图景亦有可能发生,社会治理的“社会性困境”仍存于治理空间中[14]。社会治理的“社会性”之体现在于努力提升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应当尽力去增加社会认同、社会包容、社会赋权等等的增量,从而促成民众社会良知的觉醒,使得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兼具了“诚信、尊严”社会特征,更加内含有高质量的社会生活[15]。
正是基于国际社会环境的复杂性,欧盟等国家福利社会危机日益严峻,诸多发达国家面临着诸多经济整合的现实问题,社会政策与经济政策之间的非均衡性发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治理的结构性困境,欧盟等国寻求社会治理的转型,以此来扭曲原先治理行动倾向(社会政策从属于经济政策),将“经济政策优先”的治理模式替换,目的在于增加处理日常社会事务治理的社会能力。如此的社会治理现实境况催生了社会质量理论。1997年欧洲学者通过《欧洲社会质量阿姆斯特丹宣言》,提出:“我们不希望在欧洲城市中看到数量不断增加的乞丐、流浪汉和无家可归者。我们希望欧洲社会是一个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社会,同时也希望通过提升社会公正和社会参与,使欧洲社会成为具有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由此“社会质量”这一全新的发展理念正式登上了社会政策与社会治理的历史舞台,这俨然是为了应对当时欧盟社会政策危机的一种积极回应。其理论建构的最初目的是针对于那种把欧盟发展进程看作一个“经济整合”的趋势,而不是将其视作一项“社会工程”[19]。因此可以看出的是,社会质量理论指出了这种对社会进程的新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诠释的负向效应,提出了基于“社会关系”的诠释视角,以此来弥补因负向效应而致使的整体性社会政策失灵的恶果。社会质量理论内核在于极力倡导建构可持续型的社会建设模式,以社会治理创新行动,力图达成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均衡,从而提升社会的整体性福祉,最终建设高质量的“好社会”。
场地仅钻孔(CK1、CK3~6、CK9~10、ZK1~3、ZK5~8、ZK11~20) 有揭露,揭露层厚0.50~3.81m,平均厚度1.82m;层顶高程-0.70~2.50m,层顶深度 1.30~4.30m。
社会治理传统模式的治理限度,为社会质量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应有的理论需求。而社会质量理论内涵集中体现了社会性之价值,以及通过制度、政策、行动、手段来实现社会质量的有序增加,而这正是社会治理应对“复杂条件之不确定风险”的应有之义。由此可以证实,科学地映射社会性的社会治理新模式有助于提升社会质量,实现社会福祉的增量[16]。但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之现实境况是,从中央到基层层面的社会治理体系尚未健全,传统的治理模式并未完全革新与摒弃;从传统过渡到新模式的演变过程中以内生出“社会性”的参与力量并未在治理行动网络中获得再生“空间与土壤”,代表国家力量的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仍然是当下治理的主导模式,国家之于社会的单向度影响格局仍未转变,制度与行动的滞后严重割裂了本应当以社会本体为主的治理新模式的生存空间。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其亦会增加社会治理之风险,从而加剧了国家与社会的内生张力关系,削弱了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凝聚力[17]。因此,如何提升社会质量的强烈呼吁已然成为当下社会治理的“增量式”治理行动。诚如国内学者林卡认为,“社会质量”概念孕育而生的过程是经过“反贫困、社会保障、追求生活质量”的一系列发展过程。如要建构出一个“好社会”必然需要经历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的追及过程,且这两者呈现出先后递减之逻辑关系。社会质量的提升建立在生活质量的基础之上,而社会质量的逆向效应亦会反作用于后续生活质量过程。社会治理现实议题的转向逻辑正符合了社会质量的孕育过程[18]。“社会的转变需要一个过程,政治秩序的新旧交替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设计和思考这个问题时,便不能离开中国社会的社会质量”。同时,其意味着符合现实社会治理实践逻辑。由此看出,面对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之现实境况,要坚实立足并超脱于原有治理模式的生活质量与政府质量之导向逻辑,积极开展治理创新行动,以期实现社会质量的有序提升。
三、社会质量:复杂条件下社会治理的逻辑转向
其三,治理效度受限。之所以社会治理模式的治理效度受限,原因在于:一是社会治理创新改革阻力大;二是社会行动主体思想和价值多变。一方面,社会治理创新正处于改革的深水区与攻坚阶段,过去的三十几年的改革已经将“好改”都改革了,社会治理自然成为“难改”之结构性障碍。同时应当警惕,社会治理的创新改革如若无法坚持并完成则会退回改革前的治理处境。追求传统的政府质量之增量是无法适应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实践之需,同时亦会阻碍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当治理行动无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时,社会秩序会面临解构,社会风险发生的可能亦会积增。因此,助推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意义在于努力提升治理行动的社会质量,凸显“社会性”在社会治理行动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社会行动主体思想多元与价值多变之特征户进一步致使社会治理效度的受限。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化,传统的“一元化”治理格局被割裂,型构出“一主多元”之治理格局,最终的结果往往会促使社会行动主体的思想发生诸多断裂,进而形塑出多元化思想和多变性价值。但随着其外部环境的异化,市场经济要素的嵌入,其所裹挟的理性选择逻辑会侵蚀治理行动,治理效度亦会遭受阻力。而社会治理行动并仍然是以政府主体为主,社会本体处于治理行动网络中的区位仅仅是“形式上”的参与主体,参与社会治理行动的效度仍旧有限。这一现实进一步引致了社会治理行动的“社会性”缺失,严重断裂了社会治理质量的有序提升。
与此同时,随着改革的深入化与中国社会转型速度不断加快,我们的社会正处于高度复杂性的转型阶段,社会治理充斥了诸多不确定性,其行动结果往往容易引致了风险社会和社会危机,社会的结构性障碍与缺陷正进一步消解社会运行结构之基础[20]。由此,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势成必然,“治理创新行动”已然成为当下转型阶段的关键词。社会的大环境充斥了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之风险,如若不坚定社会治理的改革创新,其结果往往是作出维护旧有制度的行动选择,与社会治理的客观性要求相去甚远。因此,即便行动者在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治理行动内容和未来方向有着相异的认知、意识以及价值取向,但拥有并将其嵌入到社会治理行动之中,这本身就会使得普罗大众会时时刻刻审视我们社会治理之境况与社会民众现实治理需求之间的客观差距,并且能够主观能动性地去消弭社会治理创新行动间的差距。一旦行动者在社会治理改革方向上趋于一致,能够在社会治理基本问题上能达成一定共识,将促使社会治理改革内容与方向的分歧最小化,从而能够有效整合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的行动力量,使得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相互平衡,最终有序提升社会质量。
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之改革创新研究的关注要义正面临着从治理模式到社会质量之范式转化,社会治理背后所蕴含的社会质量正不断被学界和实务界所认识和吸纳。因此,由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质量理论如何有限嵌入中国特色社会治理语境,并使得其能够为我们提供理念创新与治理创新行动,换言之,社会质量理论对我们国家社会治理的适用性考察,将成为当下乃至今后一段时间内值得社会治理学术研究与治理创新行动深入省思的现实课题。与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以生活质量与社会稳定结构为目标导向)相比较而言,社会质量模型在考察社会成员个体主观感受的同时,也注重对社会整体结构状况进行考察,通过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融合以及社会参与等四个维度将社会成员个体主观感受与社会客观结构整合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之中。如伯克等人认为社会质量概念具体是指“公民在哪些能够提升人们的福利状况和个人潜能的环境条件中参与其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的程度”[21],它由条件性条件因素、建构性条件因素和规范性条件因素等三类因素组成,共同构成了社会质量的三维框架,具体见表1(下页)所示。
而当下中国治理环境呈现出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社会治理风险日益突出,社会治理主体的原先格局正趋于解构之迹象,以社会本体的取向逐渐被凸显,社会治理的转型势成必然。更为关键的是,社会治理的转型要求政府主体角色让渡于社会主体,原先治理理念从传统的“政府控制以治社会”过渡到政府“引导并服务于社会”,以促“社会性”在治理行动中的积极效应。而这种“社会性”之积极效应具体表现为社会的自主性和自治性的特点,从而促成社会主体的合作共治。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容易促成主体间的积极效应,能够有效达成社会融合,从而提升社会赋权与社会包容程度。社会治理的合作共治价值导向与社会质量理论在其理论内核层面上存有高度的同质性,并且这两者理论在理论意识形态上能够形成互补效应。从詹姆斯米奇利、贝克、沃克等人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在总体层面上体现出一种健康之状态,然其任何社会有机体在社会场域空间中的社会运行质量都不可避免地呈现异化效应,因而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操控及其控制过程能否通过一系列的规范和程序来实现社会有机体的正常运转,是这一社会有机体的治理质量能够实现社会稳定结构的决定性条件[24]。显然,通过建构科学可行的社会治理模式是降低社会质量异化风险、促成社会有机体良性运转、实现高质量之社会的有效路径。尽管社会治理范式是诞生于欧洲场域,然其理论的适用性正逐渐被他者国家所吸纳,中国社会治理的现实场域空间仍然能够接纳社会质量理论的现实指导。而社会质量理论内在的四维度内容(经济社会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凝聚以及社会赋权)有机地契合了中国社会治理之现实境况。与此同时,社会质量理论的指标体系为实现社会治理创新创造了工具性价值的理想化路径,亦能为社会治理提供一系列达成理想治理之效所需的 “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的行为方式和手段。
肩袖分层撕裂修复的患者术后应佩戴外展包6周,期间可以早期行患肢钟摆运动,防止关节粘连,促进腱骨愈合。术后6周开始部分被动关节活动,术后8周开始部分主动关节活动,术后3个月开始等张强度锻炼,术后6个月开始逐渐恢复到伤前运动水平[5]。
表1 社会质量理论模型的三维互构要素
建构性条件因素 规范性条件因素 条件性条件因素人力资源维度 道德意识形态维度 社会行动维度个体保障 社会公平(平等) 社会经济保障社会认知 社会团结 社会凝聚社会反应 平等价值 社会包容个体的能力 人的主体尊严 社会赋权
绿色勘查是绿色发展理念在地质勘查领域的具体实践,是基于符合环保要求达到找矿效果的一种勘查新措施或新方法。2015年8月,中国矿业报在“走基层”活动中,发现青海省有色地勘局的“多彩模式”,并首次提出绿色勘查这一先进理念后,得到了原国土资源部地勘司的高度重视。地勘司深入青海进行调研后,形成的调研报告得到了部领导的肯定和批示,绿色勘查由此正式被列为原国土资源部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始在全国推广。
一个善治社会的“好与坏”状况,实质反映出这一社会的社会质量实况,而社会质量的影响因素来源于该社会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态、文化以及社会组织、集体、群体间的特征。人是复杂性之人,亦是社会人,人之存在无法超越社会关系,人自然无法独立于社会场域空间之外。由此看出,人之社会性集中体现。而社会质量的内核是“提升社会福祉并激发行动个体之自由潜能”,这恰恰验证了“社会性”之于人和社会质量理论的契合存在。此外,“社会性”不能仅仅映射社会个体的完全主观性之上,社会个体亦不能无视“涂尔干式”的客观存在,“社会性”就应当是行动主体“互构共生”于社会场域空间之中。社会质量模型依托于条件性因素的适度操作,从而达到强化社会运行之基础,以期弥补社会治理传统模式中的盲区[22]。社会质量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消弭社会发展与个体发展的内生矛盾,消解制度世界(亦即系统、制度与组织)与生活世界(即社区、群体和家庭)的内在张力冲突,进一步改善社会治理的现实境况,以期型构出“善治”社会,最终达到提升个人的整体性福祉和自由潜能。
四、社会质量视角下社会治理的转型路径
以政府质量为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然无法适应当下复杂性社会的现实需求,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充斥于社会行动空间之中,其不断消解社会治理之行动。由此,以政府质量导向的社会治理模式内生出了诸多治理限度。
当下中国社会治理正处于高度复杂性的状态之下,不确定风险充斥其中,社会治理内生要求和外在环境变化都在某种意义上警惕治理范式之转化。而社会质量理论为诠释社会治理的现实境况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究其缘由,社会质量理论与社会治理创新在本质层面上是相互契合的,其治理行动价值取向亦是相互共通的,两者理论内核都强调“社会性”的集中体现,凸显“社会性”之于治理行动的能指,秉持了“以人为本”的行动价值内核,让渡社会本体的权力与行动。此外,社会质量都在一定程度上尝试从意义世界与行动世界之间寻求一种张力的平衡点,有助于消解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内生张力[23]。换言之,如何通过一种良性行动为社会个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以期能够实现社会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质量,作为一种社会政策下的发展理念,有效摒弃了以往的唯经济增量的片面式发展观,强调建构出一个可持续的福利型社会,凸显民主、平等、团结以及和谐的价值导向,以期促成社会的整体性福祉的提升。因此不难看出,社会质量理论所积极倡导的是谋求全体社会成员之福祉,同时亦需要提升人之潜能以促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人之社会性在社会质量理论体系被得以凸显,“社会性”在本质上集聚为“人本主义”的价值导向。
(一)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转型的基本原则
新时代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始终要坚持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创新,提升社会治理质量,以期有效适应当下高度复杂性的社会治理境况。正是基于其契合性,从而有机地减弱多元化社会治理之风险,匹配多元主体共存之需求,最终适应多元化社会之治理需求。中国社会治理主体都仅仅存之于政府,治理方式与治理工具都依托于政府的权力网络,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约束与监控的治理行动逻辑,最终引致了“治得多,服务少”现实图景的发生。这种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在单一化经济结构中治理效度仍然显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推进,社会治理进入了深入区,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充斥于社会治理之行动网络之中,社会主体间的利益分化愈发明显,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然无法适应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需求,关键在于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以便于有效型塑出新型党建组织架构和工作协同机制。依托于如上党建协同机制进一步消解社会治理的“合作行动困境”,弥合“碎片化”治理间隙。具体而言:一方面,要积极架构出区域化党建平台,使得将基层党组织功能嵌入到社会治理的转型过程,断裂了以往的组织运行机制,从垂直领导向协商民主转变,最终有助于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另一方面,运用“党建+大数据系统”思维,始终坚持以“党建引领”的基本原则,强化“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1+3”社会治理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打造了“新引擎”动力。
普拉加葡萄酒庄(Plaga Wine)是另一个在巴厘岛上利用非酒精原料进口税低这一优势来酿酒的厂商。这个团队由一群说西班牙语的人领导,包括来自智利的市场营销员胡安·迪亚兹,来自阿根廷的酿酒师普拉伯·冈萨雷斯和来自西班牙的乔迪·莫雷诺。酒庄从智利中央山谷、意大利西西里岛以及西班牙拉曼查进口浓缩葡萄汁,并在收获期进行实地品质控制,普拉加的主要目标人群是年轻的印度尼西亚人,零售价格与当地种植的葡萄酒持平。在真正的拉丁精神中,传递的讯息是乐观的——无论在何时何地,都要过得开心。胡安给我看了即将发售的莫斯卡托视频,不得不说这是吸引消费者的一个亮点。
上一节的分析过程中,主要根据经验和差异性分析选取了连续三个采样注视点的位置X坐标和Y坐标、注视时间、眼跳幅度以及瞳孔直径共15个分量作为分类特征,本节我们考察不同眼动指标组合以及不同采样点个数对分类预测准确率的影响.并且我们将注视点的X坐标和Y坐组合进行讨论,将二者作为注视点的位置特征.表3列举了采样注视点个数为3时的眼动指标组合对应的分类预测准确率.
(二)积极回应社会本体的现实治理诉求
其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失衡关系。自20世纪三四十年代“GDP”概念提出以来,经济与社会发展一度陷入了“唯有GDP至上”的怪圈,一味地追求片面式的“经济社会增量”,这种行动误区进一步引致了发展的“扭曲效应”,甚至出现了“有经济增长而无社会发展”之行动窘境。进入21世纪以来,欧盟等发达国家立足于福利社会建设及社会本体建设的发展要求,逐渐摒弃了片面追求经济GDP增量的发展模式,反思社会治理对于社会发展的时代要求,诚如詹姆斯米奇利所言,如若无法实现整体性人口之福利,社会的治理行动将毫无现实意义。当“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理念陆续被提出,进一步映射了对社会发展实质意义之反思。社会发展的要义逐渐集中于社会治理之行动层面,其行动往往需要建立在以考察社会本体的行动“区位”,如若仅仅以一种“被治理”的态势存在于行动空间之中,传统治理模式的治理效能亦会受阻。审视中国社会治理之经验,从新中国建立之后的社会治理演进轨迹,更多凸显是以“政府治理社会”为主,治理增量的获得恰恰立足于国家与政府对社会稳定的现实需要[11]。如何有效调节和优化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失衡关系是现阶段转型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结构性障碍。因此,将社会本体充分纳入社会治理能力创新体系,强调社会性在治理创新行动的突出作用。正是基于传统社会治理的社会发展的“失位”,给予了当下社会治理创新的行动空间,凸显“社会性”的治理效应[12]。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所意蕴出的社会政策是与社会质量理论相互吻合的,如何建构并治理一个高质量的社会是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仍然需要将社会治理内嵌于社会治理创新之行动,从而达成治理有效性。
(三)权力让渡和凸显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
社会治理主体间的权力让渡社会本体,亦不可忽视社会组织(非营利组织)在社会治理转型中的作用。放权是社会治理转型的实践要求,而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社会治理模式更加注重社会本体的治理活力[27]。事实上,社会组织尽可能承担政府转移出的职能,通过开展各种行业活动,弥补政府公共服务中的不足。一方面,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工程中扮演以桥梁纽带的角色身份,将把政府的政策方针传达给社会成员,让其了解国家大政方针,起到“上情下达”的行动功能,助推政府主体与社会主体之间的对话协调;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代表所属成员群体的利益,下情上达,为所属集团成员的利益表达提供多元化渠道以及合法合理的表达方式。同时,社会组织亦可通过募集外部社会化资源,提供公益服务。借助于各种公益慈善活动、募捐活动筹集善款方式,吸纳社会化捐赠,以便于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诸如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大型社会组织,每年从海外募集资金多达50亿元左右,上述资金的扶助对象主要是贫困型弱势群体。此外,社会组织不仅自身吸纳了大量从业社会化人员的再就业,还借助于多元化渠道对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待就业群体进行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就业服务,以此来减轻这部分群体的就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
五、结语与反思
社会治理的转型与创新在本质意义上昭示了从传统的“国家质量”为主导逻辑嬗变到以“社会质量为中心”的新模式。新时代下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意味着以“社会性”为基本点,社会治理质量是其理论内核,这些都无疑会对社会治理提出相应的新时代要求。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强调国家质量的治理导向,在某种意义可认为是一种对社会治理的“政治叙事”。而社会质量的本质是为了提升社会人的整体福祉,最终获得社会人的全面发展,足以证实了在后工业社会下社会治理是以凸显社会质量为本质要求,强调社会治理的“生活实践叙事”。随着现代性节奏不断加快,历史车轮的加速运转,社会治理转型势在必行。当历史时针转到这一刻,我们应当清晰地认知到:社会治理的政治叙事强调的是权力精英对生活实践的理性回应,但从治理实践和治理应然性来看“社会治理的本质则是生活实践的范畴”[28]。正是基于社会生活实践的现实需要,社会治理的概念才得以提出,换言之,社会治理的内涵是由生活实践所赋予,其治理目标来自社会行动主体对于社会生活实践的未来预期。但是,当权力精英无法理性地回应社会生活实践所面临的现实挑战,政府质量的社会治理模式亦会遭受解构之风险。事实上,社会治理如何从一种政府质量(政治叙事)转型到社会质量(生活实践)的治理逻辑成为当下社会治理转型的关键性命题。社会质量理论弥补了以“政府质量”主导社会治理模式的社会性缺陷,有效促成了在新时代阶段下社会治理的转型。
从社会治理转型逻辑来看,以“政府质量”过渡到“社会质量”,和从“政治”叙事方式转向到“生活实践”叙事方式是相互吻合的。因此,如何在后续的“社会治理”研究深刻把握这一转型逻辑,以促研究的深度化,这就需要厘清如下几个要点:
其一,如何将社会治理从政治叙事的政府质量转向生活实践的社会质量,才有利于确定社会治理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系中的具象区位。无论从国家权威话语体系抑或是学术话语体系来看,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亦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随着治理环境与治理空间不断充斥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置于国家治理下的社会治理被要求适应“精细化治理”逻辑,同时反衬出治理边界、治理制度边界的科学化界定的不明晰与模糊状态。正是这种模糊状态内生出双面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政治叙事下的社会治理无法建构出整体性治理格局(治理权限的非均衡性配置);另一方面,处于基层社会治理无法适应外部环境的治理需求,最终将会引致社会生活实践的“无序状态”。如若无法化解上述两种结构性障碍,政治叙事下的社会治理将会被内外部力量共同消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徒增对治理合法性的负向效应。因此,只有将社会治理推向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社会生活实践过程中才有可能有成效,再经过社会生活实践的不断演进、系统反馈,才能型构出一整套的普适性治理规则和治理经验。当通过对普适性经验的外部推广,实现以社会质量为核心导向的社会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的相互衔接,从而确定了社会治理的转型。
其二,当社会治理从政治叙事的治理质量转型到以社会质量为核心的生活实践导向,有效映射并巩固了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之于社会治理的合法性要求。社会治理处于政治叙事逻辑表征出政治权力精英对社会生活实践的积极回应,这在某种意义上使得社会民众对国家统合性治理模式压力得以缓解,但国家统合治理社会确实是以社会生活实践的善治为最终目标。而这一结论来自如下基本事实:一是生活实践的制度化危机是国家统合治理合法性危机的“根子”。无论国家统合治理方式和过程存有异同,但其内在行为逻辑并未超脱于生活实践的反思与重构。正是基于社会行动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的负面情绪,社会行动内生出行动惰性,因而一旦聚集了多数人的共识性舆论,则会引致国家统合性治理的危机。二是社会个体之于社会生活实践的行动情境遭遇是社会个体对于国家统合性治理合法性认定的根本性依据。从一种整体性宏观视野来看,在整个社会系统内部体系中只存有较少数的权力精英和知识精英才能有效判定国家统合性治理的合法性问题,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既无能力也没有思考机会,只能依靠于社会个体自身生活实践经验为依据,以此来讨论与国家统合性治理的相关公共话题。
对于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治理的优化问题来说,欧洲社会质量理论及其倡导的社会治理模式有其独特的参考价值,但我们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特定的历史进程和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与分析。要厘清和剔除欧洲社会质量中不适用于中国的内容,提出中国本土化的社会质量命题。同时,伴随着社会质量理论的中国化进程,社会治理也须遵循动态和权变原则,不断推进社会治理模式的本土化转型和创新,以更加科学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的建设实践。
CCA排序图(图4)较好地反映了3类生态系统环境因子和群落物种的关系。综合来看,仅有少量物种对土壤深度(SD)、碎石含量、0~10 cm土层的土壤含水量敏感,其中大部分草本生长在露石出露面积较高的环境中,高露石面积的环境中乔灌木物种分布较少。乔灌木物种对0~10 cm深的土壤水分和土壤深度的环境条件要求比草本要高。
参考文献:
[1]徐勇,马海明.中等收入社会难题与社会治理创新——以“美丽厦门·共同缔造”行动为例[J].社会科学战线,2014,(9): 161-167.
[2]俞可平.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化[J].社会政策研究,2016,(1):73-76.
[3]林尚立.社会协商与社会建设:以区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为分析视角[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3,(7):135-146.
[4]李友梅.我国特大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分析[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6,(2):5-12.
[5]郁建兴.走向社会治理的新常态[J].探索与争鸣,2015,(12):4-8.
[6]张康之.论主体多元化条件下的社会治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4,(2):2-13.
[7]ABBOTT P,WALLACE C.Social Quality: A Way to Measure the Quality of Society[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2,(1):153-167.
[8]LINK,LIH.Mapping Social Quality Clusters and Its Implications[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7, 134:1-171.
[9]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18.
[10]王星.从维护社会稳定走向增进社会质量——中国社会治理创新的取向转型[J].学术研究,2016,(9):61-66.
[11]韩莹莹.社会质量与居民幸福感——以广东四县(区)为考察对象[J].中国行政管理,2016,(8):109-114.
[12]TOMLINSON M, WALKER A, FOSTER L.Social Quality and Work:What Impact Does Low Pay Have on Social Quality? [J].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2016,(2):345-371.
[13]詹国辉.社会质量与治理有效的互嵌: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实践的耦合性议题[J].兰州学刊,2019,(2):154-165.
[14]丛玉飞.社会质量取向:社会治理研究的新议题[J].江海学刊,2015,(1):112-117.
[15]张海东.中国社会质量问题及社会建设取向——以社会安全为核心[J].学习与探索,2014,(11):31-35.
[16]LIN K.Social Quality and Happiness—An Analysis of the Survey Data from Three Chinese Cities[J].Applied Research in Quality of Life, 2016,11(1):23-40.
[17]BERMAN Y, PHILLIPSD.Indicators of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Exclusion at National and Community Level[J].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00,(3):329-350.
[18]詹国辉.以提升社会福祉为导向的社会质量:一种新的社会发展范式——基于西方文献的理论阐释[J].宁夏社会科学,2017,(3):102-110.
[19]郑雄飞.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当代转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5):108-122.
[20]张康之.论高度复杂性条件下的社会治理变革[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4):52-58.
[21]W.BECK,L.J.G.MAESEN V D .The Social Quality: a Vision for Europe[M].The Hague:Kluwer Law International,1997:6-7.
[22]LIN K and LAURENT Van Der MAESEN.A background Paper on Behalf of the lnternational Nanjing Conference on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G] //The Confererrce Proceeding of the intenaatioraal of Social Quality and Social Welfare.Nanjing: Social Policy Research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8:15.
[23]詹国辉.现代性的延伸与社会性的本体要求——从理论体系考察社会互构与社会质量的契合性[J].学习与实践,2017,(6):79-88.
[24]唐魁玉,张旭.网络社会质量的数据化基础[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8,(8):117-122.
[25]林卡.社会质量理论:研究和谐社会建设的新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105-111.
[26]詹国辉.社会质量与社会发展的满意度是否关联? ——基于江苏农村(2005—2014年)的分析[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100-107.
[27]金太军,鹿斌.治理转型中的社会自主性:缘起、困境与回归[J].江苏社会科学,2017,(1):82-88.
[28]周晓虹.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路径[J].南京社会科学,2015,(2):9-18.
Government Quality to Social Quality:The Transformation Logic of Social Governance
ZHAN Guo-hui1,ZHANG Guo-lei2
(1.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23,China;2.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Guangzhou 510521,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at a critical stage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 is facing the risk of structural change.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realistic proposition in the new era.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social governance from traditional model to new model reflects the logic of action from “government quality” to “social quality”.The former emphasizes the increase in government-led economic indicators;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well-being.This transformational logic highlights the main function of“sociality” and increasingly maps the endogenous and symbio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ffectively fits the current era of risk social governance.In fact, the inherent nature of the social governance model with social quality as the core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ntent system of“social economic security, social cohesion,social inclusion and social empowerment”.More importantly, it insists on the core principles of grassroots party building leading social governance,highlights the rol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tends to construct a sustainable long-term picture of social governance, and strives to improve the overall welfare of society,so as to further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ocial governance during the transition period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Key words:government quality; social quality;social 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971(2019)05-0053-10
收稿日期:2019-07-18
基金项目:国家民政部课题“大数据时代下城乡“智慧社区”治理绩效及其优化路径研究”(2018MZJCZQ-0302);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测度标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18SJA0239)
作者简介:詹国辉(1989—),男,江西婺源人,讲师,博士,从事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研究;张国磊(1990—),男,广西武鸣人,讲师,博士,从事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责任编辑:唐魁玉]
标签:社会论文; 质量论文; 政府论文; 模式论文; 社会性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民政部课题“大数据时代下城乡“智慧社区”治理绩效及其优化路径研究”(2018MZJCZQ-0302)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战略下乡村社会治理质量的测度标准研究以江苏省为例”(2018SJA0239)论文; 南京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广东金融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