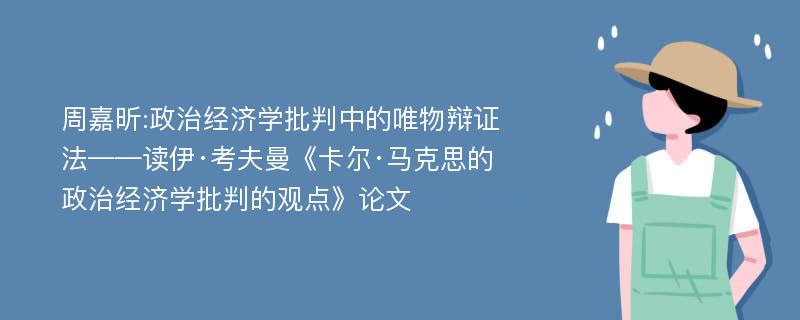
摘 要: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生涯中,曾多次提到辩证法问题。概括起来说,这主要集中在他早期批判青年黑格尔派和成熟时期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其中,最为经典的表述是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给出的。在直接的意义上,这些表述同马克思对伊·考夫曼《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的回应有关。其核心是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唯物史观与辩证法合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基于对考夫曼评论文章的文本分析和马克思《资本论》的结构、方法、创作历程的说明,我们可以发现:唯物史观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是内在统一的理论整体,唯物辩证法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运动规律,辩证法的叙述方式不仅限于“论述价值理论的一章”而且贯穿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始终。
关键词:《资本论》第二版跋;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黑格尔;唯物史观
谈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或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那些最常引用的、脍炙人口的段落大多出自《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甚至更加具体来说,出自《资本论》第二版跋最后部分。马克思借回应伊·考夫曼的机会,以文学化的笔调概要阐发了对辩证法和自己与黑格尔关系的理解。自然人们便产生了这样的好奇和需要:考夫曼对《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所作的评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到底给出了怎样的判断?为什么考夫曼将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指认为“严格的实在论的”,叙述方法则“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因此马克思是“最大的”、“极坏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样,反观跋文中的回应,为什么马克思却又认为考夫曼“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带着这些问题,利用西方学界最近重新编译出版的考夫曼《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一文,我们尝试回答: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阐发与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思想关联?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本文第一部分首先简要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法的不同谈论背后所蕴含的理论演进,第二部分集中介绍、评价考夫曼及其评论文章中对《资本论》方法和结构的说明,第三部分尝试结合《资本论》写作的历史语境,给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辩证法合理形态的学术判断。
一、马克思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表述:一个简要回顾
辩证法之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然而,正如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存在“辩证法三大规律”表述顺序的细微差异一样,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表述伴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发展和创新也存在着变化和调整。按照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手稿中的说法,三大规律的表述顺序是:量变质变—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结合《反杜林论》和列宁的相关论述,三大规律的表述还存在另外一种方式: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否定之否定。再考虑到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存在著作、手稿、书信、笔记等不同形式,以及这些手稿公开面世的不同方式,包括辩证法在内,经典理论问题和概念范畴的表述方式,承载着不同历史阶段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的思想探索和理论总结。因此,具体地历史地梳理马克思恩格斯对某一经典理论问题表述方式,构成了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的内在要求。回顾马克思恩格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表述,将为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方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辩证法的表述,我们可以遴选出以下代表性文献:“马克思致父亲的信”(1837)、《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家族》(1845)、《哲学的贫困》(1847)、《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评”(1859)、《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围绕《资本论》写作的通信、《自然辩证法》手稿(1875前后)、《反杜林论》(1876-1878)、《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
如果说,《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主要是在拓展、总结、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展开对包括辩证法在内的相关问题的论述的话,那么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的探索和制定,其中最具代表性也最常被引用的文献有:“马克思致父亲的信”(1837)、《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神圣家族》、《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1858)、“《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书评”、“《资本论》第二版跋”(1873)等。更进一步,考虑到上述文献的写作和发表情况,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对辩证法的表述主要服务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的说明。
在“马克思致父亲的信”(1837)中,马克思提到自己是在法学研究中投入了黑格尔的怀抱,因为后者克服了“是”与“应该”的分裂,“在现实中发现理性”。然而,持唯心主义立场的马克思此时尚无法发现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困境。经过《莱茵报》时期“物质利益难题”的困扰,马克思开始在反思理性主义国家观的意义上,运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批判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就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主要逻辑框架。这种人本主义的批判与政治经济学研究相结合,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以之为基础,青年马克思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义上反思黑格尔的辩证法,揭露“思辨结构的秘密”。但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站在古典经济学家立场上”,转而走向物质生产方式分析批判黑格尔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因此,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后的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几乎不再讨论甚至是提及辩证法。只是到了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马克思才在论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过程中又专门批判了黑格尔,并在“加工整理材料”的意义上发现了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1873年,经过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出版。这一版较之第一版,最大的区别是第一章的修改。马克思自己给出了说明:“第一章第一节更加科学而严密地从表现每个交换价值的等式的分析中引出了价值,而且明确地突出了在第一版中只是略略提到的价值实体和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之间的联系。第一章第三节(价值形式)全部改写了……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大部分修改了。”[1]14考虑到马克思《资本论》的写作过程,这一章的修改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早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时,马克思已经提供了一个《商品》章。但是在1866年,为了与经过结构调整的《资本论》第一卷相适应,马克思重新写作了《商品》章,并接受恩格斯的建议,写了一个价值形式的附录。这就说明:《商品》章本身构成了马克思辩证叙述方式最为困难的部分,这一章的修改与辩证法的理解直接相关。
第六部分是对《资本论》方法的一个补充性说明。考夫曼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资本论》所提供的并非是一种超历史的永恒规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消亡的特定历史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生活与有机世界呈现出相类似的特征。马克思专门摘引了其中的部分表述:“一旦生活经过了一定的发展时期,由一定阶段进入另一阶段时,它就开始受另外的规律支配。总之,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他们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资本论》“这种研究的科学价值在于阐明支配着一定社会有机体的产生、生存、发展和死亡以及为另一更高的有机体所代替的特殊规律。马克思的这本书确实具有这种价值。”[2]108-109
在本文第三部分,我们将证明:隐含在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背后的,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及其展开方式的理解。仅就《资本论》第一卷来说,正是由于它所用方法和表达方式的特殊性,在出版后引发了大量针对马克思的疑问和批评。
采用均匀设计法安排实验时,首先确定实验因素,而后选取均匀设计表,选取的均匀设计表的列数必须多于实验的因素数目。根据均匀设计使用表和实验因素安排实验。因素水平数目选取得过多或过少均会对实验产生不利影响,因此,因素水平数目需根据参数的变化范围合理选取。
二、《资本论》第二版跋与考夫曼《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
换言之,正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重新发现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并在《资本论》的叙述方式中运用了辩证方法。最为经典的两篇支撑文献是: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作的书评,以及马克思自己撰写的《资本论》第二版跋。而且,这两篇文献可以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对辩证方法的集中公开表述。反观当时已经出版的《神圣家族》和《哲学的贫困》这两部早期作品,前者是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意义上批判黑格尔思辨哲学,后者则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等量齐观,并在此基础上嘲弄蒲鲁东在理论上的贫乏。然而,即便是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对辩证法合理形态的探索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的结构计划调整,甚至包括《资本论》后续版本的修订,都体现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解不断深化基础上对辩证叙述方式的探索。
利用修订再版的机会,马克思也对《资本论》的理论效应以及自身的方法进行了专门的说明。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在《资本论》出版之初,“德国资产阶级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最初企图像他们对付我以前的著作时曾经得逞那样,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当这种策略已经不再适合当时形势的时候,他们就借口批评我的书,开了一些药方来‘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1]18。我们有理由相信:马克思在出版《资本论》之前,甚至是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时候,已经预见到自己的方法很可能会被“理解得很差”。虽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包含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论说明,但是马克思却不愿说出将要证明的结论,并把这篇导言给压下了。为了说明自己的方法,马克思要求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撰写书评。但是,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明确指认的那样,“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这已经由对这一方法的各种互相矛盾的评论所证明。”[1]19换言之,恩格斯所说的这样“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亟待澄清和说明。
为了说明《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十分关注俄国经济学家伊·考夫曼的评论文章《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并作了大段的摘引和专门的评述。对此,科瓦列夫斯基在《回忆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认为考夫曼的评论学术价值很高,马克思在俄国有关《资本论》的所有论文中,最为赏识考夫曼的文章,并且总的来说表示同意其观点。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也提到这篇文章颇为有名。马克思认为这篇文章正确地论述了他的唯物主义辩证方法。为了更好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方法,我们不妨梳理一下考夫曼的评论。
听课是初中数学青年教师“汲取营养”的一种重要途径.笔者,在刚参加工作时,每次上课之前都会先去听同备课组其他教师的课,然后根据听课体会和自己的备课过程(当然独立备课要在听课之前,否则基本没有任何效果)进行再次备课,最后才有信心走进课堂,相信大多初中数学青年教师执教初期也都是如此.
在怠速时,读取发动机控制单元中凸轮轴数据流,发现进气和排气凸轮轴位置执行器电磁阀位置在0~50%之间不停跳动,正常值应稳定在45%左右。进气凸轮轴位置实际值与期望值相差16°。通过分析数据流,我们认为可能的故障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网络时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读心成为可能,生物传感技术、情感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在网络时代社会调查领域的应用尤其值得关注。采用这些高科技,省去了提问的环节,受测试者不说话,机器也可以直接读出受测试者的心理活动变化数据,不可谓不神奇。
第一部分是对《资本论》的一个简单介绍。考夫曼从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谈起,指出马克思《资本论》的三个目标:第一,通过研究之前(政治经济学)并未提出的问题提供新的独立的结论;第二,提供针对构成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原则的系统批判;第三,提供大量准确界定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化信息。
注重酒店管理系统所包含有序子系统,进行子系统构件时根据酒店具体部门进行设置构建,按照酒店规模扩大或缩小系统构建范围,方便酒店员工对不同类型客人的识别和专业化服务。比如部门子系统满足部门经理人员管理需求,整体酒店管理系统满足高层管理者经营需求等等,以此为基于需求的酒店管理系统的实质性价值作用得以完全发挥[3]。
如前所述,针对考夫曼的评论《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马克思自己的评论是:“这位作者先生把他称为我的实际方法的东西描述得这样恰当,并且在谈到我个人对这种方法的运用时又抱着这样的好感,那他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1]21然而,结合上文对考夫曼评论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认为考夫曼“描述得这样恰当”的东西,虽然表述为辩证方法,但更为根本的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概括的“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经发现就用来指导自己工作的总的结果”,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考夫曼(1848年—1916年),生于乌克兰敖德萨。1869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1893年起担任圣彼得堡大学教授。考夫曼的专业领域是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马克思在1877年时曾批评性地提到其《价格波动论》一书。1872年,俄文版《资本论》出版后,考夫曼在《欧洲通报》1872年5月号上发表了一篇专谈《资本论》的方法的评论文章,即上文提到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评的观点》(1)最近,该文刚刚被翻译为英文出版。参见I.I.Kaufman,Karl Marx’s Point o View in his Political Economic Critique:A Review of Karl Marx,Capital:A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1872),ResponsestoMarx’sCapital,Ed.by Richard Day and Daniel Gaido,Brill:Leiden,2018。 。这篇文章的一个代表性观点是:马克思的研究方式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1]20。具体说来,这篇篇幅不长的评论虽然没有明确的分节,但根据其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七个部分。
所有患者都满足中医的中风诊断要求以及西医的脑出血、脑梗塞诊断要求[2,3]。入选条件:(1)年龄35~75岁;(2)病程不足半年;(3)初次发病,且伴有单侧偏瘫;(4)主动治疗,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条件:伴有心肌梗死、严重肝肾功不全、重度感染、凝血功能障碍、意识障碍等患者。
第四部分是考夫曼对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理解和说明。最具代表性的判断,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1]20。之所以要专门说明《资本论》的方法,在考夫曼看来,是因为在马克思的读者,特别是俄国读者中,仍然存在误解和疑惑。原因是:(1)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并未讨论这一方法的基本观点;(2)马克思的文风有很强的批判性,特别是他对孔德的批判容易让人忽视其实在论世界观,而将其误认为唯心主义者;(3)俄国的读者很容易被马克思辩证的叙述方法所误导。
第五部分是对《资本论》结构计划的简单说明。考夫曼认为,马克思《资本论》内容的丰富性远远超过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如蒲鲁东、罗雪尔等。虽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曾经提出“资本、土地所有权、雇佣劳动、国家、国际贸易、世界市场”的“六册计划”,但是经过调整,最终确定了《资本论》三卷结构,分别论述“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础”、“流通的资本主义体系”、“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基础”。考夫曼强调:这一结构计划的调整,同马克思对资本在社会生活现象中的主导地位的理解有关。
仅举一例来说明。正如马克思自己在《资本论》第二版中提到,“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在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1]22。也就是说,仅就字面意义来看,在《资本论》一书中《商品》章最多地包含了黑格尔辩证法因素,也构成了我们理解马克思在加工整理材料的过程中建构辩证法的合理形态最为直接的依据。但是,如果考虑到《商品》章自身的特殊性,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头足倒置就是一个远比直接在价值形式中找到《逻辑学》章节的一一对应要复杂得多。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除了《序言》外,还包括《商品》和《货币》两章。这个《商品》章本身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货币章》和《资本章》完成后重新写作的著作开头部分。1866年开始,在整理誊抄《资本论》第一卷的过程中,马克思从包含《资本论》三卷手稿的《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中择取了相关部分,重新写作了《商品》章和价值形式的附录。1873年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中,这一部分又经过了彻底的改写。
第三部分是考夫曼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大段摘引。在那里,马克思自认为“说明了我的方法的唯物主义基础”。这段话也就是我们最常引用的有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以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说明。在考夫曼看来,最重要的两个要点分别是:(1)生产力的发展在作为自然历史过程的社会运动中的决定作用;(2)意识要素在文化史上只起着从属作用,因此,这种批判的出发点不能是观念,而只能是外部的现象。
第七部分是对《资本论》第一卷基本结构框架的简单梳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最后两部分之间,作为一个理论的过渡,考夫曼强调指出:马克思《资本论》比任何其他社会主义者的著作都更难理解,要求它的读者不仅熟悉文化史和经济史,而且要掌握经济科学的新发现[2]110。
三、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与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二部分直接提出了理解《资本论》的关键问题,即批判的视点和方法问题。在考夫曼看来,批判的科学性保证是由方法问题提供的。紧接着,考夫曼描述了《资本论》方法的总体特征。用马克思引用的话来说:“如果从外表的叙述形式来判断,那么最初看来,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极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2]104。紧接着,考夫曼指出:(1)马克思发现了他所研究的现象变化发展的规律,并详细地考察这个现象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2)马克思所做的是通过科学研究来证明社会关系的客观必然性;(2)马克思把社会历史的运动看做是受不以人的意志、意识和意图为转移思维规律支配的自然史过程。
相应的,我们注意到:在马克思自己对唯物史观的总结和阐发中,除了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意识等问题的说明外,还有对作为特定社会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性或对抗性的阐明。马克思在《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413
而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论证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22
在对学生的采访过程中,发现大多数学生英语学习的目的在于获得证书或满足未来就业的条件,有的甚至不清楚自身学习英语的动机,只是“随大流”,出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学习本能进行自主学习,这种情况导致了英语自主学习更多地是为了应试而非应用。其中最直接的体现便是对于网络环境的应用不足,不注重自身的英语口能能力以及沟通交流能力的增强,英语的实用性被大大削弱,所应该起到的宣传湖南文化以及彰显湖南人才素养的作用难以在国际友人中展现。
在从批判性和革命性的角度出发说明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同时,为了回应包括考夫曼在内的德国和俄国学者在《资本论》叙述方法上的曲解甚至是指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交代。在这篇跋文中,有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观点的简要概括。马克思说:“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1]21-22还有对恩格斯为《政治经济学批判》所作书评观点的强调。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22针对考夫曼给出的“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评论,马克思回应道:“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22
梳理考夫曼的《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这一评论文章,回顾马克思对包括考夫曼在内的《资本论》理论反响所进行的回应,对辩证方法所给出的自我说明,我们尝试提出以下三个观点作为结论。
第一,作为马克思在研究中得到并用来指导自己研究的总的方法,唯物史观本身与辩证法是内在统一、相互关联的。在最直接的意义上,这表现为唯物史观对作为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把握及其历史性边界的阐明。而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从事物发展的暂时性中去理解,同时包含对事物的肯定的理解和否定的理解。因此,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享有共同的理论旨趣。更进一步,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将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在其思辨哲学体系的“神秘外壳”中发现“合理内核”,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是因为马克思从物质生产出发,科学阐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和运动规律。而正是在这一阐明或叙述的过程中,马克思发现辩证法在加工整理材料方面很有帮助。
第二,正如马克思自己所提到的那样,马克思和黑格尔辩证法最大的区别可以用唯物辩证法和唯心辩证法来标示。在黑格尔那里,思维过程成为现实事物的主体和创造者。但在马克思那里,观念的东西不过是在人的头脑认识并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然而,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中曾经用“观念的物(东西)”来描述商品价值一样,在现实运动的叙述过程中,材料之间的关系一旦在观念上得到反映,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与一个先验的结构十分类似。因此,叙述辩证方法仅从局部外观来看,与“先验的结构”几无二致,但是正如马克思提醒自己所说,“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在明了自己的界限时才是正确的”[3]398。也就是说,只有以阐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历史运动规律及其向未来社会转化的叙述方法,才是辩证法的合理形态。
第三,即便如马克思自己所说,自己在关于价值理论的部分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但是《资本论》中的辩证方法,或者说科学的辩证叙述方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品价值形式和拜物教秘密的分析部分,而是一个贯穿《资本论》结构计划总体的方法进程。正如本文第一节最后概要提及的那样,《资本论》第一卷《商品》章是一个为出版而重新拟定的导论性章节,涵盖《资本论》三卷四册的全部内容。商品和价值的分析作为一处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进程中的“抽象”环节,是以具体的理解为潜在的基础和前提的。如果我们将视角拓展到《资本论》第一卷甚至是《资本论》三卷的全程,可以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生产的社会总过程的分析中更为具体地发现辩证方法的存在。当然,考虑到马克思在世时只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那么他对价值理论部分的专门说明也就不难理解了。正是担心读者产生混淆,所以他才一再强调。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ResponsestoMarx’sCapital,Ed.byRichard Day and Daniel Gaido[M].Brill:Leiden,201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MaterialistDialecticin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ConsiderationswithKaufman'sReviewofCapital
ZHOU Jia-xin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In Marx’s theoretical career, dialectic was referred for many times. Marx’s discussions on dialectic were concentrated in his early approaches criticizing Young Hegelians and his mature studies around Capital, in which the most typical expressions were given in his post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Capital. This postface was written to reply I. I. Kaufma’'s review - “Karl Marx’s Point of View in his Political-Economic Critique: A Review of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 in which the main subjects wer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tudying method and explosion in Capital,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and the rational form of dialectic. With the analyses on Kaufman’s text and Marx’s Capital, it is to be argued that: 1) the rational form of dialectic is embedded with historical materialism; 2) Marx uses materialist dialectic to elucidate the specific law of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3) the dialectical explosion is not only in the value form analysis but also in the whol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Keywords: postface to the second edition of Capital; rational form of dialectic; Hegel; materialist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33X(2019)05-0006-07
DOI:10.16614/j.gznuj.skb.2019.05.002
收稿日期:2019-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17CZX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嘉昕(1982—),男,山东潍坊人,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和当代西方激进思潮。
责任编辑 李兰敏 英文审校 孟俊一
标签:马克思论文; 资本论论文; 辩证法论文; 黑格尔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研究”(17CZX003)的阶段性成果论文;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