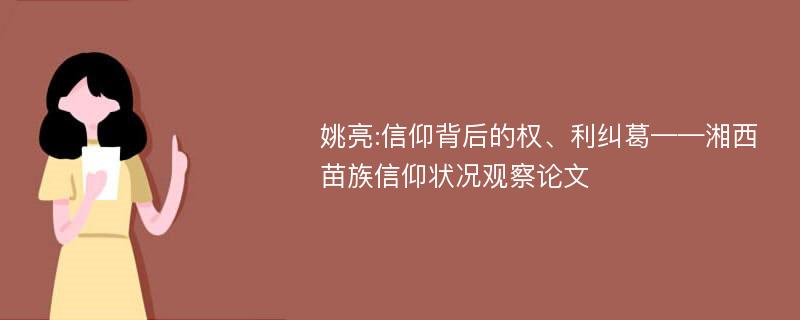
摘要:本文根据田野考察的访谈和观察对湘西苗族的信仰状况进行了讨论,揭示和描述了当地民间信仰背后所隐伏的权与利的逻辑,并指出这种对文化的消费是以信仰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逐渐式微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苗族;天王;巴岱;仙娘
笔者以凤凰县吉信镇火炉坪村为田野点对湘西苗族信仰进行了考察,同时对凤凰古城天王庙、吉首鸭溪天王庙、乾州古城城隍庙及观音阁、花垣赶秋节进行了踏访,涉及巴岱、道师、仙娘、城隍、观音、天王等民间信仰。总的来说,湘西苗族的民间信仰呈现衰落的趋势。宗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元素之一,宗教的衰落标示着民族文化的传承面临危机,这一结论与实际情况是吻合的,湘西苗族微电影《寂寨》亦可以佐证。这部电影由花垣县制作,所表达的正是对苗族传统文化后继乏人的忧虑和呼吁。造成民间信仰衰落、传统文化传承危机的关键是缺人,就像《寂寨》所展示的:村子里只有老人和小孩留守,是一座“寂静的寨子”[1]。走访村寨时,鲜有人语,唯闻犬吠,这也是田野考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缺人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少有人愿意继承传统文化,比如火炉坪村和隔壁的唐寨村,巴岱扎都没有了,只有巴岱象[注]①旧译“巴代雄”,其音更近“巴岱象”。,而巴岱象年纪大了,又没人愿学,所以巴岱在这样的村寨消失的日子并不会很远。其次,受唯科学主义和主流媒体影响,年青一代对传统信仰十分疏离,有的径斥为迷信而不愿多了解。再次,青壮年都去打工了,留下的少数青壮年都是公职人员,没有时间去做传统文化传承的工作。最后,本民族的传统信仰在外来信仰的挤压下,生存空间迅速缩小。火炉坪村有愿学道师(自称佛门俗家弟子)的,却没有愿学巴岱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道师热闹,丧家喜欢排场,报酬也高。
除此以外,湘西苗族民间信仰还有一个状况值得关注——对信仰的消费。我们在田野考察中观察到,这些信仰的从业者设法通过一些手段巩固、突出自己及其信仰的“神力”,从而获取一定的好处,也就是说,信仰背后隐伏着一套权力话语,其指向是利益(既包括从业者个人的,也包括该信仰群体的)。这样一来,信仰就不单纯是信仰,后面的权、利纠葛使得不同的信仰及其从业者、信众与信仰从业者之间的关系十分微妙,尤其是在具体的情境中,非常明显。本文无意于对该现象进行褒贬,只是尽量客观地揭示和描述所观察到的情形。
一、天王判案
火炉坪村有天王庙一座,据说原来的规模很大,“破四旧”时被拆,现在所见是重修的,只有几个平方,里面供奉着三个天王及其父母和一个侍女,香案下堆了大量供物,以酒居多,庙里还挂了不少红布。庙的左前方两米外有一个小土地庙,高一米、宽约半米。庙右边是水井,井的另一边是道师张YW[注]①为保护受访人隐私的缘故,其名均以缩写字母代替,下同。的家,他平时负责看管天王庙,祭祀时担任庙祝,功德箱也归他保管,庙会的时候把钱拿出来办宴席供应香客。由于重修是他家组织发起的,所以他是“首士”,具有管理天王庙的资格,其他香客则是“信士”。提起天王庙,村里的人都说由张YW负责。
约有10%的宝宝1岁之后状况仍未改善,此后更容易发生面部不对称甚至颈椎弯曲。这时就要根据个人情况,考虑手术治疗了。手术目的是将颈部受累肌肉的部分切除,从而改善症状。当然提到手术就要考虑到术前评估,手术、麻醉方式以及术后看护等具体问题。因此,动手术之前一定先跟医生沟通好。
天王信仰是湘西独有的民间信仰。天王判案的历史比较久远,苏堂栋(Donald S. Sutton)认为:“天王的神力帮助人们处理日常事务,接受还愿感恩并惩罚那些未履行誓言的人。最令人关注的是,白帝天王是这一地区的最高权威。信徒们借助天王信仰解决分歧:苗人争议双方,喝下混有猫血或鸡血的酒,发誓如果破坏在神灵面前立下的和解誓言,愿受‘九死九绝’。在清朝法律进入苗疆之前,白帝天王信仰在这个缺乏集权制度体系的社会中承担了习惯法的功能。[2]”
张道师讲了一个天王解决土地纠纷的故事。他特别强调冲突激烈且复杂到了无法解决的地步,官司打了三年,连法院都没办法,而在判案的现场,天王是绝对的权威,法院、政府都来了,却“都不说话”,只是一个陪衬。他的讲述还暗示了天王判案的公正性:在法院,理亏的人依然“有理”,导致官司难断;而在天王面前,理亏的人不敢来烧纸,不敢赌咒,不敢坚持其“有理”。天王庙的有效和权威自然让他这个“首士”与有荣焉,谈起来眉飞色舞。张通常扮演庙祝的角色,却是天王庙的实际控制者。
细细思想,凤凰天王庙的局从踏进山门那一刻就开始了。先是登记,外省人成为被诱导的对象。然后是关于龙脉风水的渲染,突出天王庙的神力,激起游客的好奇心和期待。第三个关节是观音殿,继续宣扬良辰吉日风水福地,引导人们求福。最后一步是黑屋算命,通过对灾厄的推算以及禳解之法的宣示,大多数游客已经没有招架之功,只能就范了。关于凤凰古城天王庙利用游客求福心理敛财的传闻屡见不鲜,网络上很多帖子暴露此事,然而至今未见改观。
吴表示,他不会掺和天王庙的事,他主要负责管理龙凤庵。天王庙在三组,龙凤庵在二组,吴家也在二组。他们似乎有明确的“势力范围”,互不越界。表面上看起来,他们只是各负责一个信仰,但背后还有更深的纠葛。据吴说,张的父亲和他父亲本来是一起做法事的,吴父比张父要多得些香米,后来张父跑出去干,是个“叛徒”,没有法名。到了他们这一代,吴QT和张YW都是道师,但村里百分之九十的家庭需要做法事都会请吴,村民们也证实了这一点。
刘克崮认为,对收入高、中、低等人群的划分,应采用国际通行的五等分法,即在样本总量中的高、中高、中、中低、低收入五类人群各占20%。为了更直观解释这一观点,刘克崮拿出笔,在纸上画了一条直线,并分成了5等分,而15%显然占据着高收入人群的最前端。
二、巴岱、道师、仙娘
道师吴QT的父亲是巴代象兼巴代扎,也是道师。吴父去世后,家里的巴岱祖师神龛并没有撤,所以吴QT要经常祭祀,否则祖师没吃的就会来家里找麻烦。因此之故,巴岱都要设法一代代传下去,如果不传,家里就会有灾殃。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自己一旦去世,也归入祖师的行列,没人接替就没有吃的。火炉坪村一组的巴岱象吴YL已经七十多了(1947年生),身材高大声音却比较小,患有严重的心脏和气管疾病,面色苍白,经常住院。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没人愿学巴岱,所以他也面临传承的焦虑。
截至目前,山水集团在境内发行的71亿元债券中尚有45亿元未进行兑付。此外,多数债权银行对山水集团信贷业务到期的处理也大多采取展期或借新换旧方式,若山水集团贷款形成不良,将对债权银行到期贷款续作造成较大不利影响,同时对其他债权银行履行债权银行公约造成一定障碍。
热闹,也是巴岱和道师竞争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巴岱做法事只需要一个人即可完成,乐器也比较单一,巴代扎用铜铃,巴岱象用竹鼓,声音都很小;巴岱象着寻常服饰,巴代扎在重要仪式上才着红袍。道师则是三五成群,唱念做打都有,铙钹锣鼓交响,还有色彩鲜艳的法袍与袈裟。巴岱做丧礼一天一夜即毕,道师则常常持续几天。相形之下,道师比巴岱做丧礼要热闹很多,排场也大,更迎合当下人们的需求。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丧礼不仅仅是关乎亡人的事,其排场和热闹更关乎活人的面子。有的丧家请巴岱的同时也请道师,他们并不关心内容,更看重形式上的隆重与体面。这种爱热闹的心理在无形中为道师在与巴岱的竞争中处于绝对的有利地位增添了关键的砝码。如此一来,巴岱的式微和道师的兴盛更是一个难以挽回的趋势。巴岱是苗族传统信仰,而道师属于佛教系统,是外来宗教。民族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传承人的责任,更需要民众的积极参与,民众才是根基。
由于历史因素,苏雪林与大陆读者一度暌隔将近半个世纪。从中国知网收录的资料看,有关苏雪林与外国文学关系的研究主要分为四个方面:
丧家爱热闹,所以多请道师,而道师则认为别有原因。据张YW说,道师请的是地藏王菩萨,巴岱象和巴岱札请的是太上老君;巴岱可以帮死人解开地狱绳索送到西天,道师则可把死人送到天堂,因为道师的神比巴岱大。也许正如吴QT所说,外人只是看热闹,他们并不关心也不明白法力高下如何分辨。但张道师关于法力的讲法似乎有些牵强:巴岱是道教体系,而道师是佛教体系,如何比高下?道教似乎并不是把亡灵送到“西天”,佛教也不是把亡灵送到“天堂”。据此看来,他纯粹是为了抬高道师、贬低巴岱而信口开河。这一结论与道师吴QT的讲述是吻合的:“他们(张YW)一伙人家里死的,百分之九十是我们做,我做师傅二十几年,他(张YW)才学几年。”[注]①2017年7月23日访谈。言下之意是说张刚入行,知之不多,技艺不高,连他自家人都不请他。因而张的讲述纰漏百出也是可以理解的。
仙娘是苗语音译,指走阴的人,男女皆有。火炉坪村有一个仙娘姓龙,自述因思夫心切遂学此技艺,通过七仙女的带领可以到天上与亡夫相会。她系初学,请的人不多。我们走访隔壁村巴岱象麻HS时偶然得知他夫人曾是仙娘,现在不做了。夫人不在家,麻表示那都是假的,没什么搞头。他的评述显然是有比较的,参照就是自己所从事的巴岱,即便如此,他对巴岱法事中的某些东西也是不确定的。比如,苗族传统文化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一般人已经不清楚了,七十岁的巴岱象吴YL还知道,据他说,人死后一个灵魂去天上,一个在坟地,一个在家里。而同为巴岱象的麻HS则表示不清楚。访谈中,很多时候他表示并不真相信他所做的法事是真的(有效),也不相信“咎留咎博”、“拿关拿勤”、“阴方大堂大殿”[注]②正常死亡的人去阴间的“咎留咎博”(苗语),那里很苦,要请巴岱追魂,找回来后送去“阴方大堂大殿”做官。意外死亡(上吊、自杀等)的恶鬼,要送去“拿关拿勤”(苗语),不许回来,否则会找麻烦,比如,吊死鬼每代要找一个人吊死。(2017年7月25日访谈麻HS),基本上只觉得是个传统和寄托。如此一来,神圣世界的悬置使得巴岱象的身份对于他而言只是一种职业,一个谋生的手段,与种地、打工并无多大差别,如果有差别,那也只是工种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那么,他与吴YL的竞争关系纯粹是“生意”上的,而无关法力高下,他所谓“高师出高徒”则是一个不攻自破的幌子了。也就是说,这只是他招徕生意的一个说辞,而不是真的有更高的法力,与村民所谓声音更大而更受欢迎的讲法暗合。那么,他口中所说他夫人的仙娘职业“没什么搞头”,恐怕也是从生意的角度说的,需要走阴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职业没有带来实际上的经济利益,所以他颇有些看不起,因为他的巴岱职业是可以实打实挣来钱的。他的生意不错,说经常忙不过来,还热情地邀请我们去观看他几天之后在某地要做的法事。
同一个村子的两个讲述者,对同一个故事的讲述差异如此之大,这不能不令人惊讶并且深思:这个故事的核心究竟是什么?在众多的变化之中有哪些因素是不变的?变与不变的原因何在?仔细考察,天王的神秘出身、神奇力量(力量/赤手空拳打三千、智慧/棋艺)、命运、成神方式在两个故事中是基本不变的,其他细节则是可以被增删演绎的。在吴道师的讲述中,天王故事更像一个虚构的传奇,似乎没有什么历史感,其功用主要在突出天王的神秘性。而张道师的版本则加入了乾嘉苗民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并且让天王扮演了重要角色,如此一来,天王的神圣性就获得了历史的基础,比张道师的版本更有现实性。这一历史—现实基础的获得并非无关紧要,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大部分由人而神的神祇被神化的重要基础。汉族“重实际而黜玄想”[3],其所亲近的神祇大抵都有历史原型,香火鼎盛者尤其如此,关公、岳飞是典型。苗族“信巫鬼,重淫祀”,其信仰的核心祖先崇拜所祭祀者也都曾是活生生的人。
吴道师负责的龙凤庵在二组马路对面的山顶上,山陡峭险峻,经四道门才能上顶。第四道门处有灵官像,旁边有山神土地和香客留下的锅碗。据张道师说,这里曾是“炸油锅”之地,把仇家放在滚开的桐油锅里慢慢炸。然而,当我们向村民求证时,无论老少均表示从未听说过此事。那么,张道师极力突出该地的阴森恐怖,似乎有拦阻别人的意思。从二人的关系来讲,这一推测是很有可能的。有意思的是,当二人在位于一组的小学里碰面,同桌吃饭,却互不招呼。张道师保持了一贯的高调风格,插科打诨让人唱苗歌,吴道师则默默吃饭,吃完便静静离开。
三、天王庙
很多人认为鸭溪天王庙是总坛,据说这里的塑像最雄伟,还有配殿供奉龙公圣母(三位天王的亲身母亲)。庙门外摆着些卖香烛的摊儿,进到里面是一个大院子,右边是算命兼卖香烛的商店,出售很多两三米的“高香”,左边是大殿,殿前搭了些架子,上面烧了不少高香,浓厚的烟味令人呼吸不畅。好不容易摆脱卖香的掮客,进得殿来,三尊天王雄踞其上。一对夫妇在一个五十来岁的妇人指引下抱着一支点燃的高香跪在天王面前,妇人站在供桌旁替他们问神,每事问毕便打卦。我们仔细观察她打卦,发现她基本可以控制卦象,也就是说想要什么卦象便能打出什么卦象。当她希望得出顺卦(一阴一阳),她就贴着供桌打卦,很容易得出一阴一阳的卦象;当她希望得出阴卦或阳卦,她就从高处抛下,经常会从桌上弹到地上,变化的几率就很大。比如,她代求钱财、平安等事,就贴着供桌打卦,基本都是顺卦;代求子女婚姻,她就从高处抛甩,顺卦的几率就小很多,于是她就告诉香客夫妇,要常来烧香敬神才会更顺利。仔细分析求问的事项与卦象的关系,不难看出她控制卦象的事实及其原因。钱财、平安这些是比较抽象、长远的事,对于那一对在机关工作的夫妇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一般不会有大的变化;而子女的婚姻则是一个急迫且充满变数的问题,所以她在这一事件上施加影响,让香客相信只有不断来求天王才会更顺利,打卦者的收入就会因此增加。
我们致电管理火炉坪天王庙的张YW,他没有正面回应关于控制卦象的推理,只说:“鸭溪是总坛,信士很多,又没有专门的人主持,那些妇女帮人打卦问神都是义务的。”他所谓“义务”并不是指不收费,而是自发自愿的意思。虽然如此,把打卦妇女对卦象的控制和收入联系起来不是没有根据的。其一,当我们在殿门外与其他妇女(都是为香客收费打卦的)搭讪时,她们三句不离卖香,一旦表明不烧香,就不再理睬我们。其二,天王庙里没有专门的神职人员,所以这些妇女是“义务”服务的,但她们也靠此维生,因此她们希望不断有回头客来,这是可以理解的。
凤凰古城的天王庙也比较气派,一坡石梯上去,有天王正殿,还有观音配殿。正殿前的院子里有“同心锁”,挂着五彩的丝带,侧院还有“千年神龟”,商业化气息很浓厚。这个天王庙比较特别,庙里有常住的和尚,还有每日轮值的义工。进庙门有门卫,先登记,如是外省的游客,会有义工引导,简单的讲解后就转到凤凰城的风水上,说该地被龙脉环绕,而龙的心脏就在此处。然后带去拜天王,接着转入观音殿,这里才是重头戏。游客被要求按家庭依次跪在蒲团上。一个胖和尚在神龛旁坐着敲木鱼,眼睛频繁地环视殿内的游客。解说员让大家买红色开光锦囊,十元一个,然后带到一个小黑屋里请大师算命。套路基本是:先问个人情况,然后按此说某事不顺,要祈福消灾,捐钱点灯,不点难脱身。
关于天王故事,火炉坪村一组的张YW道师(当地天王庙的实际管理者)与二组村民吴QT的讲述差别很大。主干部分的显著差别就有好几处:首先,在张的版本中天王的母亲是“一杨姓媳妇”,吴的版本里则说是一个未婚的女子。其次,张的版本中,天王的亲生父亲没有出现,而吴的版本则详细地弥补了这一空缺。再次,谋害天王的罪魁以及原因都不一样,一个是皇帝因害怕三兄弟的力气,一个是湘西王因嫉妒三人的棋艺。最后,吴的版本中没有天王打仗这一节,但多了引水招亲这一出。
同村的道师吴QT对这一次判案却有不同的讲法,他补充了一些细节——张的父亲把天王塑像搬去为人判案,回来后瘫痪了。这是张YW所未曾提及也不会提及的,所以吴一再嘱咐我们不要讲是他说的。吴的表述并没有否定天王的权威,却揭露了张家“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首士”及庙祝地位,为理亏的人告阴状,因此自食其果。
四、天王故事
关于天王的传说,有很多种版本,虽然只在湘西有,几百年来出于各种原因的改写、添加、移植、变异已经让源头扑朔迷离了。不少学者试图探源,基本上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暂时搁置这个执念,对不同的版本加以对照,各种叙说之间的张力与错综却是颇有意味的。
据村民说,请吴YL的人不多,因为他声音小,别人听不清楚,很多人愿意去邻村请麻HS,吴是麻的大舅子。麻也是巴岱象,五十多岁(1961年生),身板结实,声音爽朗,常常笑得很开心。问及他与麻的生意,他说请麻的很少,原因是“高师出高徒”。麻并未谈及声音的问题,也许吴年轻时声音也跟身材相称,他强调的是技艺的高低,他之所以在竞争中占优势是因为技高一筹。也许正如吴QT所说,外行人也不懂,只是看热闹,所以声音小就不好,主人不喜欢,因为不热闹。
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这意味着协同治理将成为我国社会管理的一个重要治理模式。它所蕴含的妥协理性不但使“效率”这一科学技术价值得以彰显,同时,也在整个社会管理系统中有效排除了人们“感到受压、非人化和被疏远”[1]的心理。可见,妥协理性在社会和谐的实现中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在花垣县的赶秋节[注]①2017年8月7日上午在十八洞村举行祭秋活动,与此同时,还在县城举办了“苗族(蚩尤)文化高峰论坛”和招商引资、经贸洽谈、商品交易会。上,很多巴岱被召集到会场参加表演性的仪式活动。不仅如此,还有祭祀、椎牛、苗鼓等节目。有一个节目叫“绺巾舞”,一些穿着巴岱法衣样式服饰的学生拿着巴岱作法用的绺巾在舞台上表演。很多人对此提出批评,认为这是对信仰的亵渎,也是对文化的不尊重,地方政府为了商业利益而消费传统文化和信仰。在某著名苗寨的歌舞展演间歇,身着盛装的村民在一起谈笑,用苗语说:“你们把我们当猴耍,我们还把你们当猪吃呢。”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以非遗保护的名义成了供游客猎奇的“猴把戏”,而心知肚明的村民则在其中获取维生之资,各取所需。在这种消费与交换的过程中,信仰、文化的神圣性和严肃性被消解了,只剩下实实在在的利益。
一般而言,从编故事的角度,通常会选择跟吴道师的讲述差不多的方式;但从塑造神祇的角度而言,则往往会采取张道师的讲述方式。按常理,张、吴二位肯定对这两个版本都熟悉,但是他们却选择了不同的版本讲述,其中缘由何在?从前文对二人关系的讨论中,不难得出推论,依然是不同的权力和利益诉求在支配着他们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讲述。张道师负责天王庙的管理,主管天王庙的祭祀,作为一个神职从业人员(他同时也是道师),他自然知道怎样维护天王庙的权威与神圣,所以他的故事中历史环节是不可缺少的。而吴道师在表面上并没有否定天王故事,也没有明显地贬斥天王的神圣性,但他对天王故事历史基础的空缺化处理则起到了近似“釜底抽薪”的作用。缺乏历史—现实感作为基础的神圣性使得天王故事更像一个虚构的、缥缈的神话故事一般。二者不同的用心在故事的结尾可以窥见端倪:张道师的旨归在“供奉”,还清楚地说明了具体的日期,乃是其庙祝身份使然;吴道师则强调天王的脾气暴躁不适合求子,“求善要去庵里面”,就是他所管辖的龙凤庵,巧妙地将“供奉”的对象转移到龙凤庵的诸佛菩萨身上。吴道师给人的印象比较朴实、不善言辞,然而这一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实在用得巧妙,不动声色间就完成了移花接木。
有意思的是,版本的差异不仅出现在民间,“官方”对版本的选择也是颇费心思的。凤凰古城天王庙入口处,凤凰县政府2008年所立的“湖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三王庙(天王庙)”石碑上面刻着天王庙的官方介绍:“三王庙位于凤凰县城观景山麓,又名‘天王庙’、‘三侯祠’。建于清嘉庆三年(1798年),是凤凰厅同知傅鼐为实行‘剿’、‘抚’兼施政策时为祭祀镇压苗民起义立下‘赫赫’战功的杨氏三兄弟(封白面、赤面、黑面三王神)所修建的庙宇。辛亥革命时,凤凰爱国人士曾在此誓师起义,并庆祝革命胜利。在正殿墙壁上留下了革命标语和信条。三王庙占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由正殿、戏台、厢房等组成,它对研究我国宗教、文化、艺术、古代建筑及中国革命史具有重要价值。”
地方政府的官方介绍几乎完全从历史这个角度入手,这正好印证了上文对吴道师刻意隐去历史内容的推测。与火炉坪的民间版本比较,凤凰的官方介绍去掉了传说的部分,但这依然压抑不住想象的翅膀,庙里的义工解说员和导游对杨氏三兄弟的来历做了丰富而生动的想象,说杨氏三兄弟是杨家将杨六郎的后代。这一补充为杨氏三兄弟的出身找了一个耀眼的源头,与其他版本的“龙王之后”的说法功能相当,增加了他作为神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某种意义上,杨家将已经在民间被神化了)。[注]①虽然如此,这一想象其实危机四伏:杨家将对辽的抗击与清兵对苗民的剿杀在针对“异族”这一点上何其相似。这种想象明显不符合官方对民族团结的表述。无神论的政府和有神论的群众对天王来历的说法虽然不同,其背后的权、利逻辑是一样的。官方的介绍必然要祛除神话想象,民间则可以率性而为,对趣味、传奇、神秘、神圣的追寻是人与生俱来的禀性。地方政府所看重的不再是其神圣性,所以他对神话部分做了省略,只是从历史遗迹的角度进行推介,强调的是文化内涵,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教育意义。对于一些无法抹去的内容,则巧妙地通过标点符号(“”)的使用,以进步的立场将“剿”、“抚”、“赫赫”等刺激性字眼的歧视与血腥掩去,从而达到与意识形态所宣传的民族团结相呼应的效果。
除了历史问题,还有一个现实矛盾比较棘手:既然杨氏三兄弟是镇压苗民的刽子手,为何在苗区被供奉?今日的多民族国家如何表述它?无论苗族汉族,自古皆有“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4]的说法[注]②吉首大学退休教授隆名骥先生对于天王是苗族这一点深信不疑,他在论述时也引用“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强调情感的认同,说老百姓不会弄错。,苗族和汉族都重视祖先崇拜,汉族重血统自不必说,苗族在丧葬仪式上要梳理家谱,以此接通与祖先的关系才能魂归一处。天王在湘西信众甚多,苗、汉居民都信奉,那么,苗族怎么会祭祀一个外族的神、屠杀本族人的刽子手?首先,苗族的传说中,杨氏三兄弟就是苗族人,张YW的版本中说他们杀清兵“赤手空拳打三千”;不仅如此,早期研究者认为天王信仰的源头是苗族[2]。其次,根据苏棠棣的研究,各信众团体通常会对传说进行改造,加入了本民族的东西,让它为己所用,从而名正言顺。如此一来,被重新塑造的神祇可以适应该群体的权、利诉求,毫无龃龉。所以,当其他群体(汉人移民和士兵、土家人)也信奉天王时,必然要根据自己的需要重塑天王神话,加入本群体的因子。具体怎么操作呢?苏堂栋认为神话本土化有一套比较固定的程式:“采用‘挪用’与‘叙事化’的双重手法,把借用的或原创的事件与本群体中已经存在的符号和神秘历史融合起来,再加上别处而来的口传或文本元素,然后加入与本群体相关的地点、事件和共同记忆,完成神话的本地化[2]。”
离开了驻在部门党组(党委),光靠派驻机构是抓不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是前提,监督责任是保障。没有前提,就无从谈保障,两者相互作用、浑然一体。
五、结论
以上根据田野考察的访谈和观察,从权力与利益的角度对湘西苗族的信仰状况进行了讨论,尽可能客观地还原了当时的语境,从而揭示和描述了当地民间信仰背后所隐伏的权与利的逻辑。此一视角所带来的启示是,以信仰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逐渐式微,与人们将其当做谋利的手段进行消费不无干系,大到以非遗保护为名的文化展演,小至将信仰当做谋生之凭藉,莫不如此。长此以往,作为商品的文化,其内核会被销蚀殆尽,只剩下一副空壳。这也提醒我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不能以谋利为核心,而应该存着敬畏之心,怀着“为往圣继绝学”的态度,为我们的民族保存文化的薪火,从而“为万世开太平”,苗族如斯,整个中华民族亦复如是。
一个月后,奥匈帝国在德国的支持下,以萨拉热窝事件为借口,向塞尔维亚宣战。接着德、俄、法、英等国相继投入战争。
参考文献
[1] 姚亮.苗语电影《寂寨》的多重主题与当下关照[J].电影评介,2018(3).
[2] (美)苏堂栋.族群边缘的神话缔造:湘西的白帝天王信仰[J].民族学刊,2013(3).
[3]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12.
[4] 左丘明撰,蒋冀骋标点.左传[M].长沙:岳麓书社,1988:60.
EntanglementsofPowerandInterestsbehindReligions—AnObservationonHmongReligiousConditionsinWesternHunan
YAO Liang
(SchoolofLiteratureandMedia,GuizhouUniversity,Guiyang550025,Guizhou,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mong religious conditions in western Hunan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and interviews from field research.It describes and reveals the entanglements of power and interests hidden behind religions.It concludes that such consumption of culture directly causes the decadence of the cultures of ethnic minorities.
Keywords:Hmong;religion;Tianwang;Badai;Xianniang
*收稿日期:2018-10-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 亮(1984-),男,苗族,湖北利川人,硕士生导师,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苗族文化与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B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389(2019)01-0010-06
责任编辑:陈 潘
责任校对:陈 潘
标签:天王论文; 苗族论文; 这一论文; 湘西论文; 的人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苗学通史”(15ZDB113)阶段性成果论文; 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