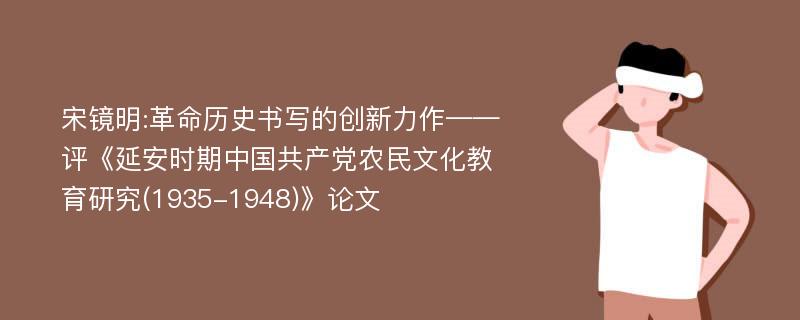
摘要: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文化教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也是近代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节点。中共从大革命时期到苏区时期再到延安时期,农民文化教育由边缘走向中心,农民革命由此具有真正的现实依托。从历史的逻辑出发,不难发现革命视域下的农民教育及其延安模式,具有与此前农民教育迥然有异的独特样态。如何从大历史观出发,同时兼顾历史微观的细节,探讨延安农民动员的历史密码,就显得尤为重要。贾钢涛教授的新著正是从农民文化这一视角尝试革命历史书写的典型范例。
关键词:文化启蒙;延安时期;农民文化教育
近年来,围绕延安时期的相关研究持续升温,无论是基于现实问题的回应还是以新史学的视野考察延安经验,都彰显出历史与现实难分轩轾的学术关怀。尤其是围绕20世纪30—40年代的陕甘宁边区革命史,学术界进行了较多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意义的成果。如周锡瑞、丛小平、秦燕、王建华、周海燕、杨琳、李静、沈文慧、杨东等人的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的生长。但毋庸讳言,论及延安时期中共农民文化教育的成果并不多见,更遑论系统研究的相关专著了。2018年12月,西安电子科技大学贾钢涛教授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1935-1948)》(以下简称贾著)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宋进指出这是“国内首部系统研究农民文化教育的专著,而且问题意识强烈,视野开阔,分析深刻,是一部优秀的党史学术专著”[1]1。该著以30万字的篇幅全面阐述了新民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延安时期中共是如何动员农民开展文化教育、如何实现“革命文化”目标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前人虽有关注但探讨不深,或是前人关注较少甚至没有探讨过的,颇值一读。
一、 革命史的再出场
随着拨乱反正的结束,延安时期中共历史研究也得到发展。在中央和陕西等省党史部门的支持下,各种历史资料的钩沉、搜集以及汇编工作得到加强,一些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得以公开发行。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历史档案的开放,极大地便利了学术界进行相关研究,也推动了党史研究学理化的进程。在此基础上,一些研究者尝试从不同视角对延安历史进行考察,出现了不少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学术著作贵在创新,而要有所创新,必须进行学术史的梳理及评介。对于该领域的代表性论文,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归纳,并指出这些论著总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毛泽东是陕甘宁边区文化建设的主导者、推动者,如戴知贤对中共抗战文化的考察:“以救亡为主题和国共合作为特征的抗战文化在区域分布上呈现出三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发展景观,分别是抗战时期的武汉,抗战中后期的重庆、昆明,孤岛上海以及中共控制的延安”[1]3;谢荫明指出:“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文化思想发展和成熟时期。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关于批判和吸收古今中外文化遗产的思想,关于知识分子要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关于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等等,都在延安时期得到了阐明和实际运用”[1]4;席文启指出:“延安时期,毛泽东总结了党在思想文化工作上的经验,站在更高的立足点上,提出建设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崭新的民族文化,把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结合起来,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1]4。二是延安农民文化与新民主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陈晋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文化基础上,在统一战线文化中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1]5;孙建娥指出:“包括延安时期在内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从理论上讲是中国共产党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创立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1]6;沈文慧认为延安时期文学语言的变化与农民身份的改变有密切的关系,焦金波也指出农民文化与延安时期知识分子的改造密切相关,“农民为主体的政治力量的崛起和文化期待的旺盛,也是知识分子身份变迁和角色转换的现实基础”[1]6。三是延安时期农民文化教育大众化。作者分析了黄延敏、李祥兴、尚子翔、尚微等人对延安农民文化的思考,认可他们提出的延安农民文化教育与中共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致性,通过农民教育实践,中共让外界了解到发展农民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所取得的重大效果。四是延安农民文化教育的微观考察。相对于宏大的叙述,微观考察更有助于洞察特定历史时期农民文化发展的独特面相。作者选取了边区农民文化教育的几个横断面,如对于关注度比较高的新文字运动,不仅选取了彭逢澍、胡现岭、王元周、王建华、秦燕等人的研究,进行了认真的学术史的梳理,而且进行了归纳分析,最后认为不能简单地将新文字运动的挫折归结为历史的误会,而要进行综合分析,回到历史现场去把握。对于社会教育的功能方面,作者也将自己此前的研究与学界同仁进行了对话,客观指出边区社会教育具有多重功能,不仅表现为识字水平的提高,而且对改变观念、建立新的社会共同体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教育的载体,作者对冬学运动、新秧歌运动、“小先生”制、“救亡室”等进行了考察,在评析学界相关研究时,注重从多学科切入,拓展了研究的视域,如对周海燕政治社会学解读冬学的关注、李静文化学对新秧歌的阐释以及崔玉婷对“小先生制”的教育史的梳理,征引规范,论证有力。五是关于边区农民文化教育价值的探讨,作者不仅引用了高华等人的研究,而且也引用了青年学者的见解,大家都一致肯定延安农民教育的巨大价值,“为战争和生成服务成为延安教育的基本精神”“广大民众积极参与乡村建设,边区逐渐实现了乡村民主自治。”这些列举都很有代表性,层次很清楚。
另外,作者还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这是十分可贵的。该著既有对斯诺成名之作的引用,也有对马克·塞尔登“延安道路”的评析,并重点聚焦延安时期民众动员和毛泽东农民观的考察,分别对海外中国史研究著名学者费正清、迈斯纳、施拉姆、约翰逊、贺大卫等人关于此问题的思考,呈现出域外学者的学术努力。
通过上述回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在以往的研究中,延安时期农民文化教育虽有涉及,但大多局限于新文字运动、冬学等,研究比较零碎,没有从整体上进行系统研究。事实上,边区农民身处文化荒漠,加之各种不利于文化发展的内外因素的制约,要想动员农民走出家庭、开展识字运动实属不易,对农民识字的动机的探讨当为一主要议题,这在现有的研究中多有体现,毋庸赘述,作者也做了比较好的梳理。但识字过程以及效果方面,诸如农民与教员、乡村秩序与党的宣传、传统文化与抗战文化等冲突却被遮蔽,缺乏必要的探讨。另外,在业已探讨的问题上,其考察路径也大多没有摆脱“政策—效果”的单向度研究框架。这种框架下,中共与农民之间只有简单的动员与被动员的关系,服从与被服从的选择,忽略了作为个体的农民所具有的复杂心态以及对中共政策的制约作用。
正是基于以上考量,在整体逻辑架构上,作者紧紧围绕“农民文化教育”这一主题,对延安时期农民文化发展进行了历时考察,充分阐述了在“抗战”和“建国”背景下,农民从家庭走向识字“集体”广阔空间的具体过程,谋篇布局环环相扣,整体论述逻辑严谨。具体讲,全书不仅对农民文化教育各相关环节的种种问题,如个人的动机、顾虑与意愿,各级组织的相关工作,党组织的动员以及模范农民的典型作用,作了入情入理的分析,对农民识字过程中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解读,还对农民文化教育的价值进行了探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理性评价。这一论述架构,缜密地再现了农民文化教育的几个关键环节,对几个重要运动之下的农民教育的生动场景进行了清晰的描绘,使得我们对革命年代中共如何争取农民、如何引导农民以及农民如何与中共同向而行等问题有了一个明晰认识。
二、 农民文化教育研究的创新
首先,研究选题属于学术前沿。该著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的结项成果,从选题来讲,比较新颖,也很有价值。正如作者所言,“农民教育是中共党史研究的传统领域,也是近年来比较受关注的学术增长点。”[1]1作者还进一步谈到,“如果说‘大革命时期’中共发现了‘农民’,‘苏区时期’中共团结了农民,那么,延安时期则是对农民进行了较为完美的形塑,为以后中共革命的凯歌行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1这些提法,也是很有见地的,符合中共革命的原貌。正是出于对延安时期农民教育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中共改造农民的独特路径,作者进行了历史的追溯和理论的反思,以纵横交叉、史论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深入研究。
知识库中的词语、短语、实体和属性需要先转换为数值表示(向量等嵌入表示)。之前的方法(如GenQA)随机初始化上述符号的数值表示,这种方法忽略了知识库内在的结构信息,不能够充分利用知识的全局表示(例如,谓词“出生地”和“出生地点”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符号,它们之间不能够相互共享信息)。为了获得具有全局信息的知识表示,首先使用无监督的方法学习知识库中概念的表示,使得相关的实体,关系和词在语义空间上更接近。
苏秋琴只有自己伸只手指头到癞阿小鼻子底下探了探,好像没有气息;这下苏秋琴慌了,急忙去剥他的牛头短裤。柳红就奇怪了,问苏秋琴你剥他裤头做啥?苏秋琴说我看看,她公公刚过世时,底下直翘翘的,过了好久才软下去。
对于一项学术研究来说,除了严谨规范的学术史梳理之外,还要有属于学术前沿的选题,资料、方法与观点的突破或创新。由此来看,贾著一书均有所突破:
将3组患者临床各项数据均输入SPSS 13.0软件中,3组患者各项检测结果均以(均数±标准差)的形式表示,予以t检验,组间对比统计学意义存在(P<0.05)。
1.4 稻瘟病抗性基因检测 采用 SDS 法提取水稻基因组 DNA。以基因组DNA 为模板进行基因片段扩增,PCR 反应体系参照范方军等[11]的方法。反应产物经 1%的琼脂糖凝胶电泳分离,溴化乙锭染色,在紫外凝胶成像仪上观察并照相。
最后,在相关问题上有新认识。谈到农民参加革命的原因,以往常见的是广大农民深受苦难,中共救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政策—效果”解释路径。该著用一段文字解释农民走向革命、中国革命与农民主体的内在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于,一是面对的敌人极其强大,二是革命的力量,尤其是工人阶级的人数极其少,这也决定了要想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寻找革命同盟军。农民阶级既有参加革命的内在诉求,也有消极保守的落后惯习,对革命积极性加以教育、改造,这是中共对农民这一革命同盟军采取的基本策略。毛泽东等人正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和农民的现状出发,提出并实践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农联盟理论,从而推动了中国革命不断发展。”[1]25然后,作者又从“唤醒农民群众,实现民族解放”,“教育广大农民,改造落后意识”,“联合广大农民,筑就共同愿景”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从中共与农民互动的角度,兼顾双方利益,让读者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农民走向革命的复杂背景。
当然,其他的一些理论和方法,该书也多有应用,并非一概放弃。比如,该书运用了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并根据具体实际借鉴了政治学、传播学、新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如此种种,使得该研究更为鲜活和丰富。
再次,在理论方法上有新突破。在学术研究中,占有资料并进行梳理,这只是正式研究的准备阶段,只有借助具体方法进行,才能在研究中取得突破、有所建树。有鉴于此,大多数学者都孜孜以求于研究方法的更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科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研究范式出现了新取向,社会史学、现代化范式、文化史学乃至乡村社会学等相继出现,部分学者开始与西方话语接轨,尝试运用西方学术界的计量史学、心理史学等范式等,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党史学科的繁荣。近年来,随着科际整合的加强,许多中青年学者从新文化学、新政治学、新史学等着手,深化革命史研究,在延安时期中共党史研究中也有所体现。贾著正是深受新史学影响,在保持党史研究优良传统的同时,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方法,对延安农民教育进行系统研究的佳作。贾著一改传统党史研究的基本套路,遵循新革命史研究的叙述逻辑,围绕“革命文化”这一中共文化建设的旨向,构建了一个农民文化教育延安模式的解释框架,呈现出特定历史背景下陕甘宁边区农民文化发展的基本面相。这种探究,既充分考虑到全书的主题,也涵盖了延安时期中共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不仅突破了以往专题史研究的思维藩篱,构建起新的研究理路,而且通过深入考察基层农民的动员实相,更为清晰地凸显出边区社会发展的综合效应。
在开展思政实践课的过程中,如何挖掘和传承高年级学生中的优秀品质,并做好老生带新生工作,一直是国内各高校领导和思政教师的夙愿。不少高校为此专门开设了思政实践课,并组织思政课教师和相关学工系统负责人开展专题讨论会,探讨如何开展以老带新的具体工作形式和办法。可见各高校对实施朋辈导师制的重视。
其次,在资料挖掘上有新发现。写作前后,作者搜集了大量的相关资料和有关论著,到延安、北京、南京、庆阳以及原陕甘宁边区所辖县进行走访,寻访历史见证人和延安学相关专家,到各图书馆、档案馆查找资料,从现代信息系统查阅最新进展以及时人的文集、年谱、回忆录、日记等资料。具体而言,一是运用了一些档案资料,既有公开出版的,也有未刊资料,从而为该书立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陕甘调查记》《老解放区教育资料》《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红色档案—延安时期文献档案汇编》等。二是运用了大量时任领导人,如毛泽东、刘少奇、高岗、李维汉、徐特立、林伯渠、习仲勋等人的文集、文选、年谱、回忆录等。三是运用了一大批当时出版的杂志,如《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共产党人》《解放》《中国妇女》《中国青年》等。除此之外,作者还参考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论著和有一定关联度的学术论文等。对以上资料和论著的征引,不仅运用规范、充满学理,而且增加了该著的厚重感。
作者对于乡村中农民精英的认知也有深入的探讨。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改造遵循文化教育与政治宣传融合进行,通过政治文化教育培养新的农村精英,从而逐步改变旧的乡村格局,使得中共意识形态在乡村真正落地。正如该著指出的,“经过系统广泛深入的社会教育,边区民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尤为重要的是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在乡村开始扎根,逐步建立了新型的乡村社会秩序”[1]91。而对于中共培养乡村农民文化精英,作者也指出了将旧文化人进行革命改造,使之发生蜕变,也是行之有效的办法。如该著提到的新正县劳动英雄惠海山就是将劳动与文化相结合的典范,绥德劳动英雄王德彪率领全村学文化等,“这种将识字与生产结合起来,劳动英雄转换为识字英雄的模式,不仅进一步实现文化教育的形塑功能,将农民改造为新型农民,而且以身边榜样的示范作用,促进了更多农民汇入识字运动的潮流,从而加快农村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步伐”。也应证了蒋南翔所指出的,这些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新人物,有光明的前途,“他们要成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担当者。”[1]160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一味地对这种乡村精英的产生方式进行全盘肯定,而是客观地进行了论述。“劳动英雄典型化、政治化,契合了中共发展生产以巩固政权的政治诉求的同时,也影响了劳动英雄及其家庭的日常生活。”[1]161
谈到延安新文字运动的曲折命运,作者进行了理性分析。其首先指出,就结果而言,它是一次不成功的文字改革试验。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加以全盘否定,而是谈到:“检视其发展的历史,尤其是三年大规模的新文字运动实践,我们不由得感慨,这场运动本身有太多需要发掘的东西。首先要承认,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文字改革,其目的是以革命的名义对民众进行文化扫盲,最终改变边区文化落后面貌的尝试。对于这场文字(文化)革命,我们理性地看待它的历史价值,那就是力图改变边区文化落后所做出的努力,尤其是大规模的新文字运动的实践,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际效果上,都对地处西北、远离文化中心的广大边区民众的一次文化洗礼,这是值得肯定的。其次,无论是运动的运行策略、实施路径还是实施效果,都带有浓厚的泛政治化和大规模的运动模式,而这种急风暴雨式的革命运作虽然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奇效,但从最终效果来看,则呈现出与初衷大相径庭的尴尬结局。最后,透视整个边区新文字改革,经验和教训都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汉字改革,也正是吸取了包括延安时期的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文字改革的‘延安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一段历史,也是中国革命亟须珍视的特殊遗产。”[1]112
对于新秧歌运动的研究,作者也有一些新思考。作者首先定位于“革命的秧歌”,从农民参与的广泛性、内容变革的政治性、宣传效果的有效性等方面,彰显出经过改造的新秧歌“实现了由边缘到中心、独乐到众乐的革命性转变。”[1]197在具体分析时,作者指出秧歌教育功能大于娱乐功能,对改造二流子、塑造乡村社会风气有明显的积极作用。其次,作者将革命文化与乡村文化的转换进行了分析,指出新秧歌的出场正是革命文化与乡村文化聚合的产物,“既有传统乡村文化与革命文化的深刻互动,更有革命意识形态的强力介入,从而使革命文艺寻找到理想的栖息地,中共文化政策最终实现了由提高到普及的成功转型。”[1]199最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双向互动,传统文化改造得以在乡土真正实现。“伴随《讲话》的发表及整风的全面推进,秧歌也经历了由‘秧歌下乡’到‘下乡秧歌’的转变,知识分子与民间艺术实现了真正的结合。在服务工农兵的大旗下,新秧歌主题的政治化指向,不仅在内容上体现和服务边区政府的中心任务,而且还承载着两个改造:对边区农民意识的改造和对知识分子及其文艺观的改造。”[1]203
三、 结 语
延安时期中共历史研究是一个深受国内外学者热衷的领域,也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中共延安十三年史,以往学者多从政策史的角度关注宏大叙事,较少从草根群众层面系统研究农民文化发展状况,事实上没有广大边区民众尤其是普通农民的支持,中共要在延安站稳脚跟,是几无可能的。处于历史学者的学术自觉和历史使命感,作者将目光投向陕甘宁边区广大普通农民,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文献中耙梳材料,试图揭开延安时期中共大规模开展农民文化教育的历史动因,“还原农民与中共之间互动的真实场景,再现那段特殊的峥嵘岁月。”[1]311正是出于这种人文情怀和史学担当,作者将选题聚焦于延安时期农民文化教育,但研究视野显然没有拘泥于这一时段,而是将视野投射到整个近代乡村建设的宏阔背景中,通过新史学“长时段”的浓描与深耕,让读者对延安时期农民教育在整个中国近代农村文化建设中的历史方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
诚然,贾著并非尽善尽美,但总体而言,这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也是延安学相关研究十分突出的一部创新力作,体现出作者深厚的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功底,必将推动延安时期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 贾钢涛.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民文化教育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InnovationWorksintheHistoryofChineseRevolution:CommentsontheStudyofPeasantCultureEducationoftheCommunistPartyofChinainYan’anPeriod(1935-1948)
SONG Jing-ming
(SchoolofMarxism,WuhanUniversity,Wuhan430072,Hubei,China)
Abstract:The peasant culture educ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in Yan’an period is a microcosm of the peasant culture develop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It is also a key point of the modern rural culture construction.While the CPC developed from the Great Revolution Period to the Soviet Area Period and then to the Yan’an Period,the peasant culture education progressed from the edge to the center.The peasant revolution had got the realistic support.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 peasant education and its Yan’an model in the revolutionary horizon have a unique form which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that in the previous periods.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discuss the historical arcanum of peasant mobilization in Ya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history and the details of micro-history.The new works of Professor Jia Gangtao is a typical example of the attempt of writing a new revolutionary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asant culture.
Keywords:cultural enlightenment; Yan’an period; peasant cultural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9-01-19
作者简介:宋镜明(1938-),男,湖南双峰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及毛泽东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D231;D422.63
文献标识码:A DOI: 10.3963/j.issn.1671-6477.2019.02.0023
(责任编辑 文 格)
标签:延安论文; 农民论文; 中共论文; 时期论文; 文化教育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