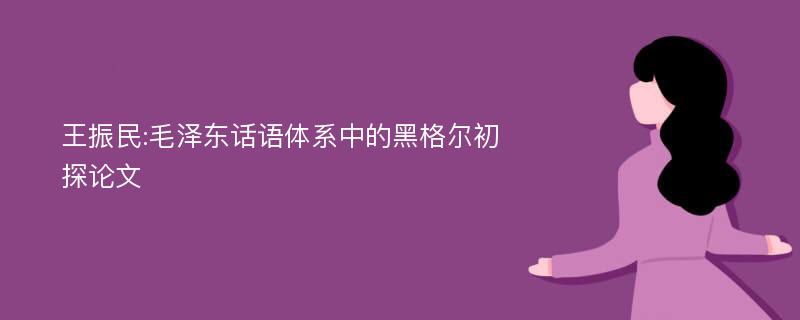
·人物研究·
〔摘要〕毛泽东与黑格尔有着长达几十年的、超越时空的思想交往。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的理论语境中,黑格尔的思想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黑格尔哲学或辩证法不仅是毛泽东青年时期改造哲学进而改造国民思想的理论武器之一,也是其在革命实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批判党内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理论质料,同时还是他晚年用以表述外交战略或国际政治思想观点,以及进行思想路线斗争的工具。
〔关键词〕毛泽东;黑格尔;哲学思想;辩证法;《矛盾论》
施拉姆(Stuart Schram)曾言:“寻求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嗜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注]Stuart R.Schram,“Mao Tse-tung and the Theory of the Permanent Revolution,1958-69”,TheChinaQuarterly,No.46,1971.在毛泽东辩证法的理论来源问题上,与国内学者主要集中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等内容不同,国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无论是从国外“毛泽东学”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来看,毛泽东以《矛盾论》为核心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一直是他们关注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例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与莱文(Norman Levine)分别基于结构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的理论视域提出了相互对峙的“断裂说”与“复活说”[注]参见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30页。;特里尔(Ross Terrill)和斯塔尔(John Starr)认为,毛泽东受到黑格尔思想强烈或深刻的影响[注]〔美〕罗斯·特里尔著,何宇光、刘加英译:《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9页;〔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著,曹志为、王晴波译:《毛泽东的政治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9页。;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则断言:“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动力的黑格尔哲学基本信仰全部被中国共产主义者吸收——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信仰一个历史性的拯救过程。”[注]〔美〕本杰明·I.史华慈著,陈玮译:《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63页。更值得回味的是,原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其回忆录中说,毛泽东把黑格尔视为他感兴趣的三个德国人之一[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大国》,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294页。。与施密特同行的梅奈特(Klaus Mehnert)也在文章中提到,毛泽东说黑格尔是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人之一[注]〔德〕恩斯特·海克尔著,袁志英等译:《宇宙之谜》,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译者导读”第3页。。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是民政部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发行和组织销售工作。李立国成为分管领导后,鲍学全挖空心思讨好。据鲍学全透露,时任民政部部长临近退休年龄,李立国作为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希望更进一步。鲍学全不断炫耀自己的“高层关系”,积极为李立国奔走,最终成为李立国的心腹爱将。
国外学者所言是否属实呢?国内学者的研究初步证实了其中一些论断。比如陈晋就从毛泽东读书史的角度梳理了毛泽东与黑格尔哲学大致的交往过程,并指出:黑格尔并没有缺席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成的理论准备过程”[注]参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贰),广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9—101页。。张仲民等则认为,从史实来看,无论是西方哲学在中国传播,还是20世纪30年代的新哲学运动以及“两论”创作期间,黑格尔的著作从没缺席过[注]参见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155页;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148页。。
国内对毛泽东与黑格尔关系的研究,整体上还比较粗疏。尤其就毛泽东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关系研究来说,对于“如何把握黑格尔哲学遗产在毛泽东《矛盾论》中的定位”这一重要学术问题,“在以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中却鲜有关注”[注]张明:《21世纪如何阅读〈矛盾论〉?》,《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之所以产生这种问题,应该与关于毛泽东为什么对黑格尔感兴趣以及黑格尔如何“涌向”或影响毛泽东的研究很不充分有关。本文试图以施密特与毛泽东的谈话为切入点,结合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与黑格尔哲学有交集的文本及其语境,对毛泽东话语中的黑格尔进行初步探究。
一、毛泽东国际政治理论语境中的黑格尔
毛泽东在和施密特谈论哲学时提到了两个让人相当诧异的人物——海克尔与黑格尔[注]对于毛泽东与海克尔的关系,笔者已经进行了初步研究。参见王振民:《毛泽东话语空间中的海克尔之谜》,《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期。。不过,与海克尔不同,黑格尔之所以让人诧异,不仅因为他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思想战线上是被严厉批判的对象,而且还因为毛泽东一方面说“理想主义(这里实质上指的是唯心主义——引者注)并不是好东西”,另一方面却坦言对黑格尔感兴趣。从二人谈话的内容看,可以肯定的是,施密特确实没有搞清楚毛泽东为什么会提起黑格尔。他只是回复说:“德国有些人把国家这个概念神秘化,他(指黑格尔——引者注)对此负有很大责任。”[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大国》,第294页。按:在另一本著作《施密特:与中国为邻》(海南出版社,2014年)中,施密特同样回避了黑格尔问题。其实,施密特还是不太适应毛泽东那穿越时空的哲学思维以及海阔天空、借古喻今的谈话方式,不太懂得毛泽东在与各国政治家交往时谈论哲学的重要意蕴,他只是觉得这些哲学问题已经“离题”了。但从毛泽东谈话的语境看,黑格尔绝不仅仅是一句外交上的托词,而是最起码具有双重深刻意蕴。
一是作为康德哲学“持久和平论”的对立面的黑格尔。当毛泽东说施密特是个康德派时——施密特本人承认他赞成康德的学说——他的寓意很清楚,即借用黑格尔对康德学说的批判,来批评西方对苏战略的乌托邦性质。这是因为在毛泽东看来,由于西方的威慑战略建立在“假设”,即理想主义的基础上,因而试图借此达到避免战争、实现欧洲和平的想法和做法也是虚幻的。如果联系自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尤其在珍宝岛事件之后出现的中苏关系严重恶化、越南战争爆发等情况的影响下,毛泽东对国际形势比较悲观的判断,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他为什么坚决反对“持久和平论”。毛泽东不仅多次提出“天下大乱”“要准备打仗”“山雨欲来风满楼”[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48、314、338、420、475、489、557页。,而且在多个场合明确提出“永远也没有”所谓的“持久和平”,“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01、521—524、554页。按:其实早在1964年,毛泽东在评注“和平是能够也应当被控制的”的观点时,也提出过类似看法。。的确,作为理想主义者的康德在谈论国家之间的关系时,就是设想“成立一种国际联盟,调停每一争端,以维护永久和平”[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95页。。此时,毛泽东话语中的黑格尔起着警示西方对苏战略的作用。因为在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永久和平仅仅是一种“饶舌空谈”而已。这不仅因为“国家是个体,而个体性本质上是含有否定性的。纵使一批国家组成一个家庭,作为个体性,这种结合必然会产生一个对立面和创造一个敌人……战争还是会发生的”[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第388页。;而且即使西方能“争取同莫斯科及其盟国建立睦邻关系,甚至是合作关系”[注]〔德〕赫尔穆特·施密特著,梅兆荣等译:《伟人与大国》,第294页。,这种做法和观念也“始终是以享有主权的特殊意志为依据,从而仍然带有偶然性的”[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第395页。。正是基于此,黑格尔“不唯论证了国际战争的不可避免性,他还指出战争是解决国际争端的唯一手段或唯一仲裁者”[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评述”第35页。按:从施密特的字里行间看,他是借反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来反对他所理解的毛泽东“迷信”战争必然性的观点。。
这是2018年7月底我去青岛参加钢琴艺术节时发表的观点。在7月30日那天,组委会给我安排了一个上午的“大师班”,共有五个学生,每人四十五分钟课,演奏一首参加过比赛的曲目,上课时间应是充足的。此时,我认为上课的重点在于音乐表现上的探讨研究和精益求精。当天上课的五位同学中,有四位都表现不错,弹奏的《皮黄》《八幅水彩画的回忆》的选段,以及《波兰舞曲》等都很熟练,并都有一定的音乐表现。因此,上大师课在探讨如何更好地表现音乐中顺利进行。
如图5所示,在同时添加5 mL乙醛(40%)、0.1 g乙醛脱氢酶和1.5 g余甘果果肉的情况下,分别测试不同温度下乙醛的降解效果,37℃时降解效果最好,其次是40℃,降解效果最差的是30℃,由此说明37℃是最适合酶和余甘果共同作用的温度。由于30℃是实验中较低的温度,所以相对于37℃、40℃而言挥发量减少,测定值比较高。可见,比最适温度高的温度不利于乙醛脱氢酶和余甘果果肉共同降解乙醛。
需要说明的是,即使确如有的学者所言,毛泽东强调要“准备打仗”,“很大程度上还是出于国内动员的需要。相信全国动员起来,一方面可以结束国内的混乱局面,一方面也可以对苏联的报复有所预防,有备无患”[注]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7页。,那么这与黑格尔所言的战争功效也有共通之处。因为在黑格尔看来,战争不仅使“特殊物的理想性获得了它的权利而变成了现实”,“防止了内部的骚动,并巩固了国家内部的权力”[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第386—387页。,而且“在战争中,国家的健康受到检验”[注]〔以〕阿维纳瑞著,朱学平、王兴赛译:《黑格尔的现代国家理论》,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第253页。。
当然,毛泽东不只想告诉施密特祈求永久和平是不可能的,而且还包括以下两层含义:一方面,欧洲要想在与苏联的较量中不吃亏,绝不能依赖美国,因为美国在战争开始后是不会保护欧洲的[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609页。。因此,欧洲只有联合成共同体,以自己为主才有希望。在这个意义上,海克尔的出现也并不突兀。因为根据海克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或者“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欧洲同样必须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基于一战的教训,西方不要试图以“推动苏联向东,推苏向华”的方式保证“西方无战事”。因为“苏联野心很大”,它针对的是“整个欧洲、亚洲、非洲”,谁也别想置身事外。其实在会见施密特之前,毛泽东就判断,苏联的主要战略重点在欧洲、中东,而不在亚洲。[注]参见《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441、469、498、534、580页。
3)药品质量标准变更后的发布渠道不统一,导致企业或检验机构等标准使用部门从不同渠道获取的同一药品标准,有的标准虽然标准编号相同,但标准内容不一致,为生产和检验带来不便。
客观来讲,黑格尔虽然是在哲学思辨的维度上谈论国家理论与战争问题,也有为资本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辩护的嫌疑,但他毕竟是以国家对内对外的同一性为基础来研究战争的本质,同时辩证地阐释了国家与战争、战争与和平的关系,说明战争不是一种“纯粹外在的偶然性”,而是带有绝对性与必然性,“把战争看成是人类历史中一种客观的、但在历史上瞬息即逝的阶段”[注]〔东德〕B.罗托、A.狄尔柏著,李黎译:《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论战争的本质》,《国外社会科学》1978年第4期。。可以说,在对国家与战争、战争与和平辩证关系的理解上,毛泽东、黑格尔和克劳塞维茨还是有共通之处的。在毛泽东看来,和平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战争是必然的、绝对的。他指出:“在现在的制度的条件下,把人分为阶级,建立国家,那就非打不可。”[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01页。按: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把社会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或帝国主义的存在,作为战争不可避免的原因。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曾解释说,“永远”不是一万年,只是讲一两百年。这是因为在他看来,革命的倾向会压倒战争的趋向。
其次是“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后的黑格尔。把哲学斗争混同于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把黑格尔哲学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这种“左”倾思维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已经初见端倪。不过,与在“批林整风”运动中彻底沦为“左”倾政治工具的状况尚有不同,此时的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完全政治化。具体来说,黑格尔在毛泽东语境中的价值要旨呈现多样性和复杂性。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合理内核”,即辩证法,依然被重视。只是其被毛泽东借用来指责刘少奇“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规律[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77页。。也就是说,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抓住的只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而忽视了黑格尔的矛盾辩证法[注]从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来看,一般认为在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和辩证方法的矛盾中,体系的保守性、反动性禁锢了辩证方法的革命性,矛盾统一的绝对性、斗争的相对性导致了矛盾的调和性,其发展观点最终陷入了形而上学。参见〔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6年,“编者前言”第7页。。从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哲学的体系和方法被毛泽东一分为二地挪借为“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的武器[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357页。。也只有在此意义上,才能理解为什么那时黑格尔的译著总会在前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流派和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者,总是死抱着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不放,或是歪曲黑格尔的辩证法(主要针对‘合二而一’论或‘矛盾调和’说——引者注[注]毛泽东在批判“合二而一”时,曾要求收集黑格尔阐释对立统一规律的材料。为了帮助人们批判地研究黑格尔辩证法,当时还曾将黑格尔著作中有关矛盾的论述进行汇编,其中不少小标题均与矛盾的普遍性、必然性有关。参见龚育之:《听毛泽东谈哲学》,《北京党史》2003年第6期;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编:《黑格尔论矛盾》,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4、263、283页。),借以攻击马克思主义。”[注]〔德〕黑格尔著,杨一之译:《逻辑学》上卷,“编者前言”第8页。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被作为突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性、革命性的参照物。当毛泽东对外宾强调“黑格尔的书也必须看”时,当他把黑格尔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并表示“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没有康德、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时,其用意不只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理论渊源,更重要的是明确“不读唯心主义的书、形而上学的书,就不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指认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斗争的持久性[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518、313页。。
二是作为克劳塞维茨战争哲学基础的黑格尔辩证法。毛泽东把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和世界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相提并论,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的放矢。众所周知,毛泽东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颇为赞赏[注]参见夏征难:《毛泽东研读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新诠》,《党的文献》2006年第2期。。而《战争论》与黑格尔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列宁就指出,克劳塞维茨在“思想上曾从黑格尔受到教益”。可以说,“战争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即暴力的〉手段的继续”[注]《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66页。这一重大论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克劳塞维茨运用黑格尔辩证法基本原理的产物。在《战争论》中,无论是阐释从绝对战争向现实战争过渡时所使用的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还是运用以事物的发展和内部联系为核心的辩证发展观来研究现实战争,都可以从中看到黑格尔辩证法的痕迹。特别是克劳塞维茨运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矛盾观对政治与战争、偶然与必然、物质因素与精神力量等关系的阐释,很容易引发熟悉黑格尔—马克思辩证法的毛泽东的共鸣。其中,黑格尔辩证法对克劳塞维茨论述进攻与防御关系的影响就很明显。[注]参见敬恩:《谈谈克劳塞维茨战争学说中的辩证法思想》,《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毛泽东和施密特谈话时,也是通过防御战与进攻战的辩证关系和历史事实来说明防御战的重要性。
目前确定合理桩间距时,各算法都做了不同的假设,例如:赵明华等[9]认为桩间仅形成桩后土拱,忽略桩侧土拱存在(方法1);郑磊等[11]认为桩间仅形成桩侧土拱,忽略桩后土拱存在(方法2);邱子义等[12]考虑了桩后、桩侧土拱同时存在,却忽略由桩侧面摩阻力提供给桩后土拱的抗滑力(方法3)。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黑格尔在毛泽东的外交语境中发挥着“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作用。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只是毛泽东对黑格尔“感兴趣”的原因之一。如果联系1975年之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黑格尔在毛泽东话语中出现时的历史情境,可以发现,黑格尔在毛泽东政治哲学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二、毛泽东政治哲学语境中的黑格尔
首先,关于众所周知的毛泽东接触黑格尔的两大间接路径。一是苏联的哲学教科书[注]主要包括西洛可夫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米丁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以及《新哲学大纲》。。这些著作虽然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联哲学论战“总清算”之后出版的,但并未像斯大林那样简单地把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它们不仅比较客观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而且基本阐释清楚了列宁在《哲学笔记》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解读[注]关于毛泽东在写作《矛盾论》时是否阅读过列宁《哲学笔记》的问题,学界尚有争议。霍勒布尼奇认为,毛泽东可以获得《哲学笔记》的两个部分,但是他指责列宁对黑格尔辩证法存在误解。黎永泰认为,毛泽东阅读过《哲学笔记》中的《谈谈辩证法问题》。莱文指出,《矛盾论》深受《哲学笔记》的影响。许全兴则认为,毛泽东不可能看到《哲学笔记》。参见Holubnychy V,“Mao Tse-tung’s Materialistic Dialectics”,TheChinaQuarterly,No.19,1964;黎永泰:《毛泽东同志对哲学的学习和倡导》,《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美〕诺曼·莱文著,张翼星等译:《辩证法内部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17页;许全兴:《〈实践论〉〈矛盾论〉研究综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3年,第119—120页。。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著作或论文。其中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注]据黎永泰考证,毛泽东在此期间阅读过这篇文章。他指出,该文早在1924年就发表在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第76期上,由李大钊翻译,原名为《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1934年,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68期又译载了这篇文章。但是从《李大钊全集》来看,李大钊译文的发表时间应为1926年5月。参见黎永泰:《毛泽东同志对哲学的学习和倡导》,《西南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李大钊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4—113页;王东红:《李大钊译述文章〈马克思的中国民族革命观〉考略》,《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7期。一文中对黑格尔的对立统一规律作了充分肯定,认为其是“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或者说是“万应的原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78页。。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注]陈晋认为:“在马恩著作中,毛泽东读得比较频繁的厚本书,当数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事实上,毛泽东在晚年还把《反杜林论》作为恩格斯的代表作,并因此提出,恩格斯的“画像是应该挂的”。参见陈晋:《风云途中 阅读与实行革命》(下),《新湘评论》2014年第11期;《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57页。更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历史功绩、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关系,以及黑格尔哲学体系与辩证法的矛盾作了比较清楚的说明。虽然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曾批判和否定黑格尔的绝对唯心主义,但他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性。这些知识在毛泽东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确实得到了延续。比如毛泽东指出,辩证法唯物论在辩证法层面,“不但继承了唯心论的最高产物——黑格尔学说的成果,同时还克服了这一学说的唯心论,唯物地改造了他的辩证法”[注]〔日〕竹内实主编:《毛泽东集补卷》(5),苍苍社(东京),1984年,第195页。。在《矛盾论》中,他更简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的部分”[注]《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3页。。张仲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较之蒋介石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推崇与使用,中共领袖毛泽东则有过之而无不及。”[注]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第154—155页。按:这里可以摘引蒋介石对黑格尔哲学的一点心得:“黑格尔所谓矛盾之理,即中国阴阳之道,黑格尔所谓绝对存在与绝对本原,即中国太极咸具万物之理也。”不考虑蒋介石的解释是否正确,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国人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解往往采用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类比的方法,可以说是“以中解西”的思路。虽然毛泽东是否也是如此理解黑格尔辩证法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不过斯塔尔认为,毛泽东所掌握的辩证法具有一种独特的“中国特征”,即在黑格尔和马克思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对西方哲学传统的一种新颖的否定和超越的地方,毛泽东却在中国背景下,在这些思想所冲击的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生机勃勃的共鸣中,发展了这些思想。参见〔美〕约翰·布莱恩·斯塔尔著,曹志为、王晴波译:《毛泽东的政治哲学》,第11页。
在此不得不提及毛泽东评价黑格尔时说的一句话,因为学者们普遍忽视了这句话。毛泽东说:“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即客观的辩证法。”[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第313页。毛泽东把黑格尔辩证法称为“客观的辩证法”,这是口误还是有别的缘由呢?在笔者看来,这不仅绝不是口误,反而恰恰说明毛泽东还是比较熟悉黑格尔辩证法的。其时,不仅列宁的《哲学笔记》已经出版多年,中苏两国学界研究《哲学笔记》的出版物已达数十本之多,而且黑格尔的主要著作均已被译介出版。单从毛泽东晚年的读书情况来看,他所阅读过的黑格尔著作,尤其是与逻辑学相关的读物,至少有十余本[注]参见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90—495页;龚育之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18页。。如果结合毛泽东曾阅读过的《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内容,可以这样说,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指黑格尔逻辑学包含“最多的客观内容”[注]张世英:《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3页。,即黑格尔辩证法虽然是唯心主义性质的,但是其逻辑范畴充满了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中辩证法的客观内容。马克思就指出:“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的、现实的叙述。”[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0页。
面对严峻的形势,林洋多次主持召开会议,广泛征求职工意见,最终达成共识:在配合政府征地拆迁的同时,因势利导,初步理出了适合本单位转型发展的工作思路——将剩余土地转型发展,建日光温室大棚。他将上述工作思路形成报告后,上报了市政府和市国资委,赢得市政府大力支持。2011年,云城乳业“日光温室大棚建设项目”顺利实施,当年建起标准化日光温室大棚131座。
最后是作为两岸思想政治斗争中介的黑格尔。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一直把黑格尔哲学作为“反攻复国”的思想武器。也就是说,台湾当局把黑格尔哲学作为两岸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是把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作为反击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进行反共思想战“不可缺少的武器”,极力指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是“邪说”,“窃取”了黑格尔辩证逻辑的方法。当然,蒋介石也在不遗余力地反对黑格尔辩证法中的矛盾统一学说,并试图用“和谐互助的辩证法”去超越和取代它。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德国汉学家缪勒(Martin Müller)指出,两岸对黑格尔哲学采取了“一种平行关系”,即“最终感兴趣的并非黑格尔本身”,而是“把黑格尔辩证法与唯心主义哲学为了政治的目的而工具化”。如果说在台湾,它被当作对抗“共产主义唯物论”的精神武器,那么在大陆,黑格尔哲学则是“资产阶级哲学的敌对象征。”[注]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下),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3—905、909页。
首先是“批林整风”运动中的黑格尔。当时,为了反对林彪、陈伯达所谓的“天才论”等唯心主义观点,毛泽东根据他所认为的党内很多人搞不清楚什么是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判断,发出了读几本哲学史,包括欧洲哲学史(黑格尔哲学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的指示。此时,毛泽东话语中的黑格尔哲学具有双重寓意:一是作为汇聚人类理性思维重要成果的黑格尔哲学。不过,虽然毛泽东有通过在思想战线(包括哲学研究领域)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揭露和批判,以帮助干部群众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意图,但归根结底还是为了继续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注]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第174页。因而这层蕴意被弱化了。二是作为批判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工具的黑格尔哲学。此时,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政治上的保守性以及反动的英雄史观被强化。在“唯物主义进步,唯心主义反动”的逻辑支配下,由于被视为林彪“极右”路线的“老根”之一,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成了“封、资、修”的“大毒草”、帝国主义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思想温床,受到严厉批判。
当然,毛泽东也能从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评价中获得这一认识。列宁曾这样说:“黑格尔的确证明了:逻辑形式和逻辑规律不是空洞的外壳,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确切些说,不是证明了,而是天才地猜测到了。”[注]《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51页。这里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列宁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注]《列宁全集》第55卷,第151页。如果黑格尔逻辑学是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载体,《资本论》是马克思辩证法的集中体现,那么可以说,理解黑格尔辩证法是更好地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条件。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必须解决,即毛泽东在建构其辩证法理论,特别是撰写《矛盾论》时,黑格尔辩证法是缺席的还是在场的?在这个问题上,虽然莱文敏锐地观察到,黑格尔辩证法以列宁辩证法为中介,参与了毛泽东建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但他把马克思和列宁的辩证法完全黑格尔化,并以此作为解读毛泽东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前提,这无疑是有问题的。阿尔都塞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断然割裂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其实是矫枉过正了[注]杜娜叶夫斯卡娅、格拉贝曼等人虽然也主张“断裂论”,但他们在实质上与阿尔都塞的价值旨趣大相径庭。因为他们是以黑格尔化的马列主义辩证法为内在标尺解读《矛盾论》,并把《矛盾论》排斥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谱系之外。参见Martin Glaberman,“Mao as a Dialectician”,InternationalPhilosophicalQuarterly,8(1),1968;Dunayevskaya,PhilosophyandRevolution:FromHegeltoSartre,andfromMarxtoMao,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9,p.163;Dunayevskaya,“HegelianLenism”,TowardsaNewMarxism,Telo,1973,p.173.。事实上,早在革命时期,黑格尔及其著作就已进入毛泽东的理论视野,并成为其通达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理论质料。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黑格尔并不认为只要是民主国家就能避免战争,而是实际上赋予战争以否定性的力量。黑格尔战争观不仅初步体现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延续的观点之部分内蕴,而且其所内含的国际政治思想绝不像施密特所说的那么不堪。从黑格尔的法哲学理论看,他虽然主张政治领导优先于军事领导,但他同时认为,政治领导决不能懦弱到放弃采用战争暴力手段的信心和勇气的地步。当然,毛泽东说自己坚信会有战争,并不意味着他想发动战争[注]关于这一点,施密特的说法是正确的。参见〔德〕赫尔穆特·施密特、弗朗克·西伦著,梅兆荣等译:《理解中国——对话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海南出版社,2009年,第9页。。从那一时期毛泽东的言论来看,他的本意是以黑格尔关于“和平的可能性应在战争中予以保存”的观点[注]〔德〕黑格尔著,范扬等译:《法哲学原理》,第397页。来告诫施密特,不要被苏联的“到处讲和平”“到处讲缓和”所迷惑。因为按照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如果不做好打的准备,就可能从思想上解除武装,“将来要吃亏”。[注]《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第556、559、554页。可以说,在黑格尔以唯心主义辩证法建构的国际政治理论中,关于由国家的至上性、排外性或者独立自主性,以及彻底的无政府状态性质导致的有国家就有战争的思想,无疑是毛泽东表述中国外交战略、试图说服施密特放弃和平幻想的重要理论资源。
三、革命时期毛泽东与黑格尔超越时空的交往
国外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泽东的《矛盾论》或辩证法理论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除了莱文极力突出黑格尔辩证法对《矛盾论》的影响外,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也十分强调毛泽东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连续性。针对阿尔都塞把毛泽东所采用的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等新概念视为毛泽东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区别的标志的做法,列斐伏尔提出,虽然毛泽东对主要矛盾和从属矛盾基本区别的明确阐述“具有一种重大的意义”,但这个基本区别“没有改变辩证法的步调”,因为其早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就已经存在了。列斐伏尔甚至认为,毛泽东在其各种文章中提出的认识、意识和社会的螺旋发展等问题,以及从一般到特殊、从特殊到一般等重要观点,也明确存在于黑格尔的思想之中。[注]〔法〕亨利·列菲弗尔著,李青宜等译:《论国家——从黑格尔到斯大林和毛泽东》,重庆出版社,1988年,第241—243页。不过,由于掌握的文献比较有限,这些认同毛泽东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之间存在关联性的西方学者,并没有阐明黑格尔著作如何多向度地涌向毛泽东。为此,笔者试图在陈晋等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以及毛泽东的相关历史文献,进一步探索这一问题。
如果说毛泽东在1975年会见施密特时所论及的黑格尔还基本符合黑格尔哲学要义的话,那么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毛泽东对黑格尔感兴趣的主要原因就不在于黑格尔哲学本身了,其侧重点是把黑格尔哲学作为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具体来说,黑格尔哲学的政治功能不仅体现在充当了两次思想政治路线教育的工具,而且成为海峡两岸思想较量的着力点。虽然黑格尔的价值意蕴在此期间有所差异,但总体上来看,毛泽东是以斗争哲学思维来批判性解读黑格尔哲学。
会计信息体统以计算机为基础,对当前的数据分析更加的快捷、便利。传统的管理模式无法适应当前信息系统的发展,阻碍了其加快的步伐。而云计算的优势便由此日益凸显。在提高管理信息时效性的同时,节省了大量的空间,缩小了内存,提高了信息的安全性能。不可避免的是,网络时代的发展使得众多资源共享。由此,不良商家为了顾及个人的利益,通过一些非法的手段以谋取个人利益。后果不堪设想。综上而言,要积极的定期对此类事件进行排查,可以在一定晨读上保障信息的安全状况,同时,完善健全监督机制,实现信息安全化的发展。
其次,关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史。黑格尔哲学经由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译介、批判、阅读和使用,业已化身为中国知识仓库中的思想资源。事实上,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因为黑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特殊的理论渊源才真正开始的。[注]参见孙江、陈力卫主编:《亚洲概念史研究》第2辑,第156—157页。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对康德哲学的深入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推动黑格尔哲学传播高潮的到来”。特别是国内文化界“自1928年至1937年的10年间,共发表有关黑格尔哲学的论文100余篇,这在当时传播的哲学家中是最多的”。[注]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第8页。这也为爱读书的毛泽东了解黑格尔哲学创造了条件。从1965年斯诺同毛泽东的谈话来看,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是斯诺为什么只问毛泽东读过黑格尔的书没有?如果联系斯诺初赴延安时的疑问——“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注]〔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3页。——以及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比如杜娜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阿尔都塞、霍勒布尼奇(Vsevolod Holubnychy)等人对《矛盾论》与马克思—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论争,可以发现,斯诺也在潜意识里把是否了解黑格尔辩证法视为毛泽东能否把握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理论条件。二是毛泽东不仅承认在1937年写作“两论”之前看过一些黑格尔的文章,而且明确指出是在打游击战争的时候读的[注]参见《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06页。。这与黑格尔哲学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间段恰好高度吻合。虽然毛泽东读了哪些书还需要考证,但其中有两本书值得注意。一是周谷城在1934年翻译出版的《黑格尔逻辑大纲》。在该书的序言中,周谷城指出:“黑格尔的逻辑,与辩证唯物论的关系似已成为普通常识了。为图正确而精深的研究辩证唯物论起见,黑格尔的逻辑,有介绍之必要。”[注]〔德〕黑格尔著,周谷城译:《黑格尔逻辑大纲》,正理报社,1934年,“序言”第1页。二是共产党人沈志远的《黑格尔与辩证法》[注]虽然学界公认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32年,但对书名的说法却略有不同。杨河、邓安庆认为是《黑格尔辩证法》,沈骥如、黄见德则认为是《黑格尔与辩证法》。结合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的文献资料,笔者在此采用后一种观点。参见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第10页;沈骥如:《沈志远传略》(下),《晋阳学刊》1983年第3期;沈骥如:《沈志远三十年代对黑格尔的研究——对〈我国的黑格尔研究评述〉一文的补充》,《复旦学报》1985年第4期;黄见德:《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12、615页。。此书是一本比较系统地用马列主义学说解读黑格尔辩证法的著作,这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是很难得的。沈志远在书中一方面对黑格尔哲学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黑格尔是创造现代革命宇宙观的先驱者。因为他的方法论、辩证法,是这个宇宙观的魂灵;不管黑格尔的出发点如何不对(客观或绝对唯心论的出发点),可是他的辩证逻辑的革命作用,确是空前无匹。”[注]沈志远:《黑格尔与辩证法》,笔耕堂书店,1932年,“绪论”第3页。另一方面,他说明了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区别与联系,阐释了辩证法与认识论、方法论以及黑格尔辩证法与列宁辩证法的关系。当然,毛泽东之所以阅读黑格尔著作,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重视黑格尔,特别是黑格尔辩证法,有着紧密关系。
最后,关于毛泽东阅读过的德波林文本中的黑格尔。无论是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还是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都对德波林派的“主观主义”、德波林的“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机械论”,特别是差异是否是矛盾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可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却说,他在苏区受排挤期间,别人给他的“狭隘经验主义”称号,“对我有很大帮助,读了几本书”,其中“德波林的《欧洲哲学史》,就是打水口期间读的。原来不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什么东西”[注]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贰),第99页。。在此先要加以说明的是,德波林并没有写过《欧洲哲学史》这本书,倒有一本《近代哲学史》[注]参见〔苏〕德波林著,林一新译:《近代哲学史》,黎明书局,1934年。。但如果按照陈晋对“打水口”时间的解释,《近代哲学史》又不符合条件。按时间以及内容来看,德波林的《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注]参见〔苏〕德波林著,林伯修译:《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南强书局,1932年。倒比较符合陈晋的说法。当然,由于这两本书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注]《近代哲学史》和《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最大的差别在于后者有德波林的第三版序言,其他内容大体一致。这两本书的确论述了从培根到马克思的欧洲近现代哲学发展史。,所以毛泽东记错书名,倒也情有可原。如果把时间推后至红军长征之前的话,毛泽东不仅可以看到与《欧洲哲学史》名称相近的《近代哲学史》,也有可能看到1933年版的德波林《伊里奇底辩证法》[注]〔苏〕德波林著,任白戈译:《伊里奇底辩证法》,辛垦书店,1933年。按:在此书中,德波林从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对立物的同一、普遍与特殊等方面对列宁的辩证法作了简明的解读。他把对立物的同一视为“世界与人类认识的根本法则”,认为“所谓跳跃,连续性的断绝,到反对物的转化,由量到质的推移及其逆,都只能从对立物的统一上来说明”。。这里仅对《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加以说明。虽然德波林写作此书时(1907年)在政治上是孟什维克主义者,但他在当时的俄国还是一位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此书中,德波林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内容、方法之本质(“超越的思维,是作为以内面的矛盾为媒介而发展和运动着的逻辑的概念而思维着自己”)、本质规定(自我扬弃或自我否定,并且向对立面转化)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原理(不是凝固了的不变的存在,而是生成;绝对精神的运动构成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基本逻辑结构等都作了比较清楚的说明。同时,德波林还对黑格尔辩证法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区别——倒置着的唯物论,以及新唯物论(辩证法唯物主义)不同于旧唯物论的要点(吸收了观念论中内蕴的辩证法的方法,即关于发生、发展及消灭观察现象的方法)进行了解释。[注]〔苏〕德波林著,林伯修译:《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第278—287页。如果毛泽东所言不虚,那么德波林在驳斥伯恩斯坦等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没有任何联系的观点时所说的“没有黑格尔哲学尤其是没有辩证法,我们便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注]〔苏〕德波林著,林伯修译:《辩证法的唯物论入门》,第341页。应该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从毛泽东当时阅读的价值旨趣看,德波林在“辩证法的唯物论与经验象征论”一章中对尤什凯维奇的经验象征论的批判,也会引起他的理论兴趣。
当然,毛泽东与黑格尔的思想对话并不限于此,他早在青年时期已初步接触过黑格尔。如果说毛泽东在革命时期接触黑格尔是为了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大众化,构建自身的矛盾理论的话,那么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黑格尔哲学在其致力于救国图存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则更多的是融会中西哲学之精粹、探索宇宙之真理的理论质料之一。国内学界对此已有研究[注]参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贰),第99页;冯凭:《试论新黑格尔主义对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美〕魏斐德著,李君如等译:《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269页。,这里仅增补一些内容。一方面,需要纠正的是,田辰山把马君武翻译的《赫克尔一元论哲学》当作黑格尔的著作,这是不对的(应为海克尔)[注]参见〔美〕田辰山著,萧延中译:《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不过,毛泽东极有可能阅读过马君武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唯心派巨子黑智儿学说》[注]马君武在文中抓住并颂扬了黑格尔哲学最有价值的东西——辩证法(他用“相反者相同”来概括之)。参见杨河、邓安庆:《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第39—41页。。这是因为毛泽东对斯诺说,他曾经“崇拜”梁启超,并对《新民丛报》刊载的文章“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注]〔美〕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红星照耀中国》,第116—117页。。另一方面,需要补充的是,杨昌济对黑格尔哲学的重要观点作过解读,具体包括:黑格尔哲学欲以绝对之原理来说明世界之现象的生成与发展;黑格尔著名的三段之辩证法内生于其哲学之理性发展之理法;从始一致到次对立,再到调和综合两反对物,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普遍法则;事物发展之动机、势力是矛盾,无矛盾则无运动、无变化、无抵抗;辩证法之不断演化过程终于绝对理念的形成[注]参见杨昌济:《西洋伦理学史·西洋伦理学述评》,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164—166页。。毛泽东从相关学者那里了解到的黑格尔哲学知识,或多或少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和《矛盾论》中有所体现。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毛泽东说黑格尔是影响他的思想或世界观的德国人之一,就在情理之中了。
四、结 语
从毛泽东与黑格尔的思想交往史看,无论毛泽东是在从唯心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思想嬗变的过程中,还是在投身革命后继续研读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延安时期恶补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进而实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国化的过程中,直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继续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过程中,黑格尔哲学对其哲学思想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具体来说,黑格尔在毛泽东不同时期的心路历程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并被赋予了不同的价值功能。黑格尔哲学,特别是杨昌济所推崇的新黑格尔主义,是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向西方寻求真理,用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进而“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以达到治学济世的目标时,可以借助的重要理论资源之一。尤其是黑格尔哲学极为重要的“自我意识”概念及其所推崇的精神能动性,在毛泽东当时“大杂烩”式的唯心主义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以至于在其晚年错误思想中折射了出来。
在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投身革命实践后,黑格尔哲学在不同阶段亦具有不同的镜像。在革命初期,一方面,作为观念史观,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是毛泽东批判的对象。另一方面,作为“终结了从前玄学研究事物的方法”的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思想,是毛泽东吸收和借鉴的对象[注]参见李维汉:《观念史观批评》,《新时代》第1卷第4号(1923年7月15日)。按:从内容来看,李维汉是从进化论的视角,即“连续的进化”的“大根本思想”,来介绍黑格尔辩证法的主要思想的。陈晋认为,李维汉这篇文章的观点,应当说是他和毛泽东、蔡和森等人长期以来对黑格尔哲学“共同讨论、共同研究”的成果。。20世纪30年代以降,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成为毛泽东更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参照物。特别是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毛泽东13次提到黑格尔,而且强调了经典作家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批判性改造。无怪乎弗朗西斯·苏(Francis Soo)认为,虽然毛泽东的辩证法体系与黑格尔完全不同,但他的矛盾概念还是具有“黑格尔的特点”,即主张“矛盾是辩证的否定过程中的一个动态环节”、矛盾概念“包括中介或扬弃过程”。而中介或扬弃不仅是黑格尔矛盾概念或辩证法的中心,而且也是黑格尔整个体系的中心。[注]〔美〕弗朗西斯·苏著,余瑞先等译:《毛泽东的辩证法理论》,内部资料,1985年,第119页。除此之外,像德波林一样,黑格尔在毛泽东此时的话语体系中有一种隐喻功能,即指向那些教条主义者。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毛泽东对黑格尔兴趣未减,还曾反对斯大林把德国古典哲学视为对资产阶级革命的反动的错误观点,也曾试图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作出新的阐释,但是,他不仅主要“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于黑格尔哲学的评价出发”[注]王树人:《散论黑格尔哲学研究——〈黑格尔哲学新研究〉一书译者序》,《哲学研究》1989年第9期。,而且主要是把黑格尔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提高党员群众路线斗争觉悟的靶子来看待的,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把黑格尔哲学过度政治化了。
总之,黑格尔及其辩证法始终在毛泽东内心深处留有一席之地。不然,他在1975年说自己对黑格尔感兴趣,就难以理解了。探究毛泽东与黑格尔的思想交往,有利于更好地回到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发展脉络中,深化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
(本文作者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西安 710127)
APreliminaryStudyonHegelianTheoryinMaoZedong’sDiscourseSystem
Wang Zhenmin
Abstract: Mao Zedong and Hegel had decades of ideological exchanges that transcended both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Mao’s theoretical lens during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Hegel presented a variety of value functions. Hegel’s philosophy of dialectics was not only one of the theoretical weapons in Mao’s transformation of philosoph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thought during his youth but also part of his understanding Marxist dialectics i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his criticism of party dogmatism and empiricism, and his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Marxist dialectics based on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n addition, it was also the tool Mao used to express his diplomatic s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ought and to struggle against the ideological line during his later years.
〔中图分类号〕A841;D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9)-06-0082-11
(责任编辑 赵 鹏)
标签:黑格尔论文; 辩证法论文; 哲学论文; 施密特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欧洲各国哲学论文; 德国哲学论文; 《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第6期论文; 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