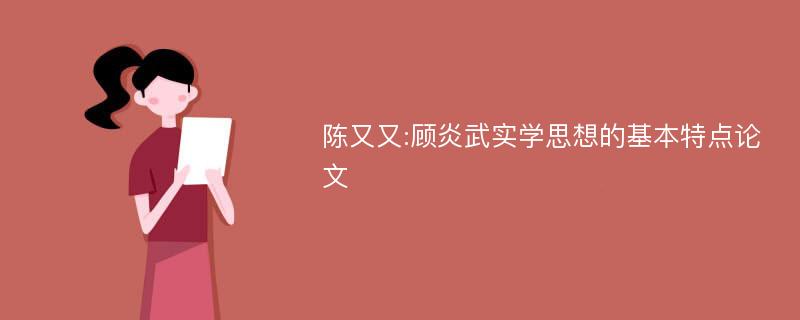
[摘要]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三大儒”之一,其哲学思想虽不及王夫之和黄宗羲,但是他所推崇的实学思想及方法至今仍值得我们继承与弘扬。顾炎武的实学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其实学基本特点则主要概括为三个方面,通过顾炎武实学思想的这三个特点,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顾炎武的实学思想。
[关键词]尊德性;道问学;博学广师;实知实行
通过前人对顾炎武实学思想主要内容的研究进行总结比较,可以将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基本特点概括为三个方面:首先,顾炎武主张“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这一特点是他针对王学末流的空疏学风所提出的;其次,博学与广师结合,这一特征是体现在顾炎武的整个求学过程中的;最后,实知与实行并重,这是顾炎武在其求学过程中广泛的实践所力求的。本文将从这三个方面探讨顾炎武实学思想的基本特点。
一、“尊德性”与“道问学”统一
关于尊德性和道学问的关系,顾炎武是主张二者统一的。他认为“能求放心,然后可以学问”[1]。这表明他是以尊德性为本的,但是顾炎武所谓“德性”,即“天之所命而人受之”的“性”,在内容上却根本不同于孟子所谓的“性”。孟子把“仁”“义”“礼”“智”都纳入“性”的范畴,这就否定了它们必须通过后天的“学”才能“知之”;与之相反,顾炎武则根据自己的见解阐发了《孟子》的“微言大义”,指出:“《孟子》言:‘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下文明指爱亲敬长。若夫因严以教敬,因亲以教爱,则必待学而知之者矣。”[1]按照他的看法,“求放心”就在于“省察此心,使克伐怨欲之情不萌于中”[2],以达到德性的自觉——了悟到“天之所命而人受之为性”的意义在于天命人以正行,而“予迓续天命,人事也”,从而自觉地存心于正行之事而不失其正行之性。此即顾炎武尊德性之底蕴所在。
一、我们营业部里的男人只有三个,除了我和小丁,就只有嘎绒了,他是塔公本地人,四十好几,正是有胆识和计谋干坏事的年岁,而且他还时时惦记着别家的女人,估计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顾炎武看来,学知不过是为了实现主体的正行之心罢了。由于他把“行”当作“知”的目的,其“行”便同时具有“知”的归宿和意义,因为“行”作为“知”的目的仅当“知”转化为“行”时才能最终实现。从顾炎武下面这段论述可以看出,其认识路线是从“学”“问”到“思”“辨”再到“行”的:“有弗学,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在“学”“问”“思”“辨”“行”中,“行”是“知”的最高阶段,是“知”的归宿[3]。
第一,互联网+视域下大数据需要管理会计具有数据分析思维。管理会计主要是为企业决策听过数据化的信息内容,随着互联网视域下大数据的发展,要求管理会计能够为其他的发展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信息参考。因而要求管理会计能够制定贤弟会计制度,从海量数据中尽可能的挖掘到各种有价值的信息以供互联网视域下的企业发展。
不过,在四十岁以前,顾炎武的博学多闻尚主要局限于书本。至四十岁,他始醒悟“丈夫志四方,有志先悬弧。焉能钓三江,终年守菰蒲”[5],感到有必要“游览天下山川风土,以质诸当世之大人先生”,于是从四十五岁开始了其“北学于中国”的生活历程。在此期间,顾炎武“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其出游“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这十多年“广师”的认知交往经历,使顾炎武深切体会到:“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2]
何谓“上达”?《论语》有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乎 !”皇侃义疏道:“下学,学人事;上达,达天命。”这个解释未必贴切。《论语·宪问》曰:“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杨伯峻解释说:“君子通于仁义,小人通于财利。”顾炎武也基本上是从“通于仁义”的意义上来理解“上达”的,故而有“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之说,这表明了在他看来“上达”最终是体现在“得其为人”上的,而儒学意义上所谓“得其为人”,无非是说通达圣人之道(仁义之道)而身体力行之罢了。按照顾炎武的看法,要通达儒家的仁义之道,必须学习“诗书六艺之文”,因为“非器则道无所寓”,儒家仁义之道不外乎“诗书六艺之文”,它就在其“文”中,故曰:“文,道也。”“非器则道无所寓”,是顾炎武主张“下学而上达”,以“下学”为“上达”的前提和基础的哲学根据[9]。
二、博学与广师结合
顾炎武将读书提高到认知交往的水平上来重新认识它的意义,把它理解为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这就赋予读书以新的内涵,即读书本质上并非个人私事,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社会性的活动。这种新的读书观对读书人——“君子”提出一种新的要求,即应当为社会的利益和需要而读书,而不能仅仅为了追求个人的名利或者只是出于个人自娱的需要抑或修身养性之目的而读书。顾炎武的读书境界之高于当时举子、文人之处,恰恰在于他对读书的性质及其意义有着与众不同的新的认识、新的理解,因而能自觉地把读书同整个社会、国家联系起来,为利益天下而读书,所谓“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8]。
顾炎武渊博的学识和扎实的学风虽在当时广为学界所推崇,但他绝没有“天下第一”的骄矜,更没有丝毫文人相轻的陋习。他总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对同时代其他学者的长处采取虚心学习的态度。他把思想僵化看作横在追求真理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认为“学者之患,莫甚于执一而不化”“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主张“问道论文,益征同志”。他十分欣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句话,主张治学要“不存门户方隅之见”“不求异而亦不苟同”。他引用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说法,表示:“非好学之深,则不能见己之过;虽欲改不善以迁于善,而其道无从也。”这种以“广师”为特征的学习方式和态度,曾使顾炎武在与朋友交往中受到很多有益的启迪。
由于顾炎武看到明末王学泛滥而流于禅释,乃至于“语德性而遗问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同,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之实学”[1],因此他尤其推崇“道问学”的规范,在《日知录》中也处处体现出他对“道问学”的重视。顾炎武说:“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显然,顾炎武这里所讲的“志”,乃是指其“救世”的抱负——这是其德性自觉的本质表现;“业”则是指其“明道”之成果——这是其问学功力的集中体现。所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恰恰道明了《日知录》乃是充分地展示顾炎武“尊德性”而“道问学”的典范之作。
提倡“下学”,强调“学识广博”和“学有本原”,是顾炎武实学思想和实学活动的主要特色,但这尚只能说是其实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特点,因为从其实学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他并非是只讲“下学”,而是也讲“上达”。其《日知录》(三十二卷本)有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非器则道无所寓,说在乎孔子之学琴于师襄也。已习其数,然后可以得其志。已习其志,然后可以得其为人。是虽孔子之天纵,未尝不求之象数也。故其自言曰‘下学而上达’。”这里顾炎武所强调的依然是“下学”,说明“上达”必须以“下学”为前提和基础;然而,毕竟他认为“下学”是有待于发展到“上达”,这表明其未尝不重视“上达”。
针对宋明理学的性理空谈,顾炎武提出了“博学为文”的治学宗旨,认为“博学”的对象应包括两大知识部类:一是自然和工艺知识,二是社会历史知识。可通过这些知识的深入讨论,极大地扩大学者认识的范围。他为此身体力行,毕生广学博览,所学涉猎天文地理、哲学、史学、政治、经济、伦理、文学,乃至金石音韵之学,且著述宏富,著作有五十余种、五百余卷。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他详细论述列举了天文气象、农田水利、采矿、制盐、造船、航海、海战和内陆河流湖泊的水战等各方面的知识,足见其学识的博大精深,以及对社会重大现实问题的关注[4]。
三、实知与实行并重
式中:F—基于Vague集的综合评价结果;Fj—待评价对象对评语等级Vj 的Vague值评语;⊗—Vague集中矩阵相乘的运算符号;⊕—Vague集有限和运算符号。
顾炎武在提倡“博学于文”的同时,更提倡“广师”。在以往的顾学研究中,学者们通常只是注意到他的“博学于文”的思想,而对其“广师”思想则未予重视。实际上,“广师”思想恰恰是顾炎武认识论中最具时代特色的内容,它反映了超前把握时代精神的启蒙思想家们,已经在呼唤知识分子走出书斋而积极地拥抱现实生活、广泛地开展社会交往——这是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一种开放年代所应有且必须具备的时代精神[6]。顾炎武就正是把握住这样一种时代精神的新型思想家。因而,在他的认知交往观中,“博学于文”乃是从属于“广师”要求的。他说:“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古之人学焉而有所得,未尝不求同志之人,而况当沧海横流,风雨如晦之日乎?……或一方不可得,则求之数千里之外;今人不可得,则慨想于千载以上之人;荀有一言一行之有合于吾者,从而追慕之。”[7]他交友的原则是由近及远、由今及古,足见顾炎武是立足于现实来开展认知交往的。他把现实的社会交往视为一切认知交往的基础。照他的思想逻辑,不与周围人交往,就不谈上与远方人交往;不与今人交往,就谈不上与古人交往。换句话说,在他看来,读书仅仅是出于认知交往的需要,不交往则无需读书,因为读书的本旨不过是结交古人,向古人讨教(“古人与稽”)而已。所以,他所谓“博学于文”,其意义就不是一般的博览群书而已,而是“广师”意义上“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的认知交往手段。
如果把顾炎武晚年的实学思想和实学活动理解为是其实学的成熟形态的话,那么他的实学的另一特征就可以也应当被概括为实知与实行并重,即“下学而上达”。
顾炎武建立“实学”的目的之一,就是试图实现“尊德性”与“道问学”的统一。其“道问学”是以“尊德性”为前提和基础的,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如果说顾炎武五十岁以前所特别重视和强调的是“下学”的话,那么他在晚年则比较重视“上达”了。相对“下学”为治学途径、治学方法而言,“上达”则是治学目的、治学归宿。顾炎武在《与毛锦衔》中曰:“君子之为学,将以修身,将以立命”,所谓“修身立命”是就“上达”而言。所以,他在《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中对明末心学有如是评论:“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之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这里“实学”与“空言”对举,以“修己治人”为“实学”的内涵,与他在《与友人论学书》中以“好古而多闻”为“实学”的内涵是有明显区别的:“好古而多闻之实学”是着眼于“知”;“修己治人之实学”则是着眼于“行”重视对儒家仁义之道的实践,是顾炎武晚年实学思想和实学活动的主要特征[10]。
起点错、跟着错、错到底,以往,公检法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常常“配合有余、制约不足”,这是导致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侦查手段和司法措施的监督,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原则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防止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及违反法定程序的案件“带病”进入起诉、审判程序,确保有罪的人受到应有制裁、无罪的人不受追究。
“下学而上达”的特征意味着顾炎武实学具有“实知”和“实行”之双重意义——实知”是“下学”,是求“道”于“诗书六艺之文”;“实行”是“上达”,是体“道”于“修己治人”之实践。他在《日知录》(三十二卷本)中再论“博学于文”时,就讲到“谥法经纬天地曰文,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如有深浅之不同矣”,这乃是以“诗书六艺”的知识为浅层次的“文”,而以“经纬天地”的实践为深层次的“文”。这样的“博学于文”,其意义显然不仅是在于学诗书六艺之文,更是在于创经纬天地之业了。
以“下学而上达”为本质特征的顾炎武实学,反映了其以知为行的前提和基础、行为知的目的和归宿的知行统一观。这种知行观看起来颇似朱熹“知先行后”“知轻行重”的知行观,而其实它们之间是有着实质性差异的。顾炎武之“知”是博学多闻之知,其博学多闻作为认知交往实践,作为一种实学活动,本质上乃是征求共识的一种实证活动,故实属于检验知识真伪的实验范畴,它显然应该被理解为也是行的一种形式,只是这种形式的行不同于“天地”之行罢了 。“经纬天地”作为一种行,在顾炎武这里具有“行道”以“天下”的意义;它不是一种实验性质的活动,而是对经由交往实践得来的反映认识主体共性的知识的实行。顾炎武知行观中的这种思想是朱熹知行观所不具有,也根本不可能有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新思想,可将它理解为是顾炎武在形式上继承朱子知行观的同时,在内容上对于朱子知行观的一种创造性的发展。
根据费希纳的对数定律,Dehaene(2003)提出了数量觉察的神经网络对数模型〔12〕,认为主观心理数字线是以客观数量的对数函数压缩。主观心理数量级成正态信号分布,与线性模型不同的是,数量梯度变化是固定的。不同数量的心理数字的正态函数分布按空间对数形式排列,数量值越大,空间距离越紧密。其神经机制是,不同数量激活顶内沟(intraparietal sulcus)区域相应位置上神经元组合同时放电,形成各自的调谐曲线。所激活的神经元放电曲线是以对数刻度分布的,因此少量神经元就可完成大范围内数量的编码。
从顾炎武实学在明清实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特征方面看,其区别于明代阳明实学的主要特征是在于注重“下学”,强调基于博学多闻的知,是经天纬地之行的前提和基础;其区别于清代考据学的主要特征是在于注重“上达”,强调经天纬地之行是知的目的和归宿。不过,据实而论,在学术上,顾炎武终其一生所最恶其“乱”而竭力“拨”之的,是明代心学而其赖以“拨乱世,反诸正”的主要精神武器,端是“下学”。他正是借助于“下学”的力量来行其破“明心见性之空言”而立“修己治人之实学”的“拨乱反正”之事的。故应当说,重视和强调“下学”,提倡“好古而多闻之实学”,是顾炎武实学显示其为明清实学的一种具体的历史形态的主要特征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顾炎武著, 黄汝成集释. 日知录集释:全校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顾炎武. 亭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3]周可真. 顾炎武哲学思想研究[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
[4]沈嘉荣. 顾炎武论考[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5]顾炎武著, 华忱之点校. 顾亭林诗文集[M]. 北京: 中华书局,2008.
[6]庞天佑. 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J]. 史学月刊,1999 (4).
[7]谢国桢. 略论明末清初学风的特点[J]. 四川大学学报,1963(2).
[8]顾炎武著. 亭林余集[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9]周可真. 明清之际新仁学——顾炎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
[10]周可真. 论顾炎武哲学的个性特点[J]. 人文杂志,1999(4).
[中图分类号]B24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292(2019)02-0009-03
[收稿日期]2019-01-13
[作者简介]陈又又,苏州科技大学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责任编辑张建国]
标签:实学论文; 顾炎武论文; 德性论文; 思想论文; 博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清代哲学(1644~1840年)论文; 《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苏州科技大学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