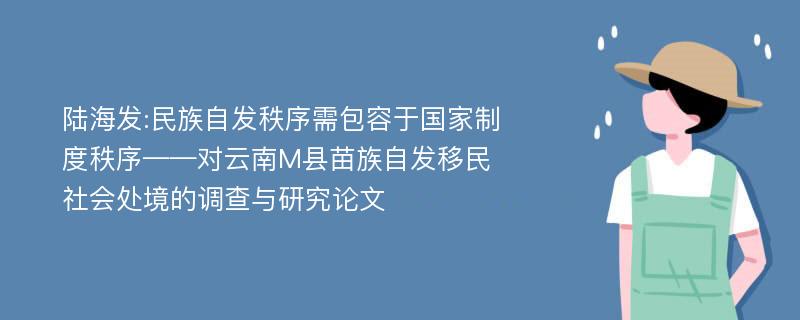
摘 要: 苗族自发迁移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通过对云南M县的田野调查发现,其在地域选择、居住格局及迁移的深层动因上,都深受苗族传统游耕式农业生产方式以及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但是,这种基于传统生计而形成的民族自发秩序难以在现有的国家制度秩序下获得合法性支持。苗族自发移民也因此在经济生活、政治权利、公共服务分享甚至社会心理等方面陷入了社会边缘的处境。为了促进其融入主流社会,必须释放国家制度秩序的包容性,以实际措施增进其现代适应性。
关键词:苗族自发移民;自发秩序;制度秩序;包容性
在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口的自发迁移不仅发生在北方的游牧民族,也发生在西南的山地民族中。北方的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的生存方式不仅保障了游牧人口的繁衍,也孕育了独特的草原文明。在南方,一些山地民族为了获得可以耕种的山地,他们往往从一座山翻越到另一座山,过着“逐山地而居”的游耕式生活。而另一面,随着民族国家制度逐渐成为世界体系主导性的国家治理制度形式,很多与之相伴的法律秩序和资源配给方式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也正处于加快推进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进程之中,这一国家进程必然会对生活在中国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各个民族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境遇等产生广泛而深入的影响。苗族自发移民问题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突显出来的现实问题。
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乃至90年代,自我国逐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生活在西南边疆的很多山地民族,仍然保留了其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延续下来的游耕式农业生产方式,其中尤以苗族为典型。他们沿袭着自发迁移的传统,在山地与山地间迁移,并未自觉到由此所引发的社会后果,特别是其自发秩序与现行国家治理制度的现实冲突。为了探索这种基于传统生计而引发的自发秩序与国家制度秩序的关系,我们于2018年2月对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进行了田野调查。通过深入实地观察、访谈等方式,笔者获取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力求探索问题的生成逻辑及破解之道,以供学界及相关政策实践者参考。
一、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的现状与特征
(一)基本现状
M县隶属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省东南部,国土面积2 228平方公里,地处云南低纬高原,属亚热带季风气候类型,主要地形以山区为主。根据《2017年M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17年全县户籍总人口为41.48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25.05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比重为60.4%。据M县政府统计的资料显示:M县有苗族自发移民135户 648人,主要聚居在其所辖的WL镇、YG镇和CB镇。
定义与分别为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中间产品的名义价格刚性,其意味着任意时期t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各自仅有与比例的中间产品价格得以调整。与Calvo(1983)相同,我们设定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中间产品的价格依据交错方式调整。定义和分别为耐用品部门与非耐用品部门中间产品替代弹性,与分别表示耐用品与非耐用品的最优价格,那么和可以表示为:
但实际上,王维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画家。尽管目前公认出自他手的画作还没有一幅能确定是他的真迹,但这对于我们这并不重要,因为我们真正关注的,是那画中如诗般的意境。
WL镇有苗族自发移民45户230人,主要集中在LML村、GTZ村(地名)、XJS村,他们大多是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由M县所辖的LQ镇、ST乡以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建水县迁入,部分则来自云南省内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等地。YG镇的苗族自发移民主要居住在MX村,有56户258人,多数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屏边苗族自治县、个旧市以及M县所辖LQ镇等地迁入。CB镇苗族自发移民主要集中在XG村,有32户150人,多数是在2012年左右从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迁入。XAS镇有苗族自发移民2户10人,一户居住于HJZ村,是上世纪80年代末由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屏边苗族自治县迁入,另一户居住于SQS村,是90年代初由M县所辖LQ镇迁入。具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11.2.5 转段:间苗后,会出现相邻两个灵芝相连而长到一起的情况,需要转段。转段时不要用手触摸灵芝菌盖。
表1:M县苗族自发移民人口分布基本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M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提供的《M县自发搬迁苗族反映问题情况报告》(2018年2月7日)整理。
然村) 户数(单位:户) 人口(单位:人次) 总人口(单位:乡镇 村社(自人次)LML村 29 145 GTZ(地名) 11 58 XJS村 5 27 YG镇 MX村 56 258 258 CB镇 XG村 32 150 150 XAS镇 HJZ村 1 6 10 SQS村 1 4总计 135 648 648 WL镇230
(二)主要特征
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相对于其他移民类型而言,不仅在迁移的地理空间选择、居住格局上表现出民族特性,并且,其迁移的动因也区别于一般移民类型,深受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显现出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
1. 从迁移的类型来看,这是一种特殊的山地农业型移民。这些苗族自发移民中的大部分,在户籍所在地主要是依靠在轮歇的火山地上种植苞谷以及在住房旁圈养牲畜为生,到了迁入地后,无论是自己开垦荒地或者林地,还是依靠租种当地人的土地取得生存资料基本保障,其生活基本都在山区,虽然有部分苗族自发移民外出务工,但从其所从事的工种来看,也是以农业生产为主。
苗族素有“高山苗”之称,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逐步具备了适应山地生活的本领,同时也有乐于山区生活的一面。他们能够在相对封闭、艰难的山地环境中,充分利用山地资源,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在生存、发展难以为继的时候,一种适应山地的本能与本领,又会诱使他们从一块山地迁到另一块山地,迁移之后的他们总是能很快适应山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从而形成了具有典型山地农业型移民的社会文化特征。
这些工作主要是在DH系扩展繁殖阶段完成。在选择过程中,要结合上述育种所制定的目标和具体的育种方式,对玉米的重点现状进行有效筛选,从而在玉米扩繁阶段和组合鉴定阶段,将六成以上的不合格DH系淘汰处理,这样可以显著降低后期育种过程中各个组合配合授粉和组合鉴定的工作量,大大缩短了育种周期,减少人工和资金成本投入,提高有效组合鉴定的准确性。
他们之所以会形成聚族而居的居住格局,概括起来看,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这些苗族自发移民与迁入地苗族基于语言、宗教、生活习惯、生计方式等的相似性,能够便利其相互之间的交往、交流;二是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多是与迁入地苗族群众有亲缘、地缘等的联系,这种亲近感更加容易形成彼此的认同,找到心理的归属感;三是基于一些现实的利益需要。很多苗族自发移民之所以能够在迁入地获得生存资料保障,而且能够持续地在迁入村寨平稳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迁入地苗族群众中有他们的亲戚或朋友的帮助、关照。
如何破局?是率先抢占新一轮的风口进行升级,还是如昙花一现,被淘汰出局?如果想做大做强,把特肥当作事业来做,最后一定会迈向前者;如果只是临时侥幸分得一杯羹,在市场打混的搅局者,故事的结局一定是后者。
2. 从迁入地的居住格局来看,呈现出聚族而居的样态。大部分的苗族自发移民是与当地更早迁入的苗族杂居在一起,比如M县WL镇所辖的LML村、LQ镇所辖的MX村等。还有一部分苗族自发移民是自发聚居成村的,多是在林木资源丰富的偏远处。因为地处偏僻,刚开始迁入这些地方的时候,往往只有一两户苗族自发移民居住在一起,后来,在亲缘纽带关系等社会资本的影响和带动下,一些苗族群众遵循着先行者的迁徙路线,分享着其迁移的经验,逐步与其汇聚在一起。随着聚居在一起的人数越来越多,也就逐步形成了自然村落。只是这样形成的村落一般都难以获得正式行政组织形式的认可,是尚未被纳入行政建制的自然村。在M县WL镇所辖的GTZ村(地名)就是一个由11户苗族自发移民自发聚居而形成的自然村落。
3. 从迁移的深层动因来看,其民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影响甚大。苗族是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史上迁徙最为频繁的民族之一,也是饱经苦难最多的民族之一。历史上,苗族大规模的迁移主要是因为受到战争的威胁与政治的压迫,他们为了“逃避统治”①此处借用了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的说法,他把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历史概括为“逃避统治的艺术”。参见[美]詹姆斯·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王晓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而不得不躲进深山密林之中。为了在深山密林中生存下去,又必须要躲避中原王朝的军事威胁,他们不得不放弃原来在平原耕种的定居生活,在逐步适应山地生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适应迁移的山地生产方式——“刀耕火种”。所以,有学者经过研究后指出:“居住在山区的苗族人民,各地不同程度上倒退到原始农业的‘刀耕火种’,一般没有牛耕和中耕施肥习惯。”②编写组:《苗族简史》(修订本),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苗族群众已经形成了一种与“刀耕火种”的山地耕作相适应的经济和生活方式。③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尽管苗族农民不知道山地的海拔高度和土壤的酸碱度,但长期的山地生活使苗族群众能凭借几代人的生产经验,从这些植被生长的情况来判断自己的庄稼在此生长得是否茂盛。选择既定,便立即动手砍伐烧荒,接着就是迁居。参见王慧琴《苗族迁徙原因新探》,《思想战线》1993年第3期。他们的房屋、服装、生活用具、习俗、传说、歌曲或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都无不与山区环境有关。逐步形成的山地生存方式,在历史演变与发展进程中形成了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也同时成为其不断迁徙的深层根源。
下面是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的部分访谈记录:
肝硬化是多种病因导致肝细胞变性,坏死,肝脏纤维结缔组织增生、再生结节形成的慢性肝病,自发性细菌性腹膜炎(spontaneous bacterial peritonitis,SBP)是失代偿期肝硬化患者的一种严重并发症[1],其发病机制是由于门静脉高压导致肠道菌群紊乱,使肠道细菌异位循肠系膜淋巴结进入体循环。SBP易复发、预后差[2],探讨肝硬化并发SBP易感因素及预后因素,对早期发现和积极防治SBP,提高失代偿期肝硬化治疗成功率极其必要。本文拟对136例失代偿期肝硬化合并SBP患者进行回顾性分析,为改善临床治疗方案、预后评估提供参考。
答:没人组织,都是自发的,自己想搬就搬了嘛。(根据调查资料整理,访谈时间:2018年2月6日。)
问:是什么原因让你们搬迁到这里的?
答:大部分人是为了讨生活。另外,我们苗族的老一辈也很喜欢搬家,小时候听说父母也经常性地搬。搬家也是我们的一种文化。我们整个村都是从外地迁移过来的。我们苗族很团结,大家约着一起搬,互相有个照应。我们刚搬到M县国有林的时候,也经常在国有林里面搬家,没有具体的在哪。搬家也很方便,看到哪边的山头没人住,条件好,就拎着自己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去,然后到大树或者山包的地方住下来,开始新的生活。
问:苗族同胞中的大部分人都这样吗?
鸨鸟肃肃地扇着翅膀,停落在桑树丛。 王家的事没了没完,稻梁全不能种植。 父母拿什么来吃?遥远的苍天呀!何时才能安定?[3]113-114
答:基本都是。我们觉得很正常,毕竟也是我们苗族的一种习惯。
随着时间的流失和客观环境的变化,现代社会所形成的法律秩序及所带来的资源配置规则与方式的大调整,已经迫使苗族自发性山地迁移的历史条件逐步丧失了。但它作为这些苗族自发移民的一种历史文化的惯性不会在瞬间消失。“无数事实说明,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的改变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不了解这一点,企图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杜绝和消灭游耕现象,那只是主观愿望,其结果不仅不能达到目的,而且还会造成一系列不良影响。”②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近年来,在农业相关数据采集工作中,采用PDA移动端设备进行数字化数据采集作业模式已受到广泛推崇[1-3]。
从以上的访谈内容中可以看出,苗族群众的自发搬迁并非仅仅受经济理性的驱动,而是与其民族迁移文化的惯性依赖密切相关。这些苗族群众在无法满足基本生存需要之时,他们只能继续着历史上战争与政治压迫造成的被迫性适应山地经济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式生产方式,走上迁徙之路——“历史上有因民族压迫和战争的逃亡,有鬼神观念的驱使,有躲避癌疫的搬迁,然而频繁发生的现象,却是为了改善生存状况,寻求可以很好从事刀耕火种的森林。”④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3页。
二、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的社会处境
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延续着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生计方式,不断从一块山地迁移到另一块山地。可是,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这种传统的生计方式所依赖的山林、植被已经有了明确的产权主体,其粗放的生产方式已经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绝大部分迁入M县的苗族自发移民都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也大都认识到,必须放弃原来“刀耕火种”的游耕式农业生产方式,走向定居农耕的生存、发展道路。所以,他们都非常期盼能够将其户籍迁入到现在居住的地方,结束其漂泊的生活形态。但是,因为其人口迁移的“自发性”特点,其行为没有得到政策的支持,也导致其社会身份处于“人户分离”的尴尬处境,不仅不能享受到国家很多政策红利,甚至部分基本公民权都因此而丧失保障,成为农村社会的一个边缘性群体。
(一)社会处境的现实:一个边缘性群体
边缘性群体一般是指一个相对于主流社会之外的相对稳定,但又与主流社会的人群在经济结构、收入水平、政治地位、文化生活等方面有较大差异而难以被主流社会所接纳的人群。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实际上是目前我国边缘性群体中的一种类型。他们的边缘性不仅体现在经济生活方面,也覆盖了其政治权利、公共服务分享、社会心理等诸多领域,成为一个尚未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群体。
1. 经济生活贫困。经济生活条件体现在经济收入水平、消费结构以及住房条件等日常生活的具体方面。这些苗族自发移民主要是依靠开垦荒地、租种土地为生,部分家庭会饲养牲畜,有的也会在农闲时间外出务工。但他们所开垦的荒地以及租种的土地往往都是山地,土地肥力极为有限,主要是以种植玉米为主,产量有限,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弱,产品的市场价格较低。他们所饲养的猪、牛、羊等品种都是本地的,养殖方式都相对粗放,带来的经济收益十分有限。
部分劳动力有时会外出务工,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所从事的劳动工种比较单一,往往是做建筑工人、农场工人等,所得到的劳动报酬比较低;并且,受到季节、气候等因素影响,其外出务工的工作也往往极不稳定,收入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从我们随机访谈的14户的情况来看,绝大部分家庭的年人均纯收入水平都低于3000元,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由于绝大部分苗族自发移民的收入水平比较低,而且收入来源也并不稳定,加上普遍存在的“超生”现象,导致家庭人口多,消费能力也就因此受到制约。其主要消费支出就是子女的教育以及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不仅如此,其住房条件十分简陋。在这些苗族自发移民聚居地,随处可见到各种用木板、石棉瓦搭建的简易房,属于目前政府所界定的C级、D级危房①依据住房城乡建设部制定的《农村危险房屋鉴定技术导则(试行)》(2009年3月26日),农村危房划分为A、B、C和D级标准。其中:A级:结构承载力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未发现危险点,房屋结构安全;B级:结构承载力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个别结构构件处于危险状态,但不影响主体结构,基本满足正常使用要求;C级:部分承重结构承载力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局部出现险情,构成局部危房;D级:承重结构承载力已不能满足正常使用要求,房屋整体出现险情,构成整幢危房。。
2. 政治权利虚化。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但是,在实际政治生活中,这种政治权利与户籍状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人户分离”的苗族自发移民,他们无法在迁入地实际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政治生活中,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绝非可有可无的权利,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利益诉求是否有代表,也关系到其基本利益保障是否能够得到正式权力机构的支持。由于在迁入地缺乏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其迁入地的地方政府从应然的政治逻辑来看,其行为主要是对选民负责,而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并非其选民,其利益也就难以得到迁入地政府的保护。所以,迁入地基层政府往往将其纳入“流动人口”进行管理。
利益表达是某些阶层、某个集团、某个群体或个体向政治体系提出利益要求的过程。苗族自发移民的利益表达渠道相对单一,其利益表达的效果也非常微弱。从国家利益表达的制度化渠道来看,国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度等,没有其选举产生的利益代表者,基层社会的群众自治制度、协商民主制度等也没有他们正式的参与渠道,即使在迁入地的地方政府专门针对其存在的困境推出的政策、措施,也没有他们的参与及利益表达权的充分保障。
4) 参考式(11)、式(12)、式(14)、式(15),对步骤3)得到的参数区间进行MDCFT处理,并利用最小波形熵法得到速度精确估计值vs,最后进行速度补偿后通过IDFT变换得到高分辨距离像。
不仅如此,这部分苗族自发移民在生存资料保障、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分享等方面,其利益诉求既不能得到户籍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的保障,也难以得到迁入地政府的有效回应——其户籍所在地的地方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往往以他们常年在外生活为由,对其正当的利益诉求搪塞推诿;在其迁入地的政府及基层自治组织也多以其户籍不在迁入地而建议其回户籍所在地办理相关事宜。这样一来,他们的利益表达被排斥于政治生活体系之外,成为了“制度外”群体,这种“集体失语”的尴尬必然会加剧其边缘性处境。
3. 基本公共服务分享不足。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这些年来,我国政府不断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特别是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条件都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对于这些苗族自发移民而言,其基本公共服务的分享却明显不足,不仅其聚居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滞后,而且所享受的各项社会权利(主要是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并不充分,国家出台的很多农村政策红利也难以覆盖到他们。
农村基础设施涉及道路建设、饮水保障、电路电网、农村文化、卫生等硬件建设。由于这些苗族自发移民没有迁入地的户籍,其所组建的村社自组织没有得到地方政府的认可,所聚居的特别是自发形成的村寨也没有纳入地方乡村的行政建制。从现行的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来看,这些苗族自发移民所聚居的村落的基础设施建设没有政策依据,无法争取政府资金的投入。因此,这些村寨的道路建设、沼气、水窖、危房改造、抗震安居、小水利建设、公厕、电网改造、文体设施建设等,都无法纳入地方政府建设规划,导致其建设水平严重滞后。
拟定预应力管桩混凝土强度等级 C50(EC为 3.45×104N/mm2),预应力钢筋采用钢绞线(1×7)(Es为 1.95×105N/mm2、fpy为 1 220 N/mm2),按照桩体受拉状态进行承载力及抗裂验算。为确保构件安全,轴向拉力设计值采用式(1)的计算结果1 189 kN。
不仅如此,其很多社会权利也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一是教育权利保障不充分。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家庭子女进入到高中学习阶段,其与迁入地有当地户籍的家庭子女在政策上会受到差别化对待,他们很难享受到迁入地政府所提供的相关奖励、补助及教育扶贫贷款等政策红利;二是社会保障不充分。这些苗族自发移民虽然大部分都属于相对贫困的人口,但并不能分享到迁入地的最低生活保障,基本上不能享受工伤保险等保障,也很少会得到当地民政部门所提供的各种社会救助。
“大不大的,咱们也得把理讲清楚,你们儿子想当光棍我们管不着!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我们筝筝说清楚?我们筝筝是传统女孩,恋爱的目的就是结婚,不结婚恋什么爱?谈了三年了,跑到登记处才悔婚,这做的叫人事吗?”辛燕晓绝不能让他们觉得好受。
同时,这些年,我国推出了很多惠农政策。其中,种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购置补贴等,是我国直接补贴的主要政策。但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却无法享受到各类惠农政策的补贴。政府各项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主要是依据其户籍及是否为农村常住人口并从事农业生产情况来确定,而这些苗族自发移民是“人户分离”的社会群体。既然迁出了户籍所在地,就不是户籍所在地常住人口,也就难以在户籍所在地享受相关政策红利;虽然是迁入地的常住人口却又不能把户口迁移到迁入地,便无法享有迁入地的系列支农惠农政策。
对于工程造价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落实,其存在的问题首先表现在信息化平台建设上,因为信息化平台建设不完善,无法形成较为流畅合理的管控效果,进而也就导致后续具体造价控制工作出现了较多的偏差失误。结合信息化平台建设工作在目前的落实状况,其存在的主要难题就是无法全方位明确所有工程造价管控任务,在流程以及管控目标方面存在混乱,最终容易导致信息化管控准确性受损。
当一个群体长期持续处于社会心理的疏离状态,产生了一种社会的“剥夺感”,其对社会运行的规则与政策秩序就可能滋生抵触情绪,就可能产生对现行的制度秩序乃至国家、政府等政治实体的认同危机。这种对既定社会秩序和规则体系的心理疏离甚至情绪抵触的长期淤积、沉淀,不仅会影响这些苗族自发移民的个体心理健康,也可能会成为其群体的一种心理定势,由此引发的社会心理可能会在一些具体事情的刺激下进一步加剧其剥夺感、失落感、挫败感,从而引发成为激烈的情绪性对抗行为,埋下社会冲突的隐患。
4. 社会心理疏离。社会心理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普遍感受和理解,表现于人们普遍的生活情绪、态度、言论和习惯之中。人们的社会心理状况最终取决于社会生活实际,直接形成于种种现实生活迹象对人们的刺激和人们的理解与感受。如果群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发展保持良性的一致性,呈现出正面的认知、情感与评价,这个群体就会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如果群体的社会心理与社会发展形成逆差,对社会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是消极的,那么,这个群体就有可能成为与其社会发展相对立的力量。
这些苗族自发移民在参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因为融入主流社会的努力受到了现实的阻滞,很多阻滞性因素又是凭借其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的。这种现实境遇的边缘化,使其对所置身的社会在认知、情感及评价等方面显现出相对比较消极的心理倾向。
此外,这种“人户分离”的尴尬处境,也使其游离于现行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体系之外。目前,从云南省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情况来看,其政策主要依托于其是否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果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可以得到国家在房屋建设、产业培育、大病医疗、子女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可是,在精准扶贫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其鉴定是否可以申请成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基本条件,就是有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如果没有迁入地的户籍,即使是常住人口,也是不能纳入精准扶贫的政策体系之内,也就无法分享精准扶贫政策的红利,由此使苗族自发移民成为国家精准扶贫政策体系覆盖的盲区。
(二)边缘性社会处境的根源:民族自发秩序与国家制度秩序的矛盾
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的边缘性社会处境,表面上看是一个社会群体遭遇国家制度秩序的排斥——因其迁移的“自发性”特点,难以获得既有政策制度及资源配给的支持,从而被排斥于权利保障及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之外,但实际上是一种基于传统生计基础上而形成的自发秩序与国家制度秩序的冲突,是苗族传统游耕式生计导致的山地自发迁移秩序与现有法律秩序及资源配给方式的矛盾所导致的现实结果。
虽然苗族群众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刀耕火种”的游耕式生计方式为其躲避政治压迫和军事威胁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且轮歇式的农耕方式在森林资源丰富的历史发展阶段,也并不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特别是民族国家制度秩序的逐步建立,森林、土地等产权制度随之也逐步确立,行政区划建制日趋规范,而且伴随着生态环境承载力的弱化,苗族自发迁移的传统生计方式所依赖的自然条件及社会条件正在逐步丧失。
正因为如此,绝大部分苗族群众都在这种“情景适应”的过程中,停止了山地自发迁移的步伐,走上了定耕的农业生产发展道路。而苗族自发移民的存在,很可能是苗族群众游耕农业生产方式延续的最后部分——他们虽然也有从事定耕的农业生产的主观愿望,但是其户籍所在地(迁出地)的生存条件过于恶劣,使其难以维持生计,不得不延续其传统生计方式,走上山地自发迁移之路。
虽然在我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后,部分国有林地及集体土地在管理过程中客观上存在“失灵”①这种“失灵”主要表现为国有林地管理的“失效”与集体土地管理“失责”。国有土地管理的“失效”主要在于林业管理部门如果依法严格管理国有林的森林、植被、林地,则会危及到一些苗族自发移民的基本生存,从而引发激烈的抵触和反抗。为了使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林业管理部门往往默许其开垦部分林地耕种;集体土地管理的“失责”主要是指在集体所有土地管理中对部分没有“包产到户”的荒地及部分集体林地并未明确具体管理主体的责任,也缺乏相关责任追究的机制,这就为部分集体林地和荒地被外来的苗族自发移民开垦种植提供了可能性条件。问题,这为苗族自发移民的生计保障预留了一定空间。但是,这种传统粗放的耕种方式在现代生态环境形势,以及以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制度秩序和资源配给方式的客观背景下,无法为其迁移行为提供合法性支持,建立于这套制度体系基础而形成的权利意识与利益观念也难以包容他们,迫使其深陷社会边缘的现实处境之中。
毫无疑问,产权制度以及建立在一定身份基础上并依托一定行政区划管理组织进行资源配给,是现代国家制度秩序的必然要求。但是,“民族国家的体制缺陷和政策失误往往导致对少数民族的某种形式、某种程度的剥夺,使之为现代化进程付出了过多的代价。”②宁 骚:《民族与国家: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4页。由此而论,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的边缘化,并非可以简单定性为是一个社会群体遭遇社会排斥的必然结果,而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生计方式遭遇国家现代化转型显现出来的一种危机和悲剧——“一种文化的衰落,实际上即意味着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人群生活出现重大危机”③何 群:《土著民族与小民族生存发展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88页。。
三、苗族自发移民的出路:包容于国家制度秩序
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的边缘化问题,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这个群体传统生计方式的生存空间还会进一步萎缩,定居成为其必然性的选择,由此导致的其与迁入地居民甚至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还会进一步加剧。在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为了实现各民族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完成国家治理的质的阶段性飞跃,必须理性认识和充分正视苗族自发移民边缘化问题,从根本上寻求破解这一问题的治理之道。
(一)正确认识苗族自发移民边缘性处境的性质
苗族自发移民是一个具有独特社会文化属性的群体,其迁移行为的发生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游耕农业生计方式延续的结果,其迁移的深层动因以及迁移活动所表现出来的地域选择(从山区迁往山区或者半山区)和居住格局,都烙上了民族文化的印记。因此,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种人口迁移活动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实际上就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于游耕民族来说,由生产方式所引致的迁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存的手段和形式,而是变成了一种文化传统、文化特质和民族特性了”。①尹绍亭:《远去的山火——人类学视野中的刀耕火种》,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3页。
访谈对象:余F,男,苗族,30岁,小学文化,M县自发移民。
问:你们的迁移有人组织吗?还是自发的?
在前文的探讨中,我们已经看到,苗族自发移民的自身处境深陷社会边缘,但归结起来,这实际上是苗族自发移民的传统生计方式与现代法律秩序与资源配给方式之间的紧张与冲突所引发的。因此,我们在认识这一社会现象的时候,不能仅仅站在现代法律秩序与资源配资方式的先赋性的合法性基础上,站在制度安排的制高点上对这一社会文化现象进行评判,也不应该从“优胜劣汰”的进化论视角对其贬斥,使其陷入道德伦理的失落境地。
作为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正在不断发展甚至崛起的多民族国家,一个依托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我们需要从最基本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社会现象:这实际上是民族现代化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不一致所引发的矛盾,是一个历史的遗留问题,是部分少数民族现代化进程与国家现代化进程失谐的结果。所以,对这一群体的认识,更多意义上应该释放的是国家制度秩序的善意和包容性——“在一般情况下,要想消除歧视,不能依靠民族独立,而只能依靠包容。”③[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7页。
(二)明确苗族自发移民融入主流社会中的政府责任
民族国家是各民族共同的政治屋顶,④这里借用了政治学者周平的提法,周平认为,民族国家对所属民族来说,意义十分重大。一个民族拥有了这样的政治体系,也就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合适而有效的政治屋顶。周 平:《民族政治学》(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1页。具有保障各民族合理利益诉求的责任。而政府作为国家责任的实际承担主体,也应该成为保障各民族合理的利益诉求得到满足的实际责任者。因此,基于苗族自发移民所具有的特定社会文化属性,对于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治理,就不能仅仅从地方保护主义立场出发采取“遣返”的方式,也不能简单地从地方利益出发,对这一群体的现代适应保持冷漠,甚至将其视为地方治理的“顽疾”。
地方政府是地方各民族利益的保障者、维护者、促进者,具有属地管理的责任。但这种属地管理的责任机制,在现有的制度框架范围内逐步衍生为地方社会治安秩序的保障,以及对居住在当地且拥有本地户籍的各民族利益的保障者、促进者,而没有将定居于本地的却没有当地户籍的民众的利益实现纳入到地方政府责任体系中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的滋长。正是在这一制度背景下,苗族自发移民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地方政府也产生畏难情绪,将其视为“烫手的山芋”,导致问题长期被搁置下来。
但是,制度性的障碍不应该成为政府责任落空的正当理由。作为国家责任在地方得以实现的主体,地方政府也不能以保护现有的制度性权威而忽略其应该承当的、对部分在现代化进程中表现出适应性滞后的少数民族群众的切身利益的保障。而实际上,这种地方政府责任是可以在既有的制度空间范围内得到实现的。关键在于地方政府,尤其是迁入地政府与迁出地政府以及其共同的上级政府能否拿出足够的决心和持续的努力来促进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有效解决。
因此,在促进问题有效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明确的一点就是,“以地域原则为基础、把公民权和平等的权利扩大到具备资格的所有居民,而不论其出身、族属和宗教”①[美]菲利克斯·格罗斯:《公民与国家——民族、部族和族属身份》,王建娥,魏 强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年,第8页。是公民国家最基本的特点,促进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解决,也就是促进他们适应现代生活,使其能够融入主流社会,是政府不容推卸的责任,是迁入地政府、迁出地政府以及共同的上级政府必须肩负的使命。
(三)切实促进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的改善
在保障苗族自发移民迁入地民众合法利益的基础上,不断提升苗族自发移民现代适应能力,显然是解决苗族自发移民问题的关键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民族的共同发展与繁荣进步。因此,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个民族都不能少。而在具体展开苗族自发移民现代适应能力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涉及到很多具体的政策、利益以及结构、人员,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必须要有步骤、分类别、整体性推进相关工作。
(四)重心下移、固本强基,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枫桥经验”源自基层,坚持发展的生命力也在基层。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建立健全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以村、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村(居民)广泛参与的管理体系,把村、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生活共同体。要以深入推进“网格化管理、组团式服务”为抓手,扎实推进乡镇(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心建设,使其成为平安建设的重要平台,成为推进平安村、平安社区、平安企业、平安学校等“细胞工程”建设的重要阵地。要加强乡镇(街道)、村(社区)综治工作队伍、“两所一庭一室”等基层政法组织和队伍建设,筑牢维护稳定的第一道防线。
所谓“有步骤”就是指要分步提升苗族自发移民现代适应能力。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这些苗族自发移民的户籍身份及基本权益保障问题(包括受教育权、互助医疗、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惠农政策优惠、精准扶贫政策照顾、选举权及利益表达权等基本权利和政策受益权),然后则需要解决生存资料保障问题(核心是土地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探索解决其产业扶持和致富能力建设问题。
所谓“分类别”就是指要根据苗族自发移民的意愿及地方实际,分类别将苗族自发移民进行安置。可以把愿意留在迁入地取得户籍身份并长期生活的自发移民进行分类安置:将与迁入地居民杂居在起的进行就地“插花”②所谓“插花”安置就是将移民安置在当地已有的村寨中,让移民与当地居民聚居在一起共同生活。安置;将已经自发聚居成为自然村落的就地集中安置;将分散聚居的进行集中或者“插花”安置。而对于不愿意服从政府在迁入地分类安置的苗族自发移民,迁入地政府则应将其纳入流动人口管理,在保障基本权益的基础上,在政策允许的弹性空间范围内,尽可能帮助其改善生活条件,增强现代适应能力。对于不愿意在迁入地就地分类安置而渴望回迁到户籍所在地的自发移民,则应积极做好政策衔接工作,由迁出地政府尽快落实精准帮扶政策,迁入地政府也需做好其回迁的相关配合工作。
所谓“整体性”就是要注重政策、资金、机构、人员等的整体性保障。在增强苗族自发移民现代适应能力的治理实践过程中,既要注重顶层设计,也要注重责任落实;既要注重加强组织领导,也要注重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力量;既要加强分步骤进行,也要适当加快进度,保障时效性;既要分类别管理,也要有总体性方案;既要注重政策落实,也要加强政策宣传;既要保障其生存权益,也要有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
结 语
云南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边缘化问题是一个民族的传统自发秩序在与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所形成的制度秩序的碰撞中逐渐演化出来的一个民族性社会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遗留问题。这些苗族自发移民所秉持的传统生计方式与现行的法律秩序、资源配给方式存在着必然性的冲突。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③[美]吉尔伯特·罗慈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页。而“在民族国家的框架内,任何族体都有权像别的族体一样,享有同等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公民权”。①宁 骚:《民族与国家: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的国际比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47页。因此,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只有民族国家能使弱小民族成员作为公民的法律地位与其民族文化的归属感联接在一起的时候,民族国家才能很好地履行其使命。②[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7页。
对于M县苗族自发移民社会处境改善来说,也许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③在泰国,一些国家和组织都参加了对于山地民族(这其中也包括苗族在内)的改革行动支持和经济援助,经过多方面的努力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都不十分理想,因为传统的农耕方式和生活方式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在他们的生活中间消失,要适应新的环境,接受新的观念还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和调适。参阅石朝江《世界苗族迁徙史》,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2页。但毫无疑问,仅仅依靠苗族自发移民的自主性行为调适,并不足以改变其社会处境的边缘化问题,而必需通过增进民族国家制度秩序的包容性,④所谓的“包容”不是把他者囊括到自身当中,也不是把他者拒绝自身之外,避免自大的狂傲,也回避无原则的退却。而“包容他者”实际上是说一个共同体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主张消除一切歧视和苦难,包容边缘群体,并且相互尊重。参阅[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才能从根本上消解苗族自发移民传统自发生活秩序与现代法律秩序及资源配方式之间的矛盾。在具体的政策实践中,需要地方政府(包括迁出地政府、迁入地政府及其共同的上级政府)能够将尊重国家制度秩序与尊重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把增进治理制度的包容性与苗族自发移民社会重建的人文关怀相结合,把促进治理体系的系统性与治理过程的渐进性相结合,从而促使苗族自发移民能够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步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发展轨道。
Spontaneous Order of Ethnic Groups Needs to Be Included in the Institutional Order of the State——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spontaneous Hmong immigrants in M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LU Haifa
Abstract: The spontaneous migration of Hmong people is a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phenomenon.An investigation of the Hmong in M county of Yunnan Province shows that the traditional shifting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and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 of spontaneous migration have affected their migration activities,geographical choices and living patterns. However,spontaneous Hmong immigrants have been marginalized in terms of economic life,political rights,public service sharing and even social psychology, because this kind of spontaneous order based on traditional livelihood is difficult to obtain legality under the existing state system order. To promote the Hmong’s integration into the mainstream society,we should increase the inclusiveness of the state institutional order and take practical measures to enhance their adaptability to modern society.
Keywords: spontaneous Hmong immigration,spontaneous order,institutional order,inclusiveness
中图分类号:D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19)05-0103-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13CMZ065)
作者简介:陆海发,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云南…昆明,650031)。
(责任编辑 张 健)
标签:苗族论文; 移民论文; 民族论文; 国家论文; 山地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民族性论文; 民族心理论文; 《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自发移民问题研究”阶段性成果(13CMZ065)论文; 云南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