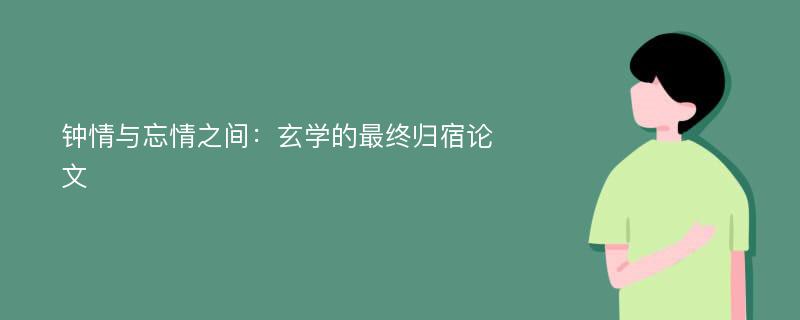
主持人语:
本期海峡两岸国学论坛专栏,有两篇文章,一篇是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谢大宁教授所撰《钟情与忘情之间——玄学的最终归宿》一文,企图藉由钟情与忘情这一对概念的讨论,说明魏晋玄学理论发展的线索,一改过去由佛学殿军的魏晋哲学发展史的认识视野;另一篇是由三明学院陈永宝所撰,题目是《殊途同归:论朱熹与严复救世思想的儒学回归》,从历史的角度,提出朱熹、严复两人的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出身、成长、环境以及际遇,兼及对两人理论贡献的讨论。以上两篇文章,都是作者创新意旨之作,并非像过去对传统哲学经典文本所做的疏解之作,有其新意。
(主持人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博士生导师杜保瑞)
钟情与忘情之间:玄学的最终归宿
谢大宁
(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台湾宜兰11605)
[摘 要] 历来均认为玄学诞生于王弼,而终结于佛教的般若学,但本文则认为玄学毕竟与佛学有本质歧异,不可能以转向佛学来解释玄学之所终。但究竟要如何理解玄学的消失,必须有新的途径。此文采取的进路,是认为必须从“情”这个命题在玄学中的特殊发展脉络来找寻答案。从嵇康对“显情”这个概念的发展,到“钟情”这个概念的确立,是玄学的重要贡献。这个概念并不来自于庄子,且与庄子思想间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是可以通过一种方式,让两者之间产生一种连结。这个方式即是通过“钟情”与“忘情”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对立统一的关系,建立起了由钟情到忘情的一种人格实践进路。而由于钟情在玄学的论证中,乃是艺术实践的必要条件,于是玄学乃转成了一种由“显情、钟情”这样的“纯粹情感”作为媒介,以艺术实践为载体,而指向一种庄子所说的“忘情”为目标的“艺术人生”之实践。这也就是说,玄学乃以转向一种忘情的艺术人生为其归宿。玄学的思想形式也许消失了,但它却在中华文化中构架起了一种思想、艺术与自在人格之实践为标的的新文化形态。
[关键词] 玄学;庄子思想;显情;纵情;钟情;忘情;艺术人生;自在人生
玄学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是很奇怪的,它仿佛知其所起,却又实不知其所起,仿佛知其所终,却也同样不知其所终。仿佛知其所起者,谓其为先秦道家之嫡脉,然实不知其所起者,以历来讲者对其间发展脉络的描述与诠释,又太过模糊,问题也太多的缘故。而仿佛知其所终者,通常认为玄学以格义的方式,直接促成了佛教龙树学的大兴,换言之,玄学改以般若学的姿态出现,化作春泥,去护了佛学之花了。然则所谓不知其所终者,格义毕竟只是格义,佛学运用了玄学作为格义,而有了长足发展,这是事实,但是格义这概念也同时说明了,玄学毕竟不能等同于龙树的般若学,那么玄学的旋起旋灭,其真正精华时间差不多只有五十年,难道这个学问就真的因为接引了佛学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吗?如果说作为中国思想史核心的儒学与佛学,尽管各时代的内涵都不免有变化,但作为一个传之久远的流派,都一直有一条清晰的思想发展线索,然何以道的线索就会有这样的尴尬呢?就算后世的道学并未中断,但它们和玄学并没有学脉相承的关系,乃是很显然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远不同于儒学与佛学,那么我们是不是该问这么一个问题:玄学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消失了吗?隐身于佛学了吗?还是到哪里去了呢?
在此之前,笔者对玄学的研究,多半集中在玄学之所起上,对于此一问题,笔者论之已多,也自信应该已经说清楚了许多问题,因此也不想再多着墨。要之,笔者不认为将玄学之所起放在何晏、王弼身上是一个聪明的作法,因为它会造成无法将先秦道家,尤其是庄子思想连接到玄学的问题,若真要把两者的关系顺利衔接起来,恐怕就得把玄学的概念限缩到由嵇康所创造的新典范上。关于这一讲法,请参阅笔者十几年来的相关讨论,此处就不再赘述了① 关于笔者对相关问题的讨论,近年的累积也算不少了,兹不一一详列,主要的论点请见拙作《历史的嵇康与玄学的嵇康》(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台北)以及《试论玄学的分期问题》(此文改以《中国玄学的重新分期》为题,正式发表于《南国学术》2019第1期,50-69页)。 。然而在玄学之所终的问题上,此前笔者的讨论是比较少触及的。即使触及,笔者也多半只是在说明,汤用彤先生的诠释方式,不适合用来说明玄学与般若学的关系,只有依照牟宗三先生的思路,这两者之间才有衔接的可能[1]。可是真正的玄学之所终,这方面的论述大体还是付之阙如的。这个问题一直到去年笔者处理了玄学中有关“情”的命题[2]之后,似乎才开启了一道曙光,我们也许终于可以在这样一个新出现的脉络中,开始思考玄学到哪里去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许可以让我们从一个特别的视角,来思考一下哲学、文学与艺术的边际问题。
一、对“魏晋玄学中‘情’的命题”一文的回顾
在去年笔者的拙作中,笔者的问题意识原本是在讨论,若我们扬弃了汤用彤先生的诠释后,也许就有可能释放出一些空间,来讨论一下像“情”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衍生的讨论空间。笔者也明白表示了,这一由情所带出来的玄学命题,首先是由吴冠宏教授提出来的[3],但笔者反对他的讨论模式与进路,希望能给出一个不一样的诠释。
在前引拙文中,笔者的论证乃是如此,这个论证是假“声无哀乐论”而展开的。嵇康在此文中反对儒家由“平和的音乐,可以导正人的哀乐情感,从而导正人的情性,以收移风易俗的效用”[2]14这一思路所谈的音乐作用。拙文对嵇康在此文中所认为的道家音乐主张的论证,是如此描述的:
以上这一概念的辨析,我认为是十分重要的,在这基础上,我们乃能进入到本文最重要的一个论题,也就是当我们区分了“显情、纵情”这两个概念和庄子思想的区别之后,可不可以再为这两者之间联系上某种关系?这也就是说从严格的概念意义上,纵情和庄子思想乃是不兼容的,但是有没有可能却在另一脉络上,重新勾连起这两者的关系?这一论题对魏晋玄学来说,自然是重要的,因为它将有可能决定魏晋玄学的何去何从,于是,下一节我们将进入这个重要论题。
2.1 2组治疗前后中医证候积分比较 2组治疗后反酸嗳气、胃脘胀满、双胁疼痛、胸闷、食欲不振及大便不畅等中医证候积分比较。中年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χ2=6.624,P=0.010(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老年治疗组与对照组比较,χ2=6.624,P=0.010(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中老年治疗组比较,χ2=5.875,P=0.017(P<0.05),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中老年对照组比较,χ2=2.43,P=0.119(P>0.05),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详见表1。
林业生态保护与天然林保护不仅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会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影响。所以,我们应该加强保护工作,使林业能够可持续发展。我国的经济建设也离不开林业的支持,只有不断提高森林覆盖率,才能有效推动我国经济发展。
吴冠宏提出从情这个概念出发,来讨论玄学的另一个为人所熟知,但却在学术上没有很好处理的论域,这样一个问题意识当然是非常有见地的,但我以为他很可惜的是没有选好论题的出发点。② 我认为吴先生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情的问题放回到了汤用彤先生的典范里去了,而在汤先生的本体论脉络中是找不到情的地位的。 在我看来,嵇康在《释私论》中所提出来的“显情”这个概念才真是一个有展开可能性的概念。所谓显情,就是“毫不掩饰自己的情志,敢表现自己的个性与情志”之谓也。这概念是特别的,也是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概念。情在中国思想史中很少作为一个独立的、正面的概念而存在[2]9,而显情这概念乃是第一次被作为一个正面的概念提出来,虽然这概念在《释私论》这篇文章中,其实也并不是主要概念,也很少有进一步的发挥,但我也说明了这概念出现的特殊意义。
绝对星等,是假定把恒星放在距地球32.6光年的地方测得的恒星亮度,它反映天体的真实发光本领。太阳的绝对星等约为4.83。
他把音声跟哀乐的关系彻底切开,音声自有一种客观的自然之和,对欣赏者而言,要想能欣赏到音乐的和谐之美,必须靠一种将自己从哀乐中抽离的能力。音乐欣赏是一种对律动的把握,也就是嵇康所说对“躁静专散”的感知,这要求对情感的某种隔离,此一隔离必须诉之于某种工夫论,也就是一种心境上的“虚静”之自我隔离工夫。但必须了解的,这种虚静并不等于老庄说虚一而静的虚静工夫,它只是抽离自己,让当下的情感活动暂时止息,不至于干扰到对音乐律动的欣赏与欣趋而已,而这工夫必须依赖一种情性上的对音乐的高度喜好,这喜好当然是情感面的,只是它不是所谓的哀乐之情,而是“情性”之情。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点,嵇康在这里和儒家论乐有了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其中当然有特殊意义,因为只有这样一种情才能真正将人带入艺术之中,浮面的哀乐情感,跟艺术欣赏与创作还是有距离的。嵇康此文的真正重点,当然还不是在这个地方,他真正想论证的乃是不用靠一种和谐情感的引导,来移风易俗。他反对儒家乐论的重点,倒不是音乐欣赏观点的不同,而是移风易俗路径的不同。他认为的路径是通过一种虚静的人格锻炼,而使人能进入一种“和域”之中,从而使得风俗得以在这种虚静里获得澄净的可能。而他认为一种“无声之乐”就是达成这一目标最好的途径。这里没有引导的问题,只有通过一种“无主于喜怒,无主于哀乐”的无执无为之修养,才可能达成。[2]15
(3)聚乙烯醇添加量对膜抗拉强度和变形率的影响。称取玉米秸秆淀粉添加量6g,再依次称取聚乙烯醇 2g、4g、6g、8g、10g,加入适量蒸馏水后再量取4mL甘油于烧杯中,其他试验操作顺序按照1.3.1和1.3.2中的试验流程进行。
拙文中笔者很清楚指出,嵇康此文的论证是有严重瑕疵的,因为他把音乐聆赏时的虚静的情感隔离,与虚静无执的人格锻炼混淆在一起了,于是他把对音乐无哀乐的虚静聆赏,当成了进入风俗之“和域”的途径,这当然是论域的混漫,从逻辑上来说,这无疑是严重的瑕疵。但是这一逻辑上的问题,在拙文看来,却恰好铺垫了一个解决问题的脉络。
笔者注意到的是,聆赏音乐时虚静的情感隔离,恰好正是一种情感上的高度专注,没有这种情感的高度专注,是不可能进入到真正的艺术世界的。如果我们把“显情”跟此处的“虚静”连在一起看,这两个表面上似乎连不起来的概念,其实正有一种情感层次的联系性。也因此,拙文乃说,这样一组概念恰好显示了嵇康对进入艺术实践、体现艺术精神这件事,是有清楚认知的。他在逻辑上也许把庄子所说的虚静和音乐聆赏的虚静混同了,可是他至少完全清楚在音乐聆赏时,必须保持情感上的高度专注与隔离,以此而带出一个纯粹艺术的世界,这就是他最大的创见。然则我们也可以说,显情也正是这样一个将人引向艺术世界的关键。这引向艺术世界的脉络,并不是庄子所提供的,而是嵇康所提供的。拙文在此认为这就是从嵇康开始的玄学所带来的第一重意义。
但接着这个层次意义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更有趣味,但也更麻烦。如果说声无哀乐论中的两个虚静的意义并不一致,嵇康的混漫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的话,那么我们要问的是,这两个意义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当然是重要的,若这两者没有关系,乃是不相干的两个概念,当然也无不可,那我们可以说虚静之情,与虚静之和只是两个不同论域,各自分途处理即可,如此玄学与艺术就没什么关系,玄学依然只是庄子式的人生哲学。但若这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某种特殊关系,那这个问题当然就有趣了。但前引拙文的处理实在太简略了,本文对此希望有进一步的处理。这个处理我们需要分成两个层次,首先,我们需要先处理庄子思想与“显情、纵情”的差别,然后再来谈谈两者之间是否具有关系。
3—6月柑桔红蜘蛛为害脐橙的叶片后,使脐橙的叶子表面出斑点。柑桔红蜘蛛为害严重时,整片叶两面变成灰白色而失去光泽,使脐橙落叶而削弱脐橙的树势,严重影响脐橙产量。如不及时防治,甚至会造成整株死亡。
二、从庄子论“方内、方外”之别,来看“纵情”是否是庄子的主张
历来对庄子的解读,特别是庄子里某些寓言的解读,都很容易认为庄子就是主张“纵情”的。比如说庄子妻死,鼓盆而歌这样的故事,① 《庄子·至乐》:“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参见《庄子集释》614页,台北:华正书局,1979年。) 一般就是说这是一种任性纵情而为的典范,但是这真是庄子的意思吗?一段类似的故事,也许值得特别讨论一下。这是《庄子·大宗师》里的一段有名的故事:
子桑户、孟子反、子禽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为友。莫然有间而子桑户死,未葬。孔子闻之,使子贡往侍事焉。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临尸而歌,礼乎?二人相视而笑曰:是恶知礼意!子贡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耶?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临尸而歌,颜色不变,无以命之,彼何人者耶?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丸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又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子贡曰:然则夫子何方之依?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虽然,吾与女共之。子贡曰:敢问其方。孔子曰: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
相造乎水者,穿池而仰给,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子贡曰:敢问畸人?曰: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也。[4]264-273
这段话第一个重点是所谓的“方内、方外”之分。庄子何以要做这一区分呢?是为了与儒家做对比,以为道家追求的是一种方外的生活,儒家则是追求一种方内的生活吗?看来他虽选择用假设的孔子与子贡来对比子桑户他们,但恐怕并不是基于儒道立场的差别,因为此处以虚拟的孔子口吻所说的这段话,表示的方内与方外这两类人,并没有基本价值观的差异,即使是方内之人,也还是追求一种“无事而生定”的人生,彼此仍要本于“相忘乎道术”的目标,其与方外的差别,不是这个价值观上的差别,而只是生活方式上“外内不相及”而已。这有点像论语里,孔子说他与隐者的生活有一种不可泯灭的差别,所谓“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差别。方外之人是离群索居的,对离开人群的人而言,世俗的礼仪规制的确是没有意义的,对一种以追求“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终穷”为人生理想的人而言,死生不是价值所在,也不必承担任何现实世界的成就,但如果说,方外之人追求相忘以生,方内之人追求相忘于道术,那么他们本质上、价值观上,就依然还是同一类人。如果我们真的说儒道的差别,则儒家的价值观绝对不是在追求“相忘于道术”上,而是以仁心来积极成就人世,这是必须清楚区分的。因此,庄子此处方内、方外的区分,不是在陈述任何家派的立场,据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方外的人生并不全等于庄子所要追求的人生。
如果说方外、方内的区分是如上所述的状况,那么我们就还要看到这段话的第二个重点,也就是“天之戮民”与“畸人”这个讲法,并且想想,如果方外、方内只是道家都认可的两种生活方式,那么庄子对之如何评价,或是更意许哪种生活方式呢?“天之戮民”或者是“天刑之,安可解”[4]205的讲法是特别的,意指“过着人间群居生活”的人,乃是一种“远离了天性自然”的,无奈的,甚至是遭受“天之刑戮”的、被“诅咒”的生活方式。由于这种生活方式远离了天性自然,所以要想回到天性自然,便需要格外的努力,他因为受到人群的束缚,因而需要以“道术”的方式来协助与引导,才能回到“无事而生定”的境界里去。从这角度来说,方内的生活是扭曲的,远远不如方外生活符合自然天性。这也就是说,从人群的角度来说,也许会认为方外之人蔑视人群的规范,乃是件奇怪的事,但方外之人的生活方式才是真正符合天性自然的,值得称许的。对庄子来说,方外、方内也许没有所谓的高下之别,但方外的生活显然更足以直接表现出他对价值的理解,也就是方外之人的生活方式,乃是一种更能直接显示道家价值追求的生活方式。之所以在庄子的文章中,我们常可以看到方外之士对方内之人的嘲笑。① 这些例子在庄子文章中俯拾即是,《德充符》篇中大概是最多的,此处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里有关“畸人”的讲法,也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德充符》里有关一群四肢不全人物的描写② 如篇中所说“鲁有兀者王骀”“申徒嘉”“鲁有兀者叔山无趾”,等等。 ,就在讲这些从人群社会的角度来说,因触犯人间刑律之畸人,看起来都是人间之小人,但当他们以天性自然来视自己的畸形时,其实他们就更能比方内之人直接表现出自然的价值,因无怪乎他们可以嘲笑这些囿于人间规范,为人间规范所束缚的人了。
(1)风险防范知识培训。通过外聘或组织本院专家采取集中授课形式每季度定期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学习,以增强一线护理人员法律法规意识;对新上岗护理人员、卫生员及护工在进行常规岗前培训外,重点组织开展回顾学习以往典型经验教训,以增强其护理风险防范的感性认识[3-4]。
然而这是否代表着庄子更意许方外的生活方式呢?如果说庄子认为方外的生活方式更直接表现了道家价值观下的一种理想型,这也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要说这就是庄子最意许的生活方式,恐怕也未必。庄子并不是糊涂人,他知道他这个学说毕竟是要放在人世中来理解的,因此标举着一种背离人世的生活方式以为理想型,这是可以的,用这种理想型来对照人间一些规范、刑律的荒唐、荒谬,这也是可以的,但若要以这种非人世的生活方式为常态而标举之,庄子恐怕也知道它的不可行。在《养生主》中,有段关于秦失吊祭老聃的故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这段话说: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吊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吊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4]127-128
这段话历来少有善解③ 这段话的批注,郭象就说得不是很清楚了。成玄英的疏干脆直指郭象矛盾,他说:“且老君大圣,冥一死生,岂复逃遁天刑,驰骛忧乐?子玄此注,失之远矣。若然者,何谓安时处顺,帝之悬解乎?文势前后,自相矛盾。是知遁天之刑,属在哀恸之徒,非关老君也。”以疏破注,真是莫此为甚了!历来解者对此一问题,很少能梳理清楚的。 。不过如果放到我们前面所述的脉络中,倒也是不难理解的。我们先把这段故事的背景,放到这样一个脉络里:秦失和老聃正是一对方外之友。老聃死了,秦失去吊祭他,本来这个吊祭该是一种方外的形式,也就是秦失该对老聃的尸体唱上一段,或者跳上一段吧,可是没有,秦失却按照世俗之礼,尽哀而出。这当然是奇怪的,方外之人怎么行起了方内之礼了呢?对此,秦失有一段精彩的解释。
秦失的说法是这样的:他说我之前看错了,老聃并不是跟我一类的人,他不是位全然的方外之士,当然,这话其实已经暗示了,老聃其实乃是一位可内可外,出入于方内、方外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只可以跟我这个方外之人以方外的方式相交往,也可以跟这个人世里的各种人相交往,所以他死了,才有这么多的老少以如此的真情来吊祭他。这种真情不是装得来的,一定是他平日感动了这些人的。于是秦失把这种老聃自觉的“委屈”自己之自然天性,把自己放到这个人群中去的做法,叫做“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并将之称为是一种“遁天之刑”。这说法真是特别的,遁天之刑跟天之戮民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一是主动的,一是被动的,老聃乃是主动、自觉如此,为的是他有必要去安顿人世,这样的讲法实在有点类似佛教所说的“留惑润生”,佛菩萨是在自觉的状态下,为了保持与众生的联系,而不刻意清除自己生命中的烦恼,留着烦恼以保持与众生的连结。虽然庄子所谓的安顿也许并不同于儒者,但人世是需要安顿的,这点庄子显然也有清楚的认知。当老聃自觉地选择这种遁天之刑时,他并没有忘记生命的本性自然,所以他仍是来去自如的,他的安时而处顺,即使是在人群之中,仍然哀乐而不能入,这就是老聃的帝之悬解,这悬解是在人间完成的,而不是在方外完成的,对老聃而言,人间的礼法规范并不构成一种束缚,他依然可以在这些礼法与刑律中,完成他自己的安时处顺,他自己的逍遥。换句话说,庄子的理想、价值之实践,并没有要求只有在方外才能完成,能自在地出入于方内与方外,一样也能达成同样的目的。这一故事就说明这点而言,应该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庄子这种存在式的心理分析,基本浅显易懂,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庄子解决问题的整个方案,其实也就很明显了。既然整个存在的苦痛皆来自比较,则停止比较也就是唯一的方法,这就是庄子“莫若以明”[4]63之所说。生命之明何由而获得呢?简单说,惟有跳出任何“对待”的执念。所有比较皆来自内在对比较对象与我差别之对比,于此差别之对比起执念,起妄想,于我胜对象则喜,于我不胜对象则悲,遂堕于比较之机栝而无以自拔矣!而于此差别对待无所执念,心无所待,这就是明。故列子有待于风,宋荣子傲然物外,遂皆有所执,唯“天地之正、六气之辩”无所不可乘者,乃为至人、真人、神人[4]16-17,也就是一种彻底的“自在人生”之完成。
对后面这一个问题,在《魏晋玄学中‘情’的命题》这篇拙文中,笔者做了一个特殊的处理,这个处理笔者借用了席勒与康德的关系。席勒奠基在康德道德严格主义的观点下,引进了情感的因素,从而带起了浪漫主义“艺术宗教”的发展。借用这样的架构,我假设了嵇康“显情”的观点与庄子思想之间,也形成了一种关系,即将庄子对精神上自在的追求,转向了一种艺术实践上的“无相”境界的创造。① “无相”一词,笔者是借用了牟宗三先生在翻译康德《判断力批判》的长序中所说,牟先生把康德所说的“无目的性原则”转成了“无相原则”,这是一个有趣的美学概念转换。(参见牟先生《判断力之批判》,台北:学生书局,1991年。) 换言之,如果这一论证是有理由的话,笔者也就因此而为庄子思想、也为玄学铺平了一条从纯思想、哲学的领域,转向到艺术实践上的新道路。此亦即是说,此一论题隐伏着一个可能性,我们有可能因此而顺带解决了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大问题,也就是玄学并不是消失了,而是转向了,它整个转向了艺术实践的领域去了,若真是如此的话,那当然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了。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进我色也,与乎止我德也,厉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连乎其似好闭也,愐乎忘其言也。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以刑为体者,绰乎其杀也,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以知为时者,不得已于事也,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于丘也,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4]234-235
据了解,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家庭清洁服务落后20年~30年,且缺乏相对前沿的清洁理念和文化,也缺乏专业的清洁剂和工具。自然正家从2015年开始投入很大的精力引入西方发达国家的清洁理念和清洁技术,并和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一起,研发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保养抑菌效果的、世界领先水平的清洁剂套组。并提出自然正家的清洁文化,即正家乃中华文明之始,和谐之本。正者,止于一。老子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正家服务,功成自然。自然正家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推广和践行环保理念,要让自然的力量呵护每一个家庭。
这段话也是让许多解者为之头疼的,因为它让人认为跟庄子很多地方对真人的那种出世形象的描绘很不一致,但这段话也恰恰说明了一些问题。这个真人的形象是亲切的,是与世推移的,他就在人群之中,所以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当他与人相与时,并不妨碍他的自在自然,这自在自然就是他“与天为徒”“其一也一”的一面,也就是他作为方外之人,畸于人而侔于天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他也顺应人世,而有了随时安时处顺的姿态,这就是“其不一也一”的“与人为徒”的方内之人、天之小人、人之君子的一面。这两个面向看似有着“天与人不相胜”的冲突,但真正的真人其实还是要在人世里成就的,这或者才是庄子的真正意思。如此说,也许颠覆了一般人对庄子的认知,但从一个角度说,庄子的学说毕竟是个人世的学说,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看到庄子的智慧呢!
综合上述,我们乃能将方外与方内构成一种“辩证”式的表述,也就是从一般意义的人进至真人的过程,其实是要经过一段辩证历程的,方外之人乃是这一过程的“反题”式的表述,他以对反于世俗的方式出现,但反题并不能停驻在反题上,它终须进至“合题”的层次,这合题也就是方内之人。真正的真人乃是作为合题的方内之人,一种基于自觉地进入遁天之刑的安时而处顺的真人,这才是庄子所称真人境界的最后归宿。这一辩证的过程是重要的,作为反题的方外之人乃是一种姿态,由此姿态显出真人理论上的理想境界,但真正理想的完成,则永远有赖于真正回到人世之中,去成就这个世间的其一也一与其不一也一,人间的各种姿态总是不一的,通过这不一而回到一,我们乃看到庄子对他所意许的生活方式的完整论述。① 关于这意思,我以前有篇拙作《庄子对孔子的评价》(台湾师大《中国学术年刊》13期,1991,台北)也曾略作说明,请参考。
以上,我大致说明了由“方内、方外”所带出的庄子的思考,由这一说明所显示的,方外之人作为一种姿态,他的“外其形骸”和魏晋名士的“放浪形骸”会是一回事吗?这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庄子是主张“纵情”的吗?如果我们可以充分掌握上述脉络,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回答的,因为方外跟纵情这两个概念之间,根本就是不兼容的。方内与方外有一个本质性的共同东西,那就是自然自在,但“纵情”的本质却是一种执情,有执情就没有真正的自然自在,这是很好理解的。方外之人显示的乃是自然自在的“对其自己”之姿态,是自在的本然形象,既已自在,便无拘束、无执着,所谓“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是也。纵情则必然在尘垢之中,它是有为,而非无为。这是一个基本概念上的区别,所以如果说庄子在方外之士的外其形骸上,表现了一种名士的“纵情式”的放浪形骸,那就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我们不能被文字描述上的姿态混淆,而乱了概念上的分际。这也就是说,纵情这个概念和方外之士,是联系不到一起的。如果说方外之士让人觉得显现出了某种纵情任性而为的姿态,那也只是诠释者概念上的混淆而已,这是不足为训的。
至于庄子所说的方内之士之安时处顺,他既然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了,这当然就更谈不上纵情而为了。我们可以说道家对安顿这个人世的看法,与儒家有积极与消极的差别,道家并不主张积极介入,去调整这个人间的各种规范,它只是追求在这个人间的各种规范中,如何应事而无所伤,所以它讲“因、顺”的智慧,讲一种“走在边缘”的策略,这不像儒家要积极把各种合理的规范承担在自己肩上。但无论如何,道家也都不曾讲对人间规范的真正蔑弃。方外之人的“蔑视礼义”乃是一种语言的姿态,而不是居于人间,却一味地在人间任性、纵情而为,这是一定要区分清楚的。这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严格推论来看,整个庄子思想,都不可能是和“纵情”这样的概念兼容的。也因此,当我们说魏晋名士的纵情,其实和庄子思想并没有关系,当阮籍在《达庄论》《大人先生传》里,隐然把他的纵情和庄子做成了某种联系② 关于阮籍思想的相关讨论,请见拙作《历史的嵇康与玄学的嵇康》129-145页。 ,这其实乃是阮籍对庄子的误读,并不足以为论据。
这概念的重要性乃在于它不只是一个偶然被提出来的概念,而是嵇康后半生在努力实践的概念,不只如此,嵇康更以此而深刻影响了阮籍。阮籍正是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而将自己的人生实践成了一种“纵情”的人生。但更重要的则是阮籍与嵇康共同以此开启了所谓的魏晋士风。这也就是说,没有这个概念,我们是没有办法理解魏晋这些士人“放浪形骸”之作为的。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名士风度的思想来源其实并不是庄子,而是来自于嵇康、阮籍”显情、纵情”的概念,这说法当然还有进一步辨析的需要,关于此一问题,下文会有些处理,兹暂不赘述。而若真是如此的话,那我们当然就会有一个新命题必须出现了,亦即如果说重新为玄学引入庄子的思想,乃是嵇康对玄学的最主要贡献,而他的“显情”说又为名士风度奠定了基础,那么“显情”的讲法和庄子思想之间,可以构成一种思想上的连结吗?还是没有关系呢?另一方面,显情这个概念的引入,又会如何丰富整个玄学的思想呢?又或者会为玄学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三、钟情与忘情之间——艺术人生与自在人生的辩证
庄子的问题意识,依其自己在《齐物论》中的表达,乃是针对一个特定的问题而发,即生命在无穷尽的比较中,自己把自己困入了一种无所逃脱的机制,直到自己生命力耗尽为止。《齐物论》的讲法是这样的: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栝,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爱慹,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4]51
此即在人世的一种“与接为构”之中,人们内心不停地交杂缠斗,斗些什么呢?无非就是在“大知、小知,大言、小言”之间来回不停地比较而已。这种比较本身就是一个隐匿于内心的机栝,这机栝能否伤人姑且不论,但伤己则是必然的,此因各种比较所带来的紧张与恐惧之故。伤之积久,遂令近死之心,莫使复阳矣!
不只如此,《大宗师》里更有一段对“古之真人”的描绘,特别值得注意,这段话是这么说的:
于是,庄子这样的主张,乃须归结于一种内在精神世界的实践,此即从内在心灵世界去掉对一切对待的执念,此一去除执念的实践,庄子即名之曰忘,忘者,非遗忘之谓也,乃精神无所住着,不为任何事物所捆绑,犹《金刚经》所谓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之谓也。因此,所谓的忘情,非所谓无情,乃于情本身之虽有情而无情之住着相,有情故此情自可一往而深,且需注意的是,此情之一往而深乃是前提,情需在自我贞定之下,进一步让此情可以自由流动,追求一种表现上的自在,所谓“情到深处情转薄”是也。此薄非对情之否定,只是以“正言若反”之“诡辞”的方式,谓一种“无着相”之情,如是而已。因此,这必是一种由情之一往而深后的另一境界,情之一往而深乃是情之自我纯粹化,由此情的纯粹化,进至情的自在化之境界。于是我们乃可说,忘情才是一种对情的真正成全,一种就庄子来说,永远于人无所伤的情。
如此而说的忘情,如前所说,当然的确和“纵情”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说纵情必以“情执”为前提,这是很显然的。纵情的概念可以是比较宽泛的,它可以是“太下不及情”的纵情,这纵字就只是放纵而已,于此之纵情即放纵情欲之谓也。《红楼梦》里说“皮肤滥淫”大概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一意的纵情无论在现实中如何普遍存在,它从来不是中国文化传统里所想表达的一面。但纵情也可以是另一意思,此即情之一往而深,即“钟情”之谓也。然无论是哪一个意思的纵情,都和忘情有着概念上的对立性,这是没有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撇开“太下不及情”的情欲泛滥之义不看,纯就“一往而深”的钟情来看,依我们上面所说,忘情在实践上又必须以一往而深的钟情为前提,则当我们讨论庄子思想与魏晋这种“显情、纵情”思想之间的关系时,就又似乎有另一层意思值得关注了。
妇科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不仅对患者的治疗造成了影响,也增加了医患纠纷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医院的声誉。为此本文对妇科护理中存在的安全隐患进行分析,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收到良好效果,现报告如下。
高龄产妇因为怀孕的时候年龄偏大,卵子分裂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染色体异常,导致胎儿染色体类疾病,也就是先天缺陷的机会明显增高,而且胎儿染色体畸形的发病率呈指数升高,其中21—三体的发病率升高尤为突出。
从钟情到忘情,存在着某种概念层次的矛盾与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我们上面分析的。就实践的层面说,忘情必须以能钟情为基础,没有情之一往而深,就不可能有机会体会情之真正自在。人固然可能只有深情,然后因情之执念而深陷于此情中,遂永不得自在,但绝无可能直接跨越此深情,即得情之自在。原则上说,情作为一种可以在生命中引发深刻执念的心理,它的情形是如此,则其他足以引发类似执念的心理也该是如此。从庄子思想的角度说,凡足以引发执念的心理终将因此执念而自伤,但换个角度来说,执念在人间也并不是一无是处,在人间,若无择善固执,就成就不了一个道德的世界。牟宗三先生在讲佛教不相应行法时,也提到这些看来是执念的不相应行,却是成就世间许多知识必须具备的心理条件[5]140-161。同样的,如笔者在《魏晋玄学中“情”的命题》一文中所说,一种情感上的专注,乃是成就艺术创作的关键。这也就是说,人间的执念固然带来了许多生命的创伤,但也同样是引发许多价值创造的原动力,这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是值得深刻体会的。
我们现在把问题回到玄学的脉络上,上文笔者说,魏晋的名士风度,其真正来源并不是庄子思想,而是来自嵇康、阮籍对显情、纵情的实践。这一方面固然表示了名士风度并不见得导向到一种庄子式人格的实践,但另一方面,如果庄子思想确实可以是由显情、纵情之纯粹化而自在化的一种价值性的发展,而且庄子思想之得以发挥,正须以显情、纵情之纯粹化为前提的话,那么嵇康就不只是如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说的,他可以为重新接引庄子思想回到整个思想发展的洪流中来,铺平了理解与诠释的道路而已,同时他也为庄子思想在人格上的实践预备好了基本的前提。还有一点,也就是笔者在《魏晋玄学中“情”的命题》文中所说的,显情、纵情乃是艺术实践的内在基础,嵇康通过音乐的实践,清楚显示了这两者间的内在关系,并且也为这一实践指出了通向庄子人格世界的道路。综合这三点,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有关玄学的新图像,这图像基本是如此的:由于嵇康的接引庄子思想,其学术兴趣是淡的,他原初的直接目的或者是为了自己人生际遇的巨变,可以排解突然遭逢的隐居生活,并为自己找到一种安顿人生的型范,但通过对艺术的爱好,与自己内在显情的需求,将自己的人生转向了一种通过艺术实践,而导向庄子人格得以实现的目标。这一导向也就初步为庄子思想与艺术实践之结合,奠立了重要基础。嵇康这一做法深刻影响了阮籍,虽然阮籍实际上对庄子的体会是很浅的,而且多半只是一种误解,他的咏怀诗文学成就固然极高,然多半只是一种纵情式的纯情表现,他的情感纯粹深沉,但通过嵇康而来的一种源自庄子的人格召唤,仍给了他一种徘徊于钟情与忘情之间的喜悦。如果说嵇康与阮籍才是真正的玄学奠基人,那么由他们所引发的魏晋玄学,其图像就十分清晰了,那就是由“显情、纵情、钟情”这样的“纯粹情感”作为媒介,以艺术实践为载体,而指向一种庄子所说的“忘情”为目标的“艺术人生”之实践。整个魏晋士人所追求的,其实不是一种思想的玄学,而是一种以艺术为载体、一种特定艺术人生为理想的玄学,庄子思想固然藉此而复兴了,但是庄子思想主要并不是以思想的形态而存在,而是只有内在于艺术与艺术人生的实践,对魏晋这个时代而言,才是其正确的实践场域。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只有在像《世说新语》这样的著作里,而不是在庄子注中,才能真正看到魏晋这个时代,他们对庄子的理解也许浅薄,但一种“纵情——艺术——庄子”的结合体,才真正代表这个时代,这应该才是事实。
5、加强田间管理:大豆发生根腐病,主要是根的外表皮(切皮部)完全腐烂,影响对水分、养分的吸收。因此,及时趟地培土到子叶节能使子叶下部长出新根,使新根迅速吸收水分和养分,缓解病情,这是治疗大豆根腐病的一项有效农业措施。
照如上所说,我们才能了解,以一种纯哲学的方式来看所谓的魏晋玄学,其实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视角。玄学当然有哲学这一面向,这是从庄子思想的复兴而带来的,但是这种哲学的层面从其开端,就被引向了艺术实践之中,成为了艺术实践的内在追求,而不是一种思想实践的追求。这也就是说,徐复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① 徐先生在此书中将庄子思想视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来源,却不曾解释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我现在的说法等于为徐先生补足了这块缺陷。 一书后半部所说,才是真正的魏晋玄学及其发展,今天的魏晋玄学相关讨论,反而偏离了真正玄学的轨迹。玄学当然促成了佛学在中国的兴起,但就玄学而言,这只是它的一个附带作用,而它本身的发展,更重要的恐怕是体现在山水文学、山水画的发展上,从山水艺术上,展现了一种艺术人生与自在人生的辩证过程,并以此而出入于钟情与忘情之间,从而为中国艺术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② 这里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哲学、文学与艺术之间的新的关系。在西方,哲学与文学艺术经常处于冲突的关系,用尼采的话说,一个是日神的精神,服膺的是理性,一个是酒神的精神,服膺的是激情。这就成了对立的关系,难有调和的可能了。但是如果顺本文所说的玄学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来说,则彼此之间也就有了一种新的、合作的可能性。在人格实践的范畴里,文学艺术提供了一个情感锻炼的基础,玄学则指向一种人格境界的完成,于是两者之间的藩篱可撤,合作的关系可成,这不就开发了一种人生的新境界吗?也许从这角度来看,玄学乃会有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未可知! 换言之,玄学的真正归宿,并不是化作了春泥,去护了佛学的花,玄学从不曾消失,因为从其源头,它就不是以思想为其主要表现场域,而是以艺术为载体,表现为一种在艺术人生中对自在人生的追求,所以玄学早已艺术化了,它早已与中国艺术的发展结合为一体,这恐怕才是我们对玄学发展比较正确也比较全面的认识!
四、结语
以上笔者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论证,处理了玄学往何处去的问题,这当然也补足了笔者对玄学整体论述架构的一个重要缺陷。至此,玄学从何而来,又往何处而去,笔者应该已经完成了一个远不同于今天玄学界相关讨论的图像,并将玄学从一种纯粹哲学架构的泥淖中拔了出来,同时也为中国思想与艺术接轨,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路径。这论证是复杂的,而要处理好从这样架构所衍生出来的,包括哲学上、思想史上的问题,乃至中国文学史、艺术史上的问题,当然都不会是简单的,但笔者认为笔者所提供的架构,应该可以提供一个最基础的框架,让诸如从两汉以迄隋唐所有的思想、历史、文学、艺术都能够放到这一框架来,并找出各自的发展脉络。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的地方,也许就是还有关于道教的一些问题,是否在其中也扮演某些角色,笔者仍然没能完全厘清吧!① 也就在玄学兴起的同一个时代,道教在中国文化的小传统中崛起,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也是一个之前一直被忽视的问题。直到陈寅恪先生开始注意到这个论题。但是这个论题也一直尚未得到比较好的处理。我现在只知道,当时养生问题的出现,和道教应该脱不开关系,而如果从这角度说,就和嵇康思想有着密切联系,那么我们当然也就不能忽视道教与玄学的可能关连。以前我曾想过去找王弼和道教的关系,但就是找不到,可是嵇康就不一样了,现在如果我们把玄学的重心转向嵇康,也就有必要厘清这个问题,可是至少到目前,这点还是我无法驾驭的问题,兹暂提于此,以为日后努力的一个提示吧!陈寅恪先生的相关说法,请见《金明馆丛稿初编》谈“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等几篇文章(参见《陈寅恪先生文集》,台北:里仁书局,1981年) 笔者曾追随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处理过嵇康家世信仰的问题[6]81-99,也了解山水文学的兴起多少和道教求仙思想有点关系,但其间的脉络我自问还是有些模糊的,不过至少到目前为止,笔者自信已经提供了一个相对所有玄学研究者更清晰的玄学图像,这点也许还不无贡献吧!
等到我们再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了,头发也已灰白了。以后数年中,头发越变越灰,变得象胡椒盐似的铁灰色,颜色就不再变了。直到她七十四岁去世之日为止,还是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
这篇拙文如果还有一些堪称突破的地方,其实都拜吴冠宏教授所提关于玄学中“情”的命题的问题意识,这让笔者注意到一个新的可能性。笔者说中国思想传统中,对情这个概念的意识是薄弱的,文学、艺术当然不可能脱离情,可是中国文学、艺术传统中所说的情,与西方宗教、文学、艺术乃至哲学所说的以“情欲”为主导的情,又有十分显著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其脉络究竟如何,似乎一直也没能讲清楚,今笔者此文也许可以提供一个新思路,至少不至于让许多文学研究者,只能乞灵于西方的架构,拿一个中国传统其实有些陌生的情欲概念,来硬套到中国的文学艺术传统中来吧!至于笔者这样一个分析架构,能有多大的展开空间,就只能俟诸异日了!
[参考文献]
[1]谢大宁.中国玄学的重新分期[J].南国学术,2019(1):50-69.
[2]谢大宁.魏晋玄学中“情”的命题[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1):7-16.
[3]吴冠宏.走向嵇康:从情之有无到气通内外[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5.
[4]郭庆藩.庄子集释[M].台北:华正书局,1980.
[5]牟宗三.佛性与般若:上册[M].台北:学生书局,1984.
[6]谢大宁.历史的嵇康与玄学的嵇康[M].台北: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
[中图分类号] B2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2991(2019)05-0025-10
doi: 10.3969/j.issn.2096-2991.2019.05.003
[收稿日期] 2019-07-0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重大招标项目“台湾的中华民族认同与记忆研究”(编号:18ZDA159)
[作者简介] 谢大宁(1957—),男,江苏阜宁人,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教授兼国际长,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访问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哲学,中国思想史。
[责任编辑 孙守朋]
标签:玄学论文; 庄子思想论文; 显情论文; 纵情论文; 钟情论文; 忘情论文; 艺术人生论文; 自在人生论文; 台湾佛光大学中文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