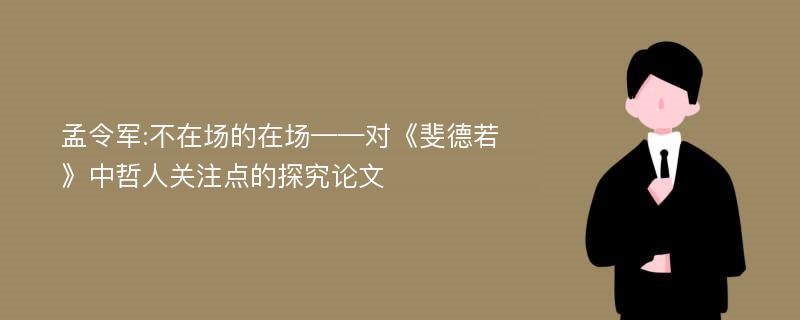
摘 要:苏格拉底一直致力于对“如何引导城邦和民众向善”问题的探索,但是在《斐德若》篇中,他却远离了城邦,与斐德若在郊外发生了一场对话。哲学想要在城邦中确立地位需要对原有的诗歌进行挑战,然而新兴的哲学并不具备直面诗歌的实力,采用隐微的方式(到城邦之外)是哲学试图进入城邦的一种举措。民众是哲人引领的对象,诗人是哲人批判的对手,虽然这场对话远离城邦之外,但是哲人的真正关注点仍是民众和诗歌。
关键词:民众;诗人;哲人;政治哲学
斐德若与苏格拉底的谈话是远离城邦之外的,苏格拉底偶遇要去城邦外面散步的斐德若,他询问斐德若从何处来,到何处去。斐德若刚从莱什阿斯家中出来想要去散步,两人都对文章感兴趣,所以苏格拉底就伴随着斐德若走到了城邦之外。这看似是一场偶遇,其实包括了民众、诗歌与哲学之间的碰撞交流,它们虽然没有直接出现,但却是以一种不在场的在场形式存在着。苏格拉底一生致力于城邦的幸福生活,他关注的重点是政治哲学,民众作为受教育的一方在城邦内如何更好地生活一直是苏格拉底关注的中心,同时也是这场关于讨论修辞术的最终目的;诗歌作为哲学一生的劲敌,苏格拉底从未有过丝毫的松懈,诗歌所具有的修辞性特点极易迷惑无知的大众,给民众灌输错误的思想理念,更可怕的是诗歌自身并不知晓它存在的错误。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就贸然去做,结果肯定是很糟糕的。同样,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的诗歌担负了引导人们更好生活的重任,相对于可怕凶猛的敌人对城邦的影响而言,这种错误的引领所带来的坏处显然要严重得多。虽然远离了城邦的生活,但无论是对受教者——民众还是对施教者——诗歌的考量,苏格拉底都以审慎的姿态来面对,从没有停止过思考。
一、城邦中的民众
苏格拉底和斐德若虽然都关注文章,但他俩关注的重点却有所不同。作为一个喜欢修辞的人,斐德若更偏向于文章带来的娱乐作用,而苏格拉底则关注文章所产生的作用。当一个人或是两个人在一起讨论的时候,把文章视为消遣的玩物无可厚非,一旦文章面对民众,在大多数人面前以演讲的姿态出现时,如何能够保证民众所受的影响是积极的?如何辨别谈话中的真实与虚假?这便是柏拉图所要面临的难题。苏格拉底和斐德若的这场谈话远离了城邦和民众,但是这场谈话的重点仍然是关于民众的教育问题。
(一)民众的不足
民众只是盲目的跟从,太容易被大多数的意见所迷惑,至于事情的对错与否,他们是不知道的,甚至说是没有能力知道的。最让苏格拉底担忧的是像斐德若们,他们有求知的欲望但并不知道真正的知识是什么,了解了一星半点关于修辞文章的技艺就四处彰显而并没有洞察事物本质的能力。对民众来说懂得些许修辞术的斐德若们更为可怕:他们不懂装懂,以自己浅显的认识去理解事物,还把这种错误的观念传播给身边人。
通过以上分析和讨论,本文基于模块建模方法,研究了碳限额与交易下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炼铁生产计划问题。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方面:①从问题角度,本文以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炼铁生产计划问题为切入点,探讨了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的两种碳排放约束——周期性碳约束和累计碳约束,对高炉生产计划的影响;②从模型角度,本文对基本模块模型进行了扩展,将多配方—多铁种因素以及两种碳排放约束——周期性碳约束和累计碳约束,纳入到基本模块模型中,构建了两种带有碳约束的多配方—多铁种高炉生产计划MILP模块模型。
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知识,斐德若们在求知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修辞的误导,错把不正确的认作真理;因为想要表现自己学识渊博,在懂得一点后又会在其他场合炫耀,误导了其他的民众,造成更严重的影响。斐德若不关注文章的内容讲的是什么,他只关心词语运用是否巧妙,话语言说是否动听。他希望得到他人的夸赞,因此在苏格拉底面前一再试图复述莱什阿斯的文章以展示自己所学的技巧。在苏格拉底要斐德若说出莱什阿斯的文章时,斐德若一开始并没有立即表演,柏拉图以讽刺的方式嘲笑了斐德若想要表现而又做作的姿态(这与苏格拉底在狱中对克里同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态度的转变也暗含了柏拉图诗学观的转换)。不过苏格拉底并没有按着斐德若的本意去做,而是直接戳破了其小伎俩,指出斐德若口袋中就有莱什阿斯的文章,被迫无奈之下斐德若朗诵了莱什阿斯的文章。苏格拉底绕过了斐德若,与没出场的莱什阿斯进行了直接的对话。“苏格拉底迫使斐德若充当演员的角色,吕西阿斯则是他背后的诗人。”[1]21
不过在《斐德若》的描述中,我们发现智术师和诗人的这种创作只是把诗歌作为了娱乐的方式: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并不涉及德行、正义等方面的内容,人人利用修辞的技巧来消遣诗歌,诗歌不具有崇高的地位。当苏格拉底询问斐德若是否有必要讨论一下写作的好坏是如何确定的时候,斐德若认为这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你问我们是否需要?研究文章是乐事,人活着干吗,若是不为着这样乐事?难道还是为着那些体肤的快乐?”[2]139-140斐德若不贪慕肉欲之欢带来的刺激而追求对文章的研究说明他有着一定的追求。只是把文章仅仅作为娱乐工具,追求它带来的快乐而不去寻找更高层次的含义,这又与苏格拉底所要引领的善好存在着差距。也正是因此,斐德若这种处于“无知”和“知”之间的人才是苏格拉底真正想要引领的人:他对表面生活带来的刺激感到不屑一顾,同时又找寻不到更好的生活方式。古希腊时期的文章不仅指写作和谈话,还包括演讲在内。写作既可以是一个人的事情(写作),也可以是两个人的事情(谈话),当然还可以是多人参与的活动(演讲)。针对文章的修辞特性苏格拉底也没有提出反对,如果文章只是被一两个人在狭小的空间内视作消遣的方式也无可厚非,“无论题材重要不重要,修辞术只要运用得正确,都是一样可尊敬的”[2]144。苏格拉底并没有全然否定修辞创造出的亦真亦幻的世界,不过在对修辞的使用时有一个前设条件:“运用得正确。”这意味着修辞并不能任意使用,必须做到适当、恰如其分。如果文章被当作了演讲,是面对民众的讲辞,那么针对修辞的考察就显得尤为必要。民众的辨识能力不高,他们轻易地被表层的现象所迷惑,不知道事物的本质,在美妙的修辞之下民众看不到事物的本真,他们很容易被修辞家诱导,分辨不出好坏。“如果说神话(muthos)代表了有关人之自我理解的诗性智慧,那么苏格拉底就证明了:这种智慧必须接受批判性的考察,以服务于人的自我认识。”[1]23苏格拉底并不否认诗歌的娱乐作用,但他更关注当被赋予了教化民众的重任时,诗歌能否做到合适恰当。
2.1.3 提取溶剂的考察 按照处方比例称取药材适量,加水煎煮,滤过,合并煎煮液,浓缩成流浸膏,水浴蒸干,置于105℃的恒温干燥箱中,干燥至恒重,得苏伯维尔浸膏。取4份浸膏粉末1 g,精密称定,置具塞锥形瓶中,分别加入25 mL水〔3〕547、30%乙醇〔3〕715、70%乙醇〔3〕714、50%甲醇〔3〕717,密塞,称定重量,超声处理30 min,冷却,再次称重,分别用相应的溶剂补足重量,摇匀,滤过,取续滤液,即得。按“2.1.1”项下进行含量测定。见表1。
“你看,苏格拉底,这篇文章如何?从各方面看,尤其是从辞藻方面看,真是一篇妙文,是不是?”[2]101斐德若看重文章的修辞而不关注内容讲了什么,尤其是在辞藻方面的使用,因此他在评价吕西阿斯这篇讲辞的时候用的是“妙”,而不是“好”或是“坏”。在斐德若看来诗歌语言形式的美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内容说了什么是无关紧要的,优秀的文章是通过对语言词句的排遣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至少在斐德若那里,文章并没有启发教育的功能,诗歌文章不过是休闲时的玩物。斐德若把文章看做消遣娱乐的方式而不是求真的工具。“柏拉图不否认模仿具有的魅力和娱乐价值,他质疑的是服务于追求真理的能力。”[3]民众看重的是文章的修辞所带来的快乐而不是真理带来的幸福,他们仅仅考虑诗歌美妙与否,不去关注诗歌是否含真。苏格拉底并没有被这篇讲辞所征服,他仍然保持着哲学家所特有的清醒与斐德若谈话,只有在清醒的状态下苏格拉底才能看得出斐德若对这篇文章的喜爱,以致于斐德若只是读它都会变得眉飞色舞。
原则反映规律,青年价值观教育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般规律,青年价值观教育的原则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一元主导原则。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着一定的社会关系,目前我国客观存在着多元化价值观念,也使得青年的价值取向呈现了多样化,所以需要以一元主导在青年群体中形成共同的价值目标。第二,动态发展原则。世界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价值观教育也要不断创新。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都要结合时代主题,与时俱进。第三,实事求是原则。开展价值观教育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既要联系青年的发展状况、思想实际,也要讲究教育实效,避免主观性和盲目性。
(二)哲人对民众的引导
从苏格拉底所说的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吟诗写文章在当时非常的流行,也足见诗人在城邦中的地位。城邦事无巨细,都需要诗歌的引导。“希腊人重视诗歌影响精神生活的能力,用希腊语来说,便是导心力。”[6]在古希腊人看来,诗歌能够起到凝聚人们内心的作用,诗歌把神话传说与英雄故事进行巧妙的结合以此来增强希腊城邦的凝聚力。诗歌在城邦生活中的地位是如此的重要,以致于创作诗歌的诗人被称为缪斯女神的仆人,他听从神明的旨意传递来自天上的启示,正是诗人把建立城邦的英雄和神话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结合不仅奠定了诗歌在城邦中的牢固根基,成为城邦强大生命力的保障,而且在无形中把诗人置于了城邦最高的统领地位。
苏格拉底对自然事物并不关心,他看重的仍然是民众的善好,只有城邦中的政治事务能够引发他的兴趣,苏格拉底真正关心的是和人有关系的政治问题,“你知道,我是一个好学的人。田园草木不能让我学得什么,能让我学得一些东西的是城市的人民。可是你好像发现了什么一种魔力,能把我从城里引到乡间来。一个牧羊人拿点谷草在羊子面前摇摆,那些饥饿的羊子就跟着他走,你也就这样引我跟你走,不仅走遍雅典,而且你爱引到哪里,我就会跟到哪里,单凭你拿的那篇文章做引媒就行了。”[2]96斐德若能够吸引苏格拉底来到城邦的外面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斐德若这里有苏格拉底一直关注的问题,苏格拉底需要借助和斐德若的谈话来对修辞诗歌这个问题一探究竟。在这里,苏格拉底把自己比喻成“饥饿的羊子”,斐德若则是“牧羊人”,诗歌文章则是滋养羊的“谷草”,苏格拉底被斐德若手中的诗歌文章所吸引到乡间。羊需要吃草料才能存活,但是草料是否能够滋养羊的身体,它对羊的生长发育来说是好还是坏,这就需要经过一番考察。因此,作为养育了古希腊公民的诗歌,它是否真的能够承担得起引领民众向善的重担?苏格拉底考察的重心就在于作为城邦根基的诗歌是否能承其重、负其责。苏格拉底之所以被斐德若手中的文章吸引,就是因为他对诗歌孜孜以求的审查。
二、城邦中的诗人
在做第一篇颂辞之前苏格拉底把脸蒙了起来,并没有以自己真实的面目露面,这是因为作为哲学家的苏格拉底是不能撒谎的。在《理想国》中我们发现苏格拉底着力批判诗歌的一点就是诗歌的谎言,哲学的求真的特点要求苏格拉底必须说实话、说真话,谎言的欺骗性是哲学排斥的,但是为了能够逐渐引导斐德若向上,苏格拉底不得不一步步吸引他的兴趣,不得已戴上了面具。“这种私人说服力对苏格拉底来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如果苏格拉底在城邦中能够用爱若斯的词汇诱惑住斐德若,他将在城邦中获得一个盟友,于此,城邦可能转换成一个依靠演讲就可以到达真理的地方。”[7]在后来《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展现出哲人狷狂的一面,我们发现这种试图通过演讲就达到真理的方式失败了,修辞语言并不能引人向善。斐德若极力想要复述模仿文章的内容以展示自己的能力,他热爱文章修辞所带来的愉悦性;苏格拉底同样也喜欢文章,但他更关注文章的内容。为了能够引导斐德若把对文章修辞的兴趣延伸到对文章内容的关注,苏格拉底势必要先从对文章的修辞入手。所以第一篇文章并不是苏格拉底本意想要创作的,他只是摹仿莱什阿斯而创作,是逐步启发斐德若而创作。当然,这一篇颂辞并不是苏格拉底对莱什阿斯的简单摹仿,他还是首先对爱欲做了定义:爱情是一种欲念,是想要的冲动。“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种指导的原则或行为的动机,我们随时都在受它们的控制,一个是天生的求快感的欲念,另一个是习得的求至善的希冀,它们有时互相调和,有时互相冲突。”[2]106在随后,苏格拉底打断了颂辞,转而问斐德若是否感觉到他凭神附。这其实是饱含讽刺的询问,因为当诗人真正被神附的时候是一种迷狂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诗人创作诗歌是一气呵成的,他不可能在创作的过程中弃缪斯女神不顾突然停止诗歌的写作去询问身边人现在是否处于凭神附的状态,并且说:“我现在所诵的字句就激昂的差不多象酒神歌了。”[2]107“差不多象”表明苏格拉底只是对莱什阿斯的模仿,“象”表明他并没有处于迷狂的状态,并没有被神附。苏格拉底一直处于清醒的状态,他不过是假借了缪斯女神的面具诵出了一篇关于纵欲的文章。“正如苏格拉底后来考察那几篇爱欲讲辞时所展现的那样,一篇书写作品只在与神灵感发相分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在回应它的读者那里引起反思而非顺从。”[1]56
(一)诗歌的价值
苏格拉底并不认为莱什阿斯这篇文章有多么好,他对斐德若称只要自己被神凭附后同样也可以创作出一篇优美动听的篇章,并在接下来吟唱了第一篇颂辞。在这里,首先苏格拉底并不认为吕西阿斯的文章有多么优秀,苏格拉底在内容层面没有对其做出评判,这不是说苏格拉底不能评判而是在面对像斐德若这样的民众时他有着自己的考量,他需要层层推进逐步地引领斐德若向上。“苏格拉底一方面必须化身为一个让斐德若从中看到自己身上的某些东西,从而想要追随的形象;同时,苏格拉底还必须揭示斐德若本人丝毫没有察觉的矛盾:他热爱文章,却根本不理解文章的力量。”[1]13苏格拉底在开始既没有认可也没有否定吕西阿斯所创作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逐渐引领斐德若们向善,另一方面也是为他第二篇的颂辞做准备(第二篇颂辞正好是对莱什阿斯文章内容的批驳)。苏格拉底认为吕西阿斯这篇颂辞在辞藻修辞方面显得拖沓重复,并不能很好地表达文章的内容,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吕西阿斯并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欲,他没有对爱欲做出全面的认识,不能在宏观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把握,就像盲人摸象一样,吕西阿斯不清楚自己要讲述的爱欲究竟是什么,所以他只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导致讲述文章内容的时候不断重复。针对这种情况,苏格拉底认为,“无论讨论什么问题,都要有一个出发点,这就是必须知道所讨论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否则得不到什么结果。许多人对于事物的本质,都强不知以为知;既自以为知,他们就不肯在讨论的出发点上先求得到一个一致的看法。”[2]106只有在开始讨论前明确讨论的问题是什么,接下来的讨论才有意义,不知道中心问题的谈话最终只能是一场毫无目的的漫谈,没有什么价值。然而民众并不理会这些,他们只享受文章带来的快乐,这种重复形式一遍遍刺激着民众的感受,迎合了他们善于遗忘的缺陷,这也是诗歌得以在城邦广受欢迎的原因,它遵循民众的意见,为了得到民众的赞同不惜回环往复的多次讲述。换句话说,斐德若(民众)是苏格拉底(哲人)和吕西阿斯(智者)共同的竞争目标,苏格拉底之所以一次次降低身份引导斐德若去思考并不是为了使斐德若获取哲性,“柏拉图从来没有说过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哲人,他的声明并不是说辩证法可以保证产生哲人,而是说只有辩证法可以产生哲人”[4]。苏格拉底式的辩证法不断引发斐德若(对话者)思考,“因此,通过辩证法哲人苏格拉底之手,辩证法成为了一个灵活的指导,不仅仅是在一场实践水准中,还体现在沉思层面”[5]。这种沉思启发民众去思考作为城邦根基的诗歌是否可靠,哲学引人向善之路是否值得追随,这种沉思所引发的对个体自主性的思考尤为重要。
(1) 如无禁忌证,无论采用何种治疗策略,所有患者均应口服阿司匹林首剂负荷量150mg~300mg(未服用过阿司匹林的患者)并以75mg/d~100mg/d的剂量长期服用(Ⅰ,A)。
(二)哲人的反讽
虽然诗人在这场会话中没有出现,但是诗人却一直附在斐德若的身后,斐德若作为一个传递者,他自己并没有表现的机会,只是转述了莱什阿斯的文章。这场看似是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对话,其实是隐藏在斐德若身后的莱什阿斯与苏格拉底之间的交锋。“这场表面上是发生于一次私人邂逅时的谈话,被苏格拉底呈现为传达给三类写作者的讯息:吕西阿斯和文章写手、荷马和诗人、梭伦和法律文书。”[1]6斐德若是苏格拉底意欲争取的对象,但他真正的敌手是斐德若背后的诗人、智术师和法律制定者。
这篇颂辞从整体上看并不是苏格拉底最好的颂辞,它是对无爱欲者(纵欲)的反讽歌颂,只是出于引导斐德若的目的被迫无奈的产物,和后面的一篇(节制)相比差远了。只有做到节制的爱欲才能追寻更好的境界,才能通过回忆追溯最完满的存在。但这里苏格拉底却把这篇关于纵欲的文章形容为像酒神歌一样,和被神明宠幸后创作的诗歌一样,把对爱的纵欲等同于诗歌的创作,由此可观,在柏拉图眼中诗歌在整个哲学构架中充其量不过是爱欲的最低层次,亦即是一种对肉体的欲念。诗歌只是对表象的欢愉的歌颂,它贪图一时的享乐而看不到最美的事物,在灵魂的三驾马车中它充其量只是最低端的对欲望的追求,这种纵欲获得的是感官的快乐而不是对最高的善的追求。
当然,斐德若并不仅仅是以一个传递者的身份而存在,他更是代表了哲人苏格拉底和智术师吕西阿斯之间所争夺的对象——有求知欲的民众。在以传递者身份出现的时候,斐德若更多是聆听吕西阿斯的教导,倾听苏格拉底的教诲,哲学和修辞术都想要在这场争夺中获得民众(斐德若)的青睐。“吕西阿斯和苏格拉底都意识到了这种心理学,他们采用策略去利用它。这就是说,为了说服斐德若,他们知道自己需要说什么以及如何表达。”[7]苏格拉底甚至不惜降低身份来召唤仙女附身创作诗篇以对斐德若进行逐步启发。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受到诗歌修辞影响的民众——斐德若与苏格拉底之间的交谈,这其中涵括了哲学、诗歌、民众三者纵横交错的关系式。诗歌不是采用直面哲学的方式,而是隐匿在有求知欲的民众身后与哲学进行对话,虽然苏格拉底远离了城邦,但城邦的根基——诗歌并没有淡出苏格拉底的视线,诗歌和哲学对民众的争夺一直存在。
斐德若和苏格拉底的谈话看上去是两个人在偶遇的情况下发生的,但实际上暗含了必然的因子。苏格拉底不关心除了城邦以外的其他事情,并且作为一个经常在城邦内考察有知识的人的哲人,苏格拉底与斐德若的这场谈话其实也是哲诗之争的必然:城邦中民众如何过上幸福生活一直是柏拉图关注的问题,民众由于自身存在的缺陷性,他们并不能看破诗歌的小伎俩,诗歌所描绘的表象世界误导着民众的认知,让人们以为现有的生活就是最好的生活,遗忘了对美好生活的回忆。哲人有必要对诗歌进行一次清查,以帮助民众区别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诗歌在城邦中具有深厚的根基,想要从根本上去除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哲学想要在城邦中确立地位需要对原有的诗歌进行挑战,然而新兴的哲学并不具备直面诗歌的实力,采用隐微的方式(到城邦之外)是哲学试图进入城邦的一种举措。“他们看似随意的耳语谈话就好像溪水从石间流过,但他们的谈话并不仅仅是调情式的聊天;如果重返城邦之中,它可以为哲学本身奠定基础。”[8]诗歌一直是哲学所要抨击的对象,虽然在这场对话中诗人并没有以在场的身份出现,不过斐德若作为莱什阿斯的代言人,实际上诗人已经变相地出现在对话中并与哲学产生了碰撞。而斐德若作为哲学试图引导的对象,是哲学和诗歌的必争之地,新生的哲学只有在城邦之外(远离诗歌的统治)才有可能对有着求知欲的人们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开拓出一条正确的求知之路。
参考文献:
[1](美)伯格.为哲学的写作技艺一辩——柏拉图《斐德若》疏证[M].贺晴川,李明坤,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2](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3](美)罗伯特·威廉姆斯.艺术理论——从荷马到鲍德里亚(第2版)[M].许春阳,汪瑞,王晓鑫,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
[4]James stephens.Palto on dialectic and dialogue[J].The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27(1993):465-473.
[5]Michael hanke.Socrstic pragmatics:maieutic dialogues[J].journal of pragmatics.14(1990):459-465.
[6](波)瓦迪斯卡夫·塔塔尔凯维奇.西方六大美学观念史[M].刘天潭,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88.
[7]Love’s litigation.Palto’s phaedrus as trial by jury[J].Susan E.Kinz.Duke law Journal,46:4(1997).
[8]Susan E,Kinz.Love’s litigation:palto’s phaedrus as trial by jury[J].Duke law Journal,46:4(1997).
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6051(2019)03-0054-07
DOI:10.13950/j.cnki.jlu.2019.03.006
收稿日期:2019-03-28
作者简介:孟令军(1992—),男,山东济宁人,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学。
责任编辑:曲筱鸥
标签:苏格拉底论文; 城邦论文; 诗歌论文; 民众论文; 修辞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欧洲哲学论文; 古代哲学论文; 《临沂大学学报》2019年第3期论文; 复旦大学中文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