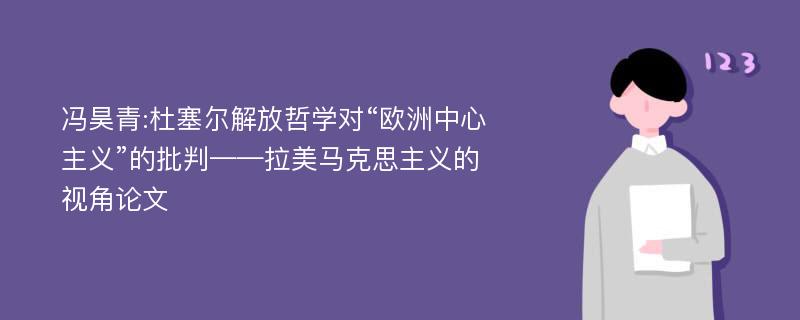
摘要:杜塞尔解放哲学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文化哲学,借助文化分析方法,创造性地将历史学与欧洲中心模式的现代性联系起来,以全球性角度来批驳“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主义预设,并以此为契机重新考察世界历史,解构那种排斥、贬低、边缘化非欧洲文化的欧洲中心主义普遍历史观,从而维护各个共同体或民族文化的可变性及差异性,肯定那些被现代性所忽视的文化传统价值。此外,他还从现代性起源、发展和当前危机出发,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企图瓦解发展至今500多年的世界体系,解放从现代性发轫之初就被否定的边缘文化传统,试图从边缘出发建立起穷苦人民的乌托邦。
关键词:恩里克·杜塞尔;解放哲学;欧洲中心主义;世界体系;现代性
一、引言
恩里克·杜塞尔(Enrique Dussel,1934—)是拉美解放哲学的主要创始人,著名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开创的以“拉美解放”为旨趣的解放哲学,在延续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拉美文化历史研究的同时,将当时盛行在全球范围内的欧洲中心主义作为集中批判的标靶。以此为契机,杜塞尔提出,解放哲学的全球化发展“不只是为了第三世界,而涉及整个地球”。[1]当然,此目标的提出,盖因其深刻洞察到,在全球化时代,若无世界意义的解放,很难论及拉美真正的解放。基于此,他试图在世界历史框架内重构拉美文化历史,为拉美文化乃至所有文化寻求新的定位。另外,杜塞尔这种文化解放的谋划还源于其对大众文化的独特理解。他认为拉美大众文化,“只有在自由解放的过程中,即经济上脱离资本主义,政治上摆脱压迫,建立一种新型的民主类型,并以此代表一种文化解放而沿着被压迫的历史文化传统走出一条创新道路时,才能得以解释、澄清和证实”。[2]于是,在受到依附论所代表的拉美解放思潮的熏陶,以及列维纳斯的《总体与无限》的影响,并在1968年人民大众和学生运动的推动下,杜塞尔逐渐转向质疑那种标准的、将非欧洲地区排斥在外的普遍历史观。在杜塞尔看来,这种普遍历史观背后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不仅形成错乱的关于非欧洲文化的解释,而且同样没有充分解释自己的文化”。[2]
词汇是语言各个系统中最不稳定的部分,因此词义的演变在语言发展变化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东西”一词经常用到,包括“鬼东西”、“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好东西”、“坏东西”等等,这里的“东西”或表示事物、或表示人。然而,“东西”一词最初是方位词。那么,表示事物的“东西”是如何在语言系统的变化中演化而来的呢?
为此,杜塞尔在《1492:遮蔽他者——揭示现代性神话的根源》一书中,创造性地将历史学与欧洲的现代性联系起来,进而以全球现代性来批驳欧洲中心模式的普遍主义预设,以此来维护各个共同体或民族文化的可变性及差异性,肯定那些被现代性所忽视的传统文化价值。众所周知,马克斯·韦伯鼓吹“在西方文明里,而且仅仅在西方文明里,文化现象呈现为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和价值的发展”。[3]3而在哲学领域,黑格尔将欧洲精神抑或日耳曼精神视为绝对真理,认为它无须借助他物,本身便能决定或实现自己。杜塞尔指责这些充满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论断,不仅纠缠着欧美,还困扰着外围世界的整个知识阶层。一方面,它夸大了欧洲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将人类历史貌似科学地分为古代、中世纪和现代,这其实是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与变形的组织。另一方面,它忽视、贬低以致抹煞了非欧洲地区对人类历史发展的重大贡献。如黑格尔就认为,“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4]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亚洲专制而愚昧,只有欧洲才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是最先进的文明。此外,他还将世界众多民族分为世界历史民族和非世界历史民族,从而将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等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
当学生说出自己的感受后,我向学生介绍了杨绛的情况,学生越听越吃惊,最后竟然要否定自己的观点。我告诉学生,杨绛虽然才华横溢,品德高尚,但是你刚才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你看这么著名的学者作品中尚且存在这种问题,其他人的文章存在一些问题也就不足为怪了,只要你认真阅读,大胆质疑,一定会发现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学生从中受到肯定和启发,也会变得越来越有质疑精神。
杜塞尔指出,这种充满偏见和傲慢的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就其他文化而言,它已经引起伦理问题”。因此,他呼吁,“哲学,特别是伦理学,需要脱离这种简化论视角,以让其自身向全球范围开放”。[3]4不仅如此,杜塞尔还进一步提出相反的看法,即在欧洲中心主义视角看来“在文化上比较匮乏的那种文化”,其实,“远远不是一种不重要的文化,它反而代表着被压迫的人民对压迫者的那种未受污染的、富有启发的反抗”。[2]因此,其解放哲学以各种文化间的对话为切入点,从一种全球性角度而非欧洲中心主义那样的地方性角度来考察世界历史。
二、全球视野的世界历史
杜塞尔最初从宗教层面来勾勒拉美文化哲学的基本轮廓,他在《关于拉美教会史的假说》(1967年)中,首次在全球文化历史的背景下重新解释宗教历史。然而,尽管该书展现的拉美文化历史“不再以欧洲为中心,但仍然是一种发展主义”。他继而带着“拉美文化”的起源问题,通过《闪米特人道主义》(1969年)、《基督教人类学里的二元论》(1974年)和《希腊人道主义》(1975年)等著作来分别讨论希伯来传统、中世纪基督教传统和希腊传统中的身体—灵魂二元论问题;并通过重构不同于基督教历史观的历史,来研究欧洲与拉美之间的关系及其向拉美的扩张。最终在依附理论的影响下,杜塞尔以受到帝国文化压迫的外围文化为各种文化间对话的重点,在区分各种文化类型的同时,得出“大众文化才是文化解放的关键”的结论,并强调指出,大众文化并不是一种平民主义,而是“指涉该民族的整个社会领域,尽管它们受到剥削或压迫,但它们同时还保持了一种外在性”。[2]他试图以此表明,尽管受到国家体制的压迫,但在压迫者所鄙视的文化领域,仍保持着自身的可变性、差异性和自由。
其次,杜塞尔将世界体系与现代性,跟欧洲对世界的统治,包括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认作是同步延伸的现象。他总结出至少两种现代性:一种是西班牙式的、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性质的现代性,它源自于欧洲的扩张——这是希内斯·德·西普尔韦达和曼带尔特的解释;另一种是随佛兰德的阿姆斯特丹兴起而开始的央格鲁—日耳曼欧洲的现代性——常常被认为是惟一的现代性——这是松巴特、韦伯、哈贝马斯和后现代主义者的解释。
首先,杜塞尔试图表明因世界体系内欧洲的世界化和中心化,几千年来在这个跨区域体系内,人类的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联系的“经验”才被欧洲独霸,而欧洲过去从来都不是“中心”,最多不过是个“边缘”。[3]5在杜塞尔看来,“尽管拉丁—日耳曼的欧洲文化曾经因为古罗马帝国而在南方有所影响,但它其实一直是外围文化,从来没有成为影响大陆文化的‘中心’”。[2]而世界体系中心的运作让欧洲可以将其自身转变为类似于世界历史的“反思意识”,亦即现代哲学的东西。但很多被当作其独有产物的价值观、发现、发明、科技、政治制度等等,其实是这个跨区域体系的第三阶段内古代中心向欧洲位移的结果——沿着时间轨迹,从文艺复兴的意大利城市到葡萄牙是先驱,然后到西班牙,再到佛兰德、英国和法国等等。[3]11-12具体来说,是从中亚移向意大利的热那亚等城市,起先与葡萄牙相联结,然后与西班牙的塞维利亚相联结。于是,从文艺复兴积累下来的地中海地区的(通过它,还联结了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的)“经验”便与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帝国相联结——尽管这个世界帝国的政治大业最终遭到经济的失败而告终,但它仍为商业、工业和当今跨国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留下了敞开的通道。作为第一个现代港口,塞维利亚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辉煌后,将其地位让给了阿姆斯特丹。这就是说西班牙在佛兰德的殖民地取代了它,成为新的世界体系中心的霸权,直至1689年这一地位才遭到英格兰的挑战,但至少到1763年为止它还必须与法国分享这一霸权。这就是现代性的第二次和第三次浪潮,其中资本主义得到了蓬勃发展。
面对“欧洲有什么权利去占领、统治和管理新发现的文化”这一哲学伦理问题,第一种现代性阐释认为,这些文化是用军队征服并加以殖民化的,即通过一种一体化文化、单一语言和单一宗教霸权,西班牙将欧洲“管理”成对世界控制的中心,以及作为军事占领、官僚组织、经济征收、人口迁徙和生态变更等等的中心。杜塞尔认为这就是世界帝国计划的实质,但正如沃勒斯坦所言,这个计划已经伴随着查理五世一起失败了。而自17世纪开始,第二种现代性不再需要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从荷兰到英国再到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已经不再受到质疑。也就是说,这种超级意识形态已经建立起自己对世界体系统治的“合法性”。直至20世纪末,同其他运动一道,解放哲学才再次开启对这种超级意识形态的质疑。杜塞尔依据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的理论坚决指出,作为世界体系的建构,欧洲没有权利在美洲进行扩张,这是不公正的暴力行为,因而它不可能具有伦理上的合法性:
在常规阅读教学中,教师通常会设计一系列的问题来处理文本,“问题”是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思维工具,教师一定要关注学生思维活动的内容和层次,由浅入深,循序渐进。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教师提出的问题可分为展示型问题、参阅型问题和评估型问题。下面就对本课例中的问题设计进行一一分析,看其在训练学生的阅读策略和批判性思维方面的成效。
最后,杜塞尔还提出了异于所有欧洲中心主义论者和大多数当代西班牙知识分子的惊人观点,即西班牙是第一个现代国家!其理据在于:现代性开始于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和殖民化。无论从欧洲中心主义视角,还是从全球视角来看,“在文化、科学、宗教、技术、政治、生态和经济领域内的这种世界观的革命才是现代性的起源”。[3]10但杜塞尔认为,一方面,尽管哥伦布始终未能从主观上突破跨区域体系的视角,接受世界体系的新阶段,但是他于1492年发现新大陆却是现代性起源的奠基性事件;另一方面,拉美盛产的白银也为第一世界提供了通行货币,而现代哲学亦诞生在征服和殖民拉美的批判之中。基于这两个理由,杜塞尔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现代性的起源。他认为,正是1546年在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发现银矿,西班牙才能迅速装备起“无敌舰队”,从而建立海上霸权,并得以将大西洋建立成为新的世界体系的中心。因此,严格来说,现代性开始于西班牙横渡大西洋征服和殖民化美洲。而且美洲自被西班牙征服和殖民化以来,便已成为世界体系与现代性的一部分,因为它具有现代性定义中所需要的第一个“野蛮人”。美洲作为西班牙的外围世界,在赋予其确定的、相对优势的同时,也构建着最初的现代性的基础结构。因此,杜塞尔赞同阿根廷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巴古,将美洲殖民时期的经济结构定义为“殖民资本主义而非封建主义类型”。[8]在他看来,美洲不但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还是现代世界体系本身的附庸。倘若一切真的如此,那么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哲学家,还有十六世纪的第一批拉美思想家应被视为现代哲学的先驱。而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希内斯·德·西普尔韦达、弗朗西斯科·德·维多利亚和弗朗西斯科·苏亚雷斯应先于笛卡尔或斯宾诺莎(他们直至1610年一直在阿姆斯特丹从事写作工作)被写入现代政治哲学的历史,亦应先于霍布斯和洛克成为第一批现代政治哲学家。
总而言之,在杜塞尔看来,自笛卡尔以来,现代哲学始终坚持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并因此对历史上的民族事件持一种片面的、狭隘的、地域性的观点。而杜塞尔清楚地将自己置于这一现代世界体系观念中,不仅研究其中心,而且考察其边缘,从而获得对人类历史的一种全球性看法。杜塞尔表示,其观点既非让人增长见闻,更非什么趣闻轶事,它完全是哲学性质的。
三、作为全球中心“运作”的现代性及其局限
杜塞尔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普遍历史观的质疑,最初是从“后现代”关于现代性本质的质疑入手的。但这仍是一种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而且他所说的“后现代”与同时期的后现代主义者们所指涉的东西是不同的。因为他从全球性角度重构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并从现代性的起源、发展和当前危机出发,对欧洲中心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杜塞尔强调,这样做非常有必要,因为在欧美,“现代性”一直拥有一种明确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内涵,著名的代表人物有利奥塔、瓦蒂莫、哈贝马斯等人,甚至在沃勒斯坦那里也还有这种轻微的不良倾向,后者被称为“第二代欧洲中心主义”。[2]
对这45个点的平面坐标误差求和统计得出,∑ΔX=1.363 m,∑ΔY=0.343 m。由此可以看出,X和Y坐标均无显著系统性偏差。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社会分工趋向细化和专门化,新兴阶层不断涌现。人们在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利益诉求,社会利益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出现利益分化,甚至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冲突的局面,造成公民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利益局面,在社会利益多元的环境中有效整合利益,将利益冲突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对公共决策机制的利益整合提出挑战。
在这样的认识背景下,弗兰克在《五千年世界体系史导论》(1990年)中提出的“中心—边缘”分析框架,及其力图证明欧洲并非“自古以来的世界中心”的思想对杜塞尔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迅速被他拿来作为理论分析工具重构世界历史叙事,即从 “外在”于欧洲中心的角度(全球性视角)将世界历史分为四个阶段,也就是三大跨区域体系阶段和(现代)世界体系阶段,[5]并且“准确”指认,这个跨区域体系至少产生于公元前4 000年的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毫无疑问,他对世界历史的这种“重构”,是希望以此来克服希腊中心主义,进而从源头上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传统历史叙事。为此,他甚至通过考证来证伪惯常认为源自希腊的政治哲学术语,以此来解构希腊中心主义。例如,杜塞尔认为,“民主”与“正义”这两个词,并非源自古希腊,而是源自古埃及语,或迦勒底语——它源自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卡德语。[6]XV紧接着,杜塞尔还进一步指出,跨区域体系的第二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00年,其中心是印欧世界,而非欧洲。至公元4世纪,跨区域体系的中心逐渐转移到亚洲、非洲和地中海地区。而世界体系则产生于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它也是最早包含美洲的全球体系,因为此前的中美洲文明和印加文明根本无法与这个跨区域体系相联结。
其次,杜塞尔不但对欧洲内部因素有所涉及,而且强调了外部因素对欧洲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更为深刻地揭示了当时欧洲得以超越奥斯曼—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的原因。许多反欧洲中心主义论者试图完全忽略欧洲的力量,因其断定如果把欧洲的力量包括进来,将会陷入强调欧洲例外论或独特性的欧洲中心论的困境。[7]杜塞尔则不避讳谈论欧洲的能动性,他肯定欧洲的前现代先驱统治着不断扩大的“边缘”——16世纪是美洲、巴西、非洲的奴隶供应海岸和波兰,17世纪是对拉美、北美、加勒比和东欧的巩固,19世纪前半叶是奥斯曼帝国、俄国、一些印度的王国、亚洲次大陆和首次深入非洲大陆。由此逐步将自身建立成世界体系的中心,并将超级霸权从西班牙传给荷兰、英国和法国。同时,他还认为,“欧洲在世界体系内的中心地位并不仅仅是在欧洲中世纪对抗其他文化而积淀的内部优势的产物,相反,它也是对美洲的发现、征服、殖民和整合(归入)这一简单事实的重要结果”。[3]4自1492年至1550年,仅仅西班牙就拥有超过200万平方公里的美洲殖民地,并统治着超过2 500万当地居民和大约1 400万黑奴。与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相比,这一巨大的空间和人口给欧洲以决定性的相对优势。此外,拉美白银也极大地刺激了欧洲的消费与欧亚贸易,并成为了欧洲经济扩张的必须品。
再次,杜塞尔在《全球化与排斥时代的解放伦理》中借用诺姆·乔姆斯基所说的“500年体系”,揭示出现代性的三个局限来预示现阶段文明的终结,即:(1)现代性将自然作为可利用对象,并以资本利润率为目标,但它在破坏地球生态的同时,还危及人类的生存和繁衍;(2)现代性无法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导致绝大多数人因贫困和饥饿而难以生存;(3)现代性无法将所有人纳入其中,特别是那些在现代性发轫之初就被攻击、被排斥、被逼入贫困的人口、经济、民族和文化。[3]21-22
首先,杜塞尔认为欧洲中心与全球体系两种对立模式描绘出了现代性问题的特点。前者从欧洲中心的视角出发,认为现代性现象完全是欧洲的,它于中世纪发展勃兴,然后传播到全世界;而后者则从全球视角出发,将现代性概念化为“世界体系”中心的文化,是该中心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在杜塞尔看来,现代性不是欧洲作为独立体系的现象,而是欧洲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现象,它具有全球性。这种假设完全改变了现代性的概念、起源、发展及当前危机,并因此改变了迟来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内容。杜塞尔从这个简单的假设出发,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不是中国,也不是葡萄牙,而是西班牙开始了世界体系,并随之开创了现代性。
那些自称为天主教徒的西班牙人,通常主要是以不义、残忍而血腥的战争,去毁灭那些可怜的民族并将他们从地球上抹去……他们之所以屠杀残害多得难以计数的人,是因为这些天主教徒的最终目的是获取黄金,在短时期内暴富,并由此上升到与他们的功德不相称的高级阶层。应该记住的是,他们那世界第一等的永不满足的贪欲和野心,就是他们恶行的原因。[3]15
根据《解放政治》的解释,之所以不是在中国开始世界体系并开创现代性,是因为中国不可能发现美洲,因为对中国来说,跨区域体系的中心在其西面的印度和穆斯林世界,[6]131-132而不是韦伯等人论证的15世纪的中国比欧洲落后,中国当时无论在科技上、政治上,还是商业上,甚至人道主义上都不落后。[3]6-7杜塞尔正确地指出,事实上,在1405至1433年间,郑和曾七次成功地由海路到达世界体系的中心,王钦于1497年紧随其后,尽管最终未能超越郑和的航行记录功绩;中国还向东航行至阿拉斯加,甚至远至加利福尼亚及其南部。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原因妨碍了它对外贸易的发展;另外还因未能在东部航线发现中国商人感兴趣的东西,因而在距离跨区域体系中心更远的地方放弃了这项艰巨的冒险计划。葡萄牙也向着东方的印度而去。但对葡萄牙国王来说,哥伦布试图从欧洲到达中心的提议,同他宣称发现新大陆一样极其愚蠢。甚至哥伦布本人直至临终时也未能从主观上突破跨区域体系的视角,让自己接受世界体系的新阶段。因此,尽管葡萄牙一次又一次地为处于边缘的欧洲打开了通往跨区域体系的道路,但它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因为虽然葡萄牙业已试图控制阿拉伯海域的商贸交换,但它没有办法生产东方的产品,如丝织品、热带产品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黄金等。[3]7-9换句话说,它是个中间人,而且永远是穆斯林世界、印度和中国的边缘力量。西班牙既无法经由陆路到达跨区域体系的中心(被穆斯林彻底堵截),又无法沿西非海岸前往地处东方的印度(被葡萄牙所垄断),因此它只能冒险西向横渡大西洋,最终偶然撞上了美洲,并因此缓慢而无法阻止地开始走向了登上第一次世界霸权宝座的征程。
但在这些全球意义的相互影响的现象面前,许多哲学流派的理论都显得天真荒谬、不负责任,且不恰当地怀疑人性,甚至有沆瀣一气的味道。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心”如此,且在边缘的拉美、非洲和亚洲更糟,这些地区的哲学家们毫无例外地把自己关在毫无生气的欧洲中心主义传统这座“象牙塔”中。[3]21一方面,实体论的发展主义观点将现代性理解为完全的欧洲现象,并从17世纪以来扩展至所有“落后”文化,因此现代性是一个必须加以总结的现象。阿佩尔和哈贝马斯等理性主义者对此抱批判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欧洲的优越性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形式上的。另一方面,尼采和海德格尔的保守虚无主义观点否认现代性的积极性,提出一种事实上没有出路的方案。虽然后现代主义者由此关注到边缘,但矛盾的是他们亦持发展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极度缺乏批判力,因此没有尝试为边缘国家,或边缘民族,或被中心以及被边缘中少数人所统治的绝大多数人提供可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出路。总而言之,理性主义者和后现代主义者之间的任何争论都没有突破欧洲中心论的视角,而且尽管欧洲中心的观点反映出“现代性危机”这个问题,但它只考虑欧洲中心的重要性,极力缩小边缘的重要性。“而越是真正的哲学,越应该清醒地选择被征服者的视角,使自己成为其合法利益的代言人。”[9]杜塞尔因此从边缘出发,将现代性过程认作是世界体系的业已指明的理性运作,并致力于重新恢复现代性中可挽救的部分,停止世界体系中的控制与排斥。简而言之,即解放从现代性一开始就被否定的边缘。值得注意的是,它不仅仅是对工具理性的替代,而是要瓦解发展至今500多年的世界体系本身。杜塞尔强调,战胜怀疑人性的经营理性(全球管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自由主义(政治体系)、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形态)、大男子主义(色情文化)、白种人的统治(种族主义)和破坏自然(生态学),是解放各种被压抑、被排斥类群的先决条件。[3]20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放哲学明确将自己定义为超现代哲学。
最后,杜塞尔指出,“在纳粹进行的大屠杀之前,现代性还进行了两次大屠杀:一个是美洲的征服,超过1 500万印第安人遭到灭绝;另一个是种族主义奴隶制,1 300万非洲人遭到灭绝,其中超过30%死在大西洋的运输船上”。[10]166正如鲍曼所说,大屠杀突然昭示,“人类记忆中最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于秩序的涣散,而是源自完美无缺、无可指责且未受挑战的秩序的统治,它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并对指令的精神和用语细致有加的人所为”。[11]换言之,大屠杀不是一些反常的人所为,而是为秩序而尽责的人所为。[10]166因此,解放哲学的关键不是如何在现有秩序下做个好人,而是如何从旧有秩序转入新的秩序。正是基于这样的洞见,杜塞尔最近格外关注政治问题,并重新弘扬似乎被历史贬抑和否定的乌托邦思想。
他在关于《走向世界性伦理观》的演说中,提出了政治问题的重要性, 倡议建设关于“政治”的新神学框架,推动关于“国家”的创造性的神学研究,为重建“上帝之国”搭桥。[12]他在该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政治学二十篇》(2006年)和3卷本的《解放政治》(2007—2011年),这些著述“是对其前中期伦理话语的延续,因为其前中期的伦理著作就包含了对政治问题的探讨”。[10]26在这些著述中杜塞尔反复申言,“对他者的尊重是对未来的希望,是对一个新秩序的正义的希望;是超越现状、超越罪、超越当前统治的渴望;是解放实践——在墙缝中打开缝隙,建造未来世代能够穿越的大门——的源头”。[10]161换言之,解放来自他者,希望来自他者。这是末世的、真正的、乌托邦环节,要实现这一目标,“不但要在乎人的全面解放、自私和罪的解放,更要在乎政治和社会的解放”。[13]208杜塞尔进一步指出:在政治上肯定他者,是政治伦理的绝对准则,一个政治行动的正义性或善性在于走向肯定、尊重穷人和被压迫阶级,以及依附民族,让其是其所是。[10]161这个对未来的希望,关乎整个边陲世界的解放或灭亡!因此,面对当前全球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动荡及混乱,杜塞尔从伦理角度批评了现存资本主义模式,并通过其解放伦理观来指引建立一种“制止生活遭到破坏”的乌托邦。换句话说,他凭借生命权利、结构性罪恶等概念,把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先知性批判注入伦理论述,极力推崇一种“与财富文明对立的生命文明,或说尊严文明。这以生命或尊严作为经济体系的内在价值,是神学反省导致的伦理结论,而非把马克思的一套经济分析拿来萧规曹随”。[13]203
不仅缺乏具有乡村旅游开发经验的专业人才,也缺少葫芦雕刻工艺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且雕刻艺人多为中老年人,存在较为严重的人才断层现象。
四、小结
综上所述,杜塞尔的解放哲学同大多拉美哲学流派一样,在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批判性争论中形成自己的立场。杜塞尔通过批评欧洲中心主义者对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葡萄牙和西班牙征服与殖民美洲,以及欧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等现代性起源的决定性事件所持的片面、狭隘的观点,将视角置于现代世界体系的观念批判之中,不仅研究其中心,而且考察其边缘,以获得对人类历史的全球性看法。但他并未采取彻底拒绝反欧洲中心主义的激进立场:这种立场视西方文化和哲学为纯粹特殊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错误的和极权主义的东西,甚至普遍的理性和伦理学也被视为欧洲中心主义的东西而遭到拒绝。[9]
杜塞尔之所以批判欧洲中心主义,是因为欧洲中心主义者将欧洲的“特殊性”直接等同于“普遍性”,而未进一步确证。他认为可以断言,“所有普遍的道德……实际上总是和一种被给予的、俗成的伦理生活(例如欧洲—北美的,保守的,自由的或社会民主的)联系在一起的”。[9]马里奥·罗雅斯·埃尔南德斯对此评价道:“如果人们跟随杜塞尔的思路,那么其论题可以被应用于他自身——而且必须被应用于自身——因此按照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他同样也很少能够批判西方哲学,也不能提出解放的伦理—普遍原则,因为他所表达的一切都源于其自身的俗成的伦理生活,例如拉美的或墨西哥的。”[9]杜塞尔解放哲学尽管带着从个别走向普遍的目的,却从不自诩文化中心,他只想真诚地表达本民族文化,以便让拉美人认识到他们的民族性中包含着世界性,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深刻的自尊。换言之,它具有鲜明的第三世界立场与民族特色,是被中心边缘化地区的哲学、贫穷民族的哲学,是通向全人类解放的哲学。此外,杜塞尔的解放哲学思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鉴于拉美不在现代化的欧洲中心范围之内,杜塞尔力图创立一种未来的、世界性的、后现代的解放哲学。在他看来,这种解放哲学“将是哲学的第四纪以及人类—逻辑第一纪:它超越了希腊的自然—逻辑、中世纪神学的、现代的理念—逻辑,但又在一种能够解释这种哲学观念的历史现实中吸收了以往的哲学”。[14]然而,即便杜塞尔本人也坦率地承认,解放哲学所开放出来的“世界历史只是部分的、初步的、指示性的准历史”,事实上它“还需要世世代代加以确证”。[6]XV换句话说,由于杜塞尔的雄伟抱负与其绝对微弱的理论解释力之间的矛盾,使其解放哲学容易陷入一种先验的、不证自明的乌托邦幻象之中。
参考文献:
[1]卓新平.当代亚非拉美神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530.
[2]杜塞尔.跨现代性与文化间性——基于解放哲学视角的一种阐释[J].朱慧玲,译.世界哲学,2016(2):17-37.
[3]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三好将夫.全球化的文化[M].马丁,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4]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北京:商务印刷馆,1963:148.
[5]DUSSEL E.Ethics of Liberation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and Exclusion[M]. 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13:1-32.
[6]DUSSEL E. Politics of Liberation[M]//World History and Criticism. London:SCM Press,2011.
[7]王晓辉.论约翰·霍布森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及其局限[J].理论月刊,2013(3):56-59.
[8]罗伊.1909年以来的拉美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中心论”与“拉美例外论”的超越[J].冯昊青,陆宽宽,译.世界哲学,2016(2):38-49.
[9]马里奥·罗雅斯·埃尔南德斯.拉丁美洲哲学:一种放弃终极辩护的批判理论?[J].牛文君,译.哲学分析,2010(2):35-44.
[10]叶健辉.托帮:拉丁美洲解放神学研究初步[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11]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99.
[12]刘承军.“解放神学”死亡了吗?[J].拉丁美洲研究,2007(1):62-67.
[13]郑顺佳.天理人情[M].北京:团结出版社,2011.
[14]索萨.拉丁美洲思想史述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276.
On the Criticism of Dussel’s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to the Eurocentrism: Marxist Philosophy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
FENG Haoqing1, LI Weiwei2
(1.InstituteofNationalGovernance,ZhejiangNormalUniversity,Jinhua321004,China; 2. PartySchool,QingtianCountyCommitteeofCPC,Qingtian323900,China)
Abstract: As a kind of critical cultural philosophy, Dussel’s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creatively links history with the Eurocentric modernity by means of cultural analysis, and criticizes the universalist presupposition of Eurocentrism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In these ways, Dussel reconsidered the world history and deconstructed the universal view of history of Eurocentrism which rejected and depreciated non-European cultures. Thus, he maintained the variability and difference of each community or national culture and affirmed the value of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 were ignored by modernity. In addition, he also made profound reflections on Eurocentrism from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crisis of modernity. He tried to defeat the world system that had been developed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liberate the peripheral cultural traditions that were denied at the beginning of modernity, and establish the utopia of the poor people from the periphery.
Keywords:Enrique Dussel; the philosophy of liberation; Eurocentrism; world system;modernity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35(2019)02-0051-07
收稿日期:2019-01-08
作者简介:冯昊青(1973—),男,云南大理人,浙江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哲学博士;李伟伟(1992—),男,福建宁化人,中共青田县委党校教师,哲学硕士。
基金项目: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探索历程、理论成就及其新进展”(17NDJC271YB)
(责任编辑 吴月芽)
标签:欧洲论文; 现代性论文; 中心论文; 杜塞尔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世界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论文; 二十世纪哲学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马克思主义拉美化的探索历程; 理论成就及其新进展”(17NDJC271YB)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论文; 中共青田县委党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