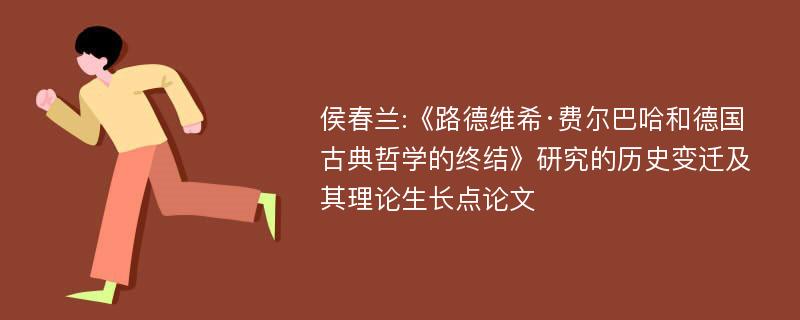
摘 要:总体而言,关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研究范式主要从20世纪的“贬低论”和“肯定论”的相互交错中发展到在回应争论中形成的“反思性”研究路径。具体来看,当前研究聚焦了五大主要热点问题,并形成了五大理论生长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哲学的终结问题”“《费尔巴哈论》与《提纲》的比较问题”研究。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捍卫、宣传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经过130多年的历史沧桑,已经证明了它的重要性和历史意义,值得我们精读、深读和常读。
关键词:《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 研究范式 理论创新
作为马克思亲密的战友和忠实的革命伙伴,恩格斯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事业鞠躬尽瘁、奋斗终生。《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写于1886年1-2月,最初发表在《新时代》杂志,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单行本。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经典著作中,《费尔巴哈论》“简短而精悍”,是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文本,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列宁指出,《费尔巴哈论》“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7页。。《费尔巴哈论》最坚决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也是宣传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及时雨”。《费尔巴哈论》发表已经130多年,历史证明,再读文本、再梳理其当前研究现状,对我们再阐述原著的经典思想、激活理论的再创新以及关注现实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费尔巴哈论》研究的历史变迁
《费尔巴哈论》自发表以来,从西方到东方,从国外到国内,主要的解读范式呈现出从基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系研究的“贬低论”倾向到回应批驳中的“肯定论”与“反思性”研究的变化。思想理论阐述和学术研究争论的流变,既呈现出中西方的范式差异,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各种社会思潮之间的博弈起伏;既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展息息相关,也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历史现实紧密联系。
当乔治·李希特海姆(1961年《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和批判的研究》)、诺曼·莱文(1975年《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特雷尔·卡弗(1983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等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之间的对立作为20世纪的一项“重要发现”而加以论证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贬低恩格斯的“马恩对立论”终于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显学”。[注]从德国实证主义者巴尔特到19世纪末的新康德主义者、新黑格尔主义者,再到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和卢卡奇、柯尔施、法兰克福学派施密特、阿多诺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南斯拉夫实践派马尔科维奇、彼得洛维奇、弗兰尼茨基,新实证主义者沃尔佩等都指责恩格斯《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等著作中的哲学思想,逐渐形成了“马恩对立论”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西方学者对《费尔巴哈论》的研究和评价基本上持否定和批判态度。20世纪末以来,“马恩对立论”逐渐走向“相对温和”的状态,对《费尔巴哈论》的认识也改变了之前的极端否定。例如,在《恩格斯传》中,麦克莱伦一方面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性,另一方面也强调了恩格斯的历史贡献。[注][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08页。西方学者多以寻找“马恩对立论”的文本证据来研究《费尔巴哈论》中的具体问题,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姆、施密特,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彼特洛维奇、米凯增、马尔科维奇等对恩格斯的“实践观”进行批评和责难。除了卡弗、莱文,卡尔·巴列斯特雷姆、麦克莱伦等也都对《费尔巴哈论》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反对意见。[注]参见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综论I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42、295、148-149页。
“在医学院的解剖学课上,有很多东西要学,”斯普金斯解释说,“我们医生需要了解很多重要的血管,但不是全部。这些血管隐蔽,但在解剖学上并非完全不为人所知,因为它们可能是头部损伤后细菌引发脑膜炎的通道。”斯普金斯困惑了好几年才了解些端倪,找到了正确的方向。
2005年10月,“纪念恩格斯逝世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俄罗斯学者巴加图利亚在会上指出,恩格斯的理论遗产蕴含着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必须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观点上的基本一致,同时他们之间也有分工,存在着一种互补原则。”[注]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综论I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34、122页。在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制造的“马恩对立论”的观点面前,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定不移地维护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关系,肯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贡献,坚持把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认为恩格斯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阐释者。普列汉诺夫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指出,“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出色的小册子里,对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观点,也以肯定的形式阐发过了。”[注]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第136-137页。海因里希·格姆科夫、列·伊利切夫、叶·斯捷潘诺娃等苏联学者都肯定了《费尔巴哈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重要作用。又如,凯德洛夫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奥伊泽尔曼从哲学的变革意义等方面肯定了恩格斯的哲学贡献。苏联学者的早期研究对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论是坚定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坚持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一致性观点,还是重在强调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差异,对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提出新探讨,《费尔巴哈论》的文本和思想研究使得国内学者在反思苏联研究范式和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尝试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范式。
1919年10月,由林超真翻译的《费尔巴哈论》在上海沪滨书局出版《宗教·哲学·社会主义》(第141-212页)。之后,彭嘉生、杨东莼、宁敦伍、青骊等翻译的《费尔巴哈论》陆续出版。[注]1929年12月,上海南强书局出版彭嘉生翻译的《费尔巴哈论》;1932年5月,上海昆仑书店出版杨东莼、宁敦伍翻译的《机械论的唯物论批判》(《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932年11月,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由青骊翻译的英汉对照版本的《费尔巴哈论》。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张仲实翻译的《费尔巴哈论》,1949、1967年又再版发行,社会反响热烈。[注]参见邱少明:《民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史(1912至1949年)》,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论文2011年。伴随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和深化,国内对《费尔巴哈论》的研究和解读也始终伴随这一历史进程并在不懈努力中。较为典型的有黄楠森、顾海良、萧灼基、朱传棨等在阐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以及恩格斯的个人传记时,均鲜明地肯定了《费尔巴哈论》对工人运动、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发展的重要作用,肯定了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等思潮影响下,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受到了挑战。国内研究主要在坚持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的一致性的同时,对各种“对立论”思潮提出了反驳。[注]聂世明:《如何理解历史发展的合力》,《郑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9-70页。与前者不同的是,在对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解方式提出质疑,并形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超越论”“实践本体论”“人道主义”“主体性”等理解的同时,高清海、俞吾金等对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等提出了不同看法,尝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做新的解释。[注]高清海:《哲学思维方式的历史性转变》,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95页;丛大川:《辩证法体系:马克思与列宁》,《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朱宝信:《从实践唯物主义看辩证法》,《理论探讨》1995年第4期;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二、“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研究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关于他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的伟大友谊进行了说明:“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他指出,共同创造的新哲学“这个理论用他(马克思)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8页。其实,“恩格斯从来也不仅只是马克思的解释者和助手——不论是在马克思生前或死后,始终一样——而是独立工作的合作者,虽然不能和马克思相等,但足以和他相比”[注][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95页。。虽然,恩格斯与马克思并肩作战近半个世纪,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信念,有着伟大的才华与智慧,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研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重大争论。从马克思主义诞生到整个20世纪(甚至当前研究中),“马恩对立论”不绝于耳。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热点,就是渲染马克思恩格斯的对立,以贬低恩格斯的理论贡献。马克思主义反对者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极力诋毁和歪曲恩格斯的哲学贡献,制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对立,以贬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从而达到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显然,这也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原因。基于《费尔巴哈论》,研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问题,基本上也是肯定与否定两大观点。
其一,以我国和苏联学者为主要代表,积极肯定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贡献,否定制造“马恩对立”的观点。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到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从科学原理的提出到不断地精确、深化和完善,从基本原则的制定到社会实践的运用和发展,从新世界观的产生到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每前进一步都离不开恩格斯的辛勤劳动和创造性贡献。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批判地阐述了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意义与局限性,“系统地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经验,全面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革命意义。”[注]黄楠森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34页。《费尔巴哈论》是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著作,是“科学地总结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领域四十年斗争的结果”[注]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38页。,“使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识别自己队伍中拥护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人,并且同他们展开斗争,使国际工人革命运动具有这样的觉悟水平,即懂得工人阶级、科学世界观和革命的阶级政党三者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注][德]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等:《恩格斯传》,易廷镇、侯焕良译,北京:三联书店,1975年,第468页。因此,“这是一部科学共产主义的卓越著作”[注][苏]列·伊利切夫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02页。,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教材”[注]李士坤:《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好教材——〈费尔巴哈论〉解读》,《高校理论战线》2006年第8期。。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之间的理论关系进行了全面的论述,视其为必须要还清的“一笔信誉债”,基本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继黑格尔之后,对马克思思想影响最大的便是费尔巴哈了,“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第二,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功绩,“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第三,恩格斯表明,“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发生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第四,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哲学并没有批判地继承黑格尔哲学,“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8页。《费尔巴哈论》基本准确地规定了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一般关系,是研究费尔巴哈与马克思关系的重要著作。
其三,与积极肯定和极端否定恩格斯思想的相比,后来的研究侧重于具体的分析模式。在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之间存在着一定理论差异的前提下,认为“马恩对立论”是带有偏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各自独特的理论个性和对于外部世界的不同的探索方式,“并没有导致两人理论的根本对立,相反,正是这种差异性,为他们在理论建树上的卓越合作奠定了基础。”[注]吴家华等:《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比较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9页。吴家华等通过比较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历史观和辩证法思想,揭示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麦克莱伦指出,包括《费尔巴哈论》在内的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确有重要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恩格斯有些“过于谦虚”了,即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有差异性,“这些思考不应以任何方式减弱我们对恩格斯为社会主义运动所做出的巨大贡献的赞赏。”[注][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臧峰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99、108页。美国学者约丹(J.D Hunley)以及利各比(S.H.Rigby)等新一代研究者,也大多怀着同情态度研究恩格斯,认为对立论者提出的“马克思是几乎完美的人道主义者,而恩格斯是几乎纯粹的实证主义者和决定论者”的观点是片面的[注]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综论I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80页;吴家华:《西方“马克思学”解构马克思主义的新动向》,《高校理论战线》2003年第11期。。法国学者米歇尔·罗伊、德国学者汉斯-迪特尔·克劳泽、雷纳特·梅尔克尔也都肯定了《费尔巴哈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作用。[注]李百玲主编:《经典作家著作研究IV》,《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1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年,第425页。
我们必须承认,恩格斯在包含《费尔巴哈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观、历史观以及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做了深入系统的论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恩格斯在其著作中表述的哲学观点和方法,就不可能有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注]徐琳、唐源昌主编:《恩格斯与现时代——兼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2页。马克思的逝世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一个重大损失,对亲密的战友恩格斯也是一个重大打击,“我仍然不能想象,这个天才的头脑不再用他那强有力的思想来哺育新旧大陆的无产阶级运动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58页。恩格斯是谦逊的,对马克思的赞美和维护是无以言表的,“既是他毕生活动的历史事实的生动写照,也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的最有力的批驳。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努力学习的崇高风范和光辉榜样。”[注]朱传棨:《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论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5页。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的绝大多数学者多是由于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系统把握而产生的误解。“马恩对立论”通过极力诋毁和歪曲恩格斯的哲学贡献,从而达到否定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但这一思潮反向地促进了对《费尔巴哈论》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和理解。
三、“哲学的基本问题”研究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9页。在总结人类认识发展史的基础上,恩格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并给出了精炼的概括。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对包括东欧在内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结合案例,因新模式增加了投资和融资,产生了财务杠杆。同时,提高经营杠杆至4.79倍,但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因此,风险较低,较之旧模式提高综合杠杆2.02倍,EBIT提高9%,节税效果明显,利于公司发展(表10)[1]。
其一,来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责难。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从形式到内容都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均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不是物质世界而是人本身,或者是人的实践活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能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相反,他们把“实践问题”“人的作用问题”“人的地位问题”规定为哲学基本问题。法兰克福学派弗洛姆、施密特,南斯拉夫实践派哲学家彼特洛维奇、米凯增、马尔科维奇等都对恩格斯的理论进行批评和责难。例如,弗洛姆在《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1966年)中提出,把物质和精神规定为谁第一性的论断是认识的形而上学问题,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既不是唯心主义也不是唯物主义,而是人本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结合。施米特认为,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概括是不科学的,是形而上学的,认为恩格斯把思维与存在对立起来,并将实践同主体的抽象活动混为一谈。南斯拉夫实践派皮特洛维奇、米凯增、马尔科维奇等认为,人的问题应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并认为马克思的中心课题是人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注]参见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0页。
其二,国内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肯定性研究。哲学基本问题是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现代哲学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面对批评与否定的观点,国内研究赞成并积极维护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一概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们探索世界的本源和认识世界的基本问题,是任何一个哲学体系都回避不了的问题,决定了哲学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并决定着对其他哲学问题的解决方式。哲学基本问题的概述“是对人类的认识发展史、特别是对近代哲学史最科学最精辟的总结和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卓越贡献。”[注]萧灼基:《恩格斯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77页。余其铨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一书的第六章中集中论述了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学术争论,对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和恩格斯的根本分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注]参见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11页。苏联学者凯德洛夫指出,恩格斯对任何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解释,“就在于他使这个问题超出了旧哲学的代表们所作的那种传统解释意义上的纯粹的认识论”[注]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综论I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何中华指出,从划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角度,恩格斯不是在形式的意义上而是在内容的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在恩格斯的语境中,“哲学基本问题”不只是“过去时”的,同时也是“将来时”的,它并没有随着哲学的终结而失效。[注]何中华:《恩格斯在何种意义上提出哲学基本问题——再读〈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年第2期。如果说何中华的观点与此前持积极肯定观点存在分歧,那么认为过高评价哲学基本问题的观点就显得具有更大的差异性了。例如,胡大平就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一直存在过高地评价哲学基本问题的倾向。但是,胡大平也没有就此否定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述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这一论述科学地说明了新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区别,这是非常重要的。[注]参见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403-416页。同样,不论是从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关系,还是恩格斯提问的语境研究,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俞吾金、吴晓明等提出了新看法。从“方法论”[注]参见吴晓明、俞吾金等:《哲学基本问题所蕴含的方法论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以及哲学“类型理论”[注]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3页。角度,俞吾金指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不再成为‘哲学基本问题’,而是下降为一种特殊的哲学类型——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注]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2页。后来的解释者和研究者将恩格斯的这一论述简单化了,磨平了马克思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的差异。需要关注的是,俞吾金提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仅是知识论哲学的基本问题之后,接着指出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从而进一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立场。
第二,深刻理解恩格斯对于哲学历史发展的一般概括。恩格斯指出,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受到外在打击而停止,而是以某种方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从而在其后产生了新的科学方向。恩格斯是从哲学革命的语境中提出“哲学的终结问题”,像历史唯物主义给予唯心主义历史观以致命打击一样,辩证的自然观也同样使一切自然哲学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东西。在实质上,是从哲学向世界观的转变;在思维方式上,是从形而上学向辩证法的转变;在形式上,是旧式体系哲学向实证科学的转变;在研究的内容上,则是从普遍规律向各种具体问题的转变;在功能上,从解释世界转向改变世界。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新世界观,一开始就是表达工人阶级心愿的,它受到了工人阶级的欢迎和赞赏,继承了以往哲学的精华。因此,只有工人运动才真正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才能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5页。,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使命和科学本质。
四、“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问题”研究
其二,在持有“马恩对立”的观点时,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责难恩格斯思想的两个方面。首先,认为恩格斯歪曲马克思思想,在把马克思主义系统化的过程中存有教条化的嫌疑;其次,否定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例如,西德学者卡尔·巴列斯特雷姆等认为,恩格斯在把马克思主义发展为包罗万象的、僵硬的体系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注]参见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综论I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295页。莱文指出,恩格斯把唯物主义解说为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在认识论方面主张“摹写论”,而这与力图克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绝对分割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在认识论方面是完全不同的。[注]参见林进平主编:《马克思主义综论II》,《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第24卷,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342页。卡弗的批判同样体现在高扬马克思以贬低恩格斯,认为恩格斯在树立世界观权威的过程中消解了实证精神,而这主要是由于恩格斯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高等教育,缺乏像马克思那样在区分人类实践的专业学术作品中显示出来的怀疑主义精神。[注][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5-146页。
第一,《费尔巴哈论》对列宁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与恩格斯一样,列宁认为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环节在于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注]《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页。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叙述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过程便引用了恩格斯的论述,“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在《马克思的学说》一文中,列宁也指出,“从1844-1845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从列宁的基本认识中可以得到:其一,列宁赞成恩格斯的看法,也认为马克思通过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克服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其二,列宁没有论及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作为马克思与黑格尔的“中间环节”的“在好些方面”的这一提法。[注]《列宁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2、308页。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中,列宁指出:“唯物主义近在咫尺。恩格斯说得对,黑格尔的体系是颠倒过来的唯物主义。”同样,列宁在《谈谈辩证法》中,用“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图式理解哲学发展史。虽然,梅林赞同恩格斯的基本看法,但与列宁不同的是,他侧重于阐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马克思思想的影响,并强调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局限性。[注]参见[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68页。梅林明确了《费尔巴哈论》对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哲学关系确定的重要影响:“我们不能指派自己那样一个任务,即在这里以坏的形式,重复恩格斯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经典著作中,早已充分明白地确定下来的东西。”梅林指出:“就最广泛的意义说来,这一历史转折点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马克思以之开始了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恩格斯以之结束了他对于卡莱尔的批判。”[注][德]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吉洪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7页。可以看到,恩格斯、列宁和梅林对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关系的理解,均坚持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是“中间环节”这一基本概括。这一理解“图式”被作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一般的理解,影响深远。
分别利用葡萄糖、正十六烷、柴油、原油、石蜡、菲、萘、芘为碳源,考察Halomonas sp.DH1利用不同碳源产表面活性剂的情况。
第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的终结问题在国内的讨论越来越多,并构成马克思恩格斯“一致论”或“对立论”争论的焦点之一。对这一问题的一般分析,国内已经具备较好研究传统。例如,徐长福对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命题及其相关表述的梳理和含义分析,特别指出,朝着体系化方向发展的后世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定程度上背离了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注]徐长福:《论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学术研究》2002年第11期;《恩格斯哲学终结观的若干比较与分析》,《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不同于徐长福归咎于后来的研究者,另一种观点直接对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概述提出质疑。[注]俞吾金:《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张建军:《论<终结>中的“唯物主义”的双重语义:为恩格斯辩护》,《江海学刊》2004年第6期。除了以上研究,学者基本认同恩格斯所提到的哲学发展的窘境,从文本着手对这一问题的提法的具体语境进行限制。胡大平侧重于研究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唯物主义发展史的阐述,指出理解这一问题是具有理论界限的。[注]胡大平:《回到恩格斯——文本、理论和解读政治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1页。侯才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终结”指的是那种对终极问题追问的传统哲学的终结,把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终结”看作“哲学研究重心”的转移,在不同于恩格斯的意义上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看作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现代哲学。[注]侯才:《对哲学及其当代任务的一种审视——兼评恩格斯哲学观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关于恩格斯的哲学终结论,俞吾金提出三个质疑[注]俞吾金在《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第一,如果哲学从自然和社会中被驱逐出来,马克思的历史观应该属于什么学科?第二,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并不主张使哲学与社会分离开来。第三,如果新哲学面对的仅是“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那么极为关注现实与人的活动的马克思哲学该置于哪个领域?。结合以上研究,这三个质疑实际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哲学”性质、基本问题及与“实证科学”关系的再考量。恩格斯总结历史的经验,提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哲学发展的坚实基础。“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4页。任何一种哲学的思维形式,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改变着自己的形式。古代朴素自发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到15-18世纪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再到19世纪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自然观,进而发展到马克思主义科学自然观,这都是由自然科学的发展决定的,正好符合了《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对三大规律对人的思维的解放作用的描述。恩格斯从哲学发展的历史出发,强调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指出哲学必须及时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来发展自己的理论,科学地阐述了哲学与实证科学的关系。伊·费切尔、诺曼·莱文等却认为“恩格斯根本不是一位哲学家,充其量只是一位研究自然界普遍规律的实证主义者。”[注]参见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塞克·科拉科夫斯基更是曲解恩格斯,认为哲学对具体科学来说是多余的,是装饰品。这些论断显然是违背文本事实的,是“断章取义”,“用歪曲恩格斯的思想来反对恩格斯”[注]参见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9页。。
尽管,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勾勒自己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时未提及费尔巴哈,但也不能就此忽略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的基本概述,从而认为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哲学在马克思创立新世界观过程中并不重要。研究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对费尔巴哈的定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极其重要。恩格斯的重要论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被线性地理解了,一定程度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黑格尔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折中主义的庸俗理解。对于以往把马克思哲学形成和演化过程描述为:黑格尔或青年黑格尔主义式的唯心主义-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马克思自己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三阶段的思想,俞吾金等的确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视角。但是,也要注意到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质疑“马克思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面也存在理解的偏颇。若否定了恩格斯所讲到的马克思哲学的“一般唯物主义”立场,我们又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实践的一般看法。因此,争论的焦点依旧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问题,以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一场哲学革命。
五、“哲学的终结问题”研究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同时提出了一个关于哲学史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重大理论问题,被概括为“哲学终结论”。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是以往哲学发展的固有结果,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意义和革命性质使人们意识到,过去对“绝对真理”的追求是无法达到的,“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这种意义上以往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6页。所以,人们应该在实证科学和辩证思维对科学之科学的概括和总结中把握相对真理。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64页。
第二,新时期的研究有了新变化,以俞吾金教授《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与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两本著作较为典型。吴晓明指出,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关于马克思和费尔巴哈的关系的规定基本是正确的,只是恩格斯的“提示性的解释方案”并没有得到更好的深入探究。俞吾金等提出“尽管费尔巴哈的思想对马克思有一定影响,但断定在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阶段是缺乏依据的,把一般唯物主义的立场看作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不符合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实际进程的。”[注]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页。区别于恩格斯、列宁的观点,俞吾金的观点“否认的只是费尔巴哈的抽象唯物主义对马克思的重大影响,而并不否认费尔巴哈的某些哲学见解为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提示”[注]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2页。。
3.牛支原体肺炎。犊牛眼和鼻腔有轻度的粘液性或脓性的分泌物排出。体温38.5℃~39.5℃;呼吸频率可能从正常到100次/分钟,脉搏正常。有时表现单发性剧烈干咳,胸部听诊,有哨笛、哮喘样啰音,但呼气时更多见一些,且在胸部前腹侧最为常见。
也有学者指出,并不能说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已是十全十美了,后续研究应该把理论向前推进。例如,易杰雄、贺来、侯才等从哲学变革和创新等角度指出,要深入研究说明哲学基本问题所蕴含的内容、出场意境等基本问题。[注]参见易杰雄:《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表述问题》,《学术月刊》1984年第7期;贺来:《重新反思“哲学基本问题”——哲学观念变革的重大课题之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孙和平:《论恩格斯如何扬弃“哲学基本问题”》,《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徐长福:《论恩格斯关于哲学终结的思想》,《学术研究》2002年第11期;侯才:《对哲学及其当代任务的一种审视——兼评恩格斯哲学观的现代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6年第2期。以上研究可以看出,不论是赞成还是质疑恩格斯关于“哲学的基本问题”的概述,实际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本质、功能等基本问题的阐发与关切。
六、“《费尔巴哈论》与《提纲》的比较问题”研究
在把《费尔巴哈论》送去出版前,恩格斯重新翻阅了《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对于没有写完的费尔巴哈一章,深感无法达到对费尔巴哈哲学本身的批判。巧合的是,恩格斯“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现在作为本书附录刊印出来。”《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是作为《费尔巴哈论》的附录首次发表的,“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献,是非常宝贵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9页。恩格斯给予了很高评价。但是,恩格斯应该没有想到,这同时发表的两个著作,在后世的研究中竟多用来思考、甚至质疑他和马克思思想传承的重要文本依据,而且研究者多使用《提纲》来反对或否定《费尔巴哈论》的观点。
据悉,昆明万达广场已将今年国家四次降价政策传递给终端用户,并规范了终端用户用电收费方式。昆明供电局将作为云南电网范围内配合清理规范转供电环节加价工作的示范供电企业,在全省范围推广。(李琳 陈丹妮)
第一,西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论”中,就有观点认为从马克思的《提纲》到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存在着一个从能动主义到机械简单唯物主义的转换。卡弗就指出:“恩格斯对这个提纲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恩格斯把此文的地位提升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之上,这与马克思在1859年序言中的论述是十分矛盾的。”[注][美]特雷尔·卡弗:《马克思与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姜海波、王贵贤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6页。援引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实践称作“实验和工业”的例子,以及与《提纲》马克思实践思想的对比,诺曼·莱文指出,在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中根本没有“实践”的概念。法兰克福学派也指出,恩格斯的实践观是非辩证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经验论,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与极端的对立论不同的是,麦克莱伦的观点饱含同情。他指出,恩格斯关于“实践”的思想是短缺的,但对这个原理最精确的表述——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由恩格斯作为他自己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附录首次发表的。恩格斯指出:“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2页。恩格斯的表述很明确,是把科学实验和工业生产看作实践的主要内容,同时又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上各类观点的分歧在于对实践的不同理解,批评者与恩格斯持截然不同的意见。莱文把实践只是理解为人的主观活动,是黑格尔的主观性、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而否定实践的物质前提和客观基础。与许多西方学者的批评一样,莱文也认为人的实践规定着世界的存在,物质世界不过是人的实践的产物。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相悖的。[注]参见余其铨:《恩格斯哲学与现时代——评“新马克思主义”对恩格斯的责难》,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19-127页。
由于人口数量不断增加,相应的建筑数量也在逐年递增,导致目前建筑非常密集。密集的建筑物会导致建筑内的用电设备数量增多,线路也因此变得错综复杂。对于电气线路的铺设问题,我国已经给出了具体的规范,电气线路必须铺设在地下1.4m以上的位置,且保护层的厚度不能低于3cm。但是目前,很多建筑企业在铺设电气线路时,忽略了对电气线路进行保护,存在很多安全隐患。
第二,在国内研究中,俞吾金提出马克思强调的是实践、本体论维度和人的问题,而恩格斯强调的则是自然界、认识论维度和纯粹思想的问题,这说明“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和马克思的《提纲》所蕴含的哲学思想之间存在着若干重要的差异”[注]俞吾金:《论恩格斯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差异——从〈终结〉和〈提纲〉的比较看》,《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与西方对立论观点所认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的差异不同的是,俞吾金虽然指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两篇著作中呈现的不同哲学思想,但他并不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存在绝对对立,“在恩格斯做过改动的《马克思论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原文《提纲》之间并不存在实质性的差别”[注]参见俞吾金:《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马克思哲学的基础理论和当代意义的反思》,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8页。。
他漫无目的独自行走在大街上,茶楼、饭馆,就连洗手间到处都张贴有“禁止吸烟”的字样,行人举止文明,精神饱满,洋溢着自信、幸福的笑容。他从口袋内掏出香烟,烟盒上面标有“吸烟有害健康,戒烟可减少对健康的危害”。他想起老婆的反对,儿媳的忠告,特别是自己的身体危害,毅然决然把烟和打火机丢进了垃圾桶,用手在脸上猛抽了几下,“不许再抽了,是要戒烟了,抽下去要死的!”
的确,《费尔巴哈论》所阐发的思想对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解释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苏联和国内学术界,俞吾金的“差异论”在国内引起了较大回响。王昌英撰文指出,“将恩格斯与旧唯物主义者等同起来,而与马克思对立起来”,是对《费尔巴哈论》的误解,而不是新解。[注]王昌英:《也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差异——读〈提纲〉、〈终结〉和俞吾金的〈差异〉》,《无锡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与王昌英观点类似,朱传棨等指出,《费尔巴哈论》与《提纲》不仅在理论原则、基本观点上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在所要达到的根本目的上也是完全一致的。[注]朱传棨:《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提纲〉与〈终结〉的“对立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4年第1期;郭星云:《论马克思的〈提纲〉与恩格斯的〈终结〉的“对立论”》,《江汉论坛》2002年第8期。同样,区别于将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对立的“差异论”,国内学界虽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形式上和某些具体内容阐述、或对某些论点强调时,在写作背景、批判具体对象、形式和历史作用等方面有着不同,但这并没有导致二者思想上的本质对立。[注]臧峰宇:《马克思之后的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兼及〈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解读》,《学习与探索》2009年第6期。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等著述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在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同时阐明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意义,其基本观点是符合马克思思想的。由于恩格斯论述的重点特别是适应国际工人运动新形势的说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某些方面有所突出,对另一些方面未予强调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状况确实呈现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关系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回到马克思”“马恩对立论”或“差异论”在利用恩格斯肢解或质疑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如说这些观点反思和解构的是以苏联哲学为代表的解读模式,而东欧马克思主义以及国内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实现解放思想。
尽管学术界对《费尔巴哈论》的研究不论是在焦点问题还是就某些具体观点方面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但是谁都不能否认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创立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结合《费尔巴哈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对象、结构和功能的讨论,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问题的发难。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形而上学本体论,或者反辩证法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不得不说带有一定的攻击性和意识形态色彩。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路径方面无法达成共识,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呈现不同意蕴,使马克思主义的形象呈现各种各样的面貌。对《费尔巴哈论》的写作背景、基本思想、文本内容及影响的研究中,学者较为重视国内外研究状况,在回应不同阶段的学术争鸣中,力图建立自己的解释逻辑与话语体系。同时,捍卫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不断开拓着理论的新视野和研究的新境界。当然,克服教条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对基本原理、范畴的现实性和历史局限性进行广泛讨论和深入研究。
中图分类号:A811.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71/j.cnki.35-1334/D.2019.01.007
作者侯春兰,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贾向云〕
标签:恩格斯论文; 费尔巴哈论文; 马克思论文; 哲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理论与评论》2019年第1期论文;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