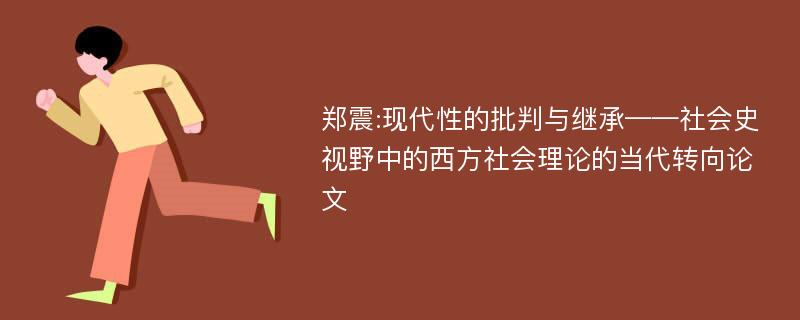
摘 要:曾经主导西方社会学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核心价值观是西方主流现代性的绝对主义的主客体二元论,这一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思想的开端,然而只是在近代西方世界才得以真正形成。20世纪以来的一系列事件促使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们在一种相对主义精神的指导下去批判和超越绝对主义的主客体二元论,然而这一工作在克服主客体二元论方面依然是不彻底的。
关键词:现代性;西方社会理论;绝对主义;主客体二元论;相对主义
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方社会理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视角,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社会理论的思想地图。这一历史事件的缘由何在?它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和思想意义?又存在着哪些局限性?对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具有怎样的启发和挑战?这些问题正是本文所试图解答的。不过我们并不打算单纯地进行一种抽象的理论分析,而是将思想史视作社会史的内在构成,尝试从包含着思想史在内的社会历史变革的角度来阐明这一理论事件的前世今生。这当然不是要将思想史的问题还原到所谓的非思想史的社会历史生活中去,仿佛思想不过是由非思所决定的派生事件;而是主张思想史是社会史的内在构成,它既有自身相对独特的逻辑和特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与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活水乳交融,这里不存在一种简单的还原论的逻辑,而是在一个整体内部的关系现象。只不过我们的研究将着重于考察思想如何从更加广泛的社会历史现实中汲取其存在和变革的动因,把思想作为多种社会历史因素共同建构的过程性关系事件来考察,而较少关注于社会理论思想在关系的轨迹中如何参与到社会世界的建构之中。因此我们的研究的确具有一种明确的分析性质。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意识到,思想史的变革也还是有其相对独立的内在逻辑特征,那些在分析上属于非思想史的社会历史因素的变革对于思想史的影响更多地还是通过激起学术领域内部的纷争而实现的(1)之所以说是“分析上的”,就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社会史是一个关系性的整体,任何一种社会史的因素都只能是一种关系性的建构。我们不能否认在思想之外的其他因素中依然可能并且确实常常存在着理论思想的建构。因此说某些因素影响另一些因素,往往只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历史限制之下的分析上的策略(相对于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某种社会历史现象具有时空上的先在性,并对前者发挥某种特定的因果作用),社会理论思想就如同其他各种社会历史现象一样,就其根本而言,在本体论上既不可能是纯粹的因,也不可能是纯粹的果。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社会历史性的因果分析,而不是荒谬地寻找一般性的因果决定。,不同作者群体之间的影响和斗争才是思想史地图得以形成的最为直接的动力,因此这一维度的讨论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一、前转向时期的主导视角
我们在此所谈论的西方社会理论与社会学这一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不仅是因为大多数社会理论家对于社会学都有着明确的专业认同(尽管并不总是唯一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思想与社会学这门学科的思想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他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式无一不体现着深刻的社会学烙印)。因此,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就具有了尤其重要的意义。这门产生自19世纪欧洲的学科自然少不了那个时代的风格和烙印,它为我们展现了前转向时代的社会理论的主导精神。我们可以将这种精神称为是主流现代性所持有的绝对主义的主客体二元论,它在社会学的思考中落实为两种紧密相关的主导视角,这就是实证主义和实在论。
尽管实证主义和实在论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存在分歧(2)如实在论者赞同有所谓无法被经验到的实在——例如社会结构,而这是实证主义者的经验主义所无法接受的(参见[英]贝尔特《二十世纪社会理论》,瞿铁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251、252页)。,但是它们却毫无争议地分享了具有绝对主义色彩的主客体二元论这一现代性的主流精神,从而分享了这一精神的某些核心价值观。我们可以以如下的方式来描绘这一二元论的基本预设,它主张主体和客体是性质上截然对立的两种存在,它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还原另一方,这就构成了二元对立的貌似事实的状态。主体被视为是拥有自由意志和绝对理性能力的、有意识的个体心灵或自我,而客体则表现为在这一个人主体的面前所展现出的、不以主体意志为转移的、绝对客观的世界,它遵循机械的因果决定论的法则,存在于绝对的时空之中。这种关于主体和客体的思想并不是通常所谓的两分法(无论是事实上的还是分析上的),而是以一种将观念建构视为事实判断的方式构成了一种世界观的基础,它成为主导现代思维方式的最为基本的预设,在各种不同的领域和议题中产生出大量的变样。以至于脱离了此种主客体二元论的预设,我们就很难理解现代西方的文化乃至文明,它的作用和意义遍及现代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式(1)为最小化t∈T阶段船舶贝内横倾力矩的目标函数,是t阶段船舶贝左侧集装箱和右侧集装箱所产生的横倾力矩之差,其中:k(t)∈N(t)为在t阶段待装箱编号;p=(i,j)∈P为船舶贝第i列第j层的箱位,i∈I,j∈J;wk(t)为集装箱k(t)的重量; xk(t)p为集装箱k(t)是否装到船舶贝的p∈P箱位,为0~1决策变量;d为集装箱宽度;Δ为相邻集装箱间隙;g为重力加速度。
虽然主客体二元论作为一种现代西方思维方式首先是由笛卡尔在哲学上加以揭示的,因此在前现代西方社会中并没有此种意义上的主客体二元论。(3)正如埃利亚斯所指出的,在古代社会中“自然”和“人”、“客体”和“主体”尚没有显示为两个在存在上彼此分裂的宇宙领域(N. Elias, Time:AnEssay, E. Jephcott(trans.), Oxfor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2,p.105)。但是它的形成线索却可以推演至西方文化的开端。正如钱穆在言及中西方文化之差异时所指出的,西方文化源自游牧和商业文化,内在的匮乏促成了向外寻求的精神,于是难免形成一种强烈的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弁言第2页。。尽管这样的对立在前现代社会尚不能够导致我们所谈论的主客体二元论的思维方式,但是它强调二元对立的方式却已经为后世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我们看到,在古希腊的思想中就已经广泛存在着对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的二元划分,例如在获取真理的问题上柏拉图把灵魂和肉体完全对立起来,设想灵魂和身体是可以彼此分离和独立的,而理性和理智则是灵魂的先天禀赋。(5)[古希腊]柏拉图:《斐多篇》,载《柏拉图全集》第1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2-64、65页;《费德罗篇》,载《柏拉图全集》第2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65页;《国家篇》,载《柏拉图全集》第2卷,第531页;《蒂迈欧篇》,载《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87页。他甚至谈论灵魂如何先于物体并统治物体。(6)[古希腊]柏拉图:《法篇》,载《柏拉图全集》第3卷,王晓朝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60页。而亚里士多德也同样热衷于灵魂和身体的划分,并将灵魂对身体的统治视为是合乎自然的有益状态,反之则意味着人的自然本性的丧失,因此常常是有害的。(7)[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4、14-15页。然而古希腊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精神(8)个人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最早形态恐怕要等到基督教的兴起,不过这依然不是现代人所熟悉的那种个人主义(参见[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谷方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这使得无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谈论的灵魂都丝毫不意味着现代西方语境中的个人主体性,例如对柏拉图而言,灵魂完全是一个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第一位的、不可见的被造物,它是永恒和不朽的。(9)[古希腊]柏拉图:《国家篇》,载《柏拉图全集》第2卷,第635页;《蒂迈欧篇》,载《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287页;《法篇》,载《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653、660-62页。而当亚里士多德把人描绘为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的时候(10)[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7、130页。,不过是在以人的合群性或者说共同体的生活(在此就是城邦)来界定人的本质。对于他而言城邦在本性上先于个人和家庭,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个体具有独立存在的可能性。(11)[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8、9页。这种主张个体从属于城邦的思想也同样适用于柏拉图。(12)[古希腊]柏拉图:《国家篇》,第326页。事实上这一切恰恰体现了城邦共同体在古希腊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支配性角色。(13)不过只需与大致同一时代的中国思想稍加比较就不难看出,古希腊的灵魂观是如何可能滋养着后世的主客体二元论的变革的。《左转》中记载了郑国子产对人之魂魄的看法,当被问及人死后是否可能变成鬼魂的时候,“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于神明。’”(《左转·昭公七年》)在钱穆看来这表明中国人思想中的灵魂与肉体是合一的,灵魂是肉体所焕发出的机能,它是不能像西方人想象的那样可与肉体分离自在的(钱穆:《中国思想史六讲》,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8、9页)。这就完全杜绝了所谓的二元论的可能性。然而伴随着古希腊城邦的衰落和希腊化时代的到来,弃世精神在哲学上的兴起似乎为出世的个人主义提供了一个契机,这恐怕是基督教得以在当时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14)[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第24页。那么具有出世个人主义精神的基督教思想又是否能够在中世纪的漫长统治中孕育出主客体二元论的精神呢?尽管作为宗教神学家的奥古斯丁把时间的存在归咎于心灵中的度量(15)[古罗马]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54-256页。,他甚至还是笛卡尔“我思”观念的先驱(16)[英]罗素:《西方哲学史:及其与从古代到现代的政治、社会情况的联系》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436页。,但这丝毫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基督教思想依然是从属于上帝的一元论统治之下的,在此种精神的语境中,人的意志不可能摆脱上帝的统治而获得一种近代意义上的独立性。尽管迪蒙指出基督教会在漫长的中世纪中出于自身的生存和统治世界的欲望而推动了出世个体向入世个体的转变(17)[法]路易·迪蒙:《论个体主义:对现代意识形态的人类学观点》,第47-48页。,这表明世俗化的个体主义的出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然而这一事实并不能否定近代西方世界的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其标志性的思想事件就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毕竟,无论是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奴隶制还是中世纪的封建制,都由于其刚性的人身依附关系而不利于世俗个人主义的产生。
虽然有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社会动荡,有工业革命所激起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等等影响广泛的事件,但是19世纪对于西方世界内部而言却是一个相对和平的繁荣世纪,这使得启蒙运动的精神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种乐观主义的情绪弥漫在19世纪欧洲的空气中。社会学这门学科正是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这也就难怪它会沾染上这个时代的主流气息,秉持着启蒙时代的理智主义,传统的实证主义和实在论成为之后很长时间中主导西方社会研究的重要力量,这一力量在西方社会学的重心于20世纪中期转向美国之后达到了其影响力的顶点。尽管存在着各种变样和分歧,但是从韦伯意义上的理念类型(ideal type)的角度来说,这种主流社会学相信社会世界是拥有其自身本质规律性的客观给定的事实,而采用实证科学方法的社会学研究者则完全能够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去把握社会世界的普遍规律,即便是历史的变革也不能外在于普遍的历史规律的支配。这一思想的背后则是启蒙时代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发挥作用,它相信人类已经掌握了打开世界的理性奥秘的钥匙,而法国大革命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则昭示了人类已经走向了进步的必由之路。(36)进化论在19世纪的西方世界兴起并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主流社会学在20世纪上半叶蓬勃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则已经在酝酿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不过历史的变革并非一种简单的因果决定,而是在不同层次的多因果作用下所促成的一种或然性的关系事件。对于我们所研究的西方社会理论思想史而言,我们首先要区分思想史内部和外部两个层次的因果机制,事实上这一划分层次的方式适用于广泛的社会历史因果解释,它也可以理解为有关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的划分。在不同的层次中我们又可以区分一般性因果关系和专门性因果关系,它意在指出特定原因对相关事件的影响所具有的针对性程度。当然这里的两分方式不过是一种理论上的类型化,它不应当被理解为是有关事实的一种绝对判断(内部和外部、一般和专门只是相对而言的),它并不排除在面对实际问题时可以分解为更为细致的类型化(如划分直接的外部因素和间接的外部因素等等),同时也不意味着在不同的类型之间不可能存在重要的因果联系。事实上,外部原因往往是内部原因被激发的直接机制,一般性因果关系和专门性因果关系也可能存在复杂的因果关联。而所谓的专门性原因也只是就相关事件而言更具针对性罢了,并不排除它在其他事件的因果解释中可能扮演一般性的角色(这种角色的变换也同样适用于所谓的一般性原因)。
企业先行的网络机制依然处于初始建设阶段,和海外发达国家大型企业的建设发展相比,我国企业不管是在内部体系的构建或者是科技化条件水平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就容易使企业在开展数据收集时容易受到阻碍,其收集到的资源、信息、数据等并不完整,只能对一些信息进行加工处理。在大部门时候,企业财务内控系统在向管理层、领导层反馈信息时,只会反映出财务工作者获得到的数据情况,但是这些片面的数据无法精准地反映出企业在生产经营中的实际情况,从而使财务信息开始出现一致性、真实性的问题,企业的财务信息化发展也难以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
必须指出的是,就如同在笛卡尔之后的西方哲学中出现了所谓的唯心论和唯物论的二元论争论一样,在西方社会学领域中也出现了类似的二元论争论,只不过争论的主角变成了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这种还原论的倾向表面看似解决了二元论的对立,但其实质不过是用两个对立的思想阵营取代了同一思想内部的二元平行关系。毕竟,如果说二元论的对立双方不过是一种人为划分和抽象的产物(包括笛卡尔本人在内的哲学家们早已困扰于身心二元论与经验事实的不符,这正是两种哲学阵营产生的理论动因所在),那么以其中的任何一方来解释或还原另一方的做法本身就只能是一种抽象,一元论的表象所掩盖的不过是对二元论的更加隐蔽的认同。
二、推动视角转向的历史机制
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世俗化的个人主义发展主要受到政治情况的影响(18)[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何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5页。,雇佣兵队长和大小暴君的统治更感兴趣的无疑是能为他们带来实际好处的个人才能而非花哨的出身,雇佣兵队长们在政治上的篡夺也极大地削弱了家庭出身与合法继承权的意义,这一切对于封建制度和贵族阶级而言无疑都是糟糕的信息。可想而知,此时的意大利“没有仿照北方形式的具有人为的各种权利的封建制度;有的只是每一个人在实际上和理论上保持了他所有的权力”(19)[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93页。。而这一切的背后则是市民阶层的兴起和贵族阶级的衰落,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宗教和教会地位的衰落。中世纪以出身为依据的社会等级观念开始被一种基于文化和财产的现代尊荣观念所取代,这暗示了一种有利于市民阶层的更加平等化的趋势。(20)[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353-354、357、361-362页。与之相伴随的就是不信教的风气开始流行(21)[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446、454、482页。,个体人格的发展使得人们不再像中世纪时那样依附于宗教的权威,而市民阶层对现世成就的兴趣则极大地削弱了彼岸世界的吸引力,世俗化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宗教与教会也只能通过宗教改革运动苟延残喘,这一改革最终也只是进一步推动了宗教的世俗化(例如加尔文派的改革)。总之,伴随着市民阶层或资产阶级的兴起,原本相互联系的贵族制度和教会统治不得不在世俗化的浪潮中日益衰落,这也正是宗教个人主义向世俗个人主义转变的主导机制所在。与此同时,宗教统治的衰落、对古代研究兴趣的崛起和世俗个人主义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世俗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上对宗教的极端违反往往被暴君和自由城邦置之不问(22)[瑞士]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86页。,对自然的态度无须再受到神学和教会的束缚。而这一切最终在启蒙时代的精神生产中激发出了丰富的思想成果,这一成果的核心价值就是主客体二元论。
社会理论内部的批判工作无疑是最为直接的内部颠覆力量(47)我们同样可以区分出一般性的原因和专门性的原因,前者是将传统主流社会学的立场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批判,它主要体现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样的基础层次上的批判;后者则体现为就某些具体的社会研究而展开的批判,它揭示了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社会学在具体问题上的局限和错误,它需要一般性原因所提供的方法论视角,同时又从具体研究的角度为全面的批判提供案例。出于篇幅上的考虑,我们以下的研究将主要针对一般性批判展开讨论,只不过我们不应当忘记这些一般性的批判总是需要各种具体研究的支撑。,它从属于学术领域内部所固有的游戏规则——对象化与怀疑是知识生产所依赖的基本预设(当一种知识放弃了对它自身的对象化和怀疑的精神的时候,它就沦为了固步自封的教条,也就是说它丧失了自我批判和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它只能等待它的他者来揭示它的问题,这个他者就是学术领域内部的反对力量)。对权力的争夺并不只是一个学术领域的外部事实,它同时也是以追求真理作为自身目标的学术领域的内在构成(48)福柯在尼采的启发下系统论述了权力和知识的内在联系。参见M. Foucault, DisciplineandPublish:TheBirthofthePrison, A. Sheridan(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TheHistoryofSexuality,Vol.1:AnIntroduction, R. Hurley(tran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这一构成同时也是整个社会领域中的权力游戏的组成部分。(49)布迪厄有关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群体的研究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P. Bourdieu, Distinction:ASocialCritiqueoftheJudgmentofTaste, R. Nice(tra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317。那些新兴的社会理论家们在科学革命和社会变革的双重启发下,把与笛卡尔的绝对主义精神截然对立的相对主义气质引入了社会理论的核心,他们在早已酝酿良久的哲学相对主义传统中寻找启发的源泉,这也就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像尼采、马克思、海德格尔之类的哲学家往往成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们所青睐的对象。(50)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在此是在一种较为宽泛的意义上谈论相对主义,它当然不能仅仅局限于诸如不可知论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与此同时,我们所例举的这些哲学家的思想也同样可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某种绝对主义的倾向(这体现了他们的思想的复杂性),我们在此仅仅是强调人们对其相对主义面向的汲取。事实上,相对主义精神并不是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它甚至在启蒙的思想中就已经占据位置,只不过它在相当长的时段中仅仅处于边缘的地位,甚至存在于那些在某种程度上认同主流现代性精神的作者身上,这体现了问题的复杂性。于是我们看到,在启蒙时代深受笛卡尔影响的斯宾诺莎和帕斯卡尔依然怀有相对主义的气质(51)参见[荷]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1、42、169页;有关帕斯卡尔的讨论可参见郑震《论帕斯卡尔的实践哲学》,载《社会理论论丛》第4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而经验主义的怀疑论、康德的物自体学说以及黑格尔将时间引入对存在的解释也都是有意或无意地为相对主义的视角增添砝码,至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尼采的透视主义以及海德格尔有关此在存在的意义是时间性的论断就更是直接地启发着当代社会理论家的相对性思维。与此种相对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的还有对二元论本身的反思和批判,毕竟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根基是绝对主义化的主客体二元论,二元论的抽象视角对于西方主流社会学的失败难辞其咎,而相对性的凸显似乎也在瓦解着主体和客体的截然对立,一种相对主义的精神似乎应当与绝对对立的思维格格不入,然而我们将看到实际的状况却远为复杂和曲折。
伴随着个人从宗教的权威和世俗出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23)如果我们不是局限于某个时点(如1789年),而是将法国大革命视为是一个时代的象征,那么它的确如同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彻底摧毁了贵族制和封建制([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60、61页),从而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21页)。这种形式上的平等打破了贵族制度下的人身依附及其相伴随的差别意识,鼓励个体的人格觉醒和自信心(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依附于权威,这可以部分地解释近代以来基督教在西方的衰落),从而成为推动世俗个人主义发展的温床。因此托克维尔写道:“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并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发展”([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第626页)。我们的研究已经表明,民主主义并没有创造个人主义,但它的确是推动个人主义精神的一股强大力量。,具有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的理性主体似乎成为可以想象的了,与这一主体相对立的客观的物质世界也摆脱了宗教所赋予的神秘气息,尽管它在近代所获得的那种普遍规律性的特征也还是包含着基督教的影响。(24)正如米德所指出的,全知全能的上帝不可能创造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理性世界的观念并非来自于古希腊,而是来自于基督教([美]米德:《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陈虎平、刘芳念译,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328页)。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笛卡尔宣称:“尽管神的意志比我的意志要远为强大,这既是因为与之相伴随的知识和力量使它更加得稳固和有效,而且也是因为它的对象,在那里它涉及了更多的方面,然而,当在本质和严格的意义上来考虑意志的时候,神的意志看起来似乎并不比我的意志更强大。这是因为意志仅仅表现为我们做或不做某事的能力(也就是肯定或否定,追求或避免);或者毋宁说它仅仅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即当理智提出某种东西来加以肯定或否定或加以追求或避免的时候,我们的意向是如此,以至于我们并没有感到我们是由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决定的。”(25)R. Descartes, MeditationsonFirstPhilosophy, J. Cottingham(tra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40.这一论断的近代色彩是显而易见的,尽管笛卡尔并没有完全否定神的存在,但人在理智上已经不再是屈居于神的权威之下的从属者了。这种对神的三心二意和不虔诚的心态引来了皈依宗教的帕斯卡尔的批评:“我不能原谅笛卡尔。他在其整个哲学中都十分希望能够摆脱上帝。但是他又不得不要上帝来轻轻地弹一下,以便让世界运动起来;除此之外,他就再也不需要上帝了。”(26)B. Pascal, Pascal’sPensées, W. F. Trotter(trans.),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and E. P. Dutton & Co. Inc. 1931, p.23.然而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证实了笛卡尔的近代性,他对人的理解可以真正使用人本主义一词来形容,甚至这个人的理智还具有客观反映物质世界的真理性力量:“‘理智中的客观存在’在此并不意味着‘由一个客体来决定理智的一个行动’,而是意指客体以如下的方式在理智中的存在,在这种方式中理智的对象是正常地存在在那里的。我的意思是太阳的观念就是太阳自身存在于理智中——当然不是形式上存在着,就像它在天上那样,而是客观地存在着,也就是说,以这样一种方式,在其中客体正常地处于理智中。现在这种存在的模式当然没有外在于理智的事物所拥有的那种存在模式完美;但正如我所说明的,它并不因此而只是虚无。”(27)R. Descartes, MeditationsonFirstPhilosophy, pp.85-86.我们可以将这种思想称为是笛卡尔的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这就是为什么实证主义者会理所当然地相信人的理智能够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而此种规律性也同样源自笛卡尔对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物质世界的理智主义的绝对判断。(28)笛卡尔的二元论的理智主义精神是和绝对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标志主流现代性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绝对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观念,我们不难在柏拉图对“型(form)”的讨论中看到这种绝对主义精神,不难在基督教神学对上帝的描绘中看到它,如此等等。事实上,对绝对性的追求不过是人类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的一种原初动力,这就是在千变万化的世界中为自身的存在寻求确定性。这种寻求确定性的倾向在东西方文明中都具有主导的色彩,尽管它并不一定是绝对主义的(即便我们在后文将指出相对主义的兴起是当代社会理论转向的核心精神,这也不意味着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投降,只不过人们不再盲目地信仰所谓的绝对主义)。在笛卡尔看来物体和心灵的本质不仅仅是不一样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29)R. Descartes, MeditationsonFirstPhilosophy, pp.9-10.这两个实在遵循本质上截然对立的逻辑,因此它们谁也不能决定谁,当然这并不是说心灵和身体(身体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对于人具有切身的意义,心身二元论也就是心物二元论)不会有所关联(30)R. Descartes, MeditationsonFirstPhilosophy, p.56.,但这种关联在本质上并不能够改变它们之间的本体论关系,这便是主客体二元论最初的表现形式。这种心物二元论对于社会学的兴趣而言显然有些过于遥远,毕竟社会学家的理论兴趣并不在于认识物质世界。不过这种原本似乎仅仅局限于对自然科学产生影响的论调(在理智的心灵和机械的物质世界之间的认识关系问题),在较晚的19世纪被法国的实证主义者以一种自然主义的态度带入了对社会现象的研究。(31)[英]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这意味着原本在心灵和物体之间的二元论在社会学领域中变样为个体和社会的二元论,社会占据了原本由物体所占据的位置,这一转变被迪尔凯姆那种将社会事实作为并非物质之物的论断完美地诠释了出来。(32)[法]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5页。不过这一转变并非偶然,它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大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动荡和社会问题所激发起来的,社会似乎成为一个难以驾驭的实在横亘在人们的面前,它和个人主体之间的“对立”似乎丝毫也不亚于那个自然的物质世界与主体之间的“对立”。(33) 与此同时,随着现代自然科学在19世纪的发展,认识自然的问题似乎没有过去那么紧迫了,主体和自然客体之间的对立变得不再重要了(N. Elias, TheSocietyofIndividuals, E. Jephcott(trans.), New York, London: Basil Blackwell,1991, p.125)。这无疑为人们将注意力转向社会生活提供了契机。于是实证主义者宣称,社会是一个拥有维持秩序的自主力量的独立自主的实体(34)叶启政:《进出“结构—行动”的困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论述对话》,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93页。,它具有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规律性。在实在论者的眼中,这意味着社会是一个客观给定的实体,它是“独立于我们有关它的表象而存在的外部世界”(35)V. Burr, SocialConstructionism,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22-23.,它的必然的规律性就是它所固有的本质特征的体现,这一本质特征维系了其作为一个实体的持存性和不可分性。
在主体问题上,对主流现代性的批判表现为对有意识的理性主体的颠覆性重建,它试图指出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观念仅仅是一个社会历史性的话语建构,它并不具有任何实体的自明性。对此,尼采这位19世纪的哲学另类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点,福柯写道:“在尼采那里有着对观念深度,意识深度的批判,他将它们指责为是哲学家的发明;……”(52)M. Foucault, “Nietzsch, Freud, Max”, in Faubion, D. James( ed.), MichelFoucault(Vol.2):Aesthetics,Method,andEpistemology, New York: New Press, 1997, p.273.这一论断无疑指向了笛卡尔的意识哲学,后者对意识主体的信心也许只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一个在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中的错觉。尼采有关身体之无意识记忆的论断极大地鼓舞了像福柯之类的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们(53)参见[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谢地坤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版,第37-38页。,对尼采而言,这种无意识的记忆是身体的记忆(54)[德]尼采:《论道德的谱系》,第39页。,“你说‘我(ego)’,于‘我’之一字颇自负。但更重大者——虽则你不肯信——是你的身体(body)及其大智慧,它不说‘我’,却如我一般行动”(55)[德]尼采:《苏鲁支语录》,徐梵澄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8页;N. Friedrich, ThusSpakeZarathustra, T. Common(trans.), Boni and Liveright, Inc., 1917, p.51.。这正是福柯身体概念的直接来源。无意识意味着对社会历史建构的遗忘,正是这一遗忘才使得对意识的错觉得以占据主体的心灵,然而也正因为这一遗忘才表明那个有意识的自由心灵或自我不过是一个话语的表层,人与其说是作为理性的自由心灵而存在,还不如说是作为前理性的或(在身体不采取对象化的理性态度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非理性的身体而存在,这个身体并非只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物体,而是代表了一种被强加的无意识的状态(社会历史性的强加的建构——尽管个体往往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像人的肉体感官对世界的感觉,高度反思性的理性的运转在此还尚未开始。这也就是为什么福柯要谈论人文科学的话语(或者说西方的文化)对身体的无意识建构,这一非反思的建构促使个体以某种他实际无法真正理解的方式行动,他只是错误地生活在这一建构为了掩盖其强制的真相而营造的幻觉中。而身体究其实质而言不过是一个权力—知识结构的消极的对象或效果(56)M. Foucault, DisciplineandPublish:TheBirthofthePrison, pp.29-30, p.305.,尽管福柯强调他笔下的现代纪律权力并不是一种单纯压制的力量,而是具有生产性的特征(57)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0, p.119.,然而这一切并不能够否认在纪律权力的运作中依然存在着压抑而不是自由(58)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p.108.,这正是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压迫性的指涉,在这个社会中所生存的人并不是他们所自以为的那个自由的主体。
金华寺汤溪镇寺平古村主要的保护模式为划归为文物,售票观览。单一的盈利方式导致未来面临的困境是可以预见的,如何打开瓶颈投入活化更新项目,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还要防止进入另外一个误区,即在中国的许多传统村落,由沿街商铺的商户构成的多以游客市场筛过“经得起市场检验”的特色小食、区域特产、文艺小铺以及饰品首饰为主流的产业[1]。这些所谓的“主流”没有地域特色,很难成长为支撑传统村落持续发展的产业。
Step 4 Figure the color graph forto show the established DWWIKP intuitively.
与消费文化和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带来的相对主义冲击几乎同时的另一个同样直接和针对性的事件就是60年代席卷西方世界的以学生运动为其代表的社会冲突,这场运动以1968年“五月风暴”作为其标志性的象征。面对这样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原本被寄予厚望的主流社会学却显得捉襟见肘,无论是帕森斯式的宏大的普遍模型,还是各种打着实证科学旗号的所谓经验研究都束手无策。正如米尔斯所言:“就实践而言,由于宏大理论表现出的形式的、含糊的蒙昧主义,以及抽象经验主义所表现的形式的、空洞的精巧,使得人们确信,对于人类和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46)参见[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章和第3章。这种尖锐的批判和嘲讽恰恰揭示了传统主流社会学在笛卡尔理智主义精神的影响下醉心于对所谓客观世界的普遍法则的追寻,但却遗忘了自身视角的社会历史局限性,在一种盲目的自然主义和科学主义自信中把一套抽象的意志强加于现实,从而无视社会现实本身的复杂性和具体性。正是主流社会学在与现实的直接碰撞中陷入困境才使得以往所积累的各种怀疑终究凝聚成一股强大的颠覆力量,这股力量通过社会理论领域的内部批判这一重要中介迫使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主流社会学退出了思想舞台的中心。
同理,完全加权负项集NI(Negative Itemset)关联度(all-weighted Negative Itemset Relevancy,awNIR)的计算如式(9)所示:
然而西方社会学尚没有及时地形成一种强大的反思力量来取代蜷缩于象牙塔之中的主流社会学的地位,尽管不同的声音几乎从社会学的开端就已经存在,但是其弱小的力量尚不足以促动占据统治地位的话语秩序——20世纪50年代无疑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研究如日中天的时候。两次世界大战的冲击无疑是一种外部的一般性因素,它的影响过于宏大而缺乏具体的针对性,而科学的革命虽然是一种专门性因素,但是它的具体性主要体现在对自然世界的认知方面,对于社会理论的方法论依然缺乏针对性(这种针对性尚需科学哲学的阐释和转化(42) 在这方面法国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和乔治·康奎荷姆的研究对于福柯的影响([美]古廷:《20世纪法国哲学》,辛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1页),以及巴什拉和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研究对布迪厄的影响([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7页;P. Bourdieu, PracticalReason:OntheTheoryofAction, G. Sapiro(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8, p.3),都不失为很好的例证。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当代理论家对于科学哲学的发现都会欣然接受,例如埃利亚斯对于巴什拉所倡导的认识论断裂的思想就不以为然([英]史密斯:《埃利亚斯与现代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13页),不过他在其他方面与科学哲学依然存在着重要的共识。)。因此历史的变革还需要更加直接和针对性的事件来改变社会学家自身的处境(43)当然我们所谓的直接性和针对性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它丝毫也不意味着那种排他性意义上的针对性,更不可能预设什么历史的目的论。,它既是一种外部因素,同时又是在层级上更加直接的外部因素,而这样的事情也很快就到来了。经过战后的恢复和改良,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似乎又获得了新的活力,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高速增长和福利国家政策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广泛推行,无产阶级的处境获得了显著的改善,中产阶级队伍也日益壮大。随之而来的就是消费文化和消费社会现象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开始蔓延开来。商品的极大丰富和具有强大消费能力的大众之间碰撞出空前强大的消费火花,而强大的生产能力一改短缺经济时代的供求关系,使得生产者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而消费者对商品的文化偏好则成为同类商品生死存亡的关键因素。这不仅极大地提升了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同时也使得来自消费者群体的多样化的文化偏好成为支配市场运转的重要力量,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诸如列斐伏尔和布希亚这样的作者才先后提出了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转向(不是消费者成为了统治者,而是消费文化取代生产成为支配资本主义社会的主导力量)。(44)H. Lefebvre, EverydayLifeintheModernWorld, Sacha Rabinovitch(trans.),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1984,p.60; J. Baudrillard, SymbolicExchangeAndDeath, L. Hamilton Grant(tran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且不论消费转向的判断是否恰当,它至少向我们表明消费文化及其多样性已经成为摆在西方社会理论家面前的无法回避的重要现实,文化的相对性显然不再是仅仅用表象或派生之类的词汇就能够敷衍过去的次要问题,这对于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无疑构成了直接的冲击。与消费文化在揭示社会历史相对性方面具有同样冲击力的事件当属进一步加速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张所带来的文化乃至文明的碰撞与冲突。这一事件同样迫使西方社会学家们无法回避社会历史的相对性问题,它同时还引发了对时空相对性的深入思考,这对于那种将人类历史视为是一个单线进化过程的19世纪的历史主义无疑是致命的一击。(45)我们在此所谈论的历史主义并不是主张历史相对性的历史主义,后者对于我们在此所谈论的历史主义也同样是一种挑战(只不过这一挑战仅仅局限于时间这一抽象的维度),事实上这种主张历史相对性的历史主义和主张空间相对性的思想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时空视角(时空的相对性成为理论的核心价值)。我们此处所谈论的历史主义仅指那种试图以单一的历史进程来消解发生在不同时空中的多样化进程的抽象的历史观,也许称之为历史绝对主义更为贴切,它设想人类历史仅仅具有一个统一的历史规律性,这显然是笛卡尔的理智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体现,黑格尔的历史观可以视为是这一思路的典范(尽管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有关意识形态和异化的观点极大地启发了相对主义的思想,但是这一切又都被他统一在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圆圈之中)。
三、西方社会理论的新视角
既然传统的主流社会学是以绝对主义的主客体二元论作为其核心价值取向,那么新社会理论在批判实证主义和实在论的过程中势必针对这一核心价值取向来组建自身的替代性方案。我们将看到,新社会理论家们以一种相对主义的主导取向重新诠释了主体和客体的各自属性,一些作者进而针对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问题给出了替代性的方案,从而试图在根本上瓦解主流社会学的统治。
基于以上的思路,我们发现在20世纪之初,当实证主义者们还在将以牛顿物理学为典范的自然科学作为社会学研究的科学榜样的时候,物理学领域中的革命却已经正在改变着牛顿—笛卡尔的绝对主义认识论模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理学主张重新思考物理时空的性质,把相对性的视角引入了对自然物理现象的解释之中,这意味着“时间与空间不是绝对的,而只是与观察者相对的”(37)[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26页。,绝对的时间和绝对的空间仅仅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虚构。与此同时,量子物理学的研究表明,在测量像电子这样的质点的位置和速度时,“要同时确定两者的想法,似乎在自然界中找不到对应的东西”(38)[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第519页。。爱丁顿将这一结果叫做测不准原理。(39)[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第519页。如果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告诉人们世界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对于长度、质量和时间的测量完全取决于观测者所处的位置,而不存在什么绝对的量;那么量子力学则从另一个角度揭示了这个充满相对性的世界就其根本而言并不遵循所谓的机械法则,正如巴什拉所言:“自然的真正秩序是我们凭借由我们自行支配的技术手段而放入自然之中的。”(40)G. Bachelard, TheNewScientificSpirit, A. Goldhammer(tran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108.这也就难怪丹皮尔会断言:“在量子论与相对论两个方向上,现代物理学似乎正在摆脱伽利略时代以来一向指导物理学而卓有成就的基本概念。”(41)[英]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宗教和哲学的关系》,第533页。这场自然科学的革命本来似乎应当给予那些笛卡尔的信徒们当头棒喝,然而对于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它最初的影响却主要局限于少数的哲学家,尤其是科学哲学家。要想促动主流社会学的视角,似乎还需要一个思想传递和消化吸收的过程,也许更重要的是需要社会现实发生某些足以引起人们反思其固有偏见的变革,毕竟自然科学的研究所直接指向的还只是那个在社会学家工作领域之外的自然物理世界,对于社会理论而言它充其量只能充当一个外部的专门性的影响因素。然而这样的变革很快就到来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和野蛮,它们几乎成为了现代世界的转折点。西方世界很难在经历了如此的相互摧毁和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之后,再延续19世纪的乐观主义情绪,那个由法国大革命所开启的人类命运的进步之途似乎并没有它最初的构想者们所想象的那样一帆风顺和理所当然,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似乎也并非只是一种单纯的进步力量,韦伯笔下的工具理性化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似乎也并没有那么理性。启蒙的理想受到了广泛的反思和质疑,它的理智主义精神不再像过去那样显得理所当然,它对于主体和客体的描绘也被蒙上了一层阴影,至少理性主体的概念显得既可疑又单薄,它显然无法在现代人的所作所为中获得充分的印证,而那个遵循永恒法则的社会客体的观念更是在世界的混乱中显得格格不入。
福柯在尼采的启发下为我们描绘那个被启蒙的理智主义者所宣称的主体在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消极和被动的无意识身体。然而这只是当代西方社会理论谈论无意识身体的一条路径,像布迪厄这样的作者则从不同的来源汲取启发,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无意识身体的视角。主要受到现象学的生活世界理论、后期维特根斯坦的实践哲学以及埃利亚斯的历史社会学的启发,布迪厄首先将社会行动者理解为以不言而喻的信念方式进行实践的身体,他赖以展开其身体思想的主要概念就是从埃利亚斯那里借用来的习性(habitus)概念,他将之视为是其行动哲学的基础概念之一。(59)P. Bourdieu, PracticalReason:OntheTheoryofAction, p.vii.布迪厄主张,行动者的习性所包含的“认知结构不是意识的形式,而是身体的倾向性”(60)P. Bourdieu, PascalianMeditations, R. Nice(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p.176.。这一论断与福柯一样将笛卡尔的意识哲学置于次要和派生的地位,对布迪厄而言更重要的是基础性的无意识身体,它具有现象学生活世界理论所描述的那种前反思和前对象的自然态度特征,尽管布迪厄认为这种自然性仅仅是一个错觉,是现象学保守主义的错误判断,但它确实表明那种将个体设想成高度理性的意识主体的思路是对社会行动者的一种误解。对布迪厄来说,身体的实践依然还是一种遗忘,只不过布迪厄采用了涂尔干对集体无意识的理解(61)[法]涂尔干:《教育思想的演进》,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主张“无意识是历史——是生产了我们的思想范畴的集体的历史,和通过它这些思想的范畴被灌输给我们的个人的历史”(62)P. Bourdieu, PascalianMeditations, p.9.。作为一种社会历史性的集体建构,它完全可能被一种社会暴力所左右,但个体不仅常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63)P. Bourdieu, PascalianMeditations, p.135, p.141.,甚至还将其视为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所谓的符号暴力。(64)[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221页。就此而言,布迪厄笔下的无意识身体与笛卡尔所主张的理性的自由的意识主体显然大相径庭。而布迪厄用倾向性来描绘身体的状态也正是为了表明,身体的实践并不具有理性意识所宣称的那种清晰的逻辑特征。(65)参见P. Bourdieu, InOtherWords:EssaysTowardsaReflexiveSociology, M. Adamson(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77.换句话说,身体的实践并不具有可以明确预知的工具理性特征,这不仅意味着行动者不是一个理智的意识主体,同时它还向我们揭示了由这样的行动者的行动所共同组建的社会世界也并非实证主义者所设想的那个机械的客观世界。尽管倾向性的判断表明依然存在着某种实践的规则,但这显然不是绝对必然的客观规律,实践的模糊性表明了社会生活不是遵循机械法则的笛卡尔的世界。
尽管并非所有的当代理论家都热衷于探讨无意识的身体,而且他们有关无意识的理论也可能存在各种具体差异,但是他们以无意识概念来批判笛卡尔的意识主体的立场却是高度一致的,在这一点上福柯和布迪厄关于无意识的探究无疑具有某种代表性,这使得我们没有必要再进一步举例。与这一对启蒙主体性的批判密切相关的就是对社会世界的客观实在论的批判,我们在讨论无意识身体的时候已经触及了这一点。在社会客体问题上,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改革者们反对将社会世界视为是一个具有本质规律性的客观实在,他们所采取的概念武器就是文化和关系。由于受到尼采的影响,福柯倾向于从权力的角度设想社会世界的基础,他既认可了尼采有关“求真的意志乃是权力意志”的论断(66)[德]君特·沃尔法特编:《尼采遗稿选》,虞龙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同时又在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的相对主义精神指导下改造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结构思想,进而提出了他的后结构主义式的权力关系概念。这就将一种相对主义和关系主义引入了对社会历史的研究。福柯明确地指出,权力不是作为实体而存在的(67)M.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p.198.,因为权力是一种社会历史性的关系状态,权力的本体论地位并不排除其社会历史性,换句话说,权力不是客观给定的绝对事实,而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不断变革着的关系性力量(关系不是实体,我们不可能设想关系先于或外在于关系各方而客观实存着)。正是此种社会历史性的权力关系通过生产知识并与知识一同构成所谓的实践性的话语,从而在实践中将人类个体建构成无意识的身体。权力的社会历史性和关系性彻底颠覆了那种实体的持存性假设,而福柯着重探讨的权力和人文科学的关系,则意味着有关文化相对性的思考。福柯认为,人文科学所研究的不是人的本质,而是在时间中变化的人,人文科学的实存、存在方式、方法和概念都扎根于文化的事件。(68)M. Foucault, TheOrderofThings: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 pp.352-355, p.371.这实际也就意味着人文科学的知识话语也只不过就是现代西方世界的一种文化现象,那么由生命权力和人文科学知识所共同构成的现代西方话语也就只能在一种相对主义的精神中被理解,它们所构成的建构身体的社会关系结构并不是什么客观的实在,也不具有什么本质的规律性,而仅仅是一种时空性的社会历史现象而已。这种彻底解构现代主体性假设的后结构主义立场也同样体现在布希亚有关符号统治的研究之中,尽管布希亚反对福柯赋予权力的本体论地位,在布希亚看来最终支配性的是符号(或文化)而非权力(69)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在权力和文化之间的二元抉择恰恰暴露了一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方式,它们恰恰忽视了权力和文化也许从来就只是统一整体的抽象的两面,是人为的分析从现实中抽象出权力与文化的区别。,是符号的编码系统生产了权力,而不是相反。(70)J. Baudrillard, SymbolicExchangeAndDeath, L. Hamilton Grant(tran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3, p.30, 86, 90.但是布希亚同样认为社会世界那决定主体(更确切地说是无意识)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客观给定的现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西方消费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消费符号不过是现代模拟物(simulacra)发展到特定阶段的产物(71)J. Baudrillard, SymbolicExchangeAndDeath,p.2.,建构消费者的无意识的符号化的客体秩序并不具有超越时空的客观给定性。事实上,在把社会现实理解为一种文化现象方面,布希亚可谓是一位彻底的文化主义者(72)福柯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有所保留,他认为在人文科学之外,诸如语言学、经济学和生物学这样的学科是研究人的一般本质的经验科学,尽管它们也是权力关系的产物。在此我们看到了福柯对其时代的主流观点的妥协。,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完全是一个符号统治的社会(73)J. Baudrillard, TheConsumerSociety:MythsandStructures, C.T.( trans.),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8, pp.191-192.,针对这样一个社会,自然也不可能存在什么绝对主义的认识,因为认识也只能是一个符号的社会历史建构。“所有的当代理论都在漂浮,并且除了作为符号彼此服务之外没有别的意义。”(74)J. Baudrillard, SymbolicExchangeAndDeath, p.44.这恐怕就是当代社会理论中将相对主义推向极致的案例,它在以一种极端相对主义的方式瓦解笛卡尔的理智主义的同时,也陷入到一种怀疑论的虚无主义之中,从而陷入一种难以克服的自相矛盾。
不过像布希亚这样的极端相对主义者并非主流,不仅我们已经提及的福柯只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其所谓的人文科学,而且像埃利亚斯和布迪厄这样的作者在看待社会学这样的人文科学时显然比福柯要更加积极,他们主张以一种历史建构性的积极态度来审视社会理论的认识论价值,这意味着在怀疑和绝对之间寻找一种历史性的定位,从而体现了对启蒙理性的某种有限的信心(当然这是在把理性视为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75)P. Bourdieu, PascalianMeditations,p.70.,是在时空中变化和成长的事件的前提下的)。埃利亚斯认为一切认识活动都只能处于主观和客观这两个极端之间,区别仅仅是主观和客观之间的比重在历史的过程中发展变化。(76)N. Elias, TheSymbolTheory, R. Kilminster( ed.), London, Thousand Oaks,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1, p.75; “Involvement and Detachment”, in S. Mennell & J. Goudsblom(eds.), NorbertElias:OnCivilization,Power,andKonwledge:SelectedWritings,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p.217; “Sociology of Knowledge: New Perspectives”, in R. Kilminster & S. Mennell(eds.), N.Elias:EssayI:OntheSociologyofKnowledgeandtheSciences(TheCollectedWorksofNorbertElias,Volume 14),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9, p.36.受到埃利亚斯的影响,布迪厄主张一种社会的客观性(即客观化的社会历史性),也就是说科学的认识及其对象都是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的社会历史产物(77)P. Bourdieu, PascalianMeditations, p.120.,它们既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社会历史的相对性),也不可能是完全任意的(社会建构的客观性)。不过在埃利亚斯、布迪厄和布希亚等人之间的分歧不仅是认识论层面的,更是本体论层面的(78)虽然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分析所关注的问题不同,而且认识的产物也完全可能参与到对本体身份的社会历史建构中,但是由于本体论最终确定认识主体及其对象的性质,这也就在根本上为认识活动的性质奠定了基调。,像埃利亚斯和布迪厄这样的作者反对像福柯和布希亚那样以一种后结构主义的立场来理解社会世界的性质,但既便如此,他们以文化和关系的视角来描绘社会世界的存在方式这一点却是高度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对文化和关系的具体看法。为了避免结构和系统这样的概念被主流社会学所赋予的偏见,埃利亚斯提出了形态概念来替代结构,他意在表明社会形态不是静止和封闭的结构,而是一种过程性的关系事件。(79)N. Elias, TheCourtSociety, E. Jephcott(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3, p.141; N. Elias, and J. L. Scotson, TheEstablishedandtheOutsiders(TheCollectedWorksofNorbertElias,Volume 4), C. Wouters( ed.),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8, p.194.这就在实质上把社会结构从实在论的阴影中解救了出来,因为埃利亚斯笔下的社会结构仅仅是在社会历史时空中变化着的关系形态,而不是什么客观的实体。(80)N. Elias, TheSocietyofIndividuals, E. Jephcott(trans.), New York, London: Basil Blackwell, 1991, p.61.而此种社会的结构或规律性也并非什么永恒和普遍的规律性,因为那种像规律一样的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一种韦伯意义上的理念类型(81)N. Elias, “The Sciences: Towards a Theory”, in R. Kilminster & S. Mennell( eds.), N.Elias:EssayI:OntheSociologyofknowledgeandtheSciences(TheCollectedWorksofNorbertElias,Volume 14), Dublin: University College Dublin Press, 2009, pp.72-73.,它在现实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项。受到埃利亚斯影响的布迪厄也同样在一种关系主义的视角中理解社会结构,他将社会结构理解为是由个体和机构所占据的各种社会位置构成的独立于个人意识和个人意志的客观关系结构(这种“独立性”源自马克思的影响)。(82)[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3页;P. Bourdieu, PracticalReason:OntheTheoryofAction, p.15.他明确宣称自己采用了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实体的概念”和“功能的或关系的概念”之间所做出的区分(83)P. Bourdieu, PracticalReason:OntheTheoryofAction, p.3.,主张社会世界不是一个客观给定的实体,而是在时空中变化着的关系结构。
不过与对现代性主流思想中的绝对主义的主体概念和客体概念的分别批判乃至颠覆相比,对主客体二元论本身的直接颠覆也许在思想上具有更加根本的重要性,毕竟主客体二元论才是现代性最为独特的核心价值观。而这也正是诸如埃利亚斯和布迪厄这样的作者所试图实现的理想。相比之下福柯和布希亚这样的后结构主义者并没有摆脱结构主义的客体主义倾向,从而完全局限于客体主义的还原论之中。虽然他们对现代主体和客体假设的解构有助于对主客体二元论的批判,但是这一批判依然还是在一种还原论的意义上在更深的层面捍卫着主客体二元论的核心逻辑。后者正是埃利亚斯等人试图有意识地加以克服的。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埃利亚斯和布迪厄反复宣称其克服主客体二元论的愿望,明确拒绝所谓的主观与客观、内在与外在或方法论个体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的二元对立,然而他们却没有能够真正克服围绕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来展开思考的思维方式(不能抛弃“个体和社会何者优先?”这个老问题),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出发恰恰暴露了其反二元论的不彻底性,它潜在地将个体和社会设定为问题的出发点,而不是本身需要解决的问题。于是埃利亚斯最终还是回到了社会关系结构相对于个体具有一种逻辑优先性的论调,他提出了一种关系的决定论或还原论:“个体的行为是由过去或现在的与他人的关系所决定的。”(84)N. Elias, TheSocietyofIndividuals, p.19.与之相类似,布迪厄也没有能够最终摆脱一种客观结构的逻辑优先性的论调,正如他的合作者华康德所表明的:对布迪厄而言“客观主义的旁观在认识论上先于主观主义的理解”(85)[法]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1页。。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在批判主流现代性的绝对主义的主客体二元论的过程中,并没有能够实现对二元论逻辑本身的彻底超越,相反他们或者停留在此种逻辑上止步不前,或者在反对此种逻辑的同时又以更加隐蔽的方式陷入到此种逻辑之中。尽管由于篇幅的原因,我们不可能讨论所有的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家,但是我们所例举的这些代表性人物已经能够足以向我们揭示实际的主要状况。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的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转向实际是对西方主流现代性思想的一种反思和超越,然而它在拒绝绝对主义视野中的主客体二元论的同时,却又无法彻底清除主客体二元论的影响,从而以一种变样的方式继承了主流现代性的核心价值观——主客体二元论。事实上,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并非没有可能摆脱主客体二元论的束缚,其以关系主义的立场来颠覆实在论的企图本身就隐含着对二元论的超越之可能性,如果意识到主体和客体不过是从关系性的现实中抽象出来的分析性概念,并坚持一种以关系作为基础性社会历史现象的研究思路,主客体二元论也就无从立足了。然而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依然没有摆脱将关系结构化的陈旧思维,依然还在关系结构和个体之间进行还原论式的抉择,这全然没有看到关系主义思维所存在的潜能。对于深受西方社会学影响的中国社会学而言,如何面对这一现实对于中国社会理论的建设无疑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一方面是如同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一样走出实证主义和实在论所编织的抽象陷阱,不再沉迷于主观和客观、主体和客体的绝对想象,不再把抽象的观念视为是实在本身;另一方面则是避免像当代西方社会理论那样依然沉浸在主客体二元论的桎梏中而不自知,避免陷入到用二元论来反对二元论的自欺欺人之中。因此,反思和超越现代西方的主客体二元论依然是当代中国社会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之一。而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恰恰为社会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非二元论的关系主义思路,这种以天人合一的整体性关系作为基本视野的思路不啻为理解社会历史现实的更具切实性的视角。尽管它的理论意义无疑还需要大量创造性的理论重建工作来加以深入地挖掘,并以此来激活这一传统思维的现代活力。
具体分项目标为:在教学内容上,将计算思维的培养融入医学院校计算机课程改革,不仅为计算机基础教育提供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更高的目标,也为医学院校的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体系提供经验和参考。在教学手段上,开展慕课与翻转课堂混合教学的实践,充分地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深入学习知识,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开展形成性评价,更科学、客观地衡量学生学习的状态和进度,做好每一步骤的及时反馈,有利于学生牢固掌握知识和得到真实的评价,同时,也有利于对课程开设质量进行基于数据的准确分析和科学评价。
TheCritiqueandHeritageoftheModernity——The Turn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heories in the View of Social History
Zheng Zhen
Abstract: The absolutistic dualism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is the dominating idea of the Western modernity. It is the key standpoint of the positivism and realism that have dominated the Western sociology for a long time. The origin of the absolutistic dualism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Western thoughts. But it came into being only in the modern West.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social theorists were aroused by a series of events of 20th century to criticize and transcend the absolutistic dualism with the instruction of the relativism. But they didn’t overcome the dualism of the subject and the object completely.
Keywords: Modernity; Western Social Theory; Absolutism; Dualism; Relativism
收稿日期:2019-04-22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9)09-0061-13
作者简介:郑 震,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江苏 南京 210046)
(责任编辑:薛立勇)
标签:社会论文; 笛卡尔论文; 这一论文; 社会学论文; 理论论文; 《社会科学》2019年第9期论文;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