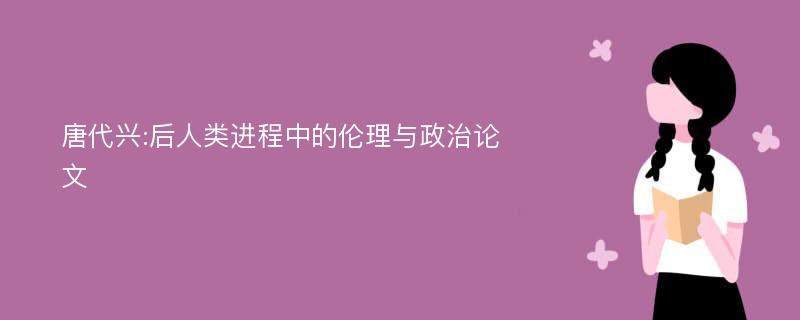
摘 要:高速发展的航天业、临床医学、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已从不同方面推动人类进入后人类进程,它以“会聚技术”方法建构起“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联系方式,形成以技术统治人为取向的后环境社会。在后人类进程中,后技术主义抛弃“以生物为基础”和“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系方式,通过技术改变人的依赖性对象及方式,使人不断丧失存在关联性,进而将人从个性引向任性,在任性中放弃责任,层累起根本的伦理困境和政治冲突:前者敞开技术准则与人性准则、自然律法的不可调和,后者突显技术权力与人性权利的根本对立。由此开启如何突破后技术主义重构后伦理纲领和后政治框架的可能性:仅前者论,就是确立伦理优先的律法体系,即自然律法引导人性,人性准则规范技术;就后者论,必须构筑人权优先的制度-法律体系,即人权规范引导技术、技术权力服从人权。
关键词:后人类进程;后技术主义;后技术时代;基因编辑;会聚技术;后环境社会;后伦理纲领;后政治框架
世界风险社会和全球生态危机,构成宏大当代语境。但相对人本身言,这些都属于“何以存在”的外部条件问题;真正的内在危机是人被悄然地改变,它突显人“以什么方式存在”这一内在规定面临消解的危机。人被悄然改变的这一进程,就是后人类进程,它正以自身方式改变着每个方面。
一、后人类进程:概念对实在的对应性指涉
本文提出“后人类进程”这一概念,是对后人类社会形成之旅的理性陈述,它揭示人类在追求文明的现代历程中如何被文明不动声色地异化塑造,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一不可逆过程通过“后人类”、“后人类主义”、“后人类语境”、“后人类社会”等概念表述它自身由隐而显的急速变迁。
这部分我们要从维氏这里讨论自我天才观与人的自我认识问题,即《战时笔记》作为哲学性的自我书写与自我书写的哲学性这一一体两面的特征。
“后人类”(Posthuman)一语,最早见于布拉瓦兹基(H.P.Blavatsky)的《秘密教义》(1888),它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而存在,应以史蒂夫·妮可思(Steve Michols)的《后人类宣言》(1988)为标志。
“后人类”话语一旦形成,必然承受时间发酵而引发系统性思考。第一个成果是佩普勒尔(Pobert Pepperell)的《后人类状况》(1995),该著明确定义“后人类”是人类“存在为延展的技术世界的一种形态”[1]。 其后,卡里·沃尔夫(Cary Wolf)在《什么是后人类主义?》(2010)中将“后人类”扩展为“后人类主义”,认为“人从来都不是‘自然的',至少从创造语言开始,我们就在凭借知识、物质和人类技术增强我们的能力。”[2]沃尔夫还认为,“后人类主义”的思想源头可溯及20世纪60年代,因为福柯的主要作品《疯癫与文明》(1961)、《临床医学的诞生》(1963)、《词与物》(1966)和《知识考古学》(1969)集中问世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词与物》,鲜明地表达了后人类主义思想:“人是近期的发明,并且正接近其终点……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3]后人类主义者将福柯等后结构论思想家纳入“后人类主义”谱系,使其获得认知的哲学基础和社会思想的滋养。
丹参川芎嗪联合替罗非班对急性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患者冠脉介入术后视黄醇结合蛋白4的影响 … …… 周琳 李嘉俊 任继刚 等(1)51
从“后人类”概念提出到“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主张,必然形成认知探讨的“后人类语境”(Posthuman context),它指后人类思考所生成的谱系化的话语情景或语义场态。只有进入这种话语情景和语义场态中,才可理解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凯瑟琳·海尔斯(N.Kaherine Hayles)研究的意义。唐娜·哈拉维于1985年发表《赛博格宣言:20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提出要通过不断开发的“新技术”重构一个“赛博格”身体,以推动“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变革。
赛博格(cyborg)概念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它由曼弗雷德·克林斯(Manfred Clynes)和内森·克兰(Nathan Kline)提出。这两位航空航天局科学家认为,可以通过药物和科学方法使人在严酷条件下生存。他们依据“cybernetic organism”而构造出cyborg,用来描述机器参与人体并形成超越生物限制的新身体。哈拉维在此意义上将cyborg定义为“一个控制有机体,一个机器与生物体的杂合体,一个社会现实的创造物,同时也是一个虚构的创造物。 ”[4](P14)并宣称“在20世纪晚期……我们都是赛博格。赛博格是我们的本体。”[4](P150)
继《赛博格宣言》之后,凯瑟琳·海尔斯发表了《我们怎样变成了后人类:赛博格、文学以及信息学中的视觉身体》(1999),在严肃区分 “后人类”(posthuman)和“反人类”(anti-human)基础上总结了后人类主义的四个特质:(1)信息构成生命的本质;(2)意识并不具有决定人类进化的功能;(3)身体并非自然物,乃后天形成;(4)人工智能机器、科技装置与生物有机体并无本质差异[5]。
其实,无论器官移植,还是安乐死或试管婴儿,都只是其浅表成就,真正深度的人体革命,却在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与创造领域。
先看器官移植。临床医学实现了从外部肢体移植到内脏移植,即或相当复杂的心脏移植也成熟为广泛运用的日常临床技术。今天,大脑移植才是器官移植的尖端技术,并将成为身体技术的最后完成式。2015年6月,意大利都灵高级神经调节组的塞尔焦·卡纳韦罗(Sergio Canavero)在美国神经和矫形外科医学学会(AANOS)年会上宣布实施一项换人头计划及时间表,其换头准备工作最早在2017年完成:2017年11月17日,调节组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与任晓平教授合作,成功地在一具遗体上完成世界首例人类换头手术,这标明人体器官移植进入了换头时代。
器官移植只局部改变人的身体及生命结构,试管婴儿和安乐死却改变了人的生死。在自然意义上,生死权利及方式、时间都严格遵循生物本性,由上帝(“自然力”)安排。安乐死和试管婴儿却假借技术窃取了“神权”,可任意处置生命和制造生命。尤其是试管婴儿技术,使生命成为了制作物。
从“后人类”概念出现,到后人类语境形成,主要源于两个领域对人本身的巨大改变。在后工业进程中,基于空间生存和资源市场开辟需要所形成的体现前沿性竞争的航天业,必须解决航天人员如何适应更恶劣的环境条件,其解决途径是充分利用药物和科技方法提升人体性能,高速发展的航天业不断突破这一人体瓶颈的过程,就是塑造人的“混血”的赛博格身体的过程。赛博格身体的出现,引发对人的重新认识,由此改变对“人”的定义。如果说航天领域的赛博格身体还仅仅是药物和技术对优质人体的强制参与,以提高优质身体对环境的适应性能,那么临床医学从不同方面汇聚形成了对人的身体以及生命予以“人工”改变的普遍性方式。这种普遍性、日常性的临床努力,不仅引发对人的重新思考和定义,也制造出更为广泛和深度的人本焦虑。
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就是通过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扩展人的智能来掌握人的大脑工作密码及情感体验机制,以实现“如何使计算机去做过去只有人才能做的智能工作”。人工智能,是技术和机器对人体生命的生物工作机制的挑战。人工智能的成功,意味着人的尊严与地位将全面丧失,并且这种丧失对于人类来讲已经为期不远:2016年初,AlphaGo在围棋领域实现了重大突破,推动人工智能形成发展新浪潮。首先,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发布了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下研究编制的 《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好准备》、《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和《人工智能、自动化与经济报告》3份报告,由此凸显人工智能在美国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升级。其次,2016年5月,美国白宫成立了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MLAI),此委员会与网络与信息技术研究发展分委会(NITRD)同隶属于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NSTC)下的技术委员会(CoT),这是美国重大科技政策、战略和计划的协调机构,由总统担任主席,副总统、内阁成员和部分政府主要官员为成员。该委员会的基本职能有三:(1)负责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的跨部门协调;(2)对人工智能相关问题提出技术和政策建议;(3)监督各行业、研究机构及政府的人工智能技术研发。美国的人工智能新战略成为最富激励性的助推器,推动全球性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大竞赛,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将使人类成为无事可做的物种。
人之所以成为万物之灵,是因为它拥有众物所不具备的大脑。人工智能挑战“万物之灵”,破译人的大脑工作原理,使其成为机器工作原理;与此不同,基因工程展开对基因编辑、复制和创造的研究,却在破译人类生命的创造机制,其目的是要实现按照如同医药配方的技术方式来生产人。这项工程的开发已进入到“人可制造和生产”的前夜:1996年1月5日,第一个克隆生物“多莉”羊的诞生,标志生物基因编码可以由技术控制。2000年2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由6个国家的科学家实施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已经完成人类基因图谱的测序,这表明克隆人为期不远。几年前,一对美国聋哑夫妇想要生一个聋哑孩子,他们想方设法找到了一个祖辈五代都是聋哑人的聋哑男子,购买他的精子培育出了一个他们所希望的聋哑孩子。这对聋哑夫妇对后代基因的人为选择,曾引发美国社会的激烈争论,包括伦理争论。“基因编辑婴儿”于2018年在中国诞生的事实,虽然遭到整个国际社会的谴责和中国政府的调查,但编辑人体基因制造生命的成功技术,却可能更加激发和加大基因工程的竞争性研发进程。今天的基因工程所能做到的,已经不仅是基因选择和编辑,还包括了不同生物的基因组合、基因复制、物种交流以及新物种创造。
在后人类社会进程中,后文明,是其价值表达;后环境,是其形态呈现;后技术,是其动力机制。讨论后人类社会进程,必须以检讨后技术社会为重心,因为后技术主义对后人类社会的形成起引导和强劲推动作用,铸造出后人类社会的伦理困境和政治难题。
大步前进的航天业、临床医学,尤其是全方位展开的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全面开启了后人类社会进程,人类已有的哲学、伦理、法律、政治、社会组织秩序等都将面临重大改变。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对于农业科研的投入也越来越大,在科研中也取得了许多成果。虽然我国的各大研究机构和高校每年都会发布上百篇的成果论文和报告,但是科研成果与实际应用之间存在的差距却越来越明显,最直接的表现就在于目前绝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依然需要依靠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技术,对于新的科研成果应用存在着各种困难。在我国的农业生产过程中,需要的是成本合理、实用性强且操作便捷的生产技术,这与科研单位研究的国际高精尖技术是存在一定差距的,使得许多研究虽然已经完成,却无法将其应用在实际生产的过程中。如何更好的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农业生产力,是科研人员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后人类社会:后文明·后技术·后环境取向
其三,后人类社会是后环境社会。
其三,后技术主义通过技术直接作用于人,将人的个性引向任性。
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将文明社会之前的时期称之为原始时代,并认为原始时代的敞开方向是从蒙昧社会向野蛮社会进化,最终因为耕种、定居生活、偶婚制、土地家庭化、财产私有的相继出现而推动文明社会渐进形成。大体而言,文明社会始于农牧时代,农业社会是其基本形态,工业社会是其高级形态;后工业社会应该是后文明社会的起点。
北美世界最有影响力的STS研究学者威廉姆·工·凡登伯格在《生活在技术迷宫中》一书中认为,人类社会结构及文明形态构成,是以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生态圈之间的联系方式为内在依据。凡登伯格认为,人与人、社会、生态圈之间的联系呈三种方式,即“以生物为基础的联系”方式、“以文化为基础的联系”方式和“以技术为基础的联系”方式[6](P2)。它们大致对应前文明社会、文明社会和后文明社会:前文明社会的联系方式是以生物为基础;从前文明社会进入文明社会,其内在联系方式由“以生物为基础”转向了“以文化为基础”[6](P3)。文明社会的高级形态是工业社会,其发展的成熟形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它推动“工业社会各个支撑物的改变逐渐引发了人类第三个大项目,而这一变化又带来了一种新的联系方式——一种建立在普遍的(也就是说非文化的)科学和技术基础之上的联系。……新的技术秩序开始将自身强加于文化秩序之上,这代表着传统关系的一种剧烈逆转——过去,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科学和技术,这种独特的科学和技术会伴随文化而扩散;而近代科学与技术产生的智力上和职业上的劳动分工却不再能够体现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系的精致之处了。 ”[6](P5-6)
式中x为不同种植作物的亩产系数;y为不同种植作物的种植面积;i表示区县的序号;j表示不同作物。t表示规划水平年。
凡登伯格所讲的“第三个大项目”,就是指“以技术为基础的联系”方式。这种“新的以技术为基础的联系也不再靠局部生态系统来维系,而是最终将可持续发展提上了历史的议程。人越多地改变技术,也就越多地改变自己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同时也就越多地改变赖以促进大脑-思维以及文化的增长的经验的类型。结果,在几代人的过程中,‘人改变技术'同时也伴随着‘技术改变人'。”[6](P18-19)在“技术改变人”的过程中,“由于一种生活方式和文化再也无法给予人类生活以意义、方向和目的,因此其成员产生了无根的感觉或是漂浮不定的感觉。”[6](P19)因为以技术为基础的社会联系方式,从“以下五个方面削弱了个体和集体人类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联系”:首先,“一遍又一遍地不断重复同样的琐碎操作会削弱人类的创造力、技能、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许许多多与生存有关的东西,这其实是将人类大部分的人性也与工作分开了”,由此导致了“人类变得越来越愚蠢”;其次,高度精致分工的劳动“虽然依旧在使用各种技能,……但这些技能不是由于经验的积累从人的大脑中涌现出来的,而是由另外一些人(在工作过程之外)来决定怎样最好地完成这份工作”,实现了劳动的“手-脑分离”;第三,“劳动技术分工越是与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结合在一起发展,工人们就愈加对自己的工作丧失控制权”;第四,“随着机械化、自动化和计算机化的向前推进,更高的要求加在了工人们的肩上……而所有这些要求再加上毫无能力的控制一道导致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不健康的工作环境”;第五,“工人们彼此的疏离也消除了曾经要求增加而控制降低时出现的社会支持。 ”[6](P16-17)概括地讲,后文明社会既消解文化基础甚至反文化,也在消解个体劳动意义和创造能力,并且最终将社会发展成为技术统治人的社会。
其次,后人类社会是后技术社会。
所谓后技术社会,从个体论而言,它是一个使人不断弱化人性能力并形成“手-脑分离”劳动模式的社会,亦是使个人劳动丧失意义和价值的社会。“劳动的技术分工的发展使得自我无法在一个从外部组织好了的工作中表达出来,从而也就祛除了工作中的人性,只允许人以手或脑的形式参与到工作中来,把各种社会关系也降低到最小,结果极大地削弱了个体和集体人类生活中以文化为基础的联系。工作转变成了某种‘纯'劳动的产品并极尽可能地消除了其中含有的人性的东西。”[6](P17)从整体论而言,后技术社会是以“会聚技术”方式消解文化的秩序功能、削平差异性、消除个性和人性取向,进行扁平化控制、管理、约束的物化社会,或可说是以会聚技术方式对人、物、事进行集约化管理的社会。
所谓“会聚技术”(NBIC),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会聚技术”概念,是于2001年12月由美国的DOC、NSF和NSTC-NSEC联合发起的有科学家、政府官员和产业界领袖参加的圆桌会议上被提出来,它特指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融合会聚所形成的技术形态和技术方法,主要用于高新项目和高新技术整合研究或开发。其认知视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从科学领域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领域拓展运用,产生广义的会聚技术方式,比如,金融行业不断更新的金融工具,政治生活领域的身份化管理方式,甚至包括大学校园里的“一卡通”等,都是会聚技术在不同层次领域开发运用的呈现。
对不断开发出来的技术予以更大程度和最高水平整合所形成的更为严谨、严密的技术形态,以及由此形成扁平化、无差异、非人性取向的集约化管理为基本运作模式的后技术社会,既是一个“支配对敬畏的绝对胜利”[7]的社会,更是把人这一理性和情感的动物变成纯粹“技术的动物”的社会。在后技术社会里,技术傲慢地消解了情感,并以与权力合谋的方式僭越性地取代理性而形成 “技术理性”。在后技术社会里,技术不再以思想为动力,更不以理性为导向,也不以文化为土壤,而是以消解文化为前提,以实利最大化为动力机制,以不断实现更新权力满足为导向:“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的)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统治的特殊和利益并不是‘随后'或外在地强加于技术的;它们进入了技术机构的建构本身。技术总是一种历史-社会的工程;一个社会和它的统治利益打算对人和物所做的事情都在它里面设计着。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它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8]在后技术社会里,技术是控制人、控制自然和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在祛人化的后技术社会里,“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奴役的扩展。 ”[9](P82)
由全速发展的航天航空业、临床医学、人工智能和基因工程合力推进的后人类进程,必然创造出一种新的复合型社会形态,这就是后人类社会。
“环境”是一个开放性的概念,它是对人类存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整合表述。后环境社会,是指人类赖以存在于其中的自然世界遭受持续扩散的破坏,从而造成人类存在发展从根本上丧失自然环境生态的支撑。后环境社会形成的基本标志有三:首先,全球气候失律并形成极端气候,表征为气候变暖与变冷、酷热与高寒无序交替展开,在局部区域酸雨天气扩散和霾气候形成。其次,地球资源枯竭社会化和全球化,具体表征为陆地资源开发达到峰值后,向海洋会聚争夺开发;地下资源掏空后,全面发展军工业和航天业,向太空要生存空间。其三,为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一方面以“竭泽而渔”方式继续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第二次全球性殖民运动。由此将人类环境推上悬崖。
三、后人类社会:后技术主义框架下的伦理困境与政治冲突
如上事件表明:技术创造了“上帝之能”,并赋予人类以“上帝之手”。超速发展的基因技术成就表明,如果允许或需要,以制作流水线方式批量生产人将迅速成为现实。
在后技术主义社会,技术改变社会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向权力输送便利的方式来改变社会结构,包括改变社会产业结构,并以此为推手改变社会的劳动-生产结构、资源-财富分配结构、社会消费结构,然后改变社会权力结构和阶层结构,最终实现社会利益结构和谋取方式的改变。在后技术主义社会里,技术改变社会的最终实现方式,是通过“人改变技术”的方式实现“技术改变人”。
首先,后技术主义通过技术直接作用于人,改变人的依赖性对象和依赖性方式。
人类是依赖性存在的物种,这源于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本原性关联:自然是人类的母体,大地是人类的土壤,人类必须以大地为根基,以自然为源泉,并以人为直接的依靠:“在所有的东西中间,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人”[10]。人的依赖性属天赋,但天赋的依赖性所指涉的依赖对象却经历着改变:第一次改变发生在农牧社会为工业社会所取代的进程中,人从以自然为师、向自然学习转向以人为师,向历史、传统、经验、文化学习。在这次转变中,人努力摆脱自然的束缚,强化了对人的依赖性。从根本论,人走出自然、摆脱自然的直接动力,是科技。科技不仅开辟财富创造之路,也创造了人的科技化生存方式。在这种生存方式中,人的依赖对象被再次改变,这就是除了技术,人无所依赖。出门坐汽车,上楼坐电梯,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回到家中,除了空调,就是电脑、电视,还有就是须臾不离手的手机。总之,人创造技术,技术创造了人生活的环境,人对技术的依赖取代了对自然的依赖,也取代了对人的依赖,更取代了对环境的依赖。
其次,后技术主义通过技术直接作用于人,使人不断丧失存在的关联性。
排除标准:①男方、免疫性、多囊卵巢、输卵管堵塞等所致不孕;②同时合并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疾病者;③拒绝参与该研究者。
天赋人以依赖性的存在本质,是关联性。当人与自然、文化、人之间的依赖性弱化或中断时,意味着人与自然、文化、他人之间的关联性丧失。对人而言,这三个维度的关联性一旦丧失,就沦为真正意义上的原子人。
进一步讲,当人的存在必须依赖自然、文化、人才可获得最低存在安全和生存保障时,必须与自然、文化、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反,当人发现不依赖自然、文化、人而可获得最低存在安全和生存保障时,其与自然、文化、人的关联性就成为多余。高度发展的技术给予人这样的好处,为人类群体和个体摆脱天赋的关联性、依赖性提供了最纯粹的客观方式是技术本身。技术使人的存在和生存减少依赖度,弱化关联性,使人能更大程度地按照自己的愿意行事、生活。在城市里,传统的实体店铺,需要多组织、多结构、多层次协作才能展开,这种多层次协作本质上是深度关联和多元依赖。与此不同,无人店铺却是以技术体系构建起来的最少关联性和依赖性的经营模式,这种纯粹技术化的经营模式一旦铺开进入社会化运行,意味着人将进入“无事可做”的原子存在境况。再比如手机,通过它,人可以在不需要任何人的“原子”状况下处理诸如出行、订票、购物、办理金融业务、操作股票、期货、收集跨国信息,以及展开融通古今中外的学习等等。技术虽然无形中强迫人增强了对它的绝对依赖性,但技术同时又回馈给人以最少关联,使人得以原子化存在。原子化存在对于人来讲,既是人的最大自在和自由,也是人丧失最多的自在和自由,因为如果离开技术或者没有技术的支撑,已经丧失许多方面天赋身体能力的我们,其生存可能步履艰难。
【美国森图斯能源公司网站2018年10月2日报道】 2018年10月2日,美国森图斯能源公司(Centrus Energy)宣布从美国能源部(DOE)获得总价值为1500万美元的工作授权,准备对能源部位于田纳西州橡树岭(Oak Ridge)的K-1600设施进行去污和退役。
首先,后人类社会是后文明社会。
作者贡献声明 张弛:参与选题、设计;撰写论文;根据编辑部意见进行修改。丁辉:收集数据;参与选题、设计及资料的分析和解释。陈晓莲、杨镇朵:收集数据;资料的分析和解释。钟兴武:选题、设计、资料的分析和解释;修改论文中关键性结果、结论;对编辑部的修改意见进行核修
人既是个体也是群性的人,由于前者,人追求个性生活;因为后者,人必须共性地存在。所谓个性生活,就是创造价值和实现有意义的生活。对价值的创造和对意义的实现,必须通过他者和公共空间才可达成,所以个性生活必须以共性存在为基本指南。在“以生物为基础”的时代,人的这一存在方式表现为向自然学习,以自然法则为导向而谋求个性地生活。在“以文化为基础”的时代,这一存在方式表现为向历史、传统、经验、文化学习,以人文法则为导向而探索个性地生活。在“以技术为基础”的时代,这一存在方式表现为向技术学习,以技术法则为导向而任性地生活。因为技术的诱惑和魅力 “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或者甚至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不是积极地、就是消极地,不是生产性地、就是接受性地,在他的工作时间里为这一制度效力。”[9](P15)后技术主义所创造的技术魅力,就是祛魅和祛公共价值,将所有存在之魅变成技术之欲,将本该遵从的公共价值转换成物质之乐。在后技术主义激励下,“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他们把小汽车、高保真装置、错层式家庭住宅、厨房设备当作生活的灵魂”。这实际上“等于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消了个人在创造财富和服务时作出决定的自由爱好和自主的需要”。这种“虚假的需要”必然产生赤裸的利己主义,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攻击性,因为要“获得成功和发财致富,就要求人们具有肆无忌惮、冷酷无情和不断攻击的特性。”[9](P1)
路桥项目是否能取得成功,主要取决于项目质量及进度能够满足建设单位提出的要求。因此,在施工管理中,主要工作是对施工质量进行监控,并兼顾进度调整。
医学实习生的临床实习是医学教学的重要环节[1-2]。在传统的医院模式中,医学生都需要在较为精细分科的专科科室进行轮转实习,带教老师对患者的关注以专科为主,因此,实习生在实习的过程中也往往只注重专科的情况,对知识的掌握比较孤立,对患者的整体病情把控欠缺,这样会导致医学生从接触临床开始即局限于病种,而不是将患者看作一个整体,不利于其临床思维的培养;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是以系统疾病为主体的中心制新型教学医院,它不同于传统医院模式,它是以系统疾病为基础,多学科合作诊疗为主要手段的医院,并充分利用中心制模式对临床实习生进行培养,现将其在临床实习教学中的应用初探汇报如下。
其四,后技术主义通过技术直接作用于人,诱使人在任性中放弃责任。
个性是人在群化生存舞台上展开价值创造和意义实现的人本方式。相反,任性,则是人在群化生存舞台上对个性的放弃,对便利、实利、好处、享受的追逐与获得。任性的本质,是对价值创造和意义建构的消解,其行为表现是放弃责任,或者反责任。比如,当在教室里安装了摄像头,教师自然会有意忽视真假、善恶、美丑方面的认知引导。再比如,在后技术社会里,如何改变、缩小或消灭不平等差异性的责任,总是被“善意”地排除。
总之,在后技术社会里,后技术主义通过唯技术论、技术准则论而制造出一种既可任性又无需担当责任的新环境。“由于技术已成了一种新环境,一切社会现象便都居于其中。说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受技术的影响是不正确的,倒不如说它们都处于技术环境之中,在这里有着一切传统的社会观念都在改变的新局面。”[12]
在本次研究中,重症组支气管哮喘患者经院前救治与急诊室救治治疗,明显降低了呼吸频率、心率以及PaCO2,并极大的升高了PH和PaO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其五,后技术主义通过技术直接作用于人,不断地消解人的自由意志,压缩人的自由空间,挤兑人的自由生活。
在后技术社会里,技术真正可以摆脱人的愿意获得越来越广泛的自主意志。并且,在后技术社会里,技术无处不在,技术对人的规训和监控亦无所不在。比如,网络,被视为是最自由的大众平台,但其后台却对前台做了最完整的监控。所以,“在社会中技术的活动越多,人的自主性和主动性就越少”[13](P134)。“在人自由的时候只能无技术。……技术必须把人降为技术动物,技术奴役的王国,面对技术的自主性,这里没有人的自主性。”[13](P134)在具体功用上,技术给予人方便、便利,人通过技术获得具体针对性的方便、便利的自由;但在本质上,技术要实现绝对共性、纯粹客观,必须消解个性,排除情感,限制自由。所以,技术可能给定一种设计(共性)的自由,但前提是剥夺人的(个性的)自由,只有当人的个性自由予以真正剥夺之后,技术给定的自由才变成现实。从根本上讲,技术越发展,人的自由度越少。技术无限度地发展,人的自由将遭受更为严重的压缩。
在后人类社会进程中,后技术主义推动对社会和人的两维改变,必然造就不可避免的伦理困境和政治冲突。前者表现为技术准则与人性准则、技术准则与自然律法之间的不可调和性,这一双重困境可概括为:到底技术至上,还是伦理优先?后者表现为技术权力与人性权利 (以人性为指南的人权,包括存在权和生存权)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即到底技术权力服从人权?还是人权服从技术权力?
四、后人类社会:突破后技术主义的后伦理纲领和后政治框架
寻求后技术主义伦理困境和政治冲突的解决之道,首先需要解决认知问题。
历史地看,后人类进程始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在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后人类进程中,人类不断面临日益深重的存在危机:“19世纪的问题是上帝死了,20世纪的问题是人死了,……过去的危险是人成为奴隶,将来的危险是人可能成为机器人。”[14]弗洛姆深刻地洞察到,后人类进程是要将人这个“理性的动物”变成“技术的动物”,这意味着人最终只是可任意运用的材料:“由于人是最重要的原料,因此可以估计到,根据今天化学的研究,总有一天要建立许多工厂来人工生产人力物质。……即有计划地按照需要来操纵生产出男人和女人。”[15]20世纪80年代的试管婴儿,90年代的克隆羊,2018年的基因编辑婴儿,以及正处于全球大竞赛热研进程的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分别从不同方面映证了海德格尔的预见:“我们现在所津津乐道的技术,除了广泛地造成自然性污染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东西了……技术在慢慢地毁灭人类,人类在慢慢地吞食自然,自然选择已经成为过去,最后留下的只有技术。”[16]后人类进程中技术带来的危机之所以被如此夸大到没有任何解决的可能性,是因为在认知上将技术绝对化了。这种绝对化的表述就是技术自主性。
后技术主义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导向机制,它通过技术引导、规范绝对服从,甚至强制人只考虑眼前利害得失。在技术的引导和规范下,人们所关心的是便利最大化、享受最大化和利益最大化,真假、善恶、美丑、真知、良心、德性等原本最富有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内容,往往被无意地忽视或有意地抛弃。比如,城市交通技术体系设定出租车上下乘客的停车时间是三分钟,超过三分钟,就会自动记录为违反交通规则并处以相应罚款。这样一来,出租车司机们就达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共识,不搭载坐轮椅者以及携带太多行李者。出租车司机的任性,源于技术的模式化控制。在后技术社会,无所不在的技术“使现代的人类不但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甚至不能选择自己的手段。……并且在技术这种固有的结局与人类为之计划的非固有的目标之间的竞争中,总是前者获胜。如果技术与人类的目标不确切相符合,如果一个人企图让技术去适合自己的目标的话,一般可以立刻看到,修改的只是目标,而不是技术。 ”[11](P47-48)
关于技术自主性,海德格尔做了最初的表述,认为技术“是一种独立的实践变换”[17],即“座架”(或“框架”)。法国技术哲学家吕埃尔对技术自主性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并概括出技术自主性不可逆的三维取向。首先,技术决定自身:“技术的自身内在需要是决定性的。技术已经成为自我存在、自我充实的现实,并有自己的特殊法则和自己的决定论。 ”[18](P134)其次,技术决定人,包括决定人的存在地位和生存目标:“技术将一切溶合在一起。它使人不再对任何事件感到震惊和轰动。人类不适应于钢铁的世界,技术使人类适应。它将这个盲目的世界重做安排,使得人类对严酷的世界逆来顺受,安于非人性化的生活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11](P46)其三,技术决定经济,更决定政治:经济发展模式及速度,政治变革的性质与方式,均受制于技术。或可说,无论经济或政治,其发展或变革总是以技术为框架和动力:“技术对经济和政治是自主的。我们已经看到,在当前,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化都不能制约技术的进步,技术进步也不取决于社会形势。……技术会诱发和制约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变革,技术是所有其余东西的最初动因。 ”[18](P134)
然而,不仅后技术时代,即使“以生物为基础”或“以文化为基础”的时代,技术发展总有自身轨迹:技术发展并非跨越式,只能是阶梯式的,一步一步奠基、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一种或多种即将产生的新技术的种子,总是蕴含在已有的技术之中,这些蕴含于成熟的旧技术中的新种子,如要变成新技术本身,是技术自身不能做到的,他需要人、需要人的大脑的天才想象和创造性运作,才可变成现实。比如,从生产纯粹物理程序的机器人到开发人工智能,这是人的作为,并不受机器人指控。同样,对于人工智能,在如何开发的层面可能要借鉴生产机器人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智慧和方法,但对于开不开发人工智能,以及要将人工智能开发到什么程度方可停止,这完全由人来决定。同样的道理,基因工程发展至今天,是否继续向前推进,也不是由已经成功克隆的技术或选择基因的技术所决定,而是由掌握这些技术的人和领导这些人的机构所决定。
2.4 培训与交流相结合 制度培训是制度掌握的前提,是确保安全的重要环节[3]。每季度对全院护理人员进行制度培训,包括护理安全与风险干预、老年人的安全管理和不同时段的防护理安全风险干预等。同时,团队每月在院内网站上发布护理安全信息,建立了护理安全管理的专业知识题库,内容包括护理安全相关制度和应急预案、个案分析和相关法律法规等,并定期进行护理安全知识护士知晓率问卷调查,根据结果调整相关培训频率。制作图文并茂的护理安全手册供家属及患者参考使用,定期对全院保洁员和护工等进行授课培训,并与后勤保障等相关部门配合,在硬件设施等方面促进保障护理安全措施落实。
由此不难发现,从表现形式讲,技术具有自主性;但从本质论,技术的自主性受制于人的自主性。比如,出租车司机不搭载坐轮椅者或负重行李者,是因为“停车不能超过三分钟”的交通技术设定,只考虑到一般,忽视了特殊,假如对搭载坐轮椅乘客,其停车时间放宽设计为6分钟或10分钟,就可杜绝出租车司机不搭载坐轮椅乘客的现象,出租车行业的公共道德状况就会好许多。从此实例可以看出,以普遍性为准则的技术所带来的伦理困境以及政治冲突,最终源于开发和运用技术的人和机构,只要解决了人和机构的问题,由此形成的伦理困境或政治冲突,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解决。
决定技术的开发主体,是技术机构及其所统领的技术人员;对技术的运用,是相应的社会组织。仅前者论,决定技术开发的动力机制有两种:一是科技人员的职业利益、科技兴趣和成就冲动;二是技术机构的利益投入与回报机制。相对来讲,作为个体的科技人员总是受制于所雇用的机构,所以决定技术开发的真正启动机制,是技术机构的利益机制。影响技术机构是否启动以及以怎样的力度和强度启动力量,对一般的常规的技术开发,就是市场的需要;对于特殊的、重大的技术项目,比如人工智能、基因工程、航天工程等等的启动力量,除了财团,就是政府,或者政府与财团携手合作。所以,在后人类社会进程中,技术所带来的所有伦理困境和政治冲突,都不是技术本身,而是技术机构、企业、财团、政府。
在实训教学中,教师设计出的任务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任务的完成情况没有一个具体的参考标准,教师要引导学生进行客观的自我评价和反思。最后,将学生的自我评价、同学评价和教师评价三者有机整合,在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能力、知识迁移能力会得到不同程度的体现,这是自主学习能力最重要的一部分。
综上所述,“技术决不是一种自主的力量,而始终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和人的工具。到目前为止,技术既不是好的也不是坏的,而仅取决于以什么方式来利用它。”[19]基于如此客观认知,“任何片面化描述,尽管有其实用性,但由于把技术看作是自主的主体,故在实际上给出了一幅根本错误的图景。”[20](P63)这是因为“技术领域中的一切事物是人创造出来的,因而,取决于特定时期的人的占支配地位的价值观和目标。”[20](P140)后人类进程中所出现的后技术主义,同样不是技术所造就,而是与技术开发和使用密切相关的人、社会组织、政府机构等多方利益整合所形成的利益冲动机制在技术开发或运用上的表现。
海德格尔曾指出,“技术不仅仅是手段,技术是一种展现的方式。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一点,那么,技术本质的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就会向我们打开。”[21]这个赋予技术本质的“完全不同的领域”,就是人的领域,就是由人和组织机构基于持久不衰的最大利益谋求所组成的领域,必然向我们敞开而突显出后人类进程中表面上由技术造成但实际上由人与组织机构造成的伦理困境和政治冲突的解决之道。后人类进程中所不断暴露出现的伦理困境和政治冲突,不是没有解决的可能性,而是只要有人存在、有政府存在,有人和政府心存解决的愿意和决心,就一定会有可解决之道。
首先,在后人类进程中,解决“到底是技术至上,还是伦理优先”的问题,实际上涉及技术与伦理的界限问题:技术的开发与运用,没有突破伦理的边界,并遵从和维护了道德,伦理应该尊重技术。反之,一旦技术开发或运用突破了伦理的边界,损害了道德,或者可能突破伦理边界且造成无法弥补的后果,那就应该伦理优先,道德先行,技术必须为伦理、道德让步,或改变方式,或放缓速度,或终止开发或运用。前者如安乐死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慎重开发和使用,就是典型的例子;后者如最能给人类未来带来毁灭性危险和不安全的基因工程、人工智能,亦当必须伦理优先,即以伦理规范和引导基因工程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以防范于未然。
以此为准则,伦理必须进行后人类重建,即建构起能够指导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后伦理体系,包括思想、原理、原则、规范和价值系统。这需要后人类哲学的奠基,因为只有当对人、生命、自然、物重新予以形而上学拷问,进行存在论的重新定义,后伦理体系的建构才有依据。
从根本讲,伦理学是哲学达向普遍实践的方式和方法论[22];伦理,也因此成为政治探索理性实践的方法。在后人类进程中,伦理的觉悟,是人的最终觉悟。后伦理体系的建构,才可为后技术主义制造的政治冲突的真正解决,提供普遍的公理、价值系统和实践行动的指南。
术后三个月及六个月时,所有患者进行复查,给予CT平扫与MR检查,瘤体血供完全消失或者显著减少,碘化油沉积较好,有碘化油聚积及瘤体缩小征象的出现。本组病例瘤体直径术前(15.47±3.27)cm,3、6个月时分别为(11.31±2.82)cm和(9.25±2.40)cm,与术前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且病灶随术后时间的增加呈进行性缩小。
当以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为准则的后伦理体系得到明确方向和整体思路的确立,后人类进程中“到底是技术权力服从人权”还是“人权服从技术权力”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技术权力是一种利益权力,相对社会共同体及所有成员而言,它只属于少数人、少数机构、少数利益集团所掌握的权力。所以技术权力是特权,是后天制造的权力,具有无限度的扩张性和剥夺性。与此不同,人权,是人的生命存在权和生存权,它属于社会共同体的每个成员。并且,普遍性的人权是天赋的权利,是完全平等的普遍权利。无论“以文化为基础”的社会,还是正在经历的“以技术为基础”的后人类社会,其不毁灭的存在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标志,就是人类共同体每个成员享有更高水平和更为平等的人权。由此,解决后技术主义所带来的政治冲突的根本路径,就是更为明确地、毫不动摇地确立技术权力绝对地服从人权的基本认知,并由此建立、健全技术权力绝对服从人权的制度机制和法律机制。只有如此,才可真正避免政治成为技术奴役人的推手。比如,人权中最根本的权利是天赋平等的生命权利,当天赋平等的生命权利遭到来自基因工程的威胁时,根据技术权力必须无条件服从人权的后政治准则,基因工程应该为此让步,否则,任由基因工程的野性发展,一旦基因突破完全成功和跨物种交流完全实现,将有什么机制可以阻止基因战争的发生?并且,基因突破的成功如何保障生物人种两性交流激情、血缘亲情、天伦之乐的情趣、美和自由?再比如,最基本的权利是劳动权利,当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的前景将使大多数行业消失,这就威胁到未来人类成员的劳动权利。为了使人类共同体成员的劳动权利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人工智能研究和开发就应该有范围和领域的限制,如果无限度开发人工智能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丧失劳动权利,人类即使没有因为技术而毁灭,也会因为“无事可做”而绝望。劳动权利,不仅仅是获得生存资源保障的权利,更为根本的是人存在于世与动物、与一切形式的机械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就是劳动是人成为人的意义的源泉、价值的源泉、创造力和美的源泉,当更多的人因为人工智能之类的高新技术的无限制开发而丧失劳动权利之后,人成为人的源泉断流了、枯竭了,很难想像,这种社会状况一旦出现,人类将有什么前景?
参考文献:
[1]肖明文.身体、机器与后人类:后人文主义视角下的《救人就是救自己》[J].文学理论前沿,2014,(20):32-33.
[2](英)尼古拉斯·罗斯.生命本身的政治:21世纪的生物医学、权力和主体性[M].尹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98.
[3](法)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506.
[4]Donna Haraway.Simians,Cyborgs,and Women:The Rein-vention Nature[M].London:Routledge,1991.
[5]林建光,李育霖.赛博格与后人类主义[M].北京:华艺学术出版社,2013.3.
[6](加)威廉姆·工·凡登伯格.生活在技术迷宫中[M].朱春艳,吕松涛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
[7](美)迈克尔·桑德尔.反对完美:科技与人性的正义之战[M].黄慧慧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97.
[8](美)马尔库塞.现代文明与人的困境[A].马尔库塞文集[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08.
[9](美)马尔库塞.工业革命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0]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9.
[11](美)J.吕埃尔.技术的社会[J].科学与哲学,1983,(1).
[12]J.Ellul.The Technological Order..In:Mitcham C,ed.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M].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3.25.
[13]J.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Vintage Books New York:knopf Random Hous,1964.
[14](美)弗洛姆.健全的社会[M].欧阳谦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370.
[15](德)冈特·绍伊博尔德.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科技[M].宋祖良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40.
[16](美)戈兰.科学与反科学[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28.
[17]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下)[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885.
[18]J.Ellul.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M].New York:Vintage Books,1964.
[19] (德)G.弗里德里奇,(波)J.沙夫.微电子学与社会[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3.
[20]F.Rapp.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M].Springer,1981.
[21]宋祖良.拯救地球和人类未来: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2.
[22]唐代兴.伦理学原理(自序)[M].上海:三联书店,2018.2.
Ethics and Politics in Post-human Process
TANG Dai-xing
(Institute of Ethics,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6)
Abstract: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industry,clinical medicine,genetic engineer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ave prompted mankind into the post-human process,which builds the “technology-based” social contact by virtue of “aggregation technologies”,and forms a post-environment society in which technology dominates human orientation.In the post-human process,post-technolism abandons “biology-based” and “culture-based” social contact,and changes the objects and ways of people's dependency through technology,which makes people constantly lose their existence relevance,thus leading people from individuality to capriciousness,giving up responsibilities in capriciousness and gradually falling into fundamental ethical dilemmas and political conflicts.The former reveals the irreconcilability between technical standards and human norms and natural law,while the latter highlights the fundamental opposi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power and rights of humanity.This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through post-technolism and reconstructing post-ethical programs and post-political frameworks.In terms of the former,it is to establish the law system of ethical priority,that is,natural law guides humans,and human norms regulate technology.In terms of the latter,it is necessary to build a legal system that gives priority to human rights,that is,the norms of human rights guide technology and technological power.
Key words:post-human process;post-technolism;post-technology stage;gene editing;converging technology;post environmental society;post-ethical programs;post-political frameworks
中图分类号:B 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原260X(2019)01-0014-10
收稿日期:2018-09-28
作者简介:唐代兴,四川师范大学二级教授,特聘教授,四川省学术带头人,主要从事生态理性哲学、伦理学研究。
【责任编辑:来小乔】
标签:技术论文; 人类论文; 社会论文; 人工智能论文; 伦理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家理论论文; 国家体制论文;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四川师范大学伦理学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