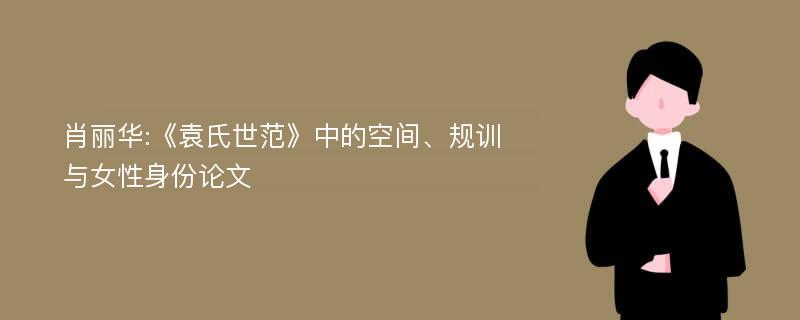
摘要: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女性因被局限在家庭内部,而成为历史的沉默他者,女性解放的道路首先要打破这一空间限制,走向公共空间;这一论断显得过于简单,且有失偏颇。事实上,中国古代女性的存在状态并非局限在家庭内部。在理学盛行的宋代,江南家训的代表《袁氏世范》呈现了复杂多元的女性生活空间与身份,女性溢出了传统性别理论设置的界限。江南地区士绅阶层的女性,作为母亲、作为妻子都被鼓励通过“内”,实现对“外”的参与与跨越,体现了中国“家国同构”在性别问题上的独特性。
关键词:《袁氏世范》;江南家训;女性;空间;身份
20 世纪70-80年代,以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和福柯为代表提出空间理论。列斐伏尔指出“权力到处都是,它无所不在,充满整个存在,权力遍布于空间”。[1]86在此基础上,将性别纳入空间与权力进行思考,探讨身份问题,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西方学者提出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二分:即男性主要在公共空间从事工作,女性则与家庭空间紧密相连。“通过强化家庭和工作场所空间分离的重要性区分出女性空间和男性空间,从而使空间有了性别特征,它使女性在一些所谓‘非女性’空间感到不舒服,从而使女性自觉处于特定空间中。”[2]67研究中国女性主义的学者遵从这一空间二分法,根据中国传统建筑布局与不同性别的活动空间分工,得出中国女性的历史就是一部被囚禁淹没在家庭内部空间的历史,而女性要想突破这一设置,就必须打破传统的空间分配。[3]6这样观点不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女性生活真面目,本文结合宋代江南家训的代表之作《袁氏世范》对女性生活空间进行分析,以期探讨我国古代女性丰富的生存空间。
一、《袁氏世范》中严守内外的女性身份
袁采,字君载,信安(今浙江常山县)人,“德足而行成,学博而文富”。袁采以儒家之道理政,在任乐清县令时,撰写了被认为仅次于颜氏家训的《袁氏世范》用来践行伦理教育,其中多有对女子生存空间的规范。而在袁采之前,原始儒家以及宋代理学对于性别与空间已多有论述,这些都是袁采的思想背景。男女有别,空间各异,可以说是儒家思想较为普遍的表述,例如在《礼记·郊特性》中“夫受命于朝,妻受命于家”;《易经》“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后世儒家大多从这个方面加以引申与规范,严守内外之限,“女处闺门,少令出户”。宋代程朱理学的发展,进一步将儒家对女性的规训推向极致,对女性空间的约束,从理论上而言愈加严苛。程颐在《程氏易传》里完成了对宋代妇女“主内”观的理论论证,朱熹则将其在日常生活领域以“礼”的形式固定下来,强调女性恪守空间规训的重要意义,“一家之中,须是内外各正,方成家道”,“一妇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这些思想成为指导宋代妇女日常行为规范的指南。女子居于内室,中门是男女、内外的分界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正是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严格规范。
从整体看,袁采的思想大致符合儒家的“严内外之限”这一核心原则,他最推崇司马光《居家杂仪》提出的方法——“令仆子非有警急修葺,不得入中门;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只令铃下小童通传内外”。中门在民居空间界定上主要起着伦理防卫作用,“治家之法,此过半矣”。袁采遵守儒家规范,将女性的活动领域局限在闺门之内,家中妇女婢妾无故不得出中门,至于“市井街巷,茶坊酒肆,皆小人杂处之地”,男性亦远之,女性更必须多有回避。对外边的妇女进入宅舍,需严加防范,房屋建筑“须令墙垣高厚,藩篱周密,窗壁门关坚牢,随损随修”,房屋高大坚固不但可以防盗贼,“且免奴婢奔窜及不肖子弟夜出之患”,高墙具有同中门一样的伦理防范功能,有效规避有悖礼法事情的发生。可见《袁氏世范》对女性活动空间的规范极为严格,也大致符合程朱理学对女性性别身份的限制,这些规范又与中国传统建筑尤其是江南民居的某些建筑特点相关,规训与权力必须通过具体的空间形式得以实现。江南民居的建筑格局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之下,同样体现上下尊卑、内外有别的等级关系,并在某些空间设置上突出其性别规训的意义,比如女儿墙,本是建筑物上起防护作用的矮墙,渐渐演化为对女性的限制,李渔在《闲情偶记·居室部》中写到:“此名以内之及肩小墙……,岂妇人女子之事哉?”矮墙成为了防护女子与外界接触的防线。再如小姐窗,除建筑上的通风采光功能外更主要也是伦理意义,隔绝外界的视线,保证待嫁女紧锁深闺的神秘性。宋代妇女在婚前起居空间便主要体现在女儿墙、小姐窗的设置中,而在婚后,活动空间主要被限制在中门内,这也是袁采对女性生存空间的设想,“这些空间关系进而被赋予了封建礼仪上的尊卑等级关系的文化意义。创造出封闭的院墙合成内向庭院而自成一体的布局方式构建成封闭的空间秩序”。[4]
她在他的描述里逐渐现出轮廓:长发、中性、神情冷峻。那是20年前,县城的大街小巷正流行甜腻的港台风,她却一身夹克长靴来到研修班上,放吉他时不忘将垂下的头发及时伸手归拢上去。那是他见她的第一眼。只一眼,她就像一颗出膛的子弹,一下洞穿了他的心。
这一空间的内外之分,男女有别,表面上看的确非常接近于西方女性主义所批判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二元对立。“与男子向外扩展的竞技场相反,女性的职责在锅灶和织机上。她的定位是向内的,在个性外表和行动上,她都是内敛的。”[5]155戴锦华与孟悦便在《浮出历史的地表》中对儒家的性别空间与伦理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受命于朝的男性理所当然是社会生活的一份子,而受命于家的女性却因生存于家庭之内,而被拒斥于之于社会之外,家庭几乎是专为女性而特设的特殊的强制系统,它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针对性和性别专制意味。男女之命确实是比如天壤,这一受命之别,乃是主人与奴隶之间,或看守与囚徒之别”。[3]7而阅读《袁氏世范》,会发现女性生存空间绝非如此严密而刻板,女性也绝非是家庭空间的囚徒,女性与家庭空间呈现丰富而多元的关系。
二、《袁氏世范》不断越“界”的女性身份
中国传统社会,母亲是家庭教育的实施者,不但要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角色,还要对孩子进行教育,士绅阶层理想的母亲形象是教育型的,而非养育型。其中,关于母亲应该如何教育孩子,《袁氏世范》提出:“闲有家训稍严,而母氏犹有庇子之恶,不使其父知之。”因而造成“破家”,“能守素业,使门户不辱”,严格教育子女,使之成才,能守家能报国,这正是母教的使命。因此教子必须从幼年抓起,“幼而示之以均一,则长无争财之患;幼而责之以严谨,则长无悖慢之患;幼而教之以是非分别,则长无为恶之患”。袁采还引用了王珪母李氏干预儿子择友的实例论证母亲对儿子结交良友的重要性。而有关母亲如何对待女儿,则超越男尊女卑思想,提出在财力许可情况下给予合理的财产,女子在婚后依然可以承担照料父母的责任,“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托女家,及身后葬祭皆由女子者,岂可谓生女不如生男也”。袁采的这些训导体现了母亲的极高权威,并表达了对理想母亲的期待。母亲必须对子女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关注与实施规矩,从衣食住行到读书、做官、品性,均是母教的领地。如同刘向在《列女传》中记录过的母仪典范,母亲通过教育子女使家族产生向外辐射的影响,同时也间接地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这源自于中国“家国同构”的特殊社会组织形态,和西方理论中家庭与公共空间的二元对立并非一致,家庭空间并不等于边缘化。中国的女性是人伦关系里的“女性”,而非性别意义的“女性”。女性处于家庭内部,其作用不止于家庭,成为母亲的女性,在家庭中拥有极高地位和威严,通过对子女的影响力实现了空间权力的极大拓展。
(一)贤妻身份对家庭内部空间的跨越
“贤妻”与“良母”是中国传统社会与家庭对女性的最高要求,但原始儒家对“贤良”的界定并非只是将女性限定在家庭内部,顺从父权与夫权,这一概念已经包含了对女性能力与地位的认可。宋代江南士绅家族的家训中“贤妻”的概念便承续了儒家的这一思想,更强调“襄助丈夫”的美德,《袁氏世范》可以说是这一类江南家训的代表,且思想更具革命性,明确强调在诸多情况下妻子对家族事务的直接管理。“有夫死子幼而能教养其子,孰睦内外姻亲,料理家务至于兴隆者,皆贤妇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营生最为难事。托之宗族,宗族未必贤;托之亲戚,亲戚未必贤。贤者又不肯预人家事。惟妇人自识书算,而所托之人衣食自给,稍识公义,则庶几焉。不然,鲜不破家。”若女子遭遇人生不测,夫死子幼,决不能因此将家庭全然托付给宗族亲戚,如果有能力使家道兴隆,这才是真贤惠。反之若只是固守“不预外事”,一味依赖他人,致使家庭破败,这才是家族不幸。当然寡居女性独立主持家族理财的能力有限,因为“很少有女人具备管理财产必不可少的识字、计算能力”。[6]168但袁采对女性德才兼备独当一面,寄予了希望,并未将内外之限僵化,对于女性的身份未做刻板处理,女性要直接料理家族事务,其生存空间必然由内转外,实现空间跨越。这一思想在《袁氏世范》中多次强调,“妇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务,计算钱谷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不肖而能与其子同理家务,不致破家荡产者”。即使丈夫在世,但愚钝无能、败家,妻子亦可以代替丈夫,料理家务,管理财务,成为家庭支柱。在袁采看来,有能力的女性可以突破内外之限,从内闱走向厅堂(公共空间),这一见解在理学极盛的宋代,革命性意义不言而喻。
(4)环境污染:矿山尾矿严重破坏了土壤、植物、大气和水源等周边生态环境,矿区及周边区域空气粉尘飞扬,植物枯黄,土地沙漠化,水源酸化,并伴随刺激性气味,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尾矿中的硫化物、重金属离子、药剂等物质常常具有一定毒性,而且这些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会加剧对周边水源、土壤以及地下水的污染,并随河流迁移影响更大区域的生态环境。目前,我国因尾矿直接和间接污染土地面积超过1 000余万亩[22]。
切除宫颈组织完整,宫颈切缘肉眼观察无病灶,石蜡切片检查切缘无残存病灶。手术时间30~50min,平均时间为25.5±3.4min;出血量10~80ml,平均20.8±13.5m L;住院时间平均2.8±1.5天,术后发热2例。子宫颈锥形切除术后与术前阴道镜病理结果诊断完全相符者29例,不符合31例。宫颈锥切术后病理检查阴道镜下多点活检程度重15例,CIN III 10例(术前诊断为CIN II 3例,CIN I 7例),CIN II 5例,术前诊断为CIN I;程度较轻16例。
《袁氏世范》中还强调了女性未嫁之前的教育,主要便是顺从父母,勤学女红。即使女红作为未嫁之女最主要的学习技能,其功能并非完全为了以此将女性约束于内室。“精英阶层家庭的女儿,都要接受体力劳动的训练,这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来应付寡居或贫困等可能遭遇的逆境,一是在家中为孩子和奴婢树立一个勤劳的榜样。寡母取代己故的父亲成为家中支柱,她用劳动所得作为儿子的教育费用,同时,操劳的母亲形象是母爱子孝的强有力的象征。”[7]204士绅阶层的女子不为生计需求,但必须接受妇功的训练,也只有具备这种能力的女性才能在婚后完成空间的突围,成为自己的主体,这彰显的正是士绅阶层家庭的独有特色。
(二)母亲身份与女性生存空间的拓展
袁采在家训中尽管也提出“妇人不预外事”,但女性在履行其身份与职责时其生存空间远远超越这言论限制。
从历史上看宋代女性的经济地位是比较高的,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妻家所得之财,不在分限”,因此女性涉及到独立的经济事务较多,借贷、购置田产与墓地都是可能的,那么就需要提高女性的能力与法律意识。《袁氏世范》专列一则,提示女性在借贷、契约问题上的注意事项,“佃仆妇女等,……而欲重息以生借钱谷,及欲借质物以济急者,皆是有心脱漏,必无还意”。江南此时的经济状况较好,女性作为契约的主体或作为保证人参加契约活动,女性经济行为已经走上历史前台,这些行为已超越了内外之限。《袁氏世范》反映了宋代江南望族的女性活跃在公共空间的生存状态,士绅家族中女性通过贤妻这一身份,完成空间转换。其实在原始儒家的思想资源中,并没有严格限定女性的活动空间,许多有才能的女性都活跃在所谓的公共空间中并受到赞美,例如《论语·泰伯》对王后女君的记录;《礼记·昏义》则记载了新妇的宗族管理责任等。从这一角度看,以《袁氏世范》为代表的江南家训对女性活动空间的宽容,与原始儒家的思想是一致的。
袁采充分认识到作为贤妻与良母的女性突破传统规训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如果女性生存空间狭隘,不仅无法成为贤妻、良母,而且会眼界狭窄,甚至搬弄是非,制造家庭不睦。“人家不和,多因妇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辈”,致使“一家之中,乖戾生矣”。家庭的不和睦,往往是因为家中妇女“传递言语”所致。妇女之所以会这样,是由于“盖妇女所见不广不远,不公不平。”妇女生活空间的促狭,决定了其视野与见解的狭隘,袁采已经认识到具体的生活空间与心理空间的关系,空间对身份与人格塑造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对空间的认识,他才在有关子女教育的部分提出不能因担心孩子会学坏就限制他的生活交友空间,“时其出入,谨其交游,虽不肖之事,习闻既熟,自能识破,必知愧而不为”,子弟生活空间越大,接触事物越多,才越能养成明辨是非的能力。家庭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与起点,在家庭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的女性,在袁采的时代其生存空间形态早已超越了物理空间的分割。空间对女性的规训,虽然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在民间真实的生活中,尤其是随着经济发展,女性的活动空间与可以干预的空间,正在变得更为宽泛。
本试验在配制C40水工混凝土时,σ的取值为5 MPa,即C40水工混凝土的配制强度应不小于48.2 MPa(混凝土强度保证率95%)。
(三)不同阶层,女性生存空间不同
如果说对于士绅阶层的妻子、女儿而言,空间的内外之限仍需“严守”的话,其他阶层的女性,很自然具有完全不同的空间自由度,好比道婆、媒婆、尼姑等等,她们可以自由出入各种场所,袁采如同大多数的卫道士一样,对这些女性保持警惕,“尼姑、道婆、媒婆、牙婆及妇人以买卖、针灸为名者,皆不可令入人家”,他认为这些不守空间规矩的女性,意味着道德品质的堕落,如果良家妇女与其来往,势必会被扰乱了心性,所以他严格限制这些女性的造访。《袁氏世范》还谈及到了对奴婢、乳母等女性的雇佣问题,阶层不同,生存空间必然不同,空间不仅仅与性别有关,更与其他具体的现实条件相连。这些贫寒妇女,为了养家糊口,被迫离开家庭,进入更复杂的空间之中。能够有条件恪守空间纯化,正是上层社会女性的特权,因此“内外各处,男女异群的原则也更可能见于精英阶级家庭不让女儿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是精英阶级显示其道德优越感的一个途径”。[6]233即对女性空间的限制主要是针对经济条件、社会地位都比较优越的家庭,“符合礼制与习俗的居住空间只是针对有此条件的家庭,没有条件的家庭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与礼制相似而已。即影响女性活动空间变化的因素主要是年龄的变化以及阶层的变化”。[8]18空间的内外之分,某种程度上成为了女性彰显自己社会地位的标志。普通家庭女性,则必然要走出家庭,走向公共空间,共同承担经济负担。
宋代女性的活动空间大有突破,史学界已多有研究。例如,《宋代妇女角色的时代特点》通过研究宋代的墓志铭,提出了宋代士绅阶层的女性多数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并且经营管理家政促进家族兴旺。同时由于宋代的手工业非常发达,陶瓷业、印刷行业、纺织业等都以女性为劳动主力,这说明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已经被突破。在商业、城市、市井文化发展过程中,作为市民阶层一部分的市井妇女,在社会转型的宋代,她们的角色定位和时代特点,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尽管儒家思想仍然居于主导地位,可是市井妇女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获得了行动自由,有了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尽管她们地位低下,却是社会经济、文化与城市生活中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量。[9]42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出理论上对女性的空间与身份的规范,在历史现实中并没有真正实现,更多是一种理论建构或者伦理理想,即使在理学确立时期的宋代,女性的生活空间也极为丰富多元,女性的活动和成就已远远超出了内闱和家庭的范畴。
三、结语
在研究中国古代女性生存状况时,有学者认为,中国女性都是被传统文化、被男权排斥到历史边缘的沉默他者,是一个地地道道被局限在家庭内部空间的第二性。通过《袁氏世范》对女性的空间限制与女性的真实身份的分析,可以看出:其一、儒家家国同构形成的家庭空间的特殊性,家和国,并不等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内和外。女子在家庭、社会和国家中扮有极其重要的角色。母亲和妻子通过儿子和丈夫社会价值的实现,使自己的价值得以体现。其二、空间与特权,阶层不同、身份不同,规矩不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古代女性”。对性别空间的区分,在现实中极难完全实现。女性是不同的女性,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是不容被忽视的。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曾经对西方白人女性主义研究方法做出批判:其一、主观概念推延;其二、非历史主义;其三、尚古主义。[10]将中国古代女性作为了一个静止的、主观概念推延出来的研究对象,理论术语又是从西方挪用来的,因此难免出现理论与复杂历史场景不完全匹配的现象。正如高彦颐所言,当时提倡女权的人,“非要把传统的女子说的一无是处,然后才可以有一个新的革命性的女权主义,有了新的女权主义,才可以建构一个新的现代国家”。[11]6而当下中国古代女性问题研究则需要我们回到历史语境中来。
参考文献
[1]Lefebvre H.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M].Bryant F, trans.London: Allison & Busby,1976.
[2]琳达·麦克道维尔.性别、认同与地方——女性主义地理学概说[M].台北: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06.
[3]戴锦华,孟悦.浮出历史的地表[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朱静,毛白滔.迁徙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女性空间[J].艺术与设计,2009(8):156-159.
[5]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6]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M].胡志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
[7]曼索思.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8]张宏.性·家庭·建筑·城市:从家庭到城市的住居学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2.
[9]郑必俊,陶洁.中国女性的过去、现在与未来[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0]肖丽华.在姐妹情谊之外——论后殖民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之争[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3(2):23-27.
[11]王政,陈雁.百年中国女权思潮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Space, Discipline and Female Identity in The Yuan Family Education
XIAO Li-hua
(1.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315000, China;2.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bstract: It holds that ancient Chinese women were confined to the family and thus became the silent others of history.But in fact, the existing stat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s more complicated.By reading The Yuan Family Education, we can understand that Gentry women, as mothers and wives, are encouraged to participate in and penetrate into the outside world through“inside”, which embodies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homeostasis”in gender issues.
Keywords:The Yuan Family Education;the precept of the families in the southern China;feminist;space;identity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124(2019)04-0029-05
收稿日期:2019-04-2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与失误:中国女性主义批判”(16YJC751032)
作者简介:肖丽华(1978-),女,山东潍坊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当代西方文论。E-mail: treesmemory@126.com
(责任编辑夏登武)
标签:女性论文; 空间论文; 家庭论文; 宋代论文; 儒家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伦理学(道德哲学)论文; 婚姻道德论文;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9年第4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在历史汇流中的抉择与失误:中国女性主义批判”(16YJC751032)论文;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论文; 浙江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