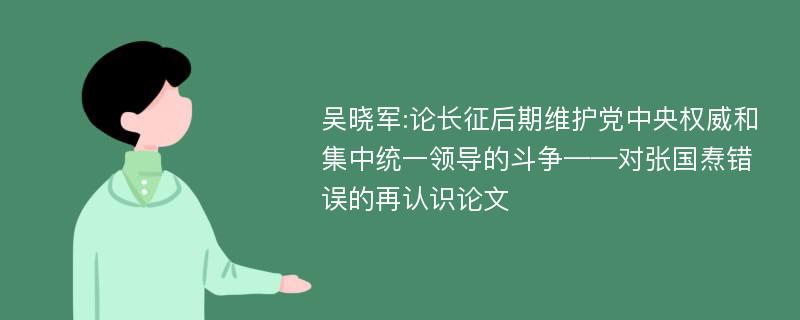
提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建设根本性和基础性工作,也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发生在长征路上的党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就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而展开。张国焘错误的本质,就是蔑视中央权威,破坏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最终导致另立中央制造分裂,给党和红军的事业造成难以弥补的恶果。回顾这段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不无裨益。
关键词:长征;中央权威;统一领导;张国焘
长期以来,批判张国焘的错误主要集中在“分裂主义”这一点上,这只是触及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他的错误的本质和根源,就是思想动摇,对党不忠诚,用军阀习气和非组织的手段破坏中央权威,反对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其目的就是谋取党的最高领导权和军队最高指挥权,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以史为鉴,汲取其中深刻教训,总结全党全军与之斗争的策略方法和经验规律,必将有助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进而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一、从误判时局、拥兵自重到另立中央:张国焘变本加厉破坏中央权威
(一)误判时局、思想动摇,用“南下”“西进”错误方针对抗中央北上
1935年6月,长征中的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红军力量实现汇合,时局出现有利于革命发展的良好机遇。此时,作为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的张国焘,一方面急于了解中央的意图,另一方面又撰文公开自己的想法:西进西康、青海、新疆,到“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的“区域发展”,或是向南“直取成都,出长江,打到武汉去”[1],抢先公布了他的“西进”和“南下”方案。此时,党也在考虑未来的战略行动。接到张国焘电报后,6月16日,由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联名回复:“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2]511这是中共中央明确宣布北上方针的最早文件[3]。北上开赴抗日前线是顺应民心,而张国焘的“西进”却脱离抗日前线,“南下”又违背了红军经长征跳出国民党统治中心地区的战略转移目的,这是对时局的误判。在西进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目标上,双方也存在着前提条件和路线的差异。中央的设想是立足于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后,再用部分兵力组织远征军。而张国焘则是要将红军全部带到西康、青海、新疆去。
张国焘最初亮出自己的想法时还不知道中央的意图,但是,接到中央16日电报后发生的情况就耐人寻味了。从17日起,张国焘就不停地寻找理由否定中央的方针。他表示“同意向川、陕、甘发展”,但又提出北上筹粮要比南下困难得多,认为南下更有利[4]59。这说明从一开始,张国焘就不曾认真考虑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因为他固执地认为北上川陕甘,缺乏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中央为了说服张国焘支持北上,于18日去电分析南下没有前途,同时指出北上川陕甘的战略重点是首先占领川北的松潘、平武,要求张国焘“望即下决心为要”[5]519。有感于双方仅用电报难以深入沟通,中央邀请张国焘来懋功,“以便商决一切”[2]523。
充足的存货对于粮食仓储企业而言是创造效益的根本,在当前的社会发展格局下,粮食仓储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较为复杂。若企业的仓储量大于需求量,粮食存储时间过长就会发生变质,造成企业的经济损失;若仓储量小于需求量,则会使企业丧失获取更多利润的机会,影响企业的创效能力。提升粮食仓储企业存货成本管理的有效性,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必由之路,应主动探究存在于当前存货成本管理当中的问题,探寻提升存货管理有效性的可行性路径。
1935年6月25日,张国焘在两河口与党中央及红一方面军领导人会面。正是这次会面,加深了他对时局的误判,动摇了他对中央的信赖。原因是他看到一方面军减员和疲劳的现状后,就不加分析地把遵义会议前后两个阶段党中央不同的领导和决策混为一谈,进而怀疑党中央提出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正确性。思想上的动摇,必然导致行动上的错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四方面军的人数占着五分之四,所以,张国焘身上“军阀主义”的“枪指挥党”的个人野心急剧膨胀,“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比例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再带入政治局”[5],具体做法就是用“西进”或“南下”对抗中央北上方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周恩来首先作报告,重申了党中央既定的北上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张国焘则抛出“三个计划”:一是“在川康地区立下脚来”的“川康计划”;二是北上川陕甘北部的“北进计划”;三是移师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的“西进计划”。张国焘为什么一再坚持被中央否决的“南下”和“西进”呢?用他的说法,在懋功初会时,他就在政治军事以及两军关系上,提出与毛泽东“针锋相对”的看法[6]216。表面看他没有否定北上,真实想法却是用“西进”和“南下”“冲淡了毛泽东的靠近外蒙的唯一主张”[6]230。
可见,张国焘在红军长征战略方向的选择上主张的“南下”或“西进”,根源于误判时局和思想动摇,并在日后演变成逼中央就范的工具和阴谋攫取党和军队的领导权的突破口。
(二)野心膨胀、不听指挥,将个人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张国焘的思想动摇并与中央的分歧,严重影响红军的行军作战。徐向前、陈昌浩贯彻中央的北上战略,在松潘前线指挥红军与胡宗南部作战,却受制于张国焘。他表面上讲“既然大家都赞成,我自然不能独持异议”[6]236,实际上却是处处掣肘。因为红四方面军担纲松潘战役的主力,张国焘恰恰瞅准了这一点,在具体行动上就通过操控红四方面军来达到个人目的。这种恶劣的做法无异于用“绑架”红四方面军的手段来要挟中央。具体就是借口两军会师以后的“统一组织”和“统一指挥”问题没有解决,拖延部队迅速北上实施松潘战役计划。
7月1日,张国焘打着“反对右倾”的幌子致电中央“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4]81。7月6日,中革军委专门电告张国焘,要求担任战役的右路军、中路军迅速行动,实现作战目的。此时张国焘却向代表中央慰问四方面军的李富春等人提出“统一组织问题”,“建议充实总司令部”[2]559。接下来要求中央和中革军委进行人事调整就成为张国焘常打的一张牌。7月9日,受张国焘操控的中共川陕省委致电中央,以“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为理由,提出张国焘设想的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构成,甚至“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4]85。10日,张国焘再次致电中央,提出“我军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反对右倾”,“特别要不参差零乱的调动部队”[2]565。
系统中模拟量输入模块为DVP-04AD-S,该模块有4路模拟量输入,其中电压输入信号为0~10 V,电流输入信号为4~20 mA.每一路都可以设置成电压输入或者是电流输入,共有4种模式可以选择,本系统采用电压信号输入模式,并在程序初始化程序里设置好需要使用的模拟量输入模式.如,要把第一路模拟通道设置成模式1(电压输入为-10~+10 V),将OFFSET值设置为0 V,GAIN值设置为2.5 V,其程序如图4所示.
张国焘按兵不动让中央十分担忧,故提醒他:“分路迅速北上原则早经确定,后忽延迟,致无后续部队跟进。”盼望红四方面军“各部真能速调速进,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同时表示:“急盼兄及徐、陈速来集中指挥。”[2]566但是,中央的真诚和期望并不能打动张国焘。因为张国焘所谓的“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表面上看是要求在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扩充四方面军干部,实质是要达到由他来担任红军最高统帅的目的。18日,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也提出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恩来任参谋长。要求中央政治局“示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权力[2]583。迫于这样的情况,7月18日,中革军委发出通知,由朱德任军委主席兼红军总司令,由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军队[2]585。
至此,张国焘向党中央摊牌,公开拒绝北上并把南下付诸行动。
由于张国焘的再三延误,导致国民党胡宗南部在松潘完成集结,薛岳部跟进,红军最终丧失了攻占松潘的有利时机,陷入了极大的危险之中。此时,红军主力分为两部分,分别在松潘县西的毛尔盖地区和马尔康县卓克基以南地区。而国民党军队已从岷江以东地区蜂拥压来,北上只能走险象环生的松潘草地一条路了。针对这种情况,8月1日,红军总部拟定了《夏岷洮战役计划》,将分布于卓克基和毛尔盖的红军分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中央鉴于张国焘的消极态度,8月15日,发电报提醒他“不论从敌情、地形、气候、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时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右路军及一方面军全部,应即日开始出动,万不宜再事迁延,致误大计”,强调“目前应专力北上”[2]626。8月29日至31日,徐向前、陈昌浩指挥右路军过草地后出奇制胜取得包座战役胜利,打开了红军北上另一通道,获得了跳出国民党重围和北上抗日的新转机。看到张国焘率左路军仍滞留在马尔康,徐向前、陈昌浩、毛泽东做出部署:等左路军抵达后,用两支部队佯攻南坪和文县,“集中主力从武都、西固、岷州间打出,必能争取伟大胜利”。然而张国焘对中央的决定置若罔闻,9月2日、3日他通过徐向前、陈昌浩转告中央,以葛曲河涨水无法渡河为由,不但拒绝北上,还公然决定从4日晨开始,“分三天全部赶回阿坝”。并且抱怨“再北进,不但时机已失,恐亦多阻碍”。提出“拟乘势诱敌北进,右路军即乘胜回击松潘敌,左路备粮后亦向松潘进”[7]561。
(三)另立“中央”、制造分裂,给党的事业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张国焘的上述行为给党中央和红军造成极大的被动。8日,徐向前、陈昌浩发电报给张国焘,指出延误北上时间“令人痛心”,表明不赞同南下态度:“我们意见以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速来北进为上策,右路南去南进为下策。”[2]665同日,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徐向前、陈昌浩联合电告张国焘,“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须要我们慎重而又迅速地考虑与决定”南下问题。告诫“如果左路军向南行动,则前途将极端不利”,并详细分析了具体原因[8]364-365。张国焘对中央的期望和规劝仍然不理不睬,他发电报给詹才芳,让他“飞令”中央纵队政委蔡树藩,“将所率人员移到马尔康待命”,“将其扣留”[2]669。命令右路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要“一、三军暂停留向罗达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2]666。9月9日,张国焘正式向其部属抛出“拟改道南打”的决定后又电告中央和徐向前、陈昌浩,肆意枉猜北上之不便。针对中央指出的南下是逃跑,会陷入敌人重围的判断,粉饰其为“真正进攻,决不会做瓮中之鳖”。他一面向中央虚伪地表示“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弟忠诚为党、为革命,自信不会胡说”[2]673-674。另一面却授意刊发题为《争取南下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的文章,颠倒黑白为自己南下错误辩解,旁敲侧击攻击党中央:“一切夸大敌人力量,不相信自己力量,丧失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企图逃跑到偏僻地区的倾向,是我们目前主要的危险,必须开展无情的斗争。”[2]787
林育英对此如何答复,没有见到相关资料。但是在6月6日,张国焘主动取消“第二中央”,结束了这场自导自演的闹剧。张国焘也觉得难以向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交代,所以,他在当日作报告时继续欺骗大家:“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在这样之决定下,我们同时要反对一切企图曲解这决定的分子。”[4]534
党中央的北上,让张国焘恼羞成怒,他拒不接受中央批评,采取了推卸责任和责难中央的恶劣态度。他于12日发电报质问中央:一是红三军撤去班佑等地警戒,乘夜秘密开走,胡宗南部反攻班佑,造成30团“与敌遭遇,团长负伤,伤亡百余。贯彻战略方针岂应如此”。二是责难中央“未留一人在徐、陈处,用意安在?”三是妄猜和指责红三军北上后,有人向胡宗南告密,将军事行动泄露于敌。四是标榜自己“自信能以革命利益为前提,虽至最严重关头,只需事实上能团结对敌,无不乐从”。将红军分离的原因归罪于中央,“诸兄不图领导全部红军,竞率一部秘密出走,其何以对国际和诸先烈”[4]148。更为卑鄙的是他亲拟电报发给林彪、聂荣臻、彭德怀等军事干部,挑拨军队与党中央的关系:“一、三军团单独东出,将成无止境的逃跑,将来真会悔之无及。”北上“战士无冬衣,不拖死也会冻死。不图以战胜敌人为先决条件,只想转移较好地区,自欺欺人论真会断送一、三军的”。煽动他们“望速归来受徐、陈指挥”[9]。
南下途中张国焘还策划着更大的阴谋。1935年10月5日,他在卓木碉召开会议,做出了另立“第二中央”的“组织决议”:“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甫应撤销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并下令通缉。杨尚昆、叶剑英应免职查办。”宣告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军事委员会”及“常务委员”[4]230。至此,他与中央已不是在战略方针上存在分歧的问题了,而是另起炉灶,在组织上公开分裂党和红军。此后,张国焘便以自封的“中革军委主席”的名义,指挥红四方面军。
近年来,政府已经习惯把宏观政策当成了结构改革的手段,这不仅造成结构改革没有实质性进展,同时加剧了市场波动,尤其是波动又造成实体经济的破坏。我们经过改革开放40年,很多改革确实到了深水区,不容易改。相比之下,宏观调控就相对容易执行和见效,毕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可控性非常高,中央政府也容易管。但是作为经济的最终掌控者,政府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而不是将引导经济发展的责任推给货币和财政政策。对此,政府应大力加强行政体制改革,深化精简放权,深入放管服改革,提供有力政策支持。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宽松的社会环境。同时,进一步减轻企业税费负担,细化和增加抵扣条目,让实体经济轻装上阵,放开手脚参与竞争。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称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2]844
为提高医院的综合竞争实力,使用有效的成本精细化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对医院来说,财务的核心业务之一就包括成本管理,成本核算的过程控制是由成本精细化管理来实现的。这样做既提高了管理能效,又降低了医院的财务风险。同时,将相关的资源进行整合,达到控制成本的目的,做到科学化管理。
(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该电报中张国焘公然以“中央”正统自居,向中共中央发号施令。上述极端错误行径完成了他由拥兵自重、反对中央北上方针,到另立“第二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再到公开篡夺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权的“三步跳”,将他思想动摇、不守纪律、破坏中央权威和反对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推向极端。
二、党带领红军为维护中央权威与集中统一领导开展的坚决斗争
(一)及时召开俄界会议,分析揭露张国焘错误的本质
对面形复杂的佛像进行测量,图9(a)为CCD相机获取的受佛像面形调制的一帧正交光栅像;图9(b)为正交光栅像的频谱.可以看出4 mm光栅间距产生频谱卷积项较小,不影响正交光栅基频的提取.利用上面所讲的方法对图9(a)进行傅里叶分析,分别得到水平和竖直方向的调制度,计算其调制度比MR,然后查找调制度比和高度映射表就可以恢复物体的三维面形,恢复结果如图9(c),实验证明,该方法可以快速且准确地恢复物体三维面形,与传统的调制度测量轮廓术相比,该方法只需采集一帧图像就可恢复物体三维面形,还可有效避免物体表面不均匀反射率对测量的影响,实现对物体实时快速测量.
根据Morisky-Green(MG)[3]标准设计慢性荨麻疹患者治疗依从性调查问卷,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在过去的三个月内,是否有按照医嘱进行规律服药;②在过去的三个月中是否有自行更改服药剂量的行为;③当病情改善时是否自行停药;④ 当不在家时,是否曾经停药。每个问题按照总是、有时、偶尔、从不分别赋予1到4分,将四个问题的得分相加既为总分,规定总分≥12分者为依从性较好。
9月12日,党中央在甘肃俄界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分析讨论与张国焘的路线分歧;二是确定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未来部署。
对于张国焘的问题,张闻天在俄界会议上的发言一语切中要害: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中央的路线,一条是右倾的军阀主义——张国焘主义”。张国焘“已经形成了反对中央的路线”,他反对中央的原因是惧怕敌人,“在红军建设上,不要党的领导,红军变成个人统治的军队。对干部的培养,是要拥护他个人”[2]681。毛泽东在俄界会议的总结中讲到:“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能发展到叛变革命。”[4]152会议最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指出张国焘对日渐高涨的反日的民族革命运动和红军长征取得的胜利估计不足,对在抗日前线的西北创建新的根据地丧失信心。思想动摇导致了分裂党和红军罪恶行为的产生。他“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对于党的中央,采取了绝对不可容许的态度。他对于中央的耐心地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的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组织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前面任意破坏中央的威信”[2]683-684。
尽管张国焘错误严重,中央仍以最大的诚意挽救张国焘,希望他迷途知返,所以,俄界会议的决议只发至中央委员。9月14日,中央再次对张国焘错误进行了批评教育:“一、四方面军目前行动不一致,而且发生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总政委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调令与电令。总政委对于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该负绝对的责任。”“张总政委不得中央的同意,私自把部队向对于红军极端危险的方向(阿坝及大小金川)调走,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而没有战略出路的罪恶行动。”解决的办法“只有总政委放弃自己的错误立场,坚决执行中央的路线时,才说得上内部的团结与一致”。再次诚恳强调为了中国革命利益,“要求张总政委立即取消南下的决心及命令,服从中央电令,具体部署左路军与4军、30军之继续北进”[4]155。
张国焘另立“第二中央”后,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毛泽东通过朱德转告张国焘:解决党内的争论,“组织上不可逾越轨道,致自弃于党”[10]。指出成立“第二中央”严重错误,重申红四方面军必须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张闻天告诫张国焘“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绝非革命之利”。希望他“自动取消”,“使四方面军进入正轨”。鉴于张国焘坚持错误,拒不悔改,1月22日中央政治局做决定:“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党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党中央除去电命令张国焘同志立刻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弃一切反党的倾向外,特决定在中央委员会内公布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俄界决定。”[2]853
以上斗争,虽然没能制止住张国焘的南下和另立“第二中央”,却也让党中央占据道义握有真理,维护了自身的威信,有利于未来的斗争。
(二)共产国际及林育英为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所起的特殊作用
在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进行斗争的艰难时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回国,他在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上发挥了特殊作用。此时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始终将毛泽东视为中共及军队的领袖,甚至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周和生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贺词中称:“我们对共产国际中有像季米特洛夫、台尔曼、毛泽东、拉科西和市川正一这样的英勇旗手而感到骄傲。”[11]王明在发言中列举“出色的党内领袖和国家人才”时,将毛泽东列为第一,而张国焘排在毛泽东、项英、周恩来之后,名列第四[11]179-180。1936年1月,王明与国民政府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商谈国共合作事宜,说到“具体条件要同毛泽东和朱德去商谈”[11]79。可见,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了共产国际的一致认可。
林育英回国后,12月18日,张国焘就给林育英写信,歪曲实事指责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为“右倾机会主义”,将红军北上行动说成是“逃跑”,要求“尽力反毛周路线”,并要陕北苏区及红军接受他的领导[2]845,幻想取得中共驻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他的支持。12月22日,林育英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电告张国焘,“第一,党内争论,目前不应弄得太尖锐,因为目前的问题是一致反对敌人,党可有争论,对外则应一致”;第二,因为中国各种情况复杂“中共中央势难全部顾及”,因此可以在地方上组织中共中央地方局,“有的直属中央,有的可由驻莫中共代表团代管,此或为目前使全党统一的一种方法”,表明了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党内的团结的态度。但是张国焘不甘心自己的野心遭遇挫折,他继续挑拨林育英与中央的关系。1936年1月20日,他电询林育英:“是否允许你来电自由?为何不将国际决议直告?我们一切都经党中央同意,假冒党中央或政府机关名义发表重要文件,此间有公开否认之权。为党的统一和一致对外,望告陕北同志,自动取消中央名义,党内争论请国际解决。”[2]852张国焘的执迷不悟致使中央1月22日做出决定,对其进行严厉批评,并得到了林育英的支持。24日,林育英回电表明态度: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
12月5日,张国焘竟然用所谓“党团中央”名义发电报给彭德怀、毛泽东: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7]584
这份电报宣告了中共中央正确的政治路线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反观张国焘的政治路线就是错误的;中央红军长征是胜利了,反观张国焘的南下就是失败。得到共产国际支持,党中央在政治上就完全掌握了斗争中的主动权。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他回电继续指责和贬低中央:“国际赞扬我党和万里长征的胜利,自是鼓舞中国革命同志最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谁也不想抹杀这个,但是否因此就不去学得教训?”“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还荒谬地认为:“党中央此时最好能在白区,但不知条件允许否?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2]856-857张国焘寻找理由为自己的错误和罪行辩解,为保全他的“第二中央”或由他来主政党中央,可谓机关算尽。
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在党和军队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为统一全党全军的认识,中共中央于9月10日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首次公开了中央与张国焘的分歧,并说明了北上的正确性。“我们无论如何不应该再退回原路,再去翻雪山,走草地,到群众完全逃跑的少数民族地区。”“只有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中央反对南下,主张北上,为红军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号召红四方面军“应该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造川陕甘新苏区去”[7]569。为了避免红四方面军南下造成更大的损失,中央政治局宣布“以后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同志指挥之”,因张国焘“不能实行政治委员之责任,违背中央战略方针,中央为贯澈[彻]自己之决定,特直接指令前敌指挥员(党员)及其政委,并责成实现之”[2]667。严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表现了中央的权威不容动摇。
(三)张国焘被迫取消“第二中央”,宣告夺权阴谋失败
党中央的坚决斗争和共产国际的鲜明态度,使张国焘及其“第二中央”陷入政治被动。但是张国焘仍然无视中央的权威,拒不接受中央的统一领导。鉴于此,为了团结争取张国焘最终北上,党中央从贯彻党的大政方针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大局出发,通过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向张国焘及四方面军做出指示,重点说服四方面军北上。
1月28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询问共产国际有关在我主力红军一致对外的战略方针和指示[2]859。2月14日,林育英、张闻天做出回答:“国际指示都是原则上的。”关于战略方针,斯大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如能一过岷江,一过长江,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陕甘,为在北方建立广大根据地,为使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打成一片(体),为使红军成为真正的抗日先遣队,为与苏联红军联合,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为提高红军技术条件,这一方针自是上策”[7]585-586。而上述的战略构想,正是长期以来中央的想法并为之努力。5月25日,基于红二、四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时局,林育英与中央其他领导发来电报,向他们通报了西北形势,说明中央红军西征向陕甘宁发展,策应二、四方面军,“猛力发展苏区,渐次接近外蒙。外蒙与苏联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国际盼望红军靠近外蒙、新疆”。要求二、四方面军“宜趁此十分有利时机与有利气候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8]533。
此时的张国焘虽然有所收敛,但并未改正对抗中央决定、破坏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错误。为了窥探共产国际对他的态度,5月30日,他以个人名义再次致电林育英:
(甲)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现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发展情况如何,此间北进时党和政权应用何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乙)我们赞成此间对一方面军取协商关系,对北方局取横的关系,原则上争论由国际或七次大会解决。[4]526
中央掌握了张国焘确要“调右路军南下”的意图,迫于时局的紧迫,毛泽东、张闻天等于9月9日召开紧急会议,做出了立即北上的正确决定。10日,党中央率红三军来到甘肃俄界与先期抵达的红一军会合。
可见,张国焘取消“第二中央”,并非真心改正错误,拥护中央并与中央保持一致,而是南下另立中央彻底失败后的权宜之计,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
三、北上途中围绕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继续斗争
(一)党中央与红二方面军形成合力,促成张国焘接受北上
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造成人数锐减,被四川军阀及蒋介石嫡系部队赶出了成都平原西部的边缘地带,只能退却到川康边地区,“南下”战略宣告彻底失败。这种形势验证了中央判断完全正确,“南下不能到四川去,南下只能至西藏、西康,南下只能是挨饿,白白地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断路”[4]146。
1936年2月24日,林育英、张闻天向张国焘诚恳地提出四方面军的战略方针:一是“第一步向川北;二步向陕甘”,这一方针自是上策。二是“二、四方面军现在地巩固的向前发展,粉碎围剿”。三是“四方面军南渡大渡河与金沙江,与二、六军取得近距离会合,甚至转向云贵滇发展”[4]371-372。此时红二、六军团已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踏上长征之旅,摆在张国焘面前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北上了。
红四方面军准备北上,张国焘最担心四方面军指战员对他南下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生怕四方面军广大将士识破了他的真面目而影响他在四方面军中的地位。所以,他不断地制造谣言,为南下寻找“正确”的依据,将其破坏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谋权分裂的罪责推诿于中央,从而得出了“我们此次的北上,是在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以后,我们主动的向北发展,这当然不能与他们的向北逃跑同日而语的”[4]398。同时又对质疑和批评意见蛮横打压:“现在有些同志只是准备在革命高潮时工作,在现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下便发生许多错误的偏向。有的在清谈起来,在议论南下对不对,北上是否向毛、周、张、博投降等等。同志们要清楚,有了政权和军队而在领导红军的党,在今天的环境下,批评是受到相当限制的,因为自由批评只有涣散我们自己,这种现象我们是要坚决反对的。”[4]399-400
1936年4月以后,红四方面军明确了北上意图,其战略任务,一是迎接二、六军团的到来,实现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的会师。二是占领西康省北部的道孚、炉霍、甘孜等地,为北上甘青做准备。四方面军的北上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既然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即将会师,四方面军准备北上,中央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团结张国焘:“现在已没有政治上与战略上的分歧……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4]520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做准备。
In order to have better insight into the operation of the proposed MOSFET structure, the physics based compact analytical model of the surface potential and threshold voltage has been presented in this section.
花奴打了电话后,小虫被罚了款后放了。从派出所出来,小虫不知道玉敏在等他,带一帮乡党去大排档喝酒,喝到半夜才回来。小虫喝高了,满嘴酒气,舌头像短了一截,对玉敏说,我……不会……放过她的。光脚不怕穿鞋的,不把钻戒要回来,老子决不罢休!玉敏看他醉醺醺的样子,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小虫,一股温暖在心头荡漾。
由图5和图6可知,微波作用时间和微波功率对脱水量影响显著,而物料量的变化对脱水量影响不显著。物料量的增减对于时间和微波功率对脱水量的影响趋势没有显著影响,但可以看出,在低功率条件下,物料量少时脱水量要略高于物料量多的情况。而在高功率的条件下,物料量越大,脱水量越高。
1936年6月,红二、六军团长征到达甘孜地区,实现与四方面军的会师。军团领导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了解到了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真相后,与朱德、刘伯承坚定地站在一起拥护中央。四方面军中的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人在事实面前深刻认识到南下的错误与危害,成为执行中央北上方针的坚定拥护者。
中央对二、六军团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极为振奋:“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的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与苏联外蒙打成一片。”[4]569。7月5日,奉中革军委的命令,红二、六军团组成红二方面军。7月10日,任弼时再次致电中央,说明他到甘孜后才得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的争论问题”。鉴于二、四方面军北上的事实做出判断,“现在陕北和川康边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为着不放松目前全国极有利局势,使我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我深切感到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建议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至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2]1081。这份电报充分表明任弼时及二方面军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维护中央权威的鲜明态度。8月初,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南部发动了岷洮西固战役。12日,中央依据在西北地区与张学良的东北军已达成停战抗日的局面,对二、四方面军做出统一部署,正是为了完成相关战略计划,故有了打通苏联、宁夏战役计划、三军大会师、西路军渡河西征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
(1)念珠菌感染[21]:口腔念珠菌感染首选制霉菌素局部涂抹加碳酸氢钠漱口水漱口,疗效欠佳时选用口服氟康唑100~200 mg/d,共7~14 d。对于食道念珠菌感染选用氟康唑100~400 mg/d,口服,不能耐受口服者静脉注射氟康唑100~400 mg/d进行治疗,疗程为14~21d;或者伊曲康唑200 mg,1次/d,或伏立康唑 200 mg,2 次/d,口服,共 14~21 d。 对于合并口腔真菌感染的患者应尽快进行HAART,可在抗真菌感染的同时进行HAART。
(二)张国焘不顾大局,借口“西进”拒绝服从中央命令
一、四方面军虽然携手北上,但是,张国焘并没有从思想深处纠正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对中央在陕甘宁建立根据地、开赴抗日前线的正确方针仍持有怀疑。甚至担心到了陕北与中央会合,就会失去对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权。这种思想和心态导致了他在北上期间仍然延续错误,不顾大局,甚至将个人的私心掺杂到有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决策与行动中来。
中央北上战略设计中,“打通国际路线”是重要的环节,具体就是“以有力一部出夏河攻击河州”[12]104-107,威胁青海,牵制马步芳在甘、凉、肃的军队,用两个方面军渡河占领宁夏,从内蒙古方向打通国际路线。而张国焘却在8月22日致电中央,提出由红四方面军经永靖西渡黄河,独自进军青海、甘西,完成接通新疆和国际路线的计划[13]。这实质上就是他主张的“西进”错误方针的翻版,其打乱了中央的统一部署。23日,中央质询张国焘:“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兄等认为有充分之把握否?”[4]573-574受此影响中央通盘考虑,在25日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发去绝密电,对没有红四方面军直接参与的情况下仅靠红一方面军攻取宁夏的前景做出判断,提出要取得战略的胜利就需要苏联和外蒙古的援助。说明:“以一方面军约15000人攻宁夏,其余担任保卫苏区,十二月开始渡河。因宁夏地形狭小,不利回旋,城寨甚多,守备坚固,估计红军本身只能占领其一部分,主要的多数的城寨,非借助从外蒙古来之飞机与炮兵没有攻克之把握。如机炮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确实到达宁夏附近,则可及时占领宁夏。”[4]659从毛泽东等人的疑虑和担忧不难看出,张国焘擅自主张单独进军青海,给红军作战并实现战略目标带来新的困难和风险。
8月30日,中央一如既往地发布了红军的行动方针,要求四方面军“占领临潭、岷县、漳县、渭源、武山、通渭地区,尽可能取得岷、武、通三城”,由此巩固红军与东北军形成的联盟,控制西兰大道,保卫新开辟的苏区。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县召开会议,朱德、陈昌浩、傅钟等西北局成员坚定支持中央北上方针,迫使张国焘放弃了西进的意见,拟定了《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但是张国焘对此极为不满,9月20日,他赶到漳县的红四方面军前线指挥部,推销他的西进方案。21日,电告朱德表明他“坚决反对静会战役计划”,要求他们速来漳县面商[2]1141,并利用职权令所有未经他“签字的电报一定不准发出”[2]1142。22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明确反对中央部署的宁夏战役,主张四方面军由兰州西永靖、循化一带渡过黄河,转移到凉州、永登一带[2]1144-1145。更严重的是张国焘还违背中央的统一领导,擅自发布西进命令,使按中央部署已展开行动的红四方面军或者原地待命,或者为西进做准备,形成了四方面军已做西进的具体事实[4]661。
坚决执行中央决定的红军总司令朱德,对张国焘这种阳奉阴违、不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的做法十分不满,同时也为四方面军西进可能产生的后果深感忧虑。当日,朱德与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电告徐向前、周纯全并转张国焘,表明自己的态度,“国焘同志电悉,不胜诧异。为打通国际路线与全国红军大会合,似宜经静、会北进。忽闻兄等不加同意,深为可虑”;“会、静战役各方均表赞同,陕北与二方面军也在用全力策应,希勿自失良机,党国幸甚”[4]714、720。同时朱德还致电党中央说明严峻形势,并表明自己坚决拥护中央决定的态度:“西北局决议通过之静、会战役计划正在执行,现又发生少数同志不同意见,拟根本推翻这一原案。”“我是坚决遵守这一原案,如将此原案推翻,我不能负此责任。”[2]1143
都什么时候,她还有心思跟我插科打诨?就在我俩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对话后,我恍然大悟,这丑丫头定是被天南星妖施了迷魂术,为他所用。怪不得之前看她忙前忙后,喝了鸡血般四处张罗着仙茅族人寻宝。
事实果然如朱德所料,9月23日,中共西北局在漳县盐井镇召开会议。张国焘一方面为自己擅自改变岷州会议决定百般辩解,另一方面又大谈西进的好处,蛮横地推翻了原来的决定,使红四方面军掉头折返,准备从永靖、循化一线渡黄河西进青海。26日,张国焘两次致电中央为他的错误行径狡辩,告诉中央“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
由于四方面军突然改变行动方向,造成在陇南一带与一、四方面军协同作战的红二方面军失去左侧屏障,在北上会师途中陷入被动,付出不该发生的人员伤亡代价。张国焘却将责任踢给中央:“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此计划实施,免西渡、北进两失时机。”[12]119
(三)党中央摆脱“西进”干扰,维护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
眼看即将到来的胜利有可能会因为张国焘的错误而丧失,中共中央立即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
阻止胡宗南部西进,确保红军东面的安全。毛泽东于1936年9月24日、25日两次致电彭德怀、聂荣臻,要求他们加派有力部队南下,阻止胡宗南部西进,填补守卫因四方面军离开造成的西兰公路的空虚。
团结各方面的红军力量拥护中央的决定。漳县会议后,任弼时、贺龙于9月25日向张国焘等四方面军领导表明态度:“关于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与红军发展前途有损。”提醒张国焘:“以四方面军目前位置再北移转会宁地区,尚不致丧失时机。我们请求你们暂以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以[待]陕北之决定。”[2]1146基于红二、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形成的密切关系,中央也十分重视红二方面军的作用,9月26日,指示任弼进、贺龙、刘伯承“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对红四方面军危害诸多,“切妨碍宁夏计划”[4]725。当张国焘同意按照中央的部署行动后,红二方面军立即致电:“建议中央即按各方情况与需要,迅速做出三个方面军目前行动计划的决定。”并说明“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2]1153。
展望未来,人类大踏步的迈进新的年代,无论是民用、建筑、医疗、通信还是高端的航空领域,材料科学都面临着技术突破和重大产业的发展机遇,以一系列新兴材料为代表的科技创新也异常活跃,由此可见材料科学的发展前程似锦,值得我们的期待。
对张国焘开展耐心细致说服工作,指出西进带来的危害。当中央得知张国焘西进想法并付诸行动后,向他仔细分析北上与西进的利弊。用毛泽东的话说,“此次我们总算仁至义尽”[2]1147。中央先后指出:“若西进到甘西,则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8]597“我一、四两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一、四两方面军合力北进,则二方面军可在外翼制敌。一、四两方面军分开,二方面军北上,则外翼无力,将使三个方面军均处于偏狭地区,敌凭黄河封锁,将来发展困难。”说明四方面军单独西进,还会造成敌人的可乘之机[8]598-599。建议四方面军执行原定的《通庄静会战役计划》,“争取与一方面军会合为目的”[2]1132-1133。明确要求:“四方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号召各军首长“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12]121-122。
张国焘西进中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中央的领导,9月26日,主动向中央表示:“关于统一领导,万分重要。在一致执行国际路线和艰苦斗争的今日,不应再有分歧。因此我们提议:请洛甫等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2]1150-1151张国焘做出这样的表态实属无奈,但是他毕竟在形式上接受了中央的领导,中止了错误行为,有利于树立党中央的权威和对全党全军的集中统一领导。27日,党中央明确告诉“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从宁夏、兰州间渡河夺取宁夏、甘西”。强调“一、二、四方面[军]首长应领导全体指战员发扬民族与阶级的英勇精神,一致团结于国际与中央路线之下,[为]完成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斗争”[2]1156。在分析敌情后指出,“四方面军现有充分时间进入隆、静、会、定大道,敌无阻止可能”[4]728。
降解培养结束后,加入表面活性剂的摇瓶内溶液较未加入表面活性剂的溶液更加浑浊。试验结果见图2,可见加入表面活性剂明显促进菌株的生长和对柴油的降解效果。加入表面活性剂的摇瓶内柴油的生物降解率比未加入表面活性剂的高22.3%。
由于受自然环境和气象条件的影响,加上中央不懈斗争和四方面军绝大多数将士的抵制,张国焘的渡河计划落空。27日,张国焘终于致电中央和红二方面军表明:“决仍照原计划东出会宁,会合一方面军为目的,部队即出动,先头26日到界石铺决不再改变。”[4]729同时对部队的行动做出调整。28日,张国焘再向中央表示“已遵照党中央指示停止西渡转向北进”[14],毛泽东立即向彭德怀、聂荣臻部署策应四方面军北上的任务。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胜利会师。这标志着张国焘最终放弃了“西进”的错误计划,也宣告了历时一年多的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
四、党中央和红军战胜张国焘错误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一)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防范来自内部的动摇和背叛
来自内部的动摇和背叛是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面临的最大危险,也是党的事业面临的最大危险。轻则危害党员、党的组织的纯洁性,重则造成党的事业的挫折和失败,对此绝不能放松警惕、姑息养奸。长征中的这场来自内部的政治危机,给党和红军造成极大危害和损失,导致红四方面军放弃北上而南下,出现了短期内党和红军的分裂,让长征付出了更多的代价,甚至险些葬送了红军和中国革命。受张国焘错误的干扰,红一方面军最终仅有不足8000人北上;红四方面军原本8万余人,错误南下的后果就是损兵折将,在会宁会师时仅剩4万余人。当三军会师在即,张国焘又发生动摇,违背中央制定的北上会师计划而擅自决定西进,造成三军协同作战被破坏和红二方面军丧失侧翼掩护而蒙受损失。党中央和红军为应对和处理张国焘的错误还耗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失去了难得的机遇,给革命事业带来意想不到的损失,教训十分沉痛。总结这场斗争,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党的组织和革命队伍最容易从内部被攻破,这是革命和建设都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二)坚定信念、统一思想是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基石
党中央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提供了战胜党内危机的成功范式。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根本是要做到坚定信念,形成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关键是防止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张国焘的错误根源在于思想认识的偏差,即对革命前途产生消极和悲观而导致误判时局,故看不清革命的有利条件而一味夸大困难。这就难免导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膨胀,做出一系列危害党和人民军队的事情。所以俄界会议通过的决定指出:张国焘一再主张“西进”和“南下”,是其“丧失了在抗日前线的中国西北部创造新苏区的信心”,是夸大敌人力量和轻视自己力量的表现。再就是张国焘“不相信共产党领导是使红军成为不能战胜的铁的红军的主要条件”,不注意“保障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2]683-684。可见,坚定革命必胜信念,将思想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上来,实事求是辩证客观地判断时局,这是全党做到维护中央权威、实现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基础。
(三)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成熟政党的标志
党中央战胜张国焘错误的过程,也是党和红军自觉维护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不断走向成熟的过程。红四方面军是党教育培养起来的一支光荣部队,骁勇善战是其特点。但是张国焘的错误严重破坏了红四方面军的政治生活和政治生态。在与张国焘错误的坚决斗争中,红一方面军以弱小的力量北上并在极短的时间内到达陕甘地区,会合陕甘红军发动东征、西征,巩固了陕甘革命根据地并将之扩大成为陕甘宁根据地,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创建了大本营。而张国焘带四方面军南下,虽然在初期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但自百丈关之战后连遭挫折。正是成败的正反对比和血的教训,使红军广大将士认识到了中央路线是正确的,紧跟中央才能取得胜利,自觉接受中央的领导,维护中央的权威逐渐成为全军的共识。所以,长征后期在与张国焘错误的斗争中,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军队的领袖地位,党中央、中革军委实现了对红军各主力的直接领导和统一指挥,中央的威信在全军空前高涨,这是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的原则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最后完成,也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标志。
参考文献:
[1]程中原.转折关头:张闻天在1935—1943[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49.
[2]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红军长征·文献[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5.
[3]佟静.历史转折中的张闻天[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00:50.
[4]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
[5]金一南.苦难辉煌[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399.
[6]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7]甘肃省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三军大会师:下册[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
[8]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9]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3[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256.
[10]郝成铭,朱永光.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74-75.
[1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7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80.
[1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13]中共甘肃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甘肃历史:第1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274.
[14]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5[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16:189.
中图分类号:D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19)06-018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俄界会议到‘七七’事变——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决策与经验研究”(12XDJ006)。
作者简介:吴晓军(1962—),男,山西山阴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巨虹;校对:暮雪
标签:中央论文; 张国焘论文; 党中央论文; 面军论文; 红军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党史论文;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1949年)论文; 《甘肃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俄界会议到‘七七’事变——党应对重大风险的决策与经验研究”(12XDJ006)论文; 中共甘肃省委党校(甘肃行政学院)社会与生态文明教研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