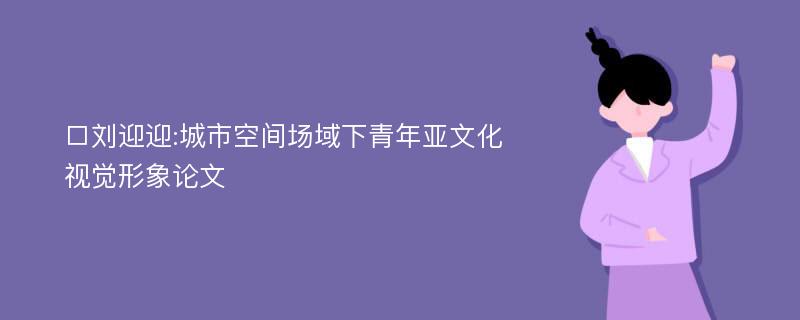
摘 要:1960年代后期空间理论兴起,福柯将注意力聚焦于社会生活的“外部空间”,列斐伏尔反对仅仅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演变的“容器”、平台,时间的霸权地位受到空间的制约。视觉技术、视觉文化的出现为青年亚文化视觉形象的空间化生产提供了技术装备和理论支持。从大众媒体的“他建”到青年亚文化群体“自建”,新媒介的出现、以及视觉技术的进步为青年亚文化视觉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空间、场地以及技术装置。从现实空间到赛博空间,青年视觉形象的构建打破时间和空间的桎梏,青年视觉形象跃然于生活、媒介、舆论之中,成为视觉文化、亚文化研究热点。然而,媒介和受众对青年视觉形象的被动性建构,限制了青年视觉形象的完整呈现。
关键词:青年亚文化;空间理论;视觉文化;视觉形象
19世纪60年代以来,学界经历了引人注目的“空间转向”,学者们开始刮目相待人文生活中的空间性,把以前给予时间和历史,给予社会关系和社会的青睐,纷纷转移到空间上来[1]。列斐伏尔的“三元辩证法”使其在空间理论之中的影响无人比肩,他认为我们关注的空间是物质、精神、社会三种,这三种空间在统一的批判理论出现之前,都是以孤立的零散的知识形式存在。而空间的知识理应将物质的空间、精神的空间和社会的空间联结起来,这样才能使主体游刃有余于各个空间之间。空间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对青年亚文化的重新解读,尤其在“读图时代”备受推崇的现在。福柯认为,空间在当今成为理论关注的对象,并不是新鲜事情,因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甚之更甚[2]。今天,社会处在高度视觉化的媒介时代,视觉技术的进步、新媒介的发展为青年亚文化建构视觉形象打下了基础。同时媒介和商品为青年提供了丰富的符号资源,青年利用符号的同时,改变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固有关系,加入了自己对符号的理解。一种新的符号资源诞生,这种符号为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支持:从衣着、装饰、妆容、动作,到音乐、涂鸦、极限运动等,亚文化群体正逐渐走入大众的视野,并且在现实城市空间以及网络空间中尽情展示自己。
一、青年亚文化的空间转向
1.权力、知识与话语建构:福柯微观政治空间
空间的命运就是在历史中反复地震荡[3],不断地被意义的机缘所填充[4]。青年亚文化在空间中生产,同时又生产着空间知识。青年亚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同空间一样在时代的发展中反复震荡。中世纪的空间生产主要涉及天国和人间,空间被完全神圣化,空间的自由被束之高阁。真正使空间得以无限放大且使统治阶级更关注空间的面积、范围的是伽利略对未知空间的探索。此时的空间神圣化标志被打破,转而引向无限自由的开垦。资本主义正是凭借对空间的探索,对铁路、航海、航线、公路运输等空间的全面部署,将物质的空间当作权力运作的工具。19世纪以来,空间的性质再一次发生了变化,以往作为“自然空间”的资本主义权力的表征手段开始渐渐模糊,转而清晰呈现的是对作为知识、权力的社会空间的探索。这时的空间研究的注意点并不是说完全转移到福柯所展现的权力的政治空间,也没有彻底被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所覆盖,恰好对于空间的那些研究不单单关注其作为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的研究,转而在建筑、村落、道路、城市、国家以及世界地理学的研究当中或多或少地开始呈现出对空间的另类研究,开始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5],此时,“世界空间乃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其中创造出来的场域”[6]。
“建筑自18世纪末叶以来,逐渐被列入到人口问题、健康与都市问题之中。……(它)变成了为达成经济-政治目标所使用的空间部署的问题”[7],空间在福柯这里表现为权力运作的工具。城市规划、公共设施、环境保护、商业以及私人建筑,已在福柯单向的微观政治中展现建筑话语的空间化建构。北京故宫作为中国最大的历史宫殿遗址,在清朝统治时期,对于公众来讲是权力的象征,但是建筑本身并不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建筑本身也不具有话语权,建筑是空间中的物质实物,权力透过空间来运作,空间才具备一定的政治向度,空间体现的是对人的管制和控制。福柯列举了圆形监狱的例子,监狱被建筑家们设计为圆形敞视建筑,在这样一个建筑当中,牢房中的个体处于外围监视中心的监视范围之内。由于监狱的特殊设定,每一个监狱单间的个体想象着自己被执法人员监视的场景,在个体内心设下一道心理空间屏障,同时这道心理空间屏障反过来约束个体的行为。执法者仅仅需要在特定的圆形敞视监狱的中心位置上,就可监视整个监狱单间里的犯人。福柯的这种对人的约束的空间权力的阐述,在当代社会建筑中的体现尤为显著。酒吧、网咖、街道、角落、胡同、大院、办公区域等等建筑的实体内,公众会自然地将自身作为饮酒作乐者、上网者、闲逛者、售卖者、大爷大妈、白领等标签个体,并且在单向度的空间内进行各自的空间性生产。这是因为,办公场所被用来规定工作人员进行工作上的操作,这与公司的利益密切相关,公司的领导自然扮演了监视者的角色,而普通员工则扮演了牢房中个体的角色;从办公场所脱离出来进入城市的街道、道路之中的社会个体,其角色变为普通市民,遵守红绿灯规则过马路、不随地扔垃圾以保护环境,按照道路交通秩序进行自己的身份转移,此刻,每个公众个体本身既是“监狱里的犯人”,同时又是“监狱的执法者”。街道、街区相对于封闭场所是一个更大的敞视型监狱,或许它的形状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作为空间权力部署的一部分,胡同、街道、街区、公路等城市规划是一个空间与权力关系的新面向;个体从开放的无限空间的交通轨道中脱离出来,进入封闭的、隐私的个人房间之中,在这个隐私的房间中,看似卸下了作为员工角色、市民角色,却进入一个更大的被伦理道德所支配的角色扮演中—家人、邻里街坊、亲朋好友、熟人等。“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空间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8]。从员工到普通市民,再回到个体自身,空间的层级不断发生变化、时间发生变化、个体所扮演的角色发生变化,但是作为权力的空间的本质却没有改变,依然处在各个统治阶级的监控当中。空间(而非建筑)是特定权力形式的运作工具[9],执法的权力可以将社区的滋事者从社区空间中排除,限制在另一空间当中,如警局或者监狱。
福柯的微观政治空间,不仅仅涉及权力和知识在空间的运作,还涉及话语权的建构。网络流行语话语研究是新媒体时代学者们研究的一个新面向,他们从对主流文化话语权的研究,转向对青年亚文化在空间中话语权的研究,更确切地说,是转向虚拟青年亚文化的空间话语权。表情包、GIF动图、短视频等等视觉符号社交媒体文本表现形式,无一不是青年亚文化传播其特定形式文化的表征方式。青年亚文化的话语权建构不仅仅在赛博空间通过视觉符号表征,“港大民主墙表情包”事件将虚拟亚文化从线上带到线下,青年学者们通过表情包的娱乐方式,表达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同时也体现了青年亚文化话语权的建构对主流文化推波助澜的作用。
2.经济、政治与社会关系:列斐伏尔三元辩证空间
相比于福柯,列斐伏尔认为:“福柯沉醉于个人主义之中因而无法探讨‘集体主义',福柯经常使用飘忽不定的空间隐喻来掩盖社会空间的政治具体性,福柯权力/知识概念的多面性没有关注‘服务于权力的知识与拒绝承认权力的知识之间的对抗'”[10]。列斐伏尔反对仅仅将空间看作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者平台,他认为空间是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并随历史的演变而重新解构和转化。青年亚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演变,同样也在空间的重新解构和转化中不断产生出新的社会关系。它包含以下三层含义:第一,“任何一个‘社会存在'渴望或者宣称变成了现实,但如果没有生产出自己的空间,就是一个古怪的实体”[11]。跑酷、蹦极、滑翔等极限运动,在普通大众看来是相对危险的、有较大难度的一类运动。人们常常将“胆儿大、不怕死”的标签强加给极限运动青年亚文化群体,并且认为“活着多好”“极限运动太危险”。在国内,素质教育和普遍应试考试机制下,父母对孩子的兴趣培养极为重视。钢琴、书法、芭蕾、民族舞、轮滑、乐高拼搭等等符合主流审美的兴趣班是父母为孩子的首要选择,父母认为这与孩子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对升学以及情操的陶冶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杂技、cosplay、蹦极、跑酷、嘻哈说唱、街舞、冲浪、攀岩、自行车越野、水橇滑水、溯溪、冲浪等传统青年亚文化活动形式,以及电竞游戏、直播、表情包恶搞等新近出现的虚拟青年亚文化形式,在大多数公众看来是一个或者一群“古怪的实体”。公众无法全盘接受此类青年亚文化视觉形象,但是在微博热搜上,却经常看到此类短视频出现。微博热搜是以网友对跑酷、蹦极等亚文化活动感兴趣程度为基础,视频发布者通过买热搜的方式或者网友评论、点赞、转发达到某一热度时,使此类视频出现在热搜榜单。微博、抖音等平台上的极限运动相关视频的分享,在网友那里越来越能接受,越来越能将之视为如打篮球、踢足球、跳舞等之类的传统兴趣爱好。此时,位于移动赛博空间里的社会个体不再是“古怪的实体”,而是网友热衷的青年文化的代言人。第二,有关社会空间的阐释,列斐伏尔解释说,“社会空间之所以晦暗不明,是因为它长期被双重幻象,即透明幻象和现实幻象所遮盖。透明幻象过分强调话语和书写在认识空间中的作用,将社会空间看作由语言、符号构成的单纯精神现象。现实幻象是一种物质拜物教,喜欢物质现实,把一切都当作物质的、真实的,认为社会空间是由物质构成的不变的‘水桶'、容器、背景”[12]。在爱德华·索亚看来,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是将物质空间和精神空间包含在内,同时又超越两种空间的存在。物质空间是真实的空间,道路、高楼、山川、河流以及领土、太空等等,这些是统治阶级在伽利略航海之后,更渴望获取与控制的空间。与其说是物质拜物教,不如说是统治阶级对空间作为生产资料的野蛮掠夺。社会空间便是由这些可见可感的水泥石墙、山川林木、社会个体、海洋太空等等物质组成,社会空间的本质亦被此番“现实幻象”所遮盖。跑酷运动爱好者穿梭在各个房间之中,穿梭在各个高楼之间,穿梭在山川之上,是将自然空间作为青年亚文化创造的实体来使用。同样,杂技表演者脚托青花瓷器、头顶油纸伞、手舞刀剑,甚至利用舞台上的绳索在空中翻转、跳跃,这是自然空间给予的实在的物质本体,青年亚文化群体可以操纵这些自然实体创造青年亚文化。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说,统治阶级通过生产空间巩固统治。
在城市、在街道、在角落,青年亚文化群体利用城市空间来建构属于自己的视觉形象。墙面上的涂鸦,广场上玩轮滑的少年,公共场所开展的cosplay动漫展,青年亚文化群体无时无刻不在利用城市空间展示自己的身体、服饰、妆容、动作等。这些亚文化活动不仅仅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其中一些经过影视化制作人员拍摄、剪辑、上传到网络空间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相同兴趣爱好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在网络上聚集,他们彼此分享自己的动态,形成自己的亚文化圈子,这种网络亚文化圈子不受时间和地点的约束,亚文化青年们因为兴趣爱好的相同而聚集在一起。但是,网络上亚文化群体圈子里的动态,以及圈子内,亚文化群体对于自身视觉形象的建构,仅仅存在于自己的圈子里,很少波及现实生活,或者影响到其他亚文化群体的视觉建构。但是,当某些群体的突出事件,经过发酵,不仅波及人们的现实生活、影响到其他亚文化群体,并且引起其他亚文化群体认同/反对的时候,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在舆论的发酵下,在现实和赛博空间之间转换。由于舆论的强大力量,使得该亚文化群体的突出事件,被毫无遮掩地披露在网络上,引得网民关注、转发、评论等。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2016年“帝吧出征FB—表情包大战”事件,该事件导火线来自国内明星林更新转发并评论台湾明星周子瑜的道歉视频,称其“来不及背稿”,之后引发台湾和大陆网民在Facebook上的表情包大战,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爱国主义情怀。该事件网络上发酵的同时,现实生活对该事件的讨论也是如火如荼,表情包作为一种青年亚文化的表现形式,为当代青年的爱国主义打下了深刻的烙印。
二、技术之变:从读字为主导到读“图”为主导
具体到油气藏勘探对数字化技术的利用,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龚斌指出,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几乎所有数据是间接获得的,不确定性极强,而且干扰数据比较多,数据产生的对象和决策的对象是分离的。通过运用大数据做高精度地质建模、高效油藏数值模拟,通过人工智能等算法,在不断丰富的数据驱动下,实现模型持续更新,这样可以对地下油藏进行精确地描述,由此在充分考虑所有数据及认知的基础上,自动做出最科学、合理地预测和决策。
推荐理由:“莎士比亚戏剧”(音频讲解版)系列图书包含《哈姆莱特》《罗密欧与朱丽叶》《威尼斯商人》《奥瑟罗》《李尔王》《麦克白》。每本书附带讲解音频,采取导读+分章节解读+总结的形式,全方位解读莎翁经典,彻底解决中国读者对莎翁名著“难度”“读不懂”的困惑。讲解者深耕戏剧创作多年,深谙西方戏剧脉络,且音质附带磁性,以轻松幽默,通俗易懂的语言娓娓道来,由浅入深,引人入胜。
过去,我们主要从传统媒体诸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上面获取新闻。对报纸编辑来讲,对文字写作能力的把握、记者写作经验的积累、写作质量的保证,对文字报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影响,此时报纸以文字报道为主。同样,对于受众而言,阅读的质量和理解的偏差,不仅取决于读者本身社会经验的积累,还取决于受众对记者文章的理解程度,即:对新闻报道的理解,对文字的理解。由此可见,“看”字对报纸受众来讲尤为重要;广播媒介不同于报纸、电视媒介,受众只能用耳朵听,肉眼无法观看。此时,播音员朗读文字时的发音、语气、感情等一系列个人因素,都影响到报道是否传达出原本的含义。广播听众主要用耳朵来“听文字”,播音员对文字报道的朗读,或者记者对现场的描述等,就是听众能够“看”到的文字。电视出现的时间要晚于报纸和广播,它从诞生之初就不同于广播、报纸媒介。早期,电视就呈现出一些视觉化优点,比如:电视观众可以在电视屏幕前观看播音员读新闻稿、观看记者从新闻现场拍摄的画面、观看各种各样的视频广告,还可以在电视屏幕上观看纯文字的画面。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进入读图时代,读字仍是重点。此时,媒介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处于严肃、样板、“被建构”状态,并且这种“被建构”表达的不一定是青年原本的形象,而是通过大众媒介的新闻框架和摄影技术、文字技术等描述修饰后的符合新闻伦理的青年形象。此刻,对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更多地停留在传统媒介上面。
三、路径之变:从大众媒体的“他建”到青年亚文化群体“自建”
现今,大众传媒的总体视觉化趋势出现,视觉文化应运而生。“视觉技术和消费社会两个趋势的最佳结合点就是大众传媒,当两者在大众传媒中有效深度融合时,一种有别于历史上任何文化形态的视觉文化便应运而生”[15]。这时,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被把握为图像”遂成为一种普遍的文化取向,可见性成为当代社会和文化中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当代文化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可见性”资源的争夺。“视觉文化是一种追求快感的消费文化,影视、广告、网络视频、摄影、手机自拍等,人们不但大批量地生产图像,而且无所不在地消费图像。视觉消费已经成为人们建构并确认自己身份认同的主要途径”[16]。按照“奇观社会”理论家德波的看法,形象即商品“奇观乃是积累到如此地步的资本,即它已成为形象”[17]。视觉文化的出现为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基础。
随着中国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技术和设备得到普及和推广,中国成为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互联网网民群体和一批世界一流的互联网应用的国家。网络技术的进步和网民数量的增加,推动了视觉技术的发展、视觉工具的研发与改进,催生了诸如数据新闻、图片新闻、VR、360全景、AR、网络直播等一系列新闻报道方式,这些视觉技术在互联网上大放异彩。“由于新技术的采用,越来越多的新的视觉装置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男男男女审视和把握世界最便捷的手段,技术的进步也在改变人们观看的行为及其习性”[14]。由此,大众传媒诸如报纸、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在应对网络信息的初期,略显疲软,更有些遭遇收视滑铁卢、部分报社宣布关闭。而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改变大众获取、发布信息的习性和途径。尤其是“千禧一代”,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使他们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网络上。哈罗德·伊尼斯 (Harold A.Innis)在《传播的偏向》(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中认为:“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因为每一次新媒介的产生,都会带来一整套新的价值评价体系,都是由人类的基本需求所引发的。人类的每一个目标行为通常都渴望得到反馈,并且人类社会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事物之间、系统之间的相互关联,形成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机器、人与虚拟世界的互动关系。这种多元的互动关系是一种必须在互动平台上才能完成的,使彼此之间产生相互作用与变化的表达体验的过程。在新媒介的冲击下,传统媒体不得不想方设法借鉴新媒体,诸如《人民日报》在纸质版相关报道片尾,附上二维码,用户浏览文字信息后,拿起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观看视频。同时新媒介开始蓄力,表情包的普及、H5新闻的应用、VR、AR、360全景等视觉技术的发展,为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提供了场地和技术装置。
再制造是指:对处于寿命周期内的旧机械结构做分解和清洗,将其中的损伤部件进行修复和重新装配,并通过合理有效的试验手段验证,最后使再制造机械结构的性能和可靠性达到或者接近原制造精度的一种技术[1]。
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从现实到赛博空间再到现实,场域之变打破了时间和空间以及亚文化群体圈子之间的界限。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的形成,使得当代青年逐渐成为“被”视觉消费的主体。媒介和商品提供大量符号资源,当代青年用网络符号获取青年话语权,巩固其视觉形象。从新闻机构到自媒体,青年视觉形象传播逐渐从刻板、严肃、被动变得活跃、多样、主动。从他建到自建,新媒介的出现以及视觉技术的进步,为当代青年提供了视觉形象建构的技术装置。从边缘到“主流”,青年亚文化在新媒介平台的传播与主流文化交相辉映。从交相辉映到喧宾夺主,青年亚文化逐渐占据大众心理,抓取大众眼球,主流文化存在缺失风险。如何应对薄积厚发的青年亚文化群体,如何确保主流文化的主体地位,如何使主流文化和亚文化相得益彰,成为当下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
从过去到现在,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介,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从他建到自建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新媒介的出现,以及视觉技术的发展对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显然,纵观当下,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并不仅仅局限在大众传媒的角落里,随着城市空间逐渐被拓展、被打开、被展示,城市空间逐渐成为青年表达自己、表现生活的场地。
老婆没好气地把头又一转:“放屁,你压根儿就没把老婆当人看。”杨力生说:“不,不不,一日夫妻百日恩,老婆就是男人的主心骨,我怎么会拿你不当人看呢!”
四、场域之变:从现实空间时空桎梏到赛博空间畅意遨游
以往,言说和文字一直是西方智型的最高形式,亦是空间知识的精神幻象。主流文化如此,青年亚文化更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变迁,言说和文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当下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已经变得不再那么神圣,反而是图像符号,更确切地说是视觉符号在文本表现中逐渐流行起来。诸如,抖音、腾讯微视、西瓜视频、梨视频、快手等等视频平台在最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可以看出短视频是当下媒体产业的热点所在。当然,单纯视空间为语言符号构成的精神现象在当下是行不通的,尤其是在青年亚文化这里。那是因为,事物本身并没有意义,只有在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历史中才会有其意义,而特定的社会和历史是由人创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和转化。服装、妆容、身体、行为等等是社会个体用来表征文化的方式,本身是作为“现实幻象”的存在,同时生产着“精神幻象”,而此两者在社会中存在,又反过来作用社会。正如第三点,列斐伏尔所提出的三元辩证法,在列斐伏尔本人看来,“我们所关注的领域:第一,物理—自然,宇宙;第二,精神的,包括逻辑抽象与形式抽象;第三,社会的。我们关心的是逻辑—认识论的空间、社会实践的空间,以及感觉所占有的空间,包括想象的产物,如规划与设计、象征、乌托邦等”[13],即空间的实践、空间的再现以及再现的空间。
如今,互联网的普及、移动互联网的发展,为大众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大门,这使得新媒介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传播媒介,尤其是对于那些受众是“千禧一代”的新媒介而言。在这样的时代浪潮下,国人更加开放,对世界的接受度更高,随之一些小众文化出现在大众的视野当中。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见的亚文化群体有很多,比如:嘻哈、街舞、跑酷、cosplay、快闪、涂鸦、轮滑、朋克、雷鬼、电竞、网红等,这些亚文化群体根据自己对事物能指的理解创造属于他们的所指。嘻哈歌手们编排押韵朗朗上口的嘻哈曲风,穿着宽松富有个性的服饰。街舞青年,不同于一般舞台剧演员,街道、广场、胡同甚至任何空间角落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舞台。对于跑酷爱好者来说,高楼、街区、房间等整个城市空间都是他们跳跃、奔跑、竞技的场地。参与快闪的青年爱好者们,他们往往素不相识,在网络赛博空间里因为相同的兴趣话题相遇,他们约定时间、地点在线下进行某种标志性活动,活动结束后立即分散、离开。这种活动一般发生在人员比较聚集的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表达参与者某种信仰和主题。cosplay爱好者们在服饰、妆面、动作、饮食等方面上模仿动漫、游戏等其他影视化作品中的虚拟角色。帝吧出征FB是2016年青年运用亚文化符号资源进行的一次政治化话语权的活动,在这项活动中青年群体自觉在网络集结,他们用表情包表达着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网红,是当下社交媒体网络中炙手可热的流行亚文化,男男女女们靠服装搭配、俊俏脸蛋、美妆分享、拍摄搞笑视频、饮食制作、萌宠分享、游戏竞技等来吸引青年群体参与到其个人形象的建构当中来,同时利用微博、微信等社交新媒体平台维持与受众之间的关系。美妆网红们,比如韩国美妆达人PONY,不定期制作主题类美妆视频,进行美妆教学,来建构自己“美妆大神”的视觉形象;视频搞笑网红们,比如“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papi酱,通过制作幽默搞笑、嘲讽戏谑的视频在社交平台传播,引发热议,从而达到建构自己“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的视觉形象;电竞网红,比如游戏女高手Miss,通过在直播类视频app虎牙来直播绝地求生游戏,以此来建构“游戏第一美女”的视觉形象。
“在任何时期,青少年首先意味着各民族喧闹的和更为引人注目的部分”[18]。青年作为青年亚文化主力军,不仅仅存在城市、媒介和舆论三者单独的空间之中,而且存在于从现实到虚拟空间的文本转换之中。读图时代的来临,使得视觉文化成为当下研究的主要课题,青年在城市、媒介以及舆论中呈现出来的视觉形象,为视觉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实践意义。同样,亚文化的研究,由来已久,从“无赖青年、光头仔、摩登族、朋克、嬉皮士到摇滚的一代、迷惘的一代、垮掉的一代、烂掉的一代……从知青亚文化到摇滚浪潮、涂鸦文化、韩寒现象、黑客、愤青、粉丝、大话文艺、戏仿经典、恶搞文化、耽美、cosplay、御宅族、快闪族,再到网红”,形形色色的青年亚文化存在于城市的胡同里、街道上、墙面上、高楼大厦、公园、广场等等角落,存在于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等新媒体上,存在于各种舆论事件当中,成为当下的热点。
青年亚文化群体在互联网上的圈子,并不是只能该圈子的人可以观看、进入、交流,有时候会出现渗透到主流文化传播渠道中。比如2016年夏天大火的网络综艺节目《中国有嘻哈》,就使得嘻哈文化这个小众文化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并且嘻哈群体们的服饰、妆容、动作和音乐风格成为大众争相模仿的对象。从嘻哈大热来看,青年亚文化大热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青年亚文化时时刻刻存在于大众身边,大众只是缺少契机去认识、了解青年亚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青年亚文化的研究就尤为重要。
五、结语:青年亚文化视觉形象的媒介呈现与认知危机
城市空间场域下青年亚文化视觉形象的呈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于青年亚文化在城市空间中对自身视觉形象的空间化生产,二是在于媒介的议程设置。大众对青年视觉形象的认知有两种途径,从媒体中获取青年视觉形象,或者大众自身对其视觉形象进行理解和传播。从一方面来说,媒体对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存在一定的机制,媒体并不是按着青年原本的视觉形象呈现,而是通过媒介机构的编辑,在符合相关规定、符合某种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制作传播的。媒体从制作和传播青年视觉形象开始,青年视觉形象就已经不是原本的了,经由媒体编码,再传播给大众。大众接收媒体对青年视觉形象的建构,由于受众从电视上接收到的青年视觉形象,和真实的青年视觉形象本身已经存在差异,再加上限制于受众经验和知识水平、理解水平,受众在解码的同时,又建构出一种自身理解的青年视觉形象。从现实到媒介再到受众,青年视觉形象的被动性建构由编码和解码者的经验、理解和知识所限制,无法完整呈现。从另一方面来说,大众自身选择性获取有关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信息,可能在城市空间中看到,可能在媒介上特意关注亚文化圈子,也可能参与到青年亚文化舆论事件当中去。受众对青年视觉形象的顺从式、抵抗式和协商式解读,会为其呈现出多元的青年视觉形象,这种青年视觉形象完全依赖于受众自身的意愿。面对这两种状况,从媒介和受众两个角度研究青年视觉形象在城市空间、媒介和舆论中的建构是十分迫切的。
在当下互联网飞速发展、空间生产极速膨胀、视觉技术突飞猛进、亚文化大肆流行的环境下,中国式的新型青年亚文化的生产与传播阵地开始偏向赛博空间,这一点毋庸置疑。赛博空间流行话语权的部署紧紧把握在青年亚文化手中。青年亚文化网络流行语的空间部署,在于他们利用电竞游戏平台、社交媒体平台、短视频平台等移动终端创造虚拟青年亚文化。他们以图像技术、互联网技术为装备,在承接主流文化的爱国情怀和民族主义的同时,他们整体呈现出传递快乐、健康、时尚、竞争与技术的主流审美观。当下时代中国青年群体的亚文化创造也显示出别样的风景,当任何事件上升到民族高度时,这些新时代的青年群体会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符号,来捍卫国家主权的完整,来彰显自己根深蒂固的爱国主义情怀。由此来看,对赛博空间的掌握,对视觉技术的熟悉,对当下青年亚文化虚拟空间部署的把握,以及对青年亚文化的新型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值得学者深入探究与思考。
推荐理由:本书讨论了社会热点问题和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中的化学基本知识及化学所发挥的作用,并介绍了一些基础化学知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并对其潜在性和危险性做出合理的评判。
参考文献:
[1][2]包亚明.现代性与都市文化理论[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
[3][4][11]汪民安. 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5][6]Lefebvre,Henri.“Space:social product and use value.” Critical sociology:European perspectives 285(1979):295.
[7][9]Wright,Gwendolyn,and Paul Rabinow.“Spatialization of power:A discussion of the work of Michel Foucault.”Skyline 14(1982):13-14.
[8][法]福柯.空间、知识、权力[M].包亚明.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10]Soja,Edward W.,and Vera Chouinard.“Thirdspace:journeys to Los Angeles & other real & imagined places.”Canadian Geographer 43.2(1999):209.
[12]潘可礼.亨利·列斐伏尔的社会空间理论[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13-20.
[13]Lefebvre,Henri,and Donald Nicholson-Smit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Vol. 142. Blackwell:Oxford,1991.
[14]董小玉,严亚. 生产与合谋:当代青年的视觉文本转换[J]. 南京社会科学,2014(10):105-111.
[15][16]周宪.视觉建构、视觉表征与视觉性—视觉文化三个核心概念的考察[J].文学评论,2017(3):17-24.
[17]Debord G. 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trans[J]. Donald Nicholson-Smith. New York:Zone,1995.
[18]埃里克·埃里克森.同一性:青少年与危机[M].孙敏纸,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刘迎迎: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陈晨
标签:空间论文; 青年论文; 视觉论文; 亚文化论文; 形象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2期论文; 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