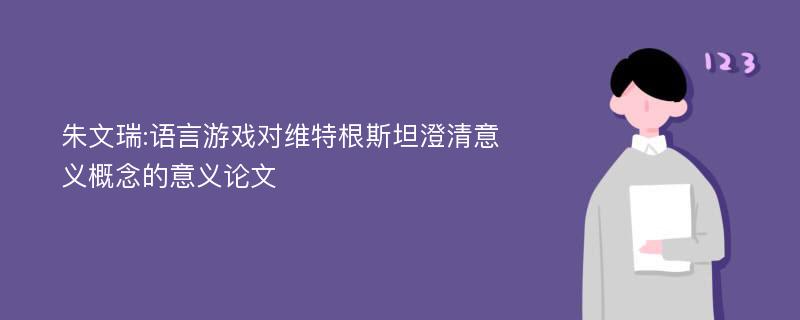
【哲学研究】
摘 要:为澄清哲学上意义概念的多重意义,后期维特根斯坦发展出语言游戏概念。语言游戏一方面为“五”“红”这类基本词汇提供意义支撑,另一方面为澄清“‘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类问题中的“意义”提供用法来源。语言游戏在以形式语言为研究对象的现代逻辑学与以语言本身为研究对象的现代语言学以外为语言与世界的关系问题重开局面,而就其展开的关于意义概念多重意义的论证也为语言哲学提供了切合实际的说理样式。
关键词:语言游戏;语词;意义;语言哲学
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最为人知的概念之一。围绕语言游戏的定义、界限及作用,学界展开过多种多样的争论,这些争论丰富了这一概念的理论生命。近年,李国山从维特根斯坦批判其前期图像论的角度,重新论述了语言游戏的哲学意义[1]。陈嘉映另辟蹊径,将话语层面的语言游戏与语词层面的语义条件对照起来理解[2]。这种理解都为重新解读语言游戏提供了新方向。不过,就语言游戏概念本身而言,它首先有一相当确定的上下文。参照《哲学研究》文本,维特根斯坦更多地将语言游戏同澄清哲学上意义概念的多重意义相联系,这也应是维氏发展语言游戏概念的初衷。
一、“意义”的意义
维特根斯坦哲学前后期分野鲜明。前期维特根斯坦循着弗雷格、罗素一派路数追求一种基于理想语言并以确定性与简单性为旨归的语言哲学研究模式,“后期维特根斯坦彻底改变了他的语言批判策略。此时,他不再像前期那样试图借助严密的逻辑分析方法澄清命题之意义,进而揭示语言、思想与世界的本质,而是将目光转向语言的实际用法”[1]。参照语言的实际用法借以分析哲学概念是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一大特色,而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意义概念则一度聚焦维特根斯坦的分析目光。在1933至1934年间流传出来的《蓝皮书》中,维特根斯坦写到:“什么是一个词的意义?”但就这一问题,维氏转而提示,“首先问‘什么是对意义的解释?’有两点益处。某种意义上,你把‘什么是意义’这个问题带回地面。因为,为了理解‘意义’的意义,你当然也应该理解‘意义的解释’的意义。……研究一番‘意义的解释’这个表达式的语法,将会教给你‘意义’这个词的语法,并帮你祛除那种四处寻找可以称为‘意义’的东西的诱惑”[3]85。而在其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中的“意义即使用”便是这一研究的初步成果,“在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下——尽管不是在所有情况下——可以这样解释‘意义’: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用法”[4]33。
这里给出的无疑是“对意义的解释”。这一解释首先受制于“词的意义”,而非其他通常与意义一词搭配的诸如“生存”“行善”之类。考察之初将目光聚焦于词的意义使得我们对意义一词意义的澄清更具方向性,从而跳脱出那种泛泛而问的“什么是意义”。我们在学习“词”这个词或“意义”这个词之际总是就着“词的意义”这一表达式一道,而非脱开这类表达式直接学习词、意义这类词。按照维特根斯坦提示,为了澄清意义一词的意义,我们须将目光投向我们使用意义一词的一大类情况,而其苦心求索的“使用”即是意义一词多重意义之一种。初看起来,将“意义”解释成“使用”不成道理。学生指着课本上意义一词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们不说“这个词是‘使用’的意思”。参照词典,意义一词的意义是“语言文字或其他信号所表示的内容”[5]1556。唯当跳脱书本,观照生活,我们才能窥见“使用”与“意义”二者之幽微联系。总之,对于意义一词意义的解释一方面须参照其崭露的表达式,另一方面须考察解释活动中对话者的说话方式。
二、语言游戏
在维特根斯坦视野中,“使用”不只系于若干日常语词以期显示生活中使用语词的方式,“使用”的基本着眼点在于澄清意义一词的特定意义。为了引导我们识见澄清意义一词多重意义的方向,维特根斯坦发展出“语言游戏”。语言游戏概念颇富应用前景,然其首先提供的是我们使用某一语词的特定情况。对于使用语词的特定情况的看重提示出语言游戏一方面勾连了说话人与听话人的特定身份与具体处境,另一方面为廓清处在特定身份与处境中的对话者所养成的说话方式提供了更为真切的生活基础。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人物有着形形色色的说话方式,《哲学研究》开篇,维特根斯坦从那类普通人大多参与的日常活动出发,就我们平日买苹果的过程作过一番描述[4]4。这一过程提醒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会提问“五”这个词的意义。唯当特定情况,我们才会提问“五”这个词的意义。然而,唯当将这里的“意义”理解成“使用”,我们的提问才能获得意义,道理在于我们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针对所有语词提问其意义是什么,我们总是在特定情况下就某个词提问其意义。哲学中泛泛而问诸如“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数”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又或“是”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里所谓意义都应首先在“使用”层面上得到理解。一旦如此理解“意义”,我们首先得到的便不再是针对某个词的解释或定义,而是一般情况下使用这个词的语境。总而言之,追问“五”“红”这类词的意义首先意味着追问其使用方式,追问使用方式首先意味着真切描述我们向来使用这类词的语境整体。
循着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动机,描述语境整体首先是为了把我们的目光引向“语词的目的以及语词是怎么起作用的”[4]5,而其更深层目的则是尝试扭转那类只顾聚焦于解释与定义的哲学,毕竟“任何解释总有到头的时候”[4]4。将“语词的意义”这一表达式中的“意义”以“目的”“作用”取代,透露出维特根斯坦独出机杼的思想方式与特具风格的思想旨趣。为了使得对于意义问题的澄清更富系统性,维特根斯坦铸造了语言游戏这一概念界说我们使用语词的语境整体:“我们还可以设想,第2节里使用话语的整个过程是孩子们借以学习母语的诸种游戏之一,我将把这些游戏称为‘语言游戏’;我有时说到某种原始语言,也把它称作语言游戏。”[4]6
前文提示,解释主要参照不同的说话方式与生活形式,而在针对“五”“红”这类词的意义为何的回答中,在一般哲学家著作中,在涉及所举语词的哲学意义层面上,我们则采取一般人从不设想的解释与定义。就哲学上所谓“‘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而论,这一问题至少涉及两重误导:第一,“五”最初并非理所当然是一个词;第二,不是所有词理所当然就能询问其意义是什么。就第一重误导而论,我们唯当指着书本上“五”这个词才会自然而然地询问“这个词怎么读”,又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离开书本,我们不会为“五”冠以“这个词”这一提法。一个不识字的人习用“五”而不自知,他不会将“五”与“这个词”搭配起来,除非他开始识字,因为我们恰恰是在语言游戏中学会“五”这类数词的。就第二重误导而论,我们更不会询问“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例如就“五个苹果”而论,我们有什么理由询问“五”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初学识字的孩子可以询问“这个词怎么读”,我们告知他“这个词读wǔ”。这时他还会询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吗?他会说“是‘五个苹果’的‘五’吗?”,一旦得到肯定回答,孩子自然不会再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维特根斯坦发展语言游戏概念在于引导我们看到我们是如何学会“五”“苹果”这类词的,而在语言游戏中学会这类词意味着我们首先不通过解释与定义学会这类词。维特根斯坦如此思索主要在于澄清意义一词的多重意义。“哲学上的意义概念”[4]4可谓云山雾罩,维氏另辟蹊径,将哲学上“一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类泛泛而问扭转至日常生活中参照某个特定的词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从而揭示我们并不总就所有的词提问意义,而是在特定情况下就特定的词提问。语言游戏概念的作用在于崭露出我们问及意义的那类语词是在我们从小到大学习母语的各类游戏里学会的。我们学会这类词的方式在于参与这些游戏,而非通过解释与定义。
维特根斯坦提示出哲学上的诸多问题恰是由于哲学家混淆了我们借以学习相关语词而开展的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就“‘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而论,这一问题本身的无意义在于我们无法给出适合提出这一问题的语言游戏。在这里,学习“五”这个词并不意味着学到其解释与定义,而是我们在使用之际所作出的诸多行动。我们学到的不是“五”这个词的意义,而是支撑其用法的语言活动。之所以问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将向来问及其他语词的“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类提问方式加诸其身,而指出这个问题的无意义无非是指出对于语言游戏的混淆与相关语词的滥用。通过对学习“五”“红”这类基本词汇的语言活动的追根溯源,维特根斯坦廓清了我们使用“词的意义”这一表达式的本来面目:在一类情况下,尤其是在自然而然地要求某种解释与定义的情况下,我们有意义地问出“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从而得到有意义的回答,这时我们得到意义一词的一重意义;在另一类情况下,在那些被问及语词恰是借由种种语言游戏才能学会而被诱导以“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一方式对其加以提问的情况下,我们不能有意义地问出这一问题,更不能得到像在前一类情况下所能得到的那般有意义回答。据此,我们得到意义一词的另一重意义,即“意义即使用”[4]12。
三、语言游戏中的词
维特根斯坦所谓“使用”首先着眼的是整个话语的使用,而不是某个词的使用。在语言游戏视野下,传统上所谓石头、板石这类“词”已然具有了“话语”“语言”的意味。在这个意义上,追问“使用”首先意味着描述与话语前后相应的活动,而描述与话语前后相应的活动也恰是在描述词的用法。实际上,一旦我们依循维特根斯坦对于话语本身功能的重视而考虑维氏提出的“‘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我们也能要求提问者给出我们平日问及此类问题的语言游戏。就这一问题,我们能给出怎样的语言游戏?难道所能设想的不恰是《哲学研究》开篇描述的买苹果活动吗?在那类活动中,我们并不涉及关乎特定语词意义的提问,甚至不涉及提问这种话语功能。前文提及,在某类语言游戏中,话语功能在于命令;在另一类语言游戏中,话语功能则是报告。但就“提问”这种话语功能而言,我们首当要求的是合乎这一功能的语言游戏。由此,澄清“‘五’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首当设想某类崭露出“提问”这种话语功能的语言游戏,再结合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清理出多种多样的提问类型。在面对这类问题之际,维特根斯坦首先留意的是这类问题何以成为问题,而非急于作出某种回答。
为澄清话语功能与提问类型提供适切可靠的原始生活材料是维特根斯坦发展“语言游戏”更为深刻的用意。究其实际,从事这项工作既不能耽于闭门玄想,亦不能失之过度概括,唯当结合与我们联系更为真切的日常生活才能有所创获。日常生活朝夕万变,其中可资哲学研究的原始素材不可谓不宏富,万千端倪更容信手拈来。生活中,我们倾向于用说话人熟悉的字词来解释他不熟悉的字词,这是一般情况下针对所谓某词的意义而言的稳妥答法。不能设想为了解释一个词,我们反而使用对方不熟悉的词。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所举诸多语言游戏也多考虑到对话者双方的身份、来历以及生活形式、行事方式甚或文化沿革之间的差异,陈嘉映评论更为适切:“生活形式不是指的特殊语境,而是一般情境如文化传统和人类生存的一般环境。”[2]
再如,汉语中的成语“狼心狗肺”(这也是人体词作为目的域概念的例子)。输入空间1是动物“狼”和“狗”,具有“残忍”“贪婪”等特点,输入空间2是人体词“心”和“肺”,都是人体的重要组成器官,表示“人的内心或情感”。经过概念的整合,我们可以发现,人的内心具有了动物的特点。故,若形容一个人“狼心狗肺”,就表明此人“心肠歹毒、残忍贪婪”。
四、语言游戏中词的意义
在给出“语言游戏”的上下文里,维特根斯坦频频提到“话语”“语言”。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涉及的还只是某种先于语词或句子的语言活动。维特根斯坦关注的是尚未被领会为“语词”的“石头”“板石”之类。与此对照,维特根斯坦也对同“语词”共生共荣的“句子”保持警惕:A下了这样一道命令:“d—板石—到那儿”,同时他拿出一个色样给B看,并且在说“到那儿”时,指着建筑工地上的某个地方[4]7。在扩展语言(2)时,维特根斯坦在“d”与“板石”,“板石”与“到那儿”之间嵌入“—”意在提醒这里给出的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而是一道命令。就“句子”及“语词”说来,这一区分着眼的是传统语法层面,G.Baker等因循传统语法仍将其视为“句法建构”则有违维氏初衷[6]62。而就“命令”说来,其与“句子”的区分着眼的是“板石!”这声呼喊的功能及其“起作用的方式”恰是语言游戏为我们崭露的。维特根斯坦给出的是一个完整的语言游戏、一次对于语词的完整使用、一种语言得以起作用的完整方式。在这一完整的语言游戏中,对这样一道命令的理解首先意味着依照命令行事,例如在听到“板石!”之际就把板石搬到指定地点。语言游戏的完整性源自与语言紧密联系的活动,“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4]7,例如上文所提“语言游戏”首先是由“板石!”这一命令以及与之相应依照命令行事的搬运活动构成的。
与“语言中的词”对照,维特根斯坦突出了“语言游戏中的词”。“语言游戏中的词”尚不具备一般意义上的语词要素,“‘板石’这声呼喊是一个句子还是一个词呢?——说是个词,它却与我们通常语言中发音相同的那个词有不同的含义,因为在(2)里它是一声呼喊。但说它是句子,它却不是我们语言中的‘板石’这个省略句”[4]10。这番论证一方面透露出维特根斯坦不得不使用传统上词这一概念来解说语言游戏的窘境,另一方面崭露出语言游戏就展现语词目的与作用而言足够真切。据此,语言游戏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醒我们语词首先不是在句子中,而是在语言游戏中。语词不是句子或语言的组成部分,而是语言游戏的组成部分。在语言游戏中,语词的分类方式不是传统所谓名词、动词、形容词等,而是依据其在语言游戏中的功能来划分,例如语言(2)中的“五块板石!”是命令,而在语言(21)中则是报告[4]12。实际上,维特根斯坦是在新的上下文中重新赋予“词”这个词以新的意义,其初衷在于澄清“词”这个词的多重意义,而这正是直指传统哲学不顾“词”这个词的特定意义而将其不加限定地盲目扩展的过分简单化、格式化倾向。
在一个基本层面上,维特根斯坦关注“五”“红”这类词以及向来用以划分这类词的数词、形容词等词类,这类词是我们用以解释其他语词的基本词汇。我们不是在解释与定义中学习这类词,而是在语言游戏中学会这类词。唯当在解释与定义中学会提问“这个词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才能将这一问题套用到“五”“红”这类基本词汇上。据此,对于这类问题的回答只能是描述我们原本学会这类词的语言游戏,而非期待某类更为基本、更为原始的语词。总之,唯有语言游戏中词的意义才能是词的用法,溢出了语言游戏,词的意义便不再是词的用法,除非我们在新的层面上谈论用法,这一新的“用法”便是维特根斯坦所谓“语法”。谈论“意义”这个词的语法实际上是谈论其在句子中的使用是否有意义,这就更多涉及到语言内部结构,而不只是语言以外的活动。
五、语言游戏的意义
检测发现,各压载舱中底层压载水中存有数量最多的致病菌,且随着水龄的增加其数量变化明显,故在研究中着重观测底层压载水。
移动互联网时代,“场景”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新的客观洞察、新的生活方式无疑成为整合创造商业生态、全面重构商业关系,从而全新定义未来生活的场景源泉。
六、语言游戏与语言哲学
当其发展“意义即使用”这一思想之际,维特根斯坦面对两道鸿沟:一道在“词的意义”与“概念的意义”之间,一道在“语言的意义”与“言语的意义”之间。就前者而论,在面对日常语词之际,围绕规定某一概念的确定内涵而发展起来的意义理论势必难以处理日常语词的语义多样性问题。恰如弗雷格要求的,在进行长程推理之际,必须保证推理链条上的各个环节不能潜入未加定义的东西,即概念不能随着推理的进行而发生意义变迁。概念文字即是弗雷格实践构造形式语言这一基本准则的产物,但日常语言绝非弗雷格意义上的形式语言。非但如此,在弗雷格构造概念文字之初,日常语言以及基于日常语言发展起来的传统语法甚至对其加以蛊惑,一度使其工作误入歧途。据此,我们很容易理解弗雷格对日常语言的基本判断:日常语言是不精确的[6]2。这就迫使我们提出另一问题:日常语言应该用“精确”衡量吗?又或者,我们至少不应仅用向来应用于数学语言或科学语言的相关概念来界说日常语言。那么,我们以何种概念界说日常语言才合适呢?维特根斯坦提示,与所谓“精确”对照,能够界定日常语言的概念恰是“合适”本身。“日常语言满合适的”[4]255,这是后期维特根斯坦对于日常语言的基本看法。维特根斯坦拒绝以基于规定“概念的意义”而发展起来的意义理论不加限定地解说“词的意义”,拒绝以狭窄参照数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建立起来的意义理论解说日常语言。
东营凹陷陡坡带砂砾岩体储层预测技术………………………………………………………………………………亓雪静(2.1)
就“语言的意义”与“言语的意义”而论,现代语言学开山祖索绪尔专门区分了“语言”与“言语”,“概而言之,语言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说的那些话,是依赖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索绪尔区分言语和语言,可以说,前者是就语境坐标来看待语言,后者是就语言的逻辑坐标来看待语言”[8]78-79。索绪尔开创的现代语言学要求某种疏离于传统语言研究的概念构造方式,与语言、言语这对概念相应,索绪尔铸造的施指、所指这对概念即是这一要求的初步实践。在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词是作为施指的音响形式与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例如“马”这个词就是“马”这个音响形式与马这个概念的结合,而非“马”这个声音与马这种动物的结合。作为科学的语言学要求脱离传统形而上学概念方式而获得某种独立性,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代表布龙菲尔德就曾将历史上关于语言的哲学思考所形成的诸多观念斥为“冒牌的常识”[9]1。随着语言学日益明确其研究对象,并由此发展出契合语言科学的概念构造方式,传统形而上学的影响也告式微。
将逻辑学与语言学各自发展史考虑进来,维特根斯坦发展语言游戏概念也就有了浓重的哲学意义。在逻辑学家与语言学家要求祛除各自学科中形而上学蛊惑之际——在逻辑学只将形式语言视为其研究对象,语言学只将语言本身视为其研究对象之际——语言以外的世界以及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必须在思想中重获位置。据此,语言游戏这一概念别具理论生命。一方面,“我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跟语词打交道,或者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用语词来做出行动。这便是由他(维特根斯坦)最早提出并由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加以系统阐述的言语行为理论”[1]。另一方面,参照扎根语言游戏中的基本词汇,我们进到语言的结构与规则层面,旁通语言和世界的关系及语言的意义这两大语言哲学基本问题。语言游戏领着我们认清语言与世界尚未分化之际的一团混沌才是哲学思想的生长土壤,“语言游戏是语言和现实难分彼此的大面积交织”[8]185。混沌并不意味着混乱,交织也多有迹可循,澄清意义概念不妨从语言游戏出发。
参考文献:
[1]李国山.后期维特根斯坦批判形而上学之策略与路径[J].社会科学,2013(11):120-131.
[2]陈嘉映.周边情况——一项维特根斯坦与奥斯汀比较研究[J].现代哲学,2012(2):63-68.
[3]Wittgenstein.Major Works: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M].New York:Harper Perennial Modern Classics,2009.
[4]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陈嘉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5]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6]G Baker,P Hacker.Wittgenstein:Understanding and Meaning,Part II:Exegesis 1-184 [M].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2005.
[7]弗雷格.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M].王 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陈嘉映.简明语言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9]布龙菲尔德.语言论[M].袁家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The Significance of Language-game to Wittgenstein’s Clarifying the Concept“Meaning”
Zhu Wenrui
(College of Philosoph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350,China)
Abstract:To make it clear that the word“meaning”is of various meanings in philosophy,Ludwig Wittgenstein presented the concept language-game in his so-called latter philosophy.The concept language-game affords,on the one hand,support to survey clearly the meanings of such elemental words as“five”,“red”etc.On the other hand,source to clear up the question“what does it mean by the word five?”Frankly speaking,regardless of the modern logic which viewed its object as formal language and the modern linguistics which viewed its object as the language itself,language-game has rebuilt such questions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language and the world,and afforded a proper way to arguments in developing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Wittgenstein given the meanings of the concept“meaning”in his latter philosophy.
Key words:language-game;words;meaning;philosophy of language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9)02-0021-06
DOI:10.13747/j.cnki.bdxyxb.2019.02.004
收稿日期:2018-11-09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性研究(1978—2016)”(TJZX16-003)
作者简介:朱文瑞(1991-),男,安徽庐江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哲学。
(责任编辑 石丽娟)
标签:维特根斯坦论文; 语言论文; 意义论文; 语词论文; 这一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保定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论文; 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代西方哲学思想中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性研究(1978-2016)”(TJZX16-003)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