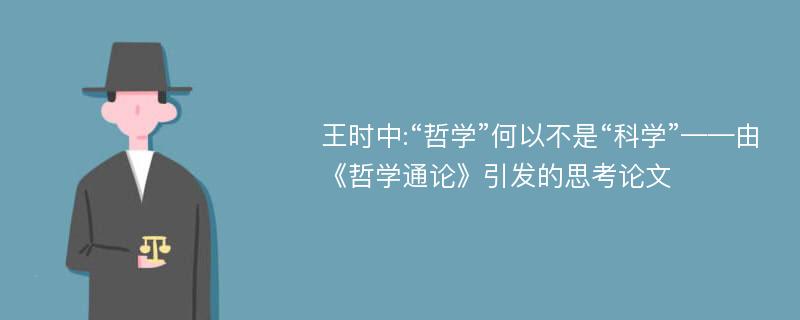
[摘要]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中对“哲学的知识论”的批判路径,厘清了“哲学世界观”与“科学图景”之间的差异;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刻度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揭示了“哲学”与“科学”对“思维”与“存在”之关系的不同态度,彰显了哲学的实践品格。如果沿着“哲学不是科学”的论断,进一步区分哲学层次与科学层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则不仅可以重新激活艾思奇之批判中国“特殊论”的历史意义,而且还显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战斗力,有利于更加坚定地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
[关键词]《哲学通论》;思维;存在;科学;哲学
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而不是一个科学问题。因为近代以来,科学已经从哲学中成功突围并自立门户之后,拥有了自己相对独立的根据地、研究方法与评价体制,除非遇到科学危机,科学家大可不必涉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更无需哲学“搅局”。
但事实上,科学与哲学又是互相需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危机的不可避免:一旦科学危机出现,即旧有的科学理论与新出现的科学事实之间出现了“裂缝”,两者之间既无法匹配又不能相互否认,双方不得不陷入僵局。此时的科学就需要哲学的“救场”,以重新批判科学的前提,限定其疆界、拓展其思路、消解其困局。科学对危机的“手足无措”,反过来揭示了科学的领地与方法论并不是自足的,也正是通过“救场”功能,哲学显示了自己对科学的不可或缺,同时,通过自觉地与科学划界,哲学也经常规整自己的领地,进而得以与科学共生共长,相得益彰。然而,自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的专门化与精细化发展,一般的哲学家既无法跟进科学的具体进程,也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科学与哲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了。但这是否意味着哲学将彻底从科学中退场呢?孙正聿教授在《哲学通论》中另辟蹊径,以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为刻度,深刻地指出:
纵观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得知:“五四”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农民是没有地位的,即便是出现过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作者没有塑造出能完全反映农民社会地位和精神面貌的人物形象,作品中虽然刻画了农民出身的宋江等系列人物,但他们并没有脱离原始的宗法意识形态的藩篱。至于其他作品中歪曲,甚至丑化农民形象的比比皆是。
“科学所提出和探索的问题,是关于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的问题,也就是实现研究成果中的‘思维’与‘存在’在规律层面上的统一,而不是追求研究活动及其研究成果中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与此相反,后者则专门反思各种思想活动及其思想成果中的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具体地研究各种存在的运动规律。这表明,在哲学与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逻辑的鸿沟:科学的逻辑是实现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的逻辑,哲学的逻辑是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的逻辑。哲学的逻辑使科学的逻辑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在哲学的反思中,实现了哲学与科学的逻辑沟通。”①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笔者深以为然,以下仅从哲学世界观与科学图景之间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关系、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出发,对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不是科学”的论点谈一些自己的理解。
一、“哲学世界观”不是“科学图景”:哲学的知识论立场批判
回到孙正聿教授关于“思维与存在之统一的前提性批判”论题,我们可以简单地引申如下:哲学之高于科学的地方,不仅在于哲学为科学提供了领地,划定了边界,引导了科学研究的方向,揭示了人类在理论思维中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将思维的视角拓展到了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处,更重要的是,只有在哲学中才可能真正将实践贯彻到底,而科学只能是以理论的方式展现实践之一维。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在实践着,每天都在实践着,但实践的整体恰恰是科学所力所不逮的领域,也是人们最容易陷入“日用而不知”之困惑的领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哲学不是科学的延伸和变形,而是对科学的反思,也就是对科学的超越”⑥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5页。。
“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表的层次来区分哲学与科学,从而把科学视为关于各种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的知识,而把哲学视为关于整个世界的普遍规律的知识。这样,哲学就成了具有最大的普遍性的科学,就成了全部科学的基础。”②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相比单项指标而言,多指标的综合评价方法能更科学、更全面地反映环境规制影响。因此,通过熵值法测算命令型、激励型和志愿型环境规制3种类型的综合强度以评价环境规制效应[19]。熵值法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这种哲学化的知识论立场,乃是以逻辑简单性为原则,对各门具体科学进行整合与统摄,以期获得一种统一的科学图景。这种知识论立场的理论形式,实际上是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近代自然科学的哲学化。这种推理的根据就是将科学视为以世界的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层次或不同的问题为对象的研究,而哲学则是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的研究,由于“部分之和”即是“整体”,科学研究若能不断前进,久久为功,有朝一日,理论的推演必然能够成功地建构起统一性,此时,“科学图景”就能够取得与“哲学世界观”等量齐观的理论地位。
3)通过对分析法兰盘进行强度的分析和厚度的计算,得出当法兰盘直径为102 mm,安全系数为4时,最优厚度为15 mm,为后续实际工况法兰盘结构设计和优化提供重要的参考.
615 Quality of life of inpatients with lung cancer and related influencing factors
但是,“部分之和”能否、何以构成一个整体,作为整体的科学图景是否就是哲学意义的世界观,这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事实上,近代以来的“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之争、康德关于“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区分、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萨特关于“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的区分等等,都可以视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如果借用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作为参照,我们可以将“部分之和能否构成整体”的问题转化为:如果世界可以理解为一个存在者,而科学是对存在者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与不同阶段的认识,那么,作为存在者的整体,即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是否可以归结为存在者?如果是的话,那么,哲学便只是科学的汇总,根本无须区分开哲学世界观与科学图景;如果不是的话,哲学世界观与科学图景之间的关系,便有待新的理论表征。
设计意图:游戏能充分体现了生物学家创立生物分类学的原旨。这个环节会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兴趣,使课堂迅速呈现出支持、主动、积极的氛围。它的实施既巧妙地不着痕迹地训练了学生的提问能力,又有效地挖掘了他们的分类技能,巩固了学生尝试按照一定的分类依据对生物进行分类的能力。
由此可见,把哲学意义上的世界观看作科学意义上的知识图景,不仅会导致理论上的逻辑悖谬,也会导致实践上的虚无主义。这也反过来证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把握哲学与科学关系的路径陷入了一个“死结”。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路径忽略了以下问题:“(1)哲学是否是具有最大的普遍性和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2)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是否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3)哲学的发展方向是否是哲学的科学化?”基于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一个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出现了:“(4)能否跳出哲学与科学的二元关系,在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理解二者的关系,并从而重新理解哲学?”③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二、哲学没有“根据地”: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刻度
孙正聿教授深刻地指出,就统一性来说,哲学与科学均是人类理论思维的维度,就差异性来说,两者体现的是人类思维的不同维度:
“这真是一次难以想象的经历,”一个男人激动地握着我的手,摇晃着,“不过,你知道的,那些我们说过的话,那个,可不可以……”
“科学集中地表现着思维与存在高度统一的维度,哲学则集中地表现反思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维度,因此,哲学对科学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既不是普遍性对特殊性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特殊性对另一种特殊性的关系,而是以‘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为中介所构成的哲学对科学的反思关系。”①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3页。
正是以“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为刻度,孙正聿教授非常准确地把握到了哲学与科学的差异:科学实现的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即科学是有“根据地”的;而哲学恰恰是反思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是没有科学意义上的“根据地”的。在我看来,这里所谓“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相对于怀疑主义与相对论,哲学需要论证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为科学划边界、打地基、摇旗呐喊;但另一个方面,相对于教条主义与独断论,哲学则激烈地批判这种虚妄的同一性,极力论证“非同一性”的绝对性,因此,这种哲学常常被人们贬为“二元论”与“不可知论”。
我们知道,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曾经这样说过:
殊不知,哲学意义上的不确定的、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恰恰是孙正聿教授所揭示的“反思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之中的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坚持的辩证法,只是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忽视进而遗忘了。
在这里,有人肯定会质疑:相对于科学的无矛盾性与规律性,哲学的这种灵活性却表现出不确定性与随机性:它不仅没有自己的“根据地”,而是四处打“游击战”、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不是显得很不认真、很不严肃吗?正因为这样,很多人对哲学抱一种怀疑、拒斥甚至批判的态度。而“哲学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也是大多数哲学从业者不敢、也不愿意直面回应的问题。
“你们会说,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这种区分是不确定的。我告诉你们:这种区分正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阻止科学变为恶劣的教条,变为某种僵死的凝固不变的东西;但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最坚决果断地同信仰主义和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同哲学唯心主义以及休谟和康德的信徒们的诡辩划清界限。”②《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正是在把握事情的这个“分寸”方面,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也认为自己与列宁的指向相一致:“问题在于防止马克思所建立的科学被变为恶劣的教条;问题在于给马克思所实现的艰巨的批评和整合工作注入活力……。”③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5页。阿尔都塞后来还引证了列宁在《怎么办?》中所采用的“矫枉过正”的思想姿态:如果要把弯曲的棍子掰直,并让它保持是直的,那就必须持久地握紧它,并稍微偏向另一边。“这个简单的比喻,却包含了理论生产与再生产的一整套机制”④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阿尔都塞坦诚,这也正是他进行“理论界划”的基本动机:
“任何哲学都在于划清一条主要的界限,他要用这条界限来抵制那些表述相反倾向的哲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在这种划清界限的行动中(即是说,在哲学实践中)的赌注,就是科学实践,科学性。”⑤陈越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这也意味着,阿尔都塞与列宁一样,从来就不是在单一的科学视角之内思考现实问题,而是在一个“近乎不可能”、“近乎出格”的位置思考。这个位置,恰恰是科学层次所不可理解、不可理喻的。事实上,恰恰是不同于科学的规律性与无矛盾性,作为表征人类活动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所具有的相对的灵活性、机动性,在哲学上才可能真正贯彻实践的观点而不是理论的观点。
由于哲学立场与哲学视角的不同,对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复杂关系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哲学观点。一种最习以为常、貌似圆融的哲学解释就是从知识论出发,认为哲学是关于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思维科学知识的概括与总结。虽然这种观点也指出:“它不是知识的简单相加,而是对其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本质和关系加以高度抽象概括的结果,是关于从整体上把握世界、把握人与世界一般关系的一般知识。”①李秀林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但这种说明依然未脱知识论的底色。这样的理解方式,孙正聿教授称之为“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三、“哲学不是科学”的方法论意义:“中国特殊论”批判
如上所述,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来理解科学与哲学,进而将哲学视为科学的总结与概括,这种观点貌似抬高了哲学、尊崇了哲学,实际上却是贬低了哲学、窒息了哲学。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下进行哲学的思考,不是强调哲学研究的实证性、科学性,便是强调哲学研究的地方性与特殊性,这两种思维方式貌似互相对立,但就其未自觉区分哲学与科学的关系来说,都是对哲学作了片面的理解。
如果以孙正聿教授所提出的“哲学不是科学”的论点来透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古今中西”之争,我们也不难发现,种种主义之争的背后,隐藏的正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之间的对立为例:激进主义以西方文化的特殊性作为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而保守主义则是以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抵制人类文化的普遍性,两者的共同失误就是都没有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个关系的处理,艾思奇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中对闭关自守的“特殊论”的批判进入到我们的理论视野。
一般来说,“国情”是指一个国家在地理环境、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也特指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基本情况和特点。但从近代以来“国情”一词的使用来看,“国情论”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拒绝者的角色,这些论者固然并不否定外国事物的先进性,但由于担心既得利益的受损,总喜欢以不合“国情”的特殊性为由,将外国的先进事物包括当时的马克思主义也拒之门外。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理论伎俩早就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反弹。
艾思奇所针对的是当时流行的一种观念,即以中国的国情与国外的差异,来反对接受一些优秀的文明成果。这种闭关自守主义的理由不外乎是:中国是农业国家,欧美是工业国家;中国是精神文明国家,而欧美是物质文明国家;中国是以孔子立教,外国却以基督立教等等。这种观念的形式虽然变化多端,但在艾思奇看来,就内容来说,不外是这样的:
9月初,著名葡萄酒讲师朱利安——中文说得最溜的法国人,收到了来自葡萄酒大师协会的邮件——自己MW的盲品的考试顺利通过了!这就意味着,他离“葡萄酒大师”只差最后的“论文”(Research Paper)。但不知道为什么,他并没有想象中那样欣喜若狂。
“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特殊的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中国自己的道路是完全在一般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之外的。”①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4-75页。
“从满清时代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开始,经过‘五四’时代的保存国粹论,大革命时代的国情论,一直到现在叶青的‘把握特殊性’的所谓‘理论’,无论它外表上怎样变化,那猴子的尾巴是一贯地带在身上的。”②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4页。
这种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的观念貌似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不可以轻易驳倒,因而具有极大的迷惑性。在哲学上持这种观点的代表就是叶青。但在艾思奇看来,这种“特殊论”与“国情论”并非新鲜玩意儿:
但从内容上批驳叶青的“国情论”易,在学理上驳倒“国情论”的理论根据却难。因为“国情论”的哲学根据乃是以特殊性对抗普遍性,如果仅仅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视为一个理论认知层次上的问题,那么,特殊性始终是理论思维的抽象性所无法统摄的异质性存在,而普遍性也只是人类思维在某种特殊情况之下对特殊性的理论把握,两者各自能言之成理,坚持任何一方的论者也必定能够找到反对另一方论点的坚实论据。一种调和的方式就是认为,两者是相反相成,不可分割的: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特殊性,反对普遍性,是必要且正当的;在另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坚持普遍性,反对特殊性,也是必要且正当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将无同”。但在这种理解方式中,根本就找不到判断的标准。如果固守在这种理论思维中,哲学便必然陷入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我们看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绝非仅仅是一个理论内部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层次区分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如果说在理论内部,思维是通过概念来把握对象的,但是实践生活中对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处理,就决不可在理论思维的延长线中来展开。因为将普遍性的理论运用于实践时,还将继续面对一个如何将理论具体化以切合于特殊实践境况的实践观念或实践智慧的思想任务。这就意味着,在从理论观念到实践观念或者实践智慧的具体化现实化过程中,我们面对两种不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前一种是观念性的理论内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后一种则是理论的普遍性与实践的特殊性之间的关系。”③王南湜:《中国哲学精神重建之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95页。
根据以上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不是科学”的论断,在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时,我们可以区分两种不同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一种是哲学层次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一种是科学层次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并依此可以区分两者不同类型的特殊性:一种是哲学层次上导向普遍性的特殊性,一种是科学层次上无法被普遍性所统摄的特殊性。在前一种关系中,普遍性高于特殊性,“丢开了一般的规律,就无所谓特殊性的把握,连那要被特殊化的东西本身也丢了,哪里还能有什么特殊化这件事呢?”①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7页。而后一种关系则相反,特殊性无法完全被普遍性所统摄。叶青所鼓吹的“中国特殊论”与“国情论”的哲学根据,正是“在口头上窃取了特殊性的名词,故意把这一点夸大,抹煞了一般,结果在实际上正是反对正确地来把握中国的特殊性,反对真正把握特殊性的科学方法。”②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6页。
在这里,我们可以引入“罗素悖论”作为类比来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众所周知,所谓的“罗素悖论”,是假设集合S是由一切不属于自身的集合所组成,即“S={x|x∉ x}”。现在的问题是:“S包含于S”是否成立?如果回答是,则不符合x∉S,那么,S不包含于S;如果回答不是,则符合x∉S,即S包含于S。罗素悖论还可以转化为一些更为通俗的描述,如理发师悖论、说谎者悖论、书目悖论等等。如果说罗素悖论使得康托尔创立的集合论产生了危机,推动数学家关注数学基础问题的研究,那么,将哲学视为知识论意义上的科学图景,混淆了“存在者”与“存在”,这种混同所带来的理论后果便是“人类的生存”成为一个问题,在这种知识论的世界观之下,人成为了无家的浪子、无底的棋盘与无根的浮萍。
数学全息定义和非全息定义的教学目标是不同的.按照布鲁姆的认知水平的层次(“记忆”、“理解”、“运用”、“分析”、“评价”、“创造”)来分类.数学定义的教学目标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初级目标、中级目标、高级目标.本文将“运用”分为三个层次,即“很简单的运用”(相当于直接运用或直接套公式)、“简单运用”(包括逆用、变用等)、“灵活运用”.全息定义教学的初级目标是达到“记忆”、“理解”、“很简单的运用”等层次的要求,中级目标是在达到初级目标的基础上还应达到“简单运用”、“分析”层次的要求,高级目标是在达到初级目标和中级目标的基础上还应达到“灵活运用”、“评价”、“创造”层次的要求.
这两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及其关系,表征的正是哲学与科学的差异:在哲学上,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特殊性只有在导向普遍性的关联之中,才能存在;普遍性当然也只能表现在特殊性之中。但在科学上,理论思维的抽象功能可以通过语言符号的普遍性来扬弃、克服多元的特殊性,虽然这种特殊性貌似是坚固的、异质的,似乎是顽固不化的,实际上则是可以被认知所归类的、整合的。叶青所鼓吹的中国的“特殊性”与“国情论”,不过是在认知的层次上对中国的历史、民族、人口与地理环境等因素的特殊性的鼓吹,而不是在哲学层次上来考察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与中国的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艾思奇据此可以激烈地批判叶青的“中国特殊论”“这种狡猾无耻的伎俩的秘密,是在于把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现状当作当然的国情,在于保持这种旧的国情。”③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77页。
根据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不是科学”的论断,我们所获得的方法论是,决不可混淆哲学层次上的普遍性—特殊性关系与科学层次上的普遍性—特殊性关系。而这一点,恰恰是叶青所拒绝承认的,因此,艾思奇才进一步明确声称:
“正因为要把握特殊,所以我们就尤其要了解一般,坚持一般规律,正因为我们要求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因为我们要具体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到中国的现实的特殊条件上来,所以我们就尤其要站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④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8页。
“匚,受物之器,象形,凡匚之属皆从匚,读若方”(《说文·匚部》)。 “方,併船也,象两舟省,总头形。凡方之属皆从方。”(《说文·方部》)
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坚持的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发现的关于社会发展的基本的科学规律,承认它有一般的指导的作用,但同时也一刻也没有忘记,这些规律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中间,因为客观条件的差异,有着各种特殊的表现形式。马克思所反对的,只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只是借“把握特殊性”为名来拒绝科学规律,拒绝中国社会的科学的合理的研究,也就是拒绝进步思想的应用。而叶青所谓的把握特殊的认识中国的方法,它实际上的目的只是在于把人们的眼光束缚在保持落后的奴隶的旧中国“特殊”范围之内,使人们不能根据科学的规律,来看出中国的向上发展的前途,看出真正自由解放的道路。
1.1.2 培养细胞 人乳腺癌细胞系MDA-MB-468购买自上海舜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培养于含有10%胎牛血清和1%青链霉素的DMEM培养基中,细胞在37℃、5%CO 2环境下培养。
基于此,艾思奇才真正清晰地揭示了“中国特殊论”的实质:
“为什么他们又要主张‘国情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拒绝外来的思想文化呢?原来他们所拒绝的,只是能帮助中国得到进步和自由的外来的思想文化,他们所主张的‘国情论’,是封建主义者所需要的‘国情论’,他们所讲的‘特殊性’,是民族失败主义者所需要的‘特殊性’,……那正是他们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传统的继承与发展!”⑤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及其他》,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80页。
事实上,哲学与科学的区分,哲学层次与科学层次上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是真正把握当代哲学的主题,回应现时代课题的“起手式”。如果基于以上所区分的理论层次与实践层次、事实与价值层次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来考察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围绕“古今中西”关系所展开的种种争论,我们发现,艾思奇所处时代的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共同失误,是都没有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而现在所流行的“普世价值论”与“中国特殊论”也不过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翻版形式而已:“中国特殊论”是以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来抵制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与一般性,而“普世价值论”则是将西方国家的特殊性当作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两者的错误之处同样是没有处理好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与此相类似的一种所谓“新保守主义”思潮,即主张一种“变革的历史连续性”,认为只有通过传统文化的中介,任何外来的文化才可能被“吸附”在中国社会的母体上。这种思潮因此主张,需要在改革过程中建立某种“过渡性机制”,以之作为新、旧制度之间的“中介”和“杠杆”,并成为嫁接外来制度的“内源性基础”。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中国特殊论”的现代变形。
从这个意义说,如何处理好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既是哲学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也是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现实问题。艾思奇写作该文的1939年,正是日本侵华,举国上下狼奔豕突,在思想上迷离失所的时候。该文发表虽然距今已近八十年,但依然具有振聋发聩的意义。正如毛泽东曾经指出的: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20页。在这一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体现了这一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辩证法。如果未能区分事实与价值、哲学与科学两个层次的辩证法,那么,在理论研究中必然导致思维混乱,在实际生活中也会带来消极后果。在这一意义上,艾思奇对以叶青为代表的“中国特殊性”的批判,与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不是科学”的论断,在思想进路上是一脉相承的。
如上所论,我们首先从哲学世界观与科学图景的差异入手,沿着孙正聿教授对“哲学的知识论”的批判路径,借助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分,揭示了将哲学视为“存在者”之“总体”所必然陷入的悖谬。然后,根据孙正聿教授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刻度对哲学与科学的区分,揭示了哲学层次上对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的区分:相对于科学对思维与存在之同一性的坚守,哲学却具有相对的灵活机动性;相对于教条主义与独断论对同一性的垄断或者独裁,哲学则需要批判这种同一性基础,坚持非同一性。这就进一步证明了孙正聿教授的观点,即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绝非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关系,而是根源于对思维与存在之间关系的不同层次的理解,这就将实践的维度引入到两者的关系之中。也正是由于实践维度的引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关系的处理,才可能获得全新的解决。最后,我们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入手,区分了哲学层次的普遍性—特殊性与科学层次上的普遍性—特殊性,进而将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不是科学”论断的方法论意义拓展到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种种主义之争,特别是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中,以艾思奇对叶青的“国情论”与“特殊论”的批评为视角,重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现实相结合的必要性与正当性这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的问题,显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战斗力。
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展开,我们可以发现,孙正聿教授关于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独到理解,不仅具有深远的哲学内涵,而且还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正如他在《哲学通论》中明确指出的:“哲学对科学,不是总结、概括、升华和转化的关系,而是一种反思的关系。”②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哲学所反思的正是科学所不会主动予以反思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如果说在关于思维与存在之“不自觉的与无条件的同一”的科学的层次,哲学是“无家可归”的“丧家之犬”,那么,在反思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层次上,哲学却是“四海为家”的“世界公民”。③孙正聿:《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5页。这种观点既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也极大地解放了哲学。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处理古今中西问题确立了可能的“定向标”与方法论指导。从这个意义说,孙正聿教授的《哲学通论》不仅为我们扫清了思想的迷雾,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重新规整哲学与科学关系的新的思想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开拓,对于深受近代以来唯科学主义之害的现代人来说,其意义无论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短期政策创新方略:在继续维持现有住房调控政策不变基础上,确保房价稳定和住房金融稳定、安全,满足生存型、刚需型、改善型住房消费对金融支持的需求,抑制奢侈型、投机型住房投资对金融秩序的扰乱,为构建新时代上海市住房金融中长期长效机制赢得时间、创造条件,有效减缓新时代上海市住房风险指数上行幅度。
[中图分类号]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1-0049-06
收稿日期:2018-07-26
作者简介:王时中(1978—),男,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8YJA720014)与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3182035)资助。
(责任编辑:周文升)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论文; 特殊性论文; 普遍性论文; 关系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1919年~)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论文;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8YJA7200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基金项目(项目编号:63182035)资助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