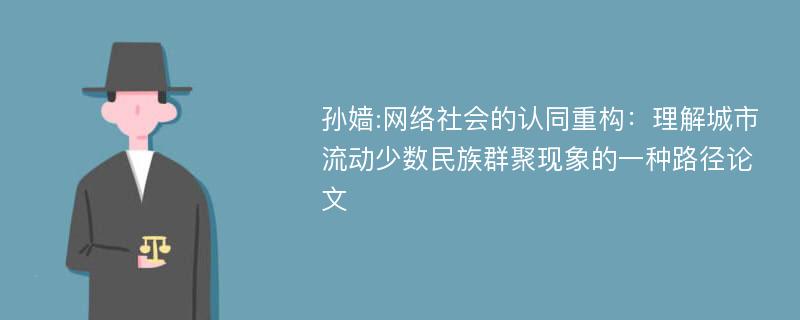
摘 要:边疆少数民族流入内地城市是中国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内在要求。他们通常以群体性方式嵌入城市产业链,并逐渐依托网络信息技术实现内部联络与群体建构,而不再单纯以实体聚居社区为主要聚集形态。这种新的群聚形态不仅建构于城乡二元分隔及其适应性需求之上,更生发于网络社会流动空间对群体成员的选择性接纳与包容,以及网络内外形成的不对等权利关系。面对这一复杂的环境,相对处于弱势的流动群体更倾向于通过重构新的“认同”以实现群体凝聚。这种不同以往的新认同具有自保性、脆弱性和裂变性特征。
关键词:认同重构;流动空间;网络社会;流动少数民族群聚
引言
伴随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发展,人口跨区域流动现象越来越普遍,其中从农牧业流入工业、商贸及相关服务业是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这些流动群体受户籍制度限制,大多并未获得流入地居民身份,却间歇性留居多年,成为事实上的常住居民。但由于他们始终保持着原居地的制度性身份和社会关系,因此往返两地流动居住成为这一群体的重要特征。这种流动居住虽出于个体自主选择,但往往体现出群体性特征。因为他们在流入地通常以各种形式的群聚形态存在,有的形成聚居社区,如著名的北京“河南村”[1]“浙江村”[2][3][4]等就是此类典型代表。而少数民族流动群体因其社会文化方面表现出的鲜明差异,使其在流入地形成的群聚现象通常带有识别度较高的族群特征,并让他人认为其更容易形成族群性的封闭群体,比如“新疆村”通常理解为维吾尔族聚集的区域[5]。随着城市建设的推进,很多原来以地名冠称的外来人群聚集地已经被重新规划,所谓的“村”大多已不复存在,但“村”这种有形空间的消失是否意味着以地域或民族为纽带的认同和群聚现象随之减少呢?
从学界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答案是否定的。从一些城市新近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少数民族聚集现象来看,其规模更大,群聚性更强。这些少数民族通常以群体形式嵌入城市经济产业链的某一环节,彼此依托现代通信网络实现实时沟通与协作,形成紧密相连的族群共同体,但却未必一定呈现集中居住的社区形态。相对于以往“村”的有形共同体,这是一种流动的无形共同体,并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而如何理解这种新的群聚性特征及以此动员的群体性行动,是当前城市化和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认识和把握少数民族流动群体行为逻辑的关键点。
本文通过总结梳理前人对这一现象的诸多讨论,认为以往对流动少数民族在城市群聚现象的讨论大多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框架,认为是其源自乡村的原生性特征遗留的影响,城乡差别和民族差别在流动情境中的叠加增强了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群体的复杂性,但导致这一现象背后的关键因素“流动”本身却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流动通常仅被作为背景,但事实上正是流动将原本具有城乡、民族差异的不同群体或个体卷入同一网络,使其具备了重构社会关系和组织的可能。因此,结合城市少数民族群体流动行为的新特征,笔者认为有必要另辟蹊径,引入网络社会理论,从流动空间角度对当下此类群聚现象进行分析,希望这一探索能够增进我们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讨论。
一、城乡二元分析框架及其局限
作为全国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学界对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的讨论依然主要基于城乡二元结构框架,将少数民族人口向城市的聚集理解为现代化过程的一种体现。[6]这种观点认为,结构性的“推力与拉力”使人们不得不趋于流动,但从原居地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保有其原生特征,当他们进入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后需要各方面的调整以适应和对接新的工作与生活。鲜明的差异性使他们往往被视为与众不同的群体,磨合过程的多方博弈与相互适应也需漫长的时日,其间种种矛盾现象多被认为是这一群体不适应现代城市生活的表现,也因此使其成为被区别对待的人群。这种区别对待又常常被这一群体理解为遭遇到 “歧视”与“不公”,从而激发他们更倾向于发展内部关系网络,增强群内凝聚加以应对。因而,这种理论的坚持者大多认为,当这些群体在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逐步与城市接近,成为现代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时,这种群聚现象就会自然消解。
这种解释对从宏观上理解现代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流动群体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但它遭遇的问题是,许多具有悠久移民或外来人口历史的城市至今也并未能够形成一致性的社会情境,不仅如此,在城市生活的某些领域反而出现了族裔化现象。一些外来少数群体依赖于某一产业领域形成较为集中的分布形态。而这一产业领域恰恰又是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环节。这种现象被一些学者概括为“族裔经济”。[7]它所揭示的情况是少数族裔群体在城市的群聚现象并非是不适应城市,而恰恰是他们借用原生资源的优势积极嵌入到城市产业中的结果。
第三,这种认同也是一种裂变性认同。虽然从客位角度来看,无论珠三角彝族,还是其他的流动少数民族群体都在认同重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内部一致性,但事实上内在的分裂却也时常发生。彝人内部基于家支、地域和代际的差别在与经济利益冲突相重合的时候,往往会造成内部严重的分化;属于不同工头带领的工人之间的联系和互动非常有限,因为他们的态度往往受工头影响。因此,流动空间中群体性认同重构的同时也会再生出次一级的认同群体,这些次级的认同群体的关系具有场景拆和性。这也正是流动空间使原生社会关系不断碎片化的体现。[18]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新的城市流动少数民族很难结成完全同质性和统一性的群聚共同体。
人口流动固然深受结构性的推拉力影响,也必然以城市产业和经济发展为载体,因此这两种分析都有重要的解释力。但从具体过程来看,在制度开放的情境下,流动的重要前提是必要的信息沟通,否则人们无从得知流动的去向,更无法判断流动的价值。因此,信息对于人口流动具有重大的组织意义,而人口聚集也可能更倾向于受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影响。这一关键环节在以往的分析中大多被过于简单化处理,但随着信息技术的提高和流动程度的增强,信息的掌握在流动过程中的意义需要得到足够的重视。[8]人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进入到了曼纽尔·卡斯特所谓的网络社会时代。网络社会以便捷的物流通道为基础,基于信息的高速传递,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口的流动与迁徙,大大地增强了社会流动性。尽管在这种情境下原生的认同纽带会持续发生作用,但群体认同的主要形式会在人们应对流动空间对其生活影响的过程中被重新建构,这种重构的认同会成为重新凝聚流动群体的重要纽带,成为发起群体动员和形成群聚共同体的重要基础。
二、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与群体认同
所谓网络社会即指全部社会结构都围绕“网络化的逻辑”而重新建构的社会。[9]曼纽尔·卡斯特是“网络社会”概念的系统论述者,在他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信息处理和沟通技术为核心的信息技术进步使社会整体进入到信息化时代,进而重新塑造了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管理和协调模式。而这一重塑的过程恰与西方国家总体上从凯恩斯经济发展方案向新自由主义经济形态的转型过程契合,从而使得原来建立于社会和自然空间的经济增长模式越来越依赖于通过信息流通以实现跨越地域和社会的新的生产与管理体系。这种体系下的生产体制以信息处理为核心业务,生产组织表现出较强的弹性,强调生产的效能,重视这一过程中的技术服务,因而在整体上表现出高度灵活性。[10]新的网络技术,资本、管理和信息通过各种节点以最迅速的方式实现连接,并组织人们的生活。依托迅速的物流系统,由信息节点发出的指令可以最快的速度实现相关对象的快速流通。在这样的情形下,原来的自然空间对人们的阻隔被限定到最小范围,不同的自然空间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通过物流网络等各种流动渠道彼此建立紧密联系的网络关系。卡斯特认为这种形态突破了以往我们对自然空间的理解,将其概括为网络社会的流动空间,即“通过流动而运作的共享时间之社会实践的物质组织”。在他看来,这种流动空间通过网络的远距沟通“把在同一时间里并存的实践聚拢起来”,[11]流动空间有其独特的空间形式,主要包括三个层次:一是电子通信网络,二是各种信息节点、生产基地或交换中心,三是占支配地位的管理精英。[12]流动是流动空间的基础,如果流动停止,流动空间也就不存在了,因此,流动空间内中心和边缘的位置相对模糊,随着流动节点的变化,其空间界线亦随时变化,具有较强的伸缩性。
因此,流动空间本身遵循“包容和排斥”双重逻辑,资本在全球性网络连接的空间中不断积累的同时,会不断深化网络内外民众之间的不平等状态,从而激起地方空间和流动空间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全球性流动空间作为社会活动的主导时,地方的意义会被弱化,传统的合法性认同会趋于瓦解。新的排斥机制的形成和传统认同的弱化使得社会不可避免遭遇新的危机,在此背景下,一种反应性和对抗性的认同形式在一些地方开始暴露出来。也就是说流动空间对社会的影响愈强,人们生活遭遇的流动性越深刻,就越容易在人们生活的地方空间中生成封闭的自我保护性社区共同体认同。[13]
流动性极强的网络社会,人口的流动和重新聚集必将是越来越普遍的一种现象。在多民族构成的中国社会,少数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会是长期的趋势,也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然而,不同于以往的是,流入城市的少数民族群体可能很少会像以往那样形成集中居住的社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建立内在紧密联系的集聚群体现象就会消失。本文基于梳理既有的讨论认为,以往从城乡二元分隔理论来讨论城市少数民族群体的群聚现象已经不太切合客观现实,而应该更加关注流动行为本身对这种聚集现象的意义。本文认为,基于信息和物流技术形成的流动空间是导致人口迅速流动的关键因素,而流动空间本身选择性的接纳和包容实际上在网络内外形成了不对等权利关系,这种不对等的权利关系使得那些处于弱势的流动群体容易重构一种新的“认同”。这种重构的认同成为凝聚流动过程中的城市少数民族的关键因素。但这种认同不同于以往的民族或族群认同,它具有自保性、脆弱性和裂变性特征,从而也使以此为基础的少数民族群聚现象同样具有类似特征。
彝族人以往主要生活于四川、云南和贵州的部分山区。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尤其是2002年以后,他们开始大量流入珠江三角洲地区,主要作为工厂的临时工人,规模一般在10万人以上,高峰期达20多万人。他们以工头带领的领工制形式数十或数百人一起进厂工作,在订单完成后又群体性地辞工离厂;他们通常依靠一个或几个工头,在工厂内服从工头管理,在工厂外与工头一起生活;他们大多使用彝语沟通,遵循传统习俗和生活观念,内部联系紧密,使其在远离家乡的珠三角地区形成一种“无形的社区”;一旦与工厂或其他人群发生纠纷,他们很容易联系和组织牵涉上百人的群体行动;等等。这些特征使之与当地其他工人群体相比呈现更强的群聚性。但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在家乡时彼此并不熟识,或认识的范围非常有限;有些虽为谱系上的家支成员,但彼此从未往来;虽有相似的节日活动和习俗观念,但具体形态差别甚大。因此可以认为,彝人在珠三角表现出较强的群聚性虽与其固有的社会文化特征有关,但更主要是在新情境中再造的结果。[15]理解这一过程需要认真剖析彝人自身的特征和珠三角的社会经济结构。
从珠三角集体务工的彝族群体这一案例可以看出,他们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既有的外贸订单工业基础上,依托于网络和信息流形成大规模群聚性的流动群体。这种群聚性和行动力的形成与他们共同从事的产业有关,但关键在于其内部生成了新的群体认同。这种认同是他们应对流动空间过程中重构某种地方空间的体现。它与流动群体原来的民族纽带有关,但具体表现已经大不相同,其认同的范畴也并不必然与族群边界相符。总体上呈现如下特征:
三、少数民族流动群体的认同重构:以珠三角彝人为例
共纳入21个研究,包括594例患者,研究间异质性较高(I2=65%),分析原因同上。随机效应模型荟萃分析结果显示:治疗后骨不愈合发生率为5.7%,CI 95%为2.8%~9.5%。
(1)走访市场,材料价格、特性调研,取得厂家报告资料;到附近同类工程现场踏勘,与该工程项目施工单位交流心得。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依托外贸订单形成的代工分包式工业生产体制使当地生成了分别以正式员工和临时工为主体的两级劳动力市场。相对于正式工劳动力市场的有限发展而言,临时工劳务市场始终在规模上占据主导地位。临时工劳务市场通常要求劳动者随时后备,哪里需要就调动到哪里,类似于“劳工游击队”。这种状态的具体运作主要仰赖于劳动者和用工企业之间形成的劳务中介或劳务派遣组织。国际外贸公司与工厂签订订单合同后,工厂即根据获得订单量和完成时间核算需要的工人数量,以最快的速度将信息通告给劳务派遣公司,派遣公司再将信息分发到网站、微信群等平台,劳务工头(中介)往往会第一时间掌握信息,并与派遣公司建立联系,开始组织配送工人,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招募到工厂所需的工人数量。这种中间劳务组织的大规模生成是珠三角特殊的外贸订单工业发展内在的需求,同时也是临时工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基础,它们的存在极大增强了劳动者在工厂之间的流动性和市场化程度。也就是说,外贸订单量的增减或合作形式改变会直接影响工厂的生产规模和用工需求,灵活化用工的特点在于能使工人以最高效的形式从订单完成的工厂流向那些获得新订单的工厂。[16]
第二,这种认同是一种脆弱性认同。流动空间本身的灵活性和伸缩性注定这些流动群体的认同重构必然具有脆弱性特征。这种脆弱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流动空间选择性的接纳与排斥使得流动群体本身存在一种结构性的张力,那些在流动空间中获利较多的个体可能与那些处于更边缘的个体态度并不一样;第二方面在于那些处于流动空间边缘的群体往往受原居地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主动退出流动网络也可以是他们重新寻找其他出路的选择。以彝人为例,其内部的差异性和流动性非常大,有的人在短时间内积累发展成为大工头,但因为经营不善,一些大工头破产重回老家务农或另谋出路的也大有人在。
彝族工人在传统语言、生活习惯、文化观念等方面与城市社会生活的差别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劣势地位。其表现一方面是他们的工价普遍低于其他工人,另一方面是他们往往多处于备选的地位。因此,彝人实际上成为了临时工队伍中的边缘群体,总是身处被选择或辞退的循环境遇,流动频率相对更高。他们不能与工厂形成稳定的关系和认同,所以大多只能依赖和围绕领工工头形成相互联系的聚集群体,期待在自己遭遇困难时能够得到工头的关照,形成一种庇护性认同。这种认同情感在工人权利受到伤害或与工厂、中介发生纠纷的时候表现得尤为突出,工头往往被要求像“家长”一样出面帮助协调解决各种问题。因此,这些彝人领工头不仅成为临时工劳动力市场运行中必不可少的关键节点,同时也事实上成为彝人群体与珠三角社会互动的中间人和彝族工人遭遇矛盾和纠纷的代言人。[17]简而言之,领工头在这里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帮助彝人进入临时工劳动力市场,是彝人与全球性的工业生产体制构建的流动空间的连接媒介,另一方面,他们同时又是彝人在新的环境中重构地方性的族群空间的重要角色。工头和工头之间虽然有直接的市场竞争关系,但更希望在总体处于边缘的位置上抱团发展。基于这种认同,我们看到在工头们的共同组织下,彝人传统的火把节、彝族年、家支活动在珠三角的环境中得以重新再造。虽然组织形式和目的都与家乡传统大不一样,但通过这些活动使其彼此进一步增强了内部认同却是客观的事实。这一认同重构的过程正是他们自发应对流动空间对其产生影响的结果,是在新的流动空间环境中依托传统进行的地方空间再造的一种体现。而这种重构的认同成为他们在流动性环境中生成群体行动的基础。
四、流动族群认同重构的特征
对于理解中国当下的人口流动现象,流动空间理论突破了城乡二元区隔的分析框架,替代以新的网络结构,即能否进入全球性的流动网络作为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区隔的重要基础。网络内外形成权利不对等的两个范畴,流动空间具有更强势的地位。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依赖于信息、物资、技术、产品等元素的高度流动,人作为重要的生产主体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到流动之中。少数民族群体进入城市本身即是被纳入流动空间的过程,他们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接入城市的各种产业链,成为流动空间的流动元素之一。但对于他们而言,流动空间对他们的包容性和排斥性是同时产生影响的,而这就取决于他们对网络的意义,取决于流动空间里那些掌握和发布重要信息的国际贸易机构、订单外包企业、劳务中介机构或信息中转机构。也就是说,在流动情境下,城市成为对所有人开放的载体,城乡区隔的意义已经逐步被淡化,少数民族和城市人群的差别也在不断被突破,取而代之的是由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构成的一种新的区隔结构。这种区隔并非建构于物化的城市壁垒或族群性的社会文化差别之上,而是生成于具有高度灵活性的流动网络或劳动力市场的关联性。新的认同机制亦必然会基于这种区隔结构而重新构建。
第一,保护性是这种认同的主要特点。珠三角彝人领工制、家支和文化习俗重建等一系列活动客观上达到的目的有两方面:一是希望建立内部整合的群体,在自己遭受不确定的困难和纠纷时,能够获得群体的帮助或救济;二是营造一种共同体氛围,让彼此能够在高频度的流动中依然感受到人情冷暖,而不至于将自己陷入完全孤立的个体境地。作为流动空间中的边缘性群体,他们大都处于从属地位,对更大的范围毫无掌控能力,在这种情景下,他们出于自保而选择在较小范围内建立和强化更紧密的内部关系网络。
珠三角的流动工人通过劳务中介人、劳务派遣公司、工厂、外贸公司与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根本上是基于结构性的经济和产业关系,但具体表现却是通过及时便捷的信息传递网络来实现的。订单发包方和订单完成方的关系是结构性的,具体的实现过程是通过信息接受者对信息的把握和及时应对,以及信息发布者的主体性选择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实现。毫无疑问,发布信息的单位处于网络的重要节点位置,信息占有量是其地位重要性的重要指标。因此,订单发包方是这一外贸工业网络中最重要的节点之一,一级分包企业则是次级节点,二级分包企业必然受制于一级分包企业。劳务派遣机构是汇聚各种用工需求和工人信息的关键网络节点,但它在结构上仍然是依附于用工需求的企业。后备的劳动者往往可以通过劳务中介获得很多信息,他们在表面上可以自主选择不同的用工企业,但实际上却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因为他们只有接受这些用工信息才能与这种外贸工业体制建立联系,进而获得劳动机会,否则只能是自我排除于网络之外。与此同时,他们的选择空间大多受限于劳务中介人(或机构)发布的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会经过多重加工、控制,甚至是虚构包装以使其更容易让人接受。因此整个外贸订单经济运营和订单完成生产的过程都受制于信息网络的支配,后备的劳动者正是基于这种形式被组织进全球贸易的流动空间之中的。
整合资源丰富特色应用。对农村地区非遗文化进行创新加工,打破原有的展示模式,对其进行挖掘与拓展,使农村传统文化拥有更大的文化魅力,能够使人们产生更深层的触动。对农村民风民俗和乡土文化进行智慧化开发,催生出美丽经济新业态,同时也为农民增收致富注入全新的活力和动力。在乡村治理环节中,推广网络化、平台化、远程化等智慧化模式,促进政务信息资源的开放共享,推动乡村治理的智慧化精细管理;对乡村房屋、水质、垃圾等加强环境数据的智能化检测,提高风险防范水平和应急处理能力。
这两种分析之所以会表现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对城市本身的理解不一样。一些人习惯性地从现代化概念出发,推导出理解人口流动的二元结构模式,非此即彼的思维束缚了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化过程中复杂形态的理解。首先,城市本身基于历史和地理空间差异便具有内在的多样性。其次,在一体化建设过程中,一方面受移民进程的影响,城市的一致化建构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改变源源不断的外来流动群体;另一方面,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要求产业内部分工始终关注效率和利润,而当族裔性特征对此有利,那它并不会排斥与其嫁接,因而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强化其族裔特征。
五、结语
由此可见,基于流动空间生成的排斥也可能是双向的,流动空间试图将全部资源都整合进全球性网络并将地方空间排斥在外时,地方空间可能按照同样的逻辑生成支配性的制度或意识形态,进而强化自身领地,排斥领地之外的一切事物。在卡斯特看来,在旧有认同机制弱化的网络社会中,这种抵制性的认同会成为重要的认同形式,很多社会运动可能正是以这种认同为基础的。但最终人类社会进步的革命性运动必须得仰赖流动空间和地方空间达成某种共同计划的可能性,寻求社会结构全面改造的新的计划性认同。而在他看来,这是可能的,因为即使流动空间的那些精英群体自身也受到流动空间的束缚,生活于隔离的权力与经验二分的情境中,他们中的反思者可能会提倡与地方空间的抵抗性力量达成计划同盟。[14]
酒店大堂精装饰中高级马赛克巨幅墙面的施工面积大、颜色多、效果要求高。现场首先把握好基层处理的质量,为马赛克的铺贴提供平整的基础条件。马赛克在正式上墙面铺贴前做好预铺贴,提前根据效果颜色分布排布好各砖位置,在墙面上按照水平和竖向位置先做好标记定位,控制好每块之间的间距,每铺贴完一条要及时进行效果验收,以便整体质量控制,最终铺贴效果良好。
无论是对本科教育阶段的“知识传承”也好,还是对于研究生阶段的“知识生产和创造”也好,任教导师可以根据学习兴趣原则和学生自组织原则等,化大班上课为小组学习,构建“教导型组织”的基本架构,然后以学生的教育知识需求为重要逻辑起点,而不是以应试教育、知识灌输为逻辑起点,鼓励学生资助学习、交互式学习,导师回归“辅导员”[14]的角色,真正将学生的价值本位树立起来。
红薯叶,由河南科技大学农场提供。大孔树脂备选型号为:D101、AB-8和DM130型,购自安徽三星树脂科技有限公司。乙醇、亚硝酸钠、硝酸铝、氢氧化钠、盐酸等试剂均为分析纯。
随着城市少数民族流动性的加剧,流动空间对人们的影响进一步增强,这种认同重构会越来越强烈,在特殊的情境下可能演变生成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并冲击既有的社会秩序。但中国社会不同于卡斯特所处的美国社会,流动空间的扩展并非毫无限制,城市的流动人群虽然受到市场导向的影响,但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少数民族政策等一系列的制度依然是一种托底的平衡性安排,流动空间对人们的影响始终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与此同时,强有力的政府对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群体的生计、社会保障和发展有一系列的计划性安排,这对他们在复杂的流动性环境中获得稳定生活和重构群体认同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唐灿,冯小双.“河南村”流动农民的分化[J].社会学研宄,2000,(4).
[2]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3]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
[4]王汉生,刘世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J].社会学研究,1997,(1).
[5]杨圣敏,王汉生.北京“新疆村”的变迁——北京“新疆村”调查之一[J].西北民族研究,2008,(2).
[6]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
[7]狄金华,周敏.族裔聚居区的经济与社会——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检视与反思[J].社会学研究,2016,(4).
[8]王迪,王汉生.移动互联网的崛起与社会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6,(7).
[9][14]闫婧.卡斯特的“流动的空间”思想研究[J].哲学动态,2016,(5).
[10]曼纽尔·卡斯泰尔.信息化城市[M].崔保国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4.
[11][12]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505.506~510.
[13]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11.
[15]刘东旭.流变的传统: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彝人家支再造[J].开放时代,2013,(2).
[16]刘东旭.流动社会的秩序:珠三角彝人的组织与群体行为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6:63~83.
[17]刘东旭.中间人:东莞彝族工头及其社会功能[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2,(6).
[18]曼纽尔·卡斯特.流动空间中社会意义的重建[J].王志弘译.国外城市规划,2006,(5).
Re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Social Recognition:A Path for Understanding the Phenomenon of Moving Minority Cluster in Cities
SUN Qiang LIU Dong-xu
Abstract:The phenomenon of frontier ethnic minorities moving to cities is a kind of intrinsic requirement of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They usually fit into the industry chains through the form of groupment and realize inner contact and group construction via internet information technology,not just in the form of real settlement community.This kind of cluster form is not only based on urban-rural separation and its adaptive need,also appeared in the selective acceptance in network social mobility space and between unequal rights relation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the network.When facing this kind of complicated situation,the relevant vulnerable moving group tends to realize the group cohesion through reconstructing new recognition,which has features of self-defending,fragility and fissility.
Keywords:Recognition Reconstruction;Moving Space;Network Society;Moving Ethic Minority Cluster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103-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部城市流动彝族人的组织与群体行动研究》(批准号:14CMZ026)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9-02-22
作者简介:
孙 嫱(1983-),女,河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主要从事西北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研究。
刘东旭(1984-),男,贵州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博士,主要从事城市流动少数民族研究。
[责任编辑 贾 伟]
[责任校对 陈慧慧]
标签:群体论文; 空间论文; 少数民族论文; 城市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东部城市流动彝族人的组织与群体行动研究》(14CMZ026)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论文; 中央民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