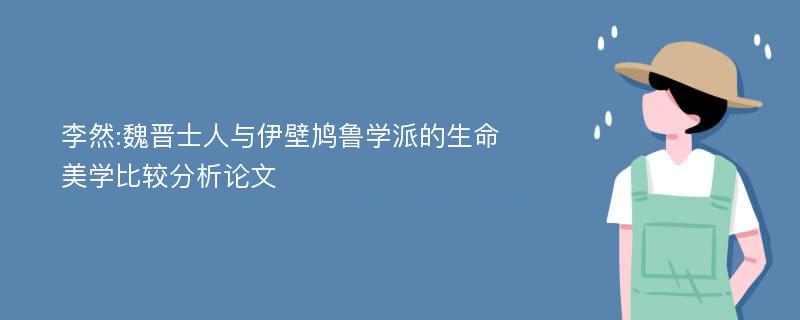
[摘要]生命美学源自于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自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性的自觉是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形成生命美学的基础。虽然两者各自形成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背景有诸多的不同,但他们对生命之美的赞叹与追求是一致的。在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个人情感地位的提升、张扬艺术的自主性、崇尚生命之美等方面,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殊途同归,而且都对后世生命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魏晋士人;伊壁鸠鲁学派;生命美学
美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可以把美学研究分为两种:认知性的理性美学和感性的生命美学。前者以美的本体为研究对象,后者以感性的生命活动为研究对象。希腊古典文明时代的理论家们普遍相信一个绝对本体的存在,他们从各个角度探寻着美的永恒理式,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着这一理性主义传统。希腊化初期的伊壁鸠鲁学派却试图在吸收借鉴早期希腊美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美学观念——关注个体感性的生命美学。魏晋之前的中国美学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美学思想。国内许多学者如潘知常、牟宗三、余福智等人认为,儒家美学乃是一种生命美学,“生命哲学是生命美学的底蕴。中国古代没有与生命哲学相对立的哲学,也没有与生命美学相对立的美学。儒家文艺美学和道家文艺美学是生命美学的两大分支”[1]77。但是儒家美学思想不寻求美的本质而专注于现世情怀,还称不上是生命美学,因为只有有了个体生命意识之后再反思生命,才会真正进入生命美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在个性自觉的基础上,魏晋士人美学才可以称之为生命美学。
魏晋士人和伊壁鸠鲁学派分别是中西方真正关注个体生命的开始,两者有共性又有差异。
一、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各自形成的基础
(一)社会基础
从历史发展来看,魏晋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期,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意识形态与秦汉时期相比,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汉帝国的衰亡和随之而来的连续不断的社会动荡,让人们饱受战乱和颠沛流离之苦,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最痛苦的时代。”[2]117
伊壁鸠鲁学派产生的公元前4世纪,希腊的光辉时代已经过去,马其顿的腓力大王和其子亚历山大大帝这时已经征服了希腊。随着亚历山大的病逝,帝国四分五裂,进入了长达20年的分裂战争,人们的社会稳定感丧失,社会矛盾激化,原有的社会体制濒临危机。
原本,因为杂志岁末盘点的一个选题,我想带大家看看圈内的这些摘取了大师桂冠的牛人们这一年来都在忙些什么?摘取了他们心所向之的桂冠之后,生活和事业又发生了怎么的变化?与吕杨的一席谈,发现13年前,从他选择葡萄酒伊始,就一早规划好了自己后来的路,而且极其坚定。于是,交谈的间隙,我跟他说:“我想把这些都写下来,这对我,对很多人,应该都有意义。”于是,就有了这一期的专题!
在相似的社会环境下,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相似的生活方式,走上了隐逸之路。面对无道的乱世之局,魏晋士人从嵇康、阮籍到陶渊明、陶弘景等人的选择似乎应对了孔子的结论:“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同样身处大变动的时代,35岁的伊壁鸠鲁在雅典城郊的一处幽僻之所购置了房屋和花园,和他的追随者一起生活了37年,远离尘嚣,伊壁鸠鲁学派因此又被称为“花园学派”。但他的“花园”既不像柏拉图的学园,又不像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校,更像是伊壁鸠鲁学派的成员们共同生活的乐土。“花园”对于伊壁鸠鲁,如同园林对于魏晋士人,都是安顿动荡心灵的适心之所。
虽然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选择了相似的生活方式,但二者又有着不同。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学说》记载,在“花园”里,伊壁鸠鲁和他的弟子们过着非常简朴清贫的生活,他们满足于面包和水,一块奶酪对他们来说都是奢侈品。这是一种苦行僧式的山林之隐,如同孔子与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论语·雍也》);这也是一种“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论语·述而》)的安贫乐道。魏晋士人的隐逸却是建立在中国悠长的隐逸文化基础上的。魏晋之前的隐士多像伊壁鸠鲁学派般,过着“岩居而水饮”(《庄子·达生》)、“积土为室,编蓬为户”(《汉书·东方朔传》)的清苦生活。进入魏晋,士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得到提高,从隐于山林到隐于园林,形成了独特的士人阶层的审美趣味。而实际上伊壁鸠鲁的所谓“隐逸”生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遁世,而是一种精神出世,追求灵魂的宁静。因此,如果说魏晋士人是诗意之隐的话,伊壁鸠鲁学派则是“孔颜之乐”。
(二)理论基础
生命美学源自于人对个体自由意识的自觉。自我意识的独立、个性的自觉,这正是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形成生命美学的基础,然而两者又不尽相同。
集体土地上不动产建设需要严格按照规定开展。当前很多农村居民为了满足使用需求,建设工具房、鸡舍、猪圈等。实际建设情况与土地审批程序中内容具有差异性,增加了不动产登记工作的难度。
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古希腊的哲学家们都在着力树立一种“贤人”的理想人格,如同孔子一样,寄希望于统治者中的“圣贤君子”来挽救岌岌可危的政治体制。因此在古希腊美学思想中,美是充满理性的,最美的境界就是神。柏拉图发现的“理式”也被认为是神的本质而加以颂扬。“理式”的发现,区分了理性思维与感性认知,并将理性提到了最高位,这一思想占据了整个古希腊的美学思想。随着希腊化文明的到来,产生了三大思想派别: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怀疑主义。斯多亚学派宣扬“世界理性”,强调人对于新秩序的顺应;伊壁鸠鲁学派却在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基础上,提出了原子“偏斜运动”,突破了理性主义的传统,否定了必然性,认为人类既不是被创造的,也不是被上帝所支配的,而是原子碰撞的偶然产物。原子“偏斜运动说”,否定了人的外部规定,实现了内部自醒,强调了人的自我意识达到心灵的自由,是一种生命美学。“他嘲笑被人们视为万物的主宰的东西——所谓命运。他认为有的事情由于必然性而发生,有的来自偶然性,有的是因为我们自己。他看到必然性消除了我们的责任,偶然性或运气则变化无常,而我们自己的行为是自由的,一切批评和赞扬都必须与此关联。”[4]34这就是伊壁鸠鲁对于人的尊严、人的自由和人的本性的最高信念,对他而言,求知不是目的,人生才是目的。
情感是审美经验中的要素之一,它伴随于审美活动的全过程。但人们对情感的认知却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人的个体意识自觉之前,情感处于理性的光环之下,只有当“人的觉醒”出现后,审美对象转向人的自身之时,情感的地位才被提升起来。魏晋士人和伊壁鸠鲁学派对情感的关注正是来自于他们对自身主体意识的自觉。
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理论传统的种种因素,形成了两者的审美意识的亦同亦异。
二、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生命美学内涵的比较
(一)喟叹生命
儒家强调的是人的社会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关于生死问题上更多的是充满理性,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魏晋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士人们的人生价值观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生命价值观。面对有限的生命,或沉迷于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邀游一世”[5]118;或服食丹药,“扪虱而言”成为一种风度;或顺应自然,超脱生死。无论是哪一种喟叹生命的形式,都显示出魏晋士人对生死问题充盈着一种庄子般的洒脱、屈子般的执着。面对“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今日良宴会》)的有限生命,人们发出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的感叹。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生的意义,活出自我,彰显感性丰盈的生命之美,成为魏晋美学的中心课题。而对于人的个性美的关注成为魏晋时期生命美学的亮点:没有心灵的干涸,没有正襟的说教,有的只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个体的张扬。汉末以来对人政治才学的品评在这一时期转化为对个体之美展现的人物品藻。这里既有“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世说新语·容止》);也有“太尉神姿高砌,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世说新语·赏誉》)。对人的个体生命之美的欣赏有仪容形色之美,有言辞才智之美,有自然任情之美,有自由精神之美。对生命之美的张扬在“肉”,在“骨”,更在“神”。
生死问题是伴随人类诞生的一个永恒的命题。然而无论是中国的汉末魏晋时期还是西方的希腊化时期,社会的动荡变化使人们对于生死问题的关注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个体意识的觉醒,带来了人们对人生苦短的感慨、喟叹,对生活、生命的无限留恋,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生命之美的赞扬和彰显。
魏晋之前,从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到荀子《乐论》再至《礼记·乐记》,儒家的音乐美学思想占据主流,成为中国礼乐文化的滥觞。《礼记·乐记》开篇便开宗明义:“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也。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 由此提出了音乐与人心的关系,人因为心感而情动,故形成了具体的音乐。音乐是人情感的表现,而人的情感不同,音乐也就不同,因此可通过音乐教化人心,正所谓“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经·毛诗序》)。音乐在此被理性化、伦理化,通过音乐使人达到“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蔡邕《琴操》)的目的,而音乐自身的美却被忽略了,艺术沦为政治伦理的婢女。直至魏晋,儒家的乐论成为了矛头所指,人们开始重新思索音乐与情感的问题。“声无哀乐”论首先提出“声之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嵇康《声无哀乐论》),从本质上否定了音乐与人心情感的关系,对儒家乐论进行了反驳,从而确立了音乐的自主性,发现了艺术的本体美。嵇康正是从音乐本体美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被称为衰德之音的“郑卫之声”,称“若夫郑声,是音声之极妙”。除去艺术之外的政治、教化和伦理,只关注艺术自身之美,这是“文的自觉”,更是人的自觉,这种自觉就是审美主体在审美活动中持有的非功利性审美态度。
(二)关于情感
五是具有智能化功能。目前,以太网被广泛应用于自动化系统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正因为如此,智能化的电气设备发展势头正劲。由于智能化技术在安全性、稳定性和可靠性等方面的突出优势,使电气自动控制系统能够在无人直接操作只靠计算机即可实现良好的控制效果[4]。
无论是儒家的“诗言志”,还是庄子的“诗以道志”,或是后来的“文以载道”,都一致认为艺术本质是从其志,而不是从其心,艺术要求代圣人立言,以礼为制,以理动人,要富有社会教化之功。而自我意识觉醒的魏晋士人却在屈原“虽九死而未悔”的重情基础上大力发扬了情感的重要性。《世说新语·伤逝》中记载王戎丧子后与前来探望的山简的一段对话:“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句话道出了魏晋士人对情感的专注,由此开启了六朝艺术缘情绮靡、重情尚丽之风。
在古代西方,音乐同样被较早地给予了关注。毕达哥拉斯曾将他的“数的理论”引入到对音乐的分析和研究中,提出了一套声学原则,认为和谐的乐音来自数的比例,这种比例不仅是琴弦的长度之比,更深层次地反映出其内部结构的一种秩序;他认为,呈现出秩序的音乐能够起到净化灵魂的作用,好的音乐可以提升人的灵魂。这与儒家的“成人伦、助教化”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毕达哥拉斯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来的柏拉图产生了巨大影响。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强调音乐教育的重要作用,通过音乐培育人的美善心灵和高尚品格。而在伊壁鸠鲁看来,艺术并不属于神,而只是人的艺术,他认为诗歌歌颂神性,从而使人产生敬畏恐惧,因而影响了人们获得快乐愉悦。伊壁鸠鲁对艺术并不持否定的态度,他只是针对毕达哥拉斯以来的音乐伦理观进行了批判。他的思想被其弟子菲洛德莫斯予以继承。菲洛德莫斯在其著作《论音乐》中指出,对人的心灵产生影响的只是附着在音乐上的诗歌因素,纯粹的音乐并不具有柏拉图等人所认定的教育功能。正如嵇康所言,人心与音乐“殊途异轨,不相经纬”,音乐唯一能够让人感受的就是愉悦,纯粹的音乐可以产生快乐。伊壁鸠鲁对于诗歌是持否定态度的,甚至主张将诗人逐出希腊城邦。因此剥去附着的道德宗教,纯粹的音乐是可以引导人进入幸福愉悦境界的,音乐自主性的美由此得以张扬。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的美学思想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强调政治教化的作用,即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发乎情”是对个体的肯定,“止乎礼”又是对个体的限定,“发乎情,止乎礼”看似是对两者的调和,实则强调了后者,将个体严格纳入社会规范,正如李泽厚所说:“儒家不否认个体,但他认为群体、社会是无限地高于个体的。”[3]97然而汉末的连年战乱,国家主权更迭,人们颠沛流离,儒家思想逐渐遭到疏离与背弃,人们开始探求人生的真正意义,玄学由此出现。“魏晋玄学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转变,那就是从汉代的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它的中心课题是要探求一种理想人格的本体。”[3]118至于那理想的人格,对于经历过思想幻灭与挣扎的魏晋士人来说,就是老庄的自由超脱、追求自我感受、重视情感、崇尚自我。《世说新语·品藻》记载:“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由此可见,魏晋士人人格意识的增强和对自我价值的肯定,重视表现自我,这是个性自觉的重要内涵,正所谓“越名教而任自然”。
(三)关于艺术的自主性
面对同样的问题和困惑,伊壁鸠鲁开出的药方是快乐生活。面对苦难和不幸,以快乐的态度去面对,达到精神的自由平和,从而获得幸福愉悦。但是这种快乐生活并不像魏晋士人的“任性而行”的自然任情之美,而是一种节制中庸的快乐,正如他在《致麦诺休斯》的信中所言:“我们所说的快乐指的是肉体没有痛苦和灵魂没有烦恼。它并非连续不断的宴饮和狂欢,并非性的诱惑,并非在一桌奢侈酒席上享受鱼或其他美味佳肴,这些只能提供舒适的生活。”[6]165要想获得快乐生活,就必须消除痛苦,而令人恐惧的痛苦主要来自神和死亡。伊壁鸠鲁在《主要原理》四十条的第二条谈论的就是关于生死的问题。他认为,人的肉体和灵魂都是由原子的一系列碰撞形成,当人死亡时原子也就四散而去,因此死亡实则为“感觉的剥夺而已”。“我们活着时,死亡尚未来临;死亡来临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因而死亡对于生者和死者都没有干系。”[7]638消除死亡带来的恐惧只是打开了通向幸福愉悦的大门,要想获得真正的幸福还需要节制与淡泊。因此,虽然伊壁鸠鲁的快乐论充溢着对生命的热爱和对于生死问题的超越,但又不如魏晋士人般超脱,而是审慎的、与理性和德行相联系的。
同样,古希腊自巴门尼德以下,皆为思辨之思维,有尚理性主义之传统,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学派更是将绝对理式视为世界的本质,指出“美是理式”,进而贬低感性。伊壁鸠鲁不同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种拒绝感性认知的观点,认为现实世界就是一个感性的世界,如果我们不相信,“不仅一切的推理都会被推倒,而且即连我们的生命也会立刻崩溃”[8]210。在充分肯定了感性的基础上,伊壁鸠鲁提出将情感作为判断人生的准则,强调情感是判断人生快乐幸福的重要指标。伊壁鸠鲁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理智认知,在逻辑和辩证之外强化了人的情感活动,并将情感作为其三大准则之一,对后世美学思想具有启示性作用。
这虽是一则寓言,却隐喻了父母对孩子是接纳还是排斥的态度,如何影响着孩子的人生。这个“犄角”,可以是孩子的左撇子、不够好看的外表、音乐的天赋等等。它们需要被呵护,而不是被压制、被掰正。心理学家武志红说:“所谓无条件接纳,就是对孩子满心的喜欢。”这个喜欢和爱不同,是一种建立在父母健康自尊之上的智慧,是切实做到了,跨越美丑胖瘦,智商高低之上的一种发自内心的欣赏,是将孩子当做一座宝藏,去源源不断地发掘出他的魅力。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较早纳入艺术视野的当属音乐,对于音乐美的认知表现出早期人们对艺术美的理解;同样,在艺术主体性发现方面,也是首先从音乐开始的。魏晋士人和伊壁鸠鲁学派在反对审美功利化、提倡艺术自主性的审美态度上是一致的。
随着经济的发展,新的媒体形式层出不穷,加上人们对电视台的要求越来越高,给电视台带来巨大的冲击和挑战。电视台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提高电视台的节目和服务质量,而电视台编辑记者的专业素质直接影响着电视台节目质量。
三、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生命美学对后世的影响
虽然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在美学思想上有诸多不同,但两者在反对理性与神性、肯定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生命之美、重视人的情感活动上是一致的。虽然,伊壁鸠鲁学派之后充满神性的经院美学占据了主导地位,魏晋之后崇尚理性的宋明理学一度鼎盛,但是两者对于后世的生命美学都具有了启示性的影响。
魏晋之后尤其是宋明士人对魏晋风度加以传承,并结合其时代的情景加以融合,推陈出新。虽然北宋社会深受“道学”复古主义和王安石实用主义的影响,苏轼却彰显出另一番生命之美。他一生坎坷,但其旷达平淡的风度却深受魏晋士人生命美学的影响。苏轼不仅将魏晋士人崇尚人的情感、强调生命之美的思想加以学习、化用,而且形成了自身独特的风度气质,这不仅表现在其思想上,也付诸于其行动中;明代李贽提出的“童心”说直面人性,向“存天理,灭人欲”的现实发起攻击,肯定人的内心欲望,追求人格的平等与自由;公安三袁的“性灵”论重视人的主观情感与感受,强调人的本性与至情,个性追求达到极致;李渔则重“本色”,否定戏曲中的道学气和华辞丽藻的堆砌,重视人感情的真实流露。从苏轼到李贽、公安三袁再到李渔,人的真心、至情、本色再次被唤醒,此皆为魏晋士人生命美学在后世地不断发展演化。
经CA-074预处理后再予以大剂量LPS刺激,与LPS组相比,CA-074+LPS组WT与TLR4-/-的组织蛋白酶B活性明显降低(P<0.05,图4)。表明组织蛋白酶B抑制剂预处理引起了组织蛋白酶B活性的明显下降。
伊壁鸠鲁学派则因其张扬人的感官欲望、追求享乐而备受后世贬低,大多数的思想家对其持否定态度,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伊壁鸠鲁学派才得以正名。人们开始对斯多亚派、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进行反思,否定将德行作为快乐的唯一源泉,从单纯追求灵魂的快乐开始转向对人体本身的肯定。将人从神性、德行中解脱出来,对人自身加以肯定,对幸福的认识也从天上回归到人间,这成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时代强音。此后西方美学中的人文主义不断发扬光大,一直影响到了当代西方美学的重要思潮。
通过对魏晋士人与伊壁鸠鲁学派生命美学的比较分析发现,无论有何等差异,人们对生命之美的赞叹与追求都是一致的。
参考文献
[1] 余福智.中国古代生命美学初探[J].学术研究,1996(4).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篇[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4] 伊壁鸠鲁,卢克莱修.自然与快乐:伊壁鸠鲁的哲学[M].包利民,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5] 朱铸禹.世说新语汇校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朱立元.西方美学思想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7]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8] 卢克莱修.物性论[M].方书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Comparison of the Life Aesthetics between the Scholar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Epicurus School
LIRan
(Centre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
[Abstract]Life aesthetics originates from people's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freedom.The independence of self-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 are the basis for the formation of life aesthetics between the Scholar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Epicurus school.Although the social foundation and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life aesthetics of the Scholar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Epicurus school are different,people's admiration and pursuit of the beauty of life are consistent.They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in terms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individual life,the promotion of personal emotional status,the publicity of the autonomy of art,and the worship of the beauty of life,and both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aesthetics in later generations.
[Keywords]the Scholar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Epicurus school;life aesthetics
[中图分类号]B83-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662(2019)01-0039-05
[收稿日期]2018-11-14
[作者简介]李然,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美学及影视艺术。
DOI编码:10.3969/j.ISSN.2095-4662.2019.01.007
(责任编辑陈咏梅)
标签:魏晋论文; 美学论文; 士人论文; 生命论文; 学派论文; 《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天津财经大学创新与创业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