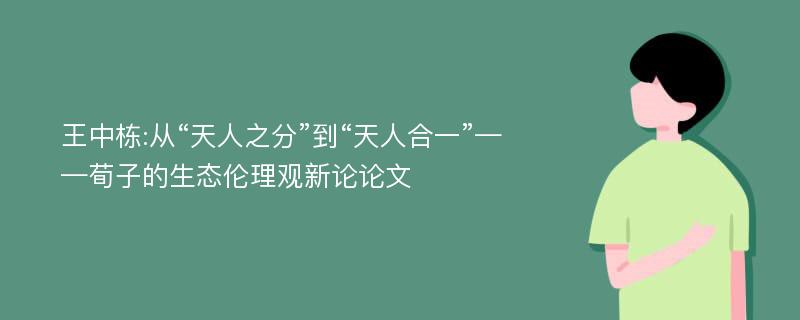
[摘 要]在批判继承儒道两家天人观思想的同时,荀子又提出要从“天人之分”的视角来重新定义人与自然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通的存在关系,这不仅动摇了中国传统浑融一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还在新的历史语境当中使主体的自我意识和能动作用得以伸张和重构。在荀子看来,人作为具有本能欲望和精神意识的生命个体,始终离不开“礼义”之道的规范与指导,更离不开天地万物的持养与供给,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一种新型的生态伦理关系。易言之,荀子的“天人之分”思想并不是对“天人合一”传统观念的简单否定,而是通过对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意识”、“整体意识”、“平等意识”的深入探寻,以期达到更高层次的“人与天地相参”的生态伦理目标。
[关键词]荀子; 天人之分; 主体性; 生态伦理观
荀子的“天人之分”哲学思想,虽然消解了儒道两家天人思想中的形而上价值和意义,并赋予了天以物质性与功利性的丰富内涵,但他的天人观思想又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根本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人先要明确人与自然所处的生命共同体的职能和责任,既要满足自身的发展需求,又要顾及自然的运行规律,进而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生态伦理关系。对此,本文将从“天人之分”观念中的主体性探究出发,结合荀子对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本质特征的基本体认,来重新阐述他的生态伦理观,以明荀子本意。
一、“明于天人之分”:对神秘天人观的突破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具有根本性的哲学观念,既是中国人对宇宙本源的探寻,更是对人生价值和生活目标的追求。老子否定了殷商以来对“神”或“天”至上权威的崇拜,将“道”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并将其作为“自然无为”的生态哲学思想的核心,也就导致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表现出了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即万事万物都是从“道”衍生而来的。老子认为“道”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是一切逻辑思维的本始;“道”也是人类社会的准则和标准,是约束人的言行举止的根本法则。正因为,“道”生万物的过程是一种无以名状、朦胧混沌的特殊状态,是阴阳之气相互交融的结果,也就带有浓厚的神道色彩。
3)经过结果分析发现,除一类桩和二类桩外,其他类型的基础桩都存在质量上的缺陷,需要相关部门进行监管,重新处理操作。
庄子基本沿袭了老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体识,并对世界本原问题加以深究,认为人作为自然界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应当充分肯定和尊重其平等的身份和基本权利,从而形成了“万物齐一”的思想主张。故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庄子·秋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毫无疑问,这同样是一种主客浑融的本体论思想,始终以一种感性的哲学形态而存在,也就无法以理性的思维方式来解释现实世界中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对此,荀子才反驳道:“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也即是说,自然界并不神秘,它可以被人所认识。他强烈批判了老庄之道是基于形而上而提出的抽象之道,是缺乏来自物质生活与社会实践的思想考量的不可知论和消极无为的思想。
先秦儒家关于人道问题的探讨也离不开对天道问题的思考,天与人的关系始终处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动态过程之中。“天”在孔子看来是社会文明和自然现象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并进一步提出了“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的哲学思想,即将生命精神与圣贤之德融入到了天人观的论述当中,使天具有了人格化的色彩。孔子认为,唯有“敬天修德”“以德配天”,才能进入人与自然相融相合的境界,从而实现理想的伦理道德目标。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天”在宇宙创生中占据主宰地位的思想,但他更倾向于探讨具有先验性的义理之天,即从人的内在心性方面来省察自身和把握天命,从而使天命与心性趋于合一。故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毋庸置疑,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很不彻底,并未明确的将天与人的界限划分清楚,同样是一种主客浑融的哲学观念。
《易传》作为先秦儒家的经典之作,也旨在强调永恒的天道不仅赋予了自然万物之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同时又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参,正如《易传·干》所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种天道观既显示了自然之天的运行法则,又包含着对传统儒家道德的解释,进而要求人要以至诚之心顺应天地万物的发展规律,做到不违天时、不违天命,亦即“天人合一”,才能逢凶化吉、吉祥安康。所以说,在论证天人关系时,虽然传统儒家有别于老庄“道法自然”“万物齐一”的哲学思想,而侧重于人格道德的阐述。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儒道两家也始终没能突破对至高无上的“天”的敬畏和崇拜,并带有某种神学目的论色彩。然而,我们不能就此否定了人与自然的独立价值和基本需求,而将两者笼统地归之为主客不分的“混沌”状态。更何况,“天人合一”的价值指向本身就具有浑融性和模糊性,甚至带有物我不分,人我不分的“一元论”思想倾向,也就无法准确地解释人与自然两者间的辨证关系。
具体而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缺乏“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并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淹没在了社会群体当中,从而造成了观念形态和思想意识中自我个性的缺失。所以说,这种直接越过“量变”过程而进入“质变”状态的探索方式,又是缺少科学精神和演绎内涵的,也就不可避免地带有形而上的神秘色彩。张世英也曾提道:“所谓‘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合一’‘一体’,也不是指人作为主体,以认识作为客体的自然,从而达到主客对立统一之后的一种通透的精神状态,而是一种朦胧模糊的混一景象。在原始的‘天人合一’中,人不理解(不认识)自然,故不能说与自然相通。”[1]
可见,真正意义上人与自然的“相通”关系是发生在两者的客观规律和个体价值得以明确之后的,否则,主体意识的缺失势必会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以及人与社会矛盾的爆发。
正如我们所知,荀子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物质世界先于理念世界而存在的唯物主义观念基础之上的,并主要通过对自然之天的部分祛魅,来颠覆原始观念中天与人混为一谈的神秘论思想,进而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明于天人之分”学说。故曰:“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荀子·天论》)在荀子看来,“道”一方面指道家“道法自然”的先天原则,也就是形成于客观万物的自然原始力量。另一方面,“道”又指儒家修身之道、政治之道,是对“天人合德”“天人感应”哲学思想的批判继承。而所谓“分”,则是对人与自然各自责任和职能的划分,并不是强调两者之间相互对立、相互斗争的关系,它既显示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价值,又突出了自然的规律性和客观性价值。
在任何时候,人与自然都只能看做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做是一种手段,其内在价值的体现也进一步构成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内涵。换言之,“只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才是需要我们最终并直接给予尊敬和肯定的。”[2]因此,人绝不能僭越自然规律、违背自然价值,甚至于对自然为所欲为,反之亦也。正如荀子言:“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荀子·礼论》)也就是说,荀子赋予了“天”以功利性和物质性的丰富意涵,并揭示了自然界所蕴含的客观发展规律,进而消解了传统观念中具有神秘性和神圣性意味的“天”,故又曰:“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自然万物和人类社会属于不同的范畴,拥有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和职能特性,自然界的内在规律无法用人类社会的发展经验加以说明和解释,人类更无法从本质上改变自然的运行法则,而只能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加以协调和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荀子眼中的“天”已经逐渐揭去了至上神灵的面纱,成为了与人类社会相对的真实客观存在。
实际上,荀子已经深刻意识到中国传统哲学观念中强求一致、简单求同的思想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唯有明确了“天人之分”之后,才能准确地揭示人与自然的内在价值和逻辑关系,并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个体与整体间的矛盾关系。这就从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以往天对人的绝对权威性这一错误观念,进而将人与自然从简单同一的认识关系中区分开来。对此,惠吉星也曾指出:“从个体生命来讲,自然界是人生存的基础,作为自然万物之一,人只能在自然提供的外在和内在条件基础上活动,而人的作用不过是自然作用的延续和完成。”[3]显然,荀子思想中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个体与整体的内在联系,并且是一种永恒的存在关系。所以说,荀子致力于对人与自然各自功能的辨析,是旨在加强对人与自然本质内涵的认识和完善,并以此来重新定位两者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故曰:
“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则天地官而万物役矣。其行曲治,其养曲适,其生不伤,夫是之谓知天。”(《荀子·天论》)
要持久有效地解决中小学生“课后三点半”的难题,政府必须立足于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的权利和需求,构筑起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利益诉求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依赖政府、学校、家庭、企业、社区和社会资源的普遍参与,营造共建、共管、共担责的课后治理模式。在确保课后服务以公益性和普惠性为前提的原则下,由政府牵头,吸纳有资质的课外培训机构、爱心企业和志愿者加入,协助学校更好地满足家长和学生的多样化教育需求。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学校的现有资源开展活动,调动在校教师的参与积极性和创造性,将课后服务与校本课程开发有效结合,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素养为目标,杜绝将课后服务变成补课的平台,变相加重学生的课业负担。
在这段话中,荀子分别将“天”字加在认知、感官、侍养、政务和情感的前面,进而构成了“天君”“天官”“天养”“天政”“天情”五个不同的概念,看似与其“天人之分”的思想相互矛盾,但其主旨意趣早已摆脱了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浑融性与神秘性。明言之,荀子通过对圣人能够“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的主观意识的肯定,抑或“清、正、备、顺、养、全”等认知与实践能力的描述,不仅彰显了人与自然所各自拥有的价值意义,而且也说明了人与天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的存在关系。赵法生就曾指出:“荀子给人加上这样多的天字,并非要提升人的地位,而是要将天从以往的圣坛上拉下来与人平起平坐,不但天失去了所有曾经拥有的神圣意蕴,人也已经没有什么神圣性可言,人的诸般功能如同天的其他物质化的自然功能并没有本质区别。”[4]也就是说,强调“天人之分”本身没有错,虽然人与自然万物各有其职、各自发展,但两者始终是一个共同体,亦有内在关联性,而绝非是相互对立的分裂关系。因此,人与自然之间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又蕴含着内在的统一性,只有将人与自然严格区分开来,才能更好地认识、接受、运用自然界的价值功能,这种先分离后整合的逻辑范式能够更有效地实现人与天地自然相融相生的理想目标。故曰:“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荀子·天论》)对此,唐君毅也解释道:“荀子所强调的是人和天地的对等相应的关系,此天人有分之说并不与天人之合有必然冲突。”[5]这也较为准确地诠释了荀子的原意。
综上所述,“天人之分”作为荀子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其最终目的并不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否定,而是借此提出了自己对于天人关系的新认识,进而建构起了更高层次的天人合一观。虽然荀子旨在强调天与人的差异性,而没有对其统一性给出充足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就直接否定了两者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基于对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辩证关系的重新界定,我们可以认识到荀子所谓的“天人之分”并不是一种人对自然的争胜观点,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抑或浅层含义上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强调人与自然拥有各自的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两者之间始终是一种既相互独立又共生共荣的存在关系。所以说,荀子素朴的“天人之分”思想又可以看作是对人与自然混沌关系的突破,对于构建新型的生态伦理观具有更为深刻的启发意义。
二、“制天命而用之”:对主体创造性的肯定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粮也。”(《荀子·王制》)
在荀子看来,人之所以能够成为天地间唯一具有理性思维的物种,关键在于人的本质不仅包括“气”“生”“知”三个基本范畴,更在于人具备拥有“义”之道德理性的可能,而“义”也就是“礼义”之道,是人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根本属性。故曰:“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也就是说,人作为生命个体具备一般物种所不存在的精神追求和道德意识,这既表现在人具有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主观能力,还表现在人的实践活动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目的性。这也就打破了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坐以待毙的原始观念,并进一步提出了“天地生之,圣人成之。”(《荀子·富国》)的哲学思想。毋庸置疑,所谓“生”,即自然界的原始创造力,是孕育万事万物生命的最初根源;而所谓“成”,则指人的后天创造力,是体现万事万物价值的必要过程,并由此明确了人与自然是共同创造者的身份。
正如我们所知,人的一切活动是不可能不围绕着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人对自然的认知也是首先要以自身的生命需求和精神需求为等价条件的,否则,人类文明早已被自然界的其他生物所取代。对此陈炎强调:“如果我们只是顺应自然,不去改造自然,那么我们的人类根本不会发展到今天,而是早被自然界的其他物种所征服了。即使我们可以像佛门弟子所坚持的那样,不杀生,只吃素,那么我们也不可能不吃不喝,对同样具有生命的植物不加破坏,否则的话,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将难以为继了。”[6]因此,只承认自然的重要性,而忽略人的主体性,这种非此即彼的观点是十分片面的,是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甚至会造成人与自然矛盾关系的激化。
模型6和模型7则主要分析了城市居民的住房保障度和就业稳定度对于社会距离的影响。由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与住房和就业之间有一定的联系,比如住房的保障程度肯定会对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造成一定的影响,从而通过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到社会距离,因此在这两个模型的分析中我都引入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这一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荀子之所以形成了既包含人的维度,又包含自然的维度的生态哲学观,关键就在于他始终强调“隆礼重法”在克制人性欲望和规范言行世事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隆礼重法”的过程同样是人之主体性得以伸张的集中体现。在他看来,人在凭借自身的本能欲望去探索未知的世界时,总是习惯性地从利己的角度去评判事物的价值和意义,甚至为了迎合自己的审美喜好和价值观念而任意地决定事物的取舍,就会不可避免地带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倾向,故曰:“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荀子·性恶》)一旦这种利己欲望得不到“礼义”法度的引导和约束,就会扰乱正常的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进而引发社会的治乱现象。因此,决定人之凶吉祸福、贫富贵贱的并不在“天”,而在于“人祆”,也就是人为的怪事,“物之已至者,人祆则可畏也。”(《荀子·天论》)荀子突破性地将社会混乱与自然损坏的根源从传统观念中对“天命”的依附转移到了对复杂人事的探讨,并将其归纳为不修农事、不修政事、不修礼义三个方面加以论述:“楛耕伤稼,耘耨失秽,政险失民。……政令不明,举错不时,本事不理。……礼义不修,内外无别,男女淫乱。”(《荀子·天论》)由此观之,荀子强烈批判的是那些不受礼义之道约束的,完全处于失控状态下的人性欲望和实践活动,而非对人的主体性和创造性的全盘否定。
即是说,由不同乐器演绎而成的“乐”作为天地万物的统率,本身就是一种秩序性与和谐性的展现,是与自然社会、人类社会紧密相连的,并不可或缺的要素。因此,礼与乐之间不仅在功能价值方面是相互依赖、相互完善的,在内容方面也是相互统摄、相互包容的关系。礼乐之统的本质就在于要使藏匿于人心中的情感得以合理宣泄,并由此感发出主体间互识与共识的意向,进而实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故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荀子·乐论》)
所谓“制天命”并非制服自然的意思,而是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应时”指顺应季节时令的变化;“因物”就是适应自然万物的发展;“骋能”是施展人的才能。荀子认为,与其懵然无知地崇拜和敬畏上天,不如将它作为平凡动物一样畜养起来,使其为己之友;与其不假思索地颂扬和顺应上天,不如学会掌握它的发展规律和本质内涵,能够为己所用;凭借万物的生长规律而仰慕它,不如施展人的才能去改造它;思慕和辨赏上天,哪比得上充分发挥它的价值而后拥有它呢?由此看来,荀子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一旦放弃了人作为主体的能动性作用和对自然的积极主动的关系,而把希望寄托于自然万物,就会错失自然能够造福人类的实用价值。
进一步说,人能否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并在符合客观规律的条件下进行生产实践和审美活动,其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因为,人始终处在一个相对复杂的“社会体系”当中,而且又深受传统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观念的影响,进而丰富了人的主体性功能。基于此,荀子则提出了积极有为与消极无为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态度和人生观念,并对两种不同的结果作出了比较分析,他写道:
“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荀子·天论》)
君子主张“敬其在己”,即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并相信人能够凭借自身力量去实现人与自然的互利共赢;小人则崇尚“慕其在天”,即肯定自然的主导性,并忽略了人的能动作用和独立价值,因而听天由命、消极度日。可见,盲目地崇拜自然力量和追求自然利益的价值观是不可取的,这不仅是对“畏天命”“知天命”原始观念的历史倒退,而且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也是相违背的。更重要的是,“慕其在天”的消极方式并不能帮助人们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与生存危机。更何况此时的“天”已不再是具有主宰性的神圣之天,而是被物质化、功利化的自然实体,故荀子曰:“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祅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荀子·天论》)所以说,荀子十分注重“敬其在己”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又在于人首先要明确人与自然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特殊性,并要战胜自身的审美偏好和愚昧观念,进而发挥人在自然中“制之”“用之”“化之”“使之”的能动作用。
以“二线三段”的教学思想为指导, 根据“数据库技术与应用”课程特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与专业课程内容的相关性,构建面向新工科的通专融合的“数据库技术及应用”课程教学模式。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管桩外径0.5m、内径0.25 m,设计桩长15 m。对于钢筋混凝土构件重度取25 KN/m3,则桩体自重G为55 kN。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荀子并没有单纯强调人的内在价值和发展利益,甚至将人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而是主张要承认和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始终秉承“不与天争职”的生态观念,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有序发展和资源利用的长久循环。故曰:“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荀子·天论》)尽管自然界蕴含着无穷多的矿藏和不可知的秘密,但是人类在探寻的过程中也要始终秉承着适度、合理的原则,否则就会物极必反、自食恶果。也即是说,荀子已经深刻认识到了“不与天争职”的生态伦理意识对于解决有限的资源与无限的欲望两者间的矛盾冲突有着至关重要的指导意义,它不仅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人的原始本性和能动力量,而且也有效地克制了人对自然万物的肆意掠夺,是实现社会进步和自然保护的必要手段和根本途径。对此,荀子在《王制》《荣辱》《富国》等篇章中曾多次提到:
基于“天人之分”的哲学形态,荀子的意图显然不只是为了突出自然本有的价值,还在于揭示人在自然整体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说,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不再是被动地束缚于自然法则的生命体,我们不仅要肯定自然客体的内在价值,还需要肯定生命主体的积极参与,以此才能实现和维持人与自然之间良性互动的发展关系。易言之,荀子的天人观思想是以人的“制天命而用之”“不与天争职”等主体性与能动性作用为思想基础,并以“礼义”道德为规范指导的,这既是对“天人之分”哲学思想的进一步演绎和运用,也是对传统认识论当中“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并与西方传统哲学观念中的“自然中心主义”,抑或“人类中心主义”有着根本性差异。
“于是又节用御欲,收敛蓄藏以继之也。是于己长虑顾后,几部甚善矣哉!”(《荀子·荣辱》)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希望我们这支庞大的写作队伍,尤其是基层的作家们,能多一些来自生活本身的朴素表达,发挥在民间的优势,少一点“文艺腔”的陈词滥调。
“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荀子·富国》)
在消解了天的神秘性和道德性进而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之后,荀子又进一步指出人与自然之间是既能“参天地”又能“总万物”的良性互动关系,实质上也就是主体的能动作用与自然外在规律的和谐统一。因此,他既强调要伸张“天人之分”中的自我个性,又要求必须超越自我,也就是超越了西方的“主体性哲学”和“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代之以人与天地万物相融相通的合作关系,“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荀子·王制》)也即是说,“人与天地相参”作为荀子生态伦理道德的最高指引,不仅是以礼义法则和道德经验为价值取向而建构起来的伦理观念,而且也体现着早期儒家的情感诉求在伦理观念中的具体应用,并主要包括着“和谐意识”“整体意识”和“平等意识”这三个方面。
(1)直接销售。民宿经营者在接到游客电话预定或是直接到店登记时,首先要给出有效、真实、准确的民宿信息,同时积极留住游客。经营者可以有专用的号码接收预订者来电,提高效率。还可以利用“电话或上门预订民宿,可有上下山接送”,或是推出游客直接与经营者预订,赠送庐山纪念品等,吸引游客成为直线门市客。
事实上,荀子强调人在天人系统中的价值和地位,绝不是为了突出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而是旨在明确人与自然的本质属性和内在关联,更好地发挥人的主体意识和能动作用。荀子认为,自然之天作为认识客体,虽然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但并非是神秘莫测、无法掌握的,而是能够被人所认识的,也就从某种程度上肯定了人可以通过对事物的探索和求知,来实现对其客观规律和内在机制的把握,故曰:“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即是说,人作为可以掌握人与自然的生成节律和动态平衡的认识主体,能够将自然感官(天官)所获得的感性认识(薄类)上升为理性认识(征知),从而有效地避免过多情感因素所带来的干扰,最终保证主体判断的科学性与可行性,即“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基于此,荀子又进一步提出了既合乎自然规律,又满足主体能动性的“制天命而用之”的理论主张,故曰:
荀子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礼义规范的内在关联,就旨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礼义”既可以对人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从而树立正确的伦理观念,又能确保人在自然整体中活动的自由和权利,并努力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创造有利的条件。故曰:“推礼义之统,分是非之分,总天下之要,治海内之众,若使一人,故操弥约而事弥大。”(《荀子·不苟》)所以说,荀子的生态伦理观,是基于对人与自然的特殊功能和整体利益的尊重与权衡而展开的,能够使宇宙万物保持相对稳定的和谐秩序,具有超越传统认识论的进步意义。
三、“人与天地相参”:
对生态伦理观的诉求
唯有掌握了自然万物的内在机理和生长节律,并以此因时制宜地进行耕种、收获和贮藏,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谷物庄稼的自由生长,才能实现人类获得更为丰富的自然馈赠。而且,荀子还强调征收赋税要与田间耕种的时间想配合,否则,过度征税同样会加剧人对自然的滥伐与破坏。正是基于对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的理性认知,荀子才强调人不能毫无节制的掠夺自然、枯竭资源,而是要适度索取、物尽其用,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所以说,荀子的生态意识,并不是主观臆造出的抽象概念,而是基于人的生产实践得出的丰富经验,具有形而下的现实意义。对于一个农耕民族来讲,正确的生产观念既可以帮助解决人与自然所面临的多种危机问题,还可以启发民智甚至改变人对自然万物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式,并能深刻地影响人对自然的审美方式。
首先,生态伦理观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不仅是对主体生命的体认,也不只是对自然价值的肯定,而是强调主体心灵与客体对象的相互融合。因为,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前提,它既表现为人的受动性与能动性的统一,也表现为主体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7]这种新型的伦理观要求我们必须突破传统认识论当中人视自己是自然的主人,以及视自然是被利用的对象的思维方式,从而才能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伦理观念。正如陈昭瑛所说:“荀子对天、地、人的合一怀有存有论的信念,天地人固然各有职分,但可以合作无间。人参天地正显现一种宇宙大生命的有机整体。天与人在宇宙化育工作中的分配、分担与分享,强烈而明显的指向双方的和谐而不是分离。”[8]也即天、地、人作为客观的存在体,始终处于动态生成的发展过程当中,共同推进着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
1.2.4 总结 课堂结尾,教师对争议性比较大的问题进行讲解以及分析,与此同时,解答构建的问题,对本次课程的重点内容进行归纳总结[7]。教学课堂中,对学生提出的新颖观点,可以及时进行查阅作出一定的判断,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积极发言,必要的时候可以增添一次讨论课[8]。
更为重要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并非只是齐一而无差异,而是基于个体差异的统一。若将这种主体间的“差异”视作是一种分离关系的话,也就无法实现“人与天地相参”的和谐状态。因为,这与“和谐”相对的“性本恶”来说又是密切相关的。换言之,导致人与自然万物“不和谐”,抑或人对自然役化的根源,就在于人之本性。“性本恶”的本质决定了人总是对美好的事物充满欲望,并按照主观意识对自然加以支配,更无暇顾及自然的规律,甚至会诱发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纷争。故荀子曰:
“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荀子·礼论》)
“礼义”作为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体现,是效法自然的结果,也是万物和谐的基质。所以,先王借助“礼义”制度来克制人的欲望、划分人的职能,这不仅是为了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样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发展。或者说,要想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交融,就必须先要解决人性中普遍存在的“争”和“乱”的难题,也就是要对人的心理情感和生产活动加以引导,才能实现对人格道德和生活需求的超越。从一定意义上讲,荀子并没有无限夸大人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而是通过“礼义”规范来实现人与自然之间对话、沟通、融合的和谐关系,进而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
最佳适应算法BF(Best Fit):在装入货品时装入到最合适这个货品的箱子里,这个箱子不是第一个可装的箱子,而是最合适的。当没有适合该物体的箱子时,打开一个空箱子。
不仅如此,荀子还认识到强有力的礼法制度虽然能够重建均衡稳定的社会秩序,但在执行的过程中势必会造成民众的逆反情绪。对此,他又提出要将“乐”之艺术形式与“礼”之法制原则结合起来,从而突出了“礼乐”功能的重要性。这不仅发挥了音乐调节人欲、陶冶性情的审美功能,也保障了礼法制度在价值判断、规范言行方面的社会功能,故曰:
“鼓,其乐之君邪!故鼓似天,钟似地,磬似水,竽笙箫和筦籥似星辰日月,鞉、柷、拊、鞷、椌、楬似万物。”(《荀子·乐论》)
“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穷本极变,乐之情也;着诚去伪,礼之经也。”(《荀子·乐论》)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荀子·天论》)
易言之,荀子的礼乐之统不仅包含着对自然人性的审美教化,即在人格修养和情感体验方面得以充足的发展;而且包含着对群体和睦的美好希冀,即追求一种自然整体和人类社会和谐一致的理想状态,进而丰富了礼乐的多样化功能。正如李泽厚所说:“中国古代的‘乐’主要并不在要求表现内在的个体情感,它所强调的恰恰是要求呈现外在世界(从天地阴阳到政治人事)的普遍规律,而与情感交流相感应。它追求的是宇宙的秩序、人世的和谐。”[9]而这种“宇宙秩序”和“人世和谐”目标的达成,又始终离不开主客体的交融交彻、共荣共生。因此,荀子关于“礼乐”的审美追求,也是对主体的精神世界与客体的生命世界之间和谐关系的肯定,这种在“美的规律”基础之上建构起来的生态伦理观,与实践美学只强调人的“内在尺度”,而忽略客体“种的尺度”的偏激观点也是不尽相同的。
[8] W.J.T 米歇尔《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P50.
“万物莫形而不见,莫见而不论,莫论而失位。坐于室而见四海,处于今而论久远,疏观万物而知其情,参稽治乱而通其度,经纬天地而材官万物,制割大理,而宇宙里矣。”
(《荀子·解蔽》)
第二,在中国哲学范畴中,人并不是与自然相对的精神实体,更不能抽象地将其概括为理念、精神等。易言之,无论是人的肉体还是人的精神都是自然的一部分,即人与自然万物始终是宇宙整体中的不同组成部分,自然界又是孕育万物生命的母体,是人类实现功能价值与获得生存权利的根本所在,人一旦离开了这个整体,就会失去他作为生命的基本条件。正因如此,荀子认为虽然万事万物都具有特殊的机理功能和自然结构,但是人与自然之间也从来不是谁战胜谁的对抗关系,而是相互依存、须臾难离的整体关系,故曰:“万物同宇而异体”(《荀子·富国》)这种带有价值导向性的宇宙总体意识,也就构成了荀子关于天、地、人三者相参的生态伦理观的基本要素。在他看来,唯有将人与自然万物作为整体来观察,才能摒弃复杂线索的干扰,从根本上把握人类社会和天地自然的运行规律,进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同时共同发展,故荀子提道:
这种由整体影响个体,再由个体组成整体的循环演变过程,也充分展现了荀子伦理观的基本内容和逻辑进程。这既是对人自身生存状态的表征,也是对人与自然的共同性与生命关联性的肯定,并由此反映了人性与物性和谐统一的可能性。诚如李记芬所说:“人的整体发展意识赋予人一种创造性能力,使得人有意识地参与天地自然的大化流行、注意到自然和人类社会在发展上的相互依存和互动。”[10]也就是说,生态伦理观作为人与自然互动共参的产物,在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始终发挥着基础性的指导作用,能够实现自然生态和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
很明显的,这种整体意识是建立在更为广阔的生态诉求之上,生态伦理观作为整体意识的组成部分,两者之间是循环往复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向度的线性关系。在整体意识的指导之下,人类活动的目的也就从对个体的关注扩展到对自然共同体及其所有成员的关怀,从利己的狭隘视角转变到对集体利益的考量,正如荀子所说:
“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荀子·礼论》)
本课题研究方法主要以行动研究法为核心,同时根据需要结合运用文献研究法、调查法、课例研究、案例研究法、经验总结法等多种方法.
“上察于天,下错于地,塞备天地之间,加施万物之上,微而明,短而长,狭而广,神明博大以至约。”(《荀子·王制》)
从最终的施工效果来分析,重锤击实处理之后,路基的承载性能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路基沉降的问题也得到了控制。在该高速公路建设完成投入使用的多年时间内,并未出现路基明显沉降的问题,且路面的平整性非常高,行驶安全性也得到了保证。因为该工程地处于我国的北方地区,存在大量的湿陷性黄土的路基形式,在填筑施工完成之后,要检查排水防护工程是否满足了工程的要求,从而可以确保其施工工程的路基稳定性达到了要求。
由此观之,荀子十分注重对天、地、人三者的客观规律和功能价值的观察和概括,而且只有将三者看作是共荣共生的整体,并能积极地调适三者间平衡发展的存在关系,才可能保证人类社会和自然万物的长久发展。易言之,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生命个体,不仅要掌握充足的自然知识,还要具备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整体意识,即做到应天时、保地利、得人和,才能为自然万物的持续发展提供更大的生存空间,为人类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故曰:“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荀子·王霸》)
对于这种人与自然相互融合的整体关系的认知,美国学者艾文荷(Ivanhoe)也曾提出:“人的价值不仅体现在人能够通过自然来满足自身的生活需求,更体现在人能调适、平衡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实现与天地的相互融合。”[11]所以说,整体意识能够对人的情感体验和道德价值起到决定性作用,人类不能为了实用性目的而去征服、主宰,甚至同化自然,而要不断超越狭隘的自我意识和审美偏好,才能实现世间万物各得其所、各享其乐的理想目标,故曰:“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
第三,生态伦理观又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平等共生的基础之上的,并强调人与自然万物之间是相互关爱、相互责任的平等关系,这与荀子“仁爱万物”的思想内涵也是相契合的。作为对孔子“仁者爱人”和孟子“仁民爱物”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在荀子看来,仁人不仅要敬爱亲人、敬爱百姓,还要敬爱天地万物,也就是要超越历史语境而追求一种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并重的存在关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把人以外的所有生命物体当作活物来对待,而不要把它们当作死的物质世界。”[12]唯有充分尊重和关心生命共同体,对万物取之有时、用之有度,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平共处,彼此发展又无伤害。故曰:
“仁,爱也,故亲。”(《荀子·大略》)
“仁者必敬人”(《荀子·臣道》)
成立于2008年的Susan Brown’s Baby苏珊布朗宝贝是来自美国的高端护肤品牌,专注于婴童的问题肌护理,特别适用于干性肌肤。其产品纯天然、无添加、易吸收,富含初榨的荷荷巴油、辣木油等天然植物精华,对于婴童的肌肤有着极强的保湿、锁水和修复作用,受到了美国好莱坞众多影星的喜爱。
“无所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恢然如天地之苞万物。”(《荀子·非十二子》)
荀子认为,人要始终秉承着对天地万物的敬爱和关怀之心,不能再以自然作为满足自身欲望的工具,而要充分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相互担当,相辅相成的平等对话关系,并由此形成了一种对宇宙生命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关爱和责任。而且,这种强烈的平等观念和公民意识也与奥尔多·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所倡导的生态伦理观如出一辙,即“土地伦理是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征服者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平等的一员。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13]正是基于对人与自然之间相对均衡与对称关系的体识,才凝聚成了荀子对自然整体的统筹与兼顾,并构成了具有进步意义的生态伦理观的哲学基础与逻辑结构。
平等意识作为生态伦理观的核心思想,不仅重新界定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也建构起了一种新的伦理价值观,能够从精神层面对人的思想认识和实践行为加以改造和指导,并且直接体现在人与自然“相持而长”的合作关系当中。在荀子看来,“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也就是说,在人类寻求发展的过程中,不能为了满足私欲而向自然肆意掠夺。相反,我们在考虑自身需求的同时,也要兼顾自然利益,并对自然大地保持适度的敬畏和相应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才能更好地实现人与万物之间平等共处、相互持养的理想目标。
显而易见,荀子对人与自然平衡发展,及其互惠共利关系的追求,也都是出于自身的责任意识和对长远利益的考虑。或者说,他充分认识到了生态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都具有平等的生存权利和内在价值,一旦失去了这种生态伦理意识和爱物思想,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甚至会加剧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诱发一系列的生态危机问题。法国学者菲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就曾告诫人们:“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就在于真正使人类回归责任意识,不仅为了目前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同样也要顾及未来地球上其他生物的命运。”[14]如果说,只是掌握了自然规律和生态知识,并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平衡发展,生态伦理观也就无从谈起。
结 语
综上所述,荀子的“天人之分”思想并不是对传统“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简单否定,他旨在通过对人与自然各自的内在价值和本质属性的辨析,来消解人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的传统神学观念,并重新认识到人的主体性在实践创造中的重要地位,进而在人与自然的双向互动中,寻求两者间的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这与西方“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模式有着根本性差异,其最终目的依旧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他看来,唯有明确了人与自然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融合的存在关系,才能构建起同时包含着人的维度和自然维度的新型合作关系,进而构成了“人与天地相参”的生态伦理观的核心思想。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这种包含着和谐意识、整体意识和平等意识的伦理观的进一步阐释,不仅为当下生态伦理思想体系的建构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为解决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与道德危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依据。
[参 考 文 献]
[1] 张世英.从“万物一体”到“万有相通:构建之中的中国文化新形态[J].南国学术,2015(4):70-77.
[2] 雷毅.生态伦理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208.
[3] 惠吉星.荀子与中国文化[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81.
[4] 赵法生.荀子天论与先秦儒家天人观的转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5):97-106.
[5] 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道篇[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442.
[6] 陈炎,赵玉.儒家的生态观与审美观[J].孔子研究,2006(1):6-13.
[7] 徐恒醇.生态美学[M].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10.
[8] 陈昭瑛.荀子的美学[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6:32.
[9] 李泽厚.华夏美学[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0.
[10] 李记芬.荀子总万物思想的生态伦理价值[J].道德与文明,2016(4):26-33.
[11] IVANHOE. P. J. Early Confucianism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in the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edited by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pp.69-70.
[12] 杜维明.二十一世纪的儒学[M].北京:中华书局,2014:82.
[13]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204.
[14] Félix Guattari. Chaosmosis: an ethico-aesthetic paradigm. Translated by Paul Bains and Julian Pefanis.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1995,pp119-120.
From“SeparationofManandHeaven”to“UnityofManandHeaven” ——A New Discussion on Xunzi’s Ecological Ethics
WANG Zhong-do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Abstract: While criticizing and inheriting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Xunzi proposed to re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eparation of man and heaven”, in which man and heaven are independent but mutually compatible. This not only shakes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heaven”, but also makes the subject 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text where the self-consciousness and dynamic function can be extended and reconstructed. In Xunzi's view, as an individual with instinctive desire and spiritual consciousness, human being is always inseparable from the norms and guidance of “etiquette”, and the support and supply of the nature, that is to say, there is a new ecological eth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other words, Xunzi’s thought of “the separation of man and heaven” is not a simple denial of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man and heaven”, but achieves a higher ecological ethical goal of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heaven and earth” through deeper exploration of “harmony consciousness”, “whole consciousness” and “equal consciousnes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Xunzi; Separation of nature and human; Subjectivity; Ecological ethics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973(2019)03-0018-08
[收稿日期]2018-12-25
[作者简介]王中栋(1992-),男,山东潍坊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美学。
(责任编辑:谢光前)
标签:荀子论文; 人与自然论文; 自然论文; 万物论文; 天人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先秦哲学论文; 儒家论文;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