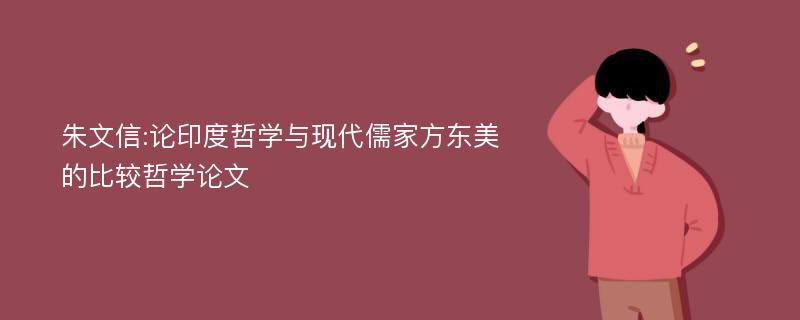
摘 要:方东美是20世纪的中国学者群中,兼备哲学比较的使命与天才,并且探赜索微、妙有深造者,他对印度哲学的判教式结论,见于晚年在辅仁大学的讲课稿。根据其学生黄振华课堂笔记所整理出的《人生哲学讲义》为线索,探究方东美将印度哲学纳入他的智慧架构中的哲学企图,并从中印文明的关系中寻找其中的时代性启示,畅明华严互摄之妙理,兼含爱国保种之微义。
关键词:方东美;印度哲学;文化比较;奥义书;世尊歌
前 言
在中国20世纪的学者群中,作为一代哲人与思想家的方东美先生的世界哲学之眼光与胸廓,就其尚在人世时,就颇有声望。除了为他赢得赞誉的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学术研究外,他的哲学比较精神,与显示出来渊粹的学养与磅礴的才气罕有其匹,如孙智燊所言:
先生幼承家学,尤以博综称,兼中、印、希、欧四大文化传统;统科、哲、艺、教四大学术领域;集儒、道、释、西四大思想源流于一身。如斯大哲,诚所谓硕学通儒,旷世罕覯,宜乎西人之惊诧而致问也。[1](P.482)
惟其如此,方东美在各种国际学术场合当中,使日人铃木大拙、中村元;西人韩路易(Dr. Lewis E. Hahn)、冯·海耶克(Hayek);印人拉达克里希南(Radhakrishnan)等纷纷为之侧目。而就世界哲学的比较而言,方东美意识到印度哲学在整体格局中的重要性,故他晚年在美国讲学时,就留意搜集大量印度的奥义书哲学资料,回台北后还曾向其学生辈的留日学人叶阿月购买《梵和大辞典》准备自学梵文等举动,可以推察他对印度哲学的钻研功夫。我们依照其门人黄振华的讲课笔记整理出一册《人生哲学讲义》,其中方东美以人类四种哲学智慧并峙而出:希腊人的如实慧;欧洲人的方便慧;中国人的平等慧;印度人的功德慧。他说:“印度人在宇宙中为人生造境,结果把宇宙人生的低层境界,打破束缚,将许多差别境界,归到宇宙的高度统一,我现在把它叫做‘功德慧’。”[2](PP.224-225)
此文便结合印度哲学家辨喜、拉达克里希南等古今贤圣,试着诠解方东美之哲学架构中这种特殊意义的“功德慧”,并从中印的哲学文明之比较中,寻找其蕴含的时代意义。此间意义,诚如贯通中西印学问的另一位学者所认定的中国学人之努力方向:“若使大时代降临,人莫我知,无憾也,而我不可以不知人,则广挹世界文教之菁英,集其大成,以陶淑当世而启迪后人,因有望于我中华之士矣。”[3](第8卷,PP.209-210)
一
整体来看,当下的汉语学界对于印度学的研究现状,实不容乐观,可以说,除佛学外,基本是一面倒向了西学的研究;而印度学,甚至整个东方文化的研究都显得人迹稀少,至于纯粹的印度宗教与哲学研究,那更是罕见。这种状况无疑是令人惋惜的。仅少数几位学者研究过古典吠陀哲学、乔荼波陀和商羯罗的吠檀多不二论哲学,余者寥寥。
筚路蓝缕、沉潜印度哲学数十载的前辈学人巫白慧多年前深有感触:“在我国的哲学研究领域里,印度哲学研究,如果不是一个空白,也是未曾引起学术界重视的课题。”[4](P.1)而深谙梵学的徐梵澄先生则一针见血指出:“《吠陀》之教,明著乎韦檀多学,其典籍乃诸奥义书,于是而义理可寻,卓为内学,说者曰:吾将信之。然且疑者曰:谓印度诸宗教各派皆导源于此者,何也?在吾国之明佛乘者,且谓此‘无’宗与彼‘有’宗,相去霄壤,何与耶?……久矣,吾国佛教徒知印度有佛教而无其他。”[5](PP.4-5)
在方东美之前的民国学人中,素以研究印度宗教与哲学著称的几乎没有,唯有三部概论式的著作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梁漱溟出版于1919年的《印度哲学概论》,二是黄忏华出版于1935年的《印度哲学史纲》,三是汤用彤于1945年出版的《印度哲学史略》。后者由重庆独立出版社问世,前两者都是商务印书馆的本子,而且两位作者都是佛门的居士,与汤用彤先生的学术立场略有不同。但是三位都是天资雄出、学养闳深之人,所以虽是概论但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汤用彤,更是学贯中西印,汲绠俱深,丰赡博洽,其清通醇厚之语言往往是寥寥数语,就切中要害,可惜他在印度学方面,远没有如佛学用力之勤,否则必会别开生面。即使是佛门居士黄忏华,也深明印度哲学研究之意义,我们略举其一言,可视为民国学人对于印度哲学总体认识之高度:
在古代印度,为世界开化最早,思想最发达之国,为宗教之国,哲学之国,诗之国,然恒人闻印度哲学一名,多以为即系佛教,他无所有。其实佛教可谓为印度思想之峰极,而未足以概印度思想全体。印度除佛教而外,固犹有林林总总之哲学说,若吠陀哲学,若净行书哲学,若奥义书哲学,若诸派哲学在。此林林总总之哲学说,各振精思,竞标新谛,颇有蔚为大国者。就中若优波尼沙陀(奥义书),其关于人生宇宙深邃而幽玄之观察,令近世西洋伟大之哲学者谢林、叔本华,为之赞叹不置,又非可若一般佛徒,一概抹杀为外道,视为毫无价值也。[6](P.1)
采用SPSS 21.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计数资料以百分数(%)表示,采用x2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而事实上,方东美从一开始也并没有关注印度的主流哲学,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他就以其全球比较哲学的气势,登上了中国的哲学舞台,他青壮年的代表作品《哲学三慧》于比较希腊、欧洲与中国等三种文化智慧时,其哲学的统摄精神之高昂便始于此时,充满了深识睿见:
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形之于业力又称方便巧。中国人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成平等慧。……希腊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方便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中国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归真。[7](PP.111-112)
该文虽短,但凝练而高华,十分精美,誉为20世纪的思想绝唱亦不为过。著名学者贺麟曾就此而赞叹:
方东美先生……博学深思,似乎受尼采的影响较深,然而他并不发挥尼采“权力”的观念,而注重生命、精神和文化。在抗战期中,他住沙坪坝,沉思写著,据说有三四年没有进过一次重庆城。闻他对于人生哲学及知识论皆写有成稿,未曾发表。且据说他未经发表的著作远较他已发表的更为精审。可惜我们现尚没有读到。……他发表了……“哲学三慧”……比较三方的哲学,揭示各自的特质和优胜处,使人用同情了解的态度去分别欣赏体会,既不陷于东西哲学优劣的窠臼,亦不说有先后层次过渡的阶段。于讨论东西哲学文化,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虚怀欣赏的正当态度。[注]见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0页。方东美的学生,在希腊哲学领域广有声誉的著名学者陈康回忆道:“康偶以拙稿《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注释》呈乞教正。先生深喜之,出示其伟著《哲学三慧》。此著非仅义理深邃,文辞亦极古奥,时人善其难解。康竭力钻研,辄生弥坚之感,与众无殊。……康也昏愚,……柏拉图学一科为先生早年学说中之次要一端。康受其业,略解端倪,得以启蒙。胸茅不刈,以后所学,无论何科,皆无由得纳。足以知先生之赐多矣。”参见《方东美先生的哲学》,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9年,第381-382页。
本研究所建立的青皮药材的HPLC指纹图谱,可反映药材样品的特异性和整体性信息。在11个共有峰中,通过与对照品HPLC图谱比对指认出了橙皮苷峰。10批药材样品的相似度评价结果表明,各批药材样品间质量存在差异。各共有峰相对保留时间的RSD差异小,但相对峰面积的RSD相差较大,提示不同产地药材样品的成分虽一致,但含量差异较大,这可能与药材的生长环境、采收季节、加工炮制等因素有关。
在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克里希纳是般度五子的盟友,英雄阿周那的御者,大智大勇。辨喜如是赞美这一位人类的导师,说克里希纳——
可惜,彼时的方东美尚未深究印度哲学,偶尔涉及印度,也是直接以大乘佛学来代替印度哲学了事。而有趣的是,方东美自身的一个志业,即毕生所致力的人生哲学与生命智慧的探究,尤其是在弘扬与阐发中国人“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生命哲学时,其中的一个助因,居然是来自于一位印度的思想家拉达克里希南的挑战。[注]中印二位大哲如是切磋较量实为人间之佳话,此典故可参见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页。
宝钗听罢扑哧一声笑了,这呆子,原是放不下臭架子,那名门望族的书香门第除了腐臭的声名,哪还有一点实质性的东西?忙顺着宝玉的话头说:“谁提起当年贾家不是羡慕得两眼发直——你随便写点回忆录啊,往事钩沉啊什么的,把当初的繁华排场,家庭隐私什么的写写,肯定比卫慧棉棉等美女作家要火爆……你没见报纸上说,六龄童都要出书哎,光版权就卖了十几万……”
而我们知道,印度哲学的根本精神并不在佛学,尤其不在中国化以后之大乘佛学,而是存在于起源夐古绵邈的吠檀多典籍,其中堪谓要典者,即是被诸婆罗门圣者视为“天启圣言”的《梨俱吠陀》(Rigveda)、《奥义书》(Upanishad),以及圣传而来的《梵经》(Brahma Sutras)与《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等诸多经籍。
6、谁真正地知晓?谁又在此宣告?一切从何而来?又因何出现?
故此,他曾如是哀叹:“中国人对于印度哲学的了解,仅限于佛学一部分;中国人了解佛学之时,又值佛教开始衰微之际。印度哲学之传统较中国尤为长远,自西元前三千年即已开始,至少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即已有哲学思想。”[2](P.60)于是,他以自己的卓越见识,为印度哲学的源流正变,理出了一份系谱学的分析,谓为——“一源一支二本三流六派”。[注]参见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第60-62页。方东美为印度哲学的判教结论是:一源,即四吠陀(Vedas);一支,即耆那教(Jainism);二本,即梵书(Brahmanas)与森林书(Aranyakas);三流,即史诗传统、佛学传统与婆罗门传统;六派哲学(Darsana),即1.数论学派(Sāmkhya),2.瑜伽学派(Yoga),3.胜论学派正理学派(Nyāya),5.弥曼差学派(Mīmāmsā),6.吠檀多学派(Vedānta)。
《人生哲学讲义》这份讲课稿虽谓简略,亦可称作统领,其中可以窥见晚年的方东美对同为东方古学的印度哲学源流有了相当系统的了解与把握。可惜年寿不永,未能深入细化之,实有遗珠之慨。他逝世之前,还有一部极重要的哲学提纲,名为《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的遗稿,不少地方皆涉及印度的哲学智慧。[注]参见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孙智燊译,第5页。“其规模擘划之深弘瑰玮,系统条理之缜密周延,睿见洞识之精辟圆明,与夫境界气象之崇高华严等,实在令人激赏嗟叹。盱衡今世,岂数覯哉!西哲中无斯比也;日、印诸贤,殆亦难能。”
二
3、起初,天地间一片混沌;没有明显之界限,宇宙一片汪洋。被虚无所覆盖的生命力,由于热能的缘故开始苏醒。
2)任务规划。利用Qt的信号槽机制和事件类QEvent,处理软件内部的消息,从而协调各子程序的关系,实现任务规划。
印度哲学的起点,实自《梨俱吠陀》开始,它虽是印度上古神话诗的合编,但在印度古文化中地位极尊,誉为“天启圣典”(sruti),如梵学家徐梵澄先生所言:“印度之第一书,《黎俱吠陀》也。为祷颂天神之诗。凡十轮,或计千十七篇,或计千二十八篇。制作远在公元前千余年。五印学者至今宗之。传统谓其出自天界,天神假‘仙人’之口而传之。”[注]参见孙波编《徐梵澄文集》第4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51页。就我们今天来说,其重要性尤在于,里面的很多诗篇构成了印度哲学的第一源头,譬如第10卷所收录的五首关于宇宙源起与造物的赞歌(Sukta),即:1、《造一切主歌》(Visvakarman Sukta);2、《祈祷主歌》(Brahmanaspati Sukta);3、《生主歌》(Prajapatya Sukta);4、《原人歌》(Purusa Sukta);5、《无有歌》(Nasadasiya Sukta)。其中代表了印度玄学思想巅峰的《原人歌》一诗的哲学意义,可参见朱文信《原人四足与玄之又玄》,《哲学与文化月刊》(台北),2014年第4期。方东美于研习奥义书哲学之际,关注到其中的《无有歌》(Nasada-asiya sukta),这也是《梨俱吠陀》第10卷里面最富有哲学意味的诗歌之一。英国学者L.贝克曾藉一代印度学名宿马克斯·缪勒(Max Müller)的话,评价了该诗歌,说道:“无论《梨俱卷》的编纂结集完成于哪个年代,但在此之前,人们已经确信有,而且只有一个神,这个神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远远超越于一切条件、超越于人的一切有局限的自然本性之上。……这首诗构想了一个不存在人格化的神的时代,或者毋宁说是后来的人格化的神还没有由超越于一切有限的原因或语言的绝对实在而创化出来的时代。这古老的神祇,比我们所能设想的任何或生或死的状态都更古老,并超越其上。这一概念实在深奥难解、令人惊奇、令人钦佩。由此可以看到,那位能如此反思并表述这一神的概念的古代圣贤,一定是在形而上学领域之中走得很远很远了。”[8](PP.18-20)
该首《无有歌》的全文为:
综上所述,成都市的会展旅游行业顺应着时代的发展,正在逐步壮大。在此过程中,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不足。会展旅游行业想要得以顺利的发展,就要以游客为中心,以提升游客的感知价值为宗旨,在营销模式上超越传统,突破创新,促使会展旅游行业的整体进步。
1、彼时,既没有存在,也没有非存在,地无界、天无边。是什么扰乱了这一切?在哪儿?又在谁的护佑之下?难道水真的深不见底吗?
2、彼时,无所谓死亡,无所谓永生,黑夜与白天一样,无有区别。那位唯一者(tad ekam)凭自己的本能,平稳呼吸,除此之外,再无别物。
从方东美留下来的课堂笔录稿《人生哲学讲义》中,我们可以见出,他曾举其荦荦大端,以三分法来划定印度哲学:1、奥义书精神;2、佛教精神;3、世尊歌[注]《世尊歌》是方东美依照古译方式翻译“Bhagavad Gita”,现通常译为《薄伽梵歌》,本文行文时涉及方东美及著作中的内容采用《世尊歌》之译名,其余则以通行的《薄伽梵歌》为名。精神。除了“佛教精神”不是印度的主流哲学外,余两者正是印度哲学之正宗圭臬,诸宗各派之学理精义皆导源于斯、发端于斯。故我们这里主要以方东美所提到的此二者为主来展开论述。
建议:不建议术前长时间的禁食禁饮。术前无胃肠动力障碍或肠梗阻的患者,麻醉前8 h禁食高脂高蛋白食物,麻醉前6 h禁食固体食物,麻醉前2 h可口服300 mL以内的清流质。
4、起初,爱欲出现于其上,它是心识最初的萌芽。智者以觉性于心中探索,“有”的联系在“无”中被发现。
5、智者的绳尺伸展过去,有在下者?有在上者?那里有持种子者,也有力量。自力在下,伸展在上。
综上所述,在白内障小切口手法超乳术中予以患者优质护理,可缩短手术时间,优化视力恢复程度,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提升护理满意度,效果可观。
7、这个创造物是如何产生的?或许它创造了自身,或许它没有这样做;在最高天俯视的那一位,只有祂知道;或许祂也不清楚。[注]关于《无有歌》的哲学解析,可以参见《黎俱吠陀的几首哲学赞歌新解》中的译文,载季羡林《季羡林全集》第10卷,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363页;也可以参考印度近代圣者辨喜尊者(Swami Vivekananda)的译文,TheCompleteWorksofSwamiVivekananda, Kolkata: Advaita Ashrama,2005 Vol.Ⅱ,p. 203,其一个节译为:“这一切根基于何处?那时,既无‘无’(asat),也无‘有’(sat)。既无天空,也无其上的天界。何物在来回转换?在何处,在谁的庇护下?那时,既无死,亦无生;无昼与夜的迹象,风不吹拂。独一之彼(tad ekam)自行呼吸。在它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泰初,黑暗掩于黑暗之中。所有这一些都是无法识别的洪水。”
一日,灯草老爹来找琵琶仙。灯草老爹是张乾的结义兄弟,在河东烧窑。几天前,汉奸刁德恒带着保安队,耀武扬威地找到河东,限他五天之内烧好三窑瓦。“烧好了,皇军有赏;若有半点闪失,提头来见!”灯草老爹是个怕事的人,当下就满口答应了。场子里备有几垅干瓦坯子,烧三孔不成问题。
而方东美也专门用古体诗亲自译过一遍,其诗则为:
1、太初无有,有无兼无,大气未形,三光未舒。包裹天地者谁乎?万有依止何所?安抚之者谁欤?淼淼洋洋,深叵测诸!
2、太初冥无,无有生死,白昼玄夜,形畔未起,太一(tad ekam)噫气,块然独峙,简此他求,他惟是此。
彼一不动而速于心,诸天所不达兮,居前逦迤。彼止而越乎奔驰者兮,彼中生命之主始立储水。彼动作兮彼休,彼在远兮又迩;彼居群有兮内中,彼亦于群有兮外止。[3](第15卷,P.458)
由于语言的有限性,无法涉入对最高实在的描述,于是,便有了印度宗教与哲学传统当中的“圣默然”,有了另外一种遮诠法(佛教里也常用的):“不是他,不是他”(Neti,Neti)。这种遮诠思维影响到了后来的吠檀多哲学,即以“奥义书”为代表的诸多典籍,成为其极重要的一个精神之源。譬如,在《广林奥义书》(Brihadaranyaka Upanishad)(Ⅲ.8:8)中云:
4、俶真杳杳,泊兮初兆;欲念生起,心胎所肇;圣智陶情,穷搜幼渺,万有空冥,渊玄难讨。
选取该院收治的90例糖尿病患者,所有患者均符合WHO糖尿病诊断标准,排除器质性疾病及非内分泌因素所引起的糖尿病患者,90例患者及其家属均对该研究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按照随机分组原则,将其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45例;对照组男25例,女 20 例,年龄 43~76 岁,平均年龄(59.5±6.3)岁,糖尿病类型:23例为I型糖尿病,22例为2型糖尿病;观察组男24例,女 21例,年龄 41~76岁,平均年龄(58.5±6.1)岁,糖尿病类型:21例为I型糖尿病,24例为2型糖尿病;两组患者性别、年龄、糖尿病类型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5、神火飏烨,洞玄烛幽,上彻九霄,下贯九邱;怳惚微茫,妙绪谁抽。生养大力,磅礴周流,形气因倚,功能不休。
公民性:通过问卷中“您对地方人大的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您在上一次的居民委员会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您对居民委员会日常工作和决策的关注程度是怎样的”和“您在上一次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中有没有投过票”几个变量来研究。每个问题中的回答为“一点也不关注”到“非常关注”五等或“没有”到“自愿”三等。由于有多个题项,因此要进行因子分析,找出其中的主要题项,拟合成一个新的变量——公民性。
6、知者伊谁,谁能昭示,宇宙生成,何缘何自。
7、神灵未起,谁畀真智,有作无作,两悬疑义,真宰高明,知之也未。[9](PP.234-235)
这首深获方东美喜爱的《无有歌》,起乎太古,发乎初民,它追思宇宙的肇因,或诸神的起源,却隐含着极深沉的哲学性追问:“实在(Reality)究竟是什么,我们能否理解它,并如何获得这种真理性的洞见?”
此哲学诗对宇宙与存在界的图景有整体的直觉;当然,这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的思辨,毋宁说是一种目击而道存的神秘经验,这就构成了印度文化最基本的特性:天启(sruti)。其中的一个关钥,即在“太一”(tad ekam),或“彼一”(that One)一词,它的出现,意味着东方哲学中至为深邃的本体论,或形上学的源头已经被印度先哲开启出来,直指那最高的“实在”(the Real)。[注]或曰绝对者(the Absolute)。在后来的哲学发展中,此概念虽慢慢被另一个重要概念“梵”(Brahman)所取代,但其影响力甚大。与“梵”一样——“(彼一)的这种惟一性是如此地彻底,以至于任何的属性与特征都被超越;即在此既不可言说、亦不可思议的过程中,‘目击’了全部的存在(有)与非存在(无)。” TheVedictExperience,trans.by Raimundo Panikkar,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Publishers,1977,p. 55.
中国的神话学学者丁山先生曾写有一篇杰出鸿文《吴回考》,在该文中,他将吠陀文献中的《无有歌》与屈原的《天问》加以比较,丁山先生指出:“但考《天问》原文,自天地开辟,问到堵敖以不长,文章风趣,极似《吠陀典》后之《古谭史话》(Itihasa-Purana);其言宇宙进化程序,则又极似《梨俱吠陀》所附《创造赞歌》。《赞歌》分为五篇:一曰《无有歌》,二曰《生主歌》,三曰《造一切歌》,四曰《祈祷歌》,五曰《原人歌》。”[10](PP. 425-426)而“太一”在先秦儒道哲学中颇为常见,如庄子在《天下篇》里概括老子之哲学时云:“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 [11](P. 1337)此处的“无”、“有”与“太一”,跟《无有歌》中的“无”(asat)、“有”(sat)与“彼一”(tad ekam)确实有很强的可比性。最近有青年学者徐达斯结合郭店楚简的《太一生水》、楚帛书《创世篇》与印度的《摩诃那罗衍那奥义书》的比较,试着探讨“彼一”或“太一”,作为先于“有无”之界域的至高存在的真实神话身份。[注]参见徐达斯《上帝的基因》,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219、258页。徐达斯利用自己对马王堆帛书的解析,认为远古华夏神话里面可能存在两个“太一”:一是藏于雷泽的太一;另一个则是高踞宇宙之巅的太一。前者应是造物主伏羲,对应的是印度吠陀神话里的毗湿奴;后者是北极紫微宫的伏羲,对应的是吠陀神话里的至尊主克利希那。需要注意的是,两者皆为人格神。“超出这个展示和不展示的物质,还有一个永恒的、不展示的自然。它至高无上,永不毁灭。当这个世界里的一切都被毁灭时,那个永恒的自然依然存在着。那个被吠檀多主义者描述为是不展示和绝无错误的自然,那个被称为至高无上的目的地,那个到达后永不返回的地方,就是我至高无上的住所。”《薄伽梵歌》(8:20-21)与(10:2),参见维亚萨《薄伽梵歌》,帕布帕德英译,嘉娜娃中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4、186页。
方东美的比较之结论是:
此不可言说之境,印度人说是“证”(忘言)。反之,真正能体验大梵的人,知道大梵之不可说,故反而自认不能设想大梵。老子说:“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亦是此意。又庄子所谓“道”,即印度人所谓Tad ekam。语言、文字、思想,都是主客对立的,而失去绝对性,只要一说便是如此,故不可说。[2](P.189)
由此可见,今人眼中人工智能和人的不同,和时人眼中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其实并无性质上的差异:他们都被认为具有本质上的、根本能力上的差异,故所具有的法律人格自然也应有所区别。但正如约翰·穆勒在那个年代便已意识到的一样,这些被称为女子气质的东西其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注][英]玛格丽特·沃特斯:《女权主义简史》,第76—77页。按此观点,上述所谓本质差异本身便是建构出来的,建基于此的法律人格差别自然也是如此。女性的法律人格在日后的发展,也显示出这一点:到了今天,我们至少在理论上承认了女性和男性之间并无本质不同,故也应具有同等的法律人格。
伽尔吉啊,婆罗门们所说的这个不灭者不粗,不细,不短,不长,不红,不湿,无影,无暗,无风,无空间,无接触,无味,无香,无眼,无耳,无语,无思想,无光热,无气息,无嘴,无量,无内,无外。它不吃任何东西,任何东西也不吃它。[12](P. 65)
根据印度学者斯瓦米·尼哈拉南达(Swami Nikhilananda)的解释,“奥义书”(Upanishad)一词来自词根“sad”,加上“upa”和“ni”。“Upa”的意思是接近、靠近,“ni”的意思是整体、整个。“Sad”的意思就是松开、达到寂灭。“Upanishad”这个词的意思就是:从一位胜任的精神导师那里,传授至上知识,使得学生藉由认识至上自我(Self),完全摧毁无明,从此世的束缚中解脱。 “奥义书”,之所以又名“吠檀多”(Vedanta),即意味着吠陀(Veda)神话时代的终结,其义理之弘富深邃,最终成为后世诸宗各派之祖的奥意出现。这是印度哲学的一大枢纽,上窥下视,莫不通畅条达,而印度文化之纲领,即不二论哲学的发轫,正在乎此间得以立其大端。譬如,在这部伟大的《广林奥义书》中,便出现了最伟大的圣言之一:
确实,在太初,这个世界唯有梵。它只知道自己:我是梵(Aham Brahmasmi)。因此,它成为这一切。众天神中,凡觉悟者便成为它,众仙人也是如此。人类也是如此。[注]参见黄宝生译《奥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9页。所有奥义书中最根本的义理,可以浓缩为如下四句圣言(Mahavyaka):1、Prajnanam Brahma (《爱多列雅奥义书》Ⅴ.3)。字面含义是:“觉知是梵”;2、Tat Tvam Asi(《唱赞奥义书》Ⅵ. X.3)。字面含义是:“你是那”;3、Aham Brahmasmi (《广林奥义书》Ⅰ.ⅳ. 10)。字面含义是:“我是梵”;4、Ayam Atma Brahma (《唵声奥义书》Ⅰ.2 )字面含义是:“这个阿特曼是梵”。
梵文中,有一个奇妙的语辞,唤作“不可思议”(Acintya),它被西班牙的印度学家潘尼卡注意到。而在中国哲学元典里,《老子》有“众妙之门”云云,直接谓为“玄之又玄”;《周易》末卦有言:“物不可穷也,故受之以未济,终焉。” [13](P.399)似乎皆在一起说明,无论人类如何努力,某些本质部位恒处人类的知解力之外,是绝然而非透明的,故其末卦为“未济”,俾令整个存在系统永呈开放与生生之状态,此颇可印证《周易》的“物不可穷”之真义。
故而印度最伟大的七贤之一的极裕仙人(Vasishta)对弟子罗摩说道:
通过在万物中运用“不是他,不是他”的遮诠法去消减,最后,那无法消去的,就是那至尊的实在;然后思索,“我就是他”,于是,便得着了最终的圆满与喜乐。[注]VasishtaYogasara,Ⅹ.Tamil Nadu, Ramanan Ashram,2005,p. 34.
这里,圣者极裕仙人已经将遮诠与表诠、默观与圣言加以综合性的圆成,构成了印度人最高的生命境界。
《无有歌》中的“既没有存在(sat),也没有非存在(asat)”,即方东美的“太初无有,有无兼无”当中的“有”与“无”这两个观念,后来成就了印度宗教与哲学之两翼,也是区别正统与非正统两大精神体系之分野:一是“常见”,一是“断见”,前者肯定一个永恒的实在,后者否定存有一个永恒的实体;前者代表着六派哲学等主流的印度哲学,而后者则是非正统派的耆那教、佛教、顺世论等哲学思想。耐人寻味的是,《无有歌》本身却是以“彼一”为实在之道枢,并没有将“有无、常断”加以对立。“如果我们要谈论存在(sat)和非存在(asat),那么我们必须认识到存在和非存在,既不对立也不互相矛盾。这两个词不可还原为抽象的表达‘A和非A’,因为非存在的非并不像非A是对A的否定一样,是对存在的否定。如果全部的存在都在存在一边,甚至否定也在这一边,那么暗含在非存在中的‘否定’就不是一种否定,因为否定已属于存在。”[注]参见雷蒙·潘尼卡《看不见的和谐》,王志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页。这种表述非有非无、非断非常的“彼一”之状态,在奥义书中甚多,譬如《白骡氏奥义书》(1:8)云:“变者非变者,显者非显者,宇宙此合成,伊莎能负荷。人若未知彼,是受者犹缚;人而知此神,缠网尽除脱。”孙波编《徐梵澄文集》第15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344页。非存在不能否定,因为否定的对象必须存在,至多是未被言说。所以,就有继承此一传统的《唱赞奥义书》试图圆融地呈现实在界的有无二维的努力,在该奥义书中:
此一处云:“最初,这个世界只是不存在。然后,它变成存在。它发展,变成卵。躺了一年,它裂开。卵壳分成两半,一半是银,一半是金。”[12](P.162)
彼一处云:“好儿子,最初只有存在,独一无二。而有些人说,最初只有不存在,独一无二;从不存在产生存在。这怎么可能呢?好儿子,怎么会从不存在产生存在呢?好儿子,最初确实是只有存在,独一无二。”[12](P.190)
这部奥义书就存在与非存在,即有与无间的语言如此之摇摆,非圣者书写的迷糊,其实是试图以有限之语言,来探寻到无限的超然之实体,以表述那非有非无、非断非常的“彼一”或“太一”之状态,在“奥义书”中所在甚多,譬如《伊萨奥义书》:
3、暗昧暗昧,幽藏暗昧;泵泉波谲,渍乎天地;浑沦含和,太一解际,内力自蒸,玄同出异。
换一句话来讲,即“存在”与“不存在”、“有”与“无”等概念本身远不足以穷尽那个超越言语思量、非可思议的“彼一”。它与中国的道家形上学颇有相同之处,譬如老子《道德经》的首章所谓的“玄之又玄”,譬如庄子《齐物论》中,得其环中,以应无穷的“道枢”,我们会发现,中印的哲学精神有惊人的相似。它们都摆明了“有”与“无”只是“彼一”,或曰“道体”的双重呈现,都来自于那绝对的“实在”,印度人唤作彼一,或梵;而中国人唤作太一,或道。故《道德经》的话可以作为总括:“二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14](P.1)这或许就是东方哲学中至为深邃的非二元论,或称不二论精神的圆满表达。而方东美对此深有领会:
依此来看,我们可以说,那个神奇世界是the world of mystery(神秘奥妙的世界),并且不只是一度的mystery,所以我上一次曾杜撰了一个名词,叫做the world of mysteriously mysterious mystery(玄之又玄的世界),这不是理性所能解释的。……没有任何人敢说对于那世界的秘密可以看透,它的秘密总是有很深的层次,一层深似一层,向后追求去,还是秘密,秘密之后还有秘密……人面临了那个世界,是无法自以为骄傲的,而处处发现自己是:一个有限的存有,面临了无限,面临了玄之又玄的神奇世界。[15](P.88)
根据医学临床经验,一旦肺癌的临床症状表现出来,治愈率就非常低了,因此在尽早期检测出相关指标并进行预测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已检测到的肺结节中仅有少数属于恶性结节,良性结节占绝大多数,因而如何对检测出的结节进行分类又对研究人员提出了新的挑战。尤其是如何准确、快速和方便地检测与识别早期肺癌结节是目前的研究重点与难点。
可见,这是古今圣贤共同默认的一种知识,它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最高的整体觉知。《薄伽梵歌》里边所表现出来的、涵纳四瑜伽于一体的雄浑浩荡的胸襟就是直接继承这种堂庑闳大、刚健中正的平衡智慧的衣钵,可惜后来没有很好地加以继承与发展,几代印度先知试图使哲学的智慧回拨至古典奥义书精神的努力至今见效甚微。
在众多的奥义书中,这个绝对的实体,最为普遍的名字当属“Brahman”,也就是“梵”。它有两面,一面为无德之梵(Nirguna Brahman),一面为有德之梵(Saguna Brahman);前者不可描述、不可思议,后者可描述、可思议。[2](PP.188-190)而最代表梵的象征词,结果印度人发明了宇宙圣音“OM”(唵)。方东美亦早就注意到此一神圣的音节:
我们晓得在印度的《奥义书》里面有许多开头就是“OM”,发出这么一个声音,这个“OM”在梵文里面,代表一切一切的秘密。[16](P.75)
OM的神圣性藏在一部极重要的《蛙氏奥义书》(Mandukya Upanishad)里,所谓,太初有音,其音为唵:
唵(OM)这个音节是所有这一切。细言之,即: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只是唵(OM)这个音节。再细言之,超越这三时的其他一切,也只是唵(OM)这个音节。因为所有这一切,是梵。唵即梵,我们在世间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梵,我们在世间无法看到的一切,也是梵。这自我就是梵。[注]Swami Lokeswarananda,MandukyaUpanishad, Calcutta:Ramakrishna Mission Institute of Culture,1995. p.6-8.亦可参见黄宝生译《奥义书》,第306页。
首先,印度人对于声音的探讨有专门的圣典《弥曼差经》,相信圣音的常住,故有声之实在论倾向:“(声)确实是常住的。因为(它的)显现(可达到)使人(知道其意义的)目的。”[注]参见《弥曼差经》第1卷第1章18节,载姚卫群译《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20页。
其次,他们相信,对于表达不可思议的梵而言,存在界的这一个“唵”音,最为准确地表达了梵的大全,梵的无所不在、无物不是的整体观,方东美按照印度的神话哲学,直接将该圣音而“唵”(OM),即A-U-M做了对应,如此解析:
A =Brahman (Creator) 生
U =Visnu (Preserver) 住
M =Siva (Destroyer) 异、灭[2](P.191)
于是,三个子音代表了生住异灭,再加上合音之余的无限沉默,就构成了四个位置,所谓“自我四位”。为了具体说明这一点,方东美利用《蛙氏奥义书》描述了四种精神状态,即醒位、梦位、睡位和第四位:
1.Buddhanta Atman 醒位
1)振动流化床能量传播行为研究。振动和气流向床层内输入能量,使原本密集的颗粒获得松散,床层呈现不同的结构和运动形态,发生离析或混合等流化行为。振动流化床能量的传播行为研究是建立振动流化床动力学模型的首要任务。
2.Svapnanta Atman 梦位
3.Samprasada Atman 熟眠(无梦位)
4.Mrta Atman 死位或
Culturtha Atman 大觉位[注]关于“四位五藏”的诠解,可以参见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第192-194页。
而在《蛙氏奥义书》中,“唵”(AUM)正好与之一一对应,醒位,即Buddhanta Atman,对应A,叫做“Vaisvanara”;梦位,即Svapnanta Atman,对应U,叫做“Taijasa”;睡位,即Samprasada Atman对应M,叫做“Prajna”;而第四位即Culturtha Atman,对应着永恒的沉默,即“Turiya”,而这样,就把存在界能够描述的任何一种生命状态,皆纳入了其中,再无遗漏。在吠檀多哲学家乔荼波陀那里,便有了不二论的发挥,直接影响了一代雄才商羯罗大师的崛起,甚至影响了佛教的命运。
这里,第四位(Turiya)与方东美喜欢探究的圣默然有关,这涉入了解脱之境,只能以虚灵相冥契,正如潘尼卡所云:“我们无法谈论真正的沉默,就如我们不可能手持电筒寻找黑暗。谈论沉默而不摧毁它,这是不可能的。”[17](P.71)所以,神圣的沉默便构成了对待实在的态度,这也是瑜伽精神的联接所发生的最高的经验,作为大我Brahman与作为小我的Atman合而为一了,这即是“彼即尔”(Tat tvam asi)。印度哲学里面的不二论精神之梁柱,存在界的统一性就在此间发生,一切皆是同一位:太一,或梵。是这个太一在支撑着所有这一切,正如奥义书所云:诸世界交相汇聚,皆交织于这个唯一的Brahman。[注]《广林奥义书》3:8:11。参见闻中《梵·吠檀多·瑜伽——印度哲学家辨喜思想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第29页。“我们不能通过辨证的理解模式理解圣言与沉默。只有通过让我们的言、我们的展示、我们的生活、存在(即我们之所是者)的启示(圣像)、精神和物质重新沉入其源泉,作为源泉的沉默才会被我们所理解。”见雷蒙·潘尼卡《看不见的和谐》,第76页。此属于非辨证的直觉性洞见的结果。而在方东美对印度哲学的判教当中,他曾列出一个图表,[2](P.195)直接将第四位的Turiya,与表示最高梵乐的Ananda对应了起来,指向了解脱之境界,这意味深长,亦可以获知他对印度慧识的深度。
三
这种对最高实在的默观与冥想,直接导源于印度文化所追求的解脱思想,故而也造成了彼岸精神过于发皇,走向喜马拉雅山与遍及次大陆各处的森林修行之现象。虽然高明,但其精神与世间法毕竟有悖。故而当充满刚健之气的《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的行动精神出现在世间,登上了哲学舞台,令人神气为之一振。可以这么讲,只要有行动瑜伽存在,印度就绝不会被人们误解为厌世主义与悲观思想的渊薮。方东美在《人生哲学讲义》一书中介绍道:“《世尊歌》(Bhagavad Gita)系《摩诃婆罗多》(Mahabbharatha)节本,它只是把Kuru战场当做符号,而把战场变成道场。……直至今日,印度之印度教徒奉此书为圣经。”[注]见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第210-211页。正如方东美所言,《薄伽梵歌》原属印度最浩大的史诗《摩诃婆罗多》第6篇“毗湿摩篇”的一部分。该歌共18章,近700来个诗节。至今还是印度人早晚课诵的经典,在他们心目中,其地位丝毫不亚于基督教的《新约》或“福音书”。于是,印度教最重要的神明克里希纳也就出现在了印度的文化史当中。
克里希纳(Krshna),名字意思是黑色,佛教旧译为黑天。他是印度神话中婆苏提婆和提婆吉之子,大神毗湿奴的第八个化身,印度教诸神中最广受崇拜的一位神祇,是诸神之首,世界之主。他吹着笛子,有着孔雀羽毛,浑身充满魅力。
其实,方东美长年穿梭于世界哲学之林,为了新时代中国哲学的唤醒,故于古今中外的学术脉络当中寻索,深察之,统摄之,最终归旨于中国哲学的精神,以救援时代精神的下坠与浮荡。方东美特别重“智慧”,据为其哲学之典要。因他曾深受佛家玄义之启示,以所有的知识为方便说,为虚妄假立,所以需要在自家的生命中用功,洽化真理,转成智慧,此谓之真如、正知见。虽然这种启示来自于佛家,但方东美以为有普遍意义。
是我所知的最圆满的人,极其殊胜而全面平衡地发展了其大脑、心灵和手臂。在他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布满富有生气的行动,无论是作为君子、战士、首席大臣,还是其它身份,皆是如此。……这种全方位和精彩的行动所兼有的大脑与心灵等特点,在《薄伽梵歌》以及其它经典中随处可见,在过去的五千年,他影响了成千上万人,不管你意识到与否,这人在整个世界范围已经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我认为他具备了完美的神圣品质。[18](PP.103-104)
《薄伽梵歌》是印度最伟大、最恢弘的圣典之一,它闳博无际、神圣圆满;一线拈提,境界全出,实属刚健雄拔的行动哲学,其为气也,至大至刚,含弘稳健,以其直养而无害,堪与吾中华元气最充沛的儒家之精神声气相通。
同时,它也影响了数千年以来的印度各家各派的哲人,他们都需要从此神圣经典中进行注解与引申,获得行动的智慧。方东美所谓的Kuru,全称就是Kuruksetra(俱卢之野)[注]据传说,在俱卢之野进行了长达18天的婆罗多王后代般度族和俱卢族的“大战”,史诗《摩诃婆罗多》由此而得名。《百道梵书》提到人们在俱卢之野祭祀诸神;而《摩诃婆罗多》也称它为“地上的天”,以梵天为首的大神与仙人们每月一次来到该地,并断言俱卢之野的居民死后可直接升天。俱卢之野,也叫正法之地(Dharmaksetra),换言之,发生在俱卢之野的大战象征着人间物欲、权势、邪恶的力量同正法、善良等正义力量之间的较量与搏斗,通过大战,人获得了新生,宇宙秩序得以恢复。因此,此地被称为圣地,此种信仰至今不衰。人们一般认为它位于印度安巴拉和德里之间的平原上。,也叫“正法之地”(Dharmaksetra),涉及“善恶”的正法之田,它既在外,也在内,在外是战场,在内是心田,都与世界与心灵的业力生灭有关,指向了人性得以圆满的达磨法则,所以,这乃是一个道场。
《薄伽梵歌》是最高层次的生命哲学,也是天人大义的至尊教育,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此教育居然是在俱卢之野,在正义与非正义的法的战场上展开。此经典在战场上讲述,意义非常重大,因为一般的经典,都是在菩提树下、在西奈山的山顶,在远离人群、远离喧嚣的种种安定中徐徐展开的。
但是,《薄伽梵歌》恰恰相反,它是在极不安定、极其严酷的战场上,在人性最为脆弱、又最为激烈,甚至充满愚昧、贪婪与嗔恨的丑恶中,诸世界的矛盾最为集中的地方讲述的。这透露出了一个极关健的信息:此经典不是让我们逃离世间,而是让我们在世间战斗,入这个世间去承担。
这个大战有一个背景必须要知道,即众人乃是尝试了所有避开战争的手段,求和无望,各种手段、各种计谋来求和解都尝试过了,一一皆归于失败,那个以难敌为首的百子,连一寸土地都不给坚战等五个兄弟,更不用说五个村庄,或者半个王国了,作为人的尊严,五个兄弟应得的一切权利一毫都没有得着。而作为战争的善恶之正义,更是刹帝利战士无容回避的法性天命之所在。那么,在这个和平无望的时候,人在二元化的世界里,必须要承担职责,维护人性的尊严与世界的正义,战争是最后的选择。所以,战争的发生虽不是完美的解决,但毕竟是直面惨淡、面对问题的解决态度,而不是一种逃避。
然而,在战场上,阿周那软弱了,用感伤主义的方式想退出战争,正因如此,阿周那的迷惑铺天盖地,只想躲开这场战争,他对克里希纳说:
我不希望胜利,克里希纳!也不愿获取王位和幸福,王位、欢乐和生命,对于我们又有什么用处?我希望获得王位、幸福和享乐,正是为了这些列阵以待的人们,而他们却要在战争中丧失财产,还要在血战中捐躯献生。[19](PP.12-13)
对于他邪恶的敌人,即持国的一百个儿子所在的对手,都是自己的亲族,是自己堂兄弟,无论胜败,都将如巨大的海洋一般的忧伤,皆令阿周那终生饮恨。所以,其首章就命名为《阿周那的忧伤瑜伽》(Arjuna Visada Yoga)。在这个世界上,他认为自己宁愿行乞,也决不愿诛戮这些尊长和亲人。所以他说:
如果说持国诸子用武器把我杀死在战场,我将放下武器而不抗争,如此倒觉得坦然舒畅。[19](P.16)
这时,克里希纳叫他不要退缩,这个时候他必须打响这场战斗。《薄伽梵歌》的精髓,总括出来,或许就是这么一句话:“起来吧,王子,请抛弃你的怯懦,抛弃软弱,站起来,去战斗,进到这个火热的、真实的人世的战场,把你所有的观念、所有的美德、所有的宗教与信条,都在其中好好检验一番,好好煅造出有你自己生命气息在场的真精神,真信仰,成为你生命真实的根基!”
但是怎么战,这是克里希纳需要告诉阿周那的,这就是《薄迦梵歌》的行动哲学,此场战斗,它不是为了欲望、权力、财富,即种种人性的贪婪而战,而是为了宇宙的法性、世界的正义、人性的尊严而战。同时,在人类的意义上来讲,他还给了阿周那一个宇宙性的大背景,这样就构建起了整个《薄伽梵歌》一章一章不同的角度,来深入阐明如何对待个体在世界宇宙中安顿的问题,也包括了死亡的问题,所以,涉及的不只是战争本身,而是更大的与生命,与宇宙的一种哲学联系。故而于俱卢之野,展开了室利·克里希纳对英雄阿周那的世间法教育,印度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对话《薄伽梵歌》就在这个战场上诞生了。
故《薄伽梵歌》虽然庞杂,但强调行动,即羯磨瑜伽(Karma Yoga)是其基本精神。印度学者苏克坦卡尔在论及印度的哲学思想与宗教精神的流变时,比较了吠陀诗篇、诸奥义书与《薄伽梵歌》之意义,有一段精彩的概括值得我们参考:
《奥义书》的先哲们在寻求真知的过程中,大胆迈出的第一步,就是把众多的吠陀神综合而为一个绝对的存在。这种综合几乎是与确定最高的神就存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隐秘之处的看法同时发生的。《奥义书》的先哲们奇迹般地把天堂整个儿从九天之外转移到了人自身的心灵之穴来。……人的“心”于是变成了祭坛,变成了圣殿,变成了虔诚的朝圣者的圣地,变成了一个世界,变成了天堂和地狱,一句话,变成了一个宇宙。人只用大胆的一击,就把你曾经把他和他之外的生命拴在一起的不可打破的锁链打了个粉碎。通过他自己的不可征服的意志的指令,人获得了自由,完全独立了,独立于现实之外了。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人成为内向性格的了。而全能的神却成了囚禁在“瑜伽者”心中的一个孤独的囚徒。为了再次使这位心灵内部的统治者积极行动起来,史诗(指《薄伽梵歌》)的作者进行了大胆的实验,把这位国王从他幽暗的住室引到了光天化日之下,让他面对着他的心情忧郁的信徒们,他们正渴望着看见他的面容,听见他的声音,看他在他自己的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从结果来判断,诗人们的这个实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你们一定已经猜测到,这位心灵内部的统治者不是别人,正是高贵的黑天(克里希纳)。[20](PP. 220-221)
所以,古印度之吠檀多三圣典(Prasthanatrayi):1、《奥义书》,2、《梵经》,3、《薄伽梵歌》,其中,以《薄伽梵歌》最是雄健浩大、贯通天人,堪称一体翕辟、同流共运、体大思精之圣典,其推崇的羯磨瑜伽,尤重知行合一,重世界法的实践。其实,《薄伽梵歌》,甚至是整部《摩诃婆罗多》都基于一个基本概念“业力”(Karma),这是行动瑜伽的哲学基础。
根据吠陀的溯源,“业力”一词,来源于“秩序”。在吠陀文化里面,世界秩序叫做“ritam”。上古的印度圣人凭着最高的直觉与启示,认为创造一旦启动,宇宙便开始运行在ritam,即世界秩序的轨道之上。而且,ritam一词,既暗示着创造的基本原理,同时也渗透在创造的整个过程之中。譬如,当它被运用于物理性的宇宙之时,它就是人们熟悉的物质科学;当它被运用于宗教的祭仪之时,它就变成了祭祀(yaina)的原则;当它在人们的社会行为中得到应用时,它就被称为道德与伦理的法则(dharma);而一旦被表达为人类的语言时,它就被称为真理。由此类推,整个宇宙中的一切秩序都是由于ritam的存在。行星运行,自然律则,季节变动,日夜相替,花开稻熟,出生入死,一切的一切,都是由于ritam,即宇宙秩序的存在。
ritam,这一永恒的有序性,它渗透、弥漫在整个宇宙间、整个存在界。但不同于神界的是,它在人间这一个二元性的世界里面,因为自由意志的存在,它会受到程度不一的侵犯,故常常被违背。这种侵犯与违背,就被称做“不义”(adharma)。后来,秩序(ritam)的观念逐渐发展,演变成个人生活中的业力法则,同时也是宇宙存在的因缘共业,人们统称为“因果”,也就是行动的根据。而解脱与救赎之道,正隐藏在对业力法则与因缘共业之生成演化的了解当中,再走向纯粹的宗教生活,避开“不义”(adharma),学会“无我”与“不执”,辅之以“献祭”与“奉爱”,关闭业力的记录器,直至纯然净化,水归河源,俾获最后的自由。
因为行动瑜珈的基础,就是因果法,业报律。所以人们的每一个行为,要么是设置了一种障碍,要么是清除的一种障碍。当下生活中的每一次行动,使我们或更惨(bitter)或更好(better);每一个问题,使我们或造就自己(make us)或摧毁自己(break us);而每一个选择,则要么使我们成为受害者(victims),要么使我们胜出,成为得胜者(victorious)。为此,只有借着自觉的行动,来救赎出自己最后的自由。
于是,行动就充满了责任、充满了尊严。一个人在没有外在的神性救赎的境况中,他救赎出他自己。这就源于《薄伽梵歌》所传达出来的健动不息、雄浑浩荡的瑜伽精神,它与力量,与创造性联结,而与悲观无为的怯懦,与软弱势如水火。 这是入世之正道法,深深符契中国以乾元精神为基础的原儒精神,故而深受方东美的喜爱。在印度,它还代表着由“梵” 这一个实体所支撑着的存在,即羯磨瑜伽的精神,已经融入了远古的“彼一”(Tad ekam,喻“蓄素守中”)和“律则”(Rita,喻“积健为雄”),藉此却开出了印度人最为刚健的生命哲学。
而且,往深处讲,《薄伽梵歌》的克里希纳与阿周那两人本身,就是一种哲学的象征性存在。阿周那代表了一个道德性的原则,而克里希纳则代表了一个审美性的原则,属于游戏三昧的精神,即Lila的态度。于是,他们一起就构建出了一种非常富有意义的平衡。用另外一种话讲,即以克里希纳的游戏与审美的眼光,宇宙性的整体为背景,然后,以阿周那的道德行为,在世界上的战斗,去尽到他的职份,唯有这样,两者在同时成立的时候,这就对应了《薄伽梵歌》第4章的18节:“见无为于有为,见有为于无为;人中彼则睿智兮,无不为兮彼瑜伽师。”[3](第8卷,PP.40-41)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谁能在力量当中发现自己最安定的平静,又能在平静的深处,找到最强大的力量,这样的人,就是最杰出的行动瑜伽士。”
这样,“Karma”(羯磨)一词所代表的精神,便成就了印度的四大瑜伽系统当中的行动之道,即辨喜尊者认为的工作哲学(unselfish work),也是通往绝对自由与解脱的有效桥梁。方东美以实践行动瑜伽的圣雄甘地为例,说道:
甘地终身服膺之一段话:一切的人要以镇定的精神去行动,放弃一切不正当的欲望,然后才能放弃小我变为大我,与宇宙合一。镇定之人格由二方面养成:(1)婆罗门的大梵精神,故要离欲。(2)要变成圣者,一切烦恼、一切痛苦不伤害他。然后此圣者便无所执……毫无所欲,然后一切百川归海。在这种情形下,人生要行动,但只是为行动而行动,而不望任何的报酬。[注]见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第212页。印度哲学长于形上的玄想,短于此岸的习规,长于出世,短于入世。而行动瑜伽之可贵在于,它为印度的世间法立下了至高的道德律令,且这种非功利、超实用的道德法则正如康德在德语世界里之哲学运思。克里希纳对阿周那的教育是:“因此,您不能有任何迷恋,经常从事应当从事的事业,从事其业而无迷恋的人,方能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薄伽梵歌》Ⅲ:19)这样的瑜伽士,其平稳使得喧嚣的世界无法侵入他的内心。
这种力量与平静、有为与无为平衡的精神,也正是中印哲学禀有的相同义理,即世间法与出世间法的不二性。哲学的实践品格才是哲学的“根本智”、“第一义谛”。诚如方东美所云:“别的学问可能客观,哲学则不然,尤其是东方哲学,东方哲学所讲的智慧是‘内证圣智’,外在的经验和事实只能助其发展。”[注]参见方东美《从比较哲学旷观中国文化里的人与自然》,载《方东美全集》第3卷《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317页。方东美一直不惮于批评西方人之哲学与生活脱节的二元化走势,而对东方哲学善于将智慧渗透至生活与实践层面的精神,颇为自豪与自得,为此,才能外合物境、内证慧知,尽生灵之本份,成为人之至德。
四
由以上可知,《薄伽梵歌》的综合性,正体现在了印度文明中颇罕见的平衡智慧。而其平衡之支点,便是梵,也就是自吠陀时代的哲学而来吠檀多传统,无时不在强调之实在——“彼一”(Tad ekam)。与中国的先秦典籍的功能类似,这种雍雍穆穆的哲学精神也滋养着无数后世的印度哲人,他们藉此行世、并藉此悟道,行在了无比恢弘的“中道”[注]何谓“中道”?“中道”即意味着非内非外,非古非今,不着文字相,不离圣言量。又基于黑格尔之可立为正鹄之言:绝对无,便是绝对有!故“中道”又意味着即内即外,即古即今。易言之,双遣双非,双即双是,此为“道枢”,兼赅有无。老子谓之“道法自然”云者,故云:“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可谓印心于恒道。诸圣慈悲,筑基有术,皆立乎 “中”, 印度著名的《伊萨奥义书》(9-14)如是表达中道,云:“人遵‘无明’兮,入乎冥幽。所乐唯‘明’兮,大暗是投。说唯异乎是兮,从‘明’所由,说异乎是兮,‘无明’所出。——如是闻之哲人,哲人示我兮‘彼一’。人知‘明’与‘无明’兮,于一俱并。以‘无明’而出死兮,以‘明’克享永生。人遵‘无生’兮,入乎冥幽。所乐唯‘生’兮,大暗是投。说唯异乎是兮,从‘生’所由,说异乎是兮,‘无生’所出。——如是闻之哲人,哲人示我兮‘彼一’。人知‘生’与‘灭’兮,于一俱并。以‘灭’而出死兮,以‘生’克享‘永生’。”参见孙波编《徐梵澄文集》第15卷,第460-462页。而中国的《中庸》则如是表达中道,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方东美也概括中国文化以言其旨归,说:“中国慧体为一种充量和谐,交响和谐。慧相为尔我相待,彼是相因,两极相应,内外相符。慧用为创建各种文化价值之标准,所谓同情交感之中道。道不方不隅,不滞不流,无偏无颇,无障无碍,是故谓之‘中’。”并云:“此乃因为中国人深悟大化流衍生生不息,宇宙全局弥漫生命,故能顶天立地,受中以立,然后履中蹈和,正己成物,完成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至德。”参见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13页;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4页。之路上。方东美曾以比较哲学的视角,在东西方哲学史上,本体论涵义各殊的情境下,结合现代西方的历程哲学而评论出两点:
(1)希腊人较为着重“存有”之静止的自立性,印度人与中国人则往往赋予“存有”一种动态流衍的特性;
(2)希腊人深通二分法,遂断言“存有”高居超越界,不与表象相涉;中国人与印度人则相信机体主义的生化历程,使“存有”能够流衍贯注于万事万物。[7](P.282)
与西方人不同的东方哲学,就是对生命境界的实践,最高的境界,在印度文化里,就是Rishi(仙人)、Sadhu(圣者)、Muni(牟尼)等完美人格;在中国文化里则唤作“至人”、“大人”,或“博大真人”等。而譬如“Rishi”,方东美以《卡塔奥义书》(Katha Upanishad)为例,说道:“作为人的圆满典型的Rishis之重要性。‘凡在知识中冥合至高圣灵者,必洋溢着智慧;凡发觉他与灵魂相合齐一者,必与内在自我圆满谐和;凡在心中实现他,必可解脱一切自私欲望;凡在时间万象中体验他,必将获致安详。Rishis,就是那些由各方面上达神明,寻获永恒和平、冥合大化,升入宇宙大生命的人’。”[7](P.292)
方东美论及中国的完美人格时,他说:“假使一个人在他的生活上面的阅历,由物质世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他这样子向上面提升他的生命地位、生命成就、生命价值,到达这个时候,他这个人得以真正像庄子所谓的‘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如此,他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人,也不仅仅是一个艺术家,不仅仅是一个道德人格,而且在他的生命里面各方面的成就都阅历过了,都提升他的精神成就到达一个极高尚的地位。……那是一个真正的大人。”[16](PP.19-20)
可惜的是,在印度文明中,原本于《薄伽梵歌》所呈现出来的刚正精进的“境界论”,被归到了“解脱论”,而且往而不返;“实在论”发展到“宇宙论”那里,则被归为“摩耶论”。
“摩耶”(Maya),即“幻”,在梵文中,它被描述为“aghatana ghatana patiyasi”,意思是“使不可能者成为可能”,这种“摩耶说”受佛教思想影响很大,但是,到了乔荼波陀和商羯罗那里,“摩耶说”才成为印度“不二论”的基本宇宙论,如商羯罗就以“世间如幻,唯梵为真”的绝对一元论出之,以为名色之开展皆是幻境,出于无明,出于邪智,乃为我执和我慢,须以正智正法去祛除之。就摩耶之意义,汤用彤解释道:“如误绳为蛇,误杌为人,误阳焰为楼阁。若精细观察,虚幻自见。全世界仅为幻景。梵如幻术师,自现幻境。然术师本身,并不受其所化幻象之影响。又若幻师用其术化为多形,梵因无明而成为多,亦复如是。”[21](P.168)
尤其是令积健为雄的“羯磨论”可悲地蜕变为“宿命论”,使得印度的刚健有为的行动哲学,陷入了悲观主义。如是种种,其原因足堪我们玩味。
印度文明弃绝离世、道归寂灭的走势,离弃了古典哲学的闳正条达的道路,原因很复杂,争议也多。概而论之,我们以为有如下原因:
第一、早期吠陀圣诗语焉不明,遂造成各自相悖与冲突的信条,俾后世圣者的教义也相互暌离、彼此吊诡;
第二、奥义书的秘传性质也妨碍了中道思想的弘扬,这种秘传传统在印度被唤作“parampara”,相当于基督教的“使徒传系”,如汤用彤所语,“《奥义书》之于婆罗门,乃为教外别传。……必智者乃可知之。其道父仅可传其子,师仅可选授优秀,中枢秘密应不著一字”[21](P.24);
第三、各种圣典都是浓缩的经偈(Sutra),高度凝练,故非有同等秉赋的天才,无法一探究竟,故而造成了哲学的迷途,如方东美所云:“伟大哲学智慧,往往出于绝顶天才。天才本身,神乎其技,每创新义,辄以短简直觉方式发舒名言、隐示至理,不事辛勤立量、译理论效果,致令后人无从体验原有之真实证据,如遇疑谬之处,更难指摘弱点、破除迷惑、转生真理。”此一问题,中西印皆有,不足为异,但在印度尤为明显,包括对佛教经偈的阐释;[7](P.125)
第四、印度民族所处的环境特点造成了避世的条件,其气候炎热、地域广袤,而森林、雪山与高原的密布就为他们提供了一种远离人间的生活方式,身披鹿皮的圣者们一旦体验到参赞天地、彻悟玄理的同时,也常常给了他们耽溺于此一梵乐之境,不理世事,撒手人寰,故泰戈尔把印度文明唤做“森林文明”,与希腊的“城邦文明”,中国的“土地文明”相异。甚至这些行为还获得印度伦理学的支持,被规定到了如《摩奴法典》等影响重大的法论典籍(Dharma-Sastras)里头,赞颂弃绝;
第五、小乘佛教的“涅槃论”之影响,完全舍弃世间法,除了无余涅槃,别无出路,别无解脱。孙智燊评价早期佛教之“解脱观”导致的涅槃趋势可以拿来形容印度文明的基本精神:“由有限趋无限;由有为法趋无为法;由生灭界趋无生灭界;由变易趋永恒;由现象趋本体……等,皆是以‘涅槃境界’为究竟归趋。”[注]参见孙智燊《从大易生生之理看中西印思想》,《孔孟学报》,1982年第43期,第7页。这种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的乔荼波陀、商羯罗等圣者,凡此种种,无俟殚述矣。
古典奥义书与薄伽梵歌里面呈现出来的深闳而肆的中道智慧渐渐破产:
印度方面的二分法则不如此,一经划分,则重心落在法界中,人性上,重心落在智慧方面去,价值落在功德一方去。故印度人走一条鞭之路,一切二分法都走向重心所在的一边。……最重现实的数论派也是着重精神这一边。印度人用二分法改变境界,用出世法去追求此境界,再用涅槃求正果。……印度人舍弃只是“转舍”这方面,舍弃现实世界后,发现神我,不但不向后转,而是精进而又精进,完成宗教生活的最后目的。这是一个估价的问题,精神生命比现实世界一切都宝贵。[2](PP. 231-233)
于是,影响了在世的人们所立下的人生四目标(Purusārtha)的重心所指:财富(artha,利益)、欢愉(Kāma,爱欲)、正义(dharma,法)和解脱(moksa)。前三者很显然是扎根尘世的基本要求,只有第四个,也就是最重要的要求,具有超拔尘世的特质,“解脱”作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他把前三者视为入世法(pravrtti,意为流转),而把“解脱”视为出世法(vivrtti,意为弃绝)。入世法无法解决人生的苦难与存在的非圆满,故有解脱之学说。[22](P. 5)
方东美曾如此总结过:
“印度人在未转变为大乘佛学前,有一段时期,宗教上的热诚,哲学上的智慧,诗的幻想都寄托在超越的世界上,在此时期,印度的历史几乎是空白,一切典章制度,了无可取。”[2](P.232)
所以,方东美说,就宇宙观为代表,像希腊的“原子论”,西洋的“无生论”,近代的“机械论”,印度的“摩耶论”等等,而惟有中国的哲学才是根本的“生命哲学,人类、草木鸟兽虫鱼,乃至山河大地,都是有生命的。宇宙是包罗万象的大生机,都是生命的流行,无一刻不发育创造,无一地不流行贯通”[2](P. 85)。
五
20世纪初,颇有传奇色彩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凯瑟琳(A. Kyeserling)曾漫游世界诸国,并著有一部灵思奔涌、异彩纷呈的《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对东西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比较,他颇有心得,与方东美可谓异国知音,旦暮相遇。曩时凯瑟琳向人们弘扬马鸣之“不住涅槃”的理想,认为惟此一理想方能救世。他说:“我想起了菩萨的一句誓言:‘只要地球上还有一个灵魂未得到拯救,正陷入人世束缚和烦恼之中,我自己就不进入涅槃(不住涅槃)。’我们把菩萨的这一形象同不顾人世现实,只去追求神的知识的贤者形象作一比较,可以看到后者尚未完全超越名称和形式(Nāmarūpa)。……他知道自己的根源在于神灵,但是,他的存在又与所有的存在者紧密相连。因此,他像爱自己那样爱一切存在。” [23](P. 39)而他心目中的理想文化,或曰“不住涅槃”的精神之集中体现者,却正是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真正的伟大性在于她有这样一个显著的特点:认为真理是具体表现在人们的实际生活当中的。孔子学说是很具体的,其理论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是对实际生活和具体现象的抽象表现。”[注]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一位哲学家的旅行日记》中凯瑟琳藉着对马鸣的“随缘真如”与“不变真如”之间的关系评价,也可以启发我们对印度哲学精神流变的一些思考:“马鸣的哲学与古代印度哲学的一般关系,正像黑格尔哲学同巴门尼德、柏格森哲学同斯宾诺莎哲学的关系一样,即,后者的抽象的静止主义哲学被前者的生动活泼的流动主义哲学所取代了。那是以绝对知识的进步为条件的。实际上,古代印度人与大乘佛教的首创者所思考的问题是一致的,只是他们未能适当地表现出来。他们关注于‘生成’的终极意义,但是他们又脱离了‘生成’,反对现象是流动的观点,达到了这样一个理论:认为存在着一种永远的‘有’。而马鸣则完成了后来黑格尔和柏格森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完成的独创性的和同样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工作。他再次提出了被割裂为二的‘有’与‘生成’的关系问题。马鸣认识到,所谓‘有’与‘生成’只不过是同一的绝对对实在的不同方面,因此,形而上学所说的‘有’与生灭变化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在时间中持续状态也就是绝对现实的存在。”Alexander Kyeserling,Trans. by Holroyd Reece,Thetraveldiaryofaphilosopher,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mpany,1925,p.677,p.854-858.参见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9-41页。
而方东美也一直在思考与寻找哲学的药石,以治疗遍处时代的虚无主义与混沌思想之病症,于种种自大自高的科学精神与自抑自卑的宗教氛围的困局中,试图找到最为刚健醇正、最为光明正大的人性论。他如此表达哲学的使命:
哲学之在今世,尚犹有前途否?并世学人颇多疑惑。吾尝遐想过去,觉哲学实为民族文化之中枢。现前种种纵有抛弃智慧、削弱哲学势用之倾向,终亦不能灭绝人类智种,阻遏伟大新颖哲学思想之重光。然则吾又何难据前世之已验,测未来之可能。[7](PP. 125-126)
与凯瑟琳一样,方东美发现此种雅正的人性论就在中国的思想里头。而基于这种哲学之旷观,宇宙非但不虚幻,而且还是一个生命存在的根源性的意义与价值系统。与印度文明的“借有入无”不同,中国的文化贵在“挈幻归真”,故能彼是相因,流衍互润,蔚成同情交感的中道精神,故能淋漓地宣畅生命此在的灿溢精神:
虽同是注重文化的道德价值,但作为宗教文化的印度文化,因为宗教的道德关注彼世,故其对于人生价值的看法,不像中国思想,纯从哲学的基础来考虑,而是掺有宗教的动机。这就使其不能不把人生的归宿置于天国,损及天人合德,人类生命与宇宙生命的同体合流的东方智慧的基本精神。所以,印度文化尚不足以代表东方文化的完美形态,纯正、完美的东方文化,应以中国文化作代表。[24](P. 928)
方东美对于欧洲人崇权尚能、戡天役物之精神早有警惕,而对于印度人的玄想非非、一往不复的危险也深有认知。他之所以推崇中国化之后的大乘佛学,其理由亦在此,在《华严宗哲学》一书中,他说:
从这一个观点上看来,印度的宗教史上,人的失败也仅只是人的精神转变上的失败,他最后仍可以同整个的“大梵天”合而为一,他可以把有限化为无穷。不过我们也可以从这一点上看出,在印度人的精神转变的最后,还受了一种限制,因为他这个大梵天的精神,对整个的现实世界、整个物质世界上面各种形态的转变,他可以不耐烦。而且假使他真正感到不耐烦之后,他可以变做数论派里面的思想,而逃到太空里面去,坐在一个境界里面寂然不动,然后说我是不坏不朽的精神,你们的世界若要变要坏,那是你们的事情,我就在这里看看你们怎么变,变好也不关我的事,变坏也不关我的事。[25](PP. 80-81)
这种溯源逆流的本体披寻之思想用方东美的话说,不妨叫做“无之无化”。我们知道,方东美的人生哲学并非孤立的人性论发挥,而是与其整个哲学体系中的价值论、宇宙论、本体论,甚至超本体论皆环环相扣、息息相关。这里我们不妨藉着本体论的思路,对印度哲学的“无之无化”与中国哲学的“玄之又玄”做一个简明的比较。
按照印度奥义书的最初义理,“彼一”(tad ekam)原本是能够摄一切相及一切相相,赅一切无及一切无无。尤其是加上“彼即汝”的不二论之申义,更可以将吠檀多哲学融贯于实际界,统摄有无,赅遍彼是,此在与彼岸的张力便得以消解,正如我们曾提到的方东美那首著名的《和平颂》一样,深闳而雅正。可是在印度哲学的实际发展中,却常常偏于一端,直探本体幽微之界域,返虚入浑,而未能回光返照于五浊恶世,借有入无,而未得返身而诚,得以无中生有,从而滞留虚寂之中,独尝第四位图利亚(Turiya)之梵乐,此自然不免乎“执著”。故有大乘佛学“破一切相、扫一切空”的革命。
而商羯罗(Sankaracarya)的崛起,虽然重振了印度教与吠檀多哲学,可是天资雄拔的他,年纪轻轻便出家隐迹,尚未用心于世道,便于32岁英年早逝。尤可叹者,他藉着无比的雄辩,一举击垮了盛极一时的大乘佛学,从此法息东移,所谓“智深言妙,遂灭佛法;大法东移,遂成绝响”[26](P. 380)。随着商羯罗的离世,其从佛学里面借来的“幻论”已经没有了最初《薄伽梵歌》里创生万有的能量义。商羯罗说,真理可以被表达为:brahma satyam jaganmithya——即“只有梵是真实的,而这个世界却是虚幻”。[注]参见洛克斯瓦南达《印度生死书》,闻中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58页。商羯罗在《分辨宝鬘》(Vivekachudamani)中说:“彼是唯一者,彼实为众因;无物可比肩,彼乃起无因;彼异于是幻,彼异幻之实,幻实即此世。”(第260偈)Swami Madhavananda, AdiSankaracharya'sVivekachudamani, Advaita Ashram。一言以敝,乔荼波陀、商羯罗一系的哲学所弘扬的“幻论”对印度教之走向无之无化,遗世独立,诚谓为加剧伤害可也。
而印度人的借有入无,甚至无之无化,一探本体幽微之界域。看似与玄远微妙的道家之趋向“玄之又玄”之奥境相同,实则颇不然。老子是“知白守黑、知雄守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中道精神鼎力于斯。而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之“用中”精神尤能体现者当数儒家,故而藉着老子与孔子的关系,开出了儒家的刚健入世并兼有了道家的柔韧之智慧,故云,道家之终,儒家之始:
老子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者,无不为也。是故,反者,道之动——反之于无,而致乎其极,则于一切有界相对存在之诸般限制悉超净尽。就佛家之眼光看来,斯即涅槃界之中国原版,同时又兼为对应真如本体界之绝妙描绘。……道家观待万物,将举凡局限于特殊条件之中始能生发作用者,一律化之为无,“无”也者,实指自然妙饰之无,为绝对之无限,乃是玄之又玄之玄秘,真而又真之真实,现为一具生发万有之发动机。道家之终,儒家之始。与道家适成强烈而尖锐之对照者,厥为儒家之徒,往往从天地开合之“无门关”上脱颖而出,运无入有,以设想万有之灵变生奇,实皆导源于创造赓续、妙用无穷之天道。天德施生,地德成化,非惟不减不灭,且生生不已,寓诸无竟。盖无限之潜能,乃得诸无限之现实。”[1](PP. 31-32)
换言之,道家之中国版的“涅槃论”,或曰“解脱论”,却被儒家返转为现实界的“人间智慧学”。道家之终,即为儒家之始,还意味着以道家奠底的儒家才是醇儒,以阿罗汉为觉体为根源的菩萨道才是此世间永不摇动的梁柱。而中国人的生命智慧,正建基于此人间世,超以象外,却得其环中,无往而不复,存在的意义皆辐辏于当下之基本人性。结合中国之先秦哲学而细言之,亦即建基于周普闳通之皇极(《尚书·洪范》),明几达变之易道(《周易·易大传》),在天地宇宙之间,触境生机,应机对法,兼以化物,一举一动:
一一符合于自然,不教而怡情适意,不言而节概充实,美感起则审美,慧心生则求知,爱情发则慕悦,仁欲作则兼爱,率直淳朴,不以机巧丧其本心,光明莹洁,不以尘浊荡其性灵。此等人达生之情,乐生之趣,原自盎然充满,妙如春日秀树,扶疏茂盛,其于形上之道,形下之器,天运之流行,物理之滋化,人事之演变,虽不立创文字之说,逞胜斗妍,然心性上自有一种妙悟冥解。[27](PP. 9-10)
方东美认为,中国哲学之伟大智慧,其悟道之妙,体易之元,兼墨之爱,会通统贯,原可轰轰烈烈,启发伟大思想,保真持久,光耀民族。却因为种种因由,譬如学术寄于官府,至理隐于故籍,思想未得自由,小智恒得流行,偏偏又匮乏坚贞持恒之素德,不图精审理性之方法。结果导致了四千年来智慧昭明之时少,暗昧锢蔽之日多,遂致文化隳堕,生命沓泄。放眼世界,比勘东西,实会发现,每一种文化与哲学精神,均有优点,亦不能无弊。譬如希腊人之所以逃禅,欧洲人之所以幻化,印度人之所以虚无,中国人之所以穿凿,各有历史根由深藏于民族内心,仅凭自救,或难致果,他山取助,尤为切要。故而生当全球化之今世,他在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时,终生致力于世界哲学之会通,融贯东西,涵摄众家,广大和谐,兼容并包:“吾人寄迹世宙,体时序之创化。……自不能拘墟束缚、回向过去、默守旧闻。是则指点前程,触发新机,光大哲理,事属分内,责无旁贷也已。”[7](P. 126)
所以,我们在这里对方东美的哲学智慧架构的探索,无非也是为了梳理出一个更有意义,更圆满的思想体系,这样,哲学的彼此相生,彼此互润也许就成为可能。而且,我们若按着方东美的思路,也许可以将希腊、欧洲、印度与中国等四大哲学之共慧命厘定为:
希腊人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如实慧演为契理文化,要在援理证真;欧洲人以方便应机,生方便慧,方便巧演为尚能文化,要在驰情入幻;印度人虚灵冥契,现功德慧,功德慧演为解脱文化,要在借有入无,离苦得乐;中国人则以妙性知化,依如实慧,运方便巧,行功德智,成平等慧,平等慧演为妙性文化,要在挈幻归真,时中达变。
结 尾
当今世界,思想与哲学领域的地方主义式偏狭已被证明是危险的。著名学者A.穆尔(Charles A.Moore)[注]查尔斯·穆尔(Charles A.Moore,1901-1967),夏威夷大学教授。生于芝加哥,193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36年受聘到夏威夷大学任教,主持哲学系,使得夏威夷大学成为世界的东西方哲学研究的重镇。他本人也身体力行,是现代东西方文化和哲学比较研究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他注意到了东方哲学的多样性、复杂性和丰富性,并开创性地提出和使用了通过考察“东西方主流倾向和立场”的方式进行哲学比较的研究方法。而“实践”这一概念是穆尔比较研究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他讨论了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比较的途径和观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关于东西哲学差异的重要观点,把当时的东西方相互理解向前推进了一步。其与印度哲学家拉达克里希南合编的《印度哲学原始资料文献选编》(普林斯顿大学出版)成了人们了解印度哲学心灵的重要材料。曾在夏大作为穆尔的门生的著名学者傅伟勋如是评价:“他有极大的胃口吸纳东方思想,而以同情的了解态度寻觅世界各大哲学传统可能会通之处之理,实在难能可贵。他可以说是比较哲学研究领域的极少数开拓者之一。”参见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1页。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经指出,哲学只有成为全球性的,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具有广泛性、综合性,它才能更好地指导人类缔造美好的世界。
而我们以为,就此而论,一代哲人方东美先生堪称当之而无愧。他不是简单的学者,更是一位哲学家,他孜孜不倦、精勤不懈,毕生都在世界哲学多元交汇中寻找,以比较之眼光,试图构建出此时代最圆融的文化精神与生命哲学,但使命与苦难往往并在,故他云:“复兴民族生命,必自引发哲学智慧始,哲学家不幸生于衰世,其精神必须高瞻远瞩,超越时代以拯救时代之隳堕。”[7](P. 117)每一时代,皆是如此,自证慧之营造,虽属变易哲学,却因绝世天才的劳作,基于某种神秘而不可见之永恒哲学,触境生机,从而构成一时代一时代的精神。
参考文献:
[1]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孙智燊译,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 方东美:《人生哲学讲义》,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3] 孙波编:《徐梵澄文集》,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4] 巫白慧:《印度哲学》,上海:东方出版社,2000年。
[5] 徐梵澄译:《五十奥义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6] 黄忏华:《印度哲学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7] 方东美:《生生之德: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8] L.贝克:《东方哲学的故事》,傅永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9] 方东美:《坚白精舍诗集》,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8年。
[10] 丁山:《古代神话与民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11] 王叔岷:《庄子校诠》下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
[12] 黄宝生译:《奥义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
[13]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载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14] 老子:《道德经》,陈忠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
[15]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16] 方东美:《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17] 雷蒙·潘尼卡:《看不见的和谐》,王志成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18] 朱文信:《试论印度宗教哲学家辨喜的行动瑜伽》,《新世纪研究》(台北),2013年第2期。
[19] 张保胜译:《薄伽梵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20] 季羡林、刘安武编:《印度两大史诗评论汇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21] 汤用彤:《印度哲学史略》,载《汤用彤全集》第3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2] 黄宝生译:《摩诃婆罗多》第5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23] 中村元:《比较思想论》,吴震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24] 蒋国保、余秉颐编撰:《方东美学案》,载方克立、李锦全主编:《现代新儒家学案》(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5] 方东美:《华严宗哲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26] 朱文信:《智慧瑜伽:商羯罗的自我知识》,载赵敦华主编:《哲学门》第23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7] 方东美:《科学哲学与人生》,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
OnIndianPhilosophyandComparativePhilosophyofModernConfucianFangDongmei
ZHU Wen-xi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 China Academy of Art, Hangzhou 310002, China)
Abstract: Fang Dongmei is one of the Chinese scholars with profound and subtle exploration in the 20th century who has both the mission and genius of philosophical comparison. His judgmental conclusions on Indian philosophy could be found in his lecture notes a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in his later years. According to his student Huang Zhenhua’s “Lectures on Philosophy of Life” as a clue,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Fang Dongmei’s philosophical attempt to integrate Indian philosophy into his wisdom structure and seek for the enlightenment of the time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Indian civilizations, indicating both the mutual implication of Huayan Sect as well as the subtle meaning of patriotism and seed preservation.
Key words: Fang Dongmei; Indian philosophy; cultural comparison; Upanishad; Bhagavad Gita
中图分类号:B35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9)03-0065-16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9.03.005
收稿日期:2019-01-16
基金项目: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方东美哲学体系中的‘印度智慧’研究”(2014QN022)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朱文信,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先秦哲学与世界宗教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蒋金珅)
标签:印度论文; 哲学论文; 奥义论文; 精神论文; 中国论文; 宗教论文; 亚洲哲学论文; 亚洲各国哲学论文; 印度哲学论文;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论文; 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项目攻关计划青年重点项目“方东美哲学体系中的‘印度智慧’研究”(2014QN022)论文; 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科学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