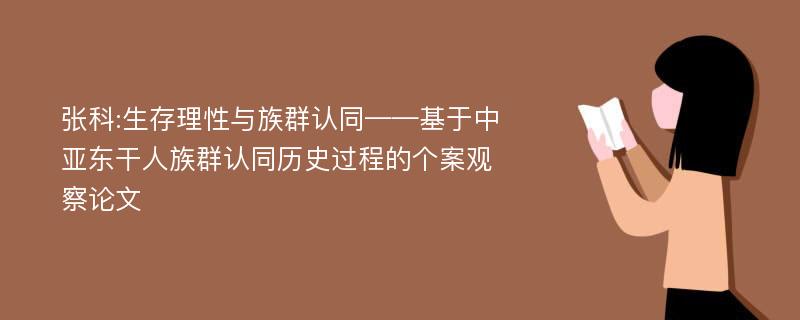
摘 要:中亚东干人是在域外定居民族保持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典型群体。自清朝同治年间迁移至中亚以来,虽然经过了与当地民族一百多年的杂居和相处,但东干人仍然在语言、习俗与生产方式等方面保持了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形成了中亚东干人遥远“故国”的记忆。本文的观察表明,基于同一地缘、亲缘与宗教信仰的“原生情感”构成了东干人族群认同建构的基础;以故土语言、风俗与生活惯习为核心要素的“历史记忆”在日常生活中的不断重复和展演,则成为东干人百年来族群认同维系和延续的保障。东干人逾百年族群认同发生与延续的历史过程显示,对于特定情境中族群认同的考察,不能仅仅将“生存理性”视为单一经济逻辑引导下的行动表达;不能将族群成员“经济人”的面相从日常生活世界中抽离出来作为认同建构的基本要素,而更应该关注族群成员“社会人”与“文化人”的双重面相在族群认同发生与延续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厘清东干人中华民族认同发生与延续的文化机制,有助于为中亚其他族群感知、理解和认同“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一种来自于生活世界的鲜活路径,以及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提供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
关键词:东干人;族群认同;历史过程;生存理性
今散居于中亚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伊塞克湖州二道沟乡、奥什州和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以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回族,前苏联给予的民族名称为东干人,还由于其祖先与中国陕甘地区的回族同源,也称为中亚回族,或者自称为老回、回回、回族。这一群体在各中亚国家属于少数民族,学界关注较多,研究成果丰富。尤对族群、族源认同等问题从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等学科视角加以考察的研究成果也不少。大致可分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早期首领白彦虎的研究,包括其出生时间、籍贯、生平活动、行为评价等。①二是关于东干学的研究。包括东干人的族源、族称问题、族群认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等。②这部分研究成果,既有中国学者的,还有俄罗斯、中亚等国研究者的作品,主要利用人类学和民族学的理念与研究方法,目前已经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国际学”。三是东干人作为中亚回族,其民族文化的形成与中国陕甘地区地域文化及伊斯兰文化之间的关系。该部分主要研究原居于陕甘回族迁居中亚后,如何长久地保存中华传统中自有的文化因素,并利用这种文化来维护新民族共同体的延续与发展。③
“昆北”去声字“字”的唱调(《长生殿·酒楼》【集贤宾】“姓字老樵渔”,776)的唱调。因去声字的调值和字腔的音势是呈状的低—高—低,故即为“字”的字腔。其中的末音,即为“字”的字腔结点,此后的即为过腔。
纵观当前中亚东干族群的研究,学科范式层面明显呈现出“孤立化”倾向,即有关东干人的研究受限于学科边界,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与综合研究较为鲜见;经验层面则“脱嵌”于具体的时空背景,即涉及东干人的讨论多集中于学理层面,缺少回应宏大时代主题的意识和趣旨。基于这种问题意识,本文一方面在历史学的框架内对东干人族群认同建构与延续的过程进行历时性梳理,尝试对当前人类学族群认同的有关范式进行跨学科的检视、验证和反思;另一方面,本文将以东干人族群认同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过程为样本,力图阐释跨境民族的认同属性对于当前“一带一路”倡议这一时代主题的现实意义。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东干人百年来族群认同
建构与延续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中亚回族,或者说东干人,自中国陕甘地区迁出,是与清末同治年间回民反清起事相关联。由陕甘等地移出的回族在其首领白彦虎的带领下,费尽周折定居中亚,其最终目的在于回避战乱、维系族群的生存和发展。就这个意义而言,斯科特(James C.Scott)所言的“生存理性”[1]构成了东干人移居中亚的关键因素。但需要进一步厘清的问题在于,在远离故土逾百年的时间里,“生存理性”对于东干人族群认同有何影响?换言之,远离故土的东干人是否会在这种理性的引导下,改变认同策略以求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获得必要的生存空间?这就需要对东干人族群认同的历史过程进行一次深度的“扫描”。我们的观察表明,自迁居之初至今的百余年时间内,东干族群不仅没有轻易改变以故土认同与文化认同为核心的族群认同,与之相反,他们将农耕生计方式引入新的生活场域,并将故土的语言、风俗和生活惯习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加以 “操演”,以此稳定地强化并延续了固有的原生认同情感。
(一)移入中亚初期原生认同的建构
迁居中亚的白彦虎部及其后裔均信仰伊斯兰教,自称“老回”或“陕西老回”,承认同源的风俗习惯、文化渊源乃至血缘联系,也与其在陕甘地区生活时期的原生地缘相关联。依照地缘关系理论,居于中国陕甘地理范围内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民众,自元迁居于此后,在漫长历史进程里,与当地其他族群共同生活与相互社会活动交往中,居住形式逐渐形成“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与周边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形成同乡邻里关系,凝结出友好的乡亲观念,视中国陕甘原居住地为本族群的家乡家园,为本族群繁衍生息的栖息地。同时,在保持自己族群地域单元的前提下,自身的民族特点愈加明显,尤其在经历了清末反清起事那种残酷的血火洗礼后,这种既包含有地缘特征又具有族群观念的亲近关系更加牢固,加之共同的宗教信仰纽带,加深了地缘关系,族群意识得以增强,形成了共同的历史记忆与集体记忆。由是,在迁移中亚后,自然而然产生了相对于原生地——中国陕甘地区的故土观念。浓厚的乡亲观念使得这些人的族群观念更强,抱团生存的痕迹在生产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尤其在迁入初期为生存而获取食物的生产活动,深深地烙上了中国陕甘地区农耕文明的痕迹。
步入20世纪30年代,在哈萨克共和国江布尔州库尔代区的马夫青镇,出现东干人的集体农庄联合体。马夫青镇,也称为喀喇库努兹,位于楚河右岸,这个集体农庄联合体先是由七个小农业联合体和几个农业组组成,1935年,又成立一个以“古比雪夫”命名的集体农庄。1950年合并成一体。[4]
③NaH2PO2为____(填“正盐”或“酸式盐”),其溶液显____(填“弱酸性”“中性”或“弱碱性”)。
细分当时移居中亚东干人的原籍故土,有一半以上源自陕西,其余为甘肃、青海、宁夏及新疆等地。清末迁移之前,尽管这些人已经怀揣着特有的经商技能,但是由于农业垦殖是陕甘地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和发展趋势,垦种农地、从事种植经济,依然是移民者们依存的主要营生方式。所以,过境后的东干人祖先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寻找可以耕作的土地,这也是迁移后的第一代陕甘回族基本都散居于便利农业灌溉的楚河两岸的缘故。据人类学者考察调研显示,营盘老人讲:白彦虎在率部过境后一再强调,必须以农为本,依靠自己,发展粮食及蔬菜种植业、商贸业,才能保证东干人的生存与繁衍。
3.新造的英文词。新造的英文词指过去没有的英文词,随着社会的发展,新事物不断涌现,人们创造出新的英文单词或短语用来表词答意。例如:
所以,自首批陕甘回族起,以农业种植为本业,开荒种地。随着移居人口的繁衍生息与社会经济发展,在楚河两岸形成五个较大的集聚地,也就是自称的“营盘”。其中有三个聚居点在七河省,包括该省的营盘、新渠、哨葫芦等地方,两个聚居点在塞尔达林省的江尔帕克——提别、奥什地方,东干人生活聚居的地方被当地政府称为“集体乡庄”或“集体农庄”,用于汲水灌溉农田的楚河则被东干人视为母亲河。[2]
首批迁徙中亚的人,在陕甘时就信仰伊斯兰教,属于回族族群,俗称回回。也正是这批首迁者,成为今天中亚东干人的祖先,在逾百年的历史里,不仅坚持原生族群的认同性,而且还讲求生存的地缘性,集中聚居,族内通婚,凝结生成了新的民族意识。1940年代,前苏联将这些生活在同一地域的群体,称为“东干人”,给这些人的民族意识认同贴上了标识。诚然,语言文字作为民族文化传承的载体,也不可分割地成为东干人的标识。
然而,移居中亚后的陕甘回族所面临的当地社会经济是以畜牧业为主流,农耕经济并不被看重,可是这批陕甘新移民则依靠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给中亚社会生活及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不仅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而且对中亚经济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从光绪八年(1882年)至清末,东干人在俄境的楚河两岸共垦殖农田26828俄亩(1俄亩=1.09公顷)。至1912年时,以陕西籍为主的营盘东干人达到983户,人口总数4935人,拥有土地13325俄亩,人均耕地达3俄亩。以甘肃籍为主的哨葫芦乡有494户,人口达3176人,开垦荒地6千俄亩。普尔热瓦尔斯克有陕甘后裔的东干人519户,2592人,人均占有耕地4俄亩多。[3]
与俄境的原住民相比,所谓新移民的东干人,并没有得到俄政府的优待,或者获得优质肥沃的土地,与此相反,这些新移民筚路蓝缕,新垦之地大多土质贫瘠,灌溉困难,农作物成活率低。但是,新移民依靠集体的力量与智慧,摆脱势单力孤之境地,大量兴修水利,平整土地,营造良田,同时向当地原住民租借肥地耕作。由于缺水严重,为灌溉田亩,哨葫芦乡甘肃籍回民开通一条人工运河,东干人自称为“黄渠”,当地人则称为“东干河”,成为沿河地区耕地的主要水源。
自迁居中亚的首批移民者起,东干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传统的天干地支的纪年法,以10个为一周期的天干与12个为一周期的地支搭配使用,构成了60年一个循环的周期纪年。同时,东干人会使用十二生肖来称呼年份,“牛年”“虎年”“猴年”等词汇时常挂在东干人的嘴上。而在询问与回答某人的年龄之时,通常会以生肖属相来作为计算标准。按民间的说法,动物循环周期的某些年份会给农民带来好的收成和风调雨顺,而个别年份则会带来灾难。民间也有同陕甘地区的民谚:“羊、马年广收田,单怕鸡、猴恶狗年”。[10]由上可见,在逾百年的历史里,正是通过语言文字、婚姻习俗及纪年方法等“媒介”,以此唤醒东干人的集体回忆,强化共同的社会记忆,无疑凝聚了族群认同。
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将族群视为人类社会亲属认同的延伸和隐喻。因此,一种基于自然或精神上的“同源”关系就成为族群认同发生的基础。换言之,在格尔茨看来,人们之所以认同和依附某一特定族群,是基于相同或相近的地缘关系和血缘关系所迸发出来的“原生情感”。但这种原生性认同如何在复杂的生活世界中得以延续?格尔茨继而认为,文化构成了族群分野的基本标识,因此,保持文化层面的一致性和普同性成为延续族群认同的必要条件。[11]
从环境史的视角审视陕甘回民的迁移,饱含有“生物箱式旅行”的生态意义。也就是说,人口移动不仅是人类本身居住与活动地的变动,还涉及到人类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利用及其生活方式的相应迁移。人们将原生地的生活方式与生产技术等具有生态意义的习惯因素原封不动的转移到新居住地,使陕甘的传统农耕方式得以继承推广,与陕甘生活习俗相关的作坊式手工业等也得以继承,还有为发展农耕的辅助灌溉工程与大兴水利工程,以及为灌溉而争取水源的行为方式等,都是中国农耕文化水资源利用的典型特征,是陕甘农耕文化中的传统方式。凡此,一方面影响了新居住地的资源利用方式,另一方面也将原生地既有的文化习俗与传统浸润在新居住地的社会发展中。
据资料显示,东干人的人口数量较之前有大幅提高。截止2010年,东干人总人口11万余人,主要居住在:一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马山青镇、朔尔——提别镇与奥克提亚勃尔集体农庄,以陕西东干人为主,4万余人;二是吉尔吉斯斯坦的德鲁日巴集体农庄与米粮樊镇,以甘肃籍东干人为主,5万余人;其余散居在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和阿拉木图、比什凯克等城市。[5]
(二)百年来中亚东干人族群认同的延续
民族意识的基本职能在于“我群”与“他群”的主观区别。在民族交往和接触过程中,当民族差别为民族心理所感知时,便会产生民族意识,这对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而族群迁徙与族群内部迁徙记忆的差异,在新的居地环境下,经过长期延续、继承和演化成新的记忆,或者说民族认同。也就是说首批迁徙新居地人群的自有族群意识与百年中新居住地环境下生成的民族意识是该民族与文化认同的核心价值。
(2)若國主能肅温,又良哲恭清儉聖讓者,皇極建也。(《太上說玄天大聖真武本傳神呪妙經註》卷一,《中华道藏》30/532)
陕甘回民自移居的第一代起,由于历史原因,几乎割断与中国陕甘地区的联系,其后裔渐渐地分散居住于中亚的三个国家,但以陕甘地区为族源地和纽带以凝聚东干人情感的民族意识并没有淡漠,而是更有力地将他们连结为一个统一的共同体,并发展成中亚地区一个经济文化较发达的民族,成为中国信仰伊斯兰教者在境外的最大侨民群体。可以说中亚东干人的文化源流、民族特征与观念乃至族群认同,均属于中国回族的一个分支,与中国陕甘回民具有共同的传统文化理念、共同的民族心理与宗教信仰。
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为我们探索心智的秘密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和观念,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经典计算主义得以兴起。
农耕种植也要靠天吃饭。楚河平原地处天山与阿拉套山之间,长200公里,宽约15~30公里,海拔高度为500~1200米,年均降雨量为250~400毫米,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一月份平均气温-6℃~-9℃,7月份平均气温24℃~25℃。最主要的是该地气候与中国陕西的关中平原十分相似,适宜农耕生产,这就使得移民者们能够将自己在原生地所熟悉和掌握的农业耕作技术直接用于新的客居地,保障生存与发展。
理论意义上,族群认同“原生论”或许可以为迁居之初陕甘回族的族群认同建构提供一种可能的解释框架:迁居中亚之后,陕甘移民尽管在住居结构上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向,但是对于同一宗教信仰、同一世居地域的强烈原生情感促使他们在陌生的土地上保持着统一性的族群认同。同时,为了维系和延续这种族群认同,迁徙后的陕甘回族将故土的农耕生计文化带入迁居地,其目的就在于通过生计层面的文化一致性,在日常实践中不断延续和“再生产”这种统一的族群认同。从这个意义而言,迁徙之后的陕甘回族对于农耕生计的选择就具有了“双重效应”:农耕生计不仅是维持生存的经济方式,亦是保持族群认同、凝聚族群情感的文化手段。
东干语中至今保留的一些词汇,是当今中国西北土著方言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为明了起见,在括号内标注其相对应的含义。如“衙门(官府)、连手(两人互相帮衬)、盘缠(外出时的费用)、调唆(教某人使坏)、茶饭(日常三餐)、儹劲(特别有能耐)、脚户(赶大车的人)、无常(不正常或不靠谱)、打平火(大家凑份子聚餐,有AA制的意思)、刻里麻嚓(意即某人办事情干净利索)、背旮旯子(较为偏僻的地方)”等。其中的“背旮旯子”为青海循化地方土著中普遍使用的老话。“打平火”也是甘青地区方言中年长者们的常用词。
无论是温馨还是浪漫的时刻,葡萄酒总能成为烘托气氛最好的陪衬,选对了酒更会让这一刻在回忆里尤其深刻。这一次的试饮会,我们便将主题定为“圣诞葡萄酒”,选取酒标有特色,或是性价比高,就算喝不完也可以调制杯圣诞热红酒的酒款进行品鉴,让你无论如何打算欢度圣诞,都能找到合适的选择。
2.3 UFMA评定及MBI指数 4周后,3组患者UFMA和MBI的评分较治疗前显著增加(均P<0.05)。3组患者改善程度比较,C组>B组>A组(均P<0.05)。第8周随访时,A组UFMA和MBI的评分与第4周及同时间点B、C组比较有所降低(均P<0.05),B组和C组的评分无统计学意义。C组UFMA及MBI评分更高于B组(P<0.05)。见表4。
如人所知,陕西民众习惯将小男孩昵称为“儿娃子”,现今东干人的名字中,也常常有这样的称呼。如有“东干文化之父”的亚瑟儿·十娃子。一代代东干人总是把陕西省叫“我爷的省”,把陕西汉人叫“老舅家人”。 自称 “中原人”“中原回回”“老回”或“回族”“回民”,将自己的话称“中原话”或“老回”话,连喝的醋都称“中国醋”。
原生族群认同的核心因子在东干人新民族观形成中浸润于社会与生活的方方面面。而饮茶又是其传承中国陕甘文化的又一例证。东干人日常饮食中的好茶习惯,明显是承袭于中国传统中悠远的饮茶与品茶之风。中国作为茶的故乡,茶文化博大精深,饮茶传统也源远流长。可以不夸张地说,任何一名生活在中亚的东干人都离不开茶,一天中的早、中、晚都要喝茶,尤其请客之时,茶便必不可少,主人会给每个客人端上沏好的茶水,这项传统一直保留至今。茶还是东干人族内婚俗中的一个必不缺少的重要物品,儿女定亲,会把聘礼叫做“茶钱”,用红色线绳捆绑在茶包的外部,探访亲友时也喜欢馈送茶叶作为礼品,以至于茶成为东干人的一种文化,有一首专门讲饮茶的诗句,被收录在东干人初中语文课本里。④这些与茶有关的习俗在今天陕甘回族乃至土著汉族中依然广为流行。
东干人族群内通婚的习俗也是其新民族观中留有原生认同的重要痕迹,对新民族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东干人婚俗的整个过程中,一般会首先安排媒人代表男方去女家提亲,媒人第三次登女方家门时,女方如果在茶点之前给媒人端水洗脸洗手,就证明同意了这门婚事。继之,女方家人与媒人互相握住右手,再将左手放到对方右手上摇三下,即算正式应允。八天后,便举行问名与纳吉的“吃定茶”。即双方父母见面,按照中国传统商议婚期与彩礼。婚礼日期选择良辰吉日,按照中国的北方地区的习惯,男方一般应在正午12点之前将新娘娶回家门,否则就不吉利。但由于时差的原因,东干人定在下午2点左右。纳征即送聘礼,东干人认为,彩礼钱是青年夫妻生活的基本物质保障,因此对彩礼的数量极为重视。彩礼一般包括牲畜、现金、金银首饰、各种布匹绸缎、衣服等。
多媒体课程资源建设涉及的动画,集中在各个章节重点、难点阐述,利用Adobe Flash CS6软件,对照教材及参考书籍中的图片,根据文字阐述的原理,补充相应的动画对功能进行完善。
在迎娶之前,东干人还有几个规矩及习俗与中国陕甘地区基本相同。其中铺房(床)最为重要。床是新房中不可缺乏的器具,同时又是新婚中富含神圣色彩的器物,故东干人对铺床缝被子很重视。成亲前一天,请有福气的妇女来新房铺床。有福气的标准是儿女双全、子孙满堂、家庭和睦、家境富裕。认为这些有福气的人会给新家庭带来幸福。铺床时妇女们口里还会念出各种吉利话,床铺下压上红枣、核桃、桂圆等物品,目的无非就是希望新人百年合好、早生贵子。这种做法是地道的陕西关中风俗,源同于西北地区的婚俗。[8]当然,东干人也沿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妇女的生育习惯与前苏联妇女的低生育愿望相反。据调查资料显示,马三奇乡1万人口中,生育子女在10个以上的东干妇女竟多达157个,她们被称为“民族英雄”“英雄母亲”。其中生育最多的一位妇女名叫乌格尔海麦,年50岁时,已生育15个孩子。政府和农庄负责给予多子女父母以经济补贴,供养这些孩子上学到成人,还给这些母亲乘汽车不买票以及其它种种优待。在前苏联,要生到够十个小孩才能当上“英雄母亲”,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每一个东干集体农庄都有一些“英雄母亲”。1977年,集体农庄的东干妇女平均生八个小孩,城市俄罗斯妇女一般只生一两个孩子。[9]
为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增产丰收,不少东干移民向当地人租种土地。仅1911年,居于普尔热瓦尔斯克东干人就从邻近村社租种土地2750俄亩,比什凯克县东干人人均租地5.5俄亩。许多居住在城里的东干移民也以租地耕种作为生存与增加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并在自己的店铺里出售自产的蔬菜、水果、烟草、豆类、亚麻等农副产品及多余的粮食。
二、东干人百年来族群认同的理论意义
以上本文对迁居中亚的东干人逾百年来族群认同形成与延续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历时性的勾勒和描述。作为一项跨学科的研究尝试,本文无意将趣旨仅仅停留在对这一历史过程的一般性描述层面。更广泛意义上,厘清和分析这一历史过程所表达的“理论相关性”,将成为我们更高的研究诉求。换言之,本文需要回答以下两个具体的理论问题:第一,百年来东干人族群认同建构与延续的历史过程蕴含着怎样的理论逻辑?第二,这种理论逻辑又能否对当前人类学现有的族群认同范式提供一种来自于跨学科的检视、验证或反思路径?
(一)东干人原生认同建构的理论逻辑
其次,建设主题鲜明、富有特色的场馆和多媒体平台。比如:建设闽东红色文化展陈馆、畲族文化主题展馆、廉政文化馆等,既可展示特色文化和资源,也可为实践教学和主题学习活动提供场所;结合闽东特色文化,建设学术报告厅、音乐厅、学生活动中心等,举办以闽东特色文化为主题的报告会、诗歌朗诵、演讲比赛、音乐会,陶冶学生的情操;成立闽东特色文化研究中心,建设闽东特色文化专题网站,开通“闽东之光”微信公众号,全面推进闽东特色文化入脑、入心。
东干人至今仍以汉语言的中国西北方言作为基本语言,尤其在族群内部的日常语言中,保留着大量清代陕西和甘肃的方言土语,这成为东干人在逾百年的历史中族群认同中最显著的痕迹和特点。可以说东干语就是陕甘语言的变体。[6]因为一套成熟语言的基本元素包括语音、词汇、语法和文字等。东干方言的音调属于陕西四声调和甘肃三声调,说话比较硬,且多用去声。陕西籍东干人口音与今天陕西关中人的口音没啥区别,而且还带有关中方言特有的一些词汇。如把“小”说成“碎”,相应地将“小孩”称为“碎娃”。 将“水”说成“费(fei)”,相应地“喝水”便说成“喝费”。 将“下”说成“哈(ha)”,则“下雨”即说成“哈雨”。 将“杏子”说成“横(heng)尔”,则“黄杏”说成“黄横尔”。 另如将“鞋袜”说成“孩袜”,“咸菜”说成“寒莱”等。 [7]
有备无患才能临阵不慌,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各相关部门和沿江各单位成竹在胸,云南电网厉兵秣马迎战“最大洪水”。
(二)东干人百年来族群认同延续的理论逻辑
对于百年来东干人民族认同的历时性梳理,清晰显示了迁居中亚的东干人对故土情感的坚守。如前所述,迁居中亚之初的陕甘回族通过同一性的农耕生计方式在异国他乡维系着自身的族群认同。但需要指出的是,一种认同在较长历史时段的稳定和保持,需要在更广泛的文化维度展示其一致性。王明珂指出,族群认同的基础是一种基于特定社会场域中的“历史记忆”,历史记忆的变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并形塑族群认同是否变迁以及变迁的方向。[12]在王明珂的定义里,历史记忆意指从集体记忆中分化出来、呈现和流传特定群体历史形态的特殊性记忆。[13]因此,能够呈现这一群体日常生活历史形态的语言与风俗便构成了历史记忆的核心要素。如上文所见,东干人不仅在生计层面以一致性的农耕文明维系着对故土的原生认同,在其后近百年的时间内,他们将陕甘故土的语言、婚俗、生育惯习及纪年方式等多维文化要素“内化”为一种稳定的历史记忆。更为重要的是,东干人对故土的“历史记忆”并没有静态地停滞在他们的思维结构中,与之相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式实践和操演这些以语言、风俗为内容的历史记忆。保罗·康纳顿曾将保持文化样式的日常实践称为“体化”(Incorporating)实践,并指出这一实践方式是社会群体记忆能够有效实现的手段和方式。[14]东干人在日常生活中坚守故土风俗和语言的文化实践实际上就是这种特定的“体化实践”,通过这一方式,他们将历史记忆“活态化”,并有效地将最初的原生族群认同延续至今。
(三)东干人族群认同历史过程的理论意义
本文在历史学的框架内呈现了百年来东干人族群认同建构与延续的全过程:因战乱而避居中亚的陕甘回民在初到迁入地时,基于地缘、血缘和宗教信仰的“原生情感”形成了以地域认同为核心的族群认同,在迁入之初,他们通过生计层面的文化一致性保持这一原生性的族群认同;在其后逾百年的历史时期内,他们又将陕甘故土的语言、风俗等文化要素整合成为一种对故土的“历史记忆”,并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对这些文化要素的 “体化实践”不断激活和重复这一历史记忆,以此稳定地保持和延续基于原生情感而形成的族群认同。当然,本文无意将东干族群百年来的族群认同状况延伸为一种关于跨境民族认同的普适性样本,但是,就这一历史过程所呈现出的理论逻辑而言,却可以为当前学界有关族群认同研究及其现实意义的探索提供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作为方法论层面的“理论实验场”,东干人百年来族群认同的历史过程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检视、验证和反思人类学有关族群认同的主流范式。人类学解释族群认同的理论框架内,一直存在着“原生论”与“工具论”两种范式之间的争鸣。如前文所述,原生论将族群认同的发生归因于一种不掺杂任何功利色彩的“原生情感”;而“工具论”则将族群认同解释为个体在争夺社会资源过程中的工具和手段。在“工具论”的解释框架中,人们对某一族群身份的认同是因为这种身份能够为其带来实际的利益和资源。“工具论”范式植根于一种经济学逻辑之上:人是一种原子化的“理性”动物,个人利益的最大化是个体行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本文所呈现出来的东干人族群认同而言,单一的“工具论”可能偏离了日常生活的真实逻辑:东干人在逾百年客居“他乡”的历史中,虽历经磨难,但其族群认同却始终未发生流变,而这一稳固族群认同的基础则来自于同一地缘、血缘和宗教而形成的“原生情感”。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可能并不符合现实场景中人们的真实状态。正如格尔茨所指出的那样,日常生活中的人并非以只顾“争名夺利”的理性动物而存在,更多场景中,人是一种“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个体行动的动机、形式和目的都会受到隐藏在其身后的文化意义之网的影响和形塑。[15]东干人在逾百年的历史中一直坚守自己的族群身份,不是因为这一身份能够为其带来可见的利益和资源,而是基于文化意义上的“同源关系”。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与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存有天然的亲缘关系,人类学族群认同“工具论”片面地将“生存理性”定义为个体通过对微观层面原子化利益的追逐,以确保获取自身的生存空间,但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却忽视了“生存理性”的宏观维度与群体维度。事实正如黄宗智所言,个体理性表达行动具有极为鲜明的文化逻辑,因为“在不同的文化场景中,个体会体现出不一样的理性表达”;[16]萨林斯对“理性”的定义更为直接,在他看来,即使是经济学奉为圭臬的“经济理性”,也不过是“更大文化价值体系的结果,它表现为一种围绕物质使用的意义体系”。[17]由此观之,理解东干人的“生存理性”,就绝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场域和意义之网,将其视为个体对可见经济利益的追逐——在保有共同文化记忆、享有同一生计方式和生活惯习的文化背景下,建构和延续强烈的故土认同和原生情感,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抱团取暖”,本身就是东干人“生存理性”的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特定群体的族群认同研究,不应该仅仅关注族群成员作为“经济人”面向,更应该考量他们作为“社会人”和“文化人”的双重面向。
三、余论
作为一个“实践样本”,中亚东干人逾百年的族群认同可能为学界在“一带一路”背景下讨论跨境民族认同的现实意义,提供一种来自于生活世界的经验范例。历史梳理与经验观察的目的不应该仅仅为某种现象或概念提供一种抽象的学理性解释,而更应该回归实践去关照和回应特定的时代主题。就此而言,将东干人族群认同这一具化的经验观察“带回”特定的时空背景中,讨论东干人族群认同与“一带一路”这一宏大时代主题的关联性,将成为本文讨论的最终趣旨。作为生活在中亚的中国回族后裔,东干人在身份属性上具有跨境民族的某些特征。已有学者从理论层面指出,培育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树立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带一路”倡议顺利实施的必要条件。[18]理论研判需要来自经验实例的支持,从这个意义出发,东干人百年来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情感,一定程度上为当前跨境民族认同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联性提供了一种经验范例:文化层面,百余年来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情感,使得东干人成为助推“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中间人”。台湾学者陈丹尼(Daniel Chew)基于对马来西亚华人的实地观察,指出活跃在东南亚的华人商人群体作为一种“市场中间人”(Market middle man),通过在日常生活和市场贸易过程中对中国文化“自然性”的展示,为东南亚土著居民全面了解和认同中国提供了一种来自生活世界的鲜活路径。[19]与此类似的是,具有中华民族认同的东干人通过对故土语言、生活惯习及生计方式的坚守,在与当地土著居民的日常交流中展示并传播烙有显著中国特质的文化体系,无疑将有助于当地居民进一步理解和认同中华文化,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奠定坚实的文化认同基础;政治层面,作为当代中国重要的对外策略,“一带一路”倡议的趣旨并不停留在国家官方层面的互动和交流,其最终目的在于能够使沿线国家的“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理解、认同并践行这一策略。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西方“国家人类学”范式认为,普通人理解国家策略的方式和逻辑并不依赖于成型的制度体系,与之相反,他们往往在“碎片化”的社会互动中感知和理解国家政策。[20]就此而言,具有强烈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的东干人的存在,有利于在日常互动中使当地普通人感知、理解和认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减少这一策略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制度生硬性”和不确定性,从而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普通人生活世界中的“生根发芽”提供坚实的“生活土壤”。
特别说明:本文的完成源于2018年10月在吉尔吉斯斯坦的学术考察,并参考了已有的相关学术成果,文中未能一一注明,在此特致谢致歉!同时,得益于中国人民大学赵珍教授、兰州大学杨文炯教授、甘肃政法大学李元元教授的精准惠助!
注释:
① 马志荣:《白彦虎退往新疆原因初探》,《回族研究》,1997年第4期;王国杰:《重新评价白彦虎》,《西北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丁宏:《关于白彦虎之复议》,《回族研究》,2001年第1期;王国杰:《中亚东干族之父白彦虎生平资料新考》,《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② 贾东海:《世界汉学中的东干学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2期;(吉尔吉斯)苏三洛著、郝苏民等译:《中亚东干人的历史与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丁宏:《东干学与东干学研究》,《回族研究》,1998年第2期;王国杰:《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王国杰:《论东干学与中国回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吉尔吉斯)张尔里著、崔红芬译:《中亚回族的民族意识与汉语论著中“东干”一词的使用问题》,《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杨文炯:《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东干”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③ 王国杰:《中亚东干族与中国传统礼俗》,《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国杰:《论东干学与中国回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丁宏:《东干人与伊斯兰教》,《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惠继东:《东干文化的中国情结》,《西夏研究》,2013年第2期;赵杰:《论当今中亚回族之特性——为回民西迁130周年而作》,《回族研究》,2007年第2期;吴生艳:《论东干文化中的中国乡土性表现》,《宁夏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李如东:《地域观念与民族认同:以中亚回族(东干人)为中心的考察》,《西北民族研究?》,2015?第3期;马建福:《跨国网络与认同:东干人日常生活中的家国情怀》,《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④天天早上起来了,各家各户。先喝茶呢不吃饭,也不吃肉。格鲁吉亚的太阳,库拉的浪。都在茶叶里头呢,血咋不旺。人说心里闷得慌,浓茶喝上。寿数能长脸色好,身体强壮。别的嗜好我没有,就爱喝茶。人老几辈都喝呢,我妈我大。这里的“我大”,是指父亲。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程立显,刘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1:1.
[2]王国杰.1877年移居中亚陕甘回族的地理分布[J].宁夏社会科学,1997,(4).
[3]王国杰.1877~1977年间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的经济活动[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4).
[4]房建昌.东干——苏联回族的历史及其现状[J].西北民族研究,1989,(1).
[5] 东干人[EB/OL].https://baike.so.com/doc/6743587-695 8118.html.
[6]海峰.东干语概况[J].民族语文,2002,(1).
[7]王国杰.论中亚东干族的方言特点[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6).
[8]慧继东.东干文化的中国情结[J].西夏研究,2013,(2).
[9]白述礼.今日中亚回族[J].回族研究,1993,(4).
[10]M·苏三洛著,速来蛮·郝,高永久,译.东干人(中亚回族):历史——民族学概述(第四章:东干精神文化之一:民间知识)[J].西北民族研究,1993,(2).
[11]Eller,J.D&Couchlan,R.M.,“The Poverty of Primordialism:The Demystification of Ethnic Attachments”,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2016,Vol.16,no.2,pp.183-201.
[12]王明珂.族群历史之文本与情境——兼论历史心性、文类与模式化情节[J].西北民族论丛,2007,(5).
[13]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J].历史研究,2001,(5).
[14][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24.
[15][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5.
[16]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9:4.
[17][美]马歇尔·萨林斯.石器时代经济学[M].张经纬,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7.
[18]崔海亮.“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跨境民族的中华民族认同[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1).
[19]DanielChew, “Chinese-IndigenousRelationsin Sarawak: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蒋斌,何翠萍.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2003:503~516.
[20]Aradhana Sharma and Akhil Gupta(ed),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1,p.10.
Survival Rationality and Ethnic Identity--Case Observation on History Process of Tunggan People’s Ethnic Identity in Middle Asia
ZHANG Ke
Abstract:Dunggan people in Mid-Asia is a typical group of people settled down abroad who maintaine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Transferred to Mid-Asia since the reign of Tongzhi,they still maintai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in language,customs and production pattern after living and contacting with local people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which has been the remote memory about the homeland of them.From the observation,the base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was native emotions that were from the same geographic relation,affinity and religion belief.Constant repetition and demonst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emory in daily life which centered on native language,customs and living habit guaranteed the maintenance and continuation of ethnic identity over hundred years.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aintaining and continuing showed that inspecting ethnic identity in particular situation should not view the survival rationality as acting expression that was led by single economic logic,not detach the face of economic man among group members from everyday life world and regarded it as the basic element of identity,but should concern the key role of double faces of social men and cultural men in the identity occurrence and continuing course.Under the current background,to clarify the cultural system of Dunggan people’s Chinese ethnic identity will be helpful for other ethnic groups of the district to perceive and understand the fresh path provided by the initia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and contribute a solid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initiative.
Keywords:Dunggan People;Ethnic Identity;History Process;Survival Rationality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9)03-0019-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回族侨胞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批准号:18XZZ007)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 :2019-03-22
作者简介:张 科(1972-),男,四川达州人,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社会史研究。
[责任编辑 骆桂花]
[责任校对 王淑琴]
标签:族群论文; 回族论文; 中亚论文; 文化论文; 民族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民族学论文; 《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亚回族侨胞的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18XZZ007)论文; 青海民族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