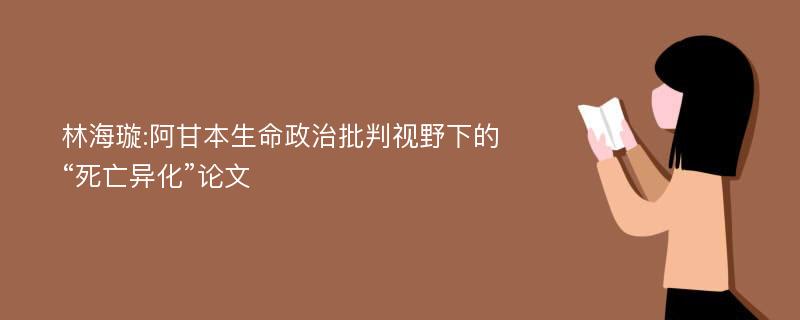
内容提要 | 意大利当代左翼政治哲学家吉乔奥·阿甘本(Giorigio Agamben)从历史重大事件“奥斯维辛集中营”出发,得出以下两个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诊断:一是当代西方资本主义政治逻辑正逐步发生“生命政治”转向,这种全新的政治统治模式以“捕获生命、占有身体”为特征;二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各种异化现象,在生命政治下相伴而来的是“死亡异化”。对此,笔者通过比较异化与死亡异化的区别与联系,并以纳粹主义特定历史时期的“死亡异化”与作为现代性残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死亡异化”为典例,以揭示“死亡异化”的现实反思价值及其警示作用,同时也对阿甘本在该理论上的独特贡献和立场偏颇进行辨析。
关 键 词 | 生命政治 奥斯维辛集中营 死亡异化 主体陷落
一、从“劳动异化”到“死亡异化”
异化理论经由马克思提出,由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几代法兰克福学派的进一步发展,到资本主义晚期,伴随西方政治发生了“生命政治”的转向,西方左翼政治哲学家(以福柯、齐泽克、阿甘本为代表)对传统的异化理论作出全新的阐述,既有别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的“劳动异化”,也异质于法兰克福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的“消费异化”,而是从生命维度将异化问题从生命生存延伸到生命死亡。这一演变,究竟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化,还是对其的背离?
法家对口语传播的贡献主要是提出了对社会舆论进行甄别和控制的理论,同时对口传技巧作了总结。法家重视对社会舆论的管理和控制,主张“以言去言”。前一个“言”是指完全代表国家利益和君主意志的言论;后一个“言”则是指社会流布的言论,或是与国家利益根本相左的异端邪说。《商君书·赏刑》曰:“所谓壹教者,博闻、辩慧、信廉、礼乐、修行、群党、任誉、清浊,不可以富贵,不可以评刑,不可独立私议以陈其上。坚者被(破),锐者挫。虽曰圣知巧佞厚朴,则不能以非功罔上利。”[3]法家的“壹教”说的就是天下一切言论只能是与农战有关并且是配合农战的。
(一)政治经济学批判下的“劳动异化”
异化劳动是马克思探讨异化问题的着眼点。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全面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异化的四大表征: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者同生产活动本身相异化;劳动同其类本质相异化;人与人
之间相异化。如果进一步将其归类的话,前两种异化属于“物的异化”,而后两种异化则涉及到“人的异化”。可以说,从卢卡奇开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受到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中展开关于“人的异化”的批判的启发,从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技术理性批判到大众文化批判,从日常生活批判到心理机制批判。西方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丰富了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内涵:实现了从传统马克思在劳动异化语境下对传统工人阶级的生存现状的关注,到对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公民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关注,阿甘本从生命政治批判的全新维度展开对异化问题的思考,成为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中为数不多批判继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激进左翼先锋,更是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西方意识形态批判之间,获得自身独特的理论批判地位。
但是,在马克思“异化理论”中曾用了一个生动的对比,说明人的异化的表现:“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54 页。人的动物化与动物的人化,这一思考路径与后来福柯、阿甘本从人的自然生命受到摧残、规制提出的生命政治似乎有着隐含关联,而所谓生命政治的核心要义,就是逐渐把“人的自然生命纳入权力的机制与算计中”2 [意]吉乔奥·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第20 页。由政治向生命政治的转向,实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在当代政治领域中出现的新异化现象。
(二)意识形态批判下的“消费异化”
承前所述,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不再囿于传统政治经济学批判维度去思考人的异化问题,他们彻底跳脱出以劳动异化为核心的人的生存异化。从卢卡奇开始的物化理论,开始关注商品拜物教现象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纵深发展商品拜物教是晚期马克思扬弃劳动异化的时代产物,发展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又由商品拜物教衍生出资本拜物教、景观拜物教等派生形式。现代社会中,人已经从马克思时代的“劳动异化”中解放出来,但重新进入了“消费异化”领域,当异化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消费领域,也就出现了马尔库塞所指出的“单向度的社会”。“单向度的社会”实际上就是消费异化的社会,在其中每个人不再是被迫劳动,而是被迫消费。随后,居伊·德波(Guy Debord)认为,在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商品无孔不入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在德波看来是一种新的“消费异化”,也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独有的“消费景观”。这种现代性的“消费异化”不仅仅指在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的被动消费行为,更会使得消费者在身心体验、情感、心理等也发生扭曲与异化。
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深受德波的景观理论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给公民灌输的是一种物欲幸福观,并对此提出质疑:以物质欲望构造起的庞大的消费社会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模式吗,是我们所追求的美好生活的载体吗?阿甘本显然并不认同这种资本主义的消费异化,甚至认为这种“欲望塑形生产”会进一步加剧人的异化。而这也成为阿甘本提出生命政治批判的现实依据之一。
(三)生命政治批判下的“死亡异化”
奥斯维辛是阿甘本展开生命政治批判所选取的历史视角,这使得阿甘本的生命政治批判既具有历史维度,又具有现实维度。在其“神圣人”系列著作之二的《奥斯维辛的残余:证人与档案》中,以纪实性的写作手法对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言进行评注,对当时纳粹主义生命政治下的独特历史现象——“活死人”进行伦理批判与道德反思。其实在二战期间及其之后的冷战时期,除了阿甘本,还有多位学者也都关注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及其“活死人”现象。诸如,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称之为“人间地狱”,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称之为“根本恶”,而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将大屠杀类比于农业的“机械化生产”,扎齐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更是进一步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中将集中营视为批量生产尸体的“死亡工厂”。
而阿甘本的理论独创性就在于,他不仅看到纳粹生命政治屠杀、宰治生命的表象,更是深入得出其本质就是一种“死亡政治”。可以说,他从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中剖开一道“死亡异化”的裂痕。在马克思那里,异化问题的探讨还未延伸至死亡维度,他坚守的理论底线是“人可以称之为人”。而到阿甘本那里,他不仅看到了纳粹生物性统治下犹太人作为被疯狂、大规模屠杀的表象(因为只有“人”才有被屠杀的资格),更通过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镜像看到其“非人”存在的本质。希特勒宣称要“干掉那些不值得活的生命”,让犹太人像“虱子般”被彻底消灭。在死亡异化下诞生的“赤裸生命”,才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本质所在。
二、纳粹生命政治下的“死亡异化”
进行地铁纵向的施工过程中,需要施工人员采用混凝土来给地铁的隧道两侧采取分段的浇筑,分段浇筑的过程会给接缝的位置留有凹槽,若凹槽有水的情况就会造成膨胀,导致有裂缝的发生,严就会造成渗漏水的问题。另外,出现裂缝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地铁隧道混凝土结构中由于钢筋封条质量次或者老化出现了损坏和脱落,进而出现了裂缝,造成渗漏水的问题。与此同时,在地铁建设中会在两侧设置止水带,如果止水带的施工质量没有按照施工的标准也会出现裂缝,导致渗漏水问题。
3.一些党员自身素质不高制约先进性的发挥。一些企业党员在党章学习上认真程度不足,多数学习处于浅尝辄止状态,并且有部分党员认为政治理论学习是空的、虚的,发展业务才是实的、硬的。还有极少部分党员认为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是企业领导的事,与己无关,对学习理论的重要性、紧迫性认识不足,影响了党员先进性的发挥。
(一)“死亡异化”是对死亡神圣性的亵渎
西方发达国家始终标榜“人权神圣不可侵犯”,但从完整意义上说,阿甘本之所以指认西方生命政治本质是“死亡政治”,就是因为他看到,西方“人权”所忽视的“死亡”维度也具有重要的伦理价值:人权不仅对于“生存权”而言具有不可侵犯性,对于“死亡权”而言更是如此。当人连正常死亡的权利都被剥夺的时候,正如张一兵教授所说:“死亡本身的本质沦丧了,这可能是人之生存最根基处的异化。”1 张一兵:《奥斯维辛背后不可见的存在论剩余》,《哲学研究》2013 年第11 期。
对大多数人来说,我们只知道集中营的存在具有非正义性和罪恶性,但是对于集中营内纳粹分子手段如何残忍,囚徒们受到的是何种非人的待遇,却是我们所无法正视也难以想象的。在这个意义上,阿甘本将奥斯维辛集中营称为“不可见的在场之物”,意味着“虽然奥斯维辛集中营现象是不可见的,却不等同于不存在的,它是客观的历史性存在,并且成为现代人类生存中永远无法摆脱的存在之痛。”2 张一兵:《奥斯维辛背后不可见的存在论剩余》,《哲学研究》2013 年第11 期。
生命政治本质上是死亡政治,这也是阿甘本生命政治理论中的核心观点。如果说福柯意义上的生命政治将现代资本主义暴力理解为一种规训和治理术的巧妙运用,理解为对活着的公民的一种隐蔽监控,那么,阿甘本则将视角聚焦于那些在生命边缘垂死挣扎的战犯、“恐怖主义”、难民,聚焦于二战时期纳粹式生命政治对人性的极端摧残,以当时最为人知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为典范,回归到生命政治最成熟时期去探究人的主体性何以在死亡维度上也受到毁灭性破坏。从一定意义上,纳粹生命政治下的“死亡异化”是现代民主政治下“死亡异化”的前身,福柯的隐形暴力实际上必须追溯到阿甘本所着眼探讨的“纳粹主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在异化问题上的新变化。
现代“营”模式下的生存境遇并没有比在纳粹集中营中好多少,甚至可以说在更加军事科技一体化管理下,对营中特殊人权主体的生物性控制在不断加强而不是减弱。美国对世界各国实行新干预主义政策,实质上扮演的就是阿甘本所指认的在法与暴力之间行使至高权力的“主权警察”的角色,而他们对现代特殊人权主体的生命政治操作,依旧是模仿纳粹时期对囚徒的“政治文身”操作,只不过从原本暴力性地留下身体烙印转向运用高科技隐形地进行“政治犯”的身份界定。如欧洲边缘地区以及中东地区,都存在介于国家边境的特殊地带,这些地区大都成为恐怖分子、难民、非法移民者的集中地。由于各国政府无法对国界之间的特殊地带进行有效管辖,这些边缘群体的人权极易受到侵害,在无所归属的境遇下,他们由此产生一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仇视心理”,成为威胁世界安全的潜在性恐怖分子。为了与美国等主权国家相抗衡,他们甚至采取“自杀式爆炸袭击”这样的极端手段,使得“死亡异化”在当代以新的形式出现。
除了幸存者,在集中营中还有这样一群特殊存在,用集中营里的行话称呼他们就是“死亡别动队”。“死亡别动队”既是奥斯维辛的受害者,又是纳粹的杀人工具。在《奥斯维辛的残余》中,记录下死亡别动队——无罪的杀人者,而这一备受唾弃的群体的心声却是发人深省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怪物;我们和你一样,只是更加地不幸。”1 Giori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p.22.阿甘本将死亡别动队在此灰色地带所进行的日常工作(批量生产、运送尸体和清理毒气室和火葬场)称为“一种灰色的、持续不断的炼金术”,既暗讽纳粹将囚徒进行人体试验的暴虐,又批判道德伦理的全面塌方:“它让传统道德的所有金属,伴随着善与恶,一起达到了熔点。”2 Giorigio Agamben, Remnants of Auschwitz the Witness and the Archive, New York: Zone Books, 2002, p.47.“ 死亡别动队”的存在是千夫所指,因为他们成为纳粹杀人的工具,成为无意识的存在。
阿甘本对奥斯维辛集中营、纳粹生命政治“死亡异化”进行历史性考古学研究,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出于对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批判?显然不是。阿甘本洞悉到二战时期以纳粹主义为代表的极权主义与现代民主制度之间存在亲缘性:虽然从历时性维度上看,它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历史断裂”,但是阿甘本在进一步思考民主与极权的关系中发现,现代民主政治并没有摆脱纳粹生命政治对人性摧残的本质,作为“奥斯维辛残余”的“死亡异化”,在现代民主政体中,以更隐蔽的方式渗透“死亡异化”的生政治逻辑。
正是在生命政治批判和对其背后“死亡异化”的深入探讨下,阿甘本才引入了“赤裸生命”、“神圣人”等核心生命政治概念。“赤裸生命”其字面意思,是生命的完全对外展开,这种展开不是面向马克思意义上的本质回归,而是被剥夺一切权利之后、其生物性生命受到全盘控制的非自由存在,其典型代表就是纳粹集中营。通过对集中营范式中的 “赤裸生命”具体分析,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深入思考:现代性“赤裸生命”的存在范式是什么,现代社会中是否仍残存着“新赤裸生命”?
(二)“死亡异化”下“赤裸生命”普遍化之实质
在此,“死亡异化”真正展露出它的罪恶本质:由异化走向死亡异化,不仅仅是营内和营外的界槛,也不仅仅是剥夺人的本质使之赴死那么简单(彻底剥夺人的生存权利),而是在死亡维度上使人彻底丧失正常死亡的权利(彻底剥夺人的死亡权利)。
通过历史溯源我们发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赤裸生命”是如何产生的:希特勒在执行“最终灭绝方案”期间,唯一坚持的法则就是,只有彻底剥夺犹太人的公民资格(其中包括在纽伦堡审判之后残余性的公民身份),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赤裸生命”,才能送入集中营。现代主权者在界定与认同公民身份上,一定程度上借鉴了这一范式:通过对公民身份的重新规介,划分出公民与非公民的二分对立,从而以正当化名义对所谓“非公民”群体采取各种政治手段。例如,美国在古巴设立“关塔那摩拘留营”,以反恐之名无限期扣押被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非法移民者,又如遍布全球的现代性收容所、难民营,这些是继传统纳粹统治时期的“集中营”之后,现代生命政治将“营”模式典型化的重要体现:剥夺当代特殊人权主体(难民、移民)等群体的基本人权。除此之外,“营”模式不仅针对特殊的人权主体,对于一般公民的日常生活也开始逐步渗透:“我们发现自己实际处于一个集中营的在场之中,无论在那里面所施行的是哪种罪行,无论它的命名是什么,无论它的特殊地貌怎样”。1 [意]吉乔奥·阿甘本:《神圣人:至高权力与赤裸生命》,吴冠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第233~234 页。阿甘本称之为集中营错位的场所化,机场的“等待区”、城市郊区、社区中心,我们生活在诸种“隐蔽的政治矩阵”之中,这就是现代生命政治统治所要达到的全球性部署和全方位覆盖这一更深层次的目标。
该系统采用SQL Server 2012数据库作为后台数据库。根据前期做的数据调查,设计相应的字段,数据库包括以下主要表:Student、Dormitory、Worker、HeadMaster和其他附表,部分表结构设计如表1、2。
三、现代民主政治下的“死亡异化”
当死亡被化约为流水线上的批量生产的时候,死亡不仅不可能拥有正常人葬礼的仪式感,甚至连体验死亡的存在都是不可能的。即便是对死亡抱有海德格尔式“向死而生”的超脱态度,依然无法摆脱对死亡本质的质疑:“他们这是死吗?他们是被压服。他们被做掉了。他们变成了单纯的数字,变成了制造尸体业务表上的一些项目。他们这是死吗?他们在灭绝营中不显山不露水地了结了。”3 [德]马丁·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问题和其它论文》,转引自朱利安·扬:《海德格尔·哲学·纳粹主义》,陆丁、周豪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261 页。这是死亡异化的又一个表征,死者无法正常体面赴死,不仅因为其残忍的非人道性而无法见证、不可目睹,而且其生产尸体的效率之高,使得人根本无法存留死亡的记忆。“死亡别动队”扮演着集中营里的尸体搬运工和垃圾处理者的角色,这也是阿伦特所抨击的,当人性坠入深渊之后,成为不会思考的“平庸之恶”。
(一)特殊人权主体的“死亡异化”
贾宝柱(1974—),男,辽宁阜新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轮机工程。E-mail:jiabzh@gmail.com
阿甘本在《什么是收容所?》一文中提到:“意大利警方1991 年在将阿尔巴尼亚非法移民遣送回国前在巴里拘留他们的足球场、维希政府当局把犹太人移交德国人之前用来圈禁他们的环形跑道、安东尼奥·马查多(Antonio Machado)1939 年死在西班牙边境附近的难民营,还有法国国际机场用来扣留难民身份的外国人的等候区。”2 [意]吉乔奥·阿甘本:《无目的的政治手段》,赵文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 年,第53~54 页。身处其中的都是带有“政治文身”的特殊公民(难民、战犯、移民等)的场所化,是确证过的“非公民群体”;而这些特殊人权主体,他们既不受本国法律的保护,也无法获得国际法的有力庇护,而只能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下苟延残喘。
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残余:见证与档案》中提到,集中营内囚徒也如在正常人类世界中一样,有三六九等之分:处于不同级别的“非人”都有各自对死亡的不同体验,都经历了“死亡异化”的不同形式。幸存者莱维就是经历了集中营“死亡异化”的历史见证者。作为一位犹太裔的化学家,他曾在营中担任人体实验等技术工作,这也是他得以幸存下来的重要原因。有许多像莱维这样在大屠杀中幸存下来的人,他们曾在死亡边缘目睹他人的死。对他们而言,也许并没有经历过活着的异化的痛苦经验,却深刻体悟了“求死不得”的更深刻的异化。这是幸存者的“死亡异化”,这种对死的切身感悟,其实在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身上也有着同样的体会,据他们多数人的言论,他们选择活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成为见证者,成为那段不可见的历史的为数不多的见证者。但他们永远也无法摆脱那种屈辱的身份,因为在集中营的那段时间,党卫军以数字编号的方式取消他们的名姓,并且以纹身的方式印刻在囚徒的手上。他们一辈子都要面对这样的记号。
(二)一般公民群体的“死亡异化”
现代生命政治对特殊人权主体进行的是公民/非公民的划分,这种划分体现为:生命政治的统治对象转向了一般公民群体,“正如最初为罪犯、外国人或犹太人制定的法规很快被推广到所有人身上一样,为识别惯犯而发展出来的技术在20 世纪开始扩展到所有公民身上。”1 [意]吉乔奥·阿甘本:《裸体》, 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95 页。阿甘本又称这一现象为“例外状态普遍化”。
这是一套融合自然之美与亲情之爱的世界经典图画书,在日本已经畅销20余年,总销量突破5000万册。在这个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10个孩子组成大家庭中,14只老鼠团结合作,其乐融融。
由此,生物识别产业应运而生。这不仅标志了从特殊群体向一般群体(公民)的转变,更实现了范围的扩大、监控程度的深入。在对一般群众展开网络化、地毯式的全方位监控时,进一步加强了对公民的“源头监控”,对中小学生日常生活展开控制型管理模式,在自助餐厅、图书馆入口、校门口都配置了光学生物识别系统,指纹、照片等身份信息存储于一张小小的芯片中,个人隐私的暴露从显性转向隐性,并逐步深入到对公民的生物和基因信息的绝对控制。这种生物技术的发展和潜在性威胁,丝毫不逊于核武器的威力。这是比纳粹统治时期的“优生学”更加残酷的生物性统治。基于此,阿甘本再次预判:“谁要是掌握了这样的权力,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以及任何可以想象的种族灭绝),将更彻底和迅速”。2 [意]吉乔奥·阿甘本:《裸体》, 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96~97 页。
首先建立多目标的综合能源系统优化调度模型。该模型分别考虑经济、绿色和综合最优3种优化目标,基于风功率预测、光伏功率预测、负荷预测等数据建立综合能源系统运行约束模型。其次,采用具有良好全局搜索能力的粒子群算法对调度模型进行求解。最后,给出具体算例,对不同优化目标的综合能源系统给出调度策略。
四、对阿甘本“死亡异化”理论的评价
“死亡异化”这一话题,涉及了当代生命伦理学对死亡问题的思考,涵盖了对当代人权问题最极端形式的诘问:如何确保当代公民具有生存权的同时,也具有死亡权?在人类一体化的进程中,异化问题也随之演变为现代性危机,但多数西方学者对异化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其建基的前提是活着的人。阿甘本尝试突破这一理论界域,开展连接生存与死亡、生命价值与尊严的一系列思考。从理论创新和对现实的敏锐洞察上看,阿甘本的态度是值得尊重的,但是,这种理论是否经得起推敲,理论本身又蕴含哪些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地进行反思性评价。
(一)阿甘本 “死亡异化”理论的积极意义
“那些东西持留在我们之中并以被遗忘的方式和我们待在一起,以且仅以此方式,成为始终不可遗忘的事物。”3 [意]吉乔奥·阿甘本:《剩余的时间:解读〈罗马书〉》,钱立卿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 年,第59 页。阿甘本想警醒我们,奥斯维辛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可遗忘的事物。它不仅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更是一个时代的延续,是纳粹统治的延续:今天,后“9·11”时代就是其变种,纳粹主义的幽灵就根植在西方民主制度之中。阿甘本所提出的生命政治批判、“赤裸生命”及其背后“死亡异化”的本质特征,无疑有利于从一个全新视角推进对战争、种族仇杀和恐怖主义活动的现代性反思,从而避免陷入盲目的历史乐观主义中,树立一种必要的、适度的时代危机意识,而这也是在全球化浪潮下人类命运一体化趋势下的必然要求,不仅要共享全球资源与发展成果,更要有时代责任感与担当意识,就要成为“同一时代的人”。
而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在对待这光怪陆离的现代性生活中唯一真实性的东西——新闻媒体报道某某地区发生枪杀等事件却置若罔闻,因为他们觉得,虽然电视新闻的报道是真实的,但是现代战争,像伊拉克、阿富汗战争,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活动以及种族仇杀活动,却好像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并形成一种旁观者的心态。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那些能够“感知时代黑暗而不是光芒的人”4 [意]吉乔奥·阿甘本:《裸体》, 黄晓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24 页。那些真正同时代的人,才能拥有我们正处在与“废墟为邻”的紧迫感,从而付诸抵抗和穿透黑暗的行动力。反之,那些浑浑噩噩之人,或许只有到了深处废墟的当下,才会恍然觉悟。
(二)阿甘本“死亡异化”理论的立场偏颇
阿甘本揭示的生命政治的本质是一种“死亡政治”,并且进一步指认在其中发生了“死亡异化”。这在理论内容上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创新发展。因此,一方面,我们对阿甘本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及其理论素养表示认可,并认同阿甘本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批判态度;但是另一方面,阿甘本在叙事方式以及价值立场上存在偏颇。
首先,阿甘本在方法论上彻底抛弃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这就导致了他在批判西方人权理论与普世价值的虚伪性的时候,缺乏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出发的那种批判力与解释力。对集中营以及现代恐怖事件的叙事性描述,也缺乏一种客观的维度,以致于让人在保持警惕的同时,又不免滑入历史悲观主义,这一定程度上是阿甘本依循后马克思主义者解构主义的叙事模式所导致的。
其次,阿甘本对“生命”理解的片面化,直接导致他在面对“死亡”问题上的悲观主义价值取向。在马克思那里,“生命”的内涵是丰富的,不仅包括自然生命,还有人的精神生命。在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强调的就是建立在人的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前提下,去发展一种更高层次的精神生命,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诉求。而阿甘本立足于现实生活中的战争以及恐怖主义等现实因素对人的肉体生命的摧残,拘泥于生命政治对于身体的规训、控制,只看到去政治化的消极性,并将特殊人权主体出现的人权危机普遍化和扩大化。我们不可否认难民问题构成了当代人权问题的主要矛盾,但是人权不仅是阿甘本所指认的主权陷阱,它作为西方政治国家的原生理念,出现在各国的权利宣言、人权宣言等规范性文本之中,并非全无真实性和积极性可言。再有,当出现人权危机时,一味的批判解构不是根治之策,更重要的是在认清世界格局的前提下提出行之有效的建构方案。
最后,阿甘本将纳粹主义生命政治下的“奥斯维辛”向美国“9·11”恐怖袭击、霸权统治直接等同起来,这一点是缺乏历史根据的。学术界目前并没有明确将美国划入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范畴,而只是存在某种倾向,所以,这是阿甘本为了进行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批判所设立的必要的“靶子”,是非历史僭越的分析模式。即便在认可阿甘本对现代性危机的敏锐洞察的前提下,我们依旧质疑的是:“死亡异化”是否夸大了生命政治的现代性含义?如果说当代诸如难民等特殊人权主体确实深陷“死亡异化”的囹圄之中,但是这种“死亡异化”是否真的扩大到每个公民身上呢?如果按照阿甘本的逻辑,我们接受器官移植、无偿参与社会献血、定期到医院做全身检查就是落入了生命政治的全面规制了,那就是全然否定了现代医学在保障社会人口总体健康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出于维护国家总体安全而设置的公共场所的监控设施,与窥探个人隐私之间是否存在必然联系?其实这里涉及到一种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何者优先至上的价值取向的根本对立问题。西方是在强调个人自由的基础上宣扬人权与公民权,而中国则是在个人与集体之间、小我与大我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前提下,更加突出国家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因此,阿甘本的“死亡异化”在理论上指涉的对象是全体公民,但在现实世界格局之中,“死亡异化”现象主要出现在第三世界国家,阿甘本的政治预判显然有夸大危机之嫌。
总之,意大利当代左翼哲学家阿甘本从生命政治批判的视野提出了“死亡异化”的全新观点,并以“奥斯维辛”为历史缘起,结合分析当代全球化趋势下恐怖主义、种族主义等国际局势,在学理创新方面开启了有别于马克思“异化理论”与西方“异化社会”的第三条对“异化问题”的理解。但是在现实层面上,阿甘本致力于理论解构,缺乏必要的理论建构与实践策略,这使得“死亡异化”理论并未成为阿甘本生命政治批判的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由于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践维度,阿甘本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也无法达到马克思的批判力与解释力,而这既是西方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普遍的理论缺陷,也是阿甘本个人研究范式的理论局限。
此处的“高墙”所指何在?文章说“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这堵“高墙”应该是殷实富裕的物质围起的高高的有形围墙,去年走访绍兴鲁迅故居,不难看出,确实是个阔气人家,庭院深深,家宅众多,围墙高大气派,与外界隔绝得很好。
“Death Alien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amben’s Life Politics:Exploring the Death Dimension in Agamben’s Life Politics
LIN Haixuan
Abstract: Italian contemporary left-wing political philosopher Giorgio Agamben started from the historical event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and came up with the following two diagnoses about the capitalist social crisis: First, the contemporary Western capitalist political logic is gradually taking a turn of “life politics”. This new model of political rule is characterized by“capture life, possess the body”. Second, Marx's “alienation theory” is not enough to explain the various alienation phenomena of capitalism. The life politics is accompanied by “death alienation”. In this regard, on one hand, the author compares the difference and connection between alienation and death alienation, and takes the “death alienation”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period of Nazism and the “death alienation” of the capitalist society as the exampl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bias of Agamben's theory.
Key Words: life politics; Auschwitz concentration camp; death alienation; subject fall
作者简介 | 林海璇(1995—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厦门 361021)
*本文系华侨大学2017 级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探寻阿甘本‘生命共产主义’的现实性及其当代价值 ”(lhx878)的阶段性成果。
(责编:俞平)
标签:阿甘论文; 生命论文; 政治论文; 马克思论文; 纳粹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19年第8期论文; 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