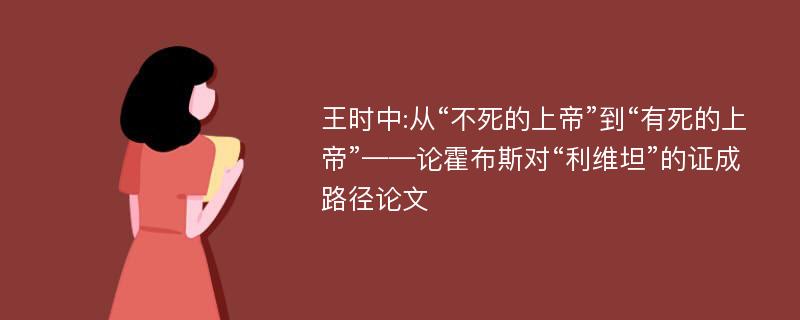
摘 要:霍布斯对“利维坦”的证成,一方面接纳了植根于唯名论革命的“自上而下”的信仰前提,另一方面,又回应了近代启蒙运动以来自下而上的理性传统。由于“奥卡姆剃刀”摧毁了经院哲学的虚假共相,建立在唯实论共相之上“不死的上帝”丧失了合法性,人类理性才需要重新寻求保卫自身和平与安全的途径。霍布斯对“利维坦”之正当性的证成,对于结束现实中的动荡和理论上的纷争,其意义自不待言,但“利维坦”也面临着自身的统治困境,故期待新的推进。
关键词:霍布斯;利维坦;不死的上帝;唯名论
霍布斯的《利维坦》一直是国内外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焦点,究其缘由,是因其从契约论的视角出发,对利维坦之正当性的论证,较为圆融地构造了主权国家的“身份证”,因而成为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不可绕过去的中转站。而近来,由于施特劳斯的阐发,更是成为了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以往对霍布斯政治哲学的研究多集中在其自然状态、人性论、社会契约与主权国家这几方面,本文试图转换视角,即从神学与科学的关系中切入,反思“利维坦”诞生之先就已存在的唯名论的信仰根基,以重估霍布斯对利维坦的证成路径。诚然,在此之前,国内外已有一些研究者对唯名论与霍布斯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持肯定态度,如国外的自然法学家A.P.登特列夫在《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中就明确强调了唯名论者的世界观对霍布斯法律观念的影响[1]89,M.A.吉莱斯皮在《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第七章中更是详细探讨了自唯名论革命开始的西方神学传统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产生的影响[2];而国内部分学者也谈及了两者间的关系,笔者通过知网搜索发现共有5篇文章或隐或显地谈及了唯名论对霍布斯的影响。本文拟通过“不死的上帝”与“有死的上帝”这一对矛盾体,进一步揭示唯名论神学传统在霍布斯构建利维坦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并表明:正是在此唯名论的视域下,人类理性才开始挣脱经院神学的束缚,王权才能独立于甚或凌驾于教权,属世的王国中“有死的上帝”最终得以取代属灵的世界中“不死的上帝”。但是,霍布斯的证成路径也存在着内在的缺陷,因而有待继续推进。
一、对“不死的上帝”之批判
霍布斯通常被认为是近代政治哲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取消了古典政治哲学的目的论因素,为近代政治哲学确立了新的基础,而这一新基础的确立首先体现在他对“上帝”的新理解之上。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用“性灵的黑暗”[3]561-562这一称谓,暗讽经院传统中以哲学来解释基督教信仰所形成的唯理体系。“性灵”一词,本指一种超出我们感知范围的存在方式,属于托马斯·阿奎那所言的崇高科学(神学)领域,常被信徒虔诚地用于基督教上帝本身,表达了基督教上帝之不死的属性,即“不死的上帝”是完满、自足、永恒存在的[4]112。而霍布斯将经院神学崇高的“性灵”斥为“黑暗”。这一称谓本身就暗示着思想史的矛盾:中世纪哲学中完满自立存在的上帝之“性灵”如何成为笼罩于近代哲学之上的“黑暗”?
“性灵的黑暗”显示了当时社会中存在的深刻神学分歧。这种分歧的核心是:人的理智能否通达上帝?对这一问题的肯定或否定回答,分别对应着基督教神学史上的两种不同观点。在经院神学的理智统治逻辑中,这个世界是被神的光辉所充盈的完满、可理解、井然有序之存在;而在唯意志主义和唯名论革命中,偶然与不义却能“流溢”出必然的审美神义论之框架。而霍布斯正是接纳了植根于唯名论革命的信仰前提,才能从中论证出“利维坦”的诞生。
具体而言,在经院神学的理智统治逻辑中,圣·托马斯将亚里士多德关注自然的理性精神纳入基督教神学中,指出人的理性有一条通达上帝的途径。人的理智虽然以感觉经验之物为本性对象,但因为万物皆是上帝的分受,一切事物都以善为鹄的,人类可以收集尽可能多的知识材料,把握事物中相似于上帝的性质,将之统摄于少数几个共相之中,上帝则作为最完满的共相而存在。致知而后知止,人类对纯粹完满之上帝的认识,也是一种止于至善的努力,永远不会停歇。虽然人的理智始终无法完全把握上帝的本质,但无论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多么遥远,上帝都能克服[5]7。如此,在托马斯·阿奎那构建的经院神学中,纵使理性起着主体构造的作用,但其地基依然是对上帝虔诚的信仰,神恩成全自然而非毁灭自然。因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并不妨碍基督教思想体系中的超自然主义之实现。古典理性精神和基督教信仰间微妙的平衡共筑了经院哲学宏伟华丽的思想大厦。
而在另一派虔诚的基督徒看来,讲求理智的经院哲学却挑战了神的神性,使神的神性服从于神的理智,极度限制了神的全能。例如至善至美的上帝虽然知晓恶,却由于自己的意志为善所决定,绝不能做违背宇宙正义秩序之事。也因之遭到了司各脱、奥卡姆等人的攻击。司各脱在哲学史中被定位为一个唯意志主义者,在回答“人的理智能否通达上帝”这一关键问题时,司各脱也以意志之自由革除阿奎那理智之弊端。他指出:一方面就上帝的本质而言,上帝的存在虽是理智之必然,但上帝的本质却属意志之偶然,上帝不受任何理智法则之束缚。他可以为善,也能够作恶。他可以给人类以恩宠,却也能在顷刻间毁灭人类,一切全凭他的意志。另一方面,就人的存在方式而言,上帝的独断意志决定了人类于存有和理智上皆属偶然。“人的存在因为与上帝没有必然的关系,因而必须借着上帝的自由决定才得以存在。同样,人若要认识上帝,由于偶有理智与必然本质没有必然的关系,则亦必得凭借上帝的再一次自由决定,才能得以认识。”[6]209人类因此回到对绝对全能与冷漠无情的上帝之深深的恐惧中。如果说司各脱挑战了理智的支配地位,奥卡姆则直接开启了一场意志主导的唯名论革命。利用司各脱等早期唯名论思想家的工作,奥卡姆为一种与经院哲学完全不同的形而上学和神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认为,除了上帝的存在以外,一切皆属偶然,共相并不能拉近我们与上帝的距离,促使我们相信共相实在性的语言名称只是纯粹的符号。“奥卡姆剃刀”则进一步揭示了唯名论逻辑的指导原则: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共相。若说司各脱的理论否定了经院神学对上帝的论证范围,使上帝摆脱了必然的审美正义论的束缚,那么奥卡姆的理论就进一步否定了经院神学对上帝的论证方式,使人们从共相接近上帝的企图彻底落空。
因而我们发现,霍布斯是用唯名论的“上帝”观念反叛了经院神学中“不死的上帝”,正是基于唯名论的上帝观,霍布斯才得以将经院神学中依据共相建立起来的永恒完满的上帝斥之为“性灵的黑暗”。如果说由于17世纪的政治现实,霍布斯不可能完全抛弃上帝的观念,那他大可拥抱任意一个上帝,不必非得在著作中对经院神学的上帝观大加挞伐。显然,霍布斯的理论旨趣并不止于此,批判经院神学的上帝观只是他创建自己全新政治哲学的前提性工作,他的最终目的是用科学的方式构建出一个给予人类和平安全的主权国家。而只有唯名论中全知全能、对人类漠不关心的上帝才能与由人类理性构建出来、拥有绝对权威的主权者相安无事。实际上,唯名论开辟了一种理解人类的全新可能性,打破了经院哲学等级森严的存在论秩序,重新将“人”从“上帝”中解放出来。既然人类理性不必再受经院哲学家创造的虚假共相指导,人服从任何道德律令都无从产生神的救赎,那么唯一现实的存在就是个体本身。在意志主导的宇宙鸿蒙中,上帝对人世漠不关心,人类只能运用自己的理性改善在尘世的命运。人的理智被迫为自己划分界限,以一种更加谦逊而坚定的方式,在自然世界和人类事物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正是凭借唯名论的世界观,霍布斯才能从目的上确立最高主权者存在的依据,并且在方法上用人类理性的手段直接推导出“利维坦”的诞生。
二是建立分层次的合同签订制度。要按照合同标的额、履行难易程度等指标将合同划分为一般合同和重大合同。对于一般合同应当规范其前期谈判、缔约过程、文本审查和履行结算报告制度。对于重大合同,除遵循一般合同的管理制度外,还应当建立内部联合审批以及定期履行报告制度,避免因合同签订引起的纠纷。
在当时的语境中,教会作为性灵的王国之现世组织、教皇作为教会的最高职权者,在世俗中无疑享有最崇高的地位。一方面,基督教教权依据圣灵而存在,被看作是圣灵在人间唯一的代表,人们要获得救赎与平安必须依赖教会;另一方面,国家主权则从基督教教权中获得自身的合法性依据,任何一个国家主权者必须得到教皇的任命才能实现自身的统治。但遗憾的是,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国”在人间始终无法找到根基,这个国家主权与基督教教权相互缠绕的蜘蛛网只是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纷争与苦难。霍布斯看到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他尖锐地指出:教皇依据自身统治欲而建立起来的教会只是一个政权组织,它要求人们外在的服从;而《新约》和《旧约》中所提到的上帝国却产生于人们内心的敬仰,它体现了人类意志的自由和理性的抉择。[3]563在“性灵的黑暗”之影响下,人们误将今世现存的教会当作《新约》和《旧约》中所提到的上帝国。[3]558但“今世在地上的教会”虽冠以耶稣基督之名,却是人为的政权组织,实与自然的“上帝之国”背道而驰。“自然之国”和“人为之国”性质的区分,正是国家怪兽“利维坦”诞生之契机。霍布斯在拒斥经院神学中“不死的上帝”在人间的统治之后,需要进一步解决世俗生活中人们对信仰的需要和权威的服从问题,也就必然要塑造一个人间的“利维坦”来稳定社会秩序。
本研究中尽管CD56+组的骨髓原始细胞比例、外周血RBC和PLT的量有低于CD56-组的趋势,而外周血WBC和Hb有高于CD56-组的趋势,但两组间的差异并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这可能与CD56的生理功能有关,CD56抗原是存在于细胞表面的一种糖蛋白,属于免疫球蛋白超基因家族, 富含聚唾液酸,可形成一种高腺苷酸屏障,降低细胞的黏附力,使肿瘤细胞更易侵袭性生长。可见CD56与AML患者白血病细胞的髓外侵袭性有关,而对骨髓的增殖并无影响,所以CD56+组与CD56-组间骨髓原始细胞比例和外周血WBC、RBC、Hb和PLT的差别不大。
在找到“利维坦”存在的根据之后,霍布斯更进一步处理了唯名论的上帝与人间主权者“利维坦”之间的关系。在《利维坦》第四十三章,霍布斯指出:背负原罪的人需要服从和信仰这两者的结合以得救。“服从”在于尊奉上帝神律的意志,“信仰”根于相信耶稣是基督,也即相信拿撒勒的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以色列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子。神爱世人,同样,神也统治着世人,两者之间不存在吊诡。“教导是信仰的原因……教义既然要由最高教士审定,所以每一个国家中一切没有得到特殊神启的人所要相信的人便是最高教士,也就是世俗主权者。”[3]476如此这般,信仰成了服从,对上帝的服从和对世俗主权者的服从之间不分轩轾。可以看出,霍布斯的野心是非常大的,他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天国的存在,但他在某种程度上将上帝的天国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尘世王国,将人的目光从神坛上拉下来,使国家在宗教合法性的外衣下获得了新生。
二、“人间的上帝”的挺立
从霍布斯的物理学中,我们已经了解到,自然状态下以感觉为唯一准绳的人类在外界持续不断的刺激中,会产生朝向某物或躲避某物的内在自觉运动,也即欲望与厌恶。每个人都欲求有利于自身之物,并厌恶不利于自我保存之事。自然状态最开始是十分美好的。由于经院哲学的存在论等级秩序被打破,古代智者学派人人平等的自然权利观点以一种新的视角出现在近代思想家的眼前,成为人类幸福的第一条件。霍布斯谈到:“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十分相等”[3]92,每个人都拥有不受外部限制地追求激情对象的自由[3]62,人人都拥有对所有事物的自然权利。然而这种平等却转瞬即逝,由于激情的影响,人类很快由美好的自然状态堕入不平等的战争状态。他谈到:“心灵永恒的宁静在今世是不存在的,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同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3]45机械的运动永不休止,人类的欲望也永无止境,而资源总是有限的,故唯有强者才拥有对物品的所有权。如同《理想国》中色拉徐马霍斯所言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7]14,争斗便作为人们实现欲望的附属物而出现了,在这场和机械指针赛跑的旅途中,人除了成为优胜者,别无其他目的。人们相互争斗、相互倾轧,每个人对所有事物的自然权利也就相当于人人都丧失了其自我保存的能力,人类时刻处于对暴力死亡的恐惧之中,自然状态中的人类生活最终是“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3]95的。激情主导的自然状态最终只能导致“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实际上,霍布斯对经验主义和机械法则的推崇,是当时自然科学不断发展的结果,也构成了他政治哲学的起点。在后文中我们将看到,离开了感觉确定性和机械的因果链条这一科学前提,人类的自然状态不可能演变成战争状态,霍布斯也就不可能建立起植根于人类恐惧心理的主权国家学说。而反过来,我们也会惊奇地发现,正是唯名论革命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和政治哲学的步伐。这一场革命使得人类回到对全知全能上帝的绝对恐惧和对偶然世界的巨大不安中,而近代自然科学和政治哲学的发展甚至是宗教改革的进程,也都是为人类在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重新找到确定性的不断尝试。所不同的只是,有些人将这种确定性诉诸于充满先天理性原则的人类心灵,如笛卡尔;有些人将之诉诸于自然界的真实性与人类感觉的确定性,如霍布斯;还有些人将之诉诸于内心对上帝虔诚的信仰,主张因信称义原则,如路德。而其中,霍布斯和笛卡尔是处于同一时代的人物,他们分别代表了近代哲学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两大思潮,并且就之与对方引发了巨大的争论。笛卡尔通过普遍数学的分析方法,得出“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命题,以“我”为根本基点,弥合了纯理智的东西(数学对象)和感官所能认识的物体之间的鸿沟,以确定性和自然科学取代了信仰和神学,在唯名论全能之神的恐惧中重新找到了自身的位置。但霍布斯却反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理论前提,指出不仅物质之外没有精神,而且思维着的“我”本身也是物质的,人类的想象、推理这些思维活动都不过是与之相关的有机物体的运动而已。但从其合题来看,无论是笛卡尔式的以数学这一最完美手段来理解和掌控自然也好,还是霍布斯式的在自然界和现实秩序中找到最高的科学确定性与人类幸福的终极方案也罢,两位思想家都完成了时代赋予他们的寻找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崇高使命。
霍布斯要在唯名论视域下构建一种物理学,首先需解释物体存在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其次需阐明唯名论那个绝对全能而又冷漠无情的上帝意志如何表现在物体运动法则中,他的经验主义和机械法则分别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霍布斯秉持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事物的存在优先于语词的本质”,语言推理有真假之别,自然感觉则确切无疑[3]22-23。他指出经院哲学家所谓“无形体的实体”“吹入的美德”[3]25-26“颜色存在于物体之中”[3]30-31等语言推理的荒谬,进一步批判了“性灵的黑暗”,确证了经验主义的立场。他的机械法则进一步批判了古典目的论体系,打破了经院哲学的等级秩序,使万物丧失了趋向上帝之最高善的内在目的论维度。自然界中只有机械的原因链条和力量的相互抵消,对人类漠不关心的上帝意志只存在于机械宇宙持续不断的碰撞中,人们的一切自愿行为本质上都是外部运动的必然结果[3]164。所谓最具主动性的激情也只是人类在感觉经验到外界物体对身体持续不断的碰撞与刺激之后产生的朝向某物(appetite)或躲避某物(aversion)的内在自觉运动。
最后,既然建基于自我保存原则上的“利维坦”有失败的可能,那么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著名自然法学家登特列夫曾对此做过系统的分析。登特列夫谈到:“他(霍布斯)的法律概念是唯名论者的概念,他的道德理论摒弃绝对价值的观念,他所谓的国家乃是人为的产物,而不是历史的产物。”[1]89登特列夫秉承“绝对价值的观念”,认为只有托马斯·阿奎那流派永恒的自然法才是真正的自然法,而霍布斯的自然法观念有名无实,是“唯名论者的概念”和“人为的产物”,登特列夫进而用实证法这一名称来定义霍布斯所开创的近代自然法,他认为实证法由于背离了永恒自然法的价值倾向而始终面临着自身的困境。对此,罗门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中也谈到:“在整个19世纪,这种形态的自然法在科学的世界中被当作最高级的自然法,因而,反对它的战斗被视为是对整个自然法的战斗。由此,现在已经开始了其胜利大进军的实证主义十分轻松地获得了它的桂冠,因为它确实能够击败这样一种历史性的法律哲学形态,它自称为自然法,其实并不是自然法的理念本身。甚至在演绎的激情淹没一切的那些世纪,后者也一直被永恒哲学所坚持。在该问题的每一历史性背景中它都试图重新获得确认,一直到实证主义耗尽,形而上学复兴,19世纪的精神崩溃,它才在革新后再度归来。”[8]98但我们也清楚,实证法在提供具体的法律细节、规范现实的社会秩序方面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因而这里的问题不在于自然法和实证法之间的对立。对霍布斯作为一个法律实证主义者的责难,也不是对实证法本身的批驳,而是要反思人类社会秩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自然法,法律能否依凭命令而实现自身的统治,以及人类能否仅靠他律而良好生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霍布斯的确需要一种具有现实效力的实证法来稳定社会秩序,但如果这一实证法的确立是为了彻底取代自然法的正义观,那就得不偿失了。对法律超越性维度的抽丝剥茧虽然能够带来一时的安稳,但却会使“利维坦”陷入长久的统治危机中。社会机制的确立必须与对绝对价值的追求相结合,才能稳固自身的统治。虽则在地上没有像“利维坦”造的那样无所惧怕,但天上却必须有他要畏惧的对象。对于上帝永恒的自然法,“利维坦”也应当遵从。
从奥卡姆到霍布斯的三百多年间,英格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既孕育了人文主义思想和科学理性精神,同时也造成了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时代赋予了霍布斯以建立一种公正持久的政治秩序之崇高使命,而在霍布斯眼中,只有拥有令人恐惧力量的“利维坦”才能守护人类的和平与安全。如上所述,霍布斯首先在唯名论的视野下批判了经院神学中“不死的上帝”,确立了“利维坦”存在的依据。接下来,霍布斯则用理性的手段,从自然状态中推导出了“利维坦”的诞生,最终实现了“有死的上帝”在人间的统治。在霍布斯的理论建构中,从描述物体性质及其运动定律的物理学,到描述人性及其运动倾向的人类学,至最终建立一种社会机制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类和平的政治学,也即霍布斯用理性的手段以此推导出的“利维坦”诞生过程,同样建基于一种唯名论的认识论,正是在此关联中,作为人间上帝的“利维坦”,才得以挺立。
在得出了根本上非正义的战争状态之后,霍布斯接着谈到:“然而这种状况却有可能超脱:这一方面要靠人们的激情,另一方面则要靠人们的理性。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对舒适生活所必需的事物的欲望,以及通过自己的勤劳取得这一切的希望。于是理智便提示出可以使人同意的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3]97霍布斯在此引入了自我保存这一根本原则:自然状态下的人类为了自我保存而不断欲求,然而当人类的激情在无休无止的权势欲之追逐中,重新危及到自我保存这一根本原则之后,又会演变成对死亡的畏惧这一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此时理智就作为另一保存自我的手段出现在人们眼前。如此,当终极的目的和最高善的维度被取消之后,激情成为人性中的首要元素,理智也失去了经院哲学中应有的地位,沦落为人类保存自我的工具。因而,古典政治哲学中理智对欲望和激情的控制能力让位给近代政治哲学中的自我保存力量,自我保存原则也一跃而成为自然法的基本内核。凡是有利于自我保存的,便是正义;而威胁人类保存自我生命的,就是不正义。若说除了唯名论那个对人类漠不关心的上帝意志之外,还有什么自然法存在,那就是说,“神通过自然法,提供了一种自我保存的动力,它为一种将使我们掌控和拥有自然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因此,霍布斯的科学不仅旨在理解世界,而且旨在改变世界,给人类力量保护自己,改变人类在尘世的命运。回应破坏人类生活的普遍恐惧,带给人类力量、安全和幸福。”[2]301正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权衡和自我保存原则,霍布斯才能从“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进一步演绎出持久稳定的公民社会,实现从人类学到政治学的过渡。
如前所述,自我保存原则成为近代自然法观念的基本内核,而人类理性在充分认识到这一基本前提后也反过来将其作为自然法的第一条诫命,其它一切法则都由此推出,都是对寻求和平或自我保护方法的说明。因而,自然首要的法则是:“每一个人只要有获得和平的希望时就应当力求和平;在不能得到和平时,他就可以寻求并利用战争的一切有利条件和助力。”[3]98人类理性在利弊权衡中又给出了第二条自然法则:“在别人也愿意这样做的条件下,当一个人为了和平与自卫的目的认为必要时,会自愿放弃这种对一切事物的权利;而在对他人的自由权方面满足于相当于自己让他人对自己所具有的自由权利。”[3]98这种权利的转让就是建立契约。第一条自然法描述了人类追求和平的目的,第二条自然法描述了所有政治努力的手段,政治学的其余内容都源于此开端。但契约关系的产生还不足以使人类走出战争状态,在唯名论的个人主义影响下,如果人们认为打破契约比遵守契约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好处,那么人类就会毫不犹豫地打破契约,当所有人重新拥有对所有人的权利之后,人类又不可避免地回到战争状态。于此,“就必须有某种强制的权力存在,以使人们所受惩罚比破坏信约所能期望的利益更大的恐惧来强制人们对等地履行其信约,并强制人们以对等的方式来维持通过相互约定、作为放弃普遍权利之补偿而获得的所有权。”[3]109而只有自然状态下的所有人作为授权人同时将自己的权利托付给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集体中,这一个人或集体作为大家的代理人使自己的意志成为共同体的意志,强制的权力才能发挥作用,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3]132或者说“人间的上帝”的诞生。如此,使人走向和平的对暴死之恐惧演变成了对伟大“利维坦”之畏惧,自我保存这一根本道德前提也转换成了对信约之遵守与对国家主权意志之服从。因而,主权者在国家中就像唯名论的神在宇宙中一样,拥有令人恐惧的绝对权能。但“利维坦”又不同于唯名论全能的神,因为它作为“人造之人”取代了神在世间的绝对统治,实现了从“不死的上帝”到“有死的上帝”之转变,并在意志主导的混乱宇宙中给予人类和平和安全的保障。
1.2 麻醉方法 术前12 h禁食,术前4 h禁饮。两组患者均给予托咪酯(0.2 mg/kg)、丙泊酚(0.5 mg/kg)、顺苯磺酸阿曲库铵(0.2~0.3 mg/kg)和芬太尼(5.0~6.0 μg/kg)静脉注射,行麻醉诱导。A组患者接受七氟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维持麻醉,浓度为2%~4%;B组患者接受右美托咪定(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维持麻醉,诱导前5 min以0.5~1.0 μg/kg静脉泵入,麻醉维持期间以0.2~0.4 μg/(kg·h)静脉持续泵入。两组患者均在手术结束前20 min停止给药。
综上,霍布斯是以唯名论上帝观为起点,一步步抽丝剥茧,为国家找到宗教的合法性外衣。并且从自我保存这条最基本的自然法出发,依赖经验论证与理性推理,成功推导出“利维坦”的诞生。而一旦由所有人的意志实现的单一人格形成之后,国家虽然仍受自然法这一最高法则的支配,但国家主权者的意志已具有绝对的权威,国家主权者以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的根据,通过制定法律限制人们的自然权利,避免人类由公民社会重新堕入自然状态中。公民只能听从国家主权者的法律和命令,对之有服从的义务,虽然与此同时公民也享有对超自然上帝之信仰的权利,但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却必须履行。如此,在霍布斯从感觉经验主义所滋生的理性法则中,人的理性只能思虑可感觉的事物,公民也只对由自己意志所组成的国家负有义务,而那全知全能、不可思量的天主,也只能形同虚设了。于此种刻意为之的“得鱼忘筌”之努力中,国家兼具宗教的合法性与主权的绝对权威,但也在主权的绝对权威之证成中,宗教被彻底架空。于是,“凯撒的当归给凯撒,上帝的当归给上帝”(路加福音20:25),既成为霍布斯对王权的论证,也是他真实意图的最佳反谶。
三、“利维坦”的统治困境
虽然“利维坦”作为“有死的上帝”取代了“不死的上帝”在人间的统治,但正因为它是“有死的”,它在人间并不完全自足,始终面临着自身的统治困境。那么,“利维坦”的统治困境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困境?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它?
首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利维坦”具有绝对的权威,它要求公民对之绝对服从。但也正因如此,它反而经常受人诟病,人们虽然无法从逻辑上避免“利维坦”的诞生,但却可以从结果上怀疑“利维坦”权威的确实性。事实上,这一质疑并非毫无道理,霍布斯甚至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暗示了“利维坦”的统治困境。他指出:一方面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中,由于法律制定者无法预料现实所有行为,公共法律依然为私人判断留有余地,[3]164而这一“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区分便作为动摇“利维坦”之统一性的罅隙一直存在。而要进一步考虑国家主权之下依然合法的私人判断,就是要思考当人们建立一个国家时究竟出让了哪些权利。毫无疑问,公民对“利维坦”的服从义务就来自于“利维坦”依据其自身武装力量而对个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因而人类自我保存的自然律法始终高居于“利维坦”之上,一旦“利维坦”命令公民去做伤害自身生命的事,例如要求公民上阵杀敌,公民就可以根据私人判断权(用自己的理性去保存自我生命的法则)而拒绝服从。[3]170另一方面在国家与国家的关系中,“利维坦”同样面临着棘手的难题。虽然“利维坦”的诞生代表民众从自然状态走向了文明社会,但“利维坦”(主权国家)之间却仍然处于“自然状态”中。究其根本,国家是代表全体公民意志的单一人格,具有最高的规定性与无可置疑的权威,但也正因如此,国与国之间就如自然状态下一切人拥有对一切事物的权利一样,彼此非理性的对峙抗争而不为不义。对此,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给予了十分鲜明的描述,“古希腊罗马人的哲学与历史书以及从它们那里承袭自己全部政治学说的人的著作和讨论中经常推崇的自由,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国家的自由,这种自由与完全没有国法和国家的时候每一个人所具有的那种自由是相同的。后果也是一样。因为在无主之民中,那儿永久存在着人人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3]166至此我们发现,“利维坦”至高无上的权威始终以个人自我保存的权利为前提,它不仅没有权力命令公民去保卫国家,而且没有办法阻止他国对自己的侵犯。如此,“利维坦”就深陷统治囹圄。
而进一步,为什么会产生这一困境呢?毫无疑问,霍布斯用以推演“利维坦”的手段是科学的,“利维坦”的诞生也是拥有自身合法性依据的。既然这一过程无可指摘,我们就只能从开始找原因。之前提到,霍布斯推演的背景是唯名论革命,推演的前提是个人自我保存的自然权利。但事件背景是已经发生的、无法改变的,而前提条件却是自己选择的、可以变更的,故尽管前提条件可能从特定历史背景中发端,我们也只能追因溯源至假设的理论前提而非已成定论的历史背景。之前曾提到,自我保存权利成为霍布斯眼中自然法观念的基本内核,它为社会政治秩序提供了基本前提,正是由于这一内在驱动力,不同个体之间才会放弃彼此对他人享有的权利并且互相签订条约,由战争状态步入公民社会。现在要问为什么“利维坦”会产生自身的统治困境,也就必须追问霍布斯为什么选择自我保存这一个体自然权利作为其自然法观念的合理内核。我们知道,在经院神学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的眼中,从上帝到万物之间有一个完满的存在论等级秩序,万物皆是上帝的分有,所有事物都朝向永恒完美的上帝而存在。因而在此意义上,作为宇宙秩序中正义法则之基础的自然法,就只能是理性受造物对来自上帝之永恒法的分有。这种自然法体现了一种对永恒价值的追求,它是神圣的义务而非狭隘的个人权利。然而当唯名论打破了经院神学完满的存在论等级秩序之后,个人对最高善的内在驱动力也因之丧失,人人生活在对偶然世界和绝对权能上帝的恐惧中。在霍布斯所处的那个年代,情况进一步恶化,人们不仅需要找到价值追求的根基,而且需要面对社会动荡纷争的事实。于此,霍布斯才将自然法的有效性从永恒的价值理性追求转化为个体狭隘的自我保存诉求,法律也因之由审美的理智转变为暴力的意志。正如霍布斯在《利维坦》第二十六章反复强调的,法律只是权威者的意志和命令,不涉及真理。“伦理道德虽然天然是合乎理性的,但唯有通过主权者才能成为法律。”[3]215反过来说也是一样,“国家以法令宣布为神律时,所有的臣民便必须把它当成神律服从……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准许人们在国家所宣布的上帝诫律以外再宣称有其它的上帝诫律。”[3]224
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大厦由物理学、人类学到政治学这一逻辑推理链条构成。人类学作为霍布斯物理学和政治学之间的过渡论述,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首先在从物理学到人类学的过渡论述中,霍布斯引入人类自然平等的前提,指出在激情的作用下,人类会由和平安宁的自然状态堕入相互为敌的战争状态。接着霍布斯开始寻求使人类走出战争状态的途径,他揭示了人类自我保存原则及作为自我保存手段的理性,寻求人类用理性为自身营造和平条件的方式,实现由人类学到政治学的过渡。
四、结语
通过前文的脉络梳理,我们发现,虽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是,霍布斯由于系统说明了自然状态理论、创建了主权国家学说而在近代政治哲学中享有重要地位,但在这些直观的表象背后,始终隐藏着一个唯名论的神学传统。无论是曾经长期统治自然的机械法则也好,还是主权高于一切的国家理论也罢,离开了这场神学革命都不可能产生。现代科学的理性精神居然受惠于一场神学革命,这点乍一看似乎过于费解,但却是任何想要真诚了解自己文明的人所不得不走的路径。正是在唯名论神学革命之后,霍布斯才有可能拨开“性灵的黑暗”这层迷雾,为政治哲学找到新的生长点。当唯名论革命打破共相之后,人失去的只是锁链,得到的将是一切。然而,当“人”从“上帝”中解放出来之后,问题又进一步产生了:当信仰退居幕后,骄傲的人类理性在大张旗鼓地改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进程中,又反过来给人类带来灾难。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利维坦”面临着自身的统治危机,人类也面临着自然界的多样性严重受损、人类在精神信仰层面的缺失、给全世界带来毁灭性打击的战争等的威胁……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我们需要不断反思、不断进步,才不至于被淹没。因而,本文虽然反思了霍布斯政治哲学的历史,指出其唯名论的神学背景,重评其对“利维坦”的证成路径,但价值导向却在于指出霍布斯的政治哲学需要改进的方向,表明霍布斯的“利维坦”必须要重拾永恒自然法的传统,才能确立“有死的上帝”在人间的统治。
参考文献:
[1]登特列夫.自然法——法律哲学导论[M].李日章,梁捷,王利,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2008:5.
[2]米歇尔·艾伦·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M].张卜天,译. 长沙: 湖南科技出版社, 2011:11.
[3]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杨昌裕,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5:9.
[4]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一册:论天主三位一体[M]. 台南: 碧岳学社,中华道明会联合出版,2008.
[5]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第二册:论天主创造万物[M]. 台南: 碧岳学社,中华道明会联合出版,2008.
[6]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精神[M].沈清松,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1.
[7]柏拉图.理想国[M].张竹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15:1.
[8]海因里希·罗门.自然法的观念史和哲学[M].姚中秋,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7:5.
From“theImmortalGod”to“theMortalGod”:onHobbes’sValidatingpathto“Leviathan”
WANG Shizhong1, HU Ting 2
(1.CollegeofPhilosophy,NankaiUniversity,Tianjin,300350,China;2.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In his validating “leviathan”, on the one hand, Hobbes accepted the Top-down belief premise which was grounded in the Nominalist Revolution; on the other hand, Hobbes felt obliged to respond the Down-top rational tradition since the Modern Enlightenment. When the “Occam’s Razor” destroyed the illusive universals of the Scholasticism and the “immortal God” founded on the universals of Realism lost its legitimate foundation, Human reason therefore needed to seek other ways to defend its own peace and stabili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at Hobbes attempted to keep civil unrest and theoretical strife at bay by legitimizing God in the secular state (“Leviathan”). However, “Leviathan” also faced its own ruling dilemma, so there is still a room to improve.
Keywords:Hobbes; Leviathan; the Immortal God; nominalism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9)02-0007-07
收稿日期:2019-01-23
作者简介:
王时中,男,湖南宁乡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式中:GPS为排放绩效,g/kWh;E为污染物许可排放量,g;D为理论发电量,kWh;c为污染物许可排放浓度,mg/m3;M为废气排放量,m3;CAP为装机容量,MW。
胡 婷,女,湖南石门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西方近代政治哲学。
近日,由中国机电一体化技术应用协会和安特威集团联合主办的“第三届石油和化工仪控技术大会暨安特威智能智造发布会”在苏州成功召开,来自各大工程公司、行业协会、设备制造商约500人共襄盛举,共同探讨如何建设安全、环保、智能工厂,共同见证了安特威近年来所取得的智能智造成果。
本试验所采用的高庙子膨润土产自内蒙古兴和县,其主要成分为蒙脱石,伴生矿物为石英、方解石等[10],主要矿物成分以及物理特性参数如表1所示,其中液塑限用联合测定仪测得.我国已确定在甘肃北山地区修建高放废物深层处置库,该地区地下水中溶解固体的阳离子主要是Na+,阴离子主要为Cl-[3].本试验采用NaCl作为盐溶液的溶质,以模拟该地区地下水中的盐溶液.本试验中混合物所用的砂为福建标准砂,去除了粒径大于0.5 mm的颗粒.砂比重为2.66,图1为GMZ07膨润土的粉末状及其饱和压实试样.
(责任编辑:方英敏)
标签:霍布斯论文; 上帝论文; 唯名论论文; 自然法论文; 人类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世界政治思想史论文;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