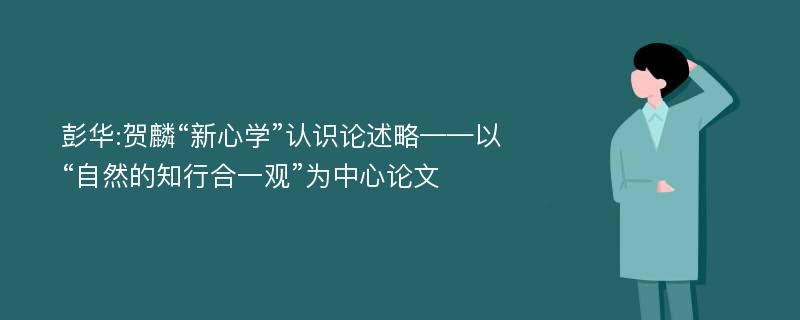
●历史学
摘要:贺麟“新心学”认识论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是从知行的概念、“合一”的意义、知行的关系、知行的难易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和展开的,包括四个基本命题(或结论)——“知行同是活动”、“知行永远合一”、“知主行从”、“知难行易”。“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与任何一种价值合一观都不冲突、不矛盾,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理论奠定了认识论的学理基础。
关键词:贺麟;新心学;知行合一;知难行易;自然的知行合一观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1902-1992)就建立了“新心学”思想体系,成为中国现代新儒家思潮中声名卓著的重镇,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①。
培训准备阶段:在培训准备阶段,培训教师需要与培训组织方进行深入沟通,针对乡村旅游具体要求,制定培训计划。同时需要到培训场地进行实地考察,重点考察培训设备、培训耗材准备等情况。培训教师需要较长时间对培训内容进行研讨,并与培训组织方充分沟通,确定最终培训方案。
贺麟的“新心学”,是对中西文化的融通,是中国的陆王心学与西方的新黑格尔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心即理”的唯心论(本体论),辩证法与直觉法(或理智与直觉)有机结合的方法论,“自然的知行合一观”的认识论,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三条途径的论述,是构成贺麟哲学思想的主要部分。
在认识论领域,贺麟吸纳了朱熹(1130-1200)、王阳明(1472-1528)的知行合一说,同时借鉴了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1632-1677)、格林(Thomas Hill Green,1836-1882)、鲁一士(Josiah Royce,1855-1916)和行为心理学的观点,构建了自己的认识理论,这就是“自然的知行合一观”。
在此,需要事先说明的是:中国哲学传统所讲的知行问题,最主要的是伦理道德问题,当然也包含认识论问题②。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所讲的知行问题,贺麟对它们进行了现代学理意义上的、认识论方向的改造。
在贺麟看来,就学理而言,“知行问题,无论在中国的新理学或新心学中,在西洋的心理学或知识论中,均有重新提出讨论,重新加以批评研究的必要”,因为“不批评地研究知行问题,而直谈道德,所得必为武断的伦理学(dogmatic ethics)”[1]130-131;就现实而言,“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足以代表中国现代哲学中讨论得最多,对于革命和抗战建国实际影响最大的一个问题”[1]4。但是,自从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后,“此后三百多年内赞成、反对阳明学说的人虽多,但对知行合一说,有学理的发挥,有透彻的批评和考察的人,似乎很少”[1]130。
贺麟说,从自然的知行合一来讲,知行既然合一、同时发动、平行并进,应当说“知行同其难易”;而就高程度的知行合一的活动言,应当说“知行同样艰难”;又就低程度的知行合一程度言,应当说知和行“两者皆同样容易”。那么,知行的难易究竟如何呢?于是,贺麟搬出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在贺麟看来,孙中山所谓的“知难行易说”,是说“显知隐行难”(如科学研究)、“显行隐知易”(如日常饮食的动作)。依照贺麟所提出的“知主行从”说,“显知隐行永远决定显行隐知”,“较高级的知行合一体永远支配较低级的知行合一体”。如此便可推出,“显知隐行较高级的知行合一体当然难,而显行隐知较低级的知行合一体当然容易”。至此,贺麟指出,“故照这样讲来,知难行易不惟是确定的真理,而且与知主行从之说互相发明”[1]146,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归宿是知行合一说”[1]189。
1938年12月,代表贺麟知行观的重要文章《知行合一新论》,完稿于昆明。该文后作为“国立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文集”之一,于1940年1月在昆明出版单行本(抽印本)。后来,该文又相继收入《近代唯心论简释》和《当代中国哲学》(后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知行合一新论》一文,是贺麟自以为“有不少新意思”的论文[1]新版序,2。其后,贺麟在《三民主义周刊》又发表了《对知难行易说诸批评的检讨》《知难行易说的绎理》《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等文。通过这些论文,贺麟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自然的知行合一观”。
贺麟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是从知行的概念、“合一”的意义、知行的关系、知行的难易等几个方面进行论述和展开的。由此出发,贺麟对历史上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全新的考察。与此相对应,贺麟的“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包括四个基本命题(或结论)——“知行同是活动”“知行永远合一”“知主行从”“知难行易”。
大量在役永久设备长期运行未能定期进行专业质量安全检测,给工程运行带来安全隐患;目前行业仅对启闭机等永久设备的生产制造环节实施许可管理,而设备安装、运行维护等环节是实施全过程监督管理的重要组成,对保障设备安全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缺乏专业质量安全检测。部分启闭机、闸门等永久设备缺乏必要的定期安全技术检定,对产品运行质量状况不明。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部分在役产品存在不同程度的质量问题,给工程运行带来安全隐患,甚至诱发发生安全事故。
一、知行的概念
贺麟不仅从正面发挥“知主行从说”的道理,而且从反面批驳了“行主知从说”。贺麟认为,西洋心理学上的副象论(epiphenomenalism),詹姆士(William James,1842-1910)、兰格(Carl Lange,1834-1900)的情绪说,以及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布里奇曼(Percy Williams Bridgman,1882-1961)所持行主知从的知行合一论,都是不能成立的。以“副象的情绪论”而言,便是错误颇多,“第一,不能解释许多普遍的经验事实”,“第二,此论既不就整个事实立论,亦无坚实理论基础”。贺麟举例说,逃避老虎的“行”不是“知”之始,见虎畏虎的“知”不是“行”之成。反之,我们可以依照王阳明说:见虎畏虎的“知”,是避虎的“行”之始;避虎的“行”,是见虎畏虎的“知”之成[1]142-145。
贺麟接着指出,“知”和“行”都是“有等级可分的”,但他认为,于此不必深究,“我们只需确认知与行都是有等级的事实即行”。贺麟进一步指出,“知”和“行”都有“显”(explicit)与“隐”(implicit)的区别。以“行”而论,最显著的生理动作,如动手动足的行为,便是“显行”;最不显著或隐晦的生理动作,如静坐、思的行为,便是“隐行”。“显行”与“隐行”虽然有如此区别,但必须明白的是,“显行与隐行间只有量的程度的或等级的不同,同是行为,而且同是生理或物理的行为”。以“知”而论,最显著的意识活动,如思、推理、研究学问,便是“显知”;最不显著或隐晦的意识活动,如本能的知识、下意识的活动等,便是“隐知”。“显知”与“隐知”虽然有如此区别,但必须明白的是,“显知与隐知间亦只有量的、程度的或等级的差别,而无根本的不同,或性质的不同”。就“知”和“行”的“显”“隐”而论,“最隐之行,差不多等于无行”,“但就理论上,我们也不能称之为生理动作”;“最隐之知,也差不多等于无知”,“但客观地讲来,此种‘无知之知’,也是一种知。只可谓为隐知,但不能谓为绝对无知”[1]132。
12月6日,知名华裔科学家张首晟家人发布声明,确认张首晟于12月1日因抑郁症意外去世,终年55岁。张首晟生前为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终身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是杨振宁的学生。因为“量子自旋霍尔效应”和“天使粒子”的发现,张首晟在全球科学界屡获殊荣。学术领域之外,他于2013年创立丹华资本,专注于投资最具颠覆性和影响力的科技成果和商业创新。
总之,贺麟认为,“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基础,不然理论不坚实;“知难行易说”应以“知行合一说”为归宿,不然理论不透彻。可以说,“由知难行易说必然逻辑地发展到知行合一说”[3]29。
二、“合一”的意义
贺麟认为,“知”和“行”的关系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具体说来,“知”和“行”的关系有一个类似于“正反合”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1)既要指出“知”和“行”本来是“合一”的(不是“混一”),(2)也要分析清楚“知”和“行”如何分而为二、彼此对立,(3)最终更要明了“知”和“行”又如何复归于一。从(1)到(2)到(3),这是“一个三部曲”[1]133。
贺麟所说的“知行合一”,指的是“知行同时发动(coincident)之意”,亦指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面”,又是“知行平行”的意思。这是贺麟为“知行合一”所作的三个规定。
所谓“知行同时发动”,即意识的活动(“知”)与生理的活动(“行”)“同时产生或同时发动”。在时间上,知行不能分先后。既不能说“知先行后”,亦不能说“知后行先”,“两者同时发动,同时静止”。贺麟交代,用“同时发动”来解释“合一”,实则采自斯宾诺莎[1]133。斯宾诺莎主张“身心合一”,认为身体的动作与心的活动是同时发动的,“身体之主动与被动的次序,与心之主动与被动是同时发动的”(斯宾诺莎《伦理学》分三,“命题二·附释”)。
“哦?”霍铁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可是……”他想了一下,止住了话头,又问:“对了,陆叔叔制作完成的蜡像放在哪里?”
“知行平行说”与“知行两面说”,实际上是互相补充的。“单抽出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孤例来看,加以横断面的解剖,则知行合一乃知行两面之意。就知行之在时间上进展言,就一串的意识活动与一串的生理活动之合一并进言,则知行合一即是知行平行”[1]134。
具体说来,“知行平行说”包括下例三层意思[1]134-135:(1)“意识活动的历程与身体活动的历程乃是一而二,二而一,同时并进,次序相同”。(2)“知行既然平行,则知行不能交互影响。知为知因,行为行因。知不能决定行,行不能决定知。知不能知身体动作,行不能使知识增进”。这是就自然事实而言。(3)就研究方法而言,知行“各自成为系统,各自不逾越范围”。以行释行,产生纯自然科学(如生理学、物理学及行为派的心理学);以知释知,产生纯哲学或纯精神科学。前者纯用机械方法,后者纯用逻辑思考。
总之,贺麟认为,“任何一种行为皆含有意识作用,任何一种知识,皆含有生理作用。知行永远合一,永远平行并进,永远同时发动,永远是一个心理生理活动的两面。最低级的知永远与最低级的行平行。……最高级的知与最高级的行,所谓真切笃实的行,明觉精察的知,亦永远合而为一,相偕并进”[1]136。由是,贺麟提出了“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又称“普遍的知行合一论”),“此种的知行合一观,我称为‘普遍的知行合一论’,亦可称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一以表示凡有意识之论,举莫不有知行合一的事实;一以表示不假人为,自然而然即是知行合一的事实”[1]136。
三、知行的关系
带变量核的Marcinkiewicz积分算子在变指标Herz型Hardy空间上的有界性 辛银萍,陶双平(6-38)
所谓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面”,是指“与行为同一生理心理活动的两面(two aspects of the same psycho-physical activity)”而言,“知与行既是同一活动的两面,当然两者是合一的”。这里所说的“知行合一”,是指“同一生理心理活动的两面”,而不是指所谓甲的“知”与乙的“行”这样不同主体间的知行关系。正因为“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面”,所以说“认知行合一为知行同时发动,方有意义”。由于“知行是同一活动的两面”,所以“知与行永远在一起(always together),知与行永远陪伴着(mutual accompaniment)”,就如手掌与手背是整个手的两面。对此同一的活动,从心理方面看是“知”,从生理或物理方面看是“行”,只是“用两个不同的名词,去形容一个活动的历程”。这就是贺麟所说的“知行两面说”,“认知行合一构成一个整个活动”[1]134。
在贺麟看来,知是主、行是从,知是体、行是用。具体说来,“知主行从说”包括下例三层意思[1]141-142:(1)“知是行的本质(体),行是知的表现(用)”。“知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行是传达或表现此意义或目的之工具或媒介”,因此,“行”应当“与知合一,服从知的指导,表示知的意义”,而“知藉行为而表现其自身”。(2)“知”永远决定行为,故为主;“行”永远为知所决定,故为从。贺麟指出,“从自然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看来,知行同时发动,两相平行,本不能互相决定,但亦可谓为内在的决定或逻辑的决定”。这就是说,“知为行之内在的推动原因,知较行有逻辑的在先性”。(3)“知”永远是目的,是被追求的主要目标;“行”永远是工具,是附从的、追求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人的活动都是一个求知的活动”,“论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情形下,他的行为永远是他的知识的功能(action is always the function of knowledge)”。
关于“知”“行”两个概念,贺麟是这样界说的,“‘知’指一切意识的活动。‘行’指一切生理的活动”[1]131。贺麟举例说,任何意识的活动,如感觉、记忆、推理的活动,如学问思辨的活动,都属于“知”的范围。也就是说,“知”是心理的或意识的活动。而任何生理的动作,如五官四肢的运动固然属于行,就是神经系的运动,脑髓的极细微的运动,也属于“行”的范围。也就是说,“行”是生理的或物理的动作。可见,“知”“行”是两种性质不同的活动,但它们同是活动,“我们不能说,行是动的,知是静的。只能说行有动静,知也有动静”[1]131。
在贺麟的“新心学”体系中,“知主行从说”与其文化观、体用观、心物观是一脉相承的。在文化观、体用观上,贺麟主张“以精神或理性为体,而以古今中外的文化为用”③。在心物观上,贺麟主张“心体物用”、“心主物从”④。因此,贺麟在知行的主从问题上主张“知主行从说”,可谓水到渠成、浑然天成!
四、知行的难易
贺麟认为,既然从逻辑上解决了知行的主从问题(知主行从),那么价值上的知行难易问题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在论述知行的难易问题时,贺麟力图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蒋介石的“力行哲学”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沟通、协调起来。贺麟明确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知行合一说”,“不但不冲突,而且互相发明”[1]5,“不惟不矛盾,而且互相发明”[1]193。
刘彬告诉记者:“农民种地就是要种好地。我们相信,通过农拓者作物一站式全程解决方案的帮助下,和保姆式服务的服务下,我们不仅能帮助农民实现优质高产的梦,同时在五到七年的时间,做大做好属于农拓者的农产品品牌。”而我们也相信,在全产业链模式的引领和带动下,新疆辣椒(色素)产业的发展也将红遍新疆的每一寸土地!
有哲学史家对贺麟这一结论提出了批评。批评者认为,贺麟“歪曲解释”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硬说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和他们的知行合一说相一致”,而“从根本上说,孙中山是反对知行合一说的”;贺麟的“这种作法是十分荒唐的”,贺麟的“歪曲解释”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2]938-939。其实,并非贺麟“歪曲解释”了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而是持此论者“歪曲理解”了贺麟的本意。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一读《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第二章《〈孙文学说〉的哲学意义——引言》的详细论证[1]158-199,同时参考张学智的具体论述[3]153-161。
贺麟进一步指出,“从价值的知行合一论看来”,所获得的结论也是“知难而行易”。“盖因显行易,显知难。由显行之行到显知之知难,由经验中得学问,由生活中见真理亦皆难。反之,由显知之知到显行之行,由知而行,由原理到应用,由本质到表现,由学术到事功,则皆易”。在贺麟看来,孙中山所谓“能知必能行”,不仅是一种信仰,而乃是一种事实。“不知亦能行”,亦是一种事实,“盖不知者可服从他人,受人指导而产生行为”。但是,“能知能行方是主动之行,不知能行,则是被动的行为”。总之,“难易是价值间题,主从是逻辑问题”[1]146-147。
后来,在《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中⑤,贺麟又考察了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的关系。贺麟认为,“蒋先生的行的哲学,乃是于王阳明的哲学及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灼然见到其贯通契合处,加以融会发挥而来”,“对于(知行)这个问题,蒋先生亦有一切实周至而又符合中山先生本旨的贡献”,“蒋先生的力行哲学实在是发挥中山先生知难行易说的伟大成果,也就是为知难行易说谋最高的出路,求最后的证明”[4]219,195,227。
那件事之后,李萍和陈建伟的关系还和从前一样冷淡。她是她的缝纫工,他干他的质检员,唯一的接触就是李萍交工,陈建伟收件,连句多余的话都没有。
而在凡俗如方某者,自不敢奢望“三不朽”,那是“圣贤”们的伟业。写写弄弄三十年,在我只许愿:曾经的笔墨并未因轻浮与应景,若干年后复读时而令自己心惭脸红,则在笔者也算是经“墨磨”过的卖稿人了!
从“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出发,贺麟对历史上的“知行合一”说进行了全新的考察。贺麟将自己的“知行合一”说概括为“自然的知行合一论”(或“普遍的知行合一论”),而将历史上的“知行合一”说概括为“价值的知行合一观”(或“理想的知行合一论”)。“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和“自然的知行合一观”的区别在于:“价值的知行合一观”视知行合一为“应该如此”的理想状态(“价值或理想”),是必须经过“人为的努力方可达到或实现的课题或任务(Aufgabe)”,并且是“只有少数人特有的功绩”;而“自然的知行合一观”则视知行合一为“原来如此”的客观事实(“自然事实”),并且认为“知行本来就是合一的,用不着努力即可达到”[1]136-137。
对于“价值的知行合一观”,贺麟又将其细分为“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观”和“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观”。“理想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观”,以朱熹为代表;“直觉的价值的知行合一观”,以王阳明为代表。在贺麟看来,在知行主从问题上,王阳明“亦持知主行从说”。王阳明曾经说过,“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传习录上》),“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传习录中》)。非常可惜的是,“阳明所谓知行,几纯属于德行和涵养心性方面的知行”[1]151,“着重在个人正心诚意、道德修养的成分居多”[1]195。在贺麟看来,在知行问题上,朱熹坚持的是“知先行后”、“知主行从”之说。朱熹曾经说过,“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九)。但是,朱熹的问题只限于“知行何以应合一”及“如何使知行合一”方面,“他全没有涉及自然的知行合一方面,也没有王阳明即知即行的说法”[1]155。贺麟晚年补充说,“朱熹对知行问题的基本思想是把知行分为二截,坚持知先行后说”,“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看来,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并没有看出知识的感性的和实践的基础。他孤立地机械地分知行为二截,方法不辩证,没有看出知行的内在联系,知行之反复推移和矛盾发展的关系”[1]200,201-202。
贺麟认为,还可以从主从(体用)关系辨别知行。他指出,“所谓主从关系,即是体用关系,亦即目的与手段关系,亦可谓为领导者与随从者的关系”[1]140。贺麟特别提醒,“主从的关系的区别要有意义的话,不能以事实上的显与隐或心理上的表象与背境定主从,而当以逻辑上的知与行的本质定二者之孰为主孰为从”[1]141。
经过一番梳理与考察,贺麟发现,“自然的知行合一观与任何一种价值合一观都不冲突”,“不唯不冲突,而且可以解释朱王两种不同的学说,为他们的知行合一观奠立学理的基础”。也就是说,“自然的知行合一论,实由程朱到阳明讨论知行问题的发展所必有的产物”[1]156。
贺麟的私淑弟子张学智说,“贺麟之所以花大力气讨论知行问题,是为了使人们明了离知无行,离开学问无涵养,离开真理的指导无道德的道理,破斥缺乏道德的知识基础的武断的道德命令、道德判断”[5]7。
对于贺麟的“知行合一新论”,今人有过中肯的评价:“这一知行关系的理论不仅仅是接着朱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讲的,它也同时吸收了斯宾诺莎、格林和鲁一士有关的思想。可以说,贺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关于知行关系理论的研究。他的知行合一新论较朱熹、王阳明的理论要系统、精致得多。其最主要的特色是把知行合一说从纯粹的德性修养的领域扩展到了逻辑和认识论的领域,从而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关系理论奠定了逻辑和认识论的学理基础,指明了道德学的研究应该以知行关系这样的认识理论为其前提。而且,由于人这一认识主体的任何活动都是在意识的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支配下进行的,所以不可能有脱离意识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知决定行,知行是合一的。虽说这一理论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但是从现代知识论研究的现状看,应该说是正确的”[6]412-413。
注释:
① 关于贺麟的生平、著述及相关情况,请参看(1)彭华:《贺麟年谱新编》,《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78-91页;全文收入《现当代学人年谱与著述编年》,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第303-332页。(2)彭华:《贺麟先生学术年表》,附录于贺麟:《近代唯心论简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12月;又附录于贺麟:《文化与人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② 相关评述,可参看张世英:《哲学导论》(修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二版,第265-275页。
我们方法的另一个优势是通过使用归一化质点滤波,可以有效地规避传统网格搜索中所需要的复杂计算。尽管如模型一节所述仍然需要先验分布,但这种分布可以根据历史记录得到。另外,也可以用初步的测量结果来选取合适的先验分布,从而得到更好的性能(Liu et al,2011)。但是这个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例如算法对先验分布的选择、质点的数目、以及Anoise、σnoise、σP和σS等的取值都非常敏感。尽管这些值可以进行实时调整,但是却需要大量的经验研究和对历史记录的分析。结果一节所述的一些慢收敛速度和高方差结果也可能是这些参数的次优选择造成的。
③ 贺麟:《文化的体与用》(1940年),《近代唯心论简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1页。具体论述,请参看彭华:《会通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第二章第四节。
④ 具体论述,请参看彭华:《会通与建设:贺麟文化思想研究》第五章第一节。
⑤ 说明:《知难行易说与力行哲学》是旧版《当代中国哲学》的第四章第五节,新版全部删除。上海人民出版社《贺麟全集》本《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将此章作为附录收入。
据了解,为加快“产、学、研、用”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增强我国河湖生态水利的技术创新能力与产业竞争力,构建行业全新的产业技术服务平台,在水生态保护行业内处于领军地位、具有显著影响力的几家核心企业成立了“中国水生态技术联盟”。该联盟成立以来,已经在北京、山东、江西等地开展了一系列科技推广和技术交流活动。
参考文献:
[1]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
[2] 冯契.中国近代哲学史(下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3] 张学智.贺麟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4] 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 张学智. 前言[Z]//贺麟选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6] 张文儒,郭建宁.中国现代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ReviewofHeLin’sEpistemologyofNewIdealism——Focus on “the Theory of Natural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PENG Hua
(InstituteofClassicalLiteratureStudies,SichuanUniversity,Chengdu610064,China)
Abstract:He Lin expounded his epistemology from such aspects as the concept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the meaning of unit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and the difficulty and easiness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His theory consists of four basic propositions (or conclusions) that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re both activities”,that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re always one”,that “knowledge is primary and practice is secondary” and that “it is easy to know and difficult to practice”. There is no conflict or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heory of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nd any kind of theory of value unity. It lay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epistemology for the theor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
Keywords:He Lin; New Idealism; th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easy to know and difficult to do; view of the natural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中图分类号:R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9684(2019)01-0020-05
收稿日期:2018-10-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0@ZH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ZS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ZH099);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项目。
作者简介:彭华(1969-),男,字印川,四川丹棱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史、近现代学术史以及中国儒学、巴蜀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杨和平]
标签:哲学论文; 难行论文; 自然论文; 关系论文; 一说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现代哲学(1919年~)论文; 二十世纪哲学论文;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10@ZH005)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ZS01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ZH099)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 学科群项目论文;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