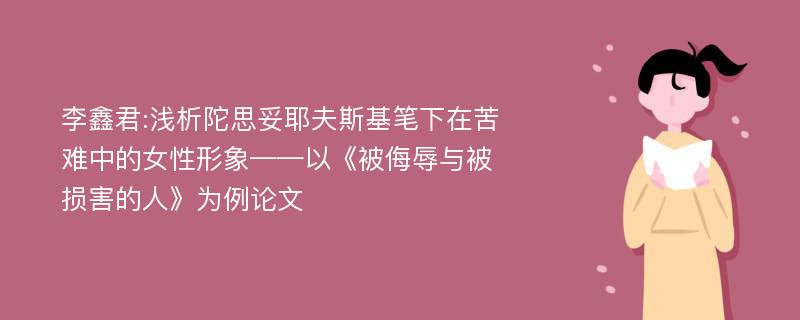
【摘 要】具有双重人格的女性一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较为喜欢描绘的艺术形象,她们人格的分裂主要体现在爱情当中。对于她们而言,爱情永远不能成为开启幸福和美满生活之门的钥匙,爱情总是伴随着怨恨和牺牲。最具典型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形象就是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娜塔莎·伊赫梅涅娃。
【关键词】双重人格;苦难;主宰;奴隶;折磨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俄罗斯19世纪伟大的作家,他的作品正如他本人一样复杂。很多学者把《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作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分水岭,认为这部作品处于作家向探索社会心理转变的过渡时期。众所周知,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掘了世界文学中的双重人格现象。双重人格现象促使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爱情关系,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无人提及的。在作家笔下,主人公的人格分裂主要表现在对待爱情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欢描绘具有双重人格的女性形象,她们自相矛盾的人格以及在爱情中的体现只有在苦难中才显得越发生动和鲜活。
一、出于本能,矛盾交加
在温柔与残酷、克己与专制间来回徘徊的女性形象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中就已初见端倪。在《女房东》和《小英雄》中可以透过卡捷琳娜和爱淘气的“金发女郎”看到双重人格的雏形。这种具有双重人格特点的人物原型更像用细微的笔触描绘的草图,直到《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双重人格的特点才更为全面地被确定下来。主人公对她父亲和卡嘉的态度是歇斯底里的,时而痛苦,时而温柔,时而慷慨,时而又渴望征服和主宰,集矛盾于一身。涅朵奇卡对自己和父亲的关系是这样定义的:“这是一种奇怪的爱……这样说,这是一种近于怜悯的母爱。在我看来,父亲永远是那样可怜,那样受害,那样被压抑,那样命苦,倘若我不能忘却一切地去爱他,安慰他,那是一件可怕的违背感情的事。”[1]但是这种类似于母爱的情感又掺杂了其他成分:“我渐渐地觉得,我甚至对他占了上风。慢慢使他服从我了,他已经离不开我,这使我心理感到骄傲。”[1]242在涅朵奇卡这个年纪,对爱情尚不能完全理解:爱是情欲,爱是激情,是所有亲密经历中最强烈的。她所熟悉的是一种完全纯净的,温柔的情感:对父亲和对朋友的爱。随着年龄的增长,对爱的理解或许会发生变化,但她的爱始终保留“母爱”的特点。这一点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娜塔莎身上显而易见。
娜塔莎·伊赫梅涅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向我们展现的第一个具有双重人格且最具信服力的女性形象。她不认为爱是平等的,她是爱情的奴隶也是爱情的主宰者,具有像涅朵奇卡一样可以称之为“母爱”的情感,总是在苦难和折磨间穿梭,无法在爱情中收获幸福的女性,她对阿廖沙·瓦尔科夫斯基的爱就说明了一切。在最终分手后,娜塔莎分析自己的感情,她问自己:“我是不是当真爱他……不是像一个女人通常爱一个男人那样来爱他。我爱他像……几乎像个母亲。我甚至觉得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彼此平等的爱。”[2]她的爱是对弱者的爱,夹杂着怜悯的爱。这是克己和牺牲的幸福,是在痛苦中的快乐,是支配他人的喜悦,是对折磨的享受。控制娜塔莎的情感非常强烈,当她决定离开家的时候,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什么,她处于某种“发狂”的状态。“……这由不得我啊。她说。”[2]35文章的叙述者伊万·彼得洛维奇总结道,“我意识到娜塔莎已经身不由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2]39女主人公无法抑制自己炽热的情感,同时也因为她与阿廖沙私奔的行为感到良心上过意不去:她被自己曾经或不久后将给亲朋好友带来痛苦和悲伤的思想所折磨。“破坏性”的激情和道德感注定了小说中女主人公内心的挣扎。
早在20世纪80年代,谢蔑尼申科娃就曾在自己的毕业论文“陀思妥耶夫斯基长篇小说《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现实主义的问题及特点”中指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俄罗斯文学中唯一一个触及本能情感的作家。在屠格涅夫那里同样可以找到对出于本能激情的浪漫诠释,尤其在他的小说《贵族之家》当中。丽莎·卡里金娜对拉弗列茨基的渴望,出于一种本能的吸引,并且和娜塔莎·伊赫梅涅娃一样,丽莎也经历了道德斗争。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人物的问题不同,女主人公心理的挣扎是由情感和责任间的斗争决定的。内心冲突的差异导致了相似故事情节上女性形象的阐释也有所不同。[3]
二、崇尚苦难,享受痛苦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无条件地崇拜且臣服于苦难。对于作家来说,苦难是获得崇高道德的福祉,因为它证实了人们丰富波澜的内心活动。受苦受难是人的内在精神需求。在主人公的意识里,苦难具有激发道德重生的潜在力量。
在我国农业工人还没有培养标准之前,在我国农业机械还没有普及之前,农业种植肯定就离不开在田间地头工作的一线产业农民。再好的农业服务技术,没有人使之落地,或者他们仍然按着自己的方式和节奏种植,结果只能是失败。
哲学家别尔嘉耶夫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没有任何迷人的爱情、任何美好的家庭生活……他揭示给我们的不是真正使人联结与融合的崇高的爱情。”[4]确实,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几乎没有完美的爱情,爱情总是伴随着愁苦的。诚然,这与作家本人的经历密不可分,因为作家一生都被苦难环绕,他经历过十年的囚禁、苦役、流放和充军。所以他笔下的人物也常常有着不幸的命运。但是作家认为正是有苦难,人才能得到救赎,进而获得新生和幸福。作家笔下的女主人公即使知道会因为所爱之人受到伤害,但内心仍然向往这种痛苦,因为在苦难中的幸福才更加甜蜜。
急性重型减压病致肝内多发积气以及通过腹部CT检查进行诊断的应用目前鲜见报道。解放军第四○一医院全军航海病医学专科中心于2016年11月收治1例急性重型减压病致肝内多发积气的患者,并通过腹部CT检查对此病例进行了诊断。现报道如下。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道:“娜塔莎本能地感觉到,她将成为支配他的主人;他甚至可能成为她的牺牲品;她预先品尝到了如痴似狂地爱一个她所爱的人,并且折磨他,使他痛不欲生的快乐,也许正由于她爱他,才迫不及待地先委身于他,成为他的牺牲品。”[2]42娜塔莎既痛苦又甜蜜地原谅了阿廖沙的一切,原谅了他的贪婪,原谅了他的轻率,原谅了他的不忠。她心甘情愿地背起苦难的十字架,但也是为了使自己经历痛苦的洗礼,用受折磨来报复阿廖沙带给她的痛苦。“我还是乐于做他的奴隶,心甘情愿地做他的女奴……这不是犯贱吗,万尼亚?她骤然问道。”[2]40这是一个典型的感慨。透过克己和奴役的喜悦,听出了威胁的意味。那些对屈辱如此敏感而且了解的人,在他们身上必然会产生一种渴望补偿的欲望,一种体会主宰的冲动。
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女主人公的痛苦是她灵魂复活的保障。在激情的斗争中,道德感越强烈,痛苦就越强烈。娜塔莎觉得苦难是弥补父母和朋友伊万·彼得洛维奇所受伤害的方式,是她恢复和人们联系的唯一途径,即使自己像他们一样受苦,或比他们更多。“娜塔莎说,必须历尽劫难才能勉勉强强地重新获得我们未来的幸福:用新的苦难做代价来换取这幸福。受苦受难能净化一切……唉,万尼亚,生活中有多少痛苦啊!”[2]76
急性支气管炎是儿科常见的呼吸道疾病,咳嗽为其的主要临床表现,病初以干咳为主,细菌感染者常咳吐黄色黏液脓性痰。病变多为自限性,全身症状3~5 d消退,咳嗽延续7~10 d,有时迁延2~3周,部分患儿护理不当或治疗不及时,易并发肺炎、中耳炎、喉炎等[7]。对于咳黄脓痰的急性支气管炎患者,推荐给予抗生素治疗[8]。因此本次临床试验,选择具有广谱抗菌作用的头孢呋辛酯干混悬剂为基础用药,既符合临床用药实际,也可避免受试儿童在临床试验过程中承担过高的风险。
三、逆来顺受,甘于牺牲
在娜塔莎身上出现的爱情是狂热而不理智的,她以一种卑躬屈膝的姿态对待折磨她的爱情,并且这种情感仿佛控制着她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选择。在娜塔莎面前存在着两种珍贵的爱——肉体和灵魂的爱。如果说,阿廖沙带给她的爱是感性的,那么万尼亚的爱则是理性的。可她偏偏选择了令她痛苦的一方,宁愿放弃美好与幸福,宁愿沉浸悲伤与折磨也要这样选择。似乎只有在这样畸形的爱情中,娜塔莎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即为了成就对方而进行的自我牺牲。她为了不让阿廖沙自责而做出了忍让和退出,她选择了用“苦难”去净化一切从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
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曾经分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但他却完全忽视了其中对于爱情的特殊心理。娜塔莎的爱在他看来是虚构的,是不可能的。“……阿廖沙这种像臭虫一样的人怎么能让一个好女孩爱上他呢?如果作者能解释一下,我们愿意跟着他的脚步,并与他进行任何艺术和心理上的探究。但却没有:要知道,五个月来,娜塔莎的爱情狂热般开始并蔓延开来,书中没有一页加以说明。女主人公的心是隐藏的,似乎作者也并不比我们更了解她内心的秘密。我们满怀期待地问他,这是怎么产生的。而他回答,“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这样。”[5]其实,杜勃罗留波夫没能成功地在激流涌动的爱情里捕捉到一种精神状态,那种驱使杰符什金之流在高傲和自卑之间、在爱自己和恨自己间徘徊的状态,所以他们对待别人同样也是爱恨交加的。这种矛盾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娜塔莎甘于在这段感情中逆来顺受,一方面,她渴望成为阿廖沙的主宰,另一方面她又甘心做对方的奴仆,即使阿廖沙对不起她,她仍然要留在对方身边。人类本身就是复杂的,尽管娜塔莎对阿廖沙又爱又恨,但她出于本能地、疯狂地爱上了阿廖沙,她就心甘情愿为了爱情做扑火的飞蛾。杜勃罗留波夫觉得娜塔莎爱上像“臭虫”一样的阿廖沙是不正常的。但如果说阿廖沙真是一个“小虫子”一样的人物,主要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尽管他20 岁了,但他仍保留着天真、无助、自私和惹人怜惜的特点。20 岁的孩子既可笑又可怜,但要知道娜塔莎的爱情正是基于同情和轻视,以及无尽的温柔和折磨。对于这种爱,显然阿廖沙是最合适的对象。
在小说中,作者对苦难的定义还有另一个层面。“享受苦难”的想法在女主人公的话语中反复出现。她对伊万·彼得洛维奇说:“我非常喜欢原谅他,万尼亚,你知道吗,有时候他撇下我一个人,我在屋里常常走来走去,我痛苦,我哭,可有时候又会想:他越对不起我,岂不是越好吗……”[2]280伊万·彼得洛维奇发现:“我觉得,她是在故意刺激自己的创伤,她感到有一种需要,需要她这样做,需要去寻求痛苦和绝望……但凡一颗失落了许多的心,往往都这样。”[2]280-281显然,娜塔莎对于苦难的态度是迎接式的,她渴望苦难,似乎只有在痛苦中才能找到一丝安慰。
这个人物的塑造同样取决于作家的世界观,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信奉基督的仁爱和自我牺牲精神。在《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开篇,作家引用了圣经里《约翰福音》中的一句话:“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落在地里如若不死,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6]这句话就是告诉人们,耶稣借着死亡得以复活,同样,人只有在困苦中学会舍身牺牲,甘于奉献才能获得新生。
四、结语
在《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首次表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艺术人类学思想,就是描绘人类心理的非动机行为,即无意识动机所产生的行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他着重表明的是:不是所有事情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事先预见到,不仅对旁观者不可预测,有时对自己也是如此。在错综复杂的动机中,一个人的道德可以“复活”一切,不仅是内心中缺失的东西,还有源于生活的各种外在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心理分析旨在揭示娜塔莎的道德感,通过她与“破坏性”的激情的斗争加以表现出来。这决定了作家敏感地发觉到女主人公精神生活悲剧性的一面。
由此可见,双重人格的矛盾性在主人公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无论何时何地,主人公总是被一种屈辱和无力所折磨,一直渴望骄傲和强大,却永远不能在爱情上获得内心的安宁。在心灵的斗争中,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无能和必然的堕落,同时,对权力和威望愈加渴望,以致于表现出受虐和犯罪的倾向。这也是那个黑暗的时代带给“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小人物的悲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女主人公身上看到了对苦难的需要,这符合他对俄罗斯性格的理解,在这部小说中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女性的形象。娜塔莎性格中“渴望痛苦”的一面是其接近生命道德的体现。作家在女性形象中突出这一特征并非偶然,因为正是在俄罗斯女性身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看到了美与理想的化身。他说:“……如果我们能够等待救赎和更新,那么希望当然就在比俄罗斯男人要优秀的俄罗斯女人那里。”[7]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女性为什么在苦难中熠熠生辉的原因:“但是上帝,她多么漂亮啊,无论过去还是以后,我从来没有见过她像在这不幸的一天那么漂亮!”[2]33
数学成绩显示:实验班低分段人数较多,有40人次成绩为不及格,而对照班成绩全部及格;实验班有8人次成绩为优秀,而对照班有18人次成绩为优秀;实验班总平均成绩为65.75分,而对照班总平均成绩为72.75,两者总均分相差7分;实验班的平均权重为0.367,而对照班的平均权重为0.426,两者相差0.059。数据表明,实验班学生的数学学习状态不佳,不仅成绩较差的学生在辩证动态双主教学中不能及时实现学习角色的转换,而且成绩优秀的学生也感到困惑和迷茫。
[参 考 文 献]
[1]陀思妥耶夫斯基.涅朵奇卡·涅茨瓦诺娃[A].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篇小说选[C].陈琳,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225.
[2]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M].臧仲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279-280.
[3]СеменищенковаЛ.Л.РоманФ.М.ДостоевскогоУниженныеи оскорбленные:про-блематика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еализма.[D]Орел,1984:102.
[4]别尔嘉耶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M].耿海英,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1.
[5]Добролюбов Н.А.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M]:в 9 т.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1963.Т.7.:309.
[6]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M].荣如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1.
[7]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М.Фрагменты Дневника писателя.[M]НеизвестныестраницыДостоев-ского.ПубликацияИ.Л.Волгина//Литературноенаследство[M].Москва,1973.Т.86.:76.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36(2019)06-0030-03
【作者简介】李鑫君(1991-),女,山东烟台人,硕士,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编 辑/李 勇
标签:斯基论文; 耶夫论文; 苦难论文; 的人论文; 娜塔莎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黑河学刊》2019年第6期论文;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