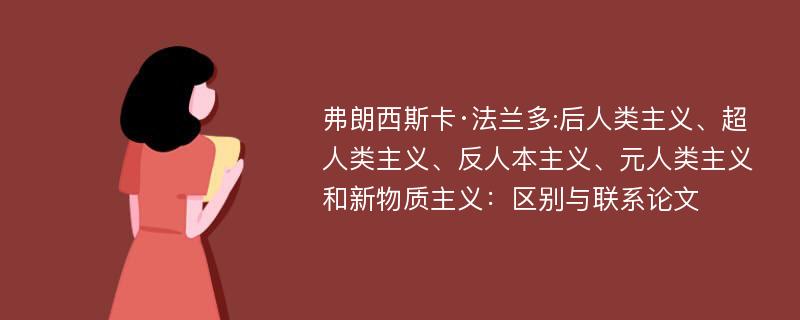
摘 要: “后人类”已经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可以用来指称各种不同思想运动或学派的概念,包括哲学的、文化的或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就其中外熵论的、自由的或民主的超人类主义而言),女性主义研究中的新物质主义进路,以及具有完全不同视野的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元人性论和后人性论等。 无论对于专家还是非专家而言,后人类这个概念普泛和无所不包的使用,已经引起了方法论和理论上的混乱。 探讨上述各种不同运动之间的区别,聚焦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所共有的指称域,并阐述这两种独立但又相互联系的思想可以表明,后人类主义为反思可能的未来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立场。
关键词: 后人类主义; 超人类主义; 反人本主义; 元人类主义; 新物质主义技术; 未来; 后人类; 超人类; 赛博格
一、引言
在当代学术讨论中,“后人类(posthuman)”已经成了一个关键性的术语,它的出现是为了应对从整体上对人这个概念进行再定义的迫切需求,这种需求缘于20、21世纪的科学理论和生物技术的进步,以及哲学理论中本体论和认识论发展所导致的结果。 就哲学方面的发展而言,其中包括了许多思想运动和学派。 而“后人类”这个标签的使用,通常呈现出的是一种普泛的和无所不包的方式,涵盖了上述许多不同的观点。 对非专业人士甚至是专业研究者而言,这引发的是方法论和理论层面的困扰。 “后人类”已经成了一个总括性的术语,其名下可以包括哲学的、文化的或批判的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就其中外熵论(extropianism)的、自由的或民主的超人类主义而言],各种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s)(特指那些女性主义的、在后人类主义框架下的理论),以及具有不同内涵的反人本主义、后人性论和元人性论等。 其中最容易产生混淆的是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所共有的指称域。 产生这类混淆,原因很多。 首先,二者都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注]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两个运动的产生时间,还能追溯得更早一些。可供参照的、与现今的超人类主义的哲学态度最为接近的观点来自Julian Huxley的著作NewBottlesforNewWine:Essays(London: Chatto&Windus, 1957, pp. 13-7)中的“超人类主义”一章。在后现代的文献中,“后人类”和“后人类主义”两个词首次出现在Ihab H. Hassan的文章“Prometheus as Performer: Toward a Posthumanist Culture?”中(载于The Georgia Review 31/4, Winter 1997, pp.830-850),以及同一作者的著作ThePostmodernTheoryandCulture,Columbus(OH: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且对于相似的问题都抱有兴趣。 它们对于人类有着共同的看法,即人类是非固定的、可变条件下的产物,但总体上,二者却有着不同的思想来源和观点。 而且,在超人类主义的讨论中,后人类主义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以一种具体的超人类主义的方式来进行解释的,这就对后人类的一般性理解又造成了进一步的混淆。 例如,对于某些超人类主义者而言,人类可以最终将自己进行根本性的改造而成为后人类,后人类时代被认为是继现在这个超中的人类时代之后的一个新阶段。 但是,这种关于后人类的观点,不应该和哲学上、文化上或批判理论中用后人类中心论的和后二元论的路径理解后人类主义的方式相混同。 本文对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这两个相互独立但又有关联的运动间的差别做了澄清,并指出作为一种鲜明的本体论和存在主义的对人的概念的再设定,后人类主义提供了一个更为全面的理解进路。
二、超人类主义
将来的人类必然要继承其过去和现在留下来的遗产吗?对此超人类主义持怀疑态度,也许更值得诉诸的是生物进化和技术进步提供的可能性。 在超人类主义者的思考中,人类增强是一个关键概念,用来达成这个目标的主要手段来自各种不同的科学和技术,[注] 1998年,一群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共同起草了《超人类主义宣言》,参见http://humanityplus.org/philosophy/ transhumanist-declaration/。 该宣言有八条主张,第一、二两条转录如下: 1)就现在的趋势而言,人类在将来会受到来自科学和技术的巨大影响。我们正在构想把人类潜能进行拓展,例如克服衰老、认知上的缺陷、无法避免的(肉体上的)痛苦,以及人类生存对地球的依赖。 2)我们相信人性潜能的大部分仍未实现。 对人的存在状态的惊人和超越性的增强,在未来是可能实现的。包括已经存在的、正在出现的和处于构想中的,从再生医学到纳米技术,到根本性的生命延长、心灵上载、人体冷冻术等,也包括其他领域中的类似技术。 超人类主义内也存在不同的流派,例如自由主义的超人类主义、民主论的超人类主义和外熵论的超人类主义。 科学和技术是这些不同流派共同的兴趣所在,但对其的倚重程度不尽相同。 自由主义的超人类主义主张自由市场是人类增强权利最好的捍卫者,[注] Ronald Bailey, Liberation Biology: The Scientific and Moral Case for the Biotech Revolution,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05.民主论的超人类主义呼吁一种对增强性技术的平等使用权,否则这类技术将被某些社会-政治阶层所独有,并成为经济特权的附属物,从而导致带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政治安排。[注]James Hughes, Citizen Cyborg: Why Democratic Societies Must Respond to the Redesigned Human of the Future, Cambridge, MA: Westview Press, 2004. (下文简为CC)外熵论这一派的奠基者是马克斯·莫尔(Max More),代表其主张的关键词是: 持续不断的进步、自我改造、实践乐观主义、智能化的技术、开放的社会(民主和信息自由)、自我导向和理性思考。[注] Max More, Principles of Extropy, Version 3:11, 2003, http://www.extropy.org/principles.htm. Last accessed November 14, 2013. (下文简为PE)之所以对于理性、进步和乐观主义等概念特别强调,是因为在哲学上超人类主义的思想源头来自启蒙运动,[注] James Hughes把《超人类主义宣言》的发布视为启蒙运动的遗产得到了最明确的重申。 通过《宣言》,超人类主义者们表明其与(主张民主和人本主义的)启蒙运动是一脉相承的(CC:178)。 同样,马克斯·莫尔指出,与人本主义者一样,超人类主义者赞同理性、进步和那些注重于人类幸福的价值,而不是一个外部的宗教权威。 但超人类主义者通过批判和创新的思维,同时借助科学和技术手段对人的极限提出了挑战 (PE n.p.)。 (相当多的超人类主义文献以在线的方式来出版,鉴于此,其他类似观点和出处不再罗列。因而它并不拒斥理性的人本主义。 通过进一步推进这种人本主义,超人类主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终极人本主义(ultra-humanism)”。[注] Bradley B. Onishi, “Information, Bodies, and Heidegger: Tracing Visions of the Posthuman,” Sophia 50/1 (2011), pp. 101-12. 但这一理论定位弱化了超人类主义的反思,下文将要论及。
3.1 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良好的护患关系是医护活动顺利开展的必要条件,患者的依从性常与护患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6]。融洽的护患关系可产生良好的心理气氛和情绪反应,促使患者遵循治疗方案。如果护患间没有充分的交流,没有形成良好的信任关系,就难以促使患者建立良好的服药依从性。因此,护士应针对老年人的特点,并结合其知识层次和性格,进行有效的沟通交流,建立良好的护患关系。
由大量传感器节点组成的无线传感器网络在环境监测、目标定位和跟踪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这些应用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一般可以归结为是从传感器采集的测量数据中估计未知的物理量参数,并且随着无线传感器网络的快速发展,该问题已经吸引了大量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通常情况下,无线传感器网络中每个传感器节点由电池供电,其计算、通信和信息存储能力有限[1],另外,网络的通信带宽也是一个有限的资源。这使得如何基于传感器网络获得有效的参数估计,同时尽可能降低网络的使用成本问题成为一个具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研究热点。
对照组(不加药)在不同时间点对PC3细胞的凋亡作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雷公藤内脂醇的浓度为10、20、40 nmol/L时,培养PC3细胞12 h、24 h、48 h后对PC3细胞的凋亡作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虽然后人类主义已经可以追溯到第一波后现代思想中,但后人类的转向却完全是由那些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主义理论家提出的,他们原属于文学批评的研究领域,这一转向后来又被称为批判的后人类主义。 与此同时,文化研究领域中也有人涉及了这一主题,产生了被称为文化后人类主义的研究方向。[注] 关于文化后人类主义的历史和理论的解释可参见: Judith Halberstam and Ira Livingston, eds., Posthuman Bod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Neil Badmington, ed., Posthumanism, New York: Palgrave 2000; Andy Miah, “Posthumanism in Cultural Theory,” in Medical Enhancement and Posthumanity, eds. Bert Gordijn and Ruth Chadwick, Berlin: Springer 2008, pp. 71-94. 到了1990年代末,(批判的和文化的)后人类主义合流成为一个更哲学性的研究(即现在所指的哲学的后人类主义)。 它对于早前人类中心主义的和人本主义理论假设中包含的各种局限具有清醒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它对哲学探究所涉及的各个领域进行了一种更为综合性的再研究。 后人类主义通常被定义为后-人本主义或后-人类中心论:[注]参见: Rosi Braidotti, The Posthuman,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3. 这个“后”是针对人这个概念,以及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人本主义而言的,如前所述,人的概念和人本主义是基于层级化的社会结构和人类中心的理论假设之上的。 物种主义(speciesism)已经作为一个部分被整合进了后人类的批判方法。 虽然,后人类的提出是为了克服人所具有的优先地位,但这并不是说用另一种优先地位(例如机器的优先)来取代它。 后人类主义可视为一种后排他主义(post-exclusivism),因为它是在最宽泛意义上对生存的和解,是一种关于居间中介(mediation)的经验哲学。 后人类主义并不采取任何先前的二元论或二元对立的观点,通过后现代解构的实践,它对任何由本体论引起的两极分化现象行了驱魅。
可以说,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对技术有着同样的兴趣,但是它们反思这个概念的方式却存在结构上的不同。 当需要对与后人类相关的议题做恰当的论述时,从历史的和本体论的维度对技术进行理解,就成了一个关键。 然而,后人类主义并没有把技术作为其主要的关注点,因为那样的话会将其理论工作缩减为某种形式的本质主义或技术还原论。 技术既不是值得恐惧或需要反抗(这表现为新卢德主义)的“他者(other)”,也不具有某些超人类主义赋予它的近乎神圣的特征(例如,强调技术作为一种外部的力量,它可以确保人类在后生物学未来中拥有一席之地)。 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所共有的是技术创世论(technogenesis)这个概念。[注] 参见: N. Katherine Hayles, “Wrestling with Transhumanism,” in H+: Transhumanism and its Critics, eds. Gregory R. Hansell, William Grassie, et al., Philadelphia, PA: Metanexus Institute 2011, pp. 215-26. 技术的特征在于它是人类的装备。 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技术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的工具,其目的是为了获取其他的东西(例如获得能量、更精密的技术,或甚至是人的不朽)。 通过女性主义这一媒介,技术进入了后人类主义的讨论中,这尤其是源于唐娜·哈拉维的赛博格概念以及她对严格的二元论和各种边界[注]Donna Haraway,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1980s,” in The Gendered Cyborg: A Reader, eds. Gill Kirkup, Linda Janes, Kath Woodward, and Fiona Hovenden, New York,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50-57.的解构工作。 例如人和非人的动物之间的边界,生物有机体和机器的边界,物质的和非物质领域之间的边界,以及最终的技术和人自身之间的边界。
三、后人类技术
此外,超人类主义者坚持认为科学和技术是重构人类所凭借的主要资源,这将承受技术还原论的风险,即技术成了等级化的投影,而这又是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以进步为驱动力的。 考虑到世界人口中的很大部分仍然处于仅能维生的状态,因而如果对所期待未来的构想仅仅是基于某些具体的技术成果,以及人和技术紧密结合的乐观估计,那么这种偏好将使得超人类主义局限为一个阶级论和技术中心论的运动。[注] 参见: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20. 三千万美国人埋头于因特网,沉迷于虚拟的经验之中,这造成了一种分隔,一边是存在于屏幕之外的物质化的身体,另一边是计算机的虚拟影像所产生的、仿佛是存在于屏幕之中的一个空间。 但对于更多的美国人来说,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虚拟化并不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 就全球而言,在其他一些更大数量级的数据对照下,虚拟化的经验简直是天方夜谭。 想想全球人口中有70%,甚至从没有打过电话,这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有益的校正。由于上述原因,尽管超人类主义对于生物和技术两大领域间正在发生的互动,提出了令人惊叹的观点,但其根脉仍是基于传统思想,后者对其观点具有无法补救的限制作用。 超人类主义对技术和科学的倚重应该从一个更广的视角来考察,少一点(人类)中心化,多一点整合型的进路,这对于讨论将是有益的。 在这个意义上,后人类主义可以提供一个更为恰当的出发点。
新物质主义是后人类主义理论方案中另一个具体的思想运动。[注]新物质主义这个概念是由Rosi Braidotti和Manuel De Landa在1990年代中期发明的。参见: Rick Dolphijn and Iris van der Tuin, New Materialism: Interviews & Cartographies, Ann Arbor, MI: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 关于在这一语境下用“新”这个形容词产生的问题,可参见:“New Materialisms and their Discontents,” paper presented at Entanglements of New Materialism, Third New Materialism Conference, Link?ping University, May 25-26, 2012. University of Michigan. 戴安娜·库勒(Diana Coole)和萨曼莎·福斯特(Samantha Frost)指出“重新提出的批判的物质主义并不等同于复兴马克思主义”[注] Diana H.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 “Introducing the New Materialisms,” in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and Politics, eds. Diana H. Coole and Samantha Fros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45, here p. 30. ,这是一个更文学化的概念。 在女性主义批判性的讨论中,物质被再次描绘成一个物质化的过程。 虽然这一观念,一直可以追溯到1990年代中期或末期肉体论的女性主义(corporeal feminism)[注] 参见: Elizabeth A. Grosz,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对身体的重视,但在21世纪最初10年中,这个被女性主义者们重新发现的兴趣点,已经成了一个涉及更广的面向物质的理论。 哲学上,新物质主义的兴起是被晚期后现代性中表征主义和建构主义各自的激进态度的激发的一定程度上都错失了对物质领域的关注。 这其实是基于一种内在的二元论,一边是通过观察和描述的行动进行操作的被感知一方,这也是观察者想要探寻的东西,另一边是相应地变得难以接近的外部实在。[注] 这类极端建构主义的一个支持者是哲学家Ernst Von Glasersfeld,其理论主要是关注认知理论等,见其著作Radical Constructivism: A way of Knowing and Learning(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1995)。 尽管新物质主义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后现代思想中,但它还是指出,虽然后现代思想拒绝了自然/文化的二元论,其中还是显现出对于自然这一方的明显偏好。 这种偏好导致了对任何自然的假设中具有的建构主义的内涵进行探究的学说,这类学说为数众多并互成谱系,[注] 关于用后人类主义的观点对建构主义和表征主义进行的批判,参见: John A. Smith & Chris Jenks, Qualitative Complexity: Ecology,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the Re-Emergence of Structures in Post- Humanist Social Theory, Oxon: Routledge 2006, pp. 47-60. 从中可以看出这是一波极端的建构性的女性主义文论的浪潮,这主要是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lter)开创性著作产生的影响有关。[注] 参见Veronica Vasterling所著 “Butler’s Sophisticated Constructivism: A Critical Assessment” (Hypatia14/3 (August 1999), pp. 17-38, p. 17),文中写道: 在最近十年的女性主义研究中,产生了一个新的范式:彻底的建构论。朱迪斯·巴特勒的著述与这个新范式有着最紧密的关联,在创造性地运用后结构主义和心理分析理论的基础上,巴特勒阐述了一种关于自然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意识的新观点。这一新理论的众所周知的表述是其著作《有所谓的身体》(1993),书中提出,不仅是社会性别(gender)甚至物质性的生理性别身体也是一种话语建构。这类文本展现了一个带有偏向的结果: 如果文化没有必要加括号的话,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然也不需要。 新物质主义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用一种反讽的语调转述了巴特勒的著作《有所谓的身体》[注]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gde, 1993. (以下简为BM),她写道: “语言很重要。 叙事很重要。 文化很重要。 就其重要的意义而言,似乎只有一件事物是不那么重要的,那就是物质。”[注] 参见: Karen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 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 Signs: 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3 (2003), pp. 801-31, here p. 801. 在言说和物质之间,新物质主义并没有提出任何区分:生物学是文化介入下的产物,这与文化是物质建构起来的同理。 新物质主义把物质作为一个正在进行中的物质化的过程,它优雅地调和了科学和批判理论,即用一种后结构主义的和后现代的意义来阐述量子力学。 无论如何,物质已不再被视为某种静态的、固定的和被动的东西,等着某些外部力量来赋予其形体。 相反,它被强调作为一个“物质化的过程”,(BM9),这样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内在地纠缠着的、衍射的和表演性的过程,除了物质化的过程外并没有什么更重要的东西了,且这个过程本身也不能被还原为描述过程的词汇。
后人类主义并没有着迷于证明其自身观点的原创性,相反它是一种后-例外论(post-exception)。 它暗含了对“新事物的分解”式的吸收,吉亚尼·瓦蒂默(Gianni Vattimo)把这点设定为一种后现代的具体特征。[注] Gianni Vattimo, The End of Modernity: Nihilism and Hermeneutics in Postmodern Culture, trans. Jon R. Snyder,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为了认定某物之为“新”,需要对叙事的中心加以定位,这样才能回答“是相对于什么而言的新”。 人类思想的创新性是相对的和具体的,在某个社会中被认为是新的,在另一个社会中则可能就是常识。[注] 在每一种文明中,当新的信息获得的时候,其他的信息便被遗忘了,于是当这些被遗忘的信息被恢复的时候,它再次成为新的了。实际上,心理分析专家Immanuel Velikovsky正是把人这个物种定义成了不断遗忘自身起源的物种。参见其著作MankindinAmnesia (New York: Doubleday, 1982)。 此外,关于西方的科学发现和传统东方精神性知识的衰落之间的关系也可以作为一个例证,参见物理学家Fritjof Capra撰写的颇有影响的著作TheTaoofPhysics:AnExplorationoftheParallelsbetweenModernPhysicsandEasternMysticism Boston, MA: Shambhala, 1975。 此外,某种占据统治地位的观念,并不会明确承认所有共存于某种具体的文化-历史范式中但与自身相左的观念,因而也就无法辨认出埋藏于任何杂乱形式中的连续性。 因而,后人类主义所质疑的不仅是传统观念中西方叙事中心的身份问题,这点早已被源自其自身边缘的各种思潮根本性地解构了,如女性主义、种族批判理论、酷儿理论、后殖民主义理论等。 这里仅列出其中的一些。 就某一视角而言,后人类主义也是一种后-中心化的理论。 它取消了中心之为中心在于其单一化的形式,无论是处于统治地位的还是处于其对抗地位的。[注] Francesca Ferrando, “Towards a Posthumanist Methodology: A Statement,” Frame. Journal For Literary Studies, 25/1 (2012), Utrecht University, pp. 9-18.后人类主义可以承认各种利益中心,哪怕这些中心是可变的、流动中的和转瞬即逝的。 它的观点必须是多元的、多层次的,并且尽可能的是综合性和包容性的。
四、后人类主义
在西方,历史地看,人是被作为一个相对于非人(non-human)领域而言的层级结构而呈现的。 这样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结构,是建立在像《伟大的存在之链》[注] 基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旧约的思想,《伟大的存在之链》一书描绘了一个始于上帝的关于所有事物和生命的等级结构(甚至包括那些假想的事物,如天使和恶魔)。 虽然在背景和具体细节上有所出入,但这个模式一直得以延续,经过了中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运动,一直到18世纪。 对这个主题的经典研究参见: Arthur O. 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一书所描绘的人类例外论(human exceptionalism)的基础上的。 这个结构在确保了人类相对于非人类动物的优势地位的同时,也形成了或暗示出了人类领域自身的标准,这标准可以表现为例如性别论的、种族论的、阶级论的、反同性恋主义的和民族中心论的预设。 换言之,人类中的某些群体——如女人、非美后裔、同性恋(男同和女同)、能力差异者(译注:残疾人的一种婉称)——并非一直以来都被当作人,事实上直到现在,他们代表的仍是人类中的边缘群体。 例如,在奴隶制中,奴隶被作为主人的一件私人财产,可以买入或卖出。 然而,就超人类主义的“终极人本主义”目标而言,他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对人的理解需要一种批判和历史的维度,他们更多的是提倡一种通用的、“适合所有(fit-for-all)”的定义方式。[注] Francesca Ferrando, “The Body,” in Post- and Transhumanism: An Introduction, eds. Robert Ranisch and Stefan L. Sorgner, Vol. 1 of Beyond Humanism: Trans- and Posthumanism, Frankfurt am Main: Peter Lang Publisher, forthcoming.
人的领域和技术领域之间的不可分离性,不仅仅是一个人类学[注] 例如: Arnold Gehlen, Ma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 trans. Patricia Lipscomb,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7] 1980. 或古生物学[注]例如: André Leroi-Gourhan, L'Homme et la Matière, Paris: Albin Michel, 1943; also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trans. Anna Bostock Berge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应该探讨的问题,而且应是一个本体论问题。 在后人类主义的框架内对技术的理解,延续了海德格尔著作中的思想,尤其是他的《技术的追问》一文。 文中海德格尔写道: “因而技术绝不是手段。 技术是一种揭示的方式。”[注]Martin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53] 1977, p. 12. 后人类主义对技术的考察正是把技术当作一种揭示的方式。 因而尽管在当代思想的设定下,技术被几乎还原成了技术性的工作,但后人类主义还是能重新获得技术的本体论意义。 与后人类主义相关的另一个需要提及的方面是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这是一个由福柯(Michel Foucault)提出的概念。[注] 福柯在其后期著作中提出了这个概念。 1984年,在他过世前不久曾提到正撰写一本关于“属于自我的各种技术”的著作。 1988年,文集《自我的技术》在福柯死后出版,主要是基于1982年其在弗蒙特大学讲习班的内容。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eds. Luther H. Martin, Huck Gutman, and Patrick H. Hutton,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8, pp. 16-49.自我的技术通过一种关系的本体论[注] 参见: Karen Michelle Barad,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7.打破了自我/他者的隔离,在对存在的揭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开启了与后人类相关的伦理学和应用哲学的讨论。 后人类主义是一种实践。 人们对未来进行构思和想象的方式,与现在其正呈现出的现实并不是无关联的,在后人类的后二元论方法看来,“(知道)是什么”就是“(知道)怎样”。 例如,超人类主义文献中经常提到太空移民(space migration),对此后人类主义也有涉及,但是基于其后现代和后殖民主义的立场,后人类主义并不支持这种观念。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证明超人类主义和后人类主义关注了同一个问题,但是以不同的观点并基于不同的理论传统。
随着后人类主义吸引了更多的关注并成为主流,新的挑战也产生了。 例如,现在有些学者更多地关注于那些“外部的”差异,例如机器人、由生物技术制造的喀迈拉(怪物)或是外星人,而不是着眼于处理内在于人类领域中的种种差异,从而使得后人类主义不再把人类的“边缘群体”作为研究出发点,例如女性主义或批判种族主义的研究。[注] 参见: Bell Hooks,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MA: South End Press, 1984.但后人类主义并不是基于一个等级的体系,当构建 一个后人类的立场时,并没有更高或更低程度的他异性可言,因而那些非人类的差别和属于人类的差别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后人类主义是这样一种哲学,它提供了一种用关系性的和多层次的方式来看问题的思考出发点,它用后二元论和后等级制的模式把研究的焦点拓展到了非人类的领域,因而允许人们去构想一个后人类的未来,这将根本性地延伸人类想象的边界。
五、新物质主义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建筑工程项目数量日益增加,而工程测量是保证建筑工程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传统的工程测量必须要花费很多时间、人力和物力,并且不能确保测量精准度。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技术具有高效率、高精准度等优点,将其在工程测量中应用,能够明显提升工程测量精准度。
六、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元人性论和后人性论
在后人类的图景中也存在一些有着重大差异的思想,每一种都形成了一个专业的话语讨论圈。 如果现代性中的理性、进步和自由意志等处于超人类主义讨论的核心,那么对这些假设的某种极端色彩的批判则占据了反人本主义的核心。[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反人本主义自身并不是一个同质性的思想运动,关于这点可参见: Béatrice Han- Pile, “The ‘Death of Man’: Foucault and Anti-Humanism,” in Foucault and Philosophy, eds. Timothy O’Leary and Christopher Falzon, Malden, MA: Wiley-Blackwell, 2010. 这一哲学立场与后人类主义都是源于后现代思想,但仅此而已,其他方面二者没什么相同之处。[注]这里我主要关注的是从尼采和福柯的思想遗产中发展出来的反人本主义哲学,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解释反人本主义的哲学家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卢卡奇(GyorgyrgyLukács),参见: Tony Davies, Human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pp. 57-69.对人这个概念的解构处于反人本主义的核心,这点是它与后人类主义的共通点之一。 但是,二者的主要差别已经在词形上显现出来了,尤其是从“后”和“反”二者的字面意义上就能看出。 反人本主义对于“人已死”这个命题所引发的各种后果完全接纳,这个命题为某些后结构主义者尤其是福柯所坚信。[注]参见: Michel Foucault,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相比之下,后人类主义并不依赖于任何象征意义上的死亡: 因为这一假设还是建立在生/死二元论的基础上的,后人类主义早已用后二元论的过程本体论观念来质疑任何严格意义上的二元论了。 毕竟后人类主义意识到等级化的人本主义假设不可能被轻易地消解或抹除。 就此而言,后人类主义更接近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而不是福柯认为的人已经死了的观点。[注] 参见: Jacques Derrida, Of Grammatology,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6.
为了完整呈现后人类的理论图景,还要提一下另外几个概念。 元人类主义是一条最近兴起的研究进路,更多的是来自德勒兹的思想遗产,[注] 参见: Jaime del Val and Stefan Lorenz Sorgner, “A Metahumanist Manifesto,” The Agonist: A Nietzsche Circle Journal, IV/II (Fall 2011), http://www.nietzschecircle.com/agonist/2011_08/ metahuman_manifesto.html, last accessed November 16, 2013. 它强调了身体作为无定形的意义重构得以发生的基点,身体通过运动关系构成了一个身体之网。 但这个概念不应与元人性论(metahumanity)混淆起来,后者出现于1980年代动漫叙事和角色扮演类游戏中,[注]“元人类(metahuman)”这个词在DC Comics (New York)出版社出版的喜剧系列中被经常用到。指那些超级英雄或变种人(mutant),它尤其在某些文化研究的语境中被用到。 最后,后人性论(posthumanities)这个概念在学术界受到欢迎,是因为它强调了某种人类内在的改变,即从人到后人类,相应地,对人之为人的研究也应延伸为对后人类之为后人类的研究,而且它也用来指相对于现在的人类物种具有进化关系的未来的生命存在形式。
七、结论
后人类的叙事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其中包含了不同的观点立场和各种思想运动,它是当代种种对人之为人进行重新定义努力的结果。 后人类主义、超人类主义、新物质主义、反人本主义、元人类主义、元人性论和后人性论,这些为重新思考各种生存的可能结果提供了有意义的方法。 本文对这些思想运动中存在的区别做了说明,并强调经常容易被混淆的后人类主义和超人类主义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关于科技发展对人这个物种的进化产生的影响,超人类主义者进行了大量的讨论,但他们仍然坚持的是人本主义和人类中心论的观点,这弱化了他们的立场; 例如,“人+”运动的目的就是提升人的条件。[注] 在超人类主义者的主要宣传网站Humanity+ (http://humanityplus.org)上这么写道: “人类+”运动主要致力于提升人的存在境遇,我们的目标是对那些勇于展望人类未来的思想家们产生影响。另一方面,物种主义成了后人类方法中的一个部分,在去中心化和非等级化的模式下,它构成了后人类中心论的认识。 虽然后人类主义对科学和技术进行了考察,但没有把这个主题作为自己反思的主轴,也没有把自己的话题限制在技术性的工作上,而是把反思延伸到了各种与生存相关的技术上了。
后人类主义,就其作为批判的、文化的和哲学的后人类主义,或者说新物质主义而言,它很适宜于探究作为地质学时期的人类纪(anthropocene)这个概念。 人类纪标示出了在整个地球的层面上人类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后人类关注的是把人从叙事的主要关注点上去中心化的尝试。 与反人本主义相一致,后人类主义同样强调对人类而言,应该意识到自身从属于一个生态系统,一旦该系统遭受破坏,将对人的生存条件产生负面影响。 正是在这一理解框架之下,人不能被理解为自主的行动者,而是置身于一个延展的关系系统中。 人类被理解为生成过程中的物质化的节点,这个过程是由生存技术所支配的。 就像新物质主义者所明确指出的,人在地球上居住的方式,他们吃什么,如何行动,保有怎样的关系,产生了一张决定他们是谁以及是什么的关系网; 这张网并不是脱离肉体而存在的,而是一个物质化的领域,其能动性超越于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生物学意义上的人而存在。 有了这个扩展的视野后,很清楚任何形式的本质主义、还原主义或内在论的偏见等对于探索这个多维度的网络起到的只能是限制的作用。 后人类主义保持了一种批判和解构的立场,它承认过去,对于现在和未来,则以一种包容和生成的观点来支撑和孕育各种可能。 处于当今的哲学大环境下,后人类主义在行动力、记忆和想象之间达成了一种独特的平衡,其目的是在相互关联的存在的进化生态学中进行融合的继承。[注]特别感谢 Helmut Wautischer和Ellen Delahunty Roby 对本文初稿提出的建议。
Posthumanism,Transhumanism,Antihumanism,Metahumanism,andNewMaterialisms:DifferencesandRelations
Francesca Ferrando
(CollegeofArtsandSciences,NewYorkUniversity,USA)
Translated by Ji Qing-hai
(InstituteofPhilosophy,ShanghaiAcademyofSocialSciences,Shanghai200433,China)
Abstract: “Posthuman” has become an all embracing term refering to a variety of different movements and schools of thought, including philosophical, cultural, and critical posthumanism, transhumanism (in its variations of extropianism, liberal and democratic transhumanism, among others), the feminist approach of new materialisms, and the heterogeneous landscape of antihumanism, metahumanism, metahumanities, and posthumanities. Such general and all-inclusive use of the term has created methodological and theoretical confusion both for experts and non-experts alike. The explor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movements, focusing in particular on the areas of signification shared by posthumanism and transhumanism to explain these two independent, yet related philosophies will show that posthumanism may prove a more comprehensive standpoint to reflect upon the possible future.
KeyWords: posthumanism; transhumanism; antihumanism; metahumanism; new materialism technology; future; posthuman; transhuman; Cyborg
收稿日期:2018-12-1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X020)
作者简介:法兰多(1978—),女,意大利人,助理教授,意大利罗马第三大学博士,专注于后人类哲学问题和女性主义。
译者简介:计海庆(1976—),男,上海人,博士,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70(2019)06-0014-07
[责任编辑 尚东涛]
(注:文中标题前的序号为编者所加。)
标签:人类论文; 主义论文; 人本主义论文; 技术论文; 物质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哲学流派及其研究论文; 其他哲学流派论文;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2CZX020)论文; 纽约大学文理学院论文;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