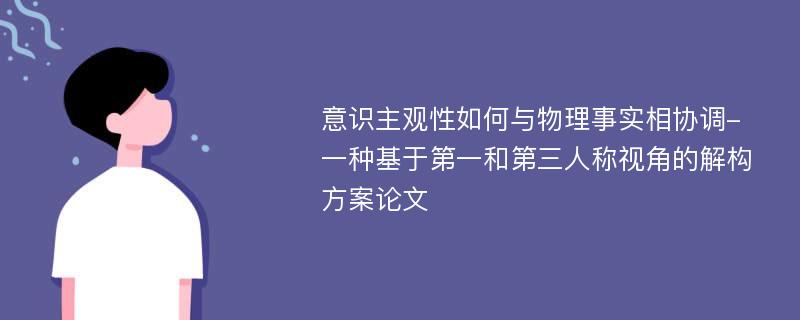
意识主观性如何与物理事实相协调?
——一种基于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的解构方案
文/陈 思
摘 要: 物理事实如何与主观意识相协调的问题被看作是意识困难问题的子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实质上是笛卡尔心身关系问题的现代版本。贝内特和哈克在神经科学的立场上,结合语言分析的方法对该问题的理论预设、方法论根源、以及该问题本身的正确性进行了考察,认为对物理事实和意识经验的区分源于神经科学描述与意识经验描述的混淆,这种描述的混淆又源于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的混淆。
关键词: 物理事实;主观经验;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
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但是笛卡尔主义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意识研究中,他们达成的一种普遍共识:物理事实和意识经验是分属于不同领域的对象。因此,物理事实如何与意识主观性相协调的问题就变得非常棘手,该问题也被看作是意识困难问题的子问题之一。我们不难发现,该问题就是笛卡尔的心身如何相互协调问题的现代版本。虽然讨论的问题的名称和概念有所更新,但是其身心二分的笛卡尔主义立场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哲学家和神经科学家仍然在身心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探讨物理事实和意识经验之间的关系。
一、物理事实和意识经验的混淆
关于意识问题存在的迷惑,许多哲学家都进行过论述。根据塞尔的观点:“存在有意识的心理状态和事件是很明确的事实,但是很难理解物理系统如何产生意识。这样的现象是怎样发生的呢?例如,我大脑中的灰色和白色的粘性物质是怎样具有意识的呢?”[1]大脑的构成物质与意识经验是两种不同存在形态的对象,塞尔对两者之间的生成关系提出了质疑。“对于认识现实,我们的观念是现实应该怎样以及将会怎样,对这一点来说,宇宙中存在着某种不能被还原的主观的东西好像是难以理解的。但是,我们都知道主观性的确存在。”[2]通过直觉,意识主观性是必然存在的东西,但是科学的还原论方法却无法对意识主观性做出还原的说明。
初看塞尔的两处论述,不少读者会认为他说中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仔细思考后,我们会发现,这类论述的依据是日常直觉而非科学的证明。根据查默斯的观点,从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出发,意识是核心的内容,但是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出发,即用时空的微粒、场和波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对世界进行说明,我们发现意识的产生又是不可预测的事实。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拥有意识经验,一方面我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从这些作用中产生的。于是产生了困惑:“我们如何使它与我们所知道的别的事物协调一致?”[3]即意识经验如何与物理事实协调一致?两者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共存关系?该如何在物理事实的基础上来解释意识主观性的产生?
赫胥黎在19世纪就曾经提出:“神经组织受刺激后产生意识是非同寻常的现象,就像阿拉丁在擦拭神灯时突然出现神灵那样令人惊讶。”[4]即使是21世纪的神经科学家也对此有同样的疑惑,“对于意识为什么在大脑中显现,我们具有的想法并不比赫胥黎更多”[5]。依据上述困惑的思路发展,意识经验似乎的确属于一个特殊的现象领域,它与物理事实截然不同。意识经验领域是主观的,每个人的意识经验都是私人的、独有的,只有通过自己的第一人称视角才能经验到,个体无法与他人交流、描述自己的意识经验,也不能对别人的意识经验是否和他相同做出判断。然而,物理世界对于第三人称视角下的观察者来说是公共可观察、可被验证的。要想对该问题做出科学的说明,物理主义则是衡量判断事物是否存在的标准。我们应该在物理主义的框架之中,通过还原的方法为意识找到其神经对应物,揭示物理事实和意识主观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即解决神经活动是如何“产生”意识的问题?这是目前神经科学家和哲学家达成的一种共识。
然而,神经科学家贝内特和哲学家哈克却对上述共识提出了批判。他们认为,物理主义的命题并不是解释心灵和意识的唯一命题,物理主义命题也没有比其它科学命题更加具有客观性,也并不比其他的命题例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的命题更加客观和基础。在涉及人类情感、人类文化、历史演进等许多问题上,物理主义命题都显示出它的局限性。物理主义只是解释世界的一种立场而已,它不是唯一的立场,因此也没有它就是最根本的真理一说。
周一刚一上班,我便接到客户李先生的电话:“你们的硒鼓太贵了,不划算,买几次你们的硒鼓,我又可以重新买台激光打印机了,请问,你们公司是否可以考虑采取优惠或让利政策?”
在已有2个不同时相的遥感影像的基础上,此方法可对比监测出基础设施、行政区划、地貌等信息的变化,可广泛应用到满足条件的工作中去,例如:林地变更调查、青山保护、国土监测等,是一种通用的方法。
贝内特和哈克提出意识是人的属性,而非大脑属性的观点。他们认为,大脑不可能有意识,灰质和白质也不会有意识,只有在有生命的有机体的整体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它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因此,“纯粹的物理系统如何能有意识”在逻辑上完全不可能。塞尔关于大脑中的灰色和白色物质如何引起意识这个问题本身是错误的。
工业革命之前,技术进步非常缓慢,一个人一生几乎感受不到技术的进步,沿着同样的技术路径劳动和生活,可谓天经地义。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个人可以感受到技术的明显进步。1980年代以来,每十年甚至每年都可以感受到技术的明显进步。
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错误共识源于将意识看作是大脑的属性而非人的属性。他们将意识经验置于整体的人的系统中来看待,他们认为,人是处在环境之中的,个体的意识经验受到来自大脑结构、身体感官、环境刺激、内在过往经历等许多因素的影响,我们了解一个人的意识经验的对应物,就要从多角度去说明。因此,对意识经验的说明也需要在多层次的真理观视角下展开。
二、基于第一和第三人称视角的解构
按照日常的语言表述,很多人疑惑的是在视觉纹状皮层被刺激之后的某个阶段,我们的大脑中为什么会产生了一种全新的视觉经验?但是,实际上根本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贝内特和哈克认为,当某个人看到桌子上的红苹果时,不是看到红苹果的意象或者说是大脑看到了它,而是这个人看到的就是作为客观对象的苹果。如果认为神经事件的结果就是关于某个红苹果的视觉经验。这就是一种错误。我们不能混淆两套语言描述的实际所指。否则“我们似乎描述了一种从物质到心灵、从物理事件到心理事件的非同寻常的转化——诸如神经元的发放这样的物理事件如何能转化为诸如视觉经验(当然,如果某人将视觉经验看作感受质,神秘化就会随之而来)这样的在范畴上不同的东西”[6]322。心理语言与物理语言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如果将两种语言混淆使用,就会导致神经活动过程完成后突然产生有意识经验的认识错误。
如果我们坚持分别用两种界限清晰的话语,如神经语言或者日常语言,我们都可以针对看到红色的苹果经验进行描述,并且两套语言表述都不会让我们产生任何的神秘和困惑。而我们的错误就是混淆了两套语言,把它们混乱使用。近几十年来神经科学在视觉研究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这些成就可以解释许多视觉的现象,并对各种视觉纹状皮层进行了复杂的描述,我们从未对此感到神秘。
这种神秘源于我们把科学描述和经验描述进行了混搭,前半段我们接受了科学的描述:“当光线从苹果投射到我的视网膜上的时候,我的视网膜投射了苹果的二维图像”,或者说,“当某种波长的光从苹果反射进入我们的眼睛,刺激了视网膜上的视杆细胞和视锥细胞,随后的冲动沿着视神经传导到丘脑并由此到达脑皮层”。后半段是日常经验的描述,在这个描述中,“我看了一个红色的苹果”或者用有歧义的表达“我具有看到红色苹果的经验”。
如果我们把意识经验等心理状态看作是仅有主体本身可以通达的主观领域,把“物理的”东西看作是物质性的领域,那么混乱就会产生。因为我们所讨论的是两个不同领域、不同的“存在的层次”。如果我们将这两个领域混为一谈的话,就会发现很多平常说话的句子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模糊不清,这是因为我们将两种不同的领域混淆在一起的缘故。
让我们以看到一个红苹果的过程为例来呈现一种描述的混淆现象。“当光线从一个红苹果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红苹果,这并不神秘。然而,当我们重新描述这一现象时,就显得令人迷惑甚至有些神秘。”[6]321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描述看到红色苹果的视觉经验的过程,这个过程并不神秘,而且非常的清晰,它能让我们获得很多有趣的清晰的知识。然而,在我们进行日常语言描述的过程中,我们才发现了某种“神秘”的经验。例如我们可以说,当光线从苹果投射到我的视网膜上的时候,我的视网膜上投射了苹果的二维图像,这些信息经过大脑的内在加工,让我看到了一个苹果的三维立体图像。这样的表述从信息编码的角度对知觉到苹果的过程进行了阐述。但是神秘如何产生的呢?
那么意识经验和物理事实之间是否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呢?贝内特和哈克认为这是一种被概念混淆的错误观念。例如,一个人喝醉了,躺在地上失去了意识,我们并没有觉得发生了什么神秘的事情。酒精的影响越过了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并没有使我们感到震惊。当神经科学家指出醉酒导致意识丧失伴随有前额叶皮层活动的某些变化时,我们并不认为有任何非常神秘的东西得到了解释。同样,认为刺激了神经组织就产生了意识状态的这种概念也是一种错误概念。对于事物的神秘印象是由于观察到被歪曲的现象而产生的。
从广泛定义上来解释融媒体,就是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优势结合,产生新的能量,发挥更大的功能作用。将媒介之间的竞争化为同一力量,通过资源的互通、宣传互融、利益共融达到互相服务的目的。
我们在心理语言和物理语言相混淆的前提下制造了某种神秘。如果在语言层面上进一步剖析,我们会发现,这是一种混淆第一人称描述和第三人称描述边界,没有对第一人称描述和第三人称描述加以严格区分而导致的错误。这种错误导致了意识经验与物理事实相互协调的困难的产生:“光线投射到视网膜上,就产生了对经验的认知。”前半段我们使用了第三人称视角下的客观科学的准确描述,而后半段在语言表达层面,我们使用了第一人称的主观表述来描述看到苹果的过程,于是关于苹果的经验就在神经过程之后产生了。类似的表述还有很多,它甚至广泛出现在我们的日常语言当中。例如,当我的C纤维神经元激活的时候,或者下丘脑的某个区域激活的时候,我感受到痛苦。这样的描述是令人误解的,有误导性的。它让我们误以为神经活动和意识经验之间具有一种因果关系,是神经活动的激发产生了某种感受,是光线的投射刺激使我们产生了红色的苹果的经验。因此,将两个不同层次,不同视角下对同一现象的描述相互混淆,是我们今天追问神经活动是怎样产生意识经验的原因之一,也是我们遇到的困境的根源之一。
视觉理论的贡献就在于说明了动物看到事物的神经过程。神经科学家在视觉神经活动的研究中已经在意识的事实和大脑的事实之间建立了很好的归纳联系。神经科学的解释(第三人称描述)让我们对意识的认识日趋清晰。“这些解释并没有在脑的过程与意识之间的任何鸿沟上假设或者试图假设沟通的桥梁,因为鸿沟的存在就是一种错误观念。”[6]323在阐明了第一人称描述和第三人称描述的共同点,即它们都指称相同的意识经验之后。我们会发现在整个描述的过程中,并没有任何神奇的意识经验突然产生,物理事实和意识经验之间并没有无法逾越的鸿沟。所有这些荒谬的假设都源于概念和视角的混淆,而不是科学尚未揭开意识的神秘本质。
基于神经科学的第三人称描述和基于意识经验的第一人称描述,是对同一对象的基于不同视角和层面的描述,它们彼此不同,但由于指称了相同的对象,而又在一定程度上互相融合,互为前提。因此,意识主观性与物理事实彼此相关,但又各自不同。从第三人称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第一人称视角下的意识主观内容进行推论。根据这一观点,我们可以从正在发生的神经事件中推断出它现在看到的经验的特性,即通过ERP、EEG来推断。比如,通过快速眼动,来推断一个人正在做梦。虽然我们不能知道这个人做梦的内容,但是我们可以在神经事件和主观意识之间做一个直接的归纳推理。“这一从‘脑的物理学’到‘意识的事实’的通道不是无法想象的,这是一个直接的归纳推理。”[6]323问题在于,我们跨越鸿沟之后所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是我们推断出这个人正在做梦?还是想要通过脑电波来推断其做梦的内容?这才是更加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前者,神经科学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并成功跨越了鸿沟。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后者,即通过脑电波来完全知晓个体做梦的内容甚至做梦的感受、做梦的原因等,仅依靠脑电波的变化就想解释这些现象,那么这种从第三人称描述向第一人称描述的推断显然是错误的。因为要想对主体的主观意识经验展开全面的阐释,我们还必须依赖身体、环境以及个体过去的经历、大脑内在信息加工的方式作出相应的解释。仅通过神经活动的描述不足以涵盖意识经验本身的所有内容。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与刑的辩证思想以及关于刑罚轻重的争论,对于我们今天推进法治建设、预防和打击犯罪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三、结语
关于物理过程如何产生意识经验的问题,可以衍生出许多子问题:这些不同于纯粹的物质的东西和性质,是怎样由某种只是更复杂的物质微粒的组合所构成的呢?意识的主观性是怎样通过神经系统中复杂度的增加而跃变为主观感受的呢?意识是如何从物理活动中产生出来的呢?我们被各种各样类似的问题所困扰。通过论述贝内特和哈克对上述问题所形成的共识批判、论述意识的进化基础、以及从神经科学描述和意识经验描述相互混淆三个方面,展开了对上述问题的解构。我们认为,上述子问题的提问方式不仅是错误的,由此衍生出的看待意识主观性的方式也是错误的。因此,意识主观性怎样与物理事实相互协调的问题本身是概念、范畴、描述的混淆的产物,应当予以解构。
参考文献:
[1]Searle. Minds,Brains and Science:The 1984 Reith Lectures[M].London:BBC Worldwide,1984:15.
[2]Searle.The Rediscovery of the Mind[M].Cambridge:MIT Press,1992:99.
[3]Chalmers.The Conscious Mind[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4.
[4]Huxley.Lessons in Elementary Psychology[M].1866:210.
[5]Glynn.An Anatomy of Thought[m].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99:396.
[6]贝内特,哈克.神经科学的哲学基础[M].张立,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32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扩展论对意识困难问题的反思与重构”(17G048)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陈思,博士,江汉大学教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精神分析与意识心理学。
编辑:宋国栋
标签:物理事实论文; 主观经验论文; 第一人称视角论文; 第三人称视角论文; 江汉大学教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