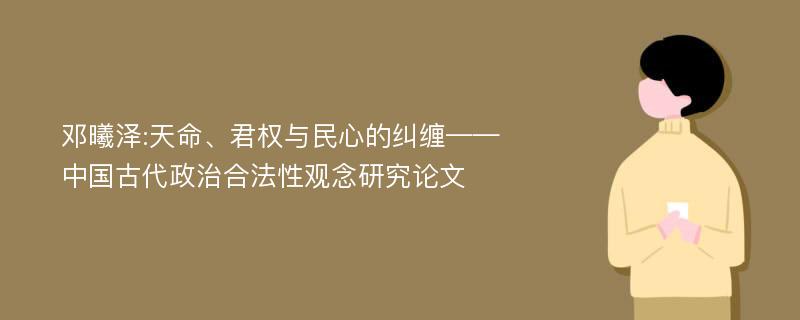
§政治合法性研究§
摘 要:政治合法性针对的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的认可问题,它是每个政权都必须面对的永恒问题。虽然中西都有悠久的政治合法性成文史,但政治合法性理论直到近代才兴起,导致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缺乏相应维度。古代世界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是君权神授。这表现在中国古代,则有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其中有三个要素:天命、君权和民心。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这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理想的合法性结构,且天与民对君权也能产生有限制约,但实际上,由于君权垄断了天命的解释权,架空了天命,致使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无法实现其初衷。
关键词:政治合法性;天命;君权;民心;君权神授
引言 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问题
“我为什么要统治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服从我?”这是任何统治者要想顺利进行统治,都必须向人民交待的问题,即政治合法性的核心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古代也要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那么,中国古代有什么样的政治合法性思想?这就是本文的基本问题。下文的讨论会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和建构行为。但是,如冯友兰所言,中国哲学有实质的系统,但缺乏形式的系统。(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0页。这一观点可以推广至整个中国古代学术。由于政治合法性理论是西方原产理论,中国古代并无一套相应的理论(包括概念),所以,本文便是借助西方合法性理论这个形式的系统来整理中国古代的政权合法性观念的尝试。
一、政治合法性理论及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不足
(一)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论
政治合法性(Legitimacy,或译正当性)问题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亚里士多德说:“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2)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89页。亚里士多德虽然没有使用政治合法性概念,但已经表达了该思想。后面,本文还会讨论《尚书·汤誓》和《尚书·泰誓》二文的合法性观念,以表明古今中外的政权都要面对政治合法性问题。直到马克斯·韦伯,合法性概念和理论才被明确提出。他说:“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地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此书首版于1921—1922年)(3)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39页。奥勒姆这样理解韦伯的合法性理论,“统治关系,在其最抽象最本质的形式上说,包括发布命令的统治者和服从命令的拥护者。因此,这个问题就是,拥护者为什么要服从?”(4)安东尼·M·奥勒姆:《政治社会学导论——对政治实体的社会剖析》,董云虎、李云龙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92页。李普塞特认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合法性是评价性的”。(此书首版于1960年)(5)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张绍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7页。哈贝马斯说:“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此书首版于1976年)(6)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张博树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184页,另见206页。阿尔蒙德等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如果大多数公民都确信权威的合法性,法律就能比较容易地和有效地实施,而且为实施法律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此书次版于1978年)(7)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35-36页。阿尔蒙德除了强调合法性的认可维度,还说出了基于认可的两个重要衍生功能:第一,降低统治成本,即交易费用;第二,当权者可以合法地使用暴力,并垄断合法暴力的使用。让-马克·夸克认为,合法性“是对统治权力的认可”,“被统治者的首肯是合法性的第一个要求”。(此书首版于1997年)(8)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中译本序,佟心平、王远飞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2页。
上述论述都体现了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特征——认可。如果说,韦伯明确表达了合法性所要应对的基本问题,那么,阿尔蒙德等则论述了合法性的基本功能,而其功能是基于认可的。认可是自变量,降低统治成本和垄断合法暴力是因变量。一切政权对于被统治者,只要它要维持正常的统治,就必须建构统治合法性。当然,对于蒙古军队这样的征服者来说,对敌人的合法性建构是不必要的,要么投降,要么屠杀。即便蒙古军队不需要对敌人进行合法性建构,它也需要对自己的成员进行合法性建构。它必须给予它的将士期望:你们跟着我打仗,我会给你什么承诺。这便是在回应韦伯的问题。
(二)方法论
任何政权都要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这一普遍现象也体现在中国古代政治中。中国古代对政治的记录和研究都非常丰富,其中包括大量的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思想和实践,但现代学术对之的梳理、分析和总结颇不到位。用合法性理论分析中国古代政治,属于以西学诠释中学的范式。这种范式究竟对不对,学术界有很多讨论,典型者就是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尽管许多学者不情愿以西学诠释中学,但很难逃逸于现代学术范式,甚至连冯友兰这种文化本位者都不得不承认,西学的形式系统更高明,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的实质系统。
那么,究竟能否使用合法性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的某些政治思想和实践?这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此略作辨析。“合法性”“政治合法性”都是来自西方的概念。西方概念所表达的内容,有些中国有,有些中国没有,无一定之规,需具体而论(这里的中国是指传统中国,截至1840年)。西方有而中国所无者,如基督教这种具体的宗教。中西皆有者,如军队、政治、小麦、煤炭等。那么,中国有无政治合法性思想与实践呢?这里,要注意两个区分。第一,理论与生活的区分。人类有某种生活,不等于有关于该种生活的理论。理论与观念或意识的区别在于它是自觉的和相对系统的。凡动物皆要进食和消化,但人类产生关于进食和消化的概念和理论,不过几千年历史。生活与理论并无确定之先后,有生活先于理论者,如消化活动先于消化概念和理论;也有理论先于生活者,如人工智能理论先于人工智能现象。第二,具体的合法性观念和实践与合法性理论的区分。根据第一个区分可知,判断古代有无合法性观念(观念处于不自觉状态,不是自觉的理论)和实践,关键不在于有无“合法性”这样的概念及相应的理论系统,而在于古人是否处理过“我为什么要统治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服从我?”这两个问题。如果是,则有;如果非,则无。通过后文的考察可以肯定地说,古代政治经常处理这两个问题,所以,古代有合法性观念与实践。因此,可以用合法性理论来整理和诠释古代的相应政治思想与实践。
(三)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研究的不足
由此可以小结,在描述层面,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属于神圣政治契约,其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正德利用厚生。但是,仅从正德利用厚生看不出其神圣性,因此,准确的表达是:上天责令天子代表上天正德利用厚生。
It is important to be able to predict theoutcome and response to chemotherapy in advanced PC. This study assessed the prognostic value of systemic inflammation based markers in patients with palliative chemotherapy due to inoperable PC.
天命确实具有一定的制约功能。但是,在古代中国,为什么每个朝代越到后期,君王便越来越失德,进而百官也因缺乏有效制约而失德,使中国社会陷入治乱循环?也就是说,为什么天命的制约功能近乎失效了呢?这是因为,在逻辑上,君权必然架空天命。
君权神授,这是古代权力来源的一般原则,而不决定具体形式。不同的君王有不同的神授方式,即有不同的“神迹”或“天象”。《诗经·商颂》说商人祖先乃是奉上天之命而降生的。《史记》说周的祖先弃则是因姜原践履巨人迹而生,刘邦是赤帝之子,连造反的陈胜也要在鱼肚子中藏一帛条,上书“陈胜王”。(14)这几例参见《史记》之《周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由于陈胜造反最终没有成功,所以其行为便沦为装神弄鬼。如果陈胜成功了,则史书肯定是另一番描述。在陈胜的事迹中,卜这个角色的作用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思。卜(可能出于对秦二世的不满)知道陈胜的意图,给出了陈胜想要的解答。其实,卜的预测是不准的,他说陈胜“事皆成”。但若以建立新政权,成帝王为目标,陈胜并未成功。卜,可以称为“通神者”。在中国古代,卜、巫、祝、史都是通神者。在其他文化中,神父、阿訇等则是通神者。这意味着,君王和通神者勾结,可以垄断天命的解释权——上天究竟说了什么,君王和通神者说了算;这也进一步意味着天命观或君权神授的困境——君权可以架空天命(下文详论)。除了上述具体的神迹,天命权力更理论化、系统化地表现为邹衍提出的五德终始说。秦始皇认为自己获得了水德,而汉朝则自认为获得了土德,因为根据五行相生相克之理,土克水。欧阳修指出:“故自秦推五胜,以水德自名,由汉以来,有国者未始不由于此说。”(15)欧阳修撰、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第二册,成都:巴蜀书社,2007年,第32页。君权神授的观念,穿越周秦之变,直到晚近仍是如此。洪秀全为了发动群众,甚至还抬出一个洋神上帝,声称其权力来自这个“上帝”。(16)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页。
二、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基本模式——以《汤誓》《泰誓》为典范
(一)君权神授的中国形式及其理想状态
在政治建构中,权力来源是第一重要的事。一切权力的终极来源只有两种可能:神授和民授,即神性合法性和人性合法性。君权神授与官权君授都属于神授权力。欧洲中世纪及一切政教合一的社会,都是君权神授。至于神、君王的称谓,各个政权及其各个时期可能各不相同。此外,各个政权中神授的形式也各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属于君权神授的一种具体形式。而民主选举而产生的权力,就是民授。在人类历史进入现代社会之前,除了雅典民主,所有权力都是神授的。当代某些宗教国家的权力,仍然是君权神授。值得辨析的是现代专制者(如希特勒的专制、斯大林式专制)的权力来源。现代专制者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或许有人说实际上并非如此,但政治合法性是一种理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一套说辞。基于这套理论或说辞的政治合法性建构本来就属于认同建构,是名义上的,至于实际如何,并非完全可以实证。这套说辞一旦被人们相信,就具有约束力;反之,一旦被怀疑,约束力就降低;一旦被否定,约束力就丧失。这与君权神授同理。实际上,神是人的一种建构,当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存在神,且神赋予君王权力,那么,这种政治合法性建构就能得到认可。神是否真实存在虽然仍是一个问题,但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是否认为神存在。人们做出判断,通常依据的是“认为如此”而非“事实如此”,这在社会领域尤其普遍。此如芬纳引用帕雷托的观点所言,“特定的政治行为不取决于一个命题的真假,而是取决于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12)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47页。如果一种文化中的人们认可神是宇宙的掌控者,并衍生出神授观念,包括神授君权、神授命运、神授财富等,那么,君权神授就能得到人们的认可,统治成本就会降低。即便在现代民主中,民主也很容易被操纵。有人怀疑一人一票的选举是否真正能表达人民意志,但只要大多数人认为选举能表达人民意志,民主就被认为是一种好制度,是有效的。比较而言,很难否认,选举扩大了人民意志在政治建构中的权重。
根据Nei的计算方法对5个广西地不容居群进行遗传距离和遗传一致度的统计分析。居群间遗传距离的范围为0.076 0~0.686 1,其中遗传距离最近的是平孟(PM)和弄民(NM)居群,遗传距离最远的是平孟(PM)和洞靖(DJ)居群。遗传一致度的范围是0.556 5~0.926 8,其中遗传相似度最高的为PM和NM居群,最低的为PM和DJ居群。遗传距离分析和遗传一致度分析得出的结论一致。
事实上,这个合法性结构对君权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天对君权的制约,二是民对君权的制约。
2000年以来,对古代尤其是儒学的政治合法性观念,学界的关注开始增多。CNKI篇名检索“合法性+古代”“合法性+儒家”“合法性+儒学”,大约30篇有效文献。最早的文献在2000年,这意味着学界对古代政治合法性的研究自觉得比较晚。新近研究都是在新的理论即合法性理论之下重新审视常见的古代文献,其独特之处不在于文献,而在于理论视角。这种做法是合理的,本文也是如此。但新近研究有两点不足。第一,在理论基础上,不少论文没有阐释合法性的基本含义和功能,也未引用西方相关经典文献。这些研究者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甚至凭空想象来使用合法性。虽然合法性的含义和功能并不难理解,但不把握西方学者的相关经典论述,理解上仍有偏差。譬如,一些论文没有区分终极合法性和派生合法性及二者的关系,也没有认识到终极合法性只能有一个,而派生合法性可以有多个,如德、民等(限于篇幅,具体文献从略)。第二,缺乏对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有效性的分析。政治合法性建构是要考虑效果的,而上述研究描述性居多,缺乏分析和评价。君权神授是否能有效实现神或天的旨意?天命如何被君王垄断?君德由谁来评价和保证?天命的转移即朝代的更替是如何实现的?人民在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中有什么地位?实际上,在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天命会被君王架空,上天并不能有效制约君王。对这些问题,上述研究缺乏批判性考察。
通过学习和活动的开展,为改革创造了良好的舆论环境,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的要求和总局党委对农垦改革的规划部署上来,凝聚起坚定不移拥护改革、支持改革、推进改革的共识。
当然,上天不会随便选择一个人做天子,它会选择正直、聪明、睿智的人。“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论语·泰伯》),《尚书·尧典》开篇就说尧的德性才干,“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尧年老后,禅位于舜。但是,孟子不认为这是尧将天子之位传与舜,而是天给予舜。并且,禹传位于子,也是天意。他引用孔子的话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上》)一在何处?——天意。所以,儒家的政治合法性观念乃是天命观,它是中国古代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合法性观念。天命的含义是天命令一切。天既是造物主,也是万事万物的运行规则、过程和结果的最终决定者。《尚书·盘庚上》“先王有服,恪谨天命”的“天命”就是此意。由此派生出后来的命运观念。天命是古代学术的一个大话题,但不是本文的专门话题。本文的对象既不是天命,也不是君权和民心或民本,而是三者的关系。所以,关于三者本身的讨论,本文从略。
1919年2月,孙中山先生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之一——《建国方略》。在《建国方略》《实业计划》第三计划第三部“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中,孙中山先生为毕节规划了三条铁路。
芬纳认为,儒家虽不是宗教,但“它是一个和中世纪时罗马天主教一样无所不包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比当权者更强大,因为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实施统治,正是借助于信仰系统”。(17)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29页。芬纳所持的乃是比较严格的宗教观念即强宗教标准。不论儒家算不算宗教,都可以肯定,儒家是一种神性文化,也是一种信仰系统。其实,判断一个社会是不是神性社会的唯一标准就是: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是否认为神是世界的最终创造者和决定者?(注意,是“认为如此”而非“事实如此”)若是,则是神性社会;若非,则不是。当然,神性社会有表现形式(是否一神)和程度的区别。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是“一神+强程度”,印度是“多神(非常庞杂)+强程度”,中国是“多神+弱程度”。儒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认为天/神是世界的最终创造者和决定者,尽管程度较弱。同时,统治者也认为天/神是政权的最终决定者,并向天/神寻求最终合法性支持。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是神性社会,只不过中国古代有多神或泛神的特征,且程度较弱。
本研究参照既往文献中个体化有限元建模方法流程,采用基于CT灰度-弹性模量关系公式对骨骼模型进行材料参数赋值[10-12]。根据下述文献公式(2-1)和(2-2),将骨骼材料分为10种梯度。
(二)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典范:《汤誓》《泰誓》
任何政权都要进行合法性建构,但未必都以成文的方式流传下来了。幸运的是,早期中国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成文文献很好地保存下来了。《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牧誓》(依时间先后)都是这样的经典文献,且都是革命动员令和战争动员令。这种动员令最能体现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方式,因为此时的领导者或统治者最需要民众的认可和支持。
从2017年11月开始,国内三家主要的新零售超市苏宁苏鲜生、阿里盒马鲜生、永辉超级物种陆续进入成都。与此同时,本土企业迅速在新零售领域崛起。在2017年一年中,成都成为各大新零售企业的主要目标市场,成都已经成为新零售的必争之地。纵览全国各地,“新零售”似乎每一个城市都在参与,这种百城争鸣的现象正加速新零售的发展势头。
《汤誓》是商汤灭夏之前对同盟者发表的动员令。其有几个层次:第一,商汤数落了夏朝的罪恶;第二,商汤不是要作乱,而是替天行道;第三,利益承诺;第四,暴力威胁。夏朝违背了天命,残害人民,这是它的罪行。这意味着,夏朝丧失了政治合法性,也就丧失了执政的资格。商汤之所以要推翻夏朝,不是作乱,而是替天行道。“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是商汤故作姿态,认为自己只不过是被迫接受上帝的旨意,从而掩盖了自己想掌权的主观动机。同时,利益承诺是政治合法性建构的必要条件(“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人们建立和支持一个政权,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接受统治者的统治,是要获得利益(广义,包括安全)。这是一种交换,准确地说,是政治交换。除了允诺利益,商汤还威吓同盟者,如果不跟从他,就要被惩罚。利诱和威逼这两种手段,商汤都用上了。
从生活与理论的关系看,虽然作为理论形态的契约论自卢梭才形成,但契约这种观念和活动早就有了。《汤誓》这个动员令其实就是一个契约,“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就是商汤对同盟者的承诺。在信仰神灵的古代,这种承诺被赋予神圣性,即“天命”。从祛魅后的现代观点看来,这种天命当然是虚构的,是掌握话语权的某些古人赋予的(如君王、御用文人,及革命者如陈胜)。久之,天命观则成为一种为大众所认可的观念。变换帕雷托的话,则是:“人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决定了“特定的政治行为”。政治合法性建构需统治者被认可,而这种认可本身是基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公共交往。统治者只有向被统治者作出一定的承诺(实现是另一回事),才存在是否被认可的问题。而这种承诺-认可的交往关系,就是契约关系。所以,政治合法性完全可以放在契约论中理解。
特别值得发掘的是,古代政治契约有别于现代政治契约。现代政治契约是世俗的,其最终保证者是作为公意的民意;而古代政治契约是神圣的,其最终保证者是神灵。现代政治契约的集中和典范表现就是选举。在选举中,竞选者作出承诺,选民投票,选民成为权力和政治合法性的最终源泉,无需借助一个外部超越者——神灵。但在古代,统治者不是作为竞选者,而是作为天命者获取权力。虽然统治者也向人民作出承诺,但人民不是选民,统治者与其说是向人民作出承诺,不如说是履行神灵的命令——至少就统治者的自我宣称来说是这样。《汤誓》所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泰誓》的“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大勋未集”,“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西方的君权神授时代,也有同类的观念。芬纳的《统治史》特别重视讨论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苏美尔王朝(大约公元前3500年)就认为,“王权从天而降”;“关于国王的神话同样别具一格……大概是因为缺少一个统治者,民众‘无视上神的命令’。于是,王权的神圣起源和功能就是为了使人类适时地服务诸神。为了实现侍从神对于其主人的角色,城市守护神可能会寻求一个凡人来以他的名义行事。这个人就是城市中的‘恩西’或者‘卢伽尔’。他是人和神之间的连接,这种方式显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他是神圣的化身……”(18)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117、122页。“恩西”和“卢伽尔”的大意都是君主。这种权力来自于神,同时统治者垄断神意解释权的结构,与中国古代的绝地天通是同构的,只是具体情节有差异。《尚书·吕刑》说:“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抱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鳏寡无盖。”《国语·楚语下》中观射父也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颛顼与苏美尔时期的凡人“恩西”的功能和地位完全一致,就是沟通神灵的人,因而是垄断神意的人。重和黎,则是对通神功能的具体分工。这种极少数凡人作为统治者垄断神意的结构,在一切君权神授乃至于一切神灵信仰社会都是一样的。这种观念到了中世纪只有情节的变化,而无结构和实质的变化。在拜占庭帝国,政治合法性是如此建构的,“皇帝由神所选出,处在神圣天意的保护之下。他是整个帝国政府的主人,是帝国军队的指挥官,是至高无上的法官和法律制定者,他还是教堂的保护者和真正信仰的守护人……作为一国之主,皇帝在事实上拥有不受限制的权力,对皇帝的资质的限制也仅限于道德观念和传统。只有在宗教事务上,皇帝们的专制主义才会受到真正限制”,“皇帝的权威直接来自于上神,这是一个教条和公理”,皇帝就是“同使徒”(等于基督的“使徒们”,因此便成为神圣的、超自然的力量)。(19)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二《中世纪的帝国统治和代议制的兴起——从拜占庭到威尼斯》,王震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3页。这样的皇帝与中国的天子观念非常接近。天子是上天之子,也是上天的使徒。秦汉后,虽然中国主流文化的神性或宗教性较弱,但其本质仍是神性的,君权仍被认为来自于天。“天命”和“神授”并无本质不同。
再看《泰誓》。《泰誓》说服同盟者、争取认可和建构政治合法性的叙事结构,跟《汤誓》完全一致,只不过换了对象和情景。而在整个古代,这套合法性建构模式一直被延续。这套被神圣化的政治契约,可以用六个字来概括——正德利用厚生。(20)《尚书·大禹谟》《左传·文公七年》。古今都有人认为《尚书·大禹谟》是伪古文,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无论其是否为伪古文,都说明古人认同该文的思想。正德利用厚生是应然意义的,违背之,便是违背政治合法性。例如,李自成便是指责明朝统治者违背正德利用厚生,从政治合法性角度攻击统治者,并建构自己的政治合法性:“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驰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爰苦于祲灾。”(21)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卷一,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28页。其核心便是,统治者失德残暴,丧失了天命。
政治合法性问题的产生时间与政权并无一致性,它要早于政权。政治合法性建构在政权产生之前、之中和之后都必须一直持续不断地进行。在政权建构之前,潜在的统治者要(以和平或暴力的方式)取代现政权,建立新政权,就必须首先动员尽可能多的人民支持他,所以,在新政权建立之前就要进行合法性建构。例如,《汤誓》《泰誓》都是在新政权建立之前的政治合法性建构。其实,可以想象,在此之前,商汤和周武王早就在做动员工作了。而其动员的方式显然不外乎作出承诺,尽量争取同盟。在政权建构之中(即正在采取行动成为统治者的过程中,如刘邦起事到正式成为皇帝之间的时期,此时的统治者仍然是潜在的),潜在的统治者也需要不断作出并加强承诺,以继续争取、扩大同盟。建立新政权后,现实的统治者还需要继续进行政治合法性建构,这表现为兑现承诺。若(严重)不能兑现承诺,就会丧失合法性,有被颠覆的风险。这种合法性建构的长期性,也完全存在于现代民主政治中。选举前和选举时都要进行宣传、承诺,以争取支持者。新政府产生后,也需要兑现选举承诺。若严重不能兑现,就会丧失合法性,在新的选举中丧失执政权。
在承认可以用合法性理论整理古代政治思想与实践的前提下,再看看民国以来的政治史研究,则可以发现一些不足。无论是在政治实践还是政治学研究中,政治合法性都是极为重要的问题。但是,现代学术范式中的古代政治史研究,包括一般性的政治史及政治思想史、政治制度史,对这个问题的关注不够。这主要还不是相关著述没有使用“合法性”概念和相应理论,而是没有回应“我为什么要统治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服从我?”这两个问题,因而缺乏理论性。要理解一个事件,理论极为重要,犹如坐标。如果不能建立合理的坐标,事件就无法被有效定位,就犹如随机分子在飘移,做布朗运动。尽管很难说哪种理论正确,但理论坐标并非随意选择的,而是可以讨论、比较并区分优劣的。
患者入院后立即通知医生并给予常规护理。嘱咐取半卧位,床头抬高15度,迅速判断患者的病情同时对患者的神志、体温、脉搏、呼吸、血压、氧饱和度、鼻腔出血量及全身状况进行评估,密切观察与监测[3]。对于出血量少的低危高血压患者积极给予心理干预,健康宣教。对于出血量多的中高危及极高危患者(>140/90mmhg)应积极给予额部冷敷,根据患者血压情况给予个性化的降压药物治疗。叮嘱患者如有血液或分泌物流入口腔应及时吐出,以免造成胃部不适引起恶心、呕吐而加重出血和血压升高。
在一切神性文化中,神掌握绝对真理,不可能犯错。所以,君权神授的理想状态就是:神选的天子都是德性、才干俱备的人。至于这一理想能否实现,又当别论。
三、政治合法性建构中天命、君权与民心的关系
(一)天是源动力,民是目的,君是中介
政治合法性建构的核心内容是正德利用厚生,它既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承诺-信用,也是被统治者对统治者进行让渡-认可的理由。古今比较,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它是三元关系和结构,即神、统治者、人民;而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是二元关系和结构,即统治者和人民。第二,在理论上,它的终极裁决者是神灵,而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终极裁决者是人。第三,在理论上,在古代的三元结构中,只有统治者与人民是互动的。神灵虽然也会以神启的方式发号施令,但它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并不参与统治者与人民的互动。而在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的二元结构中,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互动的。
在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中,有两端,一是天,二是民。天是形而上的,是合法性的终极来源;民是形而下的,是合法性的最终实现对象。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心观很重要。“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尚书·泰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天生之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君道》)等等。古代民心观,可以概括为民本观,简言之,以民为本。以民为本,就是要正德利用厚生。《尚书正义》对正德利用厚生的解释是:“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三者和,所谓善政。”由于民本观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这里不做敷述。这里的问题是:如何区分天道与民本的关系?能否把民本视作古代政治合法性的终极来源?答曰:不能。如前文所言,要区分终极和派生。民本是派生的合法性来源。重视民生,以民为本,是神灵或上天的恩赐,君王则是服从于神意而重视民生的;百官作为君权的衍生,直接服从君王,间接服从天命。黄宗羲曾概括道:“原夫作君之意,所以冶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既然君王秉承上天旨意,服务于人民,所以,百官也要服务于人民。这一政治假定在任何时代都没有人敢反对。如果君王或官员公开说他们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人民肯定不服从他们,其统治也就无法稳定地进行。所以,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在《罪己诏》中也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由于官权是君权的衍生,出于讨论方便,本文将官权合并在君权中讨论。
圩堤设计防洪标准为在湖盆区圩堤以防御相应湖口22.50m(吴淞)的洪水位,在五河尾闾区圩堤防御各河20年一遇的洪水位,穿堤建筑物设计洪水位按所在堤段设计洪水位加高0.5m,堤防等级为4级。主要建设内容为堤身加高加宽、填塘固基、护坡护岸和建筑物加固工程,加固圩堤堤线总长658.03km,工程共完成投资8.25亿元,批准设计内的项目在1998年基本完成。
古代政权合法性理论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天与民这两端,君及其衍生出来的百官反而是不重要的。天是源动力——万事万物包括人都来自于天,天因怜悯民而欲福泽生民;民是目的——被服务对象;君是中介——听从天意服务于民的工具。这意味着,在理论上,这个合法性结构完全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是非常完美的。
无可否认,直接引语在内容和形式上没有任何变化,通常看起来对读者来说更具说服力和可信度。相比之下,间接引语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新闻记者解释和重组,他们可能将自己的意识形态融入新闻话语中。因此,为了实现有效的宣传,中国报纸应该通过采用更多的直接引语来更好地使用话语权。
(二)天与民对君权的有限制约
中国古代,权力被认为来源于上天。“天佑下民,作之君”(《尚书·泰誓》)。王替天行道,故名号为“天子”,即上天之子。“天子”这个称谓直截了当地展示了君权神授。这在西方古代也是如此,“有关神圣王权的神学也是一样:统治者是神灵的体现,后来又成为神的儿子,实际上几乎就是一个神”;“国王是神和人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介和联系……除了国王以外,没有人会代替神行事。国王向神祈祷,作为回报,他得到神的赐予,神以其特殊的力量分配给他生命、权力、健康、幸福、英勇”。(13)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140、158页。
从《尚书》看,古人早就认为,如果君王作恶多端,就会被天惩罚。“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甘誓》),这是启讨伐有扈时所作的战争动员,也是合法性建构。启运用了天命观,这是最早运用天命来动员群众、惩罚对手的记载。《汤誓》(“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泰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也运用了同样的天命观。神灵可能不是真实的存在,但在神灵信仰时代,人们认为神灵存在。孔子便说:“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周易》也讲:“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是说圣人以神灵教化人们。通过一代代的教化,民众都相信有一个超自然力量——神灵存在(认为如此而非事实如此)。当然,这种相信也有客观基础,因为古人的认知能力和生产力低下,人们对世界持有恐惧。如罗素所言,“宗教最重要的起源是恐惧”。(22)罗素:《为什么我不是基督教徒》,沈海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40页。爱因斯坦也认为,“在原始人心里,引起宗教观念的最主要的是恐惧——对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恐惧。因为在这一阶段的人类生活中,对因果关系的理解通常还没有很好发展”,他把由此形成的宗教称为“恐惧宗教”。(23)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79页。中国古代的天命观,在先秦具有较强的宗教特征,在秦汉以后,也具有半宗教的特征。跟宗教具有惩罚性一样,天命观也是以惩罚为基本特征的。如果君王失德,就会遭受上天的惩罚。后来,这种惩罚观念扩展到其他人,包括佛教的因果报应观。那么,什么算失德呢?根据正德利用厚生观念,“厚生”的反面“害生”即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就是失德。《泰誓》给出了一些描述:“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焚炙忠良,刳剔孕妇。”这是君王的失德。由于官员属于君权的延伸,所以,官员的失德也是君王失德的一部分,都要记在整个统治阶级的账上。连崇祯皇帝自己也承认,“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递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殃贫,或理狱则以直为枉……嗟此小民,谁能安枕?”(24)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页。
统治者失德,上天就会惩罚。惩罚有两种方式,一是灾异,二是造反。灾异的前提是神灵的存在和天人感应。如果君王失德,上天就会以某种方式降灾于人间。“灾之为言伤也,随事而诛。异之为言怪也,先发感动之也”(《白虎通义》卷六);“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春秋繁露·必仁且智》)。当灾异发生后,准确说,当某些现象被认为是灾异后,统治者就可能会采取减轻刑罚、减免税赋、赈济灾民等措施。有时,君王还会下罪己诏。如果区分终极和派生,在形而下层面,造反属于民对君的制约,但在终极层面,仍然是天对君的制约——一切都来源于天,这是神灵信仰时代最基础的观念。古代的造反,其终极理由不是为了伸张人民权利和利益,而是替天行道。虽然替天行道包括了对人民权利和利益的部分实现,但根据不在于人民意志,而是天意。
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有些君王能够从灾异或祥瑞中反省自己,为政以德,重视民生,从而践行了“天命”。(25)古代关于君权和官权的制约,是个大课题,本文并非专门讨论权力制约问题,对权力制约的讨论是为了辅助讨论政治合法性建构。譬如,周文王、周公、周成王、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等。同时,造反也对君王有一些制约。譬如,唐太宗对隋亡的总结,承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为民能成君(成国)也能毁君(毁国)。西方也有学者认为天命观及其支配的造反理论对君权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26)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146、147页。
(三)君权架空天命
作为最早的政治思想史,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1922年)第二章讨论天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君权来自上天所赋。梁启超其实已经意识到上天是君权的合法性来源,只不过没有合法性这样的概念。不知是否因为天道观念在当时还有较大正面影响,所以梁启超讨论了天道;也不知是否天道日益被解构,所以后来的学者很少讨论天道。其实,不论天道是否应被解构,就实际情况看,它的确是古代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历史研究不能否定这种实然。学界久负盛名的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1940年代初)没有涉及政治合法性问题。该书主要以人物为纲,阐述古代政治思想家的思想,史料不可谓不翔实。但是,该书政治学意义的政治思想却并不凸显——问题不是出在史料上,而是出在理论背景上,作者对西方政治学概念和理论并不熟悉。在政治哲学中,政治合法性是建构政治系统的基础性问题,但萧公权却没有触及,不能不说是个遗憾。虽然合法性理论传入中国较晚,但“我为什么要统治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服从我?”这两个问题并非地方性的,而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任何政治,古代文献(典型者如《汤誓》《泰誓》)便有翔实的记载。萧公权之后,大多数中国古代政治史的研究也没有关注政治合法性问题,这是我们对现代政治哲学的理论框架还不够熟稔所致。吕思勉的《中国政治史》和《中国制度史》、周谷城的《中国政治史》、严耕望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纲》、白钢主编的《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一卷)、齐涛主编的《中国政治通史》(第一卷)、马平安的《中国政治史大纲》、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都没有专门讨论政治合法性问题。不过,杨鸿年、欧阳鑫的《中国政制史》明确讨论了权力合法性问题,认为君权神授是古代君权来源的基本观念。(9)杨鸿年、欧阳鑫:《中国政制史》修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0-32页。刘泽华的《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也谈到了神佑王权,(10)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通史》先秦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22-25页。但作者认为这种观念限于殷周,这并不妥当。其实,这种观念贯穿古代。上述政治史、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思想史研究,史料翔实,对于古代政治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组织、沿革、职能等有详细的陈述和总结,却乏于政治学分析。但是,西方的某些研究对合法性的理论认识及其在政治与政治史研究中的意义甚为明确。芬纳在巨著《统治史》中专门讨论了合法性问题的重要性,“统治者如果不能使自己的统治合法化,就无法维持自己的权威”。他谈到韦伯的合法性理论对其研究很有帮助,并在小标题中突出了合法性的重要性,还讨论了不同政体的合法性基础。(11)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王震、马百亮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40-43、47页。
相较于现代政治合法性建构,古代政治合法性建构要复杂得多。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引入了神灵这一维度和参与者。但麻烦也正是在于这一参与者,因为神灵在经验中不可验证。神灵(包括中国的神灵意义的天)是否真的存在,这无法确证。那么,神灵如何发挥其终极裁判者的作用呢?——通过神启和通神者,并最终取决于通神者。神灵不可能在经验中现身。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以理论的方式杜绝了神灵的经验可能。由于古代学术不发达,这种理论在当时乃是以传说的方式出现。甚至,传说比学术的论证更有力,因为传说叙说的是一个被人们认为是真实的事件,只要受众相信,就无需质疑,也无人(至少很少有人)会质疑,而学术总是源自怀疑。在西方,这种传说就是诸如神灵需要沟通者的故事(沟通的前提是隔绝),如上文的“恩西”;在中国,则是绝地天通。“绝地天通”其实比西方的表达更精准。
在神性社会,神不但是政权的终极合法性,也是人的全部生活意义。前者即君权神授,本文论述较多;后者如韦伯所言,人们生活的“全部意义在于上帝,而不在于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只有一个生存意义,即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27)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78页。不过,人民对上帝的服务并非单向的。可以说,天与民互为目的,但两个目的不同。上天是因怜悯人民并为了解决人民困苦而赐予人民各种福利,包括为之设君;人民则是为了体现上天的伟力与仁慈而努力生活,但后者才是终极的。其实,这种互为目的的结构在世俗的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有体现。父母为子女好,子女努力光宗耀祖。同样,后者是终极的。
绝地天通后,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直接获知神意。但既然神是人的生活意义,神灵就必须向人传达旨意。神灵怎么传达其旨意?——神启,即神灵通过自然界和社会的一些现象来表达其旨意,再通过通神者传达给人民。此如《周易·系辞》所言“是故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那么,谁来理解和解释神意呢?——通神者。《系辞》所言的“则之”“效之”“象之”等,就是通神行为,而圣人就是通神者。虽然圣人、卜、巫、祝、史都可以充当通神者,但其实几者不是平行的,圣人最为重要。在早期,天子本身便是圣人,且是最大的通神者,此所谓圣、王合一。时代越早,圣、王合一的特征就越明显,天子不但是最大的通神者,也是唯一的通神者。《史记·五帝本纪》便讲黄帝、尧、舜等天子自己就直接通神,且不借助其他通神者。即便存在其他通神者,也是天子加封的。这种加封是一种分工,即天子把通神的具体事宜分给了自己任命的负责通神的卜、巫、祝、史(参见《尚书·吕刑》),而这些具有不同通神功能的岗位在后世都演变为职官。在逻辑上,也不允许其他通神者先于天子或与天子同时获得天意,因为两种情况都会导致其他通神者本身也具有天子的属性,因而打破天子的唯一性。只有其他通神者的功能是天子赋予的,才能维护天子的唯一性。而《史记·五帝本纪》《尚书·吕刑》这样的文献之所以可以作为证据,是因为其有效性并不依赖于黄帝、尧、舜真有其人,更不依赖于他们真能通神,而只依赖于后人“相信”有其人、有其事。因为神灵、君权神授等本来就是一种信仰,而非可验证的事实。
由此,还可以把其他一些观念结合起来理解。根据“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礼记·乐记》),那么,只有直接通达天意的天子才能(代表上天)作则,其他人只能转述天子的意思,即作为述者,这就加强了早期的圣、王合一观念。再根据神意从上天到天子再到代理人再到人民的神性逻辑,那么,对于神意的向下传递,孔子都只是二传手(述者),作为天子的尧、舜、文、武等才是一传手(作者),才是直接且唯一的通神者。这意味着,《周易》里的圣人不是孔子,而是更早的圣王(孔子不可能在《系辞》等中自称圣人)。如果要将《系辞》里的“圣人”(复数)对应于具体人物,他们就是伏羲、文王等天子,尽管有些人物可能是传说的。所以,《中庸》讲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也就容易理解了,孔子只不过是神意的二传手。并且,此言表明,最后的圣王是周武王,即最后一个值得孔子学习的圣王。结合其他史籍可知,周武王之后,的确再也无人被尊为圣王了。放在承认神灵与君权神授的观念背景中,上述观念及相应文献都可以豁然贯通。而到孔子被尊为圣人时,圣与王已经分离了,而圣也日渐演变成形容词。因此,古代中国的圣与王的关系经历了从圣、王合一到圣、王分离的过程,这种分离在理论上使通神者与掌权者实现了分离,并必然表现为一种分工。(28)我怀疑,之所以有此分工,或许是因为天子发现,自己既是掌握最高权力者,又是公开的最高的通神者,这种高度集权将导致一种局面:神意是什么,完全由天子自己说了算,因而可能不服众。而分工,毕竟多了一个第三方(另外两方是天子与民众),因而有助于提高公信力。这虽然不是现代的分权,但跟分权有助于提高公信力的道理是一致的。因此,我怀疑这种分工是经历最初期的最高权力者与最高通神者合一的阶段后,最高权力者(这是最重要的职位)的一种自觉的制度设计。同时,卜、巫、祝、史的通神功能是不同的。这很可能是天子对通神功能进行分割,其目的是不能让任何一个通神者掌握和垄断全部通神功能而反过来凌驾于自己。这种观点的简单文献支持是《尚书·吕刑》所言“皇帝……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和《国语·楚语下》所言“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这明显是一种自觉的行为。关于此间关系,《文心雕龙·原道》的概括最为精准:“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无滞,日用而不匮。”
由此可以得出一个阶段性结论:通神者通过神启获知和解释神意。这意味着,大众没有神意的直接获知权和解释权,通神者垄断了神意的解释权。
但是,问题由此而提出:神意模糊不定,没有确定的特征,如何才能保证通神者的解释是可靠可信的呢?——没有任何手段能够保证通神者的解释是真的,因为神意是否存在完全是可疑的,无法验证。通神者本身是君王任命的,他们很大程度上要服从君王的意图,如前所举陈胜的例子。因此,通神者对神意的解释垄断权,完全可以合并到君王这一统治集团。这意味着,对神意的解释权被君王垄断。在这里,我们可以提几个问题:第一,天其实是想象的,天自己不会说话。(可质疑的是:天究竟是否存在?)第二,君王是代表上天的,并且只有君王代表上天。(可质疑的是:即便天存在,凭什么只有君王代表上天?)第三,君王把权力修饰为为民服务的义务和责任,似乎成了苦差事,并且这种使命是自赋的,而非民赋的,它不允许人民选择,人民是被动地被服务。(可质疑的是:人民可否不要君王服务?一般地看,谁服务谁,是由服务者还是被服务者决定?如果由服务者决定,是否谁都可以强行服务别人?)第四,君王只听上天的,对上天负责。(可质疑的是:上天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现身,谁知道上天对君王如何授意呢?)第五,君王及其代理人(如卜、巫、祝、史)垄断了天意的解释权,归结起来就是被君王垄断,君王根据他自己解释的天行事,也就是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例如,隋文帝晚年常常发脾气,不顾律法规定,任意妄为,滥杀无辜。“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劝解道:“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可隋文帝却认为:“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隋书》卷二十五志第二十刑法)于是执意杀人。那么,天对这样的君王有什么约束力呢?天只不过是君王自己意志的神圣化而已。(可以质疑的是:为什么平民不能获知天意?)同样,在西方古代,“国王是神和人之间独一无二的中介和联系……因此有必要创造出关于国王‘神圣’的理论”。(29)塞缪尔·E·芬纳:《统治史》卷一《古代的王权和帝国——从苏美尔到罗马》,第158页。可以参照的是,路德的宗教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了经典的解释权,人人都可以通过《圣经》直面上帝,并通过各自对《圣经》的理解来理解上帝。这样,以前基督教的宗教解释垄断权就被瓦解了。但是,在中国古代,上面几个括号中的问题都是不能讨论的,所以古代要限制言论自由。当然,这也不是中国特有,古代世界均是如此。在中国古代,为了垄断天意的解释权,君王的代理人即某些学者构造了“绝地天通”的传说,甚至禁止私家修习天文,以禁止人们获知所谓“天意”。即便开明的宋代,私家修习天文,也要受严惩。(30)薛梅卿点校:《宋刑统》,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75页。
由此可以小结,在一切君权神授观念中,在理论上,君权来自神授,但在实践上,君王及其代理人垄断神意,神意的解释很大程度上服务于君王的意志,因此,君权架空神意。在中国语境中,则是君权架空天命。这意味着,无论把天命说得多么动听,它都无法有效制约君权,进而很难成为有效的终极合法性建构资源,而古代中国也就无法避免治乱循环。在经验中,如果无法对君权建立有效的制度制约,君权就成为牟宗三所言的无限制的超越者。(31)黄克剑、林少敏编:《牟宗三集》,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210页。这是世界上一切君权神授观念所衍生的君主制度的必然困境。而导致这一困境的根源,正在于君主制度的政治合法性源泉是神灵。
以印刷为抓手,盛通印刷走出了一条多元化的发展道路。未来,盛通印刷还将充分利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工业信息化技术,聚合需求、进行产能升级,提升出版综合服务能力。同时,聚焦教育行业,积极整合教育产业优质资产,延续自身的文化基因,打造教育、出版文化综合服务生态圈。让我们期待盛通印刷的未来更加壮丽多彩。
古人之所以没有产生君权架空天命的观点,除了学术原因,政治与意识形态原因也很重要。君权神授是古代不容置疑的观念。一旦得出君权架空天命,则必然会否定天命的有效性,且否定君权的合法性,进而不但否定儒家道统的根基,儒家道统的一整套理论和秩序都会崩溃,而且政治合法性也会崩溃。这是儒家学说和现实政治都绝对不容许的。所以,古人既不敢否定君权,更不敢否定天命。因此,古人根本不敢也不可能得出君权架空天命的论断,从而无法厘清天命、君权与民心的关系。其实,其他古代文明也是如此。只不过,西方现代转型率先祛魅,(3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9、79页。成为人类古代几大文明中唯一原发性否定神性和君权神授的文明。
结语 从天命到民意:政治合法性来源的转换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君权之不可制约都是严重问题,许多社会问题都由之派生。要解决该问题,仅改革技术层面的行政制度是无效的。一切具体制度在君主那里都失效。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改变政治合法性来源,而改变的唯一途径就是从天命(神意)合法性转换为民意合法性。这一转换首先在西方的现代转型中实现了,此即终极合法性的世俗化转向(另文有讨论(33)邓曦泽:《终极合法性的世俗化转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新论》,《江汉论坛》2019年第5期,第29-37页。)。现代转型有几个层面。第一,知识生产层面的科学化,即摆脱宗教教条的束缚,不为知识设定绝对真理。第二,思想层面的启蒙运动,即在理论或说辞上把合法性源泉从以神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第三,经济层面的市场化。第四,政治层面的制度改造,即逐步实现民主化、法治化。第五,社会秩序层面的平等化。第六,生活层面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允许和鼓励人们追求现世利益,人对包括物质生活在内的世俗生活的追求不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了自己。(关于这六个层面的转型,另文有论)整个现代转型被韦伯概括为“祛魅”,即神性淡出,人性凸显。在这六个层面中,第二层面的思想解放的独特意义在于:没有合法性转向,偶尔出现的一些现代性萌芽也会不稳固和持续发展,而会被传统所吞没。合法性转向是现代转型的后四个层面(除开知识生产层面)的必要条件和基础。进言之,只有使神意合法性转换为民意合法性,一切权力才可能来源于人民、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在这个意义上,合法性转向非常重要。
TheEntanglementofMandateofHeaven,MonarchicalPowerandPublicOpinion—A Study on the Concept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ncient China
Deng Xize
Abstract: Political legitimacy mean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rulers by the ruled, which is a permanent problem that every regime will face. Although both China and the West have a long hist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did not emerge until modern times, resulting in the lack of corresponding dimensions in the study of ancient Chinese political history. The basic model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the ancient world is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s, which had unique forms and its ideal states in ancient China. Among them, there are three elements: mandate of heaven, monarchical power and public opinion. Heaven is the source of power, the people is the purpose, and the king is the intermediary. This seems to be a very ideal structure of legitimacy, with heaven and the people having limited constraints on the monarchy. In reality, however, because the monarchical power monopolize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mandate of heaven, the construc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ancient China could not realize its original intention.
Keywords: political legitimacy, mandate of heaven, monarchical power, public opinion, divine right of kings
中图分类号:D092,D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9)05-0076-12
作者简介:邓曦泽(本名邓勇),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成都 61006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13FZZ00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x201101)
(责任编辑:曹玉华)
标签:合法性论文; 政治论文; 君权论文; 天命论文; 君王论文; 法律论文; 政治理论论文; 政治学史论文; 政治思想史论文; 中国政治思想史论文;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冲突与协调——以春秋战争与会盟为中心”(13FZZ006)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skqx201101)论文;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