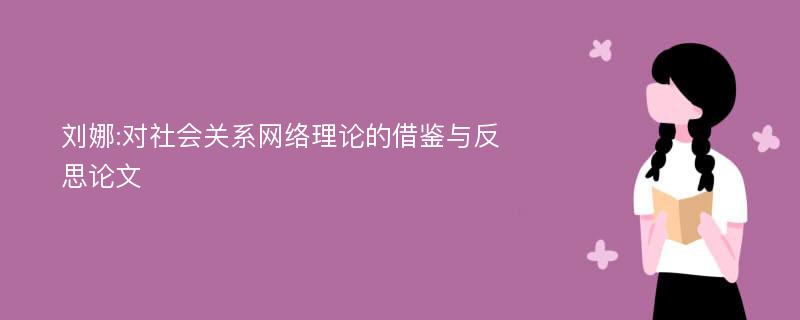
摘要:国内的社会网络研究在采借和运用西方的社会关系理论进行研究的同时,也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批判和反思。可是由于对强弱关系的界定不同,使东西方的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对话。西方学者是从多个维度去划分强弱关系的,具体包括亲密程度、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以及互惠交换等部分。而中国学者则更多的是以亲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来划分的,强调的是关系所承载的义务和责任的差异。那么如何使中国的关系网络研究能够接续到西方研究的谱系上?有学者尝试将西方的弱关系概念与具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关系”概念嫁接起来,从动态的角度解析关系的变化过程与资源动员的关系。这与专注于分析网络差异性的西方研究相比,无疑是一大进步。
关键词:社会网络;强关系;弱关系;“关系”
一、导论
国外社会关系网络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格兰诺维特提出弱关系理论以来不断发展,形成了以怀特的市场网络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博特的结构洞理论等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除此之外,验证上述理论的经验研究也在不同国家和地区迅速展开,形成了多学科研究关系网络的热潮。国内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借鉴国外的理论成果,对中国的社会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在采借和运用西方理论的基础上,也对其进行了批判与反思。本文将分别介绍中国的社会关系研究在这两个方面所取得的进展。
档案工作是单位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单位领导组织和决策提供基本保障,应受到单位领导的高度重视。如何使单位领导对档案管理重视起来,成为当前的一个普遍问题。
二、西方社会关系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虽然关于社会网络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早期的一些学者(如齐美尔以及布劳、邓肯等),但是真正使社会关系网络研究成为一门显学的是格兰诺维特。1973年格兰诺维特在对波士顿的白领群体进行求职研究时首次就“弱关系力量”的概念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具体以四个指标维度为依据来划分强弱关系。强关系指比较亲密的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弱关系指比较松散的关系或泛泛之交。他发现相较强关系而言,由于弱关系能够跨越不同群体起到关系桥的作用,所以在促进信息和资源流动方面更有效率。强关系则由于社交圈重叠,导致冗余信息较多,很难起到关系桥的作用[1]。
例如,在教学北师大版三年级数学“两位数乘两位数”时,我先让学生对整十的两位数进行计算,然后让学生在课后探究学校马上进行的“队列表演”这一活动,让学生再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探究数学问题,让学生用点子图或者列表的形式探究两位数乘两位数的横式笔算的过程与方法。学生通过课后探究,把课堂的数学学习经验和生活中实践经验相互融合,产生了新的思维和学习方法。学生对数学的学习逐渐产生真实感,学到的数学知识也就有生活价值和意义。
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理论甫一提出就引起了很多关注,有关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很多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来解释“弱关系何以会有力量”。如博特、林南分别提出了结构洞理论和社会资源理论,从关系网络位置和网络构成的角度对弱关系进行了解析,认为弱关系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跨越了连接不同群体的结构洞[2],并且能接连到优势地位的关系人[3]。但是针对不同群体以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研究表明,弱关系理论似乎只适用于西方社会经济地位相对较高的白领群体,对女性群体、弱势群体以及其他地区并不适用。对后者而言,强关系似乎更有优势。如边燕杰和臧小伟在天津和中山市的求职研究都发现,职业流动的实现,更可能是依靠强关系,具体体现在直接联系人和间接联系人之间[4-5]。有日本、台湾和新加坡的学者在调查求职研究时也发现了这一特性。这说明在重视人情关系的儒文化社会里,强关系比弱关系更加重要。因为强关系不但能够传递信息,更可以施加影响力以促进目标达成,所以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比通过弱关系找到的工作通常更加满意、收入也更高。对女性群体和弱势群体亦然。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一般由亲属和邻居组成,这种社会网络的范围不大、且呈现出密集、同质性的特点,因此很难建立起能带来更好资源的弱关系。尤其弱势群体,由于经济压迫,再加上多种困难的阻碍,他们反而能够建立起团结紧密,且功能强大的强关系。
但是上述研究并不是对弱关系理论的简单否定,弱关系与强关系同等重要,只不过他们对不同群体发挥着不同作用而已。对强关系重要性的强调并不是否认弱关系的作用,但在具体研究时的确应该考量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差异,同时注意区分不同群体的网络构成。国内学者们在进行社会关系研究时,大多采取糅合二者的视角,兼顾强关系与弱关系的作用。而且在应用强-弱关系理论进行实证研究的同时,也在理论上对其在中国的适用性进行了反思。
三、对强-弱关系理论的检验和运用
注意到上述解答中的“”.原来,F是线段OB′的中点,或者说,同时,发现第(2)小题潜在结论“DE∥CA”与求解第(3)小题没有关系,第(3)小题中的隐含等量关系仅在时成立.换句话说,当且仅当时,与DE∥CA同时成立.这引起了笔者的兴趣:若隐去平面直角坐标系这一背景,仅在矩形条件下,与DE∥CA有什么关系?能否互成因果关系?经过思考,得到如下命题:
李林艳认为,关系取向的社会离不开社会成员之间的帮助与合作,这说明与强关系文化相比,弱关系文化的生成与发展更加简单。她将中国式“关系”阐释为由弱关系向强关系转化的一种文化实践。所谓弱关系强化,是指在克服弱关系弱势的同时,充分发挥其强势之处,用以增强关系人的帮助意愿。从这个角度讲,“关系”可以是人有意识建立起来的,主要用于动员和维系弱关系,这已然成为一种文化传统。关系是一种回应,其能够对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并对社会情境加以重新界定,由于社会情境的非决定性,人们利用关系可以使其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我们可以将关系看作是一门艺术,“关系”由“冷”变“热”甚至变“熟”,从而有效解决“弱关系难题”。其中“弱关系难题”指的是弱关系中带有人们想要获取的资源,但关系人并没有帮助意愿,从而使得人们无法获得其所需资源。但是弱关系的强化旨在功能性地满足个体生存和发展方面的需要,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其目的是增强关系人的帮助意愿,而不是把弱关系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强关系。
关系的这种动态性特征也引起了其他学者的关注。有学者主张社会网络研究应超越关系分析的强-弱维度,将关系放到实践的文化脉络中去。李继宏认为:关系具有历时性、主体间性和不对称性的特点,关系的强度需要与向度结合在一起。关系是一种具体的过程,指的是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关系主体之间发生的信息和资源流通。可见关系有赖于具体事件而存在,两者相互联系,这是被分析和理解的重要前提[9]。更激进的观点则认为介于中国与西方社会的巨大差异,强弱关系概念在理解中国社会时其解释力是有限的。有学者认为社会上的个体都是独立的,因此可以格氏划分强弱关系,但这种假设并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关系构成的前提。对中国人来说,即便是没有交往的两个人,只要他们之间存在天然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便能够保证一种亲密和信任关系,体现了这种关系的义务性和复制性,所以强-弱关系理论在中国并不适用[10]。
上述研究表明学术界对强-弱关系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很大分歧。那么是否强-弱关系概念真的不适用于中国社会呢?有学者从蕴含着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关系”的角度出发,尝试将强-弱关系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关系”概念嫁接起来。将强关系对应于家庭和家族关系,将弱关系对应于中国话语中的“关系”。对此李林艳有过详细论述。她把中国社会的关系区分为两个不同范畴:一是对成员资格和地位有着明确界定的家族群体,其内部关系主要依靠家庭伦理调节,这是一种强关系文化。二是具有伸缩性的关系,是指人们在礼尚往来和互帮互助过程中所产生的,属于弱关系文化。她认为西方的弱关系概念对于认识中国社会的“关系”具有特殊的意义。家族群体由于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和内部群体压力,关系各方间的不对称交换可能在很长的时间内延续。而“关系”没有人情的往来就不可能继续下去,其建立和终止有更大的个人自由。由于没有强制性规范和内部群体压力,个体自主性及其主观能动性都是“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也正是中国社会的活力来源[13]。
四、对强-弱关系理论的阐释与发展:与“关系”概念的嫁接
介于这种情况,部分学者在研究时就抛弃了强弱关系的划分,转而采用中国传统的亲缘、地缘和业缘关系来分析问题。这种划分实际上是继承了费孝通先生关于中国乡土社会的分析概念,也即著名的差序格局概念的派生。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研究表明,虽然人们的网络伴随着一定的现代性扩张,业缘关系的重要性上升,但亲属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关系,尤其在财务支持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1]。不过城乡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农村居民在寻求社会支持时更倾向于使用血缘和亲缘关系,而城市居民则更倾向于使用业缘关系。但在社会支持内容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则表现出相同的趋势:情感性支持更偏向于夫妻邻里关系,而工具性支持则偏向于血缘、业缘关系[12]。
社会关系研究在中国兴起后,有不少学者采借西方的强-弱关系理论来研究相关问题。例如赵延东在对武汉下岗职工再就业进行研究时发现,在劳动力市场逐渐完善的背景下,强关系在下岗职工的求职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弱关系只是起到了提供信息的作用,但是由于该群体的关系网络质量不高,他们所获得的工作收入总体而言比较低。这与对其他弱势群体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比如对农民工的诸多求职研究皆发现,他们的社会交往和社会支持都是强关系[6]。在他们借助强关系的力量进城之后,为了更好的适应城市生活,他们会利用弱关系来获得信息和资源。还有学者将强-弱关系理论扩展到企业研究。针对企业行为的研究表明,强弱关系均是企业成长可以依赖的重要关系类型,但是强弱关系的重要性受到企业的结构因素和组织因素的影响。由于企业的规模不同,其产业类型和所有制结构也存在差异,这说明他们对于外界的依赖程度也有所不同,企业对重要资源的拥有和控制程度有强有弱,因此在关西使用方面也有区别。当企业的产业类型和所有制结构固定不变时,企业发展至不同阶段会展现出对强、弱关系的不同依赖程度。如规模小的企业通常会选择强关系加以利用,而大规模企业经过不断发展,其关系网络随之扩大,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关系强度是呈现减弱态势的,此时他们更加倾向于利用弱关系[7]。
可是何为强关系?何为弱关系?国内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学者把亲属关系定义为强关系,把朋友和熟人定义为强关系。有的学者则把亲属关系和老乡关系定义为强关系,把在城市中新发展出来的关系定义为弱关系。划分标准的差异不仅导致研究结论的模糊不清,也使中国的社会关系研究无法与西方接轨。这种概念对标的困难使部分学者开始质疑脱胎于西方的强-弱关系理论是否能应用到中国的社会现实。如刘林平以深圳“平江村”为案例,就城市移民关系网络的运作模式进行了深入探究[8]。他认为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动态的,会不断的发展变化。假设从过去和现在两个角度来定义关系的变化,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关系组合:无-弱、无-强、弱-弱、弱-强、强-弱和强-强。其中弱关系的关系组合包括:过去没有关系但后期形成弱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弱关系;而强关系则包括:过去无关系但后期形成了强关系、过去和现在都是强关系的关系组合。由此我们可以将社会关系大致分为四类,分别是:强关系、弱关系、强弱关系以及弱强关系。
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体育慈善公益事业为目的的社会性组织,按照《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1]。体育基金会作为基金会中的一种,主要按照《章程》中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体育公益活动,在体育慈善领域发展体育公益事业。
在中国,弱关系并不会受到强关系群体的排斥,这是其力量的延伸,强关系群体会努力吸纳弱关系,并促进弱关系发展,进而将弱关系纳入到群体内部,有助于构建更加庞大的强关系群体。强关系群体在社会中的不断延伸,能够有效增强关系群体的适应力,中国社会的分层机制是由“关系”所构成的,关系是不同家庭单位之间交流与沟通的重要渠道,家庭与其外部成员在喝过中实现资源互换,使得家族和家庭基础上的社会结构得以分化。
上述研究思路对理解中国式关系的生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可是是否家庭或家族关系都是强关系,而家族外关系都是弱关系呢?很显然,学者们对此有很大分歧,在具体研究时对强弱关系的划分标准也不尽相同。李林艳把家庭关系看作是强关系的典型,因为这种关系主要依靠强制性的权利和义务规范来治理,可以满足个体意义、归属和稳定性方面的需要。而弱关系是在自愿的基础上结成的,因此功利性的成分大大增加。这与格兰诺维特对强弱关系的界定明显不同。格兰诺维特划分强弱关系的四个维度是跨越家庭界限的,以交往双方的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和互惠交换程度来划分,家族成员有可能属于强关系也有可能属于弱关系。他关注的重点是影响信息和资源流动的关系类型。而李林艳则是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划分标准,侧重的是亲属关系的刚性和家族外“关系”的弹性,关注的主要是如何运用“关系”获取资源的实践行动,因而是针对两个不同问题的研究。但是李林艳借助弱关系理论对“关系”生成过程的阐释极大地丰富了“关系”研究,从而使本土化的“关系”概念与西方的社会关系理论深度融合起来。
五、结论
西方的社会关系网络理论介绍到中国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关注。相关研究大量涌现。学者们对源于西方的强-弱关系理论进行了检验,发现在中国社会强关系确实比弱关系更加重要。可是由于对强弱关系的界定不同,使东西方研究并不能很好地对话。以格兰诺维特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在划分强弱关系时,主要以互动频率、感情强度、亲密程度以及互惠交换四个维度为依据,而中国学者则更多的是以亲缘关系和非亲缘关系来划分的,强调的是关系所承载的义务和责任的差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西方的社会关系理论不适用于中国呢?在对强-弱关系理论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学者们试图将之与中国的“关系”概念嫁接起来,赋予“关系”以个体自主性和能动性的内涵,从动态的角度解析关系的强化过程与资源动员的关系。这相对于专注于分析网络差异性的西方社会关系研究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这一分析视角不仅丰富了国内的社会关系网络研究,也使本土化的“关系”概念接续上了西方的社会关系研究谱系。
参考文献:
[1]Granovetter,M.,Getting a Job-A Study of Contacts and Career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2]Burt,R.S.,Structural Holes: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3]Lin,N.Social Capital:A Theory of Structure and Action,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4]Bian,Y.,“Bringing Strong Ties Back In:Indirect Connection,Bridges,and Job Search in China,”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2 (1997),pp.266-285.
[5]Zang,X.,“Networks Resources and Job Search in Urban China,”Journal of Sociology,Vol.39,No.2 (2003),pp.115-129.
[6]李汉林,王琦.关系强度作为一种社区组织方式——农民工研究的一种视角: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
[7]姚小涛,张田,席酉民.强关系与弱关系:企业成长的社会关系依赖研究[J].管理科学学报,2008 (2).
[8]刘林平.外来人群体中的关系运用——以深圳“平江村”为个案[J].中国社会科学,2001 (5).
[9]李继宏.强弱之外关系概念的再思考[J].社会学研究,2003 (3).
[10]翟学伟.社会流动与关系信任——也论关系强度与农民工的求职策略[J].社会学研究,2003 (1).
[11]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J].社会学研究,1999 (2).
[12]蔡禾,叶保强,邝子文,卓惠兴.城市居民和郊区农村居民寻求社会支援的社会关系意向比较[J].社会学研究,1997 (6).
[13]李林艳.弱关系的弱势及其转化“关系”的一种文化阐释路径[J].社会,2008 (4).
作者简介:刘娜(1971-),女,汉族,山东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任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关系与社会资本等。
标签:关系论文; 社会关系论文; 理论论文; 中国论文; 社会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传播力研究》2019年第13期论文;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