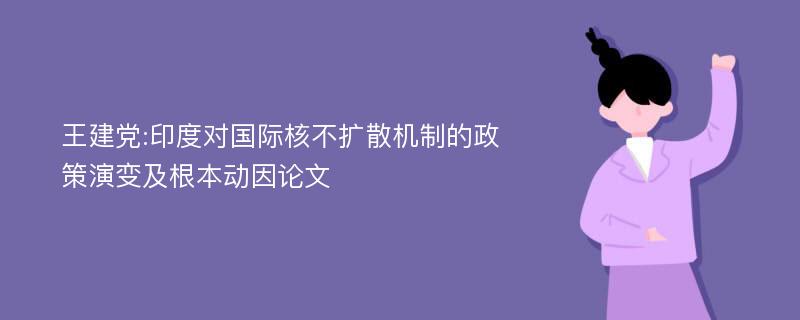
【摘要】印度在1998年公开核试验后成为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但至今未被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接纳为合法的核武器国,长期游离在核不扩散机制之外,造成其尴尬的处境。考察印度关于核不扩散政策的历史,不难发现其政策演变的轨迹。究其原因,是其大国地位追求、战略文化,以及国际身份定位等深层次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印度;核不扩散;政策演变;动因
一、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演变
受不同时期国际国内政治的影响,印度对核不扩散问题的政策随之发生变化,总体上,经历了积极支持核不扩散机制的创设,到逃避甚至脱离机制对其束缚,再到重新接触并寻求融入机制的过程。
(一)尼赫鲁时期,积极支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创设
印度独立后的国际社会处于冷战初期,美、苏核竞赛逐步展开。出于核垄断的考虑,产生了个别主要由美、苏主导的防核扩散计划。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主导的政府工作重心在于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工业化建设,加之甘地非暴力和平思想的影响,印度奉行和平的核政策,积极支持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创设。
一是参与美国“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随着苏联、英国先后成功试爆原子弹,美国的核垄断被打破,核扩散问题变得日益突出。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2月8日提出了“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目的是通过向非核武器国家提供有限的核技术用于和平目的,以换取其不开发核武器,并削减苏联或其他国家获得足够的裂变物资对美国发动致命袭击。[1]对此,苏联有针对性地向其盟国提供原子能援助,并拟扩大受援国范围。印度因此成为美、苏争取援助的对象。印度参加了美国的计划,获得了包括重水反应堆、资金、人才培养等支持,为其核能工业的发展乃至1974年第一枚核装置爆炸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支持并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尼赫鲁早在1954年就首次呼吁美、苏达成“立即停止”核试验的协议。但当时美、苏正在加紧进行核竞赛,因此遭到故意破坏。[2]古巴导弹危机使美、苏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性,并就核武器扩散的危害达成共识,于1963年7月15日开始了禁止核试验谈判。1963年8月5日,美、英、苏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并于8月8日对其他国家开放签字,印度当天便签署了条约。
三是支持成立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原子能机构是在美、苏等核大国努力防止核扩散,维护核垄断地位的背景下成立的。尼赫鲁政府对该机构的成立表现积极。早在1948年的联合国大会会议上,印度等国就提出成立原子能委员会,以控制原子能,促进和平利用核能,阻止各国用核武器装备自己。[3]1954年12月,第9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成立一个专门致力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际机构。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57年10月正式成立,印度是该机构的初始成员国之一。
(二)核开发时期,由拒不加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到完全对立
尼赫鲁1964年去世以后,由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印度国内要求发展核武器的声音开始高涨,并逐步走上了核选择的道路,最终于1998年突破“核门槛”,公开进行核试验并宣布成为核武器国家。在此期间,印度最初拒不加入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为基石的不扩散机制,逃避机制的约束,最后公开核武化,公然挑衅机制的权威性。
在婚姻的过程中,得到婚姻滋养的岸田俊子得出“男女互相怜爱”之相处之道;而秋瑾由于经济问题,留学艰辛而更加坚定经济的重要作用,更加坚信女子只能靠自己。
El Nio事件与中国降水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气候学研究热点,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春季/夏季型El Nio事件与中国夏季降水之间的关系上,通过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早在印度独立之前就对其未来的国际地位进行过明确的阐述:“印度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吸引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是可能的。”[8]这种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对印度对外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中包括对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
(三)核试验之后,积极寻求融入国际核不扩散机制
1998年公开核试验后,印度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以及美国等核大国更严厉的制裁。为此,印度开始调整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态度,通过积极的核外交,寻求与其中一些并非完全主张消除核武器的机制妥协,谋求加入有利于其核能力与核技术发展的防扩散协议,并获得国际社会对其核国家地位的承认。
内分泌与泌尿外科特色资源数据库,是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围绕本校国家重点学科网络平台建设的系列特色数据库之一,其发布方式较“肿瘤特色库”与“乳腺癌特色库”的纯本地化发布模式外,又增加了天津市数据管理中心统一发布模式,实现了以数管中心发布为主、本地发布为辅的双保险模式。即数管中心出现网络、服务器瘫痪等问题时,可直接切换至本地发布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稳定性,提升了用户的体验。
一是对机制内条约的态度发生积极转变。公开核试验后,印度第一时间表达了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积极态度。1998年5月27日,印度对外宣布,“将自愿停止并克制实施地下核爆炸试验”。[5]此后,印度一直对条约持积极态度,多次表示支持条约早日生效,并单方面遵守条约义务,暂停了核试验。此外,印度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态度出现了微妙变化。2000年5月9日,印度外长贾斯万特·辛格在议会表示:“虽然印度不是条约的成员,但印度的政策一贯符合该条约对有核国家的规定。”[6]表明其对该条约的抵制态度不再那么强烈。2009年11月,辛格总理表示,如果以核武器国家身份得到邀请,印度愿意加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7]这是印度政府首脑首次表达加入该条约的愿望,显示出对条约的立场出现了缓和迹象。
二是拒绝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美国失去了核军备竞赛对手,而且国际上出现一些接近掌握核武器技术的“核门槛”国家。为防止核武器进一步扩散,危及自身安全,美国于1993年开始推动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谈判。在各方谈判达成条约草案后,印度认为草案带有强制其批准的性质,有损其行使主权,因此拒绝签署。印度代表阿兰达蒂·高斯在谈判期间表示,“《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是为了再次确定“核隔离”制度的永久化而起草的”。[4]
随着公开核试验以及由此招致的国际社会的指责和制裁,印度意识到必须要正面这一问题,开始主动开展核外交,积极与核不扩散机制接触,并寻求融入其中。这样,印度不仅能从中获得与核材料、核技术等相关的交易带来的好处,而且有利于最终得到国际社会对其核武器国家身份的认可,进而提高其国际威望,助力其大国地位诉求。这是印度现实主义思想的又一明确体现。
ABC分类法是目前最常用的库存管理方法之一。ABC分类法又称主次因素分析法或“帕累托”现象。这种方法简单易行,在库存管理中应用广泛。ABC分类法的基本原理是将库存物资按品种和占用资金的多少分为特别重要的库存(A类)、一般重要的库存(B类)和不重要的库存(C类)三个等级,然后针对不同重要等级分别进行管理和控制[2]。该方法的核心是“分清主次,抓住重点”,针对企业库存中占用大量资金的少数生鲜农产品,需要进一步加强库存管理和控制;而企业库存中占用少量资金的大多数生鲜农产品,可进行相对较为宽松的库存管理与控制。
一是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抵制其延长。196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不扩散核武器条约》,1970年正式生效。条约规定只有在1967年1月1日前进行过核试验的国家才是核武器国家。印度认为,该条约是核武器国家的垄断机制,旨在阻止其他国家获得核武器或者发展核武器能力,因此以“歧视性”为由拒绝签署。1995年条约到期后,美国大力推动无限期延长,对此,印度态度消极,并且试图阻挠。但最终,条约得到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并得以无限期延长。
三是开展与大国的核能合作。当前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核大国主导之下建立的,在不少方面仍然体现着核大国的意志。印度要改善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并加入其中,必须首先改善与美国等核大国的关系。9·11事件后,印美关系迅速升温。2005年7月,印度总理辛格访美期间,与布什总统发表了民用核能合作联合声明。2006年3月,布什访印期间,双方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08年协议正式生效。该协议使印度摆脱了核孤立,开启了与其他国家核能合作的大门。此后,印度相继与法国、俄罗斯、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等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
二、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政策演变的根本动因
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政策转变本质上是由国家利益决定的,但在核政策与行为的背后有一系列深层次的动因,其中包括印度对实现大国梦想的不懈追求、印度战略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不同时期印度国家定位及其变化。
(一)对大国地位的追求
三是成为核供应国集团制裁对象。1974年印度进行所谓“和平核爆炸”。此次核试验直接催生了国际核出口控制机构的诞生。1975年,英国邀请其他6个主要的核供应国加拿大、美国、法国、联邦德国、日本和苏联在伦敦举行会议,就控制向《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规定的无核国家出口敏感核设备、材料及技术达成一致,通过了《核转让准则》和《触发清单》。标志着核供应国集团的成立,宗旨是加强核出口控制,印度成为该集团的首要制裁对象。
印度的战略文化受到其独特的宗教、历史、地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不仅有宗教道德色彩,更有现实主义的思想渊源。印度独立后的战略文化集中体现为尼赫鲁主义。而尼赫鲁主义的核心思想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对待武力的态度上,反对现实主义的强权政治,倾向于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在印度的国际战略定位上,强调大国抱负,视印度为国际政治中的道义力量。因此,从非暴力思想发展而来的反核伦理思想在尼赫鲁时期占据上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和平核政策充斥着强烈的道德和理想色彩;极力强调核武器的危害性、反人类性,反对发展核武器,倡议禁止核试验,主张核军控与裁军,几乎是国际社会反核扩散的旗手。
由图3可见,随着组合捕收剂用量的增加,铜精矿中的铜回收率明显提高,而其中的铜品位则不断下降。综合考虑,确定铜粗选时Z200与丁基黄药组合捕收剂的总用量为240 g/t,此时的回收率与铜品位约为6.65和72%。
无论是积极参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创建,还是脱离接触,或者重新接触,印度对该机制的政策背后都隐藏着这样一个逻辑,即不放弃开发核武器的权利,即使是在尼赫鲁时期亦是如此。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调整,是为了配合其争取世界大国地位的战略。因为印度认为,核武器是国家实力的象征,只有实力才能赢得尊重,提高国家的威望和地位。
(二)战略文化的深刻影响
尼赫鲁时期,印度奉行和平的核政策,支持国际防核扩散努力。在国内主张和平利用原子能,反对发展核武器,在国际上呼吁停止核试验,倡导核裁军。该政策使印度站在了国际道义的制高点,使其以有限的权力获得了最大的尊重和国际影响,成为第三世界国家中活跃在国际核不扩散领域的一支领导型力量。尼赫鲁去世后,印度在核不扩散问题上的政策出现大的调整,尤其是在是否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问题上,背离了国际社会的主流,逐渐脱离了核不扩散机制。在1974年“和平核爆炸”后成为后者制裁的对象。冷战结束后,南亚次大陆美苏对峙的局面改变,印度迫切地想谋求在南亚的主导地位,更想充当世界大国,印度把拥有核武器看成一个大国的标志,想通过拥有核武器来增加它谋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筹码。[9]1998年核试验后,印度成为世界上第六个公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使其在追求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更加自信。但印度开发核武器的行为使其被排斥在核不扩散机制之外,而该机制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如果印度不加入,对其成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大国将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在该目标驱动下,印度在核试验之后开始调整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重新与其接触,并积极寻求加入其中的一些防扩散机制。
尼赫鲁去世后,尼赫鲁主义的主导地位开始动摇,尤其是1968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开放签署,使尼赫鲁时期坚持的理想主义难以为继,必须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做出现实的选择。1971年印度与苏联签署准军事同盟性质的《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实际上脱离了尼赫鲁外交思想的核心不结盟政策。现实主义在印度政治决策中的影响逐步上升,主要表现在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反对其无限期延长、1974年进行“和平核爆炸”、拒签《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最终,随着人民党登上执政舞台,现实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于1998年进行了核试验,给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以沉重打击。
二是寻求加入防核扩散多边出口控制机制。核不扩散出口控制机制主要有四个,即核供应国集团、澳大利亚集团、瓦森纳协议,以及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印度曾坚决抵制,但在完成核试验后,对其态度发生了转变,逐步转向积极接触,争取加入。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度先后于2016年加入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2017年加入瓦森纳安排,2018年加入澳大利亚集团。当前正在积极寻求加入核供应国集团,而且其在2008年就已获得该集团对其核贸易的豁免。
(三)印度对国家身份的界定及其变化
国家身份是指一个国家相对于国际社会的角色,是基于国际社会承认之上的国家形象与特征的自我设定,它是随着国家间互动样式的变化而变化的。[10]因此,特定时期的国家身份界定了一定时期和条件下的国家利益,国家利益决定了国家的外交政策和行为。独立初期,不论从政治、经济、军事,还是文化影响而言,印度都不具备大国的条件。但是,尼赫鲁对印度的未来抱有很高期望,对其当时的身份定位超出了其实际能力,认为印度是美苏两大阵营之外领导世界的第三种力量。正是基于这一身份定位,在核不扩散问题上,印度代表第三世界无核国家向核大国发起挑战,提出停止核试验,进行核军控以及彻底核裁军等主张。
李清照的经历,本身就足够跌宕起伏、命途多舛了,加之她以词话人生,使她成为了别具一格的女词人。《李清照集笺注》将易安的词编年排序,笺注中说明了创作时间和背景,可以说,我们能够从易安的词中窥探到她的一生。
1970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生效,标志着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正式形成。鉴于印度独立于两大集团,反对由此确立的国际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印度的利益界定,印度不愿意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安排,认为该机制具有“歧视性”,损害了印度独立自主的权利,排斥核不扩散机制。1974年核试验后,印度与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成为后者制裁的对象。
在丰富多彩的数学教学活动中,如果教师能把进行法制教育的方法、时机掌握恰当,运用灵活,对提高学生的思想觉悟、抵制心灵污染,定会收到良好的效果。数学教材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育人因素,其中“综合与实践”板块,既能帮助学生回顾某一单元的知识网络,又能综合检测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我们也可结合切入点对学生渗透法治教育。例如,在教学“绘制校园平面图”时,学生通过测量、计算,最终绘制出校园平面图,不仅掌握了相关知识,提高了动手能力,还可渗透《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条例法》。在教学年月日,让学生绘制年历表时,对学生渗透《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冷战结束后,世界两极格局被打破,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带来的国力的提升,印度对自我身份进行重新定位,第三世界领导者角色有所淡化,更加强调“崛起中的大国”。[11]这一身份定位意味着印度要获得更广泛的国际尊重及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尤其是美国。但印度并未得到期望的结果,相反,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核扩散危险的担心,强化核不扩散机制,对印度施压,使其面临防扩散的巨大压力。印度自我身份定位与国际社会对其身份认知这一矛盾造就了印度作为现行国际机制挑战者的身份。
公开核试验之后,印度宣布为核武器国家。印度对其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及崛起中的大国这一身份定位促使其开始寻求国际社会对其合法核武器国家身份的认可,而改善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是关键一环。为此,印度再次调整对该机制的政策,改变之前强硬的立场,适当做出妥协。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调整使其对印度的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率先认同了印度的身份定位,并与其开展民用核能合作,打破了核不扩散机制对印度的孤立。
三、结语
不可否认,任何一项大的政策都是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有些因素的影响是有限、短暂的,只有那些深层次的因素其影响才是根本性的、长期的。从尼赫鲁时期开始,印度就将大国地位作为其追求的目标,不论政党政治如何变迁,这一目标始终未变,至今依然如此,深刻影响着印度的外交。在国际核不扩散问题上,凡是有助于提升印度的国际威望和地位,印度就支持,否则就抵制。而且为了提升国家地位,印度冲破国际机制的制裁,成为核扩散的典型。印度的战略文化中既有理想主义,又有现实主义色彩,贯穿在印度对国际核不扩散机制政策的始终。如果说早期印度对该机制的政策更具理想主义色彩,那么从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更多地折射出现实主义色彩。另外,印度在不同时期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定位以及国际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同,共同塑造了印度对核不扩散机制的政策。目前,其自我身份定位与国际认可已经达到了较高的程度,这也是为何印度近年来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的关系取得重要进展的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子奎:核扩散问题与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平利用原子能计划[J].世界历史,2016(5):89.
[2]N.D.Jayaprakash.Nuclear Disarmament and India[J].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2000, 35(7):526.
[3]赵伟明等:中东核扩散与国际核不扩散机制研究[M].时事出版社,2012:101.
[4]George Perkovich.Indian's Nuclear Bomb: The Impact on Global Proliferation[M].1.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79.
[5]Public Information Bureau.Evolution Of India’s Nuclear Policy[EB/OL].1998[2019-04-28].http://pib.nic.in/focus/foyr98/fo0598/Foc2705982.html.
[6]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s.Response by India to President Bush’s Speech on Missile Defense[EB/OL].2001[2019-04-28].http://www.meadev.nic.in/news/official/20010502official.htm.
[7]A.VinodKumar.Reforming the NPT to Include India[EB/OL].2010[2019-04-28].https://thebulletin.org/2010/05/reforming-the-npt-to-include-india/.
[8]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中译本)[M].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57.
[9]袁正清:印度核试验及其影响[J].成人教育学报,1998(5):16.
[10]孙溯源:集体认同与国际政治——一种文化视角[J].现代国际关系,2003(3):41.
[11]刘思伟:建构主义视角下的印度与国际核机制的关系[J].南亚研究,2013(4):86.
作者简介:1.王建党(1984.06-),男,汉族,甘肃兰州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南亚问题、大国关系;2.李晨(1987.10-),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方向:军事战略。
责任编辑/周洁
标签:印度论文; 核武器论文; 机制论文; 核试验论文; 条约论文; 政治论文; 法律论文; 外交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 《南方论刊》2019年第10期论文; 国防科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