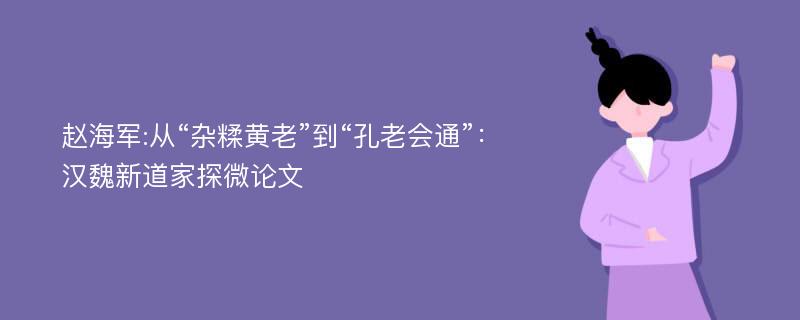
[摘 要]汉初的黄老之学和后继的魏晋玄学,在哲学基本精神上都服膺于“道法自然”,和老庄道家哲学一脉相承。从学术内涵来看,二者又都不是纯粹的道家。黄老之学是以道家思想为贯通、充分杂糅儒、墨、法、名等诸家之长的杂糅之学。魏晋玄学则是适应特定时代需求而从儒、道思想中汲取资源建立起来的一个儒道会通的哲学体系。作为新道家的黄老之学与魏晋玄学,都是道家思想顺应时代变化发展的产物,二者在与同时期的各种思想相激相荡中,内涵也不断丰富。
[关键词]新道家;黄老之学;魏晋玄学
“新道家”这一名词是20世纪40年代冯友兰先生首先提出,到20世纪80年代由余英时和熊铁基等著名学者进一步细化,就有了魏晋新道家和秦汉新道家的区分。由于陈寅恪先生等前辈学者很早就对魏晋玄学中的道家思想发表了权威的研究成果[1](p16),因此学界对于魏晋新道家这一称谓更为认可,研究成果更为丰富,主要集中于魏晋玄学对于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方面①高晨阳在《玄学的本质及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载于《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玄学不是以儒家思想去统摄道家,而是以道家思想去融解儒家;就玄学与道家的基本精神相通一面看,玄学就是道家,但就其会通儒道两家之学的一面看,实与道家对儒家思想的否定倾向不合,表现为理论的转向。梁辉成、路旭斌的《玄之又玄:由先秦到隋唐道家哲学发展的曲折历程》(载于《文艺评论》,2015年第12期)一文则认为,玄学家们以老庄思想为依托,目的是利用“自然”来挽救“名教”,因而魏晋玄学虽然在客观上丰富了老庄哲学,但在具体思想上与老庄所代表的先秦道家思想是偏离的。。相比较而言,对于秦汉新道家的研究成果则相对较少,目前所见仅有熊铁基先生的系列论文②此系列论文的核心为发表于《文史哲》1981年第2期的《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兼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一文。及由这些论文结集而成的《秦汉新道家略论稿》一书,主要是论述秦汉新道家的渊源流变、思想特点及其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与此相关,将秦汉新道家和魏晋新道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成果则更为罕见,笔者目力所及仅见王晓毅先生的《黄老复兴与魏晋玄学的诞生》(《东岳论丛》1994年第5期)一文③该文指出,道家学说是汉魏之际最具活力的思想因子,居于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变的主导地位,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流派就是黄老之学,它打着“复兴黄老”的旗帜,将早期道教、汉末的社会批判思潮和曹魏初年的形名法术糅为一体,重点发展了形名学和养生术两个方面,最终发展成为早期玄学的贵无派。。基于此,笔者拟以哲学基本精神和思想内涵为关注点,对秦汉新道家和魏晋新道家进行比较研究,以厘清汉魏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演变轨迹。
一、汉魏新道家释义
(一)“汉魏新道家”概念的提出
1947年,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时,在梳理道家演进脉络的基础上,对道家的发展阶段进行了划分,并重新命名了道家的流派,其中将魏晋玄学称为“新道家”。他指出:“‘新道家’是一个新名词,指的是公元三、四世纪的‘玄学’。……‘玄学’这个名称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2](p253)就笔者目力所及,这是“新道家”这一名称的首次出现。不过,在冯先生看来,中国古代哲学的时代思潮中只有魏晋玄学符合“新道家”的标准,故而并未明确提及“魏晋新道家”。到1980年,余英时先生在其《个体主义与魏晋新道家运动》一文中明确了“魏晋新道家”的说法,“2世纪政治的清议让位于哲学的清谈,儒家经学向新道家玄学的转变由此实现”[3](p32)。
在余英时先生正式提出“魏晋新道家”这一概念的次年,即1981年,熊铁基先生提出了有关“新道家”的另一种观点。他认为秦汉时期《文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著作中所体现的黄老之学仍属于道家范畴,不过已经迥异于老庄道家,因此应该称为“秦汉新道家”[4](p70)。这种指向跟宋人欧阳守道“太史公特标黄老之学为道家”[5](p585)的观点一致。与熊氏不同,向燕南在1987年撰文将《文子》《吕氏春秋》等视为“战国末期新道家”的代表作,认为道家到战国中后期开始沿着消极避世和积极入世两个向度分途发展,经“稷下黄老”诸子培育而逐渐形成的积极入世的一派就是“战国末期新道家”[6](p10)。虽然熊氏与向氏所论及的时代不同,一个是秦汉时期,一个是战国末期,但二者却都将“新道家”指向了黄老之学,且都将《文子》和《吕氏春秋》作为立论依据。虑及《文子》和《吕氏春秋》的成书年代均为战国末期至秦初,二者在内容上与成书于西汉中期的《淮南子》有着十分明显的因袭关系,加之作为“黄”“老”合称的“黄老”一词在西汉初年才出现,所以战国末期虽已有黄帝之学与老子之学的结合,但充其量只能是“汉初提出‘黄老’这个名称的思想源头”[7](p6)。基于此,笔者以为向氏之“战国末期新道家”亦应作为“秦汉新道家”之雏形而列入其发展序列。
(二)汉魏新道家的内涵:“道法自然”的基本精神
既然名为“新道家”,说明无论黄老之学还是魏晋玄学均属于道家的范畴,都对先秦老庄之学即原始道家的学术思想有所继承。
玄学的代表著作为“三玄”,即《老子》《庄子》和《周易》。其中《周易》以其“文本蕴含的独特的宇宙观以及深沉的道德内涵”“在产生之后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之中,被儒道思想共同视作最基本的经典,启发着人们对宇宙自然的思考”[8](p50)。而且,玄学还对另一部儒家经典《论语》进行注解。黄老之学的代表著作除了前述的《文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三部之外,尚有郭店楚简《太一生水》、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上博楚简《恒先》《三德》《凡物流形》三篇和《鹖冠子》等。尤其是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被唐兰先生视为汉初黄老之学的核心和研究汉初黄老思想的宝贵资料[9](p48)。仅就代表著作,尤其是黄老之学这些思想上包罗万象的著作而言,似乎很难将玄学和黄老之学视为道家。但正如冯友兰先生将玄学称为新道家的原因在于,玄学关注的“有无关系”这一主题能揭示其跟老庄哲学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判断玄学和黄老之学是否属于道家的关键就在于,它们的学术思想是否符合老庄道家哲学,是否跟老庄哲学的基本精神相通。
王弼所提出的“崇本以息末”虽然为自然与名教的会通指明了大方向,但却并未涉及如何落实的问题。对此,玄学中用“本”和“巧”两个词来概括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即名教不能仅注重形而下的政治实践和道德践行,还要重视形而上的本体即宇宙之终极根源,因此要以自然为本。何晏、王弼所强调的“贵无论”,即是以道家的“自然”和“无”为名教提供了一个形而上的依据。自然不能“蔽于天而不知人”,要注重对人事的追求,尤其是在社会价值、人生理想等方面以名教为标准,因此需以名教为巧。
一段视频记录了他们刚到加州的生活。邹市明拎着一个巨大的训练包,深深的呼着气:“这是职业拳击的空气,我来了。”
老子讲“道法自然”,提出了“自然”的概念,庄子则提出了“天籁”的概念,并将其释为表示万物自然而然的“咸其自取”[12](p16)。显然,庄子的“天籁”实与老子的“自然”相通,体现的也是一种崇尚自然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庄道家哲学均将自然视为天地万物运行变化的规律,主张要顺应自然,而这也正是五千言的《老子》和数十万言的《庄子》所讲的核心内容。
黄老之学虽然思想体系庞大,内容包罗万象,但都是离不开老庄道家哲学“道法自然”的基本精神:一方面,黄老之学提出了“道”“天”“命”和“自然”等概念,如《黄帝四经》中的《十大经·本伐》和《经法·论》两篇分别记有“道之行也,繇不得已”[13](p308)和“必者,天之命也”[13](p130)之语。《鹖冠子·环流》云:“命者,自然者也。”[14](p22)《吕氏春秋·知分》则云:“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15](p180)这些概念其实与老庄哲学的“道”“自然”和“天籁”异曲同工,都表示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法则。另一方面,黄老之学提出了“法天地”的原则,如《吕氏春秋·情欲》载:“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也。……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15](p20)《吕氏春秋·季冬纪十二·序意》亦载:“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天吉凶也,上挨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15](p91)《文子·九守》中亦有“故圣人法天顺地,不拘于俗,不诱于人,以天为父,以地为母,阴阳为纲,四时为纪,天静以清,地定以宁,万物逆之者死,顺之者生”[16](p51)之语。这里所谓的“法天地”,其实就是根据天地运行的本来规律而规范人的行为、制定各种规范和制度的意思,跟老庄道家的“法自然”相通。
虽然体系不若黄老之学庞大,但魏晋玄学亦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和众多的学术派别,如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和以向秀、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这些理论和派别也都本于老庄哲学“道法自然”的基本精神。如著名玄学家夏侯玄就提出了“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17](p48)的命题,所谓“天地以自然运”就是说天地的运行变化有其自然、内在的原则和规律,所谓“圣人以自然用”是指圣人的生活也是依据自然的原则。显然,夏侯玄的这一命题突出的是对顺应自然之道的强调,充分体现了崇尚自然的基本精神,对于夏侯玄的这一命题,正始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解释说:“自然者,道也。”[17](p48)《晋书》载有一段著名玄学家、司徒王戎跟阮籍之子阮瞻的对话,王戎问阮瞻:“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异同?”阮瞻回答说:“将无同”[18](p1363)。对于这段对话,《世说新语·文学》中有另一个版本,内容相同,只是对话的主角则换成了王戎的堂弟、著名玄学家王衍和阮瞻的堂兄阮修。很显然,作为著名玄学家的王戎和王衍均认为老庄道家思想的核心是“明自然”,这跟“道法自然”意义完全相同,也是对老庄道家哲学基本精神的概括。
“玄学”一词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陆云“尝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寄宿,见一少年,美丰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18](p1485-1486)。其中的“共谈《老子》”和“谈老殊进”,既清楚地表明了玄学跟道家的关系,又突出了玄学的重在清谈,而“辞致深远”则突出了玄学谈资的特点——深远。这段史料中还提及了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王弼,他曾在《老子指略》中对玄学的“玄”和“深远”有过解释,“‘玄’也者,取乎幽冥之所出也;‘深’也者,取乎探颐而不可察也……‘远’也者,取乎绵邈而不可及也”[20](p196)。“探颐”一词突出了玄学的义理深奥,故曰“深”;“绵邈”一词则突出了玄学的无关乎实际、不可及,故曰“远”。由此而言,玄学实乃玄远之学。
近年来,由于草莓果酱、果酒等加工品的出现,使得草莓不仅限于鲜食,亦倾向于果品加工。草莓在温暖的天气中生长较快,因此大部分地区,都有草莓的栽培。但传统的栽培技术草莓的产量较低,尤其是北方地区,冬季的气温较低,草莓无法继续生长,若采用设施栽培等保护地的方式,草莓一直生长在适宜的环境中,能提高草莓的产量,笔者简述了丰产栽培技术,以期为草莓的丰产种植提供参考。
二、汉魏新道家的差异:“杂糅”与“会通”
既然名为“新道家”,则黄老之学和玄学除了在继承老庄道家哲学基本精神方面完全相同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在于“新”字,而这个“新”则来自道家与其他不同学派的结合。简言之,黄老之学是“杂糅黄老”,而玄学则是“孔老会通”,这从根本上体现了汉魏新道家的差异。
(一)“杂糅黄老”的黄老之学
玄学对于调整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有着明确的原则,王弼在《老子指略》中将其概括为:“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明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未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己,此其大要也。而法者尚乎齐同,而刑以检之。名者尚乎定真,而言以正之。儒者尚乎全爱,而誉以进之。墨者尚乎俭啬,而矫以立之。杂者尚乎众美,而总以行之。夫刑以检物,巧伪必生;名以定物,理恕必失;誉以进物,争尚必起;矫以立物,乖违必作;杂以行物,秽乱必生。斯皆用其子而弃其母,物失所载,未足守也。然致同途异,至合趣乖,而学者惑其所致,迷其所趣。”[20](p196)其中的“致同途异,至合趣乖”是说儒、法、墨、名诸家的目的都是要维护名教,但具体手段有所不同。“用其子而弃其母”则说明诸家在手段上都忽视了道体之源而执着于末用,即在维护名教上用力过猛,却忽视了自然无为的原则,其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根本达不到有效维护名教,尤其是其所规定的等级性秩序的目的。对此,王弼也提出了解决方法,那就是“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即顺应自然之性,从而达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的效果。不独是作为正始玄学代表人物的王弼如此,与王弼同时代的何晏,竹林玄学的嵇康、阮籍和元康玄学的郭象等人,也都关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并且强调儒道会通以达到二者的统一。
就笔者目力所及,黄老并称并不见于先秦文献,但如任继愈先生所言,“黄老之学的起源可以追溯至战国时期”[23](p95)。正是在战国时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大历史人物——作为上古传说英雄人物的黄帝和作为春秋末期道家学说代表人物的老子,被联系在一起并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当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战国时期,儒、墨、道、法逐渐成为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四大学派,儒家和墨家更是一时的“显学”[24](p725)。为了构建新的思想体系以适应新形势,各学派当时都基于各自不同的需要而对其原来持有的传统理论进行改造,其共同之处在于“托古”——都伪托黄帝的名义著书立说,于是,黄帝成了风行一时的人物。兵家将黄帝塑造成高明的军事家、骁勇善战的战神,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之说把黄帝当作中国历史的开端,法家将黄帝说成深谙权术、无为而治的君主。志在与儒、墨抗衡的道家也不例外,该学派“虽具高深的哲理,但缺乏落实到现实世界的方案”[25](p201),于是他们将黄帝视为崇尚自然的古帝王,基于从固有文化传统中吸取精华来建构现实价值和秩序的需要,依托黄帝来论道、立言,从而成为一种极具可操作性的政治思想。如作为黄老之学代表著作的《黄帝四经》,其《十大经·成法》中记述了一段黄帝跟臣下力黑的对话:“黄帝曰:‘一者一而已乎?其亦有长乎?’力黑曰:‘一者,道其本也,胡为而无长?’”[13](p291)通过这一番对话,不难看出《十大经》的作者是把建立统一王权政治的观念托于黄帝之口,并使黄帝与“道”产生联系。此外,《十大经》还把老子的“贵柔守雌”思想推原到黄帝身上。这样,原本互不相干的黄帝和老子便连到了一起。到汉初,托古之风更加盛行,“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26](p653),黄帝和老子的联系更加密切,先秦文献中均单独提及的黄帝、老子在汉初开始合称即为明证。如丁原明所言,黄老“作为一个学术名词被提出,其时间是在西汉初年”[7](p2)。
值得注意的是,《十大经·果童》中亦记述了一段黄帝与臣下果童的对话,跟《成法》异曲同工:“黄帝[问四]辅曰:‘唯余一人,兼有天下。今余欲畜而正之,均而平之,为之若何?’果童对曰:‘不险则不可平,不谌则不可正。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13](p243)另外,《十大经·立命》中载:“唯余一人,[德]乃肥(配)天,乃立王、三公。”[13](p196)这两条记载的主旨均在于强调建立统一王权政治的必要性,表明原本“蔽于天而不知人”[27](p247)的道家在跟黄帝之学结合后,政治上变得更为积极。《十大经》中尚有其他篇章对于如何得天下、守天下有所记载,如《顺道》中载,要夺取天下就必须“安徐正静,柔节先定”“卑约主柔,常后而不失(先)”[13](p326)。《姓争》载“胜(一作“姓”)生已定,敌者生争,不谌不定。凡谌之极,在刑与德。刑德皇皇,日月相望,以明其当”[13](p263-265),讲的是刑德并重的思想;《五政》载“反义逆时,其刑视之(蚩)尤。反义倍宗,其法死亡以穷”[13](p239),则是在宣扬德义并重、刑法并重的道理。显然,《十大经》这些篇章中体现出的思想“有的原属于老子道家,有的是取自儒法诸家”[7](p10),其中,取自儒法诸家的思想,实质是将“天道”的原理与作用落实到人间。尤其是法家,黄老之学对于道家和法家的糅合,还体现在《黄帝四经》所载之《老子》中“德经”是置于“道经”之前的,按照高亨等的说法,“从先秦古籍的有关记载来看,《老子》的传本在战国期间,可能已有两种……《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这当是法家的传本”[28](p2)。而“德经”在前、“道经”在后,恰恰“是黄老学派落向现实社会的表现”[13](p6)。
由此可见,黄老之学是在融贯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儒、墨、法及名等诸家之长的杂糅之学。不过这种杂糅并非“黄帝学说与老子学说的简单拼凑,而是秦汉之际的新道家假托黄帝立言、改造老子学说,并综合吸收了先秦各家学说重要内容的一种理论体系”[29](p110)。作为一种理论体系,黄老之学的内容丰富而多元。思想内核上,黄老之学以改造过的道家思想为核心,发展了道家的道论,将道家“道生万物”的宇宙论发展为“气化宇宙论”,使“道”从形而上的精神性存在发展为形而下的物质性存在;个体修养上,黄老之学提倡重生养生,主张每个个体都要按照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来养生治身,以实现神形兼治;政治实践上,以道家的虚静无为思想为指导而行“以无为而有为”的统治,主张君主无为而治,而在具体治理过程中,“又援名、法入道,借用阴阳家之框架,重视儒家的伦理教化”[25](p201)。
正是这种兼收并蓄的风格,使得黄老之学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在儒、墨两家历经秦朝的“焚书坑儒”和“挟书令”而遭到沉重打击,法家又因秦朝统治的覆亡而被弃置一旁的情况下,杂糅各家之长的黄老之学被汉初统治者接受并确立为统治思想,“从而实现了由在野的学术向在朝的学术的转变”[7](p3),并成为汉初统治阶层争相学习的“显学”。《史记》载,窦太后“好黄帝、老子之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30](p1975)①关于窦太后喜好黄老之术,《史记》中多有记载,卷十二《孝武本纪》:“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正义:太后素好黄老术”;卷二十八《封禅书》:“窦太后治黄老言,不好儒术”;卷一百七《武安侯列传》:“窦太后好黄老之言”;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陈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30](p2062),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30](p3105),邓章“以修黄老言,显于诸公间”[30](p2748),郑当时“好黄老之言”[30](p3112),刘德“修黄老术”[31](p1927),田叔“学黄老术于乐巨公所”[30](p2775),杨王孙“学黄老之术”[22](p2775)。
企业应把培训工作纳入整体规划中,企业领导者应在战略上高度重视员工培训,“把培训工作当作一项长期的基础工作来抓,并将培训情况作为每个员工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3]。
(二)“孔老会通”的玄学
作为正始玄学的开创者,王弼还进一步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将其上升到了本体的高度。对于王弼的所谓“本体”,汤用彤先生指出:“王氏之所谓本体,盖为至健之秩序。万象所通所由,而本体则无体而超象。”[19](p79)王弼主张用本体论的思想来看待宇宙万物,并从道的层面来审视宇宙万物的生化流行,指出人道日常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得其本。所以,他在《老子指略》开篇即提出:“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夫物之所以生,功之所以成,必生乎无形,由乎无名。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20](p195)又说:“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诚焉,义其竞焉,礼其争焉,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20](p94)
周博士:这倒是。不过英语教学非常强调学生的“语感”,朗读、背诵、对话、模仿等,都可以培养学生的语感,有了语感作为保障,学生自然而然就知道应该怎么说、怎么写了。所以与其重新拾起语法,不如慢慢培养语感。您觉得呢?
对于玄学的内涵,汤用彤先生有精妙的解释:“其一为玄远义,远者,远实际也。实际或指事务,或指事物。远于事务,即出世;远于事物,则重宇宙本体,讲形上学。”[19](p305)显然,玄学所要探讨的中心问题就是远离“事务”和“事物”的形而上的本体论,即有关天道人道的关系问题和天地万物之所以存在的根据问题。按照余敦康先生的观点,“儒家思想虽然偏于人道,但当其上溯于天道去追求最高的理论依据时,不能不趋同于道家所明之自然。道家虽然偏于天道,但当其下涉于人道来讨论社会生活的各种问题时,也不能不趋同于儒家所贵之名教”[31](p6)。也就是说,玄学的主题其实还是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即前所引《晋书》中王戎跟阮瞻对话所提及的“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既然儒家贵名教,道家名自然,那么如何处理儒、道两家的关系,使二者矛盾消弭进而达到会通,就是玄学的热门话题。正如牟宗三先生所言:“从客观的学术面来看,魏晋玄学在当时也有个主要的课题,那就是‘会通孔老’的问题。”[32](p179)基于此,汤用彤先生进一步指出,魏晋玄学是“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33](p43)。
所谓黄老,按照东汉王充的解释:“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黄老之操,身中恬淡,其治无为。”[21](p781)《汉书》亦载曹参“闻胶西有盖公,善治黄老言”,其中的“黄老言”,张晏注为“黄帝、老子之书”[22](p2018)。由此,则黄老之学即为“本于黄帝、老子”之学。
老庄道家的思想包括治国和治身两部分,上升到哲学高度可以归结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0](p87)。如高晨阳先生所言,“道法自然”派生出了老庄哲学的全部义理,“是对老庄道家哲学的基本精神的揭示与概括”[11](p66)。其中的“自然”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客观上的,这个“自然”属于本体范畴,有自然而然之义。而“道”的内容也是自然,表示宇宙万物的本性或内在法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道法自然”其实就是“自然”跟“道”同义、“自然”就是“道”的含义,其指代的是天地万物的自然生化、运行的原则或道理;二是主体上的,即老子所说的“夫莫之命而常自然”[10](p173)中的自然,这个“自然”说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人生得以存在的性命本真,跟“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中的“玄德”同义。
落实到玄学家的行动上,在处理自然和名教关系的问题上,他们大都表现出了会通孔老的倾向:在学术言论和思想上,玄学家们祖述老庄,如王弼“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34](p795),何晏“少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及诸文赋著述凡数十篇”[34](p292),王衍“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35](p1236),嵇康“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长好老庄”[36](p1369),阮籍“博览群籍,尤好庄老”[18](p1359),郭象“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37](p1396)。在政治实践中,玄学家们则仍将儒家的礼教视为根本原则,如南朝粱学者刘峻注《竹林七贤论》说:“是时,竹林诸贤之风虽高,而礼教尚峻。”[38](p735)这源于玄学家们的出身和知识背景,因为魏晋玄学家多出生于官宦世家或经学世家,自幼便深受儒教教诲,熟读儒家经典,儒家思想可以说已经深入其生命之中,如冯友兰先生所言:“所须注意者,即此等人(笔者按:玄学家)虽宗奉道家,而其中之一部分,仍推孔子为最大之圣人,以其学说为思想之正统。”[39](p78)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来,对于人才的培养而言,校企合作是一种崭新的模式,不仅仅利于体育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更加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就业。为此,我们一定要转变思想,提升认识,转变思想,加大投入,做好场馆设施的建设与完善,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为职业实用性体育教学的实现创造条件,奠定基础,真正实现校企合作发展的可持续性。
在处理名教与自然关系方面堪称表率的首推正始名士夏侯玄,他以“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指导个人修养,崇尚、追求人性之自然,在政治生活中则十分重视儒家之伦理纲常,在严格遵守封建礼教的前提下追求个性的自由,从而实现了二者的融合会通,备受当时玄学家们的推崇。
玄学会通儒、道这一工作,是在其形成之初由王弼来完成的。众所周知,道家的代表著作为《老子》和《庄子》,儒家的代表著作则为《诗经》《尚书》《仪礼》《周易》和《春秋》。而《老子》《庄子》和儒家经典中以阐述天道、人事为主要内容的《周易》又合称为“三玄”,是玄学的代表著作,由此即不难看出玄学兼有儒、道的成分。在此基础上,王弼又通过《老子注》和《周易注》分别对《老子》和《周易》进行了重新诠释,先注解《老子》,通过《老子注》完成了其对“本末有无”等问题的系统认知,基本建构起了一套玄学的思想体系,然后“援老入易”,将这套思想体系用来做《周易注》。如王弼将《老子注》第五章中“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20](p13)这一重视自然的思想引入对《周易·坤》的注解,把《坤》六二爻的“直、方、大,不习无不利”注为:“居中得正,极于地质,任其自然,而物自生;不假修营,而功自成,故不习焉,而无不利。”[20](p227)在王弼看来,“直、方、大”这三种品德乃是天地自然之性的具体体现,只要体悟了自然之性,就能做到“不假修营,而功自成”。除此之外,《履》卦九二爻注为“履道尚谦,不喜处盈”[20](p273),《蒙》卦六五爻注为“任物以能,不劳聪明”[20](p242)等,也都是采用了《老子注》中的思想。
由于公办学校的基础设施投入主体是政府,其公益性质决定了有条件的学校也有义务向社会开放体育场馆设施,以缓解社会场馆资源不足和群众需求之间的矛盾。但是,在《关于推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的实施意见》文件里明确指出,开放的目的首先是“强化学生课外锻炼”,其基本原则是“坚持校内优先”、“首先要保证本校师生的教育教学和日常活动需求,优先向青少年学生和社会组织开放”,开放的对象首先是“本校学生、学区内学生”。无需置疑,学校应该首先要保证青少年学生的课外锻炼,促进青少年学生的技能学习和运动参与,这也是我们建设学校体育场馆的初衷和最主要的工作指向。
在注解《周易》时,除了引入道家思想外,王弼还继承了西汉古文易学开创者费直注解《周易》时“以传解经”的方法,大量引入儒家思想,并阐发儒家义理。如对《乾》卦九三爻《文言》的注为“进物之速者,义不若利,存物之终者,利不及义”[20](p214),将《蛊》卦注释为“进德修业,往则亨矣”[20](p308),将《蹇·象》注为“除难莫若反身修德”[20](p411),等等。这也证明了姜广辉“无论玄学的属性如何,玄学中的经学是始终存在的,王弼《周易注》这样的经学名著的出现就是突出表现”[40](p671)之言非虚。
汉魏新道家之间的传承,主要是就汉初黄老之学的影响而言的。清代学者陈澧在其《东塾读书记》中曾有一章专门论及诸子的情况,其中涉及了汉初黄老之学跟魏晋玄学的关系,“洪稚存云:自汉兴,黄老之学盛行,文景因之以致治。至东汉末,祖尚玄虚,于是始变黄老而称老庄”[42](p243)。这段话虽然失于简略,但却勾勒出了汉初黄老之学跟魏晋玄学一脉相承的学术特质。其中有三点颇值得注意:第一,其中的“变”字就表明了同为新道家的汉初黄老之学和魏晋玄学之间存在着一个演进的过程;第二,发生演进的关键点在于东汉末年的“祖尚玄虚”;第三,其中缺少了文景之治后至东汉末年之间的那个时间段。将这三点综合起来考量,就可以大致梳理出从汉初黄老之学到魏晋玄学的演进轨迹。
很显然,就“道法自然”这一老庄道家哲学的基本精神而言,无论是秦汉时期的黄老之学还是魏晋玄学,都与先秦老庄所强调的“道法自然”的原则完全相同,由此而言,二者都是道家之学,这也是汉魏新道家最根本的相同之处。
三、汉魏新道家的传承与影响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两种重要时代思潮,同名为“新道家”的汉初黄老之学和魏晋玄学持续的时间都不长,即逐渐消退。不过,虽然让出了主流话语权,但无论是汉初黄老之学还是魏晋玄学都没有彻底淡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舞台,而是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潮中,对后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一)汉魏新道家的传承
尽管对《周易》的注解没有舍弃儒家的义理,注解方法又是“以传解经”,但王弼的目标却并不在于注解《周易》的文辞,而是要将其在《老子注》中建构起来的玄学思想,尤其是重新诠释《老子》“道”时所形成的“崇本息末”思想,灌注于《周易》中,与《周易》的哲学体系融会贯通,从而达到理论上的创新。具体而言,就是将道家的自然视为形而上的体,将儒家的义理视为形而下的用,从而以道家的自然来融合儒家的名教。如王晓毅先生所言,王弼“以‘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为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以本末体用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全面融合儒道两派,在‘无与有’‘无为与有为’‘自然与名教’‘性与情’等等一系列重要哲学课题上的差异,做出‘儒道为一’的玄学新解答”[41](p94),从而完成了儒、道的会通。
试点期间,规划了总面积840亩(15 亩=1 hm2,下同),总投资 3 140 万元的杨溪生态湿地工程。2013年8月,完成投资1 040万元的一期240亩生态湿地工程并开展运行,通过湿地后的入库水质达到Ⅱ类标准;二期工程占地600亩,投资2 096万元,其中200亩已列入政府2014年度投资项目计划,在外永商对该项目捐款423万元,并已开工建设。同时,完成杨溪库区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9 120亩;成立了杨溪警务室,配备了6名警员及相关设备,开展日常巡查管理工作。
杂糅百家之长的黄老之学在汉初成为统治思想,其“无为而治”的政策使汉初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但黄老之学毕竟只是杂糅之学,并没有对重天道的道家和重人道的儒家进行会通,无法满足汉武帝为“君权神授”寻求理论依据的需要,从而给了用“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来改造儒学的董仲舒以机会。随着儒学兴起并成为庙堂之学,汉武帝“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22](p3593),黄老之学因失去统治者的支持而逐渐被边缘化,由在朝的学术重新变为在野的学术。
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间,已然成为在野之学的黄老之学沿着两个方向分化发展:一是作为宗教的雏形继续发展,黄老思想被以张楷、栾巴和王苍等为代表的方士们选择性继承,并在他们的努力下与神仙方术思想紧密结合,从而形成了具有神学迷信色彩的“黄老道学”,为早期道教的产生奠定了理论基础;二是“作为两汉儒学正统学术的一种暗流”[7](p303),被以扬雄、张衡、王充和王符等代表的儒士们吸收,尤其是吸收和发展了黄老思想中属于道家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创造出了“玄”生万物论、“浑天”学说和“元气自然论”等思想,进而利用其中科学理性的“天道自然”理论来驳斥儒家谶纬经学日趋僵化的“天人感应论”。这种对儒家经学的批判和对道家思想的吸收融合促成了“儒道合流”,使得黄老之学在哲学上取得深入的同时,逐渐渗入到两汉学术的正统当中,“正是由于这种渗入才形成汉末儒道互补的风尚,从而为魏晋玄学的出现酿成了涓涓细流”[7](p318)。正是基于此,卞敏说:“对于早期玄学来说,黄老之学可能是比老庄哲学更直接的一个思想来源”[43](p7)。
(二)汉魏新道家的影响
冯友兰先生曾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代变法和现代革命等七大思潮视为“客观的中国哲学史的七个中心环节”和“客观的中国哲学史发展的自然格局”[44](p4)。这跟冯天瑜先生将中国学术发展历程分为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和近代新学七段[45](p769)的划分方法大致相同,充分肯定了魏晋玄学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虽然二者都未提及汉初的黄老之学,但汉初黄老之学与魏晋玄学同为新道家,且汉初黄老之学又是魏晋玄学的思想来源,从这个意义上说,汉魏新道家对后世的影响可一体而论。
兄妹俩莫名其妙地对望着,罗瑞似乎恍然大悟,对老福说:“你的意思是她可能是被……哎呀,您真是高手,我怎么没想到呢!”他竟然兴奋得手舞足蹈,这是老福没想到的。
脉压雷达所采用的宽脉冲不仅可以提高雷达的平均发射功率,还能够确保足够大的作用距离。在接收端通过脉冲压缩处理将宽脉冲转化为窄脉冲,则可实现较好的距离分辨率,因此较好地解决了雷达大作用距离和高距离分辨率之间的矛盾。此外,脉冲压缩处理大大提高了雷达对非相干干扰的抑制能力[1]。如何对脉压雷达进行有效干扰已成为电子战领域的研究热点。
汉魏新道家对于中国古代尤其是魏晋之后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形态有四:一是自然论,二是唯气论(亦可称为元气论或气化论),三是唯有论,四是形神观(形质神用论)。”[46](p257)在这四种主要理论形态中,汉魏新道家占据其二,即自然论和唯气论,其对魏晋之后哲学的影响亦主要体现在这两个方面。
如前所述,王弼、夏侯玄等玄学家思想中的自然论是以汉初黄老之学为中介而转承自老庄道家,而魏晋之后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中同样贯通着来自汉初黄老之学和魏晋玄学的自然论思想。如唐代刘禹锡曾提出“自然之说”,他在《天论(上)》中说:“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剌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蹻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47](p212),并以此为基础宣扬“天与人交相胜耳”[47](p213)。宋代的张载和王安石等唯物主义哲学家发展了“天道自然”的学说,强调自然为万物之本体属性,如张载在《正蒙·天道篇第三》中说:“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识自然之为体尔”[48](p15),又在《横渠易说上经·观》中言:“有两则须有感,然天(自然——引者注)之感有何思虑?莫非自然”[48](p107);到明代,王廷相和王夫之等则进一步肯定了道的自然属性,王夫之在注解张载所说“心能尽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检其心,‘非道弘人也’”时指出:“天理之自然,为太和之气所体物不遗者为性;凝之于人而函于形中,因形发用以起知能者为心。性者天道,心者人道。”[49](p104-105)《思问录内篇》中又言:“吉凶成败皆有自然之数,而非可以人力安排。淡于利欲者,廓其心于俯仰倚伏之间而几矣。乃见仅及此,而以亿天理之皆然,遂以谓莫匪自然……故人心不可以测天道,道心乃能知人道。言自然者,虽极观物知化之能,亦尽人心之用而已。”[50](p25)戴震则认为凡为自然之事物皆有存在之必然性,所谓“由血气之自然,而审察之以知其必然,是之谓理义。自然之与必然,非二事也”[51](p171)。诚然,相较于汉初黄老之学和魏晋玄学的自然论思想,唐宋至明清时期唯物主义哲学家们所宣扬的“自然”已在内涵上有了很大程度的变化,但这种自然论乃通过汉魏新道家而滥觞于原始道家当无疑问。
除了“自然”,汉魏新道家所使用的哲学范畴还包括“道”“气”等,比如汉初黄老之学中就提出了“道、气整合”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哲学基本思想中的气论。前已述从汉初黄老之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元气自然论”,王充将“元气”视为一种物质元素,认为是“元气”构成了天地万物,体现了更加明显的唯物主义色彩。到魏晋之后,气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唐代王冰指出:“万物无非化气以生成者。”[52](p110)宋代周敦颐和朱熹均有“二气五行,化生万物”[53](p31)的说法,著名理学家程颐亦强调:“万物之始,皆气化。”[54](p130)张载在《正蒙·太和篇第一》中云:“由气化,有道之名。”[48](p9)即为以“气”来说明“道”。明代王廷相指出:“天地之先,元气而已矣。元气之上无物,故元气为道之本。”[55](p339)王夫之则言:“盖阴阳者,气之二体;动静者,气之二几。体同而用异,则相感而动,动而成象则静。动静之几,聚散、出入、形不形之从来也。”[49](p9)这是在用阴阳矛盾的对立统一去阐释“气”,戴震的“阴阳五行之运而不已,天地之气化也”[51](p182)显是继承了王夫之的思想。无论是张载,还是王夫之和戴震,都强调“气”作为天地万物的本源的重要性,“气”即是“道”,故统称为“气本论”,而这些思想的源头同样来自汉魏新道家。所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唯物主义思想中又增加了“阴阳”“动静”“五行”等哲学范畴。
小虫骑在摩托车上,一路狂奔,一路乱想,不知不觉到了凌源,到了许沁的抛光部。许沁的抛光部有十来个员工在挥汗如雨地干活,热烘烘的车间里飘荡着青腊和汗水的味道,机器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刺耳的嘈杂声大得连对面说话都听不见。
由此可见,对于以张载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和以戴震为代表的清代朴学而言,汉魏新道家为其奠定了哲学基本精神的基础,对二者的理论建构影响直接。除此之外,汉魏新道家中无论是道家与儒墨法诸家杂糅的黄老之学,还是“儒道会通”的魏晋玄学,其对待各派学说的态度和辩证的思维方式,都对“当初传入之佛学以重大影响”[43](p17),进而影响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三足鼎立局面的形成。汉魏新道家对于后世学术的影响,凸显了中国古代哲学和学术发展的一脉相承性,恰好反映出了冯友兰先生梳理中国哲学发展史和冯天瑜先生梳理中国学术发展史的内在逻辑。
四、结语
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王明先生曾系统梳理了汉魏之际老庄道家思想的演变轨迹,并提出了著名的“老学三变说”,他指出:“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凡三变,其宗旨各自不同,此三变是:一、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经国治世。二、东汉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三、三国之时,习老子既不在治国经世,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56](p323)显然,老学由黄老而道术而玄论的“三变说”,一方面指出了作为秦汉新道家的汉初黄老之学与作为魏晋新道家的魏晋玄学的哲学基本精神均为老学,而老学的核心则是老庄道家思想,另一方面指出了汉初黄老之学跟魏晋玄学之间的区别所在,即以道家为主、杂糅儒墨法各家思想的黄老之学更突出作为“政术”的实用一面,而魏晋玄学则更崇尚“虚无自然”的玄谈。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明先生的“老学三变说”,正是对汉魏新道家之间关系的最佳注脚。
参考文献:
[1]陈寅恪.《逍遥游》郭象义及支遁义探源[J].清华学报,1937(2).
[2]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3]余英时.人文与理性的中国[M].程嫩生,罗群,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熊铁基.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兼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J].文史哲,1981(2).
[5]欧阳守道.序·赠刘道士序[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6]向燕南.战国末期新道家的历史思想[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7(1).
[7]丁原明.黄老学论纲[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8]许地山.道家思想与道教[J].燕京学报,1927(2).
[9]唐兰.黄帝四经初探[J].文物,1974(10).
[10]老子[M].陈剑,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1]高晨阳.玄学的本质及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J].中国哲学史,1996(4).
[12]庄子[M].方勇,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13]陈鼓应.黄帝四经今注今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4]王云五,陆佃解.鹖冠子·环流[M].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
[15]吕不韦.吕氏春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彭裕商.文子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6.
[17]列子[M].张湛,注.上海:上海书店,1986.
[18]房玄龄.阮籍传[M]//晋书: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
[19]汤用彤.汤用彤全集:第四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20]王弼.王弼集校释[M].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
[21]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秦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4]韩非子[M].高华平,等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
[25]曹峰.关于黄老道家的一些新认识[M]//诸子学刊:第十二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2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M].冯逸,乔华,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
[27]荀子[M].杨倞,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8]高亨,池曦朝.试探马王堆汉墓中的帛书老子[J].文物,1974(11).
[29]吴光.黄老之学通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30]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63.
[31]余敦康.魏晋玄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32]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33]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35]房玄龄.王衍传[M]//晋书:卷四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74.
[36]房玄龄.嵇康传[M]//晋书: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74.
[37]房玄龄.郭象传[M]//晋书:卷五十.北京:中华书局,1974.
[38]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9]冯友兰.中国哲学史[M].重庆:重庆出版集团,2009.
[40]姜广辉.中国经学思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41]王晓毅.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M].北京:中华书局,2003.
[42]陈澧.东塾读书记[M].北京:三联书店,1998.
[43]卞敏.魏晋玄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45]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46]张岱年.文化论[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7]刘禹锡.刘禹锡集[M].赵娟,姜剑云,评注.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
[48]张载.张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8.
[49]王夫之.张子正蒙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0]王夫之.思问录俟解[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1]戴震.戴震全书(六):孟子字义疏证(卷上)[M].合肥:黄山书社,1995.
[52]王冰.黄帝内经素问[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3]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54]程颐,程颢.二程遗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55]王廷相.慎言·雅述全译[M].冒怀辛,译注.成都:巴蜀书社,2009.
[56]王明.《老子河上公章句》考[M]//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9.04.006
[中图分类号]B232;B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9)04-0042-09
作者简介:赵海军(1963—),男,吉林长岭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 罗雨泽
标签:道家论文; 玄学论文; 自然论文; 魏晋论文; 之学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中国哲学论文; 三国论文; 晋论文; 南北朝哲学(220~589年)论文; 《理论月刊》2019年第4期论文;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