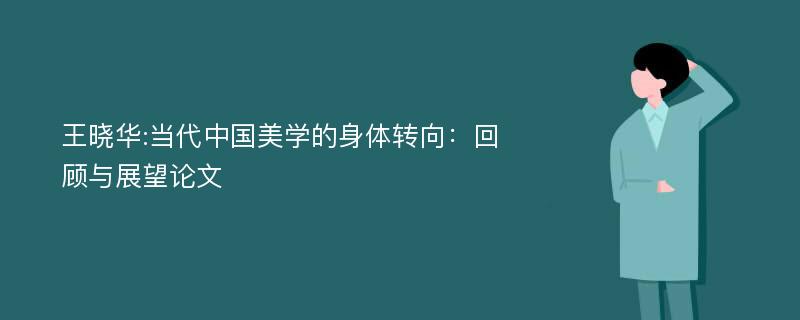
摘 要:由于生理学、神经哲学、认知理论的影响,当代中国美学建构出现了延续至今的身体转向。21世纪以来的实践美学凸显其身体维度,强调身体与实践的原初关系。生态美学发现家园意识与身体意识密切相关,力图揭示“生态审美本性论”与身体美学的内在关联。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也承认生命/生活的身体性,有意识地走向“身体之维”。随着这种转向的深入,身体美学已经成为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枢纽。
关键词:当代中国美学;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命美学;生活美学;身体转向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美学版图出现了几个活跃地带。除了实践美学继续延续其建构态势以外,生态美学、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身体美学也先后崛起。它们相互对话,形成了彼此呼应的高原群落。在交流过程中,人们发现这几个重要流派都与汉语拼音S有关。这似乎是巧合,但又提供了可以深入解读的线索。从身体学的角度看,上述流派(5S)共同崛起的逻辑清晰可见:生命、生活、生态都与牵连出身体性存在,而实践更是只能由身体承担,因此,身体是能够将这些概念牵连起来的核心范畴。换言之,实践美学、生命美学、生活美学、生态美学都以某种方式通达身体美学,反之亦然。可以说,当代中国美学研究出现了明晰的身体转向,其中蕴含着需要深入探索的深层逻辑。
一、实践美学之身体维度的凸显: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进展
在上述几个流派中,实践美学是影响最大者。它力图从实践角度探讨审美活动的起源、机制、归属,形成了具有阐释力的研究范式。从逻辑的角度看,这种立场必然导向重视身体的理论图式:其一,实践只能由身体承担,必然落实为身体活动;其二,由于实践美学的唯物论背景,它必然承认精神活动是身体的功能,因而最终会肯定身体在实践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正是由于身体维度的凸显,实践美学开始重新阐释其基本理念。
自诞生之日起,实践美学就具有清晰的逻辑起点。李泽厚曾明确表示自己“从实践出发研究人的认识”[1]。邓晓芒、易中天、张玉能等新实践美学的倡导者也都将实践当作原初范畴。那么,实践与身体的关系是怎样的?对于实践美学来说,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然而,由于时代语境的限制,在20世纪的实践美学中,身体问题并未进入其核心视域。当其代表人物对实践进行定义时,反复被强调的是“人类”“物质生产”“工具”,主体问题尚付之阙如[2]。不过,进入21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改变。随着研究的深入,实践美学开始了持续至今的话语更新。其中,以下两个理论线索都与身体概念密切相关:其一,实践存在论美学;其二,新实践美学的身体生产理论。
(一)实践存在论美学的身体维度
在《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一文中,朱立元教授曾经明确地强调:“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现代美学的哲学基础就是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遵循马克思实践的唯物主义,就应从存在论根基处着眼,运用关系论和生成论的思维方式,重新考察和审视一系列美学基本问题。”[3]25-26存在论(ontology)又译本体论,研究的是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属性。强调存在论的意义,主要动机是超越中国现当代美学研究中曾经流行的认识论图式,推动美学研究回到更为“可靠的基地”,但它又无疑又牵连出实践美学的身体维度:其一,一旦进入比认识论更为原始的存在论维度,笛卡尔式的主客对立的二元图式就会成为解构的对象,而建立统一的人学图式必然涉及身心问题;其二,恰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基于唯物论的存在论必然承认心对身的归属;其三,在确立了身体的地位之后,实践主体问题已经不言自明——身体是实在者,实在者才能实践。事实上,这正是实践存在论美学中蕴含着的命题。它可能由于研究的重点问题而暂时未被言明,但却已经绽露踪迹。在阐释了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基本含义之后,朱立元教授立刻引用了马克思有关身体的著名论述:“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4]当马克思将自然定义为人的无机身体时,他的着眼点是人的身体维度:“说人是肉体的(corporal)、有生命的(living)、现实的(real)、感性的(sensuous)、充满自然活力的对象性存在,等于说,他拥有现实的感性的客体作为自己存在或生命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在现实的感性的客体中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5]156如此被言说的身体是实践的身体:他/她不是静观感性的对象,而是改变它们。落实到具体层面,实践就是身体-主体建构世界的过程:“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对象(objective world)世界,通过作用于无机自然(inorganic nature),人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物种存在(species being),即,一种把自己物种当作自己本质性存在的存在,或者说,把自己看作物种存在。”[5]75在这个过程中,他/她超越了直接的肉体需求,开始进行全面而自由的生产,“懂得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于对象”“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5]76对于这个逻辑线索,朱立元教授显然有所领悟。在随后的论证中,他先是将实践活动定义为对象化的感性活动(这必然牵连出身体的地位),随后又直接肯定了身体的意义:“再就人和自我的关系来看,在西方中世纪,神学一再告诫人们,身体是恶的,是原罪,人必须折磨自己的身体才能使灵魂升入天堂;文艺复兴以后,解剖学产生,人们又把自己的身体视为机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弗洛伊德等心理分析学家揭示了人的潜在生命欲望,使人与自我的关系骤然变得复杂起来;在今天,身体似乎已与灵魂紧密结为一体,不再是自我的耻辱,许多艺术家甚至试图调动身体诸种感受,重新体认、揭示和阐发身体与世界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存在状态;如此等等。”[3]30如果进一步向下推理,那么,下面的逻辑线索就会显现出来:身体的感性活动—实践—世界的生成—审美的出现。显然,实践存在论美学中蕴含着身体维度,预示了更为深远的重建计划。
然后,大家围坐进行分析讨论。马克老师指导学生朗读了网上一篇关于耶鲁先生支持贩奴的文章,让学生思考这篇文章与他们的游戏之间的关系,并谈谈做游戏的感受。学生们踊跃发表自己的见解,有的学生认为商人为了利润会不择手段,所以一定要制定贸易法案;有的学生质疑这篇批判耶鲁的文章,反问如果没有像耶鲁这样的人去做这些不光彩的贸易,今天的美国会怎样;结果马上就有学生反对,认为当时的新大陆太邪恶了,竟然贩奴,为了赚钱不顾道德。这时马克老师适时追问:你认为当时的商人是怎么想的?如果把贩奴从整个贸易中去掉又会怎么样……讨论进行得不亦乐乎!
(二)新实践美学的身体生产理论
英文中的生命和生活都可以写成life,而life esthetics可以译为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虽然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关注的重点具有差异,但二者显然具有共同的渊源乃至相近的立场。从本文的立场看,身体意识是二者兴起的共同动力:(一)如果不是由于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证明了人的身体性,那么,重视感性生命的美学就无法诞生;(二)同理,假如人依旧被当作最终回归天界的灵魂,大地上的生活就不会获得珍视,生活美学曾经特别强调“日常生活的审美化(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更是无从谈起。
(4) 2台FEP采用自开发软件接口协议与外部时钟源同步,但无法确保2台FEP的时钟精度偏差均在50 ms内(仅采用NTP或PTP协议时才能确保精度在50 ms内),不能同时为下一层提供时钟源服务。
二、生态美学的身体意识:另一个重要的理论线索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只是单一讲授教学内容,理论与实践课程分开教学,单独授课[2]。由于学生具有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电路知识理论基础水平较薄弱的特点,面对复杂且枯燥的理论推导以及难记的公式,学生往往缺乏学习的热情。教师教学的形式只是课堂讲授,理论内容抽象,学生对于知识的具体应用并没有深入的了解。因此,学生在学习电子技术专业理论课时,对涉及的一些仪表、示波器、元器件、常用芯片等没有感性认识,对这些实验所需的元器件及工具并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也很少涉及它们具体贴近实际生产应用的综合性实验项目,很难将理论知识应用与实践,造成了学生实践能力较弱。
在当代中国美学中,生态美学是迅速崛起的新兴流派。它虽然没有实践美学那样长的历史,但却在短时间内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话语。那么,是什么推动了生态美学的兴起?根据笔者的研究,身体意识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
通过重构朱立元教授的实践存在论美学和张玉能教授的新实践美学,我们都不难发现潜在和显在的身体话语。从学派建构的立场上看,这种言说是序曲而非尾声。实践和身体的故事还远远没有讲完。恰如英国美学家伊格尔顿所言,马克思曾经通过劳动的身体(the laboring body)从事理论重建的工程,“将身体主体性(bodily subjectivity)”重置为社会历史的重要维度[7]。“劳动的身体”就是实践的身体。如果实践实现了身体的主体性,那么,身体的地位就不言而喻。一旦承认了身体的主体地位,实践美学就会进入全新的可能性空间,甚至可能升格为最具有阐释力的学派。倘若能揭示身体、实践、艺术生产、审美活动之间的深层联系,那么,一个更辽远的地平线就会显现出来。虽然这个逻辑线索还未被充分敞开,但相应的理论踪迹已经诞生。剩下的工作是推动已经发生的转向。
除了实践美学和生态美学外,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也是中国当代美学中影响较大的流派。在对它们进行探究时,我们同样会发现身体观念产生影响的理论踪迹。
那么,身体在生态美学中到底可以占据什么地位?对于这个多少有些敏感的问题,曾繁仁教授给出的答案非常清晰:“在生态学视野下,身体在审美活动中就不再仅仅是客体而成为了主体:它不再是被审视的对象,而成了审美经验的积极参与者。与此相应,心灵和自我不再是独立的精神实体,而还原成了身体的灵性。由此出发,审美经验不再是对象性的认识活动,而是有灵性的身体与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交流。”[11]145“灵性的身体”也就是用西方学者所说的“心智性的身体”(mindful body)。它用梅洛-庞蒂所说的世界之肉做成,但又具有了自我意识,并因此升格为主体。在对环境进行审美时,情况更是如此:“对环境的鉴赏不仅需要动用各种感觉器官,而且要求这些感官必须协同运作,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身体不再是以局部的方式,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参与到了审美活动当中。就此而言,身体已经不再是心灵的工具或中介,而直接成了审美活动的主体。”[11]148需要指出的是,强调身体的主体性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基本立场。除了曾繁仁教授外,程相占教授也倡导身体-主体概念:“主体不仅仅是能够思维的心灵,身体也是主体而不仅仅是客观对象;更加重要的是,身体对于心灵的形成和塑造具有重要作用。”[12]对于生态美学来说,身体-主体概念的提出意义重大:其一,身心二元论被克服了,可以建立统一的人学图式;其二,由于强调身体与环境的共性,它又消除了人类-环境之间的本体论裂痕;其三,随着上述进展,美学建构也获得了自我超越的机缘,其中最重要的进展就是生态美学具有了本体论表述。在由此产生的美学话语中,“身体(主体)在环境(生态体系)中”乃是一个基本前设。身体-主体既是环境的构成,又总是处于与环境的建设性互动之中,而这意味着审美是一种本体论活动:“传统美学是一种认识论美学,把审美活动当作一种主客二分的认识活动,因此关注的是一种分离式的审美体验;生态美学这是存在论或本体论美学,把审美活动当作一种生存活动,当作生态体系内部循环的一部分,因此强调一种介入式的审美体验。”[11]152在介入环境的过程中,身体既是审美的主体,而且也是鉴赏的对象。他/她是那个看风景的人,也是风景的一部分。沿着这个线索走下去,生态美学会以更完整的方式通达身体美学。
曾繁仁教授是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的倡导者和标志性人物。通过研究他的文本,笔者发现了身体转向的明晰踪迹。在《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一文中,曾繁仁教授提到了“家园意识”:“所谓‘家园’就是每个人的休养生息之所,也是自己的祖祖辈辈繁衍生息之地,那里是生我养我之地,那里有自己的血脉与亲人。”[8]此种言说实际上牵连出身体性存在:休养生息于大地上的不是灵魂,而是我们所是的身体。正因为人存在的身体性,他/她才依赖大地上的生态体系。在这种论述中,家园意识牵连出重视身体的立场,反之亦然。从谱系学的角度看,强调二者的关系乃是生态学的原初立场。当德国生态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于1866年创立生态学时,他将两个希腊词oikos(家)和logos(研究)组合起来,造出一个新词oekologie,用它来意指“研究有机体在家(环境)中生存的科学”[9]。在这个定义中,关键词有二:其一,有机体;其二,oikos(家)。如果说人类身体属于有机体的链条,那么,众多oikos(家)的聚合体就是家园。正如有机体概念涵括了人类身体,家园也是个生态学范畴。包括身体在内的有机体在家园中诞生、成长、逝去。为了揭示人类身体对家园的归属关系,海克尔强调“一个人在会消亡的生物界中只不过是一棵微小的原生物质”[10]14。这是谦逊之言,又是大胆之论,因为它蕴含着肯定身体的立场:如果人是有机体之一种,那么,他/她必然是身体性存在。在海克尔的生态学框架中,身体的地位至关重要:正是通过以身体概念代替灵魂范畴,他才“勇敢地摒弃了二元论并转向纯粹一元论”,并因此聚焦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10]407。并非巧合的是,这种立场也体现在中国当代生态美学中。在专著《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中,曾繁仁教授用一章的篇幅探讨“生态审美本性论与身体美学”。其中,有关“肉身性与人之生态本性”的论述深化了他先前的身体意识,进入到了本体论层面。通过援引梅洛-庞蒂的话,他强调“我的身体是用于世界同样的肉身做成的”[11]154,呼吁人们“体会到自身与环境的一体性”[11]156。推论至此,家园概念获得了全新的内涵,生态美学则展示了其身体维度。
在身体意识的引导下,中国当代生态美学强调介入。当介入升格为具有明晰目的的行动时,它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实践。从这个角度看,“生态美学有别于传统美学的审美静观”“具有本然的实践性”[11]328。于是,由于身体维度的绽露,当代中国美学的两个重要流派——实践美学和生态美学——开始汇合。内蕴于这种汇合动作的可能性获得充分敞开,那么,一种更富建设性的理论建构就会出现。
三、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的身体观念:同样值得重视的理论踪迹
1.1 研究对象 选取 2010年10月至 2012年12月868例在南昌大学附属新余医院住院治疗的乙型肝炎病毒感染患者为研究对象,开展基线调查,建立动态队列。纳入标准:(1)年龄≥30 岁;(2)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3)同意参加基线调查和随访。排除标准:(1)年龄<30 岁;(2)合并其他肝炎病毒感染或艾滋病毒感染者;(3)已患肝癌者。符合纳入、排除标准且调查资料完整者 523例。截至 2017年8月31 日,共435例患者完成随访调查,随访率为 83.17%。本研究通过南昌大学附属新余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纳入研究对象均知情同意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与朱立元教授一样,新实践美学的倡导者张玉能教授也重视人的自我生产。在论文《人的自身生产与身体美学的建立》中,他开篇便指出:“人的自身生产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根本的方面,因为人的肉体存在是人类一切社会实践的前提。”[6]41如果说实践具有身体维度的话,那么,它的延续依赖身体的自我生产。一旦后者终止,那么,实践就会面临“主体之死”。从这个前提出发,身体的地位再次凸显出来:“就作为一种物质生产而言,人的自身生产,在生成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的过程之中,首先应该是人体的美和审美的生成。”[6]41由于身体的自我生产总是发生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因此,它总是越过基本的物质层面,抵达更大的活动场域。这首先体现在它是广义物质实践的构成,从属于生活的总体创生。既然如此,身体就不仅仅是审美的对象,而且很可能担当更重要的角色。从唯物论的角度看,实践的主体是而且只能是身体性存在。如果认识到这一点,美学的面貌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对此,张玉能教授给予了部分肯定:“尽管身体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家、美学家所关心的一个问题,但是在鲍姆加登、尼采之前,由于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占据着主导地位,身体不仅是与心灵相对立的,而且是处于从属于心灵的地位。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时代都是如此,而笛卡尔的二元论就更加明确地规定了身心二元对立的思路,因此,心灵吞没了肉体,理性遮蔽了感性,理性主义成为了启蒙主义时代的最高原则。”[6]45显然,他对身心二分法持否定态度。那么,否定二元论后的美学建构向何处去?从本体论的角度看,答案并不难给出:一元论中的元只能的身体而不能是所谓的心灵。如果再泛泛地谈论身心问题,就难免回到二元论的老路。虽然张玉能教授并未直接得出这个结论,但他随后的论述展示了重视身体的倾向。譬如,将感性学定位为身体学。再如,肯定伊格尔顿有关“美学是作为有关肉体的话语而诞生的”[6]45这一说法。随着这个思路的展开,他明确将身体美学定位为“新实践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强调“建立身体美学”“是一种具有必然性和合理性的科学研究行为”[6]47。虽然他又强调“我们要建立的身体美学是新实践美学的分支学科”[6]47,但实践美学已经清晰地显现出其身体维度。
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确定一个事实:生命美学或生活美学至少是个现代概念,对其解释不能过于泛化,否则,它们就会丧失学派应有的边界。就此而言,福柯(Michel Foucault)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专著《词与物》中,他以略显夸张的语气指出:“事实上,直到18世纪末,生命并不存在……”[13]214。此论貌似悖理,实则意味深长:18世纪之前的生命概念是广义的,泛指矿物(被认作能生长,但不能移动和感觉)、植物(能生长并且对感觉敏感)、动物(能自发地移动)。到了19世纪,依赖对有机体、劳动、语言的阐释,有关生命的概念开始获得了确定性。就人而言,地平线变得清晰:“当人开始存在于自己的机体内、存在于自己的头颅壳内、存在于自己的四肢骨架内以及存在于他的生理学之整副肋骨内时;当他开始存在于劳动的中心时;当他把自己的思想置于语言的褶层时;现代性诞生了。”[13]414现代生命概念牵连出身体范畴。这个身体既是生物学-生理学意义上的躯体,又与劳动和语言密切相关:它作为生物存在、活着、成长;在人这里,肉体生存意味着劳动、交换、言说[13]462。离开了这几种意义上的身体概念,现代生命(生活)概念就无从诞生。从谱系学的角度看,中国当代生命美学和生活美学也存在于由此产生的知识型之中。换言之,充分获得自我意识的生命美学或生活美学必然具有身体维度。
与西方话语一样,中国生命美学中的核心概念也处于一定的知识型之中。在身体范畴产生影响之前,泛化的生命概念也曾占据上风。到了21世纪,变化发生了。生命概念开始与身体范畴联系起来,相关建构进入了生物学、生理学、生态学和实践理论相互交织的场域。在那里,一个新的生命形象建立起来:“身体在世”。作为当代身体美学的倡导者,潘知常教授明确指出:“生命美学建构的,是从‘生命’美学走向‘身体’之维,进而建构‘身体美学’,然后,再从‘身体’的延伸、身体的意向性结构去展开具体的研究。”[14]85。具体来说,生命美学研究的是“身体在世”:“‘身体在世’的日常生活世界,构成了生活之维,构成了生活美学;‘身体在世’的城市与自然世界,构成了环境之维,构成了环境美学(景观美学)。”[14]85在《回归与超越:生命美学之于生命美学的意义》一文中,范藻教授也指出:“在‘审美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的实践过程中,它理所当然地是要包括身体的存在并现身的,也就是说不论是‘审美活动’,还是人类的其他‘生命活动’,身体都是不能缺席而必须参与的。”[15]64-65正如实践是身体的活动,审美的承担者也是身体:“由于身体是既是审美的对象,也是审美的主体,还是审美的目的。因此,回归身体又超越身体,是身体美学的起点与终点,而这个终点刚好接上生命美学的起点。”[15]65推论至此,生命美学的身体维度已经初步绽露。
与生命美学相比,生活美学的逻辑脉络略显复杂,但它同样得益于身体意识。无论如何,它所说的生活(life/live)只能是身体性的存在。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并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审美化首先意味着感性化的体验,而这总是牵连出身体-主体的存在。在日常生活世界中,身体总已经在此,总已经栖居和劳作,总已经体验欢欣和痛苦。这不正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前提吗?在影响深远的专著《生活世界现象学》中,大哲胡塞尔(Edmund Husserl)强调:“就身体而言我在这里存在着,并且是围绕着我而定位的原真世界的一个中心。”[16]生活就是“身体在世”。即使是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过程中,aesthetic body(感受的身体/审美的身体)也不可或缺。如果说审美植根于感性活动,那么,它就源于身体而又回到身体。如果不意识到这点,那么,生活美学就难以获得自我意识。现在看来,当代生活美学的倡导者多少觉察到了身体的意义。在《“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一文中,刘悦笛研究员谈到了身体存在、感性活动、活的生活[17]。虽然他并未正面敞开三者的关系,但潜在的线索依然清晰可见:离开了身体,感性活动就没有着落,活的生活更是无源之水。如果说生活美学超越了康德美学,那么,它就只能是实践的、感性的、身体的美学。一旦我们在实践、感性、身体之间建立正面链接,那么,我们就会发现生活本有的超越性:在实践中感受世界的身体走向别处、越过界限、抵达远方,生活则因此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正因为如此,“生活美学”必须“重新认识肉身”。对此,张宝贵教授具有清晰的认知。在研究文化问题时,他先是强调“时尚的审美精神是在肉身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自然生长的意思很简单,即精神是在我们的肉身经验中自发出现的,而非先有个思想,再硬塞进我们的头脑中。”[18]肉身就是自我,就是审美精神的起源。从这个角度看,生活就是不断肉身化的过程。正是“通过肉身化方式”,审美精神才获得了个性和超越性。由于这些大胆之论,生活美学也开始彰显其身体维度。这是生活美学获得自我意识的标志。只有充分揭示生活于身体的关系,生活美学才能将自己确立为一个具有当代性的学派。从这个意义上讲,属于生活美学的身体转向还应深入下去。
四、结语:身体转向与身体美学的位置
在一种当代性的背景中,中国美学的主要流派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身体转向。这个过程虽然还远远没有完成,但已经形成了一个交叉地带。这就是身体美学。实践美学、生态美学、生命美学、生活美学都以某种方式通达身体美学,身体美学则因此成为理论建构的枢纽。如果说当代中国美学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原群落,那么,它的上升和下降都至关重要。从理论分工的角度看,身体美学可以直面一系列涉及自我认识的硬核问题:当生理学、认知理论、AI工程发展到了今天,应该如何定位人本身?是含混地谈论灵肉之争或身心和解,还是选择更为彻底的立场?如果人类身体、智能机器、动物生命之间出现了主体间性,又应该怎样理解它们的关系?在电子人、虚拟身体、赛博空间等词汇日益流行之际,我们需要怎样筹划美学的未来?这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必将升格为后人类语境中的主题,而它们的解决无疑需要身体学的介入。只有当身体学提供了具有足够解释力的图式,当代美学研究才能获得实质性的进展。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身体美学的出现绝非偶然:它既是某种内在需要的产物,又是对前者的积极响应。
随着信息化教学的普及与发展,对信息技术辅助教学的认识角度也从关注媒体到关注教学再到关注幼儿。信息技术与幼儿园课程的融合是各种教学资源和教学要素的有机集合,使整个教学系统保持协调一致。[1]要从整个教育活动出发,借助信息化资源和教学媒体作用于幼儿园活动的各个层面,使之成为幼儿学习环境的一部分。信息技术与课程融合的模式主要是“情境—探究”模式,有创设学习情境、激发自主探索、增进互动交流、尝试验证和意义建构四个过程。[2]学习情境的创设和自主探究都需要资源的支持,而且这些资源的组织是网络化的、开放性的。
参考文献:
[1]李泽厚.美学四讲[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45.
[2]王晓华.身体-主体的缺席与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共同欠缺[J].学术月刊,2011(5):96-102.
[3]朱立元.略论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哲学基础[J].湖北大学学报,2014(5):25-33.
[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56.
[5]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M].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Inc,2007.
[6]张玉能.人的自身生产与身体美学的建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3):41-48.
[7]Terry Eagleton.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s[M].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90:202.
[8]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J].文艺研究,2007(4):15-22.
[9]Jardins,Joseph R. Des. Environmental Ethics[M]. California: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1993:177.
[10]海克尔.宇宙之谜[M].苑建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
[11]曾繁仁.生态美学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12]程相占.论身体美学的三个层面[J].文艺理论研究,2011(6):42-47.
[13]福柯.词与物[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14]潘知常,范藻.“我们是爱美的人”——关于生命美学的对话[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6(3):80-88.
[15]范藻.回归与超越:生命美学之于生命美学的意义[J].徐州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6):64-70.
[16]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M].倪梁康,张廷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182.
[17]刘悦笛.“生活美学”的兴起与康德美学的黄昏[J].文艺争鸣,2010(3):12-20.
[18]张宝贵.都市时尚的肉身狂欢与审美精神[J].上海文化,2017(4):97-10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身体艺术研究”(17BZW067)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晓华,博士,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编辑:宋国栋
标签:美学论文; 身体论文; 生命论文; 生态论文; 维度论文; 《美与时代(下)》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主体论美学视野中的西方身体艺术研究”(17BZW067)论文;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