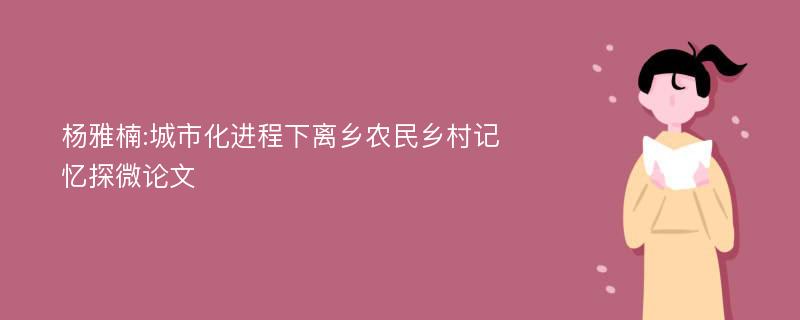
摘要:乡村记忆不随着空间的改变而流逝,它通过一些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式,将其记忆形象联系于离乡农民的实践情境里,并形塑了支配其行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对离乡农民的城市生活有着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城市离乡农民进行个案访谈,探析城市化进程下乡村记忆对离乡农民的角色作用,以帮助营造城市中体现乡村记忆的空间,试图解释乡村记忆对离乡农民及对构建和谐美好社会的意义。
关键词: 乡村记忆 ;离乡农民;城市化
费孝通先生说“乡土社会是安土重迁的,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社会。不但是人口流动很小,而且人们所取得资源的土地也很少变动[1]”。然而,劳动力的大量流动、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却成为现今中国的最基本事实之一。1983年,费老首先提出“苏南模式”[2],不久又提出“温州模式”[2],这两种模式皆是针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人口流动形态和乡村现代化的路径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的“苏南模式”,“离土又离乡”的“温州模式”都是具有现代化意义的指涉。但随着城市化进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现代性的进一步蔓延,农村空间压缩、城市空间延展的一系列改变,农村人口日益频繁穿梭于城市间,“离乡”现象越来越明显。这时,离乡农民在城市的生活将会面临各式各样的新情况。
在社会学视域下,社会化是一个重要概念,即一个人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3]。个人在与社会的互动中习得文化,文化形塑着个人,在个人身上将文化延续和传承是社会化重要的一个环节。农民在成长生活的乡村环境中进行着个体的社会化,社会化所赋予农民一套由个人习得的乡村文化传统,存于个人的身体里,表现在个人的行为中。这样,内化于个人的乡村文化传统,以有形或无形的文化形式,影响着新城市环境中生活的离乡农民,在新的空间中,他们的乡村记忆开始显现。
一、对离乡农民与乡村记忆的认识
(一)离乡农民的内涵
农民进入城市,从户籍制度上来看,他的户籍身份可能会发生改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本文观察点基于城市化进程冲击我国传统城乡二元分立模式,从而造成农民生活地域空间改变,大量的农民愿意离开家乡,进入城市这一现实。因此,文中“离乡农民”是指离开农村和土地,进城从事非农业劳动,但户籍仍在农村的农民。由于受教育程度低,他们所从事的大都是职业层次低且收入很不稳定的非农业劳动领域。同时,离乡农民可能完全没有城市经历,也可能是有一定的城市生活经历者,在城市里属于边缘群体,在城市生活中他们可能面临着一些困难,需要被关注。
(二)乡村记忆的内涵
要厘清乡村记忆,必须将其回带到原生概念——“集体记忆”中去。社会学中研究集体记忆的开拓者是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他在1925年《记忆的社会框架》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集体记忆”这一概念,他认为集体记忆是我们群体认同的活生生的过去,而集体记忆的根本在于其当下性,它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将“集体记忆”定义为:“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4]”。他指出,集体记忆的本质就是当下性,人们如何构建和讲述过去的故事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目前的利益、理念和期望。回忆是为现在的需要而服务的,过去和现在却是断裂的。“过去的记忆并不是真的过去,而是为了现在所构建的过去,回忆是在现实情况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这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研究的立足点[5]”。“当下性”和“建构性”是哈布瓦赫集体记忆最显著的两个特征。
根据紫红百香果果汁香气成分分析结果,并结合朴却香料分类原理和人工感官分析,确定百香果果汁香精的初步配方A,如表3所示,该配方A香精的感官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来看,国外学界可能受到西方社会城乡界限不明显和西方社会学理论重视城市社区研究传统的影响,围绕乡村记忆进行的研究较为少见,但也有不少研究者在进行理论或实证研究的过程中对乡村记忆有所提及。如约翰吉利斯才用“乡土记忆”的概念表示民间基层记忆;斯科特对马来西亚村庄的研究中,提出贫困的村民创造出一种“记忆中的经济”,以此来谴责机械耕作的负面影响[7]等。国内学者如郑杭生、张亚鹏探究社会变迁中的乡村记忆,认为社会记忆在社会转型中也在发生着转型。他们将乡村记忆描述为“乡村存在与流变的历程记载,构成其文化的精神脉络和灵魂核心,是乡村在历史嬗变过程中,从村民的共同生活体验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与思想形态,由此形塑了支配村民行动的思维方式与价值取向,是乡村共同体的粘合剂与文化遗产[8]”。贺雪峰将乡村记忆作为一种分析农村性质的标准,以乡村记忆强弱的差异作为背景对农村社会运行情况进行分析。最早提出以乡村记忆和村庄精英二维主线建构起理解村庄性质的分析框架,建构了四种理想类型的村庄,并对其中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类型的村庄进行调查研究[9]。
(三)离乡农民乡村记忆问题的提出
乡村记忆是集体记忆的一种特定类型,是限定在农村社区这一特定地域空间内的村民群体所共有的记忆。保罗·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开篇就提出群体记忆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有某种灵活性,既包括小的面对面的社会(如村庄),也包括宽广拥有领土的社会,其多数成员不能彼此亲知(如民族国家和世界宗教),对乡村记忆的研究成为集体记忆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6]。他主要从社会记忆角度对乡村记忆的变迁进行描述和解释,强调乡村记忆所承载的村庄价值体系与乡土社会传统秩序规则对村民生活与行为的影响与塑造。
农民在乡村共同生活、相互交往、生息繁衍,形成了具有共同认同感与亲密关系的地域群体。农民的共同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内容建构了农民对乡村的回忆,这些记忆通过仪式等载体得到保存,并在农民间的互动与交流中实现传承,形成了农民关于乡村的集体记忆,可以称之为乡村记忆,它是乡村留在每个农民身上的印记,也是农民对于乡村认识与情感的外显。本文寻找离乡农民在城市社会里生活所显现的乡村记忆印记,探析其角色作用。
来自四川自贡的90后小伙孙某,作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毕业后就留在城市,和女朋友在城市租了一室一厅的老房子。由于两人都在银行工作,孙某还是大客户经理,收入在很多人眼里已经不错了。他说,其实自己的领导就是四川人,对他也挺好,希望能融入城市,在这里扎下根。但是,他就觉得在城市的生活其实是物质的,很多人花了几个月工资就买个包,不是很习惯,而且根本无法融入当地社区,在城市除了上班就是回家,感觉生活圈很小,过节都没什么节日的气氛,尤其是到自贡灯会的时候,以前都会在家自己扎彩灯,现在都没有时间,好想再回家乡过下“灯竿节”。有时候跟女朋友吵个架都不知道能去哪里。虽然收入好,但他还是打算考一考“大学生村官”,回乡创业发展,他很是怀念村子里质朴的生活,村里的生活不像城市那么物质,感觉自己的存在并没有什么价值。
二、离乡农民的城市生活现状——乡村记忆的印记
康纳顿认为记忆是具有传递性和延续性的,并强调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是记忆的重要特征,通过仪式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离乡农民的乡村记忆来源于生活,长久的生活记忆在城市中变成了离乡农民的乡村记忆,并在城市生活中继续传递、延续。因而,要营造城市“乡村记忆”的空间,必然要选择一种可以从城市土壤中滋生乡村记忆绿芽的方式来实现,笔者认为,此种方式即为传统民俗活动。传统民俗活动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文之美、乡村之美的体现,它展示着中华文明的妁妁其华、承载着离乡农民对故土的思念和文化自信。
来自湖南怀化农村的蔡某,43岁,从事城市餐饮服务业工作,当初吸引她来城市当餐饮服务员的原因是城市餐饮行业一般都“包吃包住”,加上同村人大都是从事餐饮服务的工作,收入不错,让她下定决心到城市来。但来了以后发现,这里的餐饮服务人员都是些小年轻,对待她态度也不好,有一次,她生病无法出工,她求一位是本地人的同事带她去医院,那人却说医院费用高,她去不起,随便在床上躺两天就好了,这让她很伤心,感觉在城市里连自己的尊严都没有了。以前在家乡,大家有困难都会互相帮助,开耕地、盖楼房、修篱笆等,更不要说生病这样的小事情。在城市越久,她越发怀念家,怀念她在家乡所感受到的温情和集体的力量。
在已查阅的文献研究中,笔者发现以往学者对乡村记忆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村庄变迁中要重视和发展乡村记忆,重构乡村社区,而没有关注到在城市化加速的步调下,离乡到城市的农民是如何被这种乡村记忆所影响的,也没有辨明乡村记忆对于城市里生活的农民有着怎样的作用,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为此,笔者从离乡农民这一群体入手,关注他们所成长的乡村社区所赋予他们的乡村记忆是如何在他们的城市生活里显现的,从文献和第一手资料中探析乡村记忆的角色作用。
来自广西的35岁包工头李某,他的小工队里有大约40人,他们大都来自广西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孩子留在家里由父母照看,夫妻俩出来城市里做工挣钱,再把钱寄回去。小工队居住在工地的集装房里,夫妻可以单独一间,其他单身的则几个人一间,生活虽然条件一般,但还过得去。工友都来自同一个省份,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一起,很有以前在家里的感觉,大家都很开心。他说,刚从家里来城市那会儿,穿的比较老土,城里这些人,根本就看不起他,虽然这几年收入提高了,但说内心话,感觉自己的穿着与城市人还是不一样,感觉出去自己就是农民工,好像有点抬不起头那种感觉。他叫老婆在所住的集装箱门口弄了个像家乡房子门口一样的敬香的灶台,每天敬天地、保出入平安,这是顺着他们家乡的传统习俗,出门在外都有神明庇佑,做事也就会很顺利。他说,再拼搏几年,等为父母存够养老金,为子女挣够学费,他也会考虑在城市里买套房子,接他们来城市一起生活,就不知道他们会不会习惯城市生活。
乡村记忆里的美好,吸引离乡农民回乡,稀释了乡村与城市的分隔,使个人粘合在乡村社区里;乡村记忆的美好,让离乡农民在城市中找到归属,使个人与同质群体发生关系。乡村记忆总是在离乡农民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粘合的角色。
在分析离乡农民乡村记忆时,不仅需要从乡村记忆承载主体——离乡农民群体出发,认识到以往的记忆所扮演的教化、调控、粘合角色对其进一步认同城市文化、融入城市生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还要从乡村记忆存在客体——城市场域入手,考究城市中是否有深化离乡农民乡村记忆的空间场景,使乡村记忆的角色作用有效发挥的问题。众所周知,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是截然不同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也体现于生长在生活方式之上文化习得中。因此,离乡农民进入城市,其生活或多或少都遭到了现代化的排斥、被边缘化,原有的一套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趋于式微。不仅是城市社会的旁观者,更是城市文化的旁观者。要改变这样的社会事实,需从主观能动性的角度出发,让离乡农民在城市中有“主人翁”的意识,不以“外来者”自居,在城市中为其营造一个熟悉的、优良的“乡村记忆”空间,使他们以往在家乡所拥有的美好情感在城市的场域中得到释放,利于离乡农民与城市的良性互动,利于舒畅两者间的沟通关系。那该如何营造离乡农民乡村记忆的城市空间,实现以上目标,关键在于三点。
三、乡村记忆在离乡农民城市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
基于文献回顾以及笔者的调研,发现第一二种困难已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政府已出台相关法规政策保证离乡农民的合法权益,但对于第三个困难的解决却呈现有心无力的局面。在笔者的调研中发现,若要第三个困难解决,需靠离乡农民在之前生活乡村里社会化习得的文化去弥合,使得具有流动性的离乡农民在城市逐步稳定,让以往关于乡村的记忆在新的、充满挑战的空间中被唤起,以帮助离乡农民在城市中有安全感,帮助其在城市生活,适应城市节奏。为此,厘清乡村记忆在离乡农民城市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旅游业的发展经历了从单一入境旅游市场,到入境旅游、国内旅游两个市场并举,再到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三个市场全面发展的过程[4]。与此相应,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发展战略也经历一系列的调整变化,现定位为“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4]。
(一)乡村记忆扮演教化角色
说是乡村记忆,其实从深处剖析就是离乡农民自小在乡村社区社会化中所习得的文化、习俗,这些文化、习俗形塑了离乡农民的思维范式,影响并指导着他们在城市生活的行为。既然是文化要素,乡村记忆也必然在离乡农民的生活中扮演着教化的角色。以笔者的访谈个案来看,蔡某在城市生活中身体不适,她选择向家人求助,帮助她在当地的村庙里求平安,让她尽快康复。这一想法必然是因为在其乡村成长的经历中,受她乡村的文化影响。当她生病的时候,她这一部分的乡村记忆被唤起,让她做出这样的行为。如李某,在城市里生活还仿照家乡传统“祭天地”的设置,以保城市生活平安和顺,也如孙某、阿某对家乡传统习俗节日的怀念。
点对点的业务传输方式可以保证雷达数据的准确性和实时性,在传输过程出现异常(同步串口或TCP)的情况下,可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如若在WAN链路中实现消息压缩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利用有限的带宽保证数据传输快速和有效。
人是文化的产物,人之所以是不同的人,是因为她或他身上所熏陶、所习得文化的不同。因此,乡村记忆作为文化的载体,在超越时空的限制教化着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扮演着教化的角色,离乡农民在城市的生活也必然受乡村记忆中的文化要素教化,并受其影响。
(二)乡村记忆扮演调控角色
乡村记忆中有作为离乡农民在乡村生活所习得的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其中,提供着关于是与非、善与恶、好与坏等社会规范。在城市生活中,这些存在于离乡农民个人乡村记忆里的是非感、正义感、责任感,有助于提高离乡农民的道德情操和认识水平,调控着离乡农民在城市的相关行为。如案例中,蔡某被城市人的同事歧视,但由于有着正向的乡村记忆,她并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选择息事宁人。如李某来到城市,由于衣着问题遭遇不公平对待,以至于在城市生活了几年后还是感觉有人在给他“贴”标签,他也没有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证明自己。
个人在全新的、陌生的环境中所遇到的困难,都会从过往的生活记忆中汲取理性之光,调适自己的心理,选择理性化的方式方法来应对困难。离乡农民以往的生活记忆大都是在乡村承得的乡村记忆,他们在城市里生活应对在城市里所面临的困难,他们会从乡村记忆里选择合理的方式,帮助其渡过。从这一层面来看,乡村记忆在离乡农民的城市生活中扮演着调控的角色,调节着离乡农民的行为。
(三)乡村记忆扮演粘合角色
文化与个人、与群体、与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他们之间相互影响。文化可以维系社会的稳定,每一种文化都可以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在社会生活的时代交迭中,文化被不断传承,保持着积极的连续性。作为文化载体的乡村记忆,在这样的前提下,也扮演着粘合的角色。孙某是一名高材生,在城市也有稳定的工作,有不错的发展前途,但他总会怀念家乡的“灯竿节”,觉得那里有自己的归属,考虑报考“大学生村官”回到家乡去。无独有偶,少数民族的阿某也因为在城市中有相关纪念乡村节日的活动,并拥有同为少数民族的朋友,而愿意在城市发展。其实,不管是希望回到家乡乡村发展的孙某,还是愿意留在城市打拼的阿某,他们身上都留有他们自己乡村的乡村记忆,因此才产生这样的想法。
由图1可知,卤汁1在复卤过程中总酸含量总体上比卤汁2要高,卤汁1复卤过程中总酸最低含量为0.91 g/kg,最高含量为3.88 g/kg;卤汁2复卤过程中总酸最低含量为1.13 g/kg,最高含量为3.79 g/kg。卤汁中总酸变化的原因可能是,在豆干卤制过程中,工厂每天要进行补料和补水,所以总酸会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卤汁1在卤制过程中,总酸含量在2.71 g/kg上下波动;卤汁2在卤制过程中,总酸含量在2.31 g/kg上下波动。而变化不大的原因是工厂每天会对卤汁总酸进行监控。所以总酸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波动[9]。
来自云南楚雄州的19岁彝族女孩阿某是家里的小女儿,上面有两个哥哥,她跟着哥哥和嫂嫂来到了城市工作,由于有高中学历,所以她被招入城市的某剧场做售票工作,工作压力不大,收入还可以。在不上班的时间,她和在网上认识的同是彝族的小伙伴一起组建了个表演队,去参加一些城市商业广场的活动,跳一些民族舞蹈。她下一步打算扩大自己的表演队,丰富自有节目,争取早日进入自己工作的剧场表演。她说,不久之后就是他们民族特有的“火把节”了,她之前在城市参加过两次庆祝火把节的活动,气氛很热烈,大家倾情投入,还有些不是彝族的同胞也积极参加,让她感到自豪,对城市有一种归属感,原来她们民族的文化在城市里会被大家认可喜欢,她很期待接下来的城市生活。
四、 离乡农民乡村记忆城市空间的营造
2) 跨站防误闭锁:实现变电站与变电站之间的闭锁功能,杜绝多变电站同时操作时,线路带电情况下合出线侧接地刀闸的安全隐患。
(一) 再现民俗仪式,延续乡村记忆
离乡农民离开乡村这一自小到大成长的空间,为生活、为发展、为未来,进入到对他们而言是新环境的城市中生活。在此过程中,面对新场域,以往在乡村的习惯被冲击,离乡农民必定会遭遇一些困难和问题。通过文献回顾,发现离乡农民在城市生活普遍面临着三大困难:一是离乡农民找工作难,且大多数工作主要是体力劳动,他们大多靠着卖苦力,干着城市人不愿意干的脏累活,与此同时,还要遭受城市人的歧视;二是离乡农民由于知识水平有限,维权的意识差,经常被用人单位收取额外费用,签订“口头协议”,基本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三是离乡农民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缺乏,城市里的新兴事物对于离乡农民来说可能是一种“文化震惊”,是超越其接受度的,无所适从之感使得他们精神上较空虚,长此以往,较容易诱发恶性事件。上述三点都是据调查材料总结而来,为了更好地了解离乡农民在城市的生活现状,笔者也做了一些城市离乡农民的访谈。
有学者认为,民俗活动具有“群体性、传承性、地域性、寄托性、形象性[10]”的特征,民俗活动是群体创造、认同并遵从的文化形式,世代延续并传承,是人们适应环境、与环境相和相谐的印证,反映了积极的信念理想和直观的情感慰藉,以多元的活动形态丰富着群体的生活。对于离乡农民来说,当跨入城市的那一刻起,他们所拥有的乡村记忆被异质化的文化氛围所消磨,原有习得的乡土文化意义被消解,传统思想被新信息冲击,乡村记忆就只存在于抽象的空间里,现实里不复存在,离乡农民被城市排斥的后果不可想象,可能会有过激的反应或越轨行为的发生,不利于社会的良性运行。
标准化决定了企业的高度。华南公司始终坚持把所有的管理活动全部纳入标准化轨道,按职能类别和业务类别建立起一整套的制度、标准和流程,让员工的一言一行有章可循,一举一动有据可依,每个记录有案可查,每个岗位有责可考。
通过政务办公应用系统公文申请、审查、分发、监控、查阅,实现公文处理网上办理;通过日志列表,实现上级对下属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掌控,推行量化考核管理;通过人名排列详细信息、设置人事权限,访问相应的地图系统、公务系统;通过信息上报系统可将现场巡查的文字、图片、视频、音频等信息在线上传到管理平台,实现实时互动。
为此,社会各界需要充分了解传统民俗活动对传承乡土文化的意义,深刻认识到乡村记忆对离乡农民的角色作用,通过有计划地还原、再现传统民俗活动仪式,营造城市中体现乡土文化的空间,保证离乡农民乡村记忆的“鲜活”,增强与城市的情感联系。例如,逢传统节庆,城市开展大型纪念活动时,承办活动的部门可考虑加入具有乡土特色的表现形式;在平日,可借助城市中博物馆、纪念馆的空余空间,以公益的性质来安排民俗体验活动或开展主题展,或是使用城市社区平台,联合社会组织,在离乡农民的聚集区域,结合该地域的特色民俗活动,邀请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来进行民俗活动。这样一来,不仅增进社会各界对乡土文化的了解度、能更加理解尊重离乡农民的文化异质性,也可以有效利用城市公共空间闲余,节省空间成本和时间成本。
(二) 构建文化网络,重塑乡村记忆
在访谈个案中可以发现离乡农民乡土记忆在城市场域中存在“失落”现象,究其缘由,笔者认为是因为在城市中没有属于离乡农民的文化网络,他们是城市文化的“孤儿”。一方面,在原来村落里,人们世代生活于此,在较封闭的场域中,人们日常交际交往频繁且重复,从而形成了稳定的社会文化网络。这种社会文化网络以无形的形式存在,维持着人们的乡村记忆。但当农民进入到城市后,原有的乡村文化网络在城市中并没有存在,个体与环境间产生联系的桥梁消失,不安感、缺失感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城市中没有任何场景可以回应离乡农民的乡村记忆,使其情感得到释放,乡村记忆缺少被感知的空间。
正如哈布瓦赫所认为的那样“只有社会中人们才能回忆、识别和定位记忆”,离乡农民的乡土记忆需要一个空间,在此城市社会空间中,乡土文化网络被城市空间接受,城市文化网络也会被离乡农民所认知、记忆,他或她的乡村记忆被重塑,离乡农民的同质文化网络被构建,离乡农民能自由地“识别”和“定位”特有的乡村记忆。由此,营造城市中乡村记忆空间最好的方式就是让离乡农民在城市中拥有一个与原有文化网络较相似的文化网络,可以保存原有乡村记忆情节,使乡村记忆继续扮演好教化、调控、粘合角色,使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在笔者看来,让离乡农民在城市中拥护一个有乡土气息的文化网络的关键在于教育和宣传,若解读文化网络,可发现其核心有两点:一是“人”,二是“文化”;人是文化的承载体,文化是人生活意义的表达。离乡农民文化网络的构建靠对人的教育和文化的宣传,这里的“人”指的是城市居民和离乡农民,对城市居民来说,需要教育他们承认文化是有差异,而无优劣的,学习理解离乡农民的文化传统,尊重乡土文化;对离乡农民来说,需要使其意识到文化是可以相互融合的,城市文化和乡土文化有互通性,在新的城市场域中,乡村记忆可以被接纳。通过对城市居民和离乡农民的教育,文化的宣传在此过程中得以进行,文化在人群之中被知晓,潜移默化地让城市居民和离乡农民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体验到乡土文化所蕴含的历史精粹。
(三) 植根政策支持,振兴乡村记忆
习近平同志任福建省长时期,曾指出城市具有带动辐射作用。在社会发展的道路上,城市不应该“独善其身”,应自觉地承担责任,将所拥有的正能量“辐射”出去,支持农村的发展,实现资源和发展成果共享。中央政府也在十九大的报告中强调了“乡村振兴”战略,乡土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成为集体共同的文化记忆,振兴乡村记忆,其实就是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城市的物质基础较乡村来说必定充裕,但在非物质方面却也是旗鼓相当的,离乡农民的乡村记忆也必定存遗着文化的精华,值得重视。
在城市有能力、有机会为其提供生长的土壤时,需要植根政府的各项宏观政策文件,不遗余力地扶持与帮助,从传统文化保护、公共文化服务、行业扶持、市场监督、文化交流等方面营造离乡农民乡村记忆城市空间,将文令条规落实到实际行动中,振兴乡村记忆,帮助离乡农民融入城市生活,体现城市应有的担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在城市营造特有的乡村记忆空间,回归乡土文化的原貌,将既往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与城市生活紧密联系,加大乡土文化与城市文化的融合交流,让离乡农民对乡土文化有自信感,增强离乡农民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使其在城市生活中有踏实感,从而为城市文化发展创造新的活力素,并提升社会的凝聚力。
五、结束语
离乡农民的乡村记忆中暗隐着乡村历史的印记与乡土文化的传承,它不是一个静态的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新的城市场域下对其乡村记忆进行解读、提取,使得乡村记忆被不断唤起、不断传递,属于离乡农民乡村记忆的城市空间,将承载着离乡农民最纯粹的情感,乡村记忆历久弥新。
式中,α0表示纯气体在吸收线中心的吸收系数,νg和δν分别为对应吸收线的中心频率和吸收线半宽。当光源输出中心频率精确锁定在甲烷气体的吸收峰即ν0=νg时,将式(3)代入式(2),可得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7-8,50-51.
[2]费孝通.小城镇四记[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
[3]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41.
[4]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译.上海:仁海人民出版社,2002.
[5]吕雪.社会变迁中的乡村记忆:以安徽Z村为例[D].合肥:安徽大学,2015.
[6]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 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9-18.
[7]邓祺. 延续与分化:转型期乡村记忆的传承机制及启示[D].合肥:安徽大学,2015.
[8]郑杭生,张亚鹏.社会记忆与乡村的再发现:华北侯村的调查[J].社会学评论,2015,3(1):16.
[9]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J].社会科学辑刊,2000(4):34.
[10]尹伊君,王国武.民俗文化的特征、功能与传承[J].学术交流,2009(11):204.DOI:10.3969/j.issn.1000-8284.2009.11.054.
[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RuralMemoryundertheProcessofUrbanization:AnAnalysisofMigrantPeasants
YANG Yanan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Law and Politics,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Rural memory does not pass away with the change of space. Through its tangible or intangible cultural forms, the memory of the rural links its memory image to the practical situations of the peasants who leave home and shapes the way of their thinking and values.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urban life of the migrant peasant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rural memory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order to help reconstruct the space of rural memory in the city. It is helpful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ignificance of rural memory to the peasants who leave the countryside an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Keywords: rural memory;migrant peasants;urbanization
收稿日期:2018-09-17
修回日期:2018-10-16
网络出版日期:2019-01-17 16∶27
作者简介:杨雅楠(1993—),女,云南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政策研究。
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53.1044.s.20190117.0958.014.html
DOI:10.3969/j.issn.1004-390X(s).2019.01.007
中图分类号:C912.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90X(2019)01-0035-06
标签:乡村论文; 记忆论文; 农民论文; 城市论文; 文化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论文; 《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论文;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