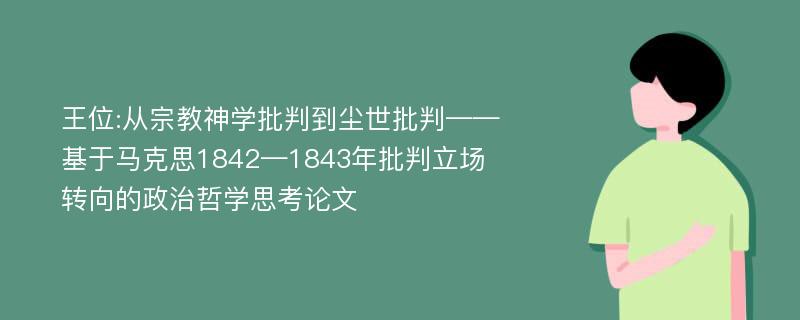
摘要:1842年《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在政治哲学思想、国家观念上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的影响,在批判立场上强调通过对宗教神学的批判,使国家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进而实现理性国家的归复;1843年,马克思意识到尘世现实问题与理性国家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矛盾和冲突,于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1842年所追捧的黑格尔理性国家理论,展开对整个政治领域的彻底的批判,并走向彻底的革命,实现了从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到对尘世批判的转向。
关键词:马克思;黑格尔;批判立场;转向
如果我们着手于研究青年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思想,我们会发现:1842—1843年马克思的批判立场,存在着从针对宗教神学、神学政治的批判向针对尘世批判的转变,而这一转变的实现源于1843年夏天——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完成。从这里开始,马克思意识到以往的在1842年所追随的那种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道路只是一种乌托邦幻象,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因此,如果说要实现自由与解放,那么就必须抛却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从而展开对整个政治领域的无情的、彻底的批判而走向彻底的革命。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批判的视角转向自己在1842年还追捧和信奉的黑格尔理性国家理论,正是在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那里,马克思在政治领域抛却黑格尔法哲学的身影,而进入到彻底的革命。
一、1842年马克思对宗教神学的批判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在中世纪的欧洲,对国家政治层面而言,基督教神学是占统治地位的,因此,很少有人从自由理性层面来思考国家的政治问题。而理性主义的产生是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以后,人们才逐渐从人的理性存在角度出发进行独立的思考和选择。理性主义主要代表人物笛卡尔、斯宾诺莎以及莱布尼茨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真知识都不能从感觉经验得来而只能起源于理性本身。”这相对于中世纪的封建性的神学政治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一种“伦理理念的现实”,是一种理性的东西,而这种理性又是绝对的自在自为的,是自由意志的最高体现,第一性的应该是绝对观念,而对现实世界、现实国家而言则从属于这种绝对观念,个人本质、个人的利益是从属于国家的,而国家是“个人的真正的自我客观化、现实化。”国家作为现实的普遍性以及庞大的整体性的机构,是个人追求的普遍目的,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作为法律、伦理以及政治的自由,必须在这个庞大的整体性的机构里才能最终实现。而对1842年的马克思而言总体上作为黑格尔信徒,在国家观念、政治哲学思想上深受黑格尔的影响,这一时期马克思很多著作中都能看到黑格尔理性国家的存在,更多的是强调把政治之物从神学那里解放出来,强调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进而实现理性国家的归复。
(一)批判宗教神学并肯定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合法性
1.马克思认为哲学与宗教神学之间应该进行公正的分离
“转动课堂”教学模式下如何提高大班授课效率的教学改革,目前有比较重的任务、有很多困难需要面对,许多条件还需要探索。但经过研究与实践,证明在“生物化学”中引入此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氛围好、学习态度积极,真正实现了课堂上学生的主体地位。大部分学生对“生物化学”课程也有了新的认识,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都有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学生的成绩也有大幅度提高。
首先,马克思强调两者的追求和使命在本质上是相互区别的,“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本性而不存在人的一般本性吗?哲学是问:什么是真实的?而不是问:什么是有效的?”马克思认为宗教神学强调的是一种强制性与服从性,在当时社会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基督教的奴役和压迫,而在哲学这里则强调的是对真理知识的追求。“你向人们许诺天堂和人间,哲学只许诺真理;你们要求人们信仰你们的信仰,哲学并不要求人们信仰它的结论,而只要求检验疑团;你们在恐吓,哲学在安慰。”所以,马克思认为哲学与宗教神学在使命目标上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应该强烈地批判宗教神学对国家的这种强制性束缚,实现哲学的理性追求。其次,马克思认为两者在认识和谈论问题的路径、形式上是不同的,哲学是一种理性的工作,因此它谈论和认识问题的方式也必然是理性的,对宗教神学而言采用的是一种自我感情色彩的路径,是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你们没有经过研究就谈论这些问题,而哲学是在研究之后才谈论的;你们求助于感情,哲学则求助于理智;你们是在咒骂,哲学是在教导”。因此,马克思认为宗教神学和哲学的区分点关键不在于纠结它们该不该谈论或者介入政治,而在于二者所遵循的形式,哲学强调以理性的形式来认识问题,更应该有权来关注国家和政治问题。哲学与宗教神学之间在使命、认识问题的形式上是截然不同的。
1842年马克思还在宣传理性国家思想,追寻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道路,到1843年马克思逐步认识到理性国家思想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幻想,与青年黑格尔派理性国家的乌托邦决裂。马克思开始谴责政治革命,而赞成一种彻底的革命。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对于德国来说,彻底的革命、全人类的解放并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只有部分的纯政治的革命,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的革命,才是乌托邦式的空想。”马克思在德国的经验中得出,政治解放是革命阶级解放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纯粹的政治解放形式是有限的。马克思强调:“即使人已经通过国家宣布自己是无神论者,即宣布国家是无神论者,但他还是受宗教的限制,这正是因为他只是间接通过中间环节承认自己。”只把纯粹的政治领域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不能治愈社会疾病的,政治解放与人的解放是不一致的,把政治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没有把人的观念从宗教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国家已经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了,而国家的公民依然有可能受到宗教的束缚。纯粹的政治解放,是从一部分条件出发的,狭隘的解放,忽略了历史条件和境遇,而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必须进行全人类的,彻底的革命。
《共产党宣言》中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和内容,其中关于全球空间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了,而对于全球空间的形成、发展、现状分析以及其形成意义的论述成为《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构成,这对当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首先,马克思认为:“看来,人世的智慧即哲学从一开始就比来世的智慧即宗教更有权关心现世的王国——国家”。马克思指出,海尔梅斯在讨论宗教以及政治问题的时候采取的是极端保守的立场,海尔梅斯认为宗教的兴衰对民族国家的兴衰起决定性作用,任何反对宗教以及对宗教的攻击就是直接反对国家,构成国家基础的不是宗教,而是作为现世智慧的哲学,强调哲学在政治领域的作用,认为哲学作为一种理性的工作才更适合谈论和认识国家问题。其次,马克思指出:“如果宗教变成了政治的因素、政治的对象,那么,再来谈论报纸不仅可以而且应该讨论政治问题显然是多余的”。哲学与政治是相互独立的,哲学质问政治领域的合法性在于建立在它独立的基础之上,宗教神学与政治共同体之间也应该相互独立,而不应该将宗教变成政治因素最终驾驭整个政治团体,在这个独立的基础上国家的本质应该从国家自身内部去寻找,而不是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质来规定。马克思批判神学与政治的联接,并强调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合法性。
(二)批判宗教神学并指出哲学在政治领域的作用
首先,马克思建立了私人利益的立足点和国家利益立足点之间的分裂,马克思把国家的逻辑定义成一种与私人利益逻辑相反的自觉组织领域,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一个独立的、宏伟的领域。如果把国家降低到私人利益或者私有财产的狭隘的维度来思考和认识,这对于国家而言是一种贬值,国家将失去它原有的身份,失去它特定的、独立的存在方式,甚至放弃国家原本的手段、职能和国家应有的灵魂之间的联系,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制度的堕落、国家与私人利益这两个异质的秩序之间的混淆。其次,对于私人的利益原则而言,马克思提醒林木所有者,“和国家相比,一棵最大的树木也抵不过一根树枝。”因此马克思认为不应该是“权利”和“自由”灭亡,而应该是“私人利益”灭亡,强调国家所做的应该是为私人利益提供一种保障,但是这种保障应该是有一种普遍性的、有界限性的保障,国家不能为私人利益而失去自己的、本应该有的正义性。最后,在马克思看来,现实社会中存在私人利益逻辑和政治代表逻辑之间的冲突。从私人利益逻辑的角度出发,政治主体被消解以此来支持所有者的专制性的主体;而从国家的逻辑角度出发,那就存在着私人利益的一种变形,私人利益在国家领域中的安置,会让它遭受一种精神化,化约私人利益的外在性,而这里化约的关键不是要压制私人利益,而是要把它带到国家的层面,带到国家的自由和正义精神的环境中。在马克思1842年后期,马克思已经开始意识到现实物质利益与理性国家之间的冲突,但是总体上来说马克思此时仍然是一个政治唯心主义的或者说是政治高度的理论家,他所强调和支持的是一种政治解决,也就是强调总体性的合理性,超越简单的表象来解决物质冲突。马克思对物质利益、现实社会与理性国家冲突的发现,对私人利益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这种认识和界定,推动了马克思在1843年批判立场的转变。
2.从教育本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性。随着高等教育普及率日益提升,高等教育的供给数量得到了极大丰富。但以陈晨明为代表的一批学者通过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跟踪分析,发现高等教育的供给质量没能有效提升,出现了人才培养供需之间不一致的现象,主要体现在学校给予求学者的知识技能与求学者潜在的知识技能需求不一致、与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的工作岗位技能需求不一致,即高等教育在人才培养方面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现象。具体到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专业设置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不匹配,课程资源建设内容与行业企业对知识技能的要求不匹配,求学者的实操技能与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不匹配。
二、1843年马克思的批判立场转向对尘世的批判
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普鲁士政府开始对新闻出版自由进行全面的压制,青年黑格尔派由分歧走向分裂,马克思意识到现实问题、现实物质利益问题与理性国家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和冲突,理性国家严重偏离现实基础,动摇其理性主义幻想。正是这种对现实的状况、物质利益的认知,使得马克思意识到以往的在1842年所追随的那种黑格尔的理性国家道路只是一种乌托邦幻象,它在最根本的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因此,马克思在政治领域抛却黑格尔法哲学的身影,展开对整个政治领域的无情的、彻底的批判而走向彻底的革命。
2.马克思认为,批判宗教神学的目的在于实现理性国家的归复。“差不多和哥白尼的伟大发现(真正的太阳系)同时,国家的引力定律也被发现了:国家的重心是在它本身中找到的……不过先是马基雅弗利、康帕内拉,后是霍布斯、斯宾诺莎、许霍·格劳秀斯,直至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则已经开始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从理性和经验出发,而不是从神学出发来阐明国家的自然规律”。马克思在这里强调国家的重心要从它本身当中去寻找,而不是从神学的角度,他从一个思辨的角度去构造了国家概念的独立性,用人的眼睛来思考和认识国家,去揭示国家内在的本身的规律,而这种思辨角度的关键意义就是强调理解国家逻辑,那么国家就必须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从社会理性的角度出发去构想国家,实现其独立性。马克思在1842年的批判立场是站立在自由理性的基础之上,对宗教神学的一种批判,强调的是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建制性作用,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政治共同体从神学中的解放,实现自由理性的国家。因此,此时的马克思仍然没有脱离黑格尔法哲学身影。
(一)对私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合理性关系的重新界定
1.马克思指出,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工作是把政治共同体从宗教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不应该根据基督教,而应该根据国家的本性、国家本身的实质,也就是说,不是根据基督教社会的本质,而是根据人类社会的本质来判定各种国家制度的合理性。”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本身的实质不能根据宗教来规定,而是根据社会本质来规定,马克思反对关于国家的经验性发生,强调一种社会理性,把国家看成一个巨大的有机总体,按照概念去思考国家,并承认其社会作用。“哲学在政治方面并没有做物理学、数学、医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在自己领域内所没有做的事情。”在马克思1842年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线索,马克思指出,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工作和其他的科学一样,就是把政治共同体从神学专制的束缚中解救出来,而解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政治领域自身专有的连贯性,这种解救的实现是需要从人的关系那里推出来的,而这个推出又是由哲学去完成的。
(二)对尘世的批判强调彻底形式的革命
2.马克思强调哲学在政治领域的合法性在于它的独立性
(三)对尘世的批判强调去除国家的神圣性
首先而言,这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与以前国家观的决裂,这种国家是一种按照无限的、自我规定的主体的模式来规定,整合一切外在性,并且与自身相符的国家。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念:“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的。”黑格尔的这种观点是强调政治制度与抽象理念的关系,马克思强调这是一种神秘主义,在这里市民社会本身而言是不具有现实性的,市民社会上升过渡到国家也只是一种观念的生存过程,而不是市民社会本身的生存过程,国家在这里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这种生存过程也是一种脱离现实基础的神秘过程。其次,马克思极力反对把政治领域、政治结构神圣化,这种神圣化认为政治领域、政治空间应该是从基础,即世俗生活垂直地上升到国家的过程,国家也就是最高的天堂。而马克思力图从多个方向、多个点出发,而不是仅仅的世俗生活,去重新组合政治领域、政治空间。在这里马克思意识到理性国家思想的本身脱离现实基础,国家与政治空间成了另一种神圣化了的存在,缺乏实现的现实基础,而力图打破这种神圣结构,并去除国家的神圣性。
进行设计期间,结合分析数据采取对象图和包图来对据点能管理系统做相应设计,此期间主要考量各因素成分关系,并对其关联性和依赖性进行实时划分,注重酒店各部门系统子系统特点,以及其所组成系统包。比如前台包、客房部包等,客房部客人往往是根据前台而来,因此注重相互之间的连续性和协调性便显得极为必要。
(四)对尘世的批判强调现实的实在性
首先,马克思指出从宗教批判转变到政治批判,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任务应该是:“去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对尘世的批判。”马克思1843年对黑格尔国家观进行了批判,颠覆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强调批判任务的现实性,指出批判就在于使每个特殊形式无论是理论意识还是实践意识都趋向现实的实在性。其次,马克思强调以现实为主体,市民社会、人民才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强调政治批判不是背离政治问题,而是站在现实的立场去穿透政治问题。最后,马克思认为批判要解决黑格尔没有解决的国家的两个规定之间的背反问题,一个方面是国家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和家庭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关系,另一方面就是国家是二者的内在目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表现为国家的二元性。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是真正积极的东西,但它是在思辨哲学逆转。”马克思强调家庭和市民社会在国家现实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国家应该是人民的,国家是市民社会的,而不是黑格尔的观念的国家,在批判过程中马克思纠正了黑格尔搞混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实现了自身立场和批判的转向。
三、结语
在1842—1843年马克思早期的思想历程中,其批判立场经历了从针对神学政治的批判到对尘世批判的转变,1842年《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思想在总体上来说仍然是黑格尔的信徒,是黑格尔理性国家观的推崇者和信仰者,强调的是对宗教神学的批判,追求的是理性国家的归复。到1843年《莱茵报》被查封,马克思开始反思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并写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彻底地颠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观,批判的矛头转向黑格尔理性国家思想和政治领域本身。总的来说,马克思批判立场转变的研究,对于研究马克思早期思想历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陈修斋.欧洲哲学史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
[3]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裴森,郭华.青年马克思理性主义国家观探析[J].哲学世界,2009(1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龙佳解,罗泽荣.论马克思的国家批判理论及其价值旨趣[J].理论学刊,2013(04).
From the Criticism of Religious Theology to the Criticism of theWorld——Politicaland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ased on Marx's Critical StandpointTransition from 1842 to 1843
WANGWei
(Marx Schoolof Southwest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Yubei,Chongqing 401120,China)
Absrtact:In 1842,Marx in the Rhine newspaper period did not completely get rid of Hegel's influence in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state concept.In his critical position,he emphasized that through criticizing religious theology,the state could get rid of the bondage of religious theology and realize the return of rational state.In 1843,Marx realized that therewere great contradictionsand impulses between the realistic problems of the world and rational countries.Suddenly,he pointed his criticism at Hegel's rational state theory,which he soughtafter in 1842,launched a thorough criticism of thewhole political field,and went to a thorough revolution,which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from criticism of religious theology to criticism of theworld.
Keywords:Marx;Hegel;Critical Position;Turn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9.09.034
中图分类号:A81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9)09—0139—04
收稿日期:2019—05—17
作者简介:王 位(1994—),男,重庆酉阳人,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责任编辑:马妍春]
标签:马克思论文; 国家论文; 黑格尔论文; 政治论文; 神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列宁主义论文; 毛泽东思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理论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恩格斯著作的学习和研究论文;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9期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