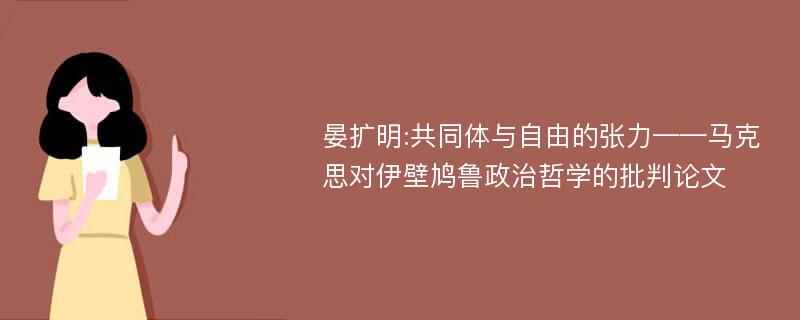
摘要:共同体的价值与自由的价值能否相容,是认清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批判与继承当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对共同体与自由之间关系的梳理和阐释。一方面,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认为真正的自由只能通过在共同体中积极的社会实践来实现;另一方面,马克思从价值层面出发,将“共同体”视为一种内在于人的本质属性的价值,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将自由的实现与人类共同体的实现融汇到一起,论证了二者的统一性。以此出发,在对伊壁鸠鲁式的消极自由进行批判的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应当代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价值断裂问题。
关键词:共同体;自由;伊壁鸠鲁哲学;唯物史观;价值
从古希腊城邦的公共生活,到现代民族国家的代议制政体,政治哲学家们对共同体理论的建构从未止息。“共同体”就其所指涉的政治形态而言可以包括部落联盟、国家等;就其所指涉的生活领域而言则包括伦理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政治共同体、社会共同体等。无论共同体的形态如何变化,其所指向的都是人类赖以存在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随着经典社会理论家以及社群主义的当代兴起,除以往关于共同体的历史形态的讨论之外,关于“共同体”的价值层面的论争也逐渐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因此,若以“共同体”概念本身为研究对象作出梳理和划分,就应当把各种复杂的“共同体”概念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共同体的外在形态的探讨,即何种共同体(或者何种程度的共同体)是好的共同体,人们是否生活在某种特定的共同体模式之下,以及现实的人类生活环境是何种程度的具体的共同体形态;二是一种关于“共同体”的内在价值的探讨,即“共同体”是否是一种由人的本质出发引申出来的,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的价值。也正是在这种划分之下,“共同体”才能够与“自由”在价值层面上进行对话。
可以说,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就是从具体的共同体形态与抽象的共同体价值这两重意义上来分析人类社会的。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如何看待共同体与自由之间的关系,就要首先对马克思的共同体理论进行“形态”和“价值”的理论区分,进而将共同体之“价值”抽象出来,去解读马克思意义上的共同体与自由之间的张力。如果赋予共同体更宽泛的内涵,那么共同体与自由之间可能并没有大多数社会学家们所表达的那种冲突和矛盾,甚至可以说,回归共同体和回归人的自由本性是趋于一致的。在这种意义上重新审视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就会发现马克思对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内在联系所进行的重构。这种重构最早体现在马克思对伊壁鸠鲁政治哲学的批判之中。
第二,东道国制度在发挥中国OFDI经济增长效应时有着重要的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只有东道国制度质量越过拐点,中国作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直接投资活动才能够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否则,这一相互作用将严重阻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但由于中国目前对“一带一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活动有相当比例集中在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若想这部分投资收到预期的经济效果,必须重视东道国制度的作用。
至于“一鹤冲天”,张三爷则说:“当时我急中生智,用尽平生之力蹬踏坐马,借劲上蹿,抓住一块突出的岩石,脚蹬手爬,爬上山顶的。当时腿也撞伤了,手也磨破了。”
一、伊壁鸠鲁对“共同体”与“自由”之间张力关系的理解
伊壁鸠鲁在对古希腊城邦哲学做出批判时,对“共同体”与“自由”的价值关系做出了“原子偏斜”式的解读。伊壁鸠鲁认为,作为“原子”的个人只有偏离作为“共同体”的城邦,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自由”。因此,“共同体”与“自由”的关系在伊壁鸠鲁那里显然是对立的。想要更好地理解这种对立,就必须回归到古典政治哲学的视域当中去剖析伊壁鸠鲁的理论逻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伊壁鸠鲁这种“偏离政治”的政治哲学最终改变了古典政治哲学的研究理路和方法,颠倒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价值观念,实现了由古典政治哲学向后古典政治哲学的转向,对近现代政治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亚历山大时代,制定决策的地方根本遥远得大多数人听都没听过。从此以后,人必须从帝国政治讨生活,走政治之路者必须离开生长于斯的城市,前往远在外地的首府。政治再也不是一个近在眼前的经验世界。”[1]102在这个意义上,伊壁鸠鲁所“偏离”的不仅仅是政治,还有古典时期的政治赖以存在的城邦共同体。又因为,伊壁鸠鲁快乐哲学最终诉诸自由,由此,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既是人的自然本性对共同体生活的偏离,又是自由的价值对共同体价值的偏离。但是,伊壁鸠鲁所忽略的是,城邦共同体作为古希腊时期的一种具体的共同体形态,由于历史原因,其本身存在着历史局限性,这就必然会影响到上述观点对于共同体价值本身的判断。无论是传统的古希腊哲学家们还是伊壁鸠鲁,都是从一种具体的共同体形态出发,进而上升到对共同体价值本身的认知。由于二者的历史性经验活动受到历史局限性的影响,因此,在此基础之上所作出的关于共同体的价值判断就难免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们还是城邦解体时期的伊壁鸠鲁,他们都没有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超越的视角来看待具体的“共同体”形态与抽象的“共同体”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城邦作为一种具体的共同体形态存在于希腊化时期,必然受到其时代的局限和历史的影响。而城邦的解体仅仅是一种形态的共同体的解体。随着历史的发展,另一种共同体形态逐渐形成——帝国。这显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价值也随着城邦形态的共同体的瓦解而瓦解,也不意味着共同体的价值在本质上与人追求自由的价值相割裂。因此,伊壁鸠鲁所认为的,共同体并不是内在于人的本性之中,并且自由与共同体是相互冲突的、矛盾的两种价值的观点,是基于以城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或以城邦为基础的共同体形态被破坏,而导致的关于共同体价值的理解失衡。
2.1 基本资料 患者82例,男59例,女23例,年龄18~96,平均(66.13±18.26)岁,均为汉族。其中一般脓毒症5例,严重脓毒症24例,脓毒症休克53例。平均住院时间(13.23±10.07)d。肺部感染50例,腹腔感染15例,癌症8例,糖尿病5例,外伤3例,中枢神经系统感染1例。54例死亡,28例存活。死亡组及存活组患者临床基本资料在性别、年龄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但死亡组APSCHEⅡ及SOFA均比存活组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首先,城邦共同体的瓦解使得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有理由开始怀疑共同体的价值。希腊化时期的“城邦”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组织,在政治哲学当中具有关键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尽管古希腊的哲学家们对城邦的某些制度不尽满意,但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城邦共同体作为依托,对城邦共同体本身的价值持一种肯定性的态度。对于城邦共同体作为一种政体的争论也仅仅是关于什么样的城邦政体是好的。因此可以说,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哲学是一种“城邦哲学”,亦即是一种关于城邦之善的哲学。换言之,如果将城邦视为一种具体形态的共同体,那么在希腊化时期的政治哲学当中,哲学家们则或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共同体的价值从城邦形态的共同体当中抽象出来加以讨论,其根本的立足点就是人的价值与共同体的价值是不可分的。这种将共同体价值视为人的本质价值的政治哲学是朴素的,是从稳定的城邦共同体生活当中抽象出来的。例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生活于城邦中的公民,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因此,人不仅求生活,而且求好的生活、善的生活,城邦生活就是向善的生活、自由的生活,是公民应该积极参与的生活。这就意味着,亚里士多德将人的政治的共同体生活视为一种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然而,随着马其顿帝国的入侵,这种情况出现了动摇。犬儒学派以极端化的形式表达了共同体观念的价值所产生的危机:“在被帝国改变了的社会、道德及政治环境下......城邦向来就无甚价值,其规则与价值观也向来虚假。”[1]102古希腊晚期,以城邦为基础的政治哲学失去解释力和吸引力,亟须一种非城邦的政治哲学取而代之。伊壁鸠鲁的政治哲学就是这样一种在城邦的废墟上建立的新型政治哲学。
二、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双重批判:积极的自由与共同体价值的统一
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的兴趣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马克思在1857年12月21日“致斐·拉萨尔”的信中坦言:“[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4]可以判断,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研究就是从政治哲学的视野切入的。而对伊壁鸠鲁的共同体理论的批判,也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后来马克思共同体理论的基础。在涉及到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张力关系时,马克思在两种层面上对伊壁鸠鲁做出了批判:
一方面,在马克思的积极自由观视域之下,伊壁鸠鲁关于众多原子偏离直线的观点固然体现着每个人自由的可贵精神,但是这种避世的消极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偏斜”式的消极自由既不是实现自由的有效途径,也不是实现自由的有效方法。在消极自由观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自由理论是有缺陷的,而积极的自由才是实现自由的有效途径。个人不是通过回避政治生活而自由,而是要成为政治共同体中的主体,从而获得自身自由的政治保证。马克思的观点在于,不能满足于经验的个体一味消极地回避不合理的现存政治统治,而要将个体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性观念,通过观念的积极外化,建立合乎普遍理性的政治制度,实现每个人的自由。与之相适应的,要实现真正的自由,就必须要回到现实的实践当中去逐步积极地完成。因此,马克思在讨论自由时,强调对现实政治的积极反抗,强调对现存政治秩序的革命以及建立“自由人联合体”。
其次,伊壁鸠鲁反对将城邦的“共同体”生活视为是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认为原子式的个人应当回归自然,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正如政治哲学家施特劳斯曾指出的:“古典时代的论敌们在一个最为根本之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承认自然与习俗之间的分别是具根本性的。”[2]尽管哲学家们对于“自然”和“习俗”的含义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在人应当超越习俗意见和人为假定,进而向往合乎自然本性的生活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那么将共同体理解为自然的还是习俗的,就关系到共同体的价值是否与人的本性的内在价值追求相一致。由于传统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将作为政治生活的共同体生活视为符合人的本性生活,因此,关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亦即关于共同体的生活是否属于人的“自然本性”的生活的解读,就直接影响了传统的古希腊政治哲学对共同体的价值认知。在这种影响之下,产生了两种不同的理论路径:一种是古希腊传统的政治哲学家,如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人,将共同体的价值视为人的自然本性所拥有的;另一种则将共同体之价值视为是习俗的,其代表人物就是伊壁鸠鲁。伊壁鸠鲁对城邦哲学所做出的批判在于,他认为人若想实现自由,就必须脱离作为“习俗”的“共同体”生活,回归其“自然”的本质生活。伊壁鸠鲁通过继承和发展自然哲学中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思想,提出原子偏离直线的运动,并将其用于解释人的生活。他采取区分自然本性和人为习俗的思维范式,认为政治共同体是习俗性的,是外在的必然性,而“偏离政治”、避开痛苦则是人的自然本性,是个人自由的表现。这一点,最终导致伊壁鸠鲁与传统的古希腊哲学产生了根本的分歧。在伊壁鸠鲁看来,原子是个人的原型和象征,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偏斜运动是为了论证个人行为的自由。而政治共同体则被认为是习俗性的,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按照伊壁鸠鲁的观点,如果个人热心于政治生活,那就是按照命运的必然性而生活,按照社会秩序安排的生活,是与自由的本性相背离的。伊壁鸠鲁看到了现实的政治生活对人性当中自由的限制,并且将现实的政治生活视作真正的共同体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生活。在伊壁鸠鲁看来,选择政治的生活就是选择一种必然性的生活;选择生活于社会秩序之下就是等同于与自由无缘。他指出:“必然性是一件坏事;但是生活在必然性的统治之下并不是一件必然的事。”[3]在这里,伊壁鸠鲁将社会秩序、政治生活、共同体生活不加区分地放置在一起,统统归结到实现“自由”的反面——“必然性”的生活之下。此外,伊壁鸠鲁还提到,现有的政治秩序束缚着个人,个人要摆脱这种不自由的状况,就要全力反抗命运。但是,与马克思对现存政治秩序的反抗不同,伊壁鸠鲁的这种反抗是消极的。伊壁鸠鲁式的反抗是劝诫人们去过淡泊名利、与世无争的生活,强调抛弃掉共同体精神的不完整的自由。
另一方面,马克思始终坚定地认为“共同体”的价值是人的本质价值,是与自由的价值相统一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只有超越对现存的具体形态的共同体的理解,才能把握住共同体的价值与自由价值的统一性。在这种自由与共同体价值的统一性理解之下,积极的自由就必须要回到真正的共同体当中去完成。其立足的逻辑起点在于,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有其合乎人的自然本性追求的基础,亦即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背后的共同体价值是合乎人的自然本性的,那么共同体的生活方式显然不是一种对人性的“必然性的统治”,而是相反的,是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东西。诚然,每一个时代具体的共同体形态各有不同,并且人类共同体的发展还并不完善,需要在历史当中不断推进,但是,对于自由和共同体在价值层面上的认知,决然不能依据某种受到现实条件限制性因素影响的具体的共同体形态,以及在该种共同体形态下表现出的不自由状态,来判定自由与共同体是必然对立的两种价值。
割台主传动轴缠绕杂草造成过桥输送爬链跳齿故障,建议考虑爬链结构设计、链条质量,改进过桥输送爬链箱体结构。
首先,伊壁鸠鲁关于自由与共同体之间的思考体现了某种契约论的倾向。如果说在伊壁鸠鲁那里持有一种否定外在统治秩序,肯定人与人相互协调的关系的观点,那么按照伊壁鸠鲁所说,只有当一个人与之发生关系的不再是他物,而是个人时,个人之间才能形成共同的意志,从而订立契约。可以看出,虽然伊壁鸠鲁否认政治、城邦的价值,抱有一种个人独立于共同体之外从而能够获得自由的倾向和态度,但是他最终走向了契约式的共同体理论。在这个过程中,最为明确的有价值的观点在于他认为人应当面向人而非物,这与马克思的思想十分接近。但是对于将自由与共同体相分离的态度,马克思是不认可的。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对精神的本质、对国家的看法”在于“他把契约看作基础”[5]34。因此伊壁鸠鲁并没有对人从内在本性当中是否需求一种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层面上以及在人的本性当中是否天然就具有了共同体精神的层面上来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伊壁鸠鲁关注个体自由的思想都对近代以来的政治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两种批判的视域之下,马克思重新审视了伊壁鸠鲁关于自由与共同体关系的判定:
其次,伊壁鸠鲁将时间从原子概念当中去除的做法忽略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变量,因此也导致他忽略了对特定历史时期下具体形态的共同体与作为内在于人的本性的共同体精神加以区分。对过往的城邦共同政治生活的否定以及对某种以契约形式建立的共同体的追求,这其中正表现出了伊壁鸠鲁矛盾的态度:既认为自由与共同体是对立的,又认为自由与共同体是结合起来实现的。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那样,他只是“把有益的原则看作目的”[5]34。因此,伊壁鸠鲁对自由的价值和共同体的价值本身是没有深刻讨论的。对于共同体形态与共同体价值之间的关系也是没有涉及的。而马克思则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出发,指出:“时间在现象世界中的地位,正如原子概念在本质世界中的地位一样,也就是说,时间是把一切确定的定在加以抽象、消灭并使之返回到自为存在之中。”[6]因此,马克思所持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使得马克思对具体历史时期下的共同体形态与存在于个体观念中的共同体精神区分开来。这就说明,作为现实的共同体,无论是希腊时期的城邦共同体,还是现代的民族国家共同体,都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产生改变,但是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当中的共同体精神将会与自由一样,指导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自由的价值追求与共同体精神的价值追求同属人的自然本性之追求。由此,现实的政治生活仅仅是现存历史条件下具体的共同体形态下的政治生活,而并不是共同体的真正的价值所在。共同体的价值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社会条件、生产力发展程度等因素隐含在共同体生活之中。现存的共同体生活所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仅仅是具体的共同体形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非“真正的”共同体生活,也无法完整地表现共同体的价值。伊壁鸠鲁将政治共同体视为习俗性的,是忽略了人的内在本质需求的表现,是把具体形态的政治共同体完全等同于共同体的内在价值的做法。人之所以要生活于共同体当中并不是因为习俗性的外在要求,而恰恰是对共同体价值的内在追求。马克思主义真正的共同体观念所要认清的,就是人对真正的自由之价值以及人对真正的共同体之价值的渴望与现实历史之下不具备条件的具体生活实践之间的矛盾;是自由与共同体并非是割裂对立而是相统一的价值理念。自由离不开共同体,脱离共同体的自由正如水(人的本质)中的氢(自由)脱离了氧(共同体)一样,会使得原本的水(人的本质)变得不再健全。因此,“真正的共同体”和“自由”王国是始终统一在一起的。
三、共同体与自由的张力
在政治哲学中,自由向来是重要的价值诉求,而将自由与自然本性视为一致的东西也是政治哲学所公认的。因此,伊壁鸠鲁运用原子偏斜说来说明个人和政治共同体的关系,也正是基于个人应当回归自然本性的生活,而非被迫过着必然性的习俗生活的这一重要观念,来论证个人摆脱共同体秩序的束缚而获得自由的。因为按照伊壁鸠鲁的理论逻辑,政治共同体的秩序是令人痛苦的习俗生活,那么,偏离政治共同体秩序的自由生活也就是摆脱痛苦的生活,即快乐的生活。因此,他的原子偏斜论与他的自由论、快乐论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是相异于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典政治学的。伊壁鸠鲁对“共同体”价值的完全抛弃,毫无疑问地是受到其对何者能够作为人的自然本性的认知的影响。在伊壁鸠鲁看来,个人的肉体欲望是出于自然本性的欲望,因而个人为满足这种欲望而追求自身利益就是善的、快乐的。人的必要的肉体欲望只需要一些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即可满足,因此,快乐是可以得到的。伊壁鸠鲁说道:“一切自然的,都是容易获得的;一切难以获得的,都是空虚无价值的(不自然的)。”[3]33因此,共同体的价值无论如何都不符合伊壁鸠鲁对自然本性的定义。
但是,这个逻辑仅仅是对古典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等人关于城邦之善的批判,却无法对马克思所提出的共同体思想做出反驳。因为,古典政治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与马克思意义上对“共同体”价值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对此,马克思已经给出过批判。因为在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人意义上的城邦生活与自由的统一性,是马克思眼中的“拟人化的哲学”。马克思认为古希腊哲学家们,如苏格拉底等人对城邦共同体生活和自由相统一的认知实际上是“哲人”的矛盾性认知,是统治阶级以外在的特定条件下的生活方式的规则为依托,脱离了人的本质性认知而获得的对自由的认识。他这样批判苏格拉底:“一方面,他本身来源于实体的东西,他存在的权利仅仅建立在他的国家权利、他的宗教权利之上,一句话,建立在一切实体条件之上,这些条件在他身上表现为他的本质。另一方面他本身包含着目的,这目的对该实体性来说就是法官。所以他自己的实体性在他自身中受到审判,因而,他的灭亡正因为他的诞生地是实体精神,而不是那种经受和克服一切矛盾、没有被迫承认任何自然条件本身的自由精神。”[5]68亚里士多德在这个意义上,在马克思看来,与苏格拉底并无不同。但是值得肯定的是,将共同体的生活作为一种切入人的本质需求的考察维度是必要的,共同体的价值与自由的价值是统一的,这个判断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在伊壁鸠鲁看来,人是非政治的原子式的个体,只是为了避免与他人在利益上的互相伤害,个人之间才订立契约,建立共同体。因此,在伊壁鸠鲁那里,共同体不是先在的,而是人们慎思的结果、利益权衡的结果。伊壁鸠鲁对人的规定使得政治哲学由原来的共同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政治哲学对后来的政治自由主义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这种由个人之间订立契约关系组建共同体的思想,也与后世契约论者们的契约观念存在联系。
此外,对共同体的具体形态与共同体的价值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是许多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所存在的普遍问题。对此,马克思则对共同体形态和共同体价值有区别性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之上,对共同体的价值与自由的价值在逻辑上进行统一性的论证和思考,最终形成了“真正的共同体”理论,明确了共同体价值内在于人的基本价值的认识。马克思意义上的真正的共同体是以人的本质为基础的。这里的“共同体”绝对不是指向齐美尔所指出的那种具有人身依附关系的旧有社会秩序,而是更加趋近于鲍曼所追求的与真正的自由共在的共同体。尽管以往的和现存的人类共同体形态存在许多对自由的限制性条件,其往往表现为现阶段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的自身发展的矛盾,但是,共同体本身所表现出的价值绝对不是与人的自由本质相冲突的,一切具体的共同体都会伴随着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的社会生活实践而改变。对于真正共同体的追求与人对自由的追求是本质上一致的,共同体与自由这二者都是向人的类本质的全面复归。以此观之,我们就能够更加容易地理解马克思是如何对“虚幻的共同体”进行批判的。因为,“虚幻的共同体”表现为人对物的依赖性,仅仅是作为人类共同体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历史阶段存在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7]33这是马克思对现阶段民族国家性的政治共同体形态的明确认知。马克思同时指出,人能够获得最终的解放和完全的自由就必须抛弃这种政治的状态,从而进入一种人类的共同体当中,在那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不存在种族和地缘的边界。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所提出来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53这里所说的自由就不是自由主义所强调的政治自由,而是彻底摆脱政治和市民社会双重奴役的真正的自由。那么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共同体实际上也就是最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共同体目标。
参考文献:
[1] 麦克里兰:西方政治思想史.[M].彭淮栋译.海南:海南出版社.2003.
[2] 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M].彭刚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3.
[3] 伊壁鸠鲁等:自然与快乐.[M].包利民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7.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2.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TheTensionbetweenCommunityandFreedom——Marx’sCriticismofEpicurus’PoliticalPhilosophy
YAN Kuo-mi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kai University,Tianjin,300350)
Abstract: The compatibility of the value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e value of freedom is a prerequisite for recognizing the Marx community. In Marx’s critique and inheritance of Epicurus’ philosophy, it is clear that Marx combed and explained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On the one hand, starting fro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arx regards “community” as a form of society that evolves continuousl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Marx regards “community” as a kind of internalization of value of human essential attributes, and on this basis, brings together the realization of freedom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uman commu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turning to the nature of human beings, it demonstrates the unity of the two, and then criticizes Epicurus’ negative freedom, to a certain extent, bridges the value fracture between freedom and community.
Keywords: Community; Freedom; Epicu; Epicurean Philosophy; Historical Materialism;Value
收稿日期:2018-08-1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21世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18BZX030)。
作者简介:晏扩明(1991-),男,辽宁省盘锦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图分类号:F4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2815(2019)01-0033-06
标签:共同体论文; 马克思论文; 自由论文; 价值论文; 政治论文; 哲学论文; 宗教论文; 哲学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 《科学经济社会》2019年第1期论文; 国家社科基金:21世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18BZX030)论文; 南开大学哲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