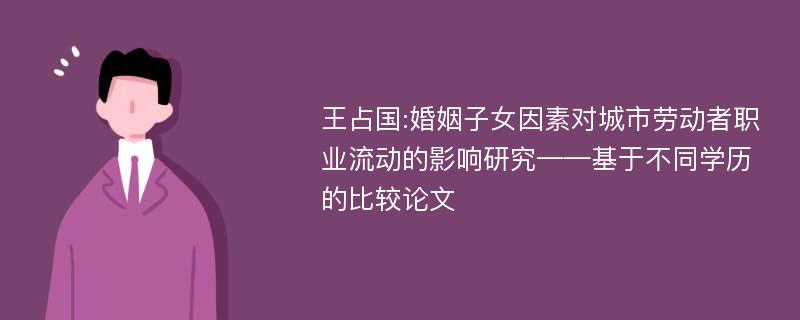
摘 要: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考克斯比例风险模型、泊松回归模型,探讨了婚姻子女因素对当前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及其学历差异。研究表明:婚姻子女变量对城市劳动者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且婚姻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对高学历劳动者的抑制作用相对更大。据此可以认为,家庭整体利益在劳动者职业流动决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劳动力市场分割体制下低学历劳动者和高学历劳动者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职业流动决策模式。
关键词:职业流动;婚姻子女因素;学历差异
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我国改变了过去完全用行政手段和再分配机制进行劳动力配置的局面,人们有了更多自主择业、自由发展的机会,职业流动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频繁。劳动者的职业流动不仅影响个体职业地位获得,还会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迁,因此,职业流动成为目前多学科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围绕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研究,学者们基于不同的学科视角和研究范式建立了多种解释模型。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运用大规模的调查数据深入考察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在具体分析中,本研究不仅关注个人因素和结构因素,还重点关注中观层面的婚姻子女因素,并运用“动态方法”探究职业流动这一“社会事实”所表现出来的动态特征。
包括无效、有效、显效,无效:早搏减少低于50%;有效:早搏减少50%~90%;显效:早搏小时或减少超过90%,总有效率=1-无效率。
一、文献回顾
关于职业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探讨,西方学术界主要存在四种研究视角:结构与制度视角、市场和理性视角、人力资本视角、社会网络视角。结构与制度视角认为,社会结构与制度决定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结构,进而影响职业流动。该视角在解释职业流动的原因时衍生出空位竞争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两种理论[1-2]。市场和理性视角认为,劳动者的职业流动是充分考虑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后的理性选择的结果,获取更高的经济报酬是职业流动的重要原因。工作搜寻理论和职业匹配理论均属于该视角范畴[3-4]。人力资本视角认为职业流动水平取决于劳动者人力资本的存量高低,但二者的关系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具有更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劳动者拥有更多职业流动的机会,向上晋升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面,通用人力资本(教育程度)较高者,初职职业地位较高,福利待遇、职业发展、工作环境都相对较好,就业稳定性反而更高[5]。社会网络视角认为,劳动者的社会关系网络可以弥补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缺陷,为合理配置劳动力提供方便。因此,社会网络有利于劳动者的职业流动[6]。
国内学者依据上述视角,结合具体国情,对当代中国社会职业流动的产生机制进行实证分析。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看,多数研究者认为教育对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7]。但对农民工而言,以技能水平为指标的人力资本因素对其职业流动的影响显著为正[8]。核心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对不同阶层农村家庭的职业流动性存在截然相反的影响作用[9]。从社会网络视角来看,随着转型经济的发展,以亲属和朋友关系为主的强关系仍然是职业流动者所使用的主要社会网络关系[10]。从关系使用者的角度来看,初职获得方式不同的劳动者在职业流动模式上存在显著差异[11]。此外,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多种形式的分割现象,而分割的成因多与制度因素有关,因此,国内研究者更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产业分割、学历分割等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有学者以劳动力市场的部门分割为背景,考察了我国城市劳动力从国有部门向非国有部门的跨体制职业流动现象,结果表明,教育程度、干部身份、党员身份、单位级别、单位类型等对劳动力跨体制职业流动有显著影响[12]。产业分割导致不同劳动者进入垄断产业的机会不同,进而影响其职业流动[13]。劳动力市场的学历分割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也得到了证实:高学历劳动者通常被划归于主要劳动力市场,与低学历劳动者相比,他们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低且换工作的次数更少[14]。
现有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搭建了理论框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深化研究:其一,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个人因素和结构因素,很少关注中观层面的家庭因素,即使有所涉及,也主要是考察父母亲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这实质上反映的是个人的先赋性因素,仍属个人范畴。本研究主要分析以婚姻子女变量为指标的家庭因素对劳动者代内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其二,现有研究在分析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时往往过于关注总体状况而忽视了研究对象内部的分层现象,因而无法了解相关因素对不同层次的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通过对不同学历劳动者的横向比较分析,详细考察各影响因素对不同特征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其三,本研究将借助大规模的社会调查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将职业流动过程中随时间变化的因素纳入分析之中,从而把结构变迁和个人特征结合起来。
二、研究假设
注:(1)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误差;(2)显著性水平:1)表示p < 0.1,2)表示p < 0.05, 3)表示p < 0.01,4)表示p < 0.001,表4同。
婚姻状况是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的重要因素。婚姻不仅是男女两性的简单结合,还意味着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经由婚姻组建家庭伊始,夫妻双方均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从家庭功能角度来看,满足家庭成员的情感需要是家庭最基本的功能之一。但是职业流动会加大夫妻双方分离的可能性,弱化家庭的情感功能。因此,劳动者在结婚以后会更倾向于选择稳定的工作。经济功能是家庭的另一种基本功能,家庭要能够满足成员的各种经济需求。已婚劳动者用于家庭照护的经济压力更大,有更稳定的经济收入。个体职业流动往往会在一定时间内打破家庭收入的稳定性,从养家糊口角度来说,相对较为稳定的工作对已婚劳动者更加有利[17]。子女因素是影响劳动者职业流动的另一因素。照料、抚育子女需要家庭有相对稳定的经济来源,有更充分的陪伴时间。而频繁的职业流动不仅使家庭的经济收入存在降低的可能,还可能导致父母陪伴子女的时间减少,因为他们在转换工作后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适应新的工作。因此,家庭子女照护需求可能会对劳动者职业流动产生抑制作用。子女数越多,家庭照护需求越大,对劳动者职业流动的抑制作用可能会越强。从生命周期角度来看,子女年龄与家庭照护需求密切相关。子女年龄越小,照护需求越大。因此在考察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时,不仅要考虑子女数的影响,还应该关注子女年龄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婚姻状况、子女数、年龄段子女数影响劳动者的职业流动。
H1a:与未婚者相比,已婚者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低,流动次数更少。
2.2.2 日常饮用水。村民们的日常饮用水主要有两种渠道供应:①饮用水质较好的公共井水。②安装净水机,将自来水净化后使用。同时也会买瓶装水在家里供饮用。
H1c:低年龄段子女数越多,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流动次数越少。
3.控制变量
H2:婚姻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存在学历差异,对高学历群体的影响更大。
青岛港:初步测算,青岛港约8.3%的美国航线箱量将受到影响。青岛港集装箱吞吐量中美国航线占比为21%,国际航线受影响程度约1.8%。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3)较强的创业实践精神。创新创业是一项实践性较强的活动,作为教学主体的一部分,教师自身的实践经历能为教学活动提供更好的素材,提升教学效果。现有师资中8人有不同程度的国内外企业工作经历,3人有创业经历;其他教师也通过指导学生参加不同类型的创业活动提高创业实践,过去3年所有的教师均指导过学生参加“互联网+”创业大赛,获得校赛、区赛多个奖项;指导立项国家级、区级大创项目6项;指导GMC、ERP、创业之星等创业模拟竞赛获得区级、国家级奖项。这些都不同程的提升了教师的创业实践能力。
化学气相沉积法具有工艺流程短、产品纯度高、经济性好等优点,因此是MoS2纳米微球的制备的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曾一等[5]以硫粉与三氧化钼粉为原料,以高纯氩气为载气,用化学气相沉积法在900 ℃下保温8 h,制备出平均粒径在250 nm左右的高纯富勒烯结构MoS2纳米粒子。Hua[6]等通过快速化学气相沉淀法制备出了MoS2纳米微球,并将其添加在聚甲醛基复合层中,制备出了减磨性能优异的耐磨复合材料。虽然化学气相沉积法具有一系列优点,但该方法在制备过程中容易产生硫化氢,因此需要对尾气进行处理以防止对环境的污染,且在制备过程中当气相流量或者压力改变时,产品的形貌难以保证。
(二)变量选择
1.因变量
职业流动,是指劳动者就业期间在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变换。本研究以“初职流动风险率”作为职业流动的一个测量指标,该指标以初职的开始时间为起点,结束时间为终点,计算初职的持续时间。直到调查的截止时间仍没有发生过职业流动的样本为删失样本。这一指标既包含了劳动者是否流动的信息,又包含了流动的确切时间信息。“职业流动次数”是职业流动的另一测量指标,是指访谈对象从初职获得开始直至数据收集时点的这一时期内,发生职业流动次数的总和。
2.自变量
婚姻状况。在数据收集中,CGSS2008明确询问了访谈对象的初婚时间。分析时用初婚时间与初职持续期每个时点(年)做比较来确认调查对象在该时点上是已婚还是未婚。该变量为时变变量,分析时以未婚为参照组。颇为遗憾的是,调查并没有详细询问婚姻变动(离婚、丧偶等)时的确切时间,因此本研究无法对婚姻变动后的状况进行考查。因此本研究中的已婚是指已经有过婚姻的经历,那些初婚后离婚、丧偶的调查对象亦归属于此类。
子女数。指的是家庭在特定时点上所生育子女的数量。已婚无子女家庭记为0。在统计模型中,该变量为连续型变量。
年龄段子女数。首先对子女年龄分组,然后计算每个年龄段的子女总数。考虑到子女成长周期与家庭照护需求的关系,把该指标划分为四个变量:0~3岁组子女数、4~6岁组子女数、7~12岁组子女数、12岁以上组子女数。它们均为连续型变量。
H1b:子女数越多,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越低,流动次数越少。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单一的竞争市场,而是由几个非竞争的市场组成。中国学者往往把单位所有制、户籍、行业等因素看作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维度。吴愈晓[14]从高考制度出发,认为因高等教育造成的群体分化是中国社会另一种形式的分割现象。据此,可以按照是否接受高等教育的标准将劳动者群体划分为低学历群体和高学历群体两个部分,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婚姻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在这两个群体中可能存在差异。高学历群体的工资报酬较高,职业稳定性较强,家庭照护所需要的经济条件和时间因素等都能够从当前职业中得到较好的保障。一旦发生职业流动,劳动者就会在一定程度上丧失这些保障,承担更大的流动成本。因此,婚姻子女因素对其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更明显。低学历群体从属于次要劳动力市场,其工作环境较差,劳资关系不稳定,往往需要通过职业流动谋求更好的职业地位。即使结婚生子以后,他们仍然会频繁发生职业流动。基于此,提出如下假设。
1.2.4 适当加大棚间距:由于后墙厚度加大,所以适当加大前后棚之间的距离,以免出现前栋温室影响后栋温室的采光。要求每栋棚占地宽度达到18~20米。
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以女性为参照组;户口类型,指初职期间户口是农业户口还是非农户口,以农业户口为参照组;年龄,指离开初职时的年龄,为连续型变量。
K-M生存函数曲线能够更形象地展示事件的发生趋势。依据是否结婚,分类描述了不同样本的K-M生存函数曲线(见图1)。无论是未婚样本还是已婚样本,随着时间的推移,访问对象中尚未发生职业流动的人员比例都呈现急速下降趋势。相比较而言,已婚样本生存曲线的位置明显高于未婚样本,表明已婚劳动者在相应风险时间上尚未发生职业流动的人员比例较高。或者换句话说,婚姻对劳动者的初职流动存在抑制作用。
教育年限。以文化程度来计算教育年限:从未受过任何教育=0年,私塾=2年,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职高、中专、技校=13年,大学专科(成人高等教育)=14年,大学专科(正规高等教育)=15年,大学本科(成人高等教育)=15年,大学本科(正规高等教育)=16年,研究生及以上=19年。
初职单位变量。单位性质分为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两类,前者包括国有或国有控股以及集体或集体控股单位,后者包括私有、港澳台资、合资、外资等单位,以非国有单位为参照组。单位人员规模,是初职所在单位的人员总数,分析时先对其取自然对数。单位住房类型。租住集体宿舍、租住单位单元房、购置单位房合并为“租/购单位房”,廉租公房、租住私人房、购置商品房、自建住房合并为“非租/购单位房”,以“非租/购单位房”为参照组。单位所在地区。按照国家行政区域级别从低到高分为农村、城镇/县城、地级市、省会市或直辖市,以省会市或直辖市为参照组。
对于O3前体物NO2,其日变化随呈现早晚双峰分布。受假期的影响,早高峰时间也推迟到100,此时NO2出现峰值。随后由于太阳辐射增强,臭氧前体物在光化学反应作用下不断被消耗,并在100达到最低点。此后,NO2浓度又逐渐回升,并在夜间凌晨出现第二高值点,这与晚高峰和夜间边界层高度较低、大气扩散条件差有关。1月20日~1月26日相比,NOx高值点均出现000及100左右。(见图7)
普京总统指出,创造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者将成为“世界的主宰”,他认为俄罗斯的计算机领域属强项,人工智能理应发展迅猛,这是改变俄罗斯命运的有效抓手。当前,俄罗斯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入仅7亿卢布(约合1 250万美元)左右,与美国和中国的数十亿美元相比微不足道;到2020年预计也才280亿卢布(约合5亿美元),这显然不够。普京要求政府站在国家利益的高度,在法律上保障对人工智能研发的管理和资金支持,尽快出台相关法律对人工智能与人的关系进行规范化管理,也要兼顾人工智能带来的失业新问题。
(三)模型构建
本研究首先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中的考克斯比例风险回归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以下简称Cox模型)对“初职流动风险率”进行估值分析,并且将时变变量纳入模型之中,以使模型估计更加完善。
hi(t)=h0(t)×exp (βixi1+β2xi2+…+βkxik)
(1)
式中:hi(t)为持续时间的风险率或风险(hazard rate or hazard),即第i名调查对象初职在职时间持续到t时刻的条件下,初职流动事件在区间[t,Δt]内发生的瞬时概率;h0(t)指当所有风险因素不存在时(即Xik=0)的基准风险率函数,由时间决定。exp(βixi1+β2xi2+…+βkxik)为风险得分,由协变量决定;βk是一组未知参数,表示相应的自变量xik对个体i风险率的影响效应,即模型的回归系数;X=(xi1,xi2,…,xik)指k个可能与生存时间有关的风险因素(解释变量)所构成的向量,即模型的协变量向量。
将式(1)转化为较为常用的对数形式:
ln [hi(t)/h0(t)]=βixi1+β2xi2+…+βkxik
(2)
协变量与回归系数的线性组合等于相对风险率函数的自然对数值。模型中的回归系数需用最大偏似然估计法进行估计。βk>0,表示相应解释变量是促进初职流动的因素,其系数值越大,初职持续时间越短,发生流动的可能性越大;βk<0,表示相应解释变量是抑制初职流动的因素,其系数值越大,初职持续时间越长,发生流动的可能性越小。
“职业流动次数”属于计数型变量。对于计数型变量,常用的统计估计模型是泊松回归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模型,二者如何选择主要取决于计数变量的分布是否过度离散。如果计数变量的方差大于均值则为过度离散,则负二项回归模型较为合适。如果计数变量的方差并不大于均值,则泊松回归模型是最合适的选择。从数据来看,职业流动次数的均值为1.43,方差为0.63,方差并不大于均值,因此我们选择泊松回归模型进行估计。
本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8年度调查数据(CGSS2008)。该调查采用四阶段PPS不等概率系统抽样方法,以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抽样框,在除港、澳、台、西藏、青海、海南以外的28个省(含市、自治区)抽取了一个6 000人的样本。数据样本包含了调查对象详细的工作经历(每一份工作的起止时间、工作单位信息),能够为研究提供充分的实证资料。
四、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统计结果
为了适用于事件史分析模型,首先将原始数据转换成事件导向的人年(person-year)数据。表1是转化后的人年数据的概要统计结果。从总样本来看,5 224名访问对象共计有39 602个人年生存期。如果假定每年的初职流动风险率都相同的话,那么平均每个人年的初职流动风险率为0.053 6。生存时间的四分位值可以直观地反映调查对象达到相应风险率所需要的生存时间。数据显示,在总样本中,前5年发生职业流动的平均概率为25%,前12年发生职业流动的平均概率为50%,前28年发生职业流动的平均概率为75%。对样本分类后发现,未婚样本的平均流动风险率比已婚样本高大约0.015 9,而从生存时间的四分位值来看,未婚样本到达风险率的各个分位值所需要的生存时间均低于已婚样本。说明在结婚之前更容易发生职业流动。
初职入职时期。按照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以前、早期、中期、深化期)把它划分为四个时期:1978年以前、1978—1992年、1993—2002年、2003—2008年。以1978年以前为参照组。
资源丰富但未得到开发。景点存在设施落后、管理水平低、人员职业素质低而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此外,对生态旅游理念宣传力度小、投入少技巧不高;从而对文化旅游资源缺乏深度挖掘,特色模糊未有大的效果。
表1 不同婚姻状况下初职生存时间数据结构的概要统计
婚姻状况风险时间/人年风险率样本数生存时间/年25%50%75%未婚134410.0641110041125已婚261610.0482312451328总体396020.0536522451228
图1不同婚姻状况的初职流动K-M生存函数估计图
为了进一步检验子女数对初职生存时间的影响,可以按照子女数不同输出生存数据统计概要(见表2)。无子女样本比一个子女样本和多个子女样本的初职流动风险率分别高约0.010 5和0.014 2。从初职生存时间的四分位值来看,前者到达风险率的各个分位值所需要的生存时间都比后两者要低。一个子女的样本与多个子女的样本相比,风险率略高,但差异性并不明显。总体而言,子女数对初职流动存在抑制作用,子女数越多,初职流动的可能性越小。
表2 不同子女数量下初职生存时间数据结构的概要统计
子女数量风险时间/人年风险率样本数生存时间/年25%50%75%无子女201550.0604326051226一个子女175800.0499191861631多个子女103660.046265661832
图2更形象地展示了不同子女数样本初职流动的发生趋势。三条生存曲线的高低位置基本按照子女数的顺序排列,无子女样本对应的曲线位置最低,多子女样本对应的曲线位置最高。这说明子女数越多,初职流动的可能性越小。
图2子女数与初职流动K-M生存函数估计图
(二)初职流动风险率的影响因素
表3列举了Cox比例风险模型的分析结果。模型1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导入了婚姻变量。婚姻变量统计显著,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已婚职工比未婚职工离开初职的风险率大约低20.07%(1-e-0.224)。统计结果表明,婚姻可以有效延长初职持续时间,已婚者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更小。假设H1a得以验证。
针对已婚样本,进一步检验子女因素的影响效应。加入子女数变量,构建模型2。由于子女数变量与职业流动的关系不一定是线性关系,因此模型中又加入了子女数变量的平方项。两个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说明子女数与初职流动风险率之间确实存在非线性关系。调查对象离开初职的风险,随子女数的增加呈现U型变化趋势。进一步测算可知,当子女数为2.94时,U型曲线下降到最低点。由于样本中绝大多数调查对象的子女数小于3,故总体而言,初职流动风险率随着子女数的增加而降低,假设H1b得以证实。平方项的存在说明,下降的速度不是线性的,而是随着子女数的增加下降的幅度逐渐减小,即:子女数对初职稳定性的影响呈边际效应递减趋势。
表3 估计离开初职风险率的Cox风险比例模型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控制变量-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自变量已婚-0.2243)(0.073)-0.1722)(0.080)子女数-0.1602)(0.070)-0.1612)(0.069)子女数平方0.0322)(0.013)0.0282)(0.013)0~3岁组子女数-0.1562)(0.076)4~6岁组子女数-0.1802)(0.090)7~12岁组子女数-0.012(0.067)12岁以上组子女数0.018(0.054)交互项高学历-0.1571)(0.090)-0.5244)(0.110)已婚×高学历-0.2261)(0.123)子女数×高学历-0.2043)(0.065)模型参数对数似然值-14158.62-8576.14-8573.98-14164.56-8575.58似然比卡方793.274)382.534)386.864)781.404)383.674)自由度1415171516样本量29992086208629992086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主体,个人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的原则进行迁移决策[15-16]。依照该理论逻辑,在劳动者职业流动决策过程中影响个体行动选择的因素不仅包括个人利益,还包括家庭整体利益。对于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来说,家庭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在个体职业流动决策过程中,家庭因素的作用会更明显。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主要强调经济收益的影响,且研究主题是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对于职业流动研究来说,其理论逻辑可以借鉴,但在分析过程中,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之外,还应关注家庭照护等方面的影响。
加入4个年龄组子女数变量,构建模型3。统计结果发现,0~3岁年龄组子女数、4~6岁年龄组子女数使初职流动风险率显著降低, 7~12岁年龄组子女数、12岁以上年龄组子女数对初职流动风险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个结论表明,低年龄段子女数越多,职业流动的可能性越小。但随着子女年龄的增大,达到进入学校教育的年龄以后,子女数的影响效应就会消失。假设H1c得以验证。至此,假设H1全部得到了验证。
为了检验婚姻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将初职入职时的教育程度转化为学历变量,并将取值合并为两类:高中及以下教育程度为低学历,高中以上教育程度为高学历。在模型中分别加入学历与婚姻、学历与子女数的交互项,构建模型4、模型5。模型4统计结果显示,学历与婚姻的交互项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对于不同学历层次的劳动者而言,婚姻变量的职业流动效应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低学历劳动者而言,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已婚职工比未婚职工离开初职的风险率大约低15.80%(1-e-0.224);对于高学历劳动者而言,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已婚职工比未婚职工离开初职的风险率大约低32.83%(1-e-0.224-0.226)。这个结论表明,相较于低学历群体,高学历群体婚姻变量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大。模型5统计结果显示,子女数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同样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相较于低学历群体,高学历群体子女数变量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大。据此,假设H2得到验证。
(三)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因素
泊松回归模型中婚姻子女变量的取值与Cox模型稍有不同。婚姻状况取调查时点的观察值。子女数指调查时点的子女数总和。考虑到对职业流动次数的观察期比较长,子女的年龄跨度会比较大,在泊松模型中年龄分组指标变为未成年子女数(18周岁以下)变量。其余的自变量与Cox模型完全一致。统计结果见表4。
表4 估计职业流动次数的泊松回归模型
变量类型变量名称模型6模型7模型8模型9模型10控制变量-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已控制自变量已婚-0.2914)(0.047)-0.2304)(0.051)子女数-0.1052)(0.052)0.070(0.052)子女数平方0.013(0.010)-0.010(0.010)未成年子女数-0.1152)(0.051)交互项高学历-0.038(0.074)-0.3944)(0.075)已婚×高学历-0.2593)(0.093)子女数×高学历-0.1814)(0.046)模型参数常数项1.7374)(0.107)1.5694)(0.131)1.5254)(0.132)1.4794)(0.094)1.3914)(0.113)对数似然值-3256.43-3253.88-3251.35-3252.07-3245.34似然比卡方890.134)895.224)900.284)898.854)912.314)伪决定系数0.12020.12090.12160.12140.1232样本量29961348138612561398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婚姻变量可得模型6。统计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对职业流动次数有显著影响。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与非在婚职工相比,在婚职工职业流动次数大约少25.24%(1-e-0.291)。在模型7中,子女数变量统计显著,但其平方项并不显著,这表明子女数与职业流动次数之间不存在U型关系。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子女数每增加1,职业流动次数减小约9.97%(1-e-0.105)。在模型8中,未成年子女数变量统计显著。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未成年子女数每增加1,职业流动次数减小约10.86%(1-e-0.115)。据此,从职业流动次数角度,假设H1也得到验证。
核电作为高科技能源产业,我们始终把注意力集中在安全性和先进性上,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电力市场产品,经济性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在电力市场竞争中,经济性是评判任何发电技术竞争力最重要的指标,电力市场化已导致核电“一厂一价”上网电价机制退出历史舞台,我国核电建设成本过高,导致上网电价在国内电力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核电的经济性成为制约我国核电快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
同理,在模型中加入了学历与婚姻、学历与子女数的交互项,统计结果见模型9、模型10。模型9统计结果显示,婚姻变量对职业流动次数的影响效应存在学历差异,其对高学历层次的劳动者职业流动次数的抑制效应更大。模型10统计结果也表明,子女数变量对高学历群体职业流动次数的抑制效应相对更大。因此,从职业流动次数角度,假设H2也得到验证。
五、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婚姻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首先,结婚可以降低发生初职流动的可能性,在婚劳动者职业流动的次数相对更少;其次,子女数越多,劳动者越倾向于职业稳定;再次,低年龄子女数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较大。可以尝试运用新迁移经济学理论来解释这一研究结论。传统人口迁移理论认为,迁移行动是理性人为达到经济利益最大化而进行主体选择的结果,而新迁移经济学理论认为,家庭是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主体,个人往往根据家庭预期收入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进行迁移决策。依据该理论,劳动者在职业流动决策过程中不是只考虑个人效用的最大化,还会从维护家庭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个体行动选择。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在解释职业流动现象时,选择该理论逻辑或许更加符合社会事实。
但与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主要强调经济利益不同的是,劳动者在职业流动过程中所考虑的家庭整体利益还应包括家庭照护需求。对于已婚、有子女且子女年龄较小的劳动者而言,家庭照护责任较大。这不仅影响个人对工作的投入程度,而且还会影响其职业流动。职业流动对家庭生活的冲击主要表现为生活的稳定性被打破,而稳定性恰恰是满足家庭照护需求的基本条件之一。因此,对于上述劳动者而言,家庭照护需求会抑制其发生职业流动的可能性。
婚姻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的学历差异,对高学历劳动者的抑制作用相对更大。这主要与高等教育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作用有关。不同学历劳动者处于不同性质的劳动力市场之中,由此决定了他们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职业流动模式。高学历劳动者更易于进入首要劳动力市场,其工资收入、劳动保障、工作时间等较为优越,能够较好地满足生存需要,追求更好的发展往往是他们发生职业流动的主要目的。这是一种发展取向的职业流动。低学历劳动者大多只能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劳资关系极不稳定,往往需要通过职业流动谋求更好的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其职业流动是一种生存取向的职业流动。为了满足家庭照护需求,劳动者需要拥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和较为充分的陪伴时间。在职业流动决策过程中,他们会首先考虑生存问题而非发展问题。对于高学历劳动者而言,现有职业可以很好地解决生存问题,职业流动的机会成本相对较大。因此,在结婚生子以后,出于对家庭照护需求的考虑,他们会逐渐倾向于维持现有职业,尽量避免发生职业流动。对于低学历劳动者来说,职业流动本身就是维持生存的主要策略,即使在结婚生子以后他们仍然需要通过频繁的职业流动来谋求更好的生存机会,婚姻子女因素对其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并不明显。从发展趋势来看,随着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职业流动的主体开始从生存取向朝发展取向转变,所谓“孔雀东南飞”现象逐渐增多。这种变化会使婚姻子女因素的抑制效应发生改变,其中的变化机制需要更多的实证资料予以验证。
部分施工单位不能充分认识竣工结算审计的重要作用。他们往往持相反的看法,对完成结算审计态度消极,从而使得审计工作不能正常开展。事实上,竣工结算审计能够促进工程管理、提高工程质量和水平。此外,目前结算审计仍是项目审计的一种重要形式,错误纠正、事后监督、提出整改意见,都仅仅是事后补救,时效性很差。这就容易给人造成错觉,认为审计工作是在寻找错误和证据,很容易使被审计单位造成紧张气氛,使得整个项目的审计环境不佳,严重影响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虽然全过程审计正在充分实施,但由于时间短、缺乏有效沟通,而实际结果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效。
玉米品种试验中宜机收指标的探讨……………………………………………………………………… 冯 勇,宋国栋,侯旭光(21)
此外,生育率的下降是中国社会变迁的不争事实,其对职业流动的影响不容小觑。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推行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发生了根本改变,高学历劳动者生育率下降更为明显。对于家庭而言,生育率的下降使子女数减少,拥有低龄子女的时间缩短,子女因素对职业流动的抑制效应将会降低。因此可以预见,随着人们生育意愿的转变,中国的职业流动水平还会持续升高。
本研究主要从是否发生职业流动和职业流动次数两个方面考察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虽然,研究尽量全面考察调查对象不同特征和维度,但由于数据所限,无法对职业流动状况进行更加深入、精细的划分(譬如:关于强制性流动与自愿性流动的区分、体制内外不同流向的区分等),从而无法更为明确地验证某些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 SORENSEN A B. The structure of inequality and the process of attainmen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7,42(6):965-978.
[2] DOERINGER P B, MICHAEL J P. Internal labor market and manpower analysis[M]. Lexington: Health lexington books,1971:34-39.
[3] BURDETT K A. Theory of employee job search and quit r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1):212-221.
[4] JOVANOVIC B. Job matching and the theory of turnover[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79,87(5):972-990.
[5] BLINDER A.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73,8(4):436-455.
[6]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3,78(6):1360-1380.
[7] 翁秋怡,蒋承.教育能够促进工作转换吗——基于CHNS数据的实证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3(5):31-36.
[8] 柳建平,魏雷,李孜孜.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流动:甘肃样本[J].重庆社会科学,2016(5):34-39.
[9] 张锦华,沈亚芳.家庭人力资本对农村家庭职业流动的影响——对苏中典型农村社区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12(4):26-35.
[10] 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
[11] 吴愈晓.社会关系、初职获得方式与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2011(5):128-152.
[12] 郑路.改革的阶段性效应与跨体制职业流动[J].社会学研究,1999(6):37-53.
[13] 张展新.劳动力市场的产业分割与劳动人口流动[J].中国人口科学,2004(2):45-52.
[14] 吴愈晓.劳动力市场分割、职业流动与城市劳动者经济地位获得的二元路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11(1):119-137.
[15] 洪小良.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07(6):42-50.
[16] 殷俊,刘一伟.工作转换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J].城市问题,2017(4):70-76.
[17] 风笑天,王晓焘.城市在职青年的工作转换:现状、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J].社会科学,2013(1):81-91.
OntheInfluenceofMarriageandChildrenFactorsonUrbanLaborers’JobMobility—AComparisonamongDifferentEducationalBackgrounds
Wang Zhanguo
Abstract:Based on the survey data from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 using Cox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and 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i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marriage and children factors on current urban laborers’ job mobility and the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marriage and children variables hav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s on job mobility. In addition, there are obvious educational differences when marriage and children factors affect job mobility, and the inhibitory effect on laborers with high-level education is relatively great.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overall benefit of the famil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of laborers’ job mobility. In the system of labore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re are two distinct types of career mobility decision-making modes for laborers with low-level education and laborers with high-level education.
Keywords:job mobility; marriage and children factors; educational difference
作者简介:王占国,社会学博士,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江苏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职业稳定性研究”(17SHB005);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江苏省民办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流动研究”(2017SJB1775)。
中图分类号:C913.2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2095-042X.2019.05.007
(收稿日期:2019-07-29;
责任编辑:沈秀)
标签:职业论文; 子女论文; 劳动者论文; 变量论文; 模型论文; 社会科学总论论文; 社会学论文; 社会生活与社会问题论文;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论文;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 "; 江苏专业社会工作人才职业稳定性研究"; (17SHB005)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 江苏省民办机构社会工作者的职业流动研究"; (2017SJB1775)论文; 常州大学瞿秋白政府管理学院论文;
